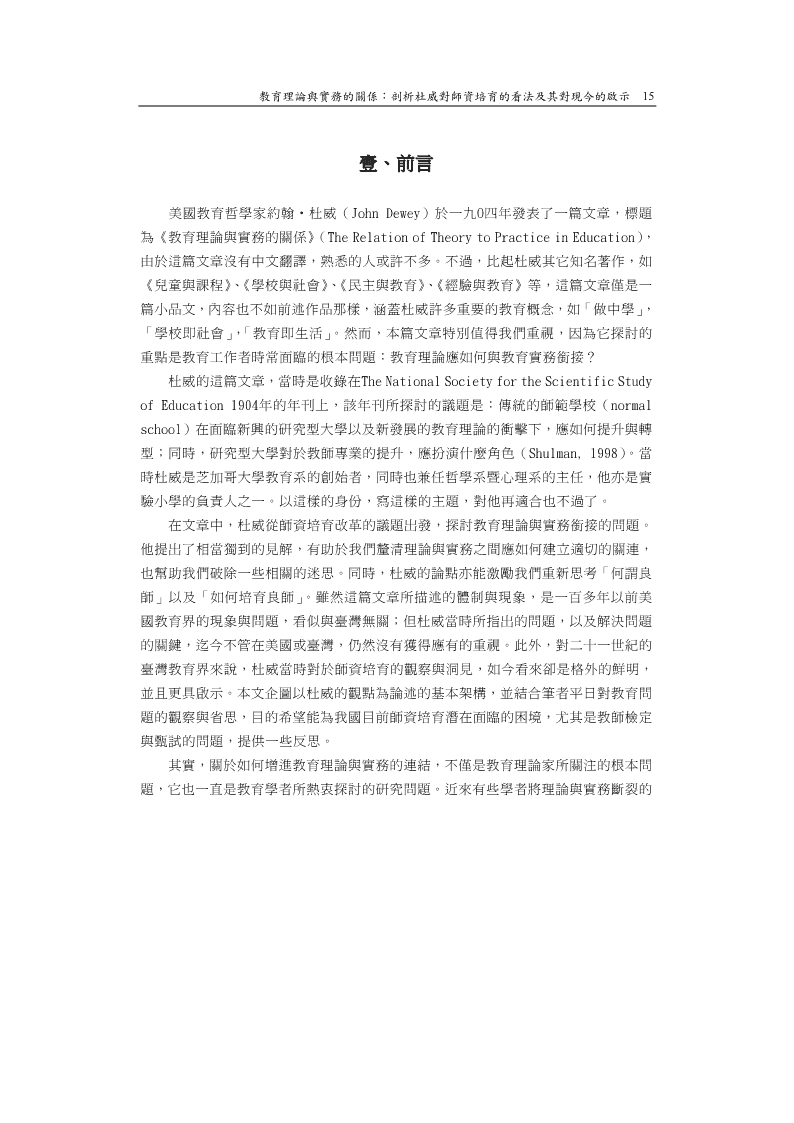- 1.17 MB
- 2022-08-15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13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2008年十二月頁13-34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1王清思中文摘要本研究以杜威(1904)的文章《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為立論基礎,探討教育理論應如何與教育實務銜接的問題。此文中,杜威從師資培育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學徒制」與「實驗制」兩種不同的師培方式,並說明為何「實驗制」優於「學徒制」。文中,杜威提醒我們,師培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培養能獨立思考與探究問題的教師。杜威的見解相當獨到,有助於我們釐清理論與實務之間應如何建立適切的關連,也幫助我們破除一些相關的迷思。同時,杜威的論點亦能激勵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良師」以及「如何培育良師」。本文企圖以杜威的觀點作為論述的基本架構,並結合最新的實證研究結果,以及筆者平日對教育問題的觀察與省思,希望能為目前師資培育所面臨的理論與實務問題提供一些反思。中文關鍵詞:杜威、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1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n14JournalofElementaryEducationDecember,2008,Vol31pp.13-34TheGapbetweenTheoryandPracticeinEducation:ExploringDewey’sViewsofTeacherEducationandTheirImplicationsforTodayChing-szeWang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JohnDewey’s1904essay,“TheRelationofTheorytoPracticeinEducation”andaddressesthequestionofhowtointegratetheoryandpracticeineducation.Inthisarticle,Deweyapproachedthequestionbylookingatthetwomodelsofteachereducationinhistime:theapprenticeshipandthelaboratorymodel.Preferringthelaboratorymodel,Deweyclaimedthatthemostchallengingtaskforteachereducationistocultivateindependentthinkingandaspiritofinquiryinfutureteachers.Dewey’sinsightsintoteachereducationcanhelpusreconsiderwhatitmeanstobeagoodteacherandhowtoeducatefutureteachers.Overall,thispaperemploysDewey’sviewsasatheoreticalpointofdeparture,combiningwithmyownobservationsandreflections,inordertoshedsomelightsonthecurrentproblemsofteachereducationinTaiwan.KeyWords:Dewey,teachereducation,theoryandpractice\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15壹、前言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於一九O四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TheRelationofTheorytoPracticeinEducation),由於這篇文章沒有中文翻譯,熟悉的人或許不多。不過,比起杜威其它知名著作,如《兒童與課程》、《學校與社會》、《民主與教育》、《經驗與教育》等,這篇文章僅是一篇小品文,內容也不如前述作品那樣,涵蓋杜威許多重要的教育概念,如「做中學」,「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然而,本篇文章特別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探討的重點是教育工作者時常面臨的根本問題:教育理論應如何與教育實務銜接?杜威的這篇文章,當時是收錄在TheNationalSocietyfortheScientificStudyofEducation1904年的年刊上,該年刊所探討的議題是:傳統的師範學校(normalschool)在面臨新興的研究型大學以及新發展的教育理論的衝擊下,應如何提升與轉型;同時,研究型大學對於教師專業的提升,應扮演什麼角色(Shulman,1998)。當時杜威是芝加哥大學教育系的創始者,同時也兼任哲學系暨心理系的主任,他亦是實驗小學的負責人之一。以這樣的身份,寫這樣的主題,對他再適合也不過了。在文章中,杜威從師資培育改革的議題出發,探討教育理論與實務銜接的問題。他提出了相當獨到的見解,有助於我們釐清理論與實務之間應如何建立適切的關連,也幫助我們破除一些相關的迷思。同時,杜威的論點亦能激勵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良師」以及「如何培育良師」。雖然這篇文章所描述的體制與現象,是一百多年以前美國教育界的現象與問題,看似與臺灣無關;但杜威當時所指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關鍵,迄今不管在美國或臺灣,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此外,對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教育界來說,杜威當時對於師資培育的觀察與洞見,如今看來卻是格外的鮮明,並且更具啟示。本文企圖以杜威的觀點為論述的基本架構,並結合筆者平日對教育問題的觀察與省思,目的希望能為我國目前師資培育潛在面臨的困境,尤其是教師檢定與甄試的問題,提供一些反思。其實,關於如何增進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不僅是教育理論家所關注的根本問題,它也一直是教育學者所熱衷探討的研究問題。近來有些學者將理論與實務斷裂的\n16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原因歸咎於師培訓練沒有在「課程」(course)與「田野經驗」(fieldexperience)之間提供緊密的連結(Feiman-Nemser,2001);有些學者則認為師培訓練沒有提供足夠的機會讓學生進行反思(reflection)。另外有學者的研究則指出,問題在於許多實習生只關切如何快速地獲取實際具體的活動點子和想法,能讓他們在剛開始教學便可以安然過關(Rust,1994),而無暇考慮更深層、複雜的教學問題。然而,很多研究也同時發現,快速的獲得所謂的生存工具箱(survivalkits),通常僅是解決了技術面的問題,而非真正了解問題,並進行修正和檢討,這樣的作法最終只會帶來負面的效果(Korthagen&Vasalos,2005)。杜威在《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一文中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和上述實證研究的結論互相呼應,有些則是杜威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文企圖將杜威在這篇文章裡所表達的主要想法,做系統性的呈現與詮釋,輔以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作為對照,並配合筆者自身的經驗分享與觀察,希望透過這三方面資料與文獻的整合與分析,能加深我們對教育理論與實務問題的了解與省思。貳、師資培育的模式一、學徒制v.s.實驗制在《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此篇文章的一開頭,杜威將師資培育的方式簡略地分成兩大模式:「學徒制」(theapprenticeshipmodel)與「實驗制」(thelaboratorymodel)。學徒制是一般傳統的師範學校(normalschool)所熟悉的方式,它強調課堂教學與管理的技巧,目的是希望能迅速並有效地培養學生立即進入職場的能力;實驗制則是一般研究型大學努力的方向,它強調學生習得「學科知識的教育意涵」(theeducationalsignificanceofsubjectmatter)(Dewey,1904/1996,p.250),並且重視教育史,教育哲學,以及教育心理學等教育基礎相關科目的基礎訓練,目的是希望學生獲得足夠的學識、培養成熟的心智涵養,以面對教育現場各式各樣的挑戰。整體來說,學徒制的師培模式將教學視為可傳授的技巧或技能,師傅(有經驗的老師)怎麼教,徒弟(學生)就怎麼做;它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立即帶班的能力,例如能掌控班級秩序以進行課程講述。實驗制的師培模式,則認為教學無法直接傳授,教\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17學的藝術無法靠模仿而得,唯有仰賴學習者自己不斷探索與試驗,方能真正領會其中的堂奧。因此,實驗制注重開發學生未來成為優良教師的潛能,特別重視學生對教學原理、兒童心理、以及教育思潮等專業知識的吸收與融會貫通,希望他們能掌握學科內容與兒童生活之間的關連,並運用在教學上。透過這些科目的學習,培養未來的教師具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和實驗探究的精神。相較之下,杜威所推崇的師培模式顯然是實驗制。他認為上課秩序的管理固然重要,但若一味地把眼光放在控制學童的外顯行為,則容易忽略對學生內在心智世界的觀察與理解,反而因此錯失一些真正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契機。杜威認為,學童的專注力可以分內在和外在,當學生乖乖地靜坐在教室,眼睛盯著黑板和老師,顯示他有外在專注力,但並不確保他們真正有所學習;當學生能將專注力放在學科本身,他們才能真正有所學習(Dewey,1904/1996,p.254)。杜威更進一步分析,學徒制模式下所培育出的老師,在教學生涯的一開始,可能會比較順利和佔優勢,因為他們能掌控學生的外在專注力,使學生上課安靜;但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老師日後的學習與成長卻相當有限,儘管他們很有心地參加各類的研習營,學習最新的教學技巧,亦是枉然,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引發學生內在的專注力與學習興趣(Dewey,1904/1977,p.256)。二、學徒制的侷限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學徒制模式下所培育出來的老師,對教學的認知與看待學生的眼光,一開始就被窄化了、侷限了。即使他們很會教書、很會管秩序,也能使學生獲得好成績,但他們不懂如何讓學生樂於學習本身──而非好成績所伴隨而來的獎賞。這樣的老師其實不了解何謂真正的學習、不知道如何啟發學生對該學科產生興趣、不懂得如何引發學生主動求知,也無法引導學生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簡言之,學徒制模式下所培育出來的老師,對教與學的認知受到傳統僵化教育與舊有思維的影響,因此缺乏敏銳的洞悉與反思,無法在教育活動的根本層面上不斷的發現問題、探究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即使累積了許多年的教學經驗,他們終究無法有所真正的學習與成長,亦無法提升個人的教學智慧。舉例來說,學徒制模式下所培育出的老師,因為一向習於考量學生的外顯行為,\n18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並且只關注學生的行為是否合乎既有的規範,所以不會去探究學生行為背後的內在動機與個別原因。於是,在他們眼裡,上課不專心、作業遲交、成績低落的學生,就是不乖、偷懶或不用功的學生。他們相信只要施以懲罰,就能糾正學生的不良行為,而不會去思考是否自己本身的教學方法,以及與學生互動應對的方式,是否需要調整,以適應學生不同的背景與需求。相反地,實驗制模式下所培育出的老師,絕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刻板印象,也不願意將任何人的行為做如此簡單的化約,他們會去探究不同學生不良行為背後的個別原因,針對不同的原因,分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當他真正去探究原因之後,才能對症下藥,而不致於錯過教育的良機。由於他們習慣探究與實驗的精神,他們的教學智慧隨著教學活動與日俱增。三、實驗制教師圖像之勾勒實驗制模式所培育出的老師,是能獨立思考且具有反思能力的老師,他們會隨時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對學生的影響,而時時準備好修正自己的行為。例如,上課時被點名上臺的學生,無法立即解題時,一般老師會很快地直接點下一位,那麼這位學生很可能所得到的訊息即是:「只要遇到我不會的題目,我不用嘗試,嘗試了也不會有用,不如直接等別人給答案」。這樣的互動模式很可能因而造成學生學習上的被動,或甚至自我放棄。觀察敏銳與細心的老師,會盡量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思考,並且輔以正向的鼓勵,他們希望傳達給學生的觀念是:只要你再多想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不要輕易放棄。這樣一來,讓學生不僅學到知識的內容,也同時學習到正確的態度。除了具有獨立思考和反思能力之外,實驗制模式所培育出的老師,應對課程的教育意涵有深刻的了解,並且能融會貫通。對他們而言,老師的責任絕非僅是把課本中的知識,照本宣科地灌輸給學生,而是應努力連結學校的課程與兒童的生活。他們不會武斷地假定兩者之間很難建立關連,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假設,無疑斷送了學生能真正學習的契機。讓筆者舉一些實例來說明上述的概念。在教導學生學習月的陰晴圓缺之變化時,能獨立思考與反思的老師,會反問自己(也會幫助學生思考):學習如何分辨上弦月與下弦月有何意義?過去的人類,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發明這樣的知識?這知識對我們現在的生活又有何影響和助益?學會了之後,我們是否可以光憑著對月亮形\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19狀的觀察,而得知現在是農曆的上旬還是下旬?甚至今天可能是農曆的幾號、離初一、十五還有多久?──而無須翻閱日曆。透過學校課程的學習,月亮對學生而言,便有了新的意義和啟發。或許當學生日後讀到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們會不禁探問:李白所仰望的明月是什麼樣的月?又如在教導分數時,老師們會幫助學生思考,如果人類不曾發明分數的數學概念,會有哪些後果?有哪些觀念或事物我們無法描述、無法認知(例如,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是海洋這個觀念?)我們還能了解地球表面,海洋與陸地的關係嗎?一個有探究心、有思考力的老師會鼓勵兒童將所學應用與日常生活之中,進而豐富原本可能單調又乏善可陳的生活,進而增加生活的視野和樂趣。試想,若兒童在學校裡學到如何分辨葉子的形狀與種類,那麼公園對他的意義,不僅是能去玩盪鞦韆的地方,還是可以去探索植物的地方;他的日常生活經驗,因為他的學習,而得到了更大的開展。此外,他可能發現公園裡許多樹木葉子的形狀,是學校課本裡沒有教過的,他若觀察出興趣來,可能會自己主動進一步的探究。總而言之,實驗制所培育的老師能掌握學科的教育意涵,引導學生進行深度的學習,並拓寬生活與知識的視野。四、實驗制教師的優質教學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一書中的第十一章,杜威談到了思考訓練之於教育的重要性,並分析了他心中理想的教學情境。根據他的想法,課堂教學可分成三類,最不可取的是把每一課當作一個獨立的完整體,不要求學生找出這一課與同一科目的其他單元的相關之處,或與別的科目是否有相通之處;另一種教學則是能避免這個缺點,會企圖連結學生的先備知識與新知識;但最優良的教學會使教材與生活產生互相關連,並且會使學生養成一定的學習態度和習慣,去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互關連與意義(Dewey,1916/1985,p.170)。杜威提醒說,如果老師們不懂得正確地引導學科知識的學習,則所造成之不良的後果有二。其一,學校習得來的知識無法用在豐富日常生活的經驗上。意思是說,日常生活得不到應有的充實與滋養(原本的生命經驗依舊單調、貧乏)。其二,在學校中養成慣有的學習方式(如將一知半解的知識強硬地囤積在大腦中,只為了應付考試),會漸漸地削弱兒童原有思考的活力與效力,使學生學得越多,腦筋變得越不靈\n20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活,思想變得越無法通達(Dewey,1916/1985,pp.169)。相信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最不願見到的事,因為這實在抹煞了教育的本質。為了恢復教育的本質,老師必須成為良好的示範。由於實驗制模式所培養出來的老師,能獨立思考與探究,並且能不斷地學習,因此杜威說他們會永遠自許為所謂「學科的學生」和「心智活動的學生」(studentsofsubjectmatter,studentsofmind-activity)(Dewey,1904/1977,p.256)。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杜威在這裡鼓勵老師成為「學科的學生」,並非要老師們當該學門知識的專家、研讀精深的理論,而是要老師從教育者的觀點,充實自己對該學科知識的了解與認知。意思是說,這樣的老師必須不斷地充實自己對學科知識內涵的瞭解,也同時必須不斷地細心觀察兒童心智活動的本質與特色,盡量給予空間讓兒童發揮他們的好奇心與創造力。關於這個論點,杜威在《兒童與課程》(TheChildandTheCurriculum)中闡述地較為清楚與具體。他說道,我們可以分別用「科學家」和「教師」的角度,看待學科學習的內涵,兩者之間雖然並不決然相斥,但確有重要的不同。科學家所關切的是如何運用該學科的知識,進而發現與創造新知識、定義新問題;相反地,以教師的立場面對該學科知識的學習時,關切的問題是如何呈現該學科知識發展中某個實際歷程與經驗,並且在學生的經驗中搭起連接的橋樑,讓學生對學科知識所產生的背景和脈絡,產生個人的體會和共鳴。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科的學習可以滿足兒童既有的好奇感與探究心,讓他們可以感受到探索知識的心理歷程和樂趣,亦即將學科「心理化」(topsychologizethesubject)。杜威認為,教師所關切的是如何「使學科成為經驗的一部份」,因此必須仔細觀察「兒童現有的能力和經驗因素中有哪些與學科有關連」(Dewey,1902/1977,pp.285-86)。教師對學科內涵的深切理解會幫助他詮釋兒童的經驗,以及特定學科知識在兒童整體成長經驗中的位置,幫助他在兩者之間搭起連結的橋樑。若教師本身對學科知識的瞭解是片段的、一知半解的,那則很難將學科與兒童的心智經驗作連結。另一方面,若教師對兒童的心智發展缺乏深刻的洞悉和瞭解,那則也無法將學科經驗與兒童經驗作連結。總而言之,優質教學的兩大重點在於:教師應注重課程與學生生活層面的融合,亦即課程對於學生個體生活與生命的意義性;教師應注重課程與學生心理層面的融合,亦即課程的學習方式滿足了兒童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慾望。因此杜威說,教師\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21必須永遠將自己視為所謂「學科的學生」(studentofsubjectmatter)和「心智活動的學生」(studentofmind-activity),才能不斷學習與成長,才能達成以上兩大目標。五、小結杜威以上所談到的優質教學,是學徒制的師培模式所無法培養出來的,因為它不重視理論與原則,假定教學不需要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認為教學只是一種勞力而非勞心的工作,這樣的想法當然很有問題。筆者認為,懶於探究與思考的人,不應該也不適合當老師。然而,在許多人的觀念裡,教書好像很容易,只要照本宣科,以及會訓誡學生即可。這樣的想法,包括《優秀是教出來的》暢銷書作者隆‧克拉克先生(2003/2004),都曾經在他的書中坦承過:「教書這麼無趣、缺乏挑戰和麻痺心智的行業,我壓根都沒想過」(頁13)。教了書之後,他才發現他原本的想法是一種偏見,教書的生涯其實充滿了冒險和刺激,隨時都有新的挑戰考驗著他的思考與應變能力,隨時都有問題等待他解決,只要他未曾忘卻「一個孩子都不放過」的初衷。以上杜威描繪的優良教師,是實驗制的師培模式所期望培養的,因為他認定教學活動的成功,必須仰賴高度的學識與智慧,因此他認為師資培育應重視教學行為背後的理論脈絡和原理原則,強調理論與實務緊密的連結,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獨立思考與探究精神的老師,使得教育理論能得到實務的驗證,教育實務才能得到理論的指導與滋養。參、師資培育的挑戰和杜威對教學實習的建議筆者常將這一句話銘記在心:很多人能教書,但很少人能啟發(Manycanteach,butfewcaninspire)。能啟發他人的人,必須有獨立思考、判斷、與探究的能力,才能將客觀的知識不斷地轉化為個人處事態度與智慧,才能活潑靈巧地將信念轉化為行動。在這篇文章中,杜威很明確地指出師資培育面臨最大的挑戰:如何培養老師們獨立思考的能力(Dewey,1904/1977,pp.256-57)。以往學徒制所培養出來的老師,\n22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沒有一套自己深刻思考與實踐之後所發展出的教學理念與原則,大多僅能靠著模仿別人的技巧或擷取別人的點子,勉強維持教學活動的基本運作;今天用的是一套,明天可能用的是另一套,如此隨波逐流,行事毫無準則,教學的品質令人堪憂。由於杜威所重視的是培養教師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在此文中特別建議師培學生在實習時,應採漸進的作法,不要一下子就直接進入課堂負責帶班和授課,而是先應以助理(assistant)的身分協助班級教師,並且仔細觀察師生互動的狀況。也就是說,教學實習一剛開始的重點在於觀察(Dewey,1904/1977,p.268)。之後,等實習生有了足夠的觀察經驗之後,再讓他們自行設計課程和親自試教。不過,觀察雖然很重要,但如何觀察、觀察什麼,卻足以決定教師們日後是否能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杜威指出,實習學生在觀摩有經驗的老師教學時,很容易只把眼光放在如何汲取的好點子,舉凡遊戲方法、教具製作、管理秩序、評量成績等,雖然這看來是最實際、最有用,但大家通常沒有細心觀察兒童的心理運作,也沒有留意學校整體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沒有細心觀察老師與學生之間,心智互動與心靈交流。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去注意老師如何引導學生看待事情和思考問題,沒有去留意老師的一言一行對學生產生什麼樣薰陶的作用?這種「心智與心智的相應」(Howmindanswerstomind)(Dewey,1904/1977,p.260),即是教育的根本關鍵,因為學生的心靈實實在在地得到滋養與開展。而這些都應該實習生應觀察的重點,而不只是教師用了什麼好方法賞罰學生。杜威強調,教學就像彈琴一樣,必須根據某些原理原則(principles)而進行,不應只是一味地仰賴某種方法或技巧(techniques)(Dewey,1904/1977,p.260)。若一味地強調立即帶班的能力,會使得學生不依據他所學的教育理論或原則,來調整他的教學方法,反而是根據每個當下的好用或不好用,根據別人怎麼做或怎麼說,這樣一來容易養成人云亦云的心態與習慣,無法發展出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提升個人的教學智慧。所以,為了幫助實習生發展出教學的原理原則,杜威建議在他們正式試教之後,班級指導老師應協助實習生,自行思考自己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幫助學生清楚地認知自己教學背後的思維假設為何、省思這些想法是否符合良好的教育目標和意義,並進而釐清自己對教學所抱持的信念和原則。總而言之,杜威強調班級指導老師,應協助實習生進行自我評鑑,而不應以自己個人偏好的方法或技巧,來批評和評量學生的表\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23現;指導老師所關切的應該是大方向、原理上的引導,而非小細節上的檢視。唯有如此,實習教師才有機會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在日後不斷地活化教學(Dewey,1904/1977,p.269)。杜威上述提到關於教育實習的重點以及應注意的事項,相信對我們現在的實習生和實習指導老師,應該有相當重要的啟發──如果我們也認為師資培育的目標是培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老師。肆、杜威的師培理念與現今實證研究之呼應接下來,筆者將討論杜威對師培模式的理念,與現今實證研究結果之間的對照與呼應。如上所述,杜威強調教師應具備基本的獨立思考與探究精神,才能成功地連結理論與實務,此一想法可從最新的教育實證研究結果中獲得支持。例如,Postholm(2008)研究挪威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到挪威於2003年新制訂的師資培育法規中,指出教師應具備的五種專業能力(competences),其中包括學科能力(subjectcompetence),規劃教學的能力(competenceinplanningtheirteaching),與社交溝通能力(socialcompetence),良好的工作倫理(agoodworkethic),最後則是改變與發展的能力(changeanddevelopmentcompetence)。最後一項能力意旨教學不應該一成不變,而應隨著時代的變化,學生特質的不同,和社會整體需求的改變做適當的調整,並隨時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因應新的挑戰。培養這種能力的關鍵即是教師平日的反思能力和習慣(reflection)。的確,教學的藝術無法與脫離反思的活動,Postholm(2008)的研究發現,教育理論中所提供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概念,能有效激發老師反思他們的教學,使他們對平日的教學活動,保有高度的敏覺性,能賦予教學事件更多的意涵,並勾勒出更多的可能性。不過,理論雖然有用,但也不能盲信。Kvernbekk(2001)提醒教師不應毫無批判的接受所有的理論,而應該將理論轉化為個人的知識(personalknowledge),並且將理論視為是反思過程中的工具(atoolinthereflectionprocess),而非不容挑戰的絕對真理。杜威的想法與洞見除了能獲得學理上的支持外,教育實務上亦可找到許多成功的個案,足以為杜威的真知灼見背書。舉一個最近頗受大家關注與敬佩的美國優良教師\n24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雷夫‧艾斯奎(2007/2008)為例。從他的教學自傳《第五十六號教師的奇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獨立思考與反思能力的呈現。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對語文教學的堅持:「我要我的學生愛上閱讀,要讓孩子長大後成為與眾不同的成人──能思考、考慮他人觀點、心胸開放、擁有和他人討論偉大想法的能力──熱愛閱讀是一個必要的基礎」(頁72)。為了讓學生愛上閱讀,他獨排眾議,堅持不用坊間現成的、過度簡化的教學讀本,而使用自己精心挑選的文學著作,相信學生能夠透過閱讀發人省思的文學名著,一方面提昇他們的閱讀能力,另一方面則訓練他們的心靈思考。由於艾斯奎老師保有獨立判斷與反思的精神,還有不斷追求真善美的決心和行動力,他成功地點亮了無數學生原本幽暗的學習歷程。當然,我們不可能希望每一個老師都是如此全力地奉獻、而且如此的熱愛和投入他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每一個老師多發揮一點點──那怕就是那麼一點點──獨立思考、反思與探究的精神,那麼他們的教學就會慢慢有所改觀,學生的學習也會慢慢得到進展。伍、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造成老師無法發展獨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升個人教學智慧的原因,是否是因為老師們不知道如何連接教育理論與實務?從杜威的文章看來,理論與實務斷裂的原因,即是錯誤的學習心態。首先,筆者想指出,杜威對於教學的看法,可能和一般師培學生所期待的有所不同。了解杜威作品的人,或許會注意到,杜威很少直接指出老師應如何教,或教學應注意哪些技巧;他總是將重點放在學習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教育的本質為何。其中的奧妙,依筆者的拙見,在於杜威認為,一個自身敏於學、樂於學、並志於學的人,自然能將璞石化為美玉,成為他所謂的artistteacher。換句話說,真正懂得學,才能懂得教。談「教」,不如先談「學」。然而,一般進入師資培育體系的同學,很早就將自己定位在老師的角色,因此大多希望從課堂中學得一些實際教學可用的方法或技巧,以便未來進入職場時,能馬上適應實際的教學現況,能管理好上課的秩序,以便教學。很多人期望立即學到「怎麼\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25教」,卻又不免質疑抽象的理論是否真能對未來實際的教學有所助益。遇到理論無法實際運用時,乾脆直接宣告理論破產。教育最大的問題,莫過是理論與實務的斷裂,也就是如杜威所謂的「理論與實務並非從老師自身的經驗中焠鍊成長而來」(Dewey,1904/1977,p.255)。這不僅造成教育的專業性強烈地受到質疑,也使得理論無法從實踐中獲得驗證或修正。同時,教育實務亦無法因理論的指引而獲得改善。其實理論到底有沒有用,最大的關鍵在於我們是怎麼學這些理論、怎麼看待這些理論、怎麼斷定理論有用或無用。我們若一味將理論當成絕對的真理或不證自明的法則,用一貫熟悉的方式,將之強記在腦中,以應付考試,那麼,理論自然無法內化成個人觀察、思考與行事的一部份。理論如果是這樣學的,當然很難產生實際的效用。反之,我們若能暫時撇開理論所呈現的法則與結果,將理論看成是一種對人類心智發展與社會文化脈絡,所提出的疑問以及所進行的探索,企圖了解理論之所以形成的過程,將思考的面向擴及當初被提出來的問題,對問題所提出的假設,以及驗證假設的過程。這樣一來,我們對理論,不僅能「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如此才能活用理論於教學實務中,而不是死記理論。教學現場中的許多問題與迷思,藉由理論所提供的概念和想法,可以使得教師對學生的認知與行為獲得一番新的了解。理論的最大用處在於啟發思考,而非禁錮思考。理論應激發我們的好奇心與滿足我們的求知欲。一個好奇的心靈蘊藏了無窮的潛力,一個受到桎梏的心靈,將在無形中也桎梏他人的心靈。此外我們必須了解,很多的理論不應被直接拿來套用,也無法直接轉換成立即可用的教學方法,但理論所提供的思考向度與眼光,常常能使我們明白真正的教與學,在何種條件與情況下才有產生的可能。理論的用處在於幫助我們了解教與學的本質。相信這樣的了解,可以增強我們在教學上的觀察力、判斷力、行動力、創造力,以及反思力。杜威指出,師培的學生在學習教育理論時,常犯了一個錯誤的心態:大多數的學生將教育理論看成是空洞無用的,除非他們能馬上拿去運用在實際的教學現場。杜威說,這個想法反映出一個很大的盲點,亦即認為教室裡的學習與日常生活中的學習是二分的、是互無關連的。因為有這樣的想法,學生便不會將課堂上所接觸的教育理論,用來反芻和檢視他們自己或身邊他人的學習經驗。因為鮮少以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經驗,來理解、運用和檢視這些教育理論,理論對他而言,自然是空洞的身外物,與他個人的經驗斷裂。理論歸理論,他的經驗歸他的經驗,沒有因為接觸了理論而得到\n26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轉化或提升。要能有效的運用教育理論,學生必須採用循序漸近的方式,首先以自身的經驗出發,再來才檢視自己週遭他人的經驗,最後才企圖真正地引導日後的學生(Dewey,1904/1977,p.362)。畢竟一個沒有整理、反芻過自身學習經驗的人,便無法了解以及引導別人學習。筆者認為,大多數的人忽略了要確保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首先所需要的是學習心態的改變,除了上述提到應將理論視為過程而非只是結果之外,另外重要的是,應從關心如何「教別人學」到關心如何「教自己學」。也就是說,我們應用教育的專業課程所提供知識,檢視自己作為一個學習者的行為、習慣、方法與態度,並進而涵養與提昇自己的學習經驗。唯有我們能反芻我們自身的學習經驗,以這些既有的經驗作為素材,才能對理論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將抽象的理論換化成活潑的生命智慧,如此我們才能打破理論與實務的藩籬。陸、成為良師的根本關鍵之前,我們談到師資培育所面臨的挑戰是提升教師的獨立思考與探究能力,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同一個觀點的延伸。在《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此篇文章的結尾時,杜威提到,一個老師真正能對學生有所啟發,關鍵常常在於老師自身的學問內涵以及治學態度和方法。杜威說:「學術研究本身可以變成訓練出良師的好方法之一」(Scholarshippersemayitselfbeamosteffectivetoolfortrainingandturningoutgoodteachers)(Dewey,1904/1977,p.263)。杜威的話,乍聽之下,好像有點違反常理,因為我們或許都曾遇到過學術研究的很精深的老師,卻好像不懂得如何教學。然而,我們如果將杜威的「學術」(scholarship)理解成廣義的「學問」,那杜威的想法,的確是不無道理的。舉例而言,孔子能啟發顏回、蘇格拉底能啟發柏拉圖、杜威能啟發胡適,都是由於後者從前者身上學到了「治學」的根本方法:亦即不斷的學、不斷的問、不斷的行、以及不斷的精進自己。杜威在描述他所謂的artistteacher時談到:「他們渾身上下充滿了探索的精神,這樣的氣息自然地感染了每一個與他們接觸過的人」(Dewey,1904/1977,p.265)。不論是孔子、蘇格拉底、或是杜威,若非他們對其畢生致力研究的學問本身有相當\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27大的探究熱情,以及深刻的了解和體會,不管他們的教學技巧如何高明,不管他們如何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最終都無法對學生有真正的啟發。以孔子為例,他若不是對「仁」有深切的體悟,他如何能對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下,所提出的同一個問題,提供不同的詮釋與答案;以蘇格拉底為例,雖然他口口聲聲說自己無知,若非他對正義有深刻的洞悉,他如何不斷地引導別人重新思考正義為何;以杜威為例,若非他本身善於思考,他如何啟發胡適領悟出那有名的十字箴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值得一提的是,杜威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及論文指導教授,胡適受杜威的影響很大,還曾邀請杜威到中國講學兩年(1919-1921),將民主與科學的理念介紹給當時熱切學習西方理論的中國知識份子(Wang,2007)。不過,杜威自己是否是個絕佳的好老師,各方的看法或許不一。杜威的學生曾經有人描述他上課時,眼睛常望著窗外,口中念念有詞,彷彿陷入一陣深思,實在談不上什麼有趣(Martin,2002)。然而若仔細研究課堂上所抄的筆記,赫然會發現杜威上課所講的內容以及所呈現的思想,其實是很有系統的,是杜威一步一步地、穩健地推敲出來的結果。懂的欣賞的人,會發現原來上了一堂思想的饗宴,我想,胡適是其中之一。否則,胡適(1996)不會說他從杜威身上學會了如何思考。杜威認為,重視自己對學問的素養是成為良師的重要關鍵之一。他說,學問做得很好的老師,即使從未接受過任何教學法的訓練,也很有可能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老師。畢竟在尚未有任何教學法的發明以前,好老師已存在。雖然如此,杜威並非否認教學法的重要,他只不過希望大家可以體會到學問本身對教學的意義。他認為,求學問的方法與教學的方法,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換句話說,一個老師對自己「學問」學習的「歷程」,正是他教學與啟發學生的來源與重點。杜威指出,經過系統化與抽象歸納整理出來的學科知識本身即隱含了一種方法,他在此篇文章中稱之為「心智的方法」(methodofmind)(Dewey,p.263)。雖然有學者指出,由於杜威對mind一詞的描述通常顯得很「隱晦模糊」,並且「片片斷斷」(Hansen,2006,p.3),所以不太容易懂他真正的意思為何。之前本文提到概念,即是很好的例子,如「心智與心智的相應」(Howmindanswerstomind),以及「心智活動的學生」(studentofmind-activity)。Hansen(2006)甚至認為杜威自己在提筆為文時,也苦思著該如合理解與表達mind的意思。如Hansen所言,杜威對mind的\n28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定義時常很抽象,不過筆者認為,杜威這裡所謂「心智的方法」(methodofmind)的意思,可以廣義地理解成「求學問的方法」,或狹義地理解成「科學的方法」,或者更簡單的說,就是獨立思考與探究的方法。總而言之,杜威認為雖然呈現在教科書上的學科看來只是冰冷抽象的知識,但學科之所以成為學科的真正精神是一種態度和方法,在於它是人類幾千年來一直不斷運用心智探索宇宙生命真理的結果。學科中所涵蓋的分類、解釋、與歸納的知識,表面上離實際的生活很遠,但它的源頭來自於人類對於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好奇、探索與發現。在杜威的眼中,學科的成就無疑地展現了「人類心智的偉大」(greatnessofthehumanmind)。可惜,科學的發現,一旦被列入教科書中,科學家對宇宙奧秘的好奇與敬畏、對探求真理的奉獻與執著,就完全被忽略了。杜威提醒我們:學科之所以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在於學科背後所彰顯出來的人類心智(Dewey,1904/1977,p.266)。學習之所以有意義在於,透過學習,我們能與一些偉大的心智接觸與交流,進而提升我們自己的心智與發展。然而,老師們若僅僅將學科當成現成的知識灌輸給學生,而忽略了原初探索知識的心路歷程,原初的好奇與熱情,這無疑剝奪了兒童自然的求知欲與渴望探索的樂趣。一個真正對學科有深入了解的人,對學科的知識是充滿熱情與活力的。換句話說,因為老師的了解是穩固紮實地源自於深刻的感受和體認,他可以很自然地能引導學生探索知識的內容是如何而來的,對生活與生命又有何意義。因為他自己是那樣熱愛他所要教的內容,他自然能在學生身上激起同樣的感受。此外,當老師本身對「真摯和適切的心智活動有清楚的了解」,那他對學生所表現的心智力量,與也會給予相同的尊重(Dewey,1904/1977,p.264)。換句話說,當老師自身擁有孩子般的赤子之心和好奇感,他也會懂得欣賞孩子童言童語中所流露的探究心和智慧。現在大家常提到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應設計各式各樣的活動讓學生實際的參與,藉此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並且能讓學生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另外一方面,則有人強調教學應凸顯教師的教學魅力,於是一群又一群所謂的「麻辣鮮師」,將課堂轉變成個人的表演秀,讓學生因為崇拜老師,進而熱愛學習。相較之下,現今的教育思潮和教學理論的確鮮少強調學科知識或做學問的方法的重要;大家似乎假定,強調學科便等於贊成填鴨式的教學。其實學科(subjectmatter)本身的教育功能是很關鍵的,但它真正的意涵卻常被忽略或誤解。杜威在此篇文章的最後,提到他\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29對「學科」意涵的獨到詮釋。筆者認為,杜威的想法可為現今強調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教育現場上常會遇到的問題,其實是老師對他所要教的學科本身,缺乏整體的了解和過於僵化;對於所要「教」的「內容」,究竟有何價值與意義更是一知半解。其實這個問題,與我們這整篇所談的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是相同的問題。亦即老師本身如何靈活地學習、了解、與應用學科知識和教育理論。這種侷限若不突破的話,教育理論與實務如何銜接的問題,很難獲得根本的改善。柒、本篇文章對臺灣師資培育的啟示這篇文章對一百年後的臺灣教育場域,有何意義與啟示呢?首先,大家可以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的師資培育方式是杜威描繪的「學徒制」,還是「實驗制」?這個問題乍看之下似乎很容易回答,從課程安排的角度而言,當然可以毫無疑問說,我們的師培方式是「實驗制」,因為課程中有強調教學原理、兒童心理與發展、以及教育史哲學等教育基礎科目的學習,並強調這些科目為教師專業的必備知識。再者,我們現在還有所謂的學科教材教法,這一切看起來,不都是相當進步的表徵?不都是相當符合「實驗制」的精神?在回答此問題之前,先讓筆者分析一個有趣的現象。一百多年前杜威寫作的當時,教育理論的發展才剛剛起步,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才漸露頭角,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等教育專業科目,當時都還未曾聽聞;然而一百年後的今天,各式各樣的教育學說和理論紛紛興起,內容和種類或許多到讓學生吸收不良。於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學徒制」不夠重視理論的問題,而是「實驗制」所衍生的新問題:如何讓學生有效地學習理論,並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問題。有趣的是,雖然表面上杜威當時面臨的問題與我們的很不一樣,甚至相反。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地思考:杜威當時所關切的問題,如今已經得到解決了嗎?教育的理論與實務,是否仍存在某種斷裂?從臺灣目前教師檢定考試的內涵上來看,它是重視理論,是屬於「知識本位」的(張鈿富、葉連祺,2002),我們希望透過教師檢定內涵的嚴格把關,以確保教師基本的知能。或許我們可以說,新進教師的專業知識,已經透過各類的考試,獲得了層層嚴\n30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格的檢驗與把關;然而,我們是否真能透過教師檢定測驗,測出教師在實務上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不管這基本能力是五項,還是五百項(汪履維,1999)?我們是否能確定,大多數的教師,會將他們所習得的教育專業知識,轉化成實際的教學行為?在臺灣,我們常聽到的是:教師們因為外在的壓力,如行政長官的命令,授課進度的要求,學生的成績表現,家長的關切與反應等等,無法將他們的專業知識與教學信念徹底地落實在教學中。雖然這些外在的環境因素,無疑地阻撓了教學專業的落實,但是我們除了能消極地怨嘆環境太險惡、或理論過於理想之外,問題就真的那麼單純嗎?筆者在此並不想落入「專業知識」重要和還是「基本能力」重要的二元對立爭議。關於所謂的「理論知識」(theoreticalknowledge,knowingthat)和「實際知識」practicalknowledge,knowinghow)孰輕孰重的問題,文獻中的爭議從來沒有間斷過(Orland-Barak&Yinon,2007)。筆者認為,杜威的文章給予我們思想上的啟示是:當教師無法發展自己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當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教學信念並未真正的內化成個人行事風格和處事態度時,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鴻溝是必然的結果,不管教師檢定和甄試如何嚴格地把關教師們的專業知能,不管外在的教育環境險惡與否。如前所述,某些教師的專業知識和個人經驗是二分的;他們所學的知識歸知識,他們原有的信念、價值和想法,沒有得到應有的衝擊與轉化,所以他們的行事易受到舊有經驗的影響和侷限。簡言之,他們並未因習得了新的知識,發展新的願景和視野,進而成為一個不同的人,更不可能將知識靈活運用於現實的教學生活中。更具體地說,如果他們在學習豪爾‧迦納(HowardGardner)的多元智慧理論時,並沒有同時學到尊重個別差異的基本精神,不能用同樣欣賞的眼光看待一個數理邏輯強的孩子和一個肢體動能強的孩子,即使他們考試能一字不漏的背誦八種智能的特色,那也是毫無益處。在學習柯爾堡(Kohlberg)的道德發展理論時,若不能體會培養兒童自律的基本精神與價值,那他們即使能將三期六段的道德序階背得滾瓜爛熟,亦是枉然。這麼說,並不是要大家絕對認同迦納或柯爾堡的理論,以批判、審慎的態度看待這些西方的理論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學習了這些理論,是否有真正地撼動了他們原有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與他人的方式;學習了這些理論是否觸動了他們內在深層的想法與感受,還是他們的理解與學習只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一切只為了應付無可避免的紙筆考試。\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31在現今臺灣的教育界裡,理論與實務斷裂的問題,看似更加嚴重了。我們的師培學生,由於面臨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等各項考試的壓力,很難保有良好的學習心態。這類考試的內容多半有固定的答案(方便出題的簡易性與閱卷的公正性),因此學生在學習教育理論時,常常缺乏批判與反思的精神,只關心重點是什麼、如何最有效的將重點整理與記誦起來,而不去管他們個人對理論的批判與見解為何,理論對個人的啟發又是什麼,更別提他們是否認真反思國外的理論套用在國內的情境時,是否會有某些盲點與侷限。此外,令筆者憂心的是,師培的課程是否會因此導向考試領導教學?曾經有學生在筆者的課程提出這樣的疑惑:內容設計很豐富,討論也很有趣,但使否對教師檢定或教師甄試有實質的幫助?雖然這個同學剛開始有些懷疑與憂慮,但最後對整門課的評價是肯定的。然而,她的問題卻不禁令筆者陷入深思:在高等教育趨於市場化的氛圍下,我們是否應考慮「消費者」的需求和滿意度?我們的課程是否應配合並幫助學生能順利的通過教師檢定與甄試?如果老師是如此單一的角度去教授理論,學生亦是以如此單一的角度學習理論與準備考試,那我們很難期待學生到正式的教學場域時,能排開重重困難,將理論轉化為實務,用理論檢視實務,進而用實務修正理論。如此一來,理論與實務斷裂的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從師資培育發展的歷史來看,自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師資培育,所重視的皆是提供學生實際的「生存技巧」,功利主義色彩極為濃厚(Beyer,1996,p.5)。現在,教師已經被視為一種專業,如同醫生和律師,教師也同樣地要學習整套的專業理論,要通過基本的專業技術檢定,要具有基本的專業態度。一百年後的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應不應」學理論的問題,而是如何讓理論發揮功用,真正與實務連結;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學徒制」和「實驗制」之間的選擇,而是如何讓實驗制真正發揮培養教師獨立思考與探究的精神,如何讓我們課程提供良好的活動和整體環境,讓學生透過實際經驗的反思來探究理論、驗證理論,使得我們的師培模式成為實質的,而非名義上的,「實驗制」。\n32初等教育學刊第三十一期參考文獻中文部分卞娜娜、陳怡君、凱思(譯)(2008)。第五十六號教室的奇蹟(原作者:艾斯奎․雷夫)。臺北:高寶國際。(原著出版年:2007)諶攸文(譯)(2004)。優秀是教出來的(原作者:RonClark)。臺北:雅言文化。(原著出版年:2003)汪履維(1999)。「中小學教師基本素質」研究與評量上一些「技術面」與「非技術面」的考量。「中小學教師素質與評量」研討會。高雄師範教育大學主辦,1999年五月24-25日。胡適(1996)。四十自述。臺北:遠東。張鈿富、葉連祺(2002)。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檢定制度之問題和興革對策。教育研究,103,31-38。英文部分Beyer,L.(Ed).(1996).Introduction:Themeaningofcriticalteacherpreparation.InL.Beyer(Ed.),Creatingdemocraticclassrooms:Thestruggletointegratetheoryandpractice(pp.1-26).NewYork:TeachersCollege,ColumbiaUniversity.Dewey,J.(1902/1977).Thechildandthecurriculum.InJ.A.Boydston(Ed.),JohnDewey,themiddleworks1899-1924:Vol.3(pp.273-291).Carbondale: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Dewey,J.(1904/1977).Therelationoftheorytopracticeineducation.InJ.A.Boydston(Ed.),JohnDewey,themiddleworks1899-1924:Vol.3.1903-1906,Essays(pp.249-272).Carbondale: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Dewey,J.(1916/1985).Democracyandeducation.InJ.A.Boydston(Ed.),JohnDewey,themiddleworks1899-1924:Vol.9.DemocracyandEducation1916(pp.273-291).Carbondale: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Feiman-Nemser,S.(2001).Frompreparationtopractice:Designingacontinuumtostrengthen\n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剖析杜威對師資培育的看法及其對現今的啟示33andsustainteaching.TeachersCollegeRecord,103(6),1013,1055.Hansen,D.T.(2006).Introduction:ReadingDemocracyandEducation.InD.T.Hansen(Ed.),JohnDeweyandoureducationalprospect:AcriticalengagementwithDewey’sDemocracyandEducation(pp.1-21).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Korthagen,F.,&Vasalos,A.(2005).Levelsinreflection:Corereflectionasameanstoenhanceprofessionalgrowth.Teachersandteaching,11(1),47-71.Kvernbekk,T.(2001).TheAcademicidentityofpedagogy.InT.Kvernbekk(Ed.),Pedagogyandteacherprofessionalism(pp.17-30).Olso:GyldendalAkademisk.Martin,J.(2002).TheeducationofJohnDewey:Abiograph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Orland-Barak,L.&Yinon,H.(2007).Whentheorymeetspractice:Whatstudentteacherslearnfromguidedreflectionontheirownclassroomdiscourse.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3(6),957-969.Postholm,M.B.(2008).Teachersdevelopingpractice:Reflectionaskeyactivity.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AnInternationalJournalofResearchandStudies,24(7):1717-1728.Rust,F.O.(1994).Thefirstyearofteaching:It’snotwhatIexpected.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10(2),205-217.Shulman,L.S.(1998).Theory,practice,andtheeducationofprofessionals.TheelementarySchoolJournal,98(5),511-526.Wang,J.C.(2007).JohnDeweyinChina:Toteachandtolearn.Albany,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