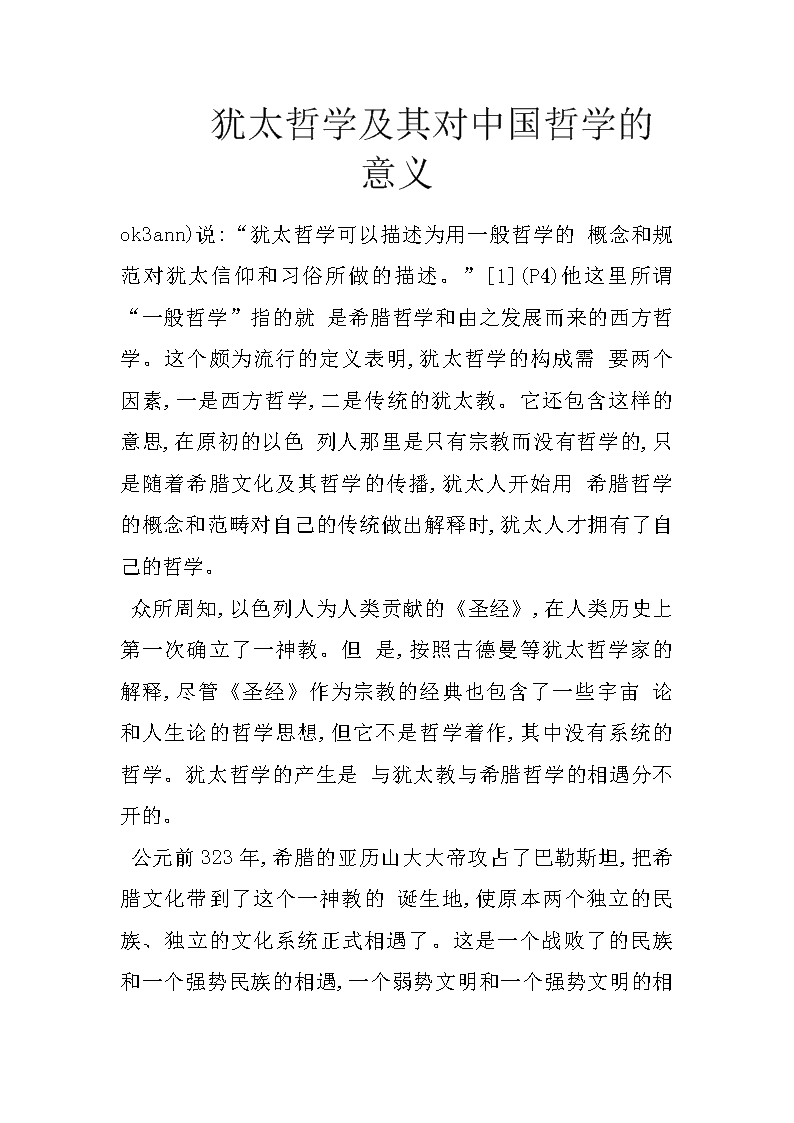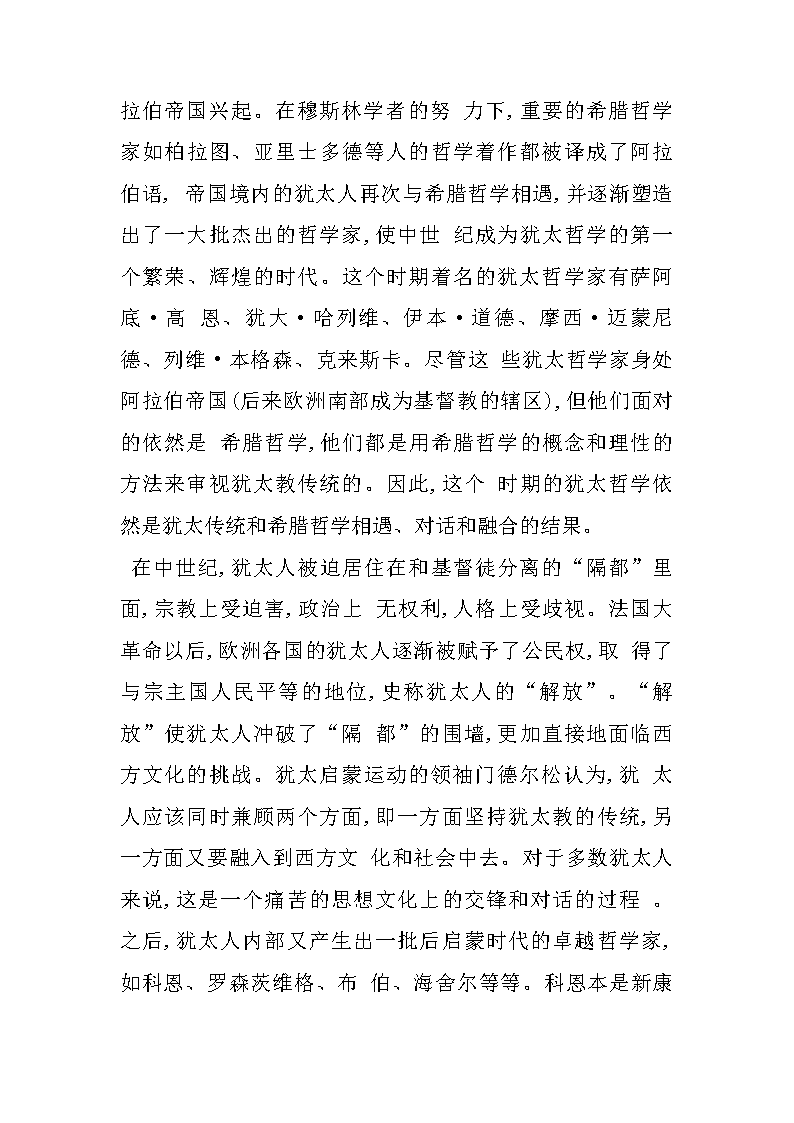- 66.50 K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ok3ann)说:“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做的描述。”[1](P4)他这里所谓“一般哲学”指的就是希腊哲学和由之发展而来的西方哲学。这个颇为流行的定义表明,犹太哲学的构成需要两个因素,一是西方哲学,二是传统的犹太教。它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原初的以色列人那里是只有宗教而没有哲学的,只是随着希腊文化及其哲学的传播,犹太人开始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自己的传统做出解释时,犹太人才拥有了自己的哲学。众所周知,以色列人为人类贡献的《圣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神教。但是,按照古德曼等犹太哲学家的解释,尽管《圣经》作为宗教的经典也包含了一些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哲学思想,但它不是哲学着作,其中没有系统的哲学。犹太哲学的产生是与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相遇分不开的。公元前323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巴勒斯坦,把希腊文化带到了这个一神教的诞生地,使原本两个独立的民族、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式相遇了。这是一个战败了的民族\n和一个强势民族的相遇,一个弱势文明和一个强势文明的相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相遇具有“不得不”的性质。这样的相遇不似朋友间平等的会面,其间有冲突、对抗,包括犹太人“以身殉教”这样的血的代价,当然也有温和平静的对话,天长日久的熏陶和逐渐的相互融合。两种传统相遇300年以后,在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孕育出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他在血统上是地道的犹太人,笃信犹太教,而且以诠释犹太教的《圣经》为毕生的事业,他同时也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精通希腊语言、哲学、历史和诗歌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希伯来的信仰和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和理性主义精神交织在这位希腊化的犹太人心中,经过艰苦的综合与调和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希腊哲学,同时又包含犹太教信仰和希腊理性内容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犹太哲学。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斐洛哲学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犹太人所知,因而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犹太哲学,但是,他作为犹太哲学的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1][2][3][4][5][6]下一页nbsp;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焚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犹太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巴比伦、西班牙和德国、波兰先后成为犹太人最为集中的地区\n。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在穆斯林学者的努力下,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着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再次与希腊哲学相遇,并逐渐塑造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使中世纪成为犹太哲学的第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着名的犹太哲学家有萨阿底·高恩、犹大·哈列维、伊本·道德、摩西·迈蒙尼德、列维·本格森、克来斯卡。尽管这些犹太哲学家身处阿拉伯帝国(后来欧洲南部成为基督教的辖区),但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希腊哲学,他们都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犹太教传统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犹太哲学依然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遇、对话和融合的结果。在中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和基督徒分离的“隔都”里面,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无权利,人格上受歧视。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逐渐被赋予了公民权,取得了与宗主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史称犹太人的“解放”。“解放”使犹太人冲破了“隔都”的围墙,更加直接地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门德尔松认为,犹太人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坚持犹太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中去。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文化上的交锋和对话的过程。之后,犹太人内部又产生出一批后启蒙时代的卓越哲学家,如科恩、罗森茨维格、布\n伯、海舍尔等等。科恩本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代宗师,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但是,他在退休后却回到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发展出犹太教哲学的体系,影响了罗森茨维格、布伯等哲学家。这就是犹太教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这个历程表明,犹太哲学是古代犹太教传统和与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用一位犹太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亚伯拉罕主义”和“雅典主义”相会合的结果。二、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的特征作为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产物,犹太哲学有亦东亦西的特点。这里的亦东亦西性就是犹太教中固有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理性和逻辑的成分的整合与统一。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前提是承认对象的可理解性,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研究的对象——这种对象也许是自然界,也许是人类社会秩序或人的本性,也许是科学知识和语言,诸如此类,并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逻辑地表达出来。尽管西方哲学的发展曲折多变——古希腊的繁荣时期,中世纪的“奴婢”阶段,近现代的鼎盛春秋,后现代时期传统的衰微,然而其主导的方面是理性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唯\n心主义哲学,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哲学,如古希腊原子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如洛克、巴克莱、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现代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唯理论的认识论,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有以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着称的学派,例如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反理性主义哲学表面上看与理性主义无缘,但其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这是因为,这些体系所研究或重视的对象是非理性的成分,如意志、情感、性欲等,而其方法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即运用理性对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并理性或逻辑地诉诸文字表达。后现代哲学以反传统着称,传统的理性主义当然也在其反对之列。但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理性主义的,因为它是对古代和现代传统所做的理性的批判,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如前所述,犹太哲学的源头是犹太教。犹太教是东方(中东)的产物,体现着东方的精神特征,这就是信仰至上和神秘主义。犹太教的前提是对造物主和神性立法者上帝的信仰。有这样的信仰,才有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上帝和[6]下一页以色列人立约,给予“十诫”和诸多律令典章,使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有所依从。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前提,就不会\n有犹太教的存在。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是希伯来《圣经》,它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隐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它没有也无须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圣经》对于上帝的描述多是神秘莫测的,其中尤以《创世纪》中的创造论和《以西结书》、《以赛亚书》中对于神车的描述最为突出。在历史上,这些篇章的内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与信仰的结合。这个特点有两层涵义:其一是说犹太哲学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上帝的存在、人生的信仰、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信仰对象的结合。其二是说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对他们来说,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信仰,就只有犹太教而没有哲学;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就只能导致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是犹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中世纪着名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哲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2](P107)在他看来,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信仰作一番理性的考察,使之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通过他的\n理性的考察,《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被解释成按上帝的“理智”造人;“看见”、“看”、“望”在被用于上帝时,“都是指理智的把握,决不是指眼睛的看到”。[2](P29)这样一来,犹太传统中的人格神就被抽掉了神人同性论的特征而被理性化了。同时,迈蒙尼德又始终把信仰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上。当亚里士多德派的宇宙永恒论和犹太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学说发生冲突时,迈蒙尼德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犹太教信仰一边,认为犹太教的创世论远比宇宙永恒论更为可取。还有,在论述先知何以作出预言的时候,迈蒙尼德把上帝和从他而释放出的“流”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认为神不但是预言的最终源泉,而且在预言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理性和信仰是同时共存,互相补充的,只有具备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将潜在的预言现实化。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是调和理性和信仰,使《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神车论”、犹太教传统中的“先知论”等等,都成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哲学的内容既是有关宗教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在他那里,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论证下结合起来,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一种整体的统一性。[3]\n理性主义讲求概念的清晰、分析和论证的合逻辑性,它与东方的神秘主义那种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风格迥然不同,因而很难与之兼容并存。但是,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它们却被有机地融汇在一个体系之中。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借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派的哲学阐述犹太教的创造论,试图通过理性主义的阐释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理论化、系统化。他认为,上帝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借助于理念渐次产生出世界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是他用以规范质料的工具,也是为被造物的形式或本质。“它们赋予万物以形式,给无序以有序,给无限以界限,给无形状以形状,总之,变坏事为好事。”[4](P210)但是,他对于“逻各斯”的解释则充满神秘主义。“逻各斯”(Logos)是最高的理念,是“理念的理念”,“神的言辞”或“智慧”,它还被说成是“上帝的长子”、“上帝的形象”、最高的天使,以及宇宙的力量源泉等等。它内在于物质世界,即为自然界的规律,内在于人,即为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体现在犹太教的《托拉》中,则成为神圣的律法。在他那里,逻各斯在概念和功能上都是不清楚的。我们无法形成它的明确认识,只能靠体悟来把握它在不同场合下的意义和功用。类似“逻各斯”这样的神秘性概念也体现在各个时期的其他犹太哲学家那里,即便在20世纪的马丁·布伯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布伯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我-你”关系,指人与人之间应有\n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不把别人作为外在的它物(It),也不作为和自己不相干的他者(He),而是作为和自己处在直接的关联中的你(Thou)。我和你的这种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相互包容,共同结成一个整体。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彼此界限分明,而我-你关系强调的是[6]下一页二者的交互性(co-relation)和“伴侣”(partnership)关系,突出的恰好是二者之间的不明晰性。不仅如此,他承认上帝的存在,认为《圣经》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是永恒的你,人与上帝的关系也是我-你关系。无疑,这样的关系也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在宗教经验中才能体会其意蕴所在。理性与信仰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结合,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犹太哲学家那里,二者结合、统一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犹太哲学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区别的两派,一派推重理性,代表性的哲学家有斐洛、萨阿底、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科恩;另一派推重传统的犹太教信仰,其主要代表是哈列维、卢扎托、克莱斯卡、罗森茨维格、布伯和海舍尔。卢扎托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两种力量构成的,这就是雅典主义或希腊文化与作为犹太宗教思想的亚伯拉罕主义。前者给世界带来了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对和谐和壮丽的热爱,后者带给人类的是公正、平等和仁爱之类,使人类讲道德\n和慈善。希腊文化中的唯智主义对生活没有意义,它只适用于哲学家,而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因为大众需要的是“道德维生素”。[5](P281—282)马丁·布伯也严肃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不足:它拥有最全面的和高度发达的知识,然而自己却无法找到意义;它拥有最严格的和最纯正的规训,但自己却无法找到道路。这样的道路就是对于超越存在的信念,它关乎人类的本真的生活,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样的道路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中,即犹太教和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家哲学之中。因此,东方文化可以弥补现代西方文化的缺陷。[6](P555—556)犹太哲学的以上特点表明,犹太哲学不是纯粹东方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因此,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可以说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思想之路。它还表明,犹太哲学家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他们对西方文化和哲学采取开放、学习和汲取精华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妄自菲薄,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在他们的新哲学中得到了创造性地保持和弘扬。犹太哲学这样一些特点及其态度和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应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三、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n中国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都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形式,都有丰富厚重的文化传统——在犹太人那里为犹太教,在中国人这里为儒释道宗教和哲学。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有的虽然没有中断,但是迄今尚未开发出完整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如印度哲学——她和西方的相遇几乎与中国同时,目前也和中国一样正处在探索和形成新哲学的时期,还没有成熟到成为范例的程度。而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相似,现代的中国也是在和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和对话的大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而且这样的相遇都曾经有过被迫的性质。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这样,对于正在建设的中国哲学应该有积极意义。首先,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都是很有哲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的理学和心学都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但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n遇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换言之,假如没有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假如没有由此而引起的中西哲学的相遇、碰撞和整合,中国哲学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儒释道的传统中,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含义,冯友兰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捏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他所谓现代逻辑学的成就指的是共项和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关系的学说。这也就是说,和犹太哲学相似,现代中国哲学的旨趣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6]下一页方法来阐释古代的哲学传统。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之处主要是犹太哲学在先,中国现代哲学于后;前者历史悠久,后者历史短暂罢了。中国现代哲学之始,哲学家们对犹太哲学一无所知,即使是最近的中国哲学家如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对犹太哲学也不甚了了,没有受其影响。今天我们“发现”了犹太哲学,始知犹太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所走的竟是同一条道路,这本身就是对现代中国哲学走向的认同。同时,先行的犹太哲学向世人表明:东方传统与西方\n理性主义结合是可行的,同时也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昭示:“中西合璧”的现代中国哲学之路是可以走通的。其次,犹太哲学提供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范例。如果说犹太哲学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思想之路,那么,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式上,它成功地运用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使传统犹太教中观念和问题学理化、系统化。二是在内容上较好地做到了信仰与理性、神秘主义与逻辑风格,即犹太精神与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而且越是靠近现代,这种融合的工作就越完善。在中世纪,迈蒙尼德这种综合与融合的工作做得最好;在现当代,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则是整合和融合犹太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典范。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哲学在后一方面还有明显的欠缺。冯友兰着有《贞元六书》,创建了名曰“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他的新理学,就是用共项和殊相以及其他希腊哲学的概念去分析宋明理学中的范畴,如“真际与实际”、“理”与“气”、“性”与“心”、“太极与无极”、“道体”、“大全”、“精神境界”等,以期使它们明晰并充实起来。他所谓“真际”就是事物的形而上学根据,属于一般或本体界;“实际”则是可以见到的这个或那个事物,属于个别或现象界。由于“理”是一般,是个别事物之所以为个别事物的形\n而上的根据,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所以理是属于“真际”的;“气”被解释成“料”,或“质料”,是使事物能够存在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和人都是由“理”和“气”即形式和质料两者构成的,都以“理”和“气”为形而上的根据。他还认为,与人的认识或得到的概念的层次相联系,人生有四种境界,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的,指的是人在直觉中达到的“浑然与物同体”或“自同于大全”的精神状态。[7](P200—216、240—243)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接着讲”之区别于“照着讲”就在于前者能够用西方近代逻辑学的成就,“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在这个意义上,新理学没有在内容上对“旧理学”做实质性的发展,他的工夫和主要贡献是,使宋明理学在形式上学理化和系统化。借用冯友兰自己的说法,这仍然属于“新瓶装旧酒”。牟宗三对西方哲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吸收多少西方哲学的内容。如郑家栋先生所说,康德对他影响也只是在形式上为他提供了诠释中国哲学的框架罢了。[8](P510)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很好的西方哲学素养。但是,似乎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的内容\n对于他们多半还是异己的,他们对于中西哲学的认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体西用”的模式,他们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中国的,其精神也仍然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哲学的工具而已。如前所述,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尤其是在当代犹太哲学家那里,西方哲学与犹太传统是糅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义的阐述,西方哲学的内容与犹太宗教的精神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可以说,他们做到了“即体即用”、“体用无间”。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所欠缺的,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创建新哲学时应该向犹太哲学家学习的地方。第三,犹太哲学提醒中国哲学家关注宗教信仰因素。如前所述,犹太哲学乃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犹太教信仰的统一体,实质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哲学。它在揭示了西方哲学与犹太教会通的可能性的同时,表明了宗教对于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宗教和哲学不应该是纯粹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哲学家在从事哲学研究时应该关注宗教和信仰因素。许多中国学者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和哲学,而忽视了宗教。冯友兰于1934年在布拉格世界哲学大会上说:“我们把它们(中西文化)看作是人类进步[6]下一页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n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9](P271)在他看来,所谓东西方的联合就是用中国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没有宗教意识,其目标是“以哲学代宗教”。牟宗三虽然认识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早期儒学的宗教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强调的是“理智的直觉”对于“智性存在体”的把握,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也没有融入宗教信仰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如果此岸的现象世界之后或之外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那么,如康德所解释的,这样彼岸世界就不仅是作为自然界的本体——物自体,而且包括自我的本体——灵魂和整个宇宙的本体——上帝,而后二者正是宗教所由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如果理智的直觉可以把握自然界的本体(牟宗三称之为“物如”),那么,似乎信仰就应该被承认为把握灵魂和上帝的方式。牟宗三、冯友兰等现代中国哲学家认同直觉的哲学意义,而且在理性和直觉的综合统一上做了出色的工作,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大贡献。但是,当我们知道犹太哲学是一种融理性与信仰为一体的哲学后,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哲学研究中充分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恐怕不止以上这三条,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列举更多。\n最后,我想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这样一段话:“假如没有犹太人,我们用来看世界的眼睛,听世界的耳朵,感受世界的感觉就会不同。不仅我们借之接受世界的感觉中枢不同,就连我们思想世界的心灵也不相同,我们将对自己的经验给出另外的解释,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得出另外的结论。我们将为生活设计不同的轨迹。”[10](P3)我想,这段话是值得认真对待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