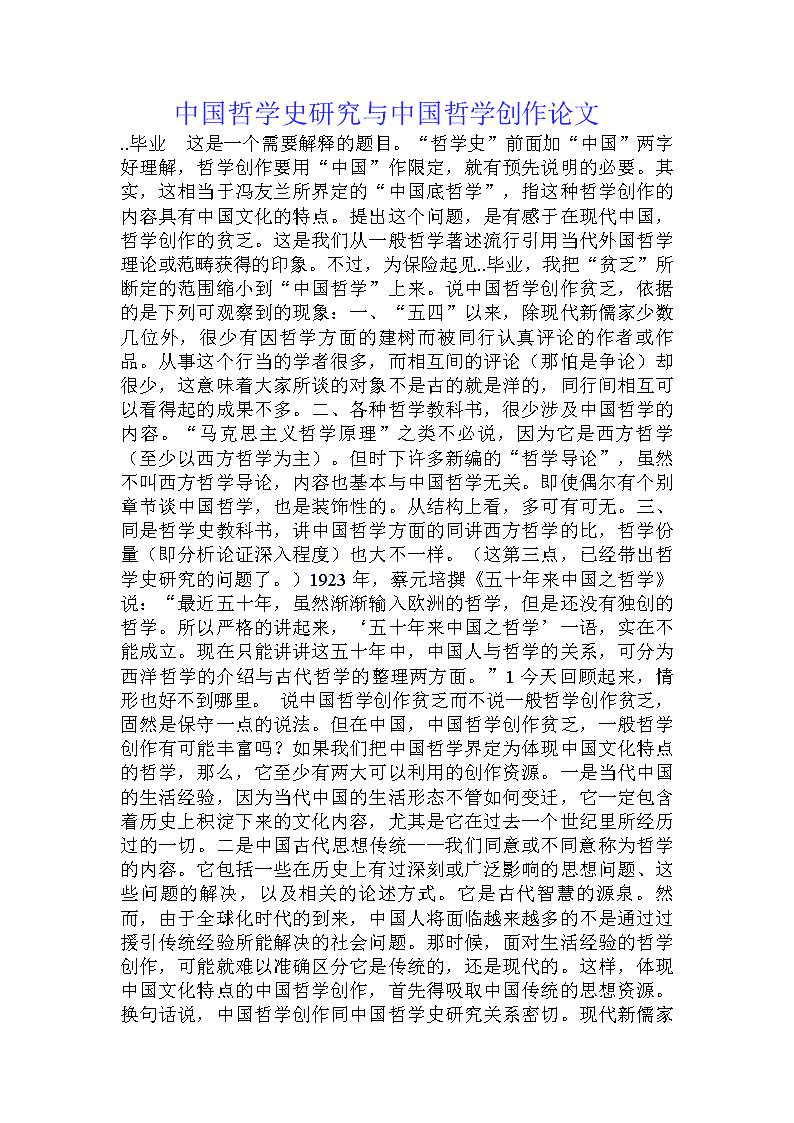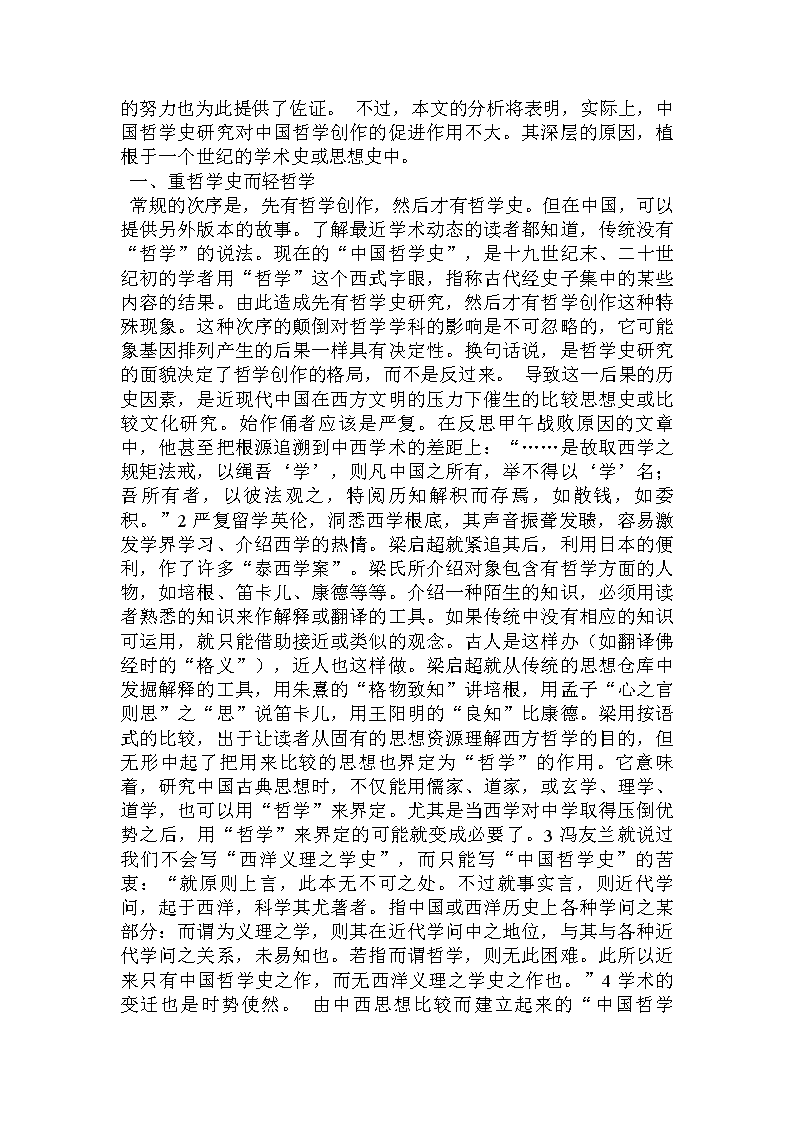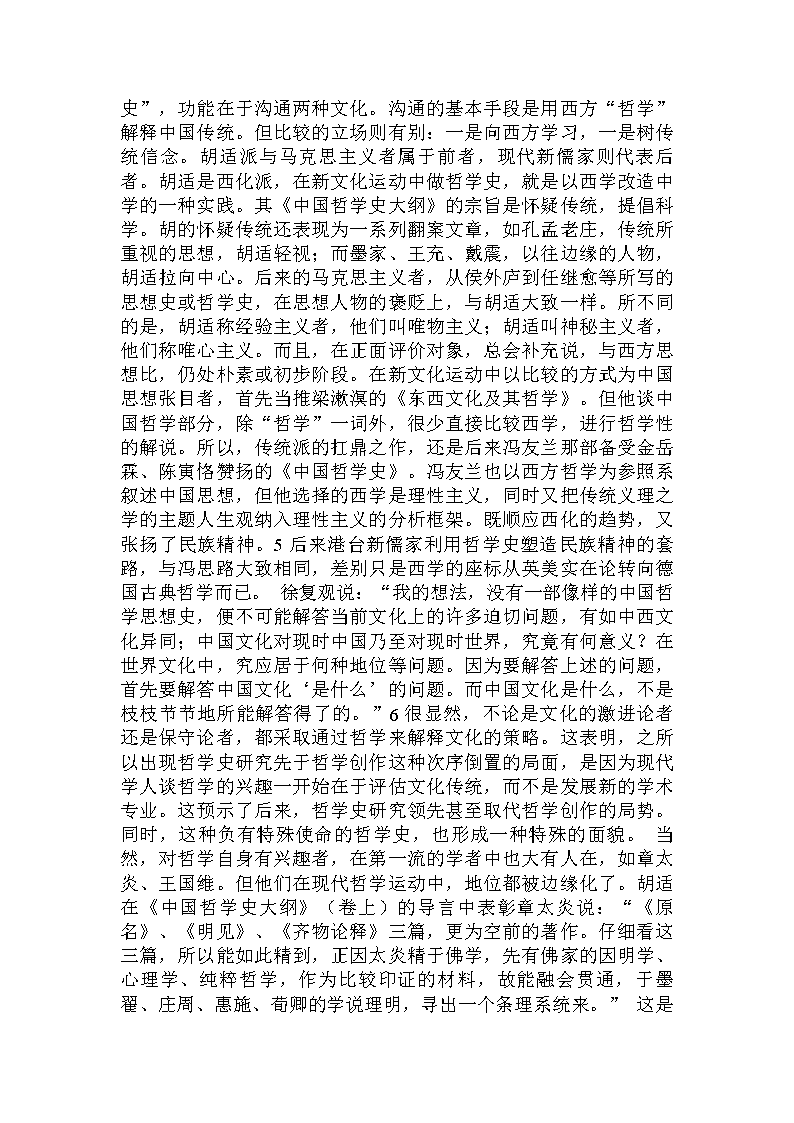- 58.00 K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论文..毕业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题目。“哲学史”前面加“中国”两字好理解,哲学创作要用“中国”作限定,就有预先说明的必要。其实,这相当于冯友兰所界定的“中国底哲学”,指这种哲学创作的内容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在现代中国,哲学创作的贫乏。这是我们从一般哲学著述流行引用当代外国哲学理论或范畴获得的印象。不过,为保险起见..毕业,我把“贫乏”所断定的范围缩小到“中国哲学”上来。说中国哲学创作贫乏,依据的是下列可观察到的现象:一、“五四”以来,除现代新儒家少数几位外,很少有因哲学方面的建树而被同行认真评论的作者或作品。从事这个行当的学者很多,而相互间的评论(那怕是争论)却很少,这意味着大家所谈的对象不是古的就是洋的,同行间相互可以看得起的成果不多。二、各种哲学教科书,很少涉及中国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类不必说,因为它是西方哲学(至少以西方哲学为主)。但时下许多新编的“哲学导论”,虽然不叫西方哲学导论,内容也基本与中国哲学无关。即使偶尔有个别章节谈中国哲学,也是装饰性的。从结构上看,多可有可无。三、同是哲学史教科书,讲中国哲学方面的同讲西方哲学的比,哲学份量(即分析论证深入程度)也大不一样。(这第三点,已经带出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了。)1923年,蔡元培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1今天回顾起来,情形也好不到哪里。说中国哲学创作贫乏而不说一般哲学创作贫乏,固然是保守一点的说法。但在中国,中国哲学创作贫乏,一般哲学创作有可能丰富吗?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界定为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哲学,那么,它至少有两大可以利用的创作资源。一是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因为当代中国的生活形态不管如何变迁,它一定包含着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经历过的一切。二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n我们同意或不同意称为哲学的内容。它包括一些在历史上有过深刻或广泛影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及相关的论述方式。它是古代智慧的源泉。然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不是通过过援引传统经验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那时候,面对生活经验的哲学创作,可能就难以准确区分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样,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哲学创作,首先得吸取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创作同中国哲学史研究关系密切。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不过,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实际上,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哲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大。其深层的原因,植根于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中。一、重哲学史而轻哲学常规的次序是,先有哲学创作,然后才有哲学史。但在中国,可以提供另外版本的故事。了解最近学术动态的读者都知道,传统没有“哲学”的说法。现在的“中国哲学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者用“哲学”这个西式字眼,指称古代经史子集中的某些内容的结果。由此造成先有哲学史研究,然后才有哲学创作这种特殊现象。这种次序的颠倒对哲学学科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可能象基因排列产生的后果一样具有决定性。换句话说,是哲学史研究的面貌决定了哲学创作的格局,而不是反过来。导致这一后果的历史因素,是近现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催生的比较思想史或比较文化研究。始作俑者应该是严复。在反思甲午战败原因的文章中,他甚至把根源追溯到中西学术的差距上:“……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2严复留学英伦,洞悉西学根底,其声音振聋发聩,容易激发学界学习、介绍西学的热情。梁启超就紧追其后,利用日本的便利,作了许多“泰西学案”。梁氏所介绍对象包含有哲学方面的人物,如培根、笛卡儿、康德等等。介绍一种陌生的知识,必须用读者熟悉的知识来作解释或翻译的工具。如果传统中没有相应的知识可运用,就只能借助接近或类似的观念。古人是这样办(如翻译佛经时的“格义”),近人也这样做。梁启超就从传统的思想仓库中发掘解释的工具,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讲培根,用孟子“心之官则思”之“思”说笛卡儿,用王阳明的“良知”比康德。梁用按语式的比较,出于让读者从固有的思想资源理解西方哲学的目的,但无形中起了把用来比较的思想也界定为“哲学”的作用。它意味着,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时,不仅能用儒家、道家,或玄学、理学、道学,也可以用“哲学”来界定。尤其是当西学对中学取得压倒优势之后,用“哲学”来界定的可能就变成必要了。3冯友兰就说过我们不会写“西洋义理之学史”,而只能写“中国哲学史”的苦衷:“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4学术的变迁也是时势使然。由中西思想比较而建立起来的“\n中国哲学史”,功能在于沟通两种文化。沟通的基本手段是用西方“哲学”解释中国传统。但比较的立场则有别:一是向西方学习,一是树传统信念。胡适派与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前者,现代新儒家则代表后者。胡适是西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哲学史,就是以西学改造中学的一种实践。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宗旨是怀疑传统,提倡科学。胡的怀疑传统还表现为一系列翻案文章,如孔孟老庄,传统所重视的思想,胡适轻视;而墨家、王充、戴震,以往边缘的人物,胡适拉向中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侯外庐到任继愈等所写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在思想人物的褒贬上,与胡适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胡适称经验主义者,他们叫唯物主义;胡适叫神秘主义者,他们称唯心主义。而且,在正面评价对象,总会补充说,与西方思想比,仍处朴素或初步阶段。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比较的方式为中国思想张目者,首先当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但他谈中国哲学部分,除“哲学”一词外,很少直接比较西学,进行哲学性的解说。所以,传统派的扛鼎之作,还是后来冯友兰那部备受金岳霖、陈寅恪赞扬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叙述中国思想,但他选择的西学是理性主义,同时又把传统义理之学的主题人生观纳入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既顺应西化的趋势,又张扬了民族精神。5后来港台新儒家利用哲学史塑造民族精神的套路,与冯思路大致相同,差别只是西学的座标从英美实在论转向德国古典哲学而已。徐复观说:“我的想法,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便不可能解答当前文化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有如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对现时中国乃至对现时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在世界文化中,究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因为要解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解答中国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是枝枝节节地所能解答得了的。”6很显然,不论是文化的激进论者还是保守论者,都采取通过哲学来解释文化的策略。这表明,之所以出现哲学史研究先于哲学创作这种次序倒置的局面,是因为现代学人谈哲学的兴趣一开始在于评估文化传统,而不是发展新的学术专业。这预示了后来,哲学史研究领先甚至取代哲学创作的局势。同时,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哲学史,也形成一种特殊的面貌。当然,对哲学自身有兴趣者,在第一流的学者中也大有人在,如章太炎、王国维。但他们在现代哲学运动中,地位都被边缘化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表彰章太炎说:“《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仔细看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理明,寻出一个条理系统来。”\n这是较确切的肯定。太炎谈哲学,虽然也不脱比较之法,但非泛论文化问题,他更有辨名析理的兴趣,以认识论、逻辑学的观点看古典名学,创获颇丰。故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断定“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王国维对哲学的兴趣也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头几年,其时他除大量介绍德国哲学的文章外,还有后来收入《静安文集》及其续编的《论性》、《释理》、《原命》等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名篇。王国维也同样用比较的方法,但他的比较不是中西不同范畴的归类比附,而是深入的逻辑分析。如《释理》对中西思想具有某些一致性的揭示:“吾人对种种之事物而发见其公共之处,遂抽象之而为一概念,又从而命之以名。用之既久,遂视此观念为一特别之事物,而忘其所从出,如理之概念,即其一也。吾国语中‘理’字之意义之变化,与西洋理字之意义之变化,若出一辙……”该文对“理”的涵义所作的抽丝剥茧的分析,今日仍有典范意义。王评论严复引入西学的动机在科学而非哲学,而感叹自己“欲为哲学家则事情苦多,知力苦寡”。(王还尝试性的提出“古雅”作为美学的新范畴)7冯友兰则说:“与严复同时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哲学方面理解比较透彻,见解比较深刻,可是是在他放弃哲学研究之后,他才闻名于世。他是王国维。”8不论章太炎还是王国维,谈哲学都不能脱离比较之法。但与那些以治哲学史为比较文化的方便法门者比,其兴趣在哲学本身。其表现就是更重视思想的方式、理据,而非孤立的价值结论。即使在诠释传统思想范畴或命题,也不是以还原本意为满足,而是努力从说理方式上进行反思或重构。这是真正的哲学性研究。只有创作“新理学”的哲学家冯友兰,才是这种学风的承继者。但是,《齐物论释》、《静安文集》的影响甚微。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史著述,给章、王的篇幅相当小,即使提及,焦点也在其结论或思想内容上,很少有把眼光放在其更能体现哲学性思考的论述方式上。这意味着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标准不在哲学本身。简言之,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大势,导致哲学研究中哲学史研究的动力压倒了哲学创作兴趣,同时也导致哲学史研究中非哲学性倾向的发展,这是很可能今日中国哲学创作先天不足的历史根源。二、哲学史研究的歧向\n尽管哲学史研究的动力压倒了哲学创作的兴趣不太合乎常规,但是,发展中国哲学创作,却不能不关心哲学史研究的走向。换句话说,我们得询问,哲学史研究为何没能促进创作本身。事实上,在现代中国本来就不发达的哲学创作中,除金岳霖外,说得上有创获的,也就是现代新儒家。9现代新儒家正是从哲学史研究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同西化派一样采取通过哲学史来比较或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战略。不同之处在于新儒家对传统有一种持守的精神,其得其失均与此有关。因此,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所作的哲学史,下面都一并加以检讨。但对不同错误的归属,则会适当加以区分。1、立场优先所谓立场优先,就是指首先关心一种观点或命题所表达或蕴涵的政治态度或学派立场,而不是重视它论证的深度与创新性。这个价值包括文化、政治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学派三个层次的问题。简言之,它是把哲学意识形态化,把学术取舍变成“政治正确性”的表态。问题的根子在于通过哲学史作文化比较的动机,它不同程度表现于新(激进)旧(保守)两派的研究中。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学术研究多服务于他反传统、倡西化的立场,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立足于做翻案文章,对孔孟老庄所讲求的义理较轻视。所以冯友兰讥他“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10他本人后来也无法按原来的思路写下去,只好将续编改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不叫哲学史。胡适的套路在其后被同是反传统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侯外庐就说:“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家,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11当侯所代表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中占居主流以后,其追随者则将其推至极荒谬的地步。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或经济地位可以成为衡量其哲学水平的尺度,而一个承认常识但没有文化的人则可以被认为比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更高明。从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到港台新儒家,谈中国哲学都是为寻求或重塑中国文化精神。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与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直言“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之哲学思想之中心,再一层一层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中国历史文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综结起来。”12针对中国传统“疏于界说之厘定,论证之建立”的弱点,他们要求透过对先哲的生活方式看问题,“而人真能由此去了解中国哲人,则可见其思想之表于文字者,虽似粗疏简陋,而其所涵之精神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则正可极丰富而极精深。”\n13由于新儒家目标在于借哲学重建传统精神文化,故对中国哲学的探讨自然比反传统者更有建设性。但是,强烈的卫道情结,也给其学术的深入造成限制。皮锡瑞曾指出经术不同于学术之处在于:“盖凡学皆贵求新,唯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14新儒家之学不是传统经学,但其道统意识使其学同经学一样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是把学术变成宣传,对价值信条可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厌其烦。政治正确性比学术创新更重要,大量哲学史教科书就是这一原则的牺牲品。新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大陆意识形态虽然对立,但卫道的立场,对哲学固有的批判精神却是一种阻碍。2、范畴错置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较文化催生的产儿。经验层次或局部事物的比较,可以借助超越于两者之上(或之外)的更有涵盖性的知识来解释,如两种动物的行为方式,或两种作品的主题或风格的比较,我们可以用人类理智的基本模式,或者用文学艺术的一般理论来作为解释的工具。被比较的双方都同样是对象化的。但对不同文化的精神结构,或者说“哲学”的比较,一开始却不存在一种元理论作为通用的工具。(除非你是在比较两种与你的本土文化无关的其它两种文化。)实际上,它只能是用一种文化解释另一种文化,即比较者选择自己熟悉或认同的文化作为工具,另一种则是被解释的对象。我们说梁启超的“泰西学案”是用他熟悉的传统介绍、解释另一种陌生的思想文化。胡适则是用他认同的文化解释他熟悉的文化。一旦被比较的双方差距太大,或者解释者对双方的了解、特别是对解释工具的了解程度太浅,比较的结果就会像是照哈哈镜一样。冯友兰说过的两种文化的相互阐明或相互批评,必须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的工作。\n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当长时间内做的是照哈哈镜的工作,因为主流的作品多是从西方哲学中截取某些流派或论题,作为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工具。一个世纪来,用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大多数范畴,如本体、现象,主体、客体,共相、殊相,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感性、理性,原因、结果,先验、经验,自由、必然,等等,基本上,它们都来自西方近代哲学,即唯理论、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胡适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现代新儒家均如此。(相对而言,后者处理比较灵活些。)这个解释框架有两个性质是与中国传统大相庭径的:第一,它是一种讲究逻辑论证,并以形成知识系统为目标的理论哲学;第二,其哲学主题是以认识论为中心,即致力于说明人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这两点,都是中国传统中所或缺的。中国传统中,像天人、性命、善恶、是非、有无、物我、本末、体用、言意、形神、理气、心性、知行、道器,等等范畴,则是围绕着对人生的意义及其根据展开的。同时,其表达思想的方式,散见于谈话、讲课、寓言、诗、书信、碑记、及各种经典注疏中。这些表达多数具有一种“对话性”的特征,与理论作品大不相同。所谓“对话性”,指“说—听”关系,与“写—读”关系不一样。在信息交流上,后者是单向的,前者则是双向的。同时,由于说、听双方都了解特定的语境,因此预设许多不需明言的前提,这就导致其表达缺乏逻辑上推论的完整性。在这一意义上,经典注疏也是“对话”的变种。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