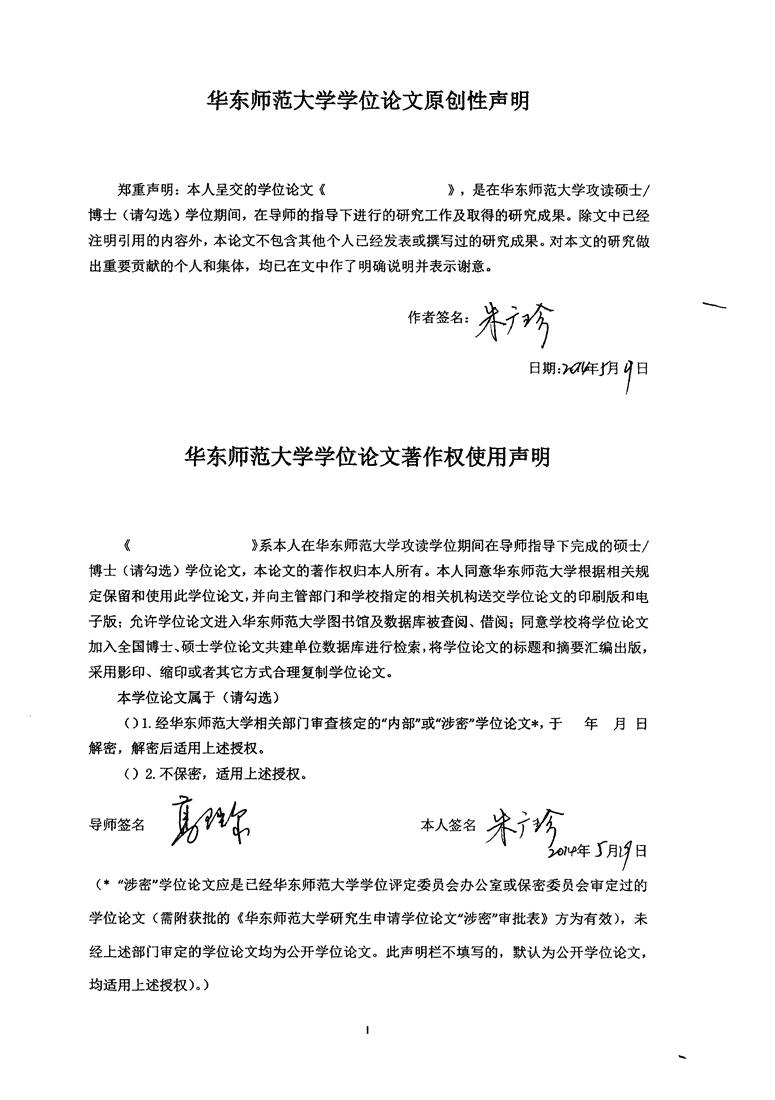- 4.26 M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201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分类号:学校代码:密级:学号:凝縣鴨士芽位文论文题目:庄子的生死哲学院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专业: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指导教师:高瑞泉教授论文作者:朱广珍年月\nSchoolCode:ationforMasterDegree,2014::::::\n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郑重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宂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系本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论文,本论文的著作权归本人所有。本人同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和学校指定的相关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数据库被查阅、借阅;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釆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本学位论文属于(请勾选)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门审查核定的内部或涉密学位论文,于年月曰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涉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需附获批的《华东师范大学研宄生申请学位论文涉密审批表》方为有效),未经上述部门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n朱广珍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姓名职称单位备注顾红亮教授哲学系主席方旭东教授哲学系刘梁剑副教授哲学系?\n摘要《庄子》关于生死的讨论在文本中贯穿始终,然而通过生死观考察《庄子》对于个体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研宄尚在少数。本文通过视角批评的方法,考察了先秦哲学关于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理解,明确生死观是以个体存在及其价值为问题核心,并且在庄子不同的理解是源自不同的视角。首先是观之以物视角下乐生恶死的观点,庄子指出,该观点将生命片面的定义为形体的生命,并且对个体对于存在的确证和对乐生恶死价值评定没有合理的辩护;其次是观之以俗视角下生死由命的观点,庄子指出该观点忽略了个体价值由个体自身所决定,并且个体存在自然性应当置于社会性之先。在批评上述两种视角及其观点的同时,庄子以其道论为理论背景,阐释了观之以道的生死观,观之以道,则个体在道的意义上与天地万物同一,万物以气相通,因而生死只是气的聚散,而精神生命才是生命本真性的体现,因此,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依道而行,也即合乎自然的生活,看待生命也应当自然而然,而个体生命的意义源自个体与自然世界相谐。而在定义和评价生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实践的主旨,实践的维度是生死问题一个题中应有的视角。关键词:庄子,视角,生死,自然\nABSTRACTTherearerichDialoguesonLifeandDeathinZHUANGZItextbook,howeveritisseldomresearchedaboutexistenceandmeaningoflifethroughinthosedialogues.Thisstudybasedonmethodofvisualcritique,overviewedthesubjectandthoughtoflifeanddeathbetweenRU(儒)墨)道)物)俗),道)气):\n目录一、导论二、生死问题的视角三、生死问题直接的规定性:以物观之乐生恶死四、生死问题非“物”的视角:以俗观之死生有命五、生死问题的本真维度:以道观之死生无变于己六、结论参考文献麵\n一、导论希腊神话中,宙斯让普罗米修斯去除人类关于死亡的知识,于是人们对死亡心存忧惧,却又痴迷于对死亡的思索,神话象征着人类对生死的思考,始终是是终极而具体的。生死问题是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关乎生、也关乎死,古今哲学家大多痴迷于这一终极而又具体的困惑,在苏格拉底看来,生死是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生人不必为死后世界而担忧,其行刑前的遗言广为流传,然而,正如莎士比亚名言所说:“活着,还是死着,这是个问题。”孔子也曾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在世的我们处在生的界域,还是通往死的途中,殊难分辨,死亡对于生者而言,始终是神秘的,而如大部分亘古常新的哲学问题一样,生死问题也始终是开放的。周秦时期,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关于生死观念的基调,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古代世界存在着关于死后世界的观念,在最早的甲骨文卜筑记录中,可以看到“两个世界”的对话,周秦的考古和传世、出土文献中对中国古代死后世界的观念图景描绘的更为清晰。另一方面,关于生命和生死的理解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大众层和知识层的分野。尽管知识层的诸子思想对生命和生死有着理性的理解和思考,对生命和生死的思想比宗教和神话的知识更为深刻,但宗教和神话的观念始终支配着世俗生活,两者没有显著的分界。《庄子》寓言中诸多人物和场景大多依托神话故事,从世俗的知识背景中蕴育出哲学洞见。可以说,周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丧葬制度反应了周秦时期的生死观念的缩影,也是战国诸子的哲学思想萌发的土壤。在诸子争鸣时期,《庄子》是对生死问题最感兴趣的一位,现存《庄子》三十三篇为魏晋时期郭象所编集,其内容与大部分先秦古籍一样,是多人多时结集的成果,保存了庄周及其追随者的思想轨迹。柏拉图著,杨锋译,《斐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n其中对生死问题多有讨论,郭象亦将“达生死之变”作为《庄子》核心思想之一,其诡谲的语言风格和思考方式对于个体存在及其意义的探宄常有启迪意义。《庄子》哲学影响深远,对其研究历来不绝如缕,形成薪为壮观的庄学史,对其生死问题的研宄也颇为丰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己经注意到生死问题,撰《死亡八说》进行宣传,其中将庄列分属一派,主张“齐生死”,但这篇文章只是收集世界不同文化中关于生死的不同学说,没有展开讨论;之后胡适、冯友兰在其哲学史著作中已有专论《庄子》的生死观,“达观主义”和“出世主义”是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做出的概括,指出《庄子》的生死观有着出世和超脱生死的一面,这一评价却并未进一步做出哲学解释;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提出其早期的“以理化情”说,认为对生死的认识可以破除对生死的忧患,之后在《新原人》中又提出“四境界”说,不同境界中的人对生死的理解各有不同,道家的《庄子》是自然境界和天地境界相混,在身体层面不知生死,在精神层面超越生死;冯契先生认为,与杨朱“贵己”和“重生”不同,《庄子》认为个人的生命无非是自然界给予了形体,又赋予了和谐,一方面更彻底的否定了儒墨的人道原则,教人顺从自然命运,而另一方面其“逍遥游”中强调人与自然的交互,与自然为一,达到审美的自由。冯友兰先生提出的“齐生死”的认识命题如何过渡到“哀乐不能入”的价值命题,还需要做出进一步说明,并且冯契先生指出道家将天道置于人道之先,但是若要对“逍遥游”的审美自由做进一步展开,还需要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积极理解做出补充。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庄子》研究逐渐兴起,诸多学者(包括毕治国,《死亡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华书局,年版,页。冯友兰,《新原人死生》,《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年,页。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页。\n海外学者)对其生死观的探究也日渐卓著,中国学者专著有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该书对《庄子》其人其书考证翔实,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庄子以“气”、“化”、“道”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和《庄子》对个体存在的三重限制的揭示:死与生自然之限)、时与命(社会之限、情与欲(自我之限),据此指出:《庄子》依据其自然哲学的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实现对死生大限的观念的突破,通过阐发其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实践,对上述困境的超越,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如果说上述成果着眼于《庄子》思想的整体性,崔宜明教授《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则从个体视角出发,通过还原《庄子》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庄子的个人境遇,揭示出《庄子》对现实生存境况的迷惘和对理想自由的向往之间的理论张力与内心矛盾,杨国荣教授也从个体生命的存在视域出发,认为就其现实的形态而言,个体的存在总是有其时间之维,生死是《庄子》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庄子》用“养其寿命”和“说(悦)其志意”表达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另一方面,肯定生命价值的同时,《庄子》对“死”也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与自然的原则及“齐物”的本体论立场相应,《庄子》从自然的观点看待“死”,也以“齐”与“通”的原则规定“死”,“死”在《庄子》那里一开始便既不同于虚无化,也有别于彼岸的现象,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在”世过程的延续。通过对照“生”的假借性、悲剧性与“死”的完美性,《庄子》将“死”视作“反其真”,即向道的回归。从个体生命的存在视域出发,《庄子》对待生命的态度难以脱离消极、迷惘的色彩。因此,宇宙论的角度和人生论的角度是否并存不悼,以及《庄子》对上述两种角度作何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海外学者庄子研究概况,参《诸子学刊》(第三辑)“世界庄子研究动态”,方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年。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年,页。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页。\n《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一一以〈庄子〉为中心》以思想史的方法还原了先秦道家思想的产生背景、源流以及后续的演变轨迹。该文以文献对比为基础,梳理了“黄老”、“老庄”、“道家”等称谓背后道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据此指出,首先,促使道家思想诞生的社会基础,从宏观的角度看,是春秋、战国时代激荡的社会本身,而早期道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正是那些被“是”、“可”等正面价值所抛弃的人,“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是那些在激荡的社会中能巧妙地生存下来、可以把握财富和权力并得意非凡的人,正相反,是那些到哪里都找不到安身之处的自由的士大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庄子》;其次,就《庄子》的思想演变而言,早期道家“万物齐同”哲学转向了“物化”哲学,以物化、转生、轮回为根据,本体论的“一体”占据了主流。作者倾向于认为转生、轮回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就己经存在,并非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存在,而通过梳理《庄子》与《淮南子》关于“物化”的论述,会发现梦是对转生轮回的“记述”,而阴阳二气则为转生之根据。另外,作者还揭示了道家思想中“乐”的思想,对道家思想而言,真正的快乐,毫无疑问就在作为世界的终极的根源者“道”使“万物”而“物化”、转生、轮回的主宰者当中,庄子称这种乐为“至乐”,受《庄子》以及后期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学,都对此有所发展,尤其表现在其理想人格当中。《庄子》的思想由杨朱、老聰等早期道家思想继承而来,但是囿于资料匮乏,对早期道家思想的生死观很少论及,现存《庄子天下篇》和散见于先秦各家的文献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死的看法,以及对《庄子》生死观的影响,对早期道家生死观的管窥有助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海外学者代表作品有吴光明两篇专著《庄子:游世哲人》、《庄子内三篇沉思录》,主要通过文化检释学的方法对《庄子》文本做出融池田知久,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年,页。池田知久,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宄: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年。页。池田知久,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年。页。\n贯的途释,《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爱莲心,江苏人民出版社,对《庄子》思想作出了清晰的理路分析,此外,还有将《庄子》与西方哲学家比较的研宄成果。此类研究不可避免的需要考虑到两种文化背景,古代西方哲学有着灵肉二元论和神学的背景与特定问题,如死之恶,不朽等,而现代西方哲学讨论生死则偏重于语言和逻辑的分析,如死亡与时间、同一性的关系等,与西方文化背景对死亡的消极态度不同,《庄子》(甚至整个古代东方文化,将死亡看作另一个世界的“门檻”,宇宙生成论和对待死亡的态度常常显示出积极的观点,文化途释学的研宄虽然兼顾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异同,但是在评价时难以跳出各自的窠臼。对生命和生死的思考是全人类的主题,与文化和思想的切入点不同,如果以问题作为切入点讨论中西哲学对于生死的思考,使得各自的成果可以相互参照与启发,虽然难度相应增加,却更有意义。从现有的研宄成果来看,除上述已经论及的可探讨空间以外,多数成果都或隐或显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将“必死”视作必然的、消极的事实,而《庄子》的生死观是应对这一事实的结果,但这一前提却没有进一步做出说明,即必死何以是一个消极的事实,《庄子》是否也持一种消极的立场,对于《庄子》的生死观,缺乏哲学上的进一步追问。本文尝试问题的研究,将生死作为生命哲学的基础问题,并梳理先秦哲学对个体存在及其意义的思考,并考察《庄子》为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何种进路。本文以《庄子》的视角批评和道论为主线,围绕个体生命的定义及其价值、死亡的本质和意义,从天人、物我、群己三个层面展幵讨论。《庄子与伊壁鳩鲁生死观之比较》(时洪艳,《群文天地年第期》;《庄子与波德莱尔的生死观之比较》(朱玉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庄子与海德格尔生死观比较》(张利群,《江汉论坛》年第期)。:。\n二、生死问题的视角尽管“人固有一死”的信念比任何一种信念更牢固,我们却很难说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生死的定义是一致的,即使是同时代,不同的观念支配下对必死的理解也各有不同,甚至混杂。人可能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命,突出的表现在人的生命兼具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因此,人的生死标准也是最难定义的。我们常常把生死的标准和生死的概念相混淆,不同社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死标准,但生死的概念只有一个。从概念的角度看,生的意思是生命的获得,死则意为生命的失去。而另一方面,有生命才有生死,生命的价值决定着生死的价值,而死亡又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呈现,因而生死是一切与生命有关价值的基础。先秦时期,儒、墨、道三家对生死的理解各有不同,“出于司徒之官”的儒家思想继承了礼乐文明关于生死的观念,将生命看作天地和合的产物,有着“天命”的观念,这表现在昭穆分明、贵贱有序的丧葬制度和规格中,按照儒家的思想,宇宙本身有着天然的价值等级,而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嵌于”整体秩序之中,具体化为家族宗法和据此相应的社会制度设计,因此个体生命的价值由外在的伦理等级所赋予,贵贱生死均由天定,这种思想倾向在两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一统局面而愈发稳固。具体说来儒家将生死看作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是人道的最终体现,也是礼的根本目的:“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而另一方面,儒家进一步扩展了“以德配中国古代以精气的聚散定义生命的有无,而生和死就文字学角度而言,‘‘生”意为从地上生出,向上生长,获得生命,而“死”则是转入地下,失去生命。因而生有三层义项:出生、生长、生命本身,死也有三层义项:失去生命(殁、离开人世(逝、消散于天地(亡)。此处借用现代社会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嵌入”(的概念,即前现代社会,社会想象‘‘自我”是将个体“嵌入”在各种有序的关系当中: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而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由整个秩序和关系给予。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页。\n天”、“修德配命”的思想,将伦理价值排在生命价值之先,且伦理价值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因而在做出道德选择时,儒家是典型的道义论者:“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总的来说,尽管儒家的仁义学说有着人性论的依据,但其理论却侧重于外在规范和整体秩序,仁义诸美德最终也以入世为目的,因此对于人的定义偏重于社会性而非自然性。墨家思想以“贵义”和“尚利”为价值原则,《庄子天下篇》总结道:“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巳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一方面,墨家贵利。与儒家提倡厚葬久丧不同,着眼于“天下之利”的墨家主张节葬:“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藍漏,气无发曳於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其反对争斗杀戮,维护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出发点亦在于使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相一致,即“兼相爱,交相利”。而另一方面,墨家尚义,将道义的价值置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之先,“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甚至走向极端,成为以义捐命的任侠风格:“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手足,子为子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页。孙治让,《墨子间估》,北京:中华书局,页。\n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因此,墨家思想和儒家一样,以社会属性定义个体生命,在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问题上表现出为天下之利而牺牲自我的精神。道家则比较复杂,“道家”是汉代才有的名称,杨朱老聃、田骈慎到、宋經尹文、列子等被看作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在《庄子》中也多次提及。按照上述各家思想的侧重点,分为以下三类:宋妍(也作宋趣、宋輕、宋荣子)尹文持“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的观点,一方面安定生存环境,维护生命,“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另一方面持寡欲说,不以礼法荣辱等外在规范伤害生命,“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因此,宋荣子被《庄子》评价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宋、尹的思想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维护和对世俗价值评判的挑战,然而这两种思想亦不相兼容,体现在宋、尹思想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消解和对他者价值的维护,因而《庄子天下篇》批评他们“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彭蒙、田骈(也作陈骈、慎到主张“齐万物”和“去知”:“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彭、田的思想中明确表达了道的普遍意义(“齐”)和天人关系中天道的优先地位,以及道物关系中物相对于道的有限性,即物有可与不可之分,而道则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亦是最高的善。因此人道需要遵循和依归道的普遍、优先、和无限性,也即成为“无知之物”:“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孙治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如果将生命定义为无知之物,则无需用知识认识生命自身,亦无需维护自身的价值。然而没有感知的生命,似乎是个悼论的表达,因此《庄子》借讽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另外一派是关尹老聰和杨朱所代表的“贵己”、“重生”、“为我”的观点,杨朱不同于儒墨两家,而将生命价值排在伦理价值之先:“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为天下,吾不为也”。就个体与群体而言,个体才是首位,因而在自我与外物的价值排序中,自我的价值要优先于其他价值。关尹、老胁则主张“重生”,以柔弱、被动的方式,通过“寡欲”、“去知”来保全生命:“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儒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贵生”即维护和保全得自于天的生命,是道家天道原则在人道中的落实,而“为我”的观点将个体生命价值的优先性彰显出来,主体的生命价值优先于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选择也具有优先性,即决定何者更有价值。《吕氏春秋不二》对上述各家总结为:“老稱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膑贵势……。”《庄子》集原始道家思想之集大成,继承并融合了上述早期道家的思想,例如齐、虚、一等思想在《庄子》思想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朱裏,《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中国科学院哲学研宄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下),中华书局,年,页。《列子》一书后人疑为后汉作品,其中多数内容与《庄子》相同,《庄子》也多有称引《列子》,有学者考证《列子》在《庄子》之先(钱钟书《管锥篇》,也有学者考证杨朱即庄子(陈冠学,《庄子新传:庄周即杨朱定论》;而庄子的挣友惠施对《庄子》思想也有影响,例如“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与《天下篇》介绍惠施思想中“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语义相近。\n中举足轻重,然而对道的追求和体验是《庄子》与早期道家思想共通的基础,因此对道的论述依然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首先,就道的本质而言,道的存在形态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因而道与有形、可见的万物有所区别。相应的,道不是万物,那么道也不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不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因而道无法用空间性和时间性描述道的本质;因为道不同于万物的存在,所以虚无性是道的本质,在对存在的否定和对自身的否定中,道揭示了绝对的虚无:“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其中,道就是最初的“未始”。其次,就道与万物的关系而言,作为本源和开端的道,道自身作为自身的根据:“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即《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因而自本自根的道即是自然本身,是天地万物的根据,也是人的根源,是道生养万物,生养人: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闲,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道、物、人的演化过程,具体而言,是由无(太初)、一(有、德(物)、命(分、形(气)、性(精神),再向初(无)的循环,一方面是从道到人的展开,个体生命由道(无)获得形体、精神,另一方面是从人到道的回归,个体生命再从有的形态转入无的形态。虽然道不同于万物,自身是虚无,但同时道又生养万物,因而又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存在于万物之中:“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因而万物都具备道的特质,不仅不同的事物皆有道,而且相互对立的事物也有道,不仅高级的事物有道,低级的事物也有道:“故为是举奠与楹,厉与西施,恢桅橘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所以,道即自然,道生万物,万物也具有自然,即具有自身的本性,万物自身的存在是依自身本性而存在,在此意义上,道通为一。再次,就道与人的关系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给予人以形体、精神,也给予其价值:“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万物有道,人亦具备道,因而人在道的意义上与万物齐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和天地万物以气相通,“通天下一气”,随宇宙演化而变化无常:“种有几,得水则为继……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因而人的生死只是气之聚散,万物流转,往复不已:“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最后,就个体生命及其存在而言,人的生命与道息息相关,而人的存在据于道,也即自然,在此意义上,万物之间没有差别,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亦无差别,而人自身的存在与否也没有差别,因而生与死只是形式变化,“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是对《庄子》生死观的概括,生死只是对个体的形式变化的描述,是宇宙整体的演化中的一部分。因此,《庄子》及周秦道家文本中常用“出入”、“进出”“将迎”等描述生死过程,用“化”描述万物形态的流转,在《庄子大宗师》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巾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中,很大部分篇幅都在论述这种观点。通过对先秦思想家关于个体存在及其意义的回顾,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幵,首先是如何定义个体生命及其价值,儒、墨两家将个体存在置于伦理秩序之中加以定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也由生命价值以外的伦理价值所赋予,道家总体而言将生命视作道也即自然)的存在物,天地万物包括人以道为存在的根据,并以道的价值规定自身的价值,道法自然,人法道;其次是如何看待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的价值关联。在儒墨两家人道优先于天道,在道家则是天道优先于人道。儒墨两家强调规范的价值(群体价值和他者的价值,伦理价值优先于个体生命的价值,而道家强调自然的价值(自然世界和自然而然,个体生命与道相一致,以自身为存在的依据,亦以自身存在作为价值根源。就对生死的态度而言,儒墨两家将生死定义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并以伦理价值定义生命的价值,即以个体生命对于伦理道德的践行程度来衡量生与死的价值;道家则将生命定义为道的落实和具体化,道生万物,道亦生人,因而人依道而存在,因而贵生,亦与道共存,因而贵虚。而《庄子》在道论、道与物的关系和道与人的关系方面做了系统论述,主张以人的自然性定义人的生命属性,并将生命的价值定义为合乎自然的价值,也即合于道。通过对生死问题的问题核心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视角的差异是产生不同的生死观的根源。在《秋水》篇中,《庄子》指出了视角如何决定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评判: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在《庄子》看来,虽然万物就其自身而言是无差异的,然而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万物时,则会获得不同的观点,形成对于事物的不同评价。对于万物的观察有道、物、俗、差、功,趣等不同的视角和角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度,其中围绕着“贵贱”这一价值,有以道观之、以俗观之和以物观之三种主要的视角,“贵贱”原指财富的多寡(二字皆从“贝”,弓申为权力与地位的髙低,归结为个体生命的价值优劣。就三种视角本身而言,以物观之是以某物为中心而以他物为边缘的视角,是一种还未摆脱人的偏见的视角;以俗观之,则意味着不以万物自身去观察万物,而是凭借世俗的观点去观察万物。因此,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之下,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发生着改变,但这些视角本身却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以物观之而言,每个事物都以己为贵,而以他物为贱,照此则万物均有贵贱,也即是说,以物观之,则每个个体均以生为贵,以死为贱,以自身生命为贵,以他者生命为贱;就以俗观之而言,万物的贵贱不在万物自身,而在世俗世界,世俗世界的价值不断变迁,万物的贵贱也发生着相应改变,因而万物均可贵可贱,这就是说,观之以俗,则个生命的贵贱在不同社会等级、伦理地位甚至不同天然廪赋中各有不同,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生命价值也随之发生改变,时贵时贱。而从差、功、趣的视角而言,万物在是非和价值上甚至没有可比性,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评价也更加相对化。只有以道观之,以道观物才是对于万物如实的关照,以道观人才能得到对生命最真实的评价。在道的境界中,万物均按其本性而存在,即与道一样,按其自身而存在,并由自身规定自身的价值,生命自身的存在与消亡亦依据自然原则,生与死均遵循道(即自然)的规定,与道同在,流变不息。上述考察明晰了生死问题的问题核心和问题视角,就生死问题本身而言,正如本章起始所言,有生命才有生死,生命的价值决定着生死的价值,而生死又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呈现,又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本标准。按照上述三种视角,观之以物,则每个个体均以生为贵,以死为贱,以自身生命为贵,以他者生命为贱,相应的,任何有利于自身生存的事物价值均优于任何对生存有害的事物价值,任何不利于死\n的事物价值均优于任何有助于死的事物价值,即“乐生恶死”的观点;观之以俗,则个生命的贵贱在不同社会等级、伦理地位甚至不同天然廪赋中各有不同,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生命价值也随之发生改变,个体生命的价值在群体中被赋予,则群体的价值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由外在的标准所评定,即“死生由命”的观点,“命”指天命、时命和运命,因而死生有命、贵贱由命也意味着个体生命的价值在自身之外;《庄子》通过对“乐生恶死”和“死生由命”的观点的批评,指出因囿于偏狭的视角而对个体生命不合理的评价,并以其道论作为理论基础,观之以道,展开对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思考。生死问题的三重视角的逻辑关联在于:“乐生恶死”是对生死问题的质的规定,在其中,生与死呈现为简单的对立,并仅仅在自身之内构成全部价值的基石,可以说是与道无涉。“死生由命”的观点则超越了生死范畴自身,进入到其对立面亦即社会、文化所代表的关系之中,生死因为进入文化的视野从而服从于自身之外的规定性,并随着外在价值的变化而相应具有不同的价值,然而这个视角仍然没有达到真理,在于它仅仅是对“以物观之”视角的简单反对。“死生无变于己”的观点作为“以道观之”视角所达到的对生死问题的终极认识,包含着对前两重视角的总体超越。既避免了物的视角对生死问题中人的层面的忽视,又扬弃了俗的视角对生死问题的自然一面的背离。因此在道的视角中,生死问题才扬弃了最简单的规定和过度的人化这两重偏差,复归到道(自然)的本真的存在境界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生死问题直接的就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实践的修行,三重视角就无所依托,同时,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会直接反映到人在实践中取得何种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以及在更广的层面上形成社会文化中的生死态度。认识和实践两重维度的交织,是生死问题应有的面貌。为了使问题集中,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理论层面\n的考察,但生死问题的实践维度绝不应被忽略。三、生死问题直接的规定性:以物观之乐生恶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利与害常常被确立为首要的价值评判标准,直接与事物的价值好坏相关,“趋利避害”甚至被经验主义哲学家视作道德问题的讨论起点,并将对个体生命的维护和保全视为利害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如霍布斯),这也显示出世俗价值观的倾向:在事物的价值本身和人的趣向之间,事物的价值总是偏向事物向人所显现的价值。《庄子》同样注意到“利害”如何影响到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最大的利害莫过于生死,对于生死问题的困惑,常常扭曲人们对于事物自身价值的判断。在《庄子》看来,“乐生恶死”代表了世俗生活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基本观念: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上述批评集中于“形”上面,《庄子》这样定义“形”:“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在道与物的演化过程中,“形”之前为“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闲,谓之命。”,事物虽然没有形体,但己有阴阳二气之分,事物以气的形式流行,流行的气凝聚而成为物,并形成各自相异的独特形体,是为“形”,之后为“性”:“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在这一阶段,事物不但具有了形体,而且灌注了精神。人作为万物之一,通过对精神的修炼(而非形体),可以返于泰初,与道相合。也即是说,对于人而言,精神比形体更接近道,因而更能体现生命的本真性,而形体只是假借的形式,不具有生命本真的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意义。此处的“形”具体化为外在的身体感官,从《庄子》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乐生恶死”的观点产自于生者可以享受诸多善和追求更多的善,尤其是身体的善,这诸多的善都是以人的感知能力为前提,而死则剥夺了感知一切的可能,进而对各种善的追求和获得也不可能。所以,从形体出发,最大的利害莫过于生死,即以俗观之,以生为善,以死为恶,以拥有和保全甚至延长生命为善,以损害、失去生命为恶。“乐生恶死”的观点有两个前提,一是确证了自身的存在,二是对“乐生恶死”的评价有合理的说明,也即是说,何以存在是好的而死亡又是坏的,《庄子》认为这两个前提都值得怀疑。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确证自身存在的方式主要有理性的和经验的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于思维和存在何者为先,但对于此处的讨论而言,身体和心智都是我们拥有生命的前提,并且对于生命存在的确证,身体的感知能力和心智的观念一起构成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即“我们活着”这件事。但有意识的活动并不能保证我们关于自身存在知识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对于自身的存在所形成的观念也不一定正确,从柏拉图的“洞穴”说到笛卡尔的“恶魔”比喻,均指向了人的认识能力。《庄子》对认识能力同样有所怀疑:喘缺问乎王悅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拒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炬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庄子的质疑同时指向了事物和认识主体:事物是否可以被认知?主体是否可以认知事物?这种质疑不断引向极端,最终,《庄子》指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向了对自身存在的可靠性的怀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庸炬知吾所谓吾之乎?‘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梦,那就已经不在梦中了,甚至更高阶,而对于生死而言,生者不可能在生之外证明生,同样,死者不可能在死之外证明死。吊诡的《庄子》婉熟的运用梦与觉的比喻,成功运用与对我们存在的怀疑中,因此,在《庄子》看来,信服的说明主体存在并确实拥有生命,并非易事。那么,我们是否有知晓死亡的能力呢?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将死亡包含于生命之中,有生命才有死亡,不知生则更不知死,维特根斯坦与孔子一样罕言生死,他的理由则是:“死亡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事件,我们不可能活着经历死亡。”,这是对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鸡鲁的回应,伊壁鸡鲁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死亡啥也不是,因为一切好与坏都在于感觉,而死亡是感觉的丧失。……因此,死亡这种最可怕的恶,对于我们来说啥也不是,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到来,而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巳经不存在。所以无论对活人还是对死人,死亡都不算什么,因为活人没有它而死者不再存在。伊壁鸡鲁的论证基于“好或坏意味着是否有感觉”,死之恶不在于让人产生可怕的感觉,而在于一切感觉的丧失,即死剥夺了感知的可能性。因此,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回应的,既然生命应当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那么死亡就不应包含于生命之中,因为在世时不可能有“死亡”的感觉,正如《列子》“祀人忧天”寓言中“生不知死,死不知生”的观点: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伊壁鸡鲁、卢克莱修等,包利民等译,《自然与快乐:伊壁鸡鲁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n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庄子》在上述认识能力的质疑中成功运用了生死相隔所导致的生死不能相互确证,并且以寓言的方式,《庄子》指出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的不合理: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当豢,而后悔其泣也。也即是说,以生为乐、以死为恶的价值判定,均没有明确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因为我们对于生前和死后的知识是断裂的,那么正如丽之姬的例子所表达的,这种价值判断甚至有可能是相反的。与《庄子》的回应相类似,伊壁鸡鲁思想的继承者卢克莱修也指出:对于我们死不算一回事,和我们也毫无半点关系……灾祸能降落于其身上的那个人,必须本人是在那里,在那个时候。但死亡已经取消了这种可能……所以应该承认死不值得我们害怕,对于那不再存在的人痛苦也全不存在,正如他从来就未被生出来一样那么,既然“恶死”是没必要的,那么,“乐生”是否就是更为可取的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们“乐生”的理由在于生者可以享受诸多善和追求更多的善,尤其是身体的善,这诸多的善都以人的感知能力为前提,而死则剥夺了感知一切的可能,进而对各种善的追求和获得也不可能。《庄子》则继承了寡欲说,认为身体的善的追求反而对生命有害: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傻中颖;四曰五味油口,使口厉爽;五曰趣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年,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卢克莱修,方书春译,《物性论》,商务印书馆,年,页。\n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在“點髅寓言”中,被认为是在世时的种种善,反而被死者“點髅”视为生之累。“乐生”的另一层含义是长生,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说死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那么,是否人活得足够长就是好的呢?《庄子》从宇宙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一生放在整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时间,而人的存在也极其撤小:鹤鹤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因此,有意追求长生不死,似乎是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狭溢的视角,将生命视作某种拥有,而如果将视野放到流变不已的宇宙演化中,人的生命十分短暂和无常:夫藏舟于塾,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然而这只是《庄子》论辩的策略,并非其真正目的,《庄子》的真正目的在于遵循道的规定来定义生命,并给予合于道的评价。若观之以道,则并不存在独立于天地的个体生命,只是天地(道)所假借的形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纟兑也。相应的,若观之以道,则个体生命不应以私情遮蔽人的本然存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形态,不以世俗的好恶来定义生命的价值,《庄子》与惠施的论辩中,《庄子》提出了“人固无情”的命题: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施以物观之,将人定义为有情的存在,即有好恶、有私情的存在,以拥有、延长生命为人的特质,而《庄子》则以道观之,将人定义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的存在,道无好恶之分,人亦不应有好恶之分,道无私情,人亦不应有私情,即不以己为中心而以他物为边缘的视角产生的偏见。“人故无情”进一步解释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一方面,不应以世俗的标准定义生命,即将生命等同于形体的生命,然而性比形更能体现生命的本质,也即精神生命重于形体生命,并且,对形体生命的注重不但没有根据,反而有损于精神的生命:“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另一方面,与其有意追求长生不死,不如顺其自然。因此,“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的视角的偏狭之处就在于拘泥自我的视角,导致“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的结果。然而人的存在不同于道的存在,道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道的本质是虚无,道不在时间序列之中,因而不生不灭,不在空间范围之内,因而不能被语言所描述,道的虚无性也体现着无限性;而人存在于时空之中,有形体、语言等诸多感性特点,而人所具备的存在者的特性正是其有限性的体现,其中死亡便是最大的有限性,而伴随着死亡而来的是生存意义的危机,因为死亡似乎摧毁着生命的一切意义:人生天地之间,若白购之过郄,忽然而巳。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1当我们思考死亡时,为何会将其与生命的意义相联系,并且将死亡直接视作生命意义的丧失?分析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认为,当人们思考生命时,存在外部和内部两种分离的视角,外部的视角以宇宙和整个世界作为思考的背景,从中得出的答案是:人的生命是偶然的和不重要的,这似乎是一个客观的观点,而内部的视角则是思维的“自我”审视自身的存在,得出的答案是必然的和重要的,这似乎是个主观的观点:从足够遥远的外部来看,我的出生似乎是偶然的,我的生命似乎是盲目的,而且我的死亡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内部来看,简直不能想象我从未出生过,我的生命似乎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的死亡似乎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尽管这两种观点明显的属于一个人(若非如此,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但他们相当独立的发挥着作用,以至于每一种观点对另一种观点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一种暂时被忘棹的特性。因此,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生死的两种观点也不同,客观的观点将自我与其他生命共同视为偶然的和不重要的,而主观的观点则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当下的存在便己证明我的存在是必然的和重要的。这两种观点是冲突的,并且两种冲突的观点同时交叠在人身上,在直面生死之时,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凸现出来。《庄子》在批评墨翟“节用”和“兼爱”两种理论之间的不兼容时,便指出这一冲突: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是对两种视角相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托马斯内格尔著,贾可春译,《本然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冲突的概括。按照托马斯内格尔的两种视角,《庄子》尽管从外部视角出发,以完整的宇宙论解释道、物与人的关系,对生命和生死有着客观的观点,但《庄子》却不能完全放弃内部视角,思考本身即内部视角的展幵,这就意味着人类自我超越的内在意识始终存在,并使得两种视角冲突的并存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死,那么生命的意义问题也不会产生,正是死亡将生命的意义问题照进现实,摆在眼前。而正是“必死”这一事实迫使人类去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死亡是否真正摧毁着生命的一切意义,而生命的本真意义又在何处,以及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庄子》关注到个体生命在时空序列中的存在的短暂、无常与对意义的困惑。在足够长远的视野下,个体生命也越发溉小,“芒荀”之感既表达了个体生命在混纯宇宙的对道的体验,也表达了在混纯宇宙中的不确定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西方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和托马斯内格尔将这种“芒药”感称为“荒诞感”。内格尔认为,荒诞感的产生源自人类思想中超越自身的能力:荒谬是我们身上最具人性的事情之一:是我们的最高级和最有趣的特点的表现。像认识论中的怀疑论那样,荒谬是可能的,知识因为我们具有某种洞察力:在思想中超越自身的能力。但是他紧接着认为,荒谬感的存在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荒谬感是一种感知我们的真实处境的方式(即使这个处境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丨丨。(译文参考自程炼《伦理学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n感知发生之前并不荒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憎恶或逃避它呢?就像引起认识论的怀疑论的能力一样,荒谬是由理解我们人类局限性的能力产生的。它不是一件苦恼的事情,除非我们把它弄成这样。它也不必唤起一种让我们感到勇敢或自豪的、对命运的挑衅式的蔑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即使在私下做,也露出了鉴别不出这种处境在宇宙中并不重要的马脚。如果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没有任何了理由相信任何事情是有所谓的,那么这也是无所谓的,而我们可以讽刺性地而不是英勇地或是绝望地去过我们的荒谬生活。而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揭示出人类理性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他称之为“理念对生活的欺骗”,在加缪看来,一方面,人类有自己的热情追求,可是现实世界对人类的热情不作任何反应,它不在乎人类是如何选择的:“荒谬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在《庄子》那里,人类理性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也即天道与人道的冲突,天道是自然的,人道是非自然的,是人的存在形态的延伸: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天道与人道的冲突集中在无为与有为,即是否遵循自然本性。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天道与人道何者为先,《庄子》以天道为主,以人道为臣,天道优先于人道,而加谬则更重视人的自由即选择的能力。对于生命的意义无非有三种来源:个体选择产生、外在世界给予,个体与外在世界共同创造产生,其中前两种来源在逻辑上互斥,也即个体生命的意义若不是来源于个体选择,便是由外在世界所给予,而第三种来源在逻辑上兼容,即生命的意义既要求个体具备自由的选择。(译文参考自程炼《伦理学关键词》,(译文参考自程炼《伦理学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法】阿尔贝加谬著,沈志明译,《西西弗神话》,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丨),上海译文出版社,年,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能力,也要以外在世界作为条件,二者共同创造意义。加缪选择了第一种,《西西弗神话》的主题便是个体对于命运的反抗。加缪思想的合理之处在于:有选择本身即是生命有意义的前提,有选择意味着未被决定,从而可以说,使生命具有意义的一个前提是个体生命需要有选择的能力,也即自身生命的贵贱至少要与自身相关。所以,既然生命的意义需要与自身相关,那么第二种来源便不能成立,也即生命的意义由外在世界给予,即《庄子》所批评的“以俗观之”得出的“贵贱不在己”结论。四、生死问题非“物”的视角:以俗观之死生有命观之以俗,则贵贱不在己,而在于世俗世界。世俗世界由一套社会等级、伦理关系和观念所建构而成,以人的思想、语言来运作,有着是非、名实、荣辱、贵贱等一系列事实和价值评判标准,因而世俗世界建构的原则依据人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世俗世界不是自然的世界,而是非自然的世界,因而非自然的世界也非道的世界。世俗世界不是自然的世界,因而遵循人道而非天道。对于《庄子》而言,以儒墨为代表的仁义学说是典型的人道,因而儒墨思想对于生命及其价值的视角也即观之以俗的视角。具体说来,观之以俗,即借助人所具备的语言、思想和知识来描述道,描述和评价事物自身。以俗观之,也就意味着从“物”的视角走向其对立面,以人化社会价值来看待生死问题,因而是对“物”简单否定,抽离其自然的因素,强调其人化的层面。的然而道的本性是虚无,道不在时空范围之中,因而不能被描述,亦不能被评价:“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而以人的知识和语言去描述和评价道,无疑是对道的损害:“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荣华”。人若要知道和得道,并非以其聪明才智去辨析和言说道,也即观之以“俗”,而是通过观察人自身的本性而体悟道,也即观之以“道”:“吾所谓减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巳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巳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巳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巳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观之以俗的视角对于生命的价值也有不同的观点,以俗观之,事物的贵贱不在事物自身,而在自身之外,也即世俗世界,在世俗世界,不但命由天定:“死生存亡,穷运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而且死生由命,不可改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这与事物自身相悼,因为万物都有道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因而万物均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事物的价值由自身决定。因此,贵贱不在己所导致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被其他价值所挑战甚至取代。正如鲁侯养鸟和伯乐相马的寓言所表达的观点,“以己养养鸟,非以鸟养养鸟”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每个个体生命均有各自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并且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之分;另一方面,如果以他物的价值强加于事物自身,则导致事物自身的价值受损。《庄子》并非简单的述说故事,寓言所指向的是儒墨所代表的仁义学说和世俗世界的伦常秩序,因为在世俗世界中,评判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与个体自身,而在于外在的伦理价值,即贵贱。对伦理价值排在生命价值之先的的批评中,《庄子》思考更加深入,对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只是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正如迷失方向一样,只是小惑,而更大的危险存在于盲目的定义生命的意义,以生命的价值换取生命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之外的其他价值,这种伤害导致的结果甚于前者,也即“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的观点: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拜利,士则以身掩名,大夫则以身家,圣人则以身残天下。《庄子》将生命的绝对价值置于首位,认为以生命的价值去换取仁义等伦理价值有悼于人的自然之性,“以物易性”的危险之处更在于:《庄子》指出了许多伦理价值不但没有人性基础,甚至对人构成损害: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淘,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藤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妬之非乎!天下尽鴻也。彼其所拘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鴻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贵贱在世俗世界之中不仅代表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优劣,还代表了政治权力的多寡,《庄子》对于贵贱之辩的政治批评深化为哲学的创造,表现在对于世俗世界的认识和价值的判断之中,《庄子》及其道家哲学的产生,正是在反对儒家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之中展开,因此,《庄子》哲学有着政治批评与哲学创造双重意蕴,二者互为表里。围绕着“是非”、“有用无用”、“贵贱”、“荣辱”等主题,《庄子》将批评延伸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层面,并且“是非”之辩的真正目的不在判定真伪,而是对伦理价值的挑战:就认识层面而言,作为真值判定的是非,既有互斥的一面,也有互相证成的一面,然而当彼此固守于自己的是非标准并且试图说服不同于自己的是非标准之时,作为真值判定的“是非”本身便失去了判定的能力: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高瑞泉,《论庄子物无贵贱”说之双重意蕴》,《社会科学》年第期。\n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麒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倶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通过“是非”之辩的展幵,《庄子》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达到“是非莫辩,而照之于天”: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就价值层面而言,不同的价值评定者之间也有不同的标准,彼此之间亦有差异,因此不能一而论之,但是《庄子》不停留于不同价值的差异之间,而是进一步指向了主体将自我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他者导致的淆乱局面,以及对儒家所代表的仁义学说的不满: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倫栗徇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围绕着“贵贱”之辩,在带有政治抗议的文字中,《庄子》批评了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伦理等级和价值标准,最典型者莫过于君子小人之分: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子君子,人之小人。世俗世界对于个体价值的评判,始终在个体自身之外,世俗埋界不断变迁,万物的贵贱也发生着相应改变,因而万物均可贵可贱,这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是说,观之以俗,则个体生命的贵贱在不同社会等级、伦理地位甚至不同天然廪赋中各有不同,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生命价值也随之发生改变,时贵时贱: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完桀之行,贵贱有时,未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默默乎河北,汝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所以就个体生命的意义来源上说,外在世界给予其价值的同时,个体丧失了自身的价值。所以《庄子》宁愿放弃世俗的价值,而选择“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例如“持竿不顾“的寓言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庄子》文本的多处出现了儒家的代表孔丘,《庄子》将其描述为潜心求道者,受道家思想指引而最终成为得道者。在一段对话中,《庄子》借孔丘的对话讨论了天道和人道关于死亡的不同理解:莫然有闲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巳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临尸而歌的得道者与事之以礼的子贡表现出了对于死亡截然不同的态度,道家对死亡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而儒家无疑是消极的。对于死亡的不同理解,孔丘将得道者描述为游方外者,而将自己描述为游方内者: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尚建飞,《寓言化的孔子形象与庄子哲学主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在《庄子》的论述中,孔丘持人道,而得道者持天道,天道与人道不同,“内外不相及”,不同之处在于得道者对于生命和生死的理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悬)庞,以死为决n遗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悅;芒然仿惶乎尘话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正如前面所论及,道、物、人的演化过程经历了由无(太初)、一(有)、德(物、命(分、形(气、性(精神),再向初(无)的循环,一方面是从道到人的展幵,另一方面是从人到道的回归。人作为万物之一,通过对精神的修炼(而非形体),可以返于泰初,与道相合。也即是说,对于人而言,精神比形体更接近道,因而更能体现生命的本真性,而形体只是假借的形式,不具有生命本真的意义。因而得道者将人道所重视的形体生命看作“附赘悬抚”,而将形体生命的死亡视作“决肤淸痈”,而人道与天道不同,人道与天道对立,因而人道对于生死的理解与天道相反,天道是自然的,人道则是人为的,甚至是虚伪的:“愦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在天道的视野里,道生养万物,生养人的生命,而在人道的视野里,道(也即天)夺人的生命: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观之以俗,则人为天之“戮民”,观之以道,则“视丧其足犹遗土”,将形体生命的消亡等同于土块烂在土地上。在天道的视野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即是说,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以气相通,所以虽然形体生命的形式发生变化,却与天地同在,而在人道的视野里,个体生命有其有限的感性特征,正如形体有死,世俗世界将形体有死等同于生命的丧失。在另一段对话中,孔丘以得道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的语言论述了天道与人道对于死亡的不同理解: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孔丘“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的观点得自于老子的教诲(对话见于《庄子天运》),即“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作为得道者的孔丘观之以道,不执著于形体的生命,也不以形体论生命,而是“游心乎德之和”。“心”即人的真实生命的主宰,是精神的寓所,因而《庄子》称之为“天府”,因此,对于人而言,观之以道,也即观之以心: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道的本性是虚无,“唯道集虚”,因而心作为道的寓所,唯有保持虚空和专一,才能使道显现出来:“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将心比喻为明镜和止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宁静的心灵才是人的心灵的本性,也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观之以道,即如实的照见万物。而生命的本真意义就在于保持宁静、虚空的心灵,与道同在: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括淡寂漠无为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此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五、生死问题的本真维度:以道观之死生无变于己只有以道观物才是对于万物如实的关照,以道观人才是对生命最真实的评价。在道的视角中,万物均按其本性而存在,即与道一样,按其自身本性而存在,并由自身规定自身的价值,生命自身的存在与消亡亦依据自然原则,生与死遵循道(即自然)的规定,与道同在,流变不息。以道观之,是对“物”和“非物”(人化、俗)两重视角的超越,分别克服了两者的弊端,既避免了生命意义的落空,又纠正了人道对天道的落实和背离,从而在复归于自然的过程中达到了对生死问题的真正认识。首先,观之以道,死亡是向道的回归,即反其真。就道与万物的关系而言,作为本源和开端的道,道自身作为自身的根据:“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因自本自根的道即是自然本身,是天地万物的根据,也是人的根源。道、物、人的演化过程中先是从无(太初)到有,有再向初(无)的循环,一方面是从道到人的展开,另一方面是从人到道的回归。虽然道不同于万物,自身是虚无,但同时道又生养万物,因而又存在于万物之中,因而万物都具备道的特质,不仅不同的事物皆有道,而且相互对立的事物也有道,不仅高级的事物有道,低级的事物也有道:“故为是举慈与楹,厉与西施,恢憶橘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就道与人的关系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给予人以形体、精神,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也给予其价值:“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万物有道,人亦具备道,因而人在道的意义上与万物齐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和天地万物以气相通,“通天下一气”,随宇宙演化而变化无常:“种有几,得水则为继……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因而人的生死只是气之聚散,万物流转,往复不己:“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人的生命与道息息相关,而人的存在据于道,也即自然,在此意义上,万物之间没有差别,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亦无差别,而人自身的存在与否也没有差别,因而生与死只是形式变化,“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因此,死亡只是向道的回归:“解其天瞍,堕其天(衣),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在鼓盆而歌的寓言中,《庄子》全面的表达了上述观点: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如果追溯个体生命的源头,则要追溯到芒芴而无生死的道,而个体生命获得的形体只是“气变”的结果,因而生与死只是短暂而偶然的过程。因此,在老聃之死的寓言中,《庄子》得出了“安时处顺”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的结论: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悬)解。其次,观之以道,死生无变于己。尽管人有道作为自身根据,但是人终宄存在于世俗世界,世俗的世界也即有限的世界。世俗世界的有限性表现在人在世俗世界的有限性和世俗世界对于人的有限性两个层面。一方面,世俗世界由一套社会等级、伦理关系和观念所建构而成,以人的思想、语言来运作,有着是非、名实、荣辱、贵贱等一系列事实和价值评判标准,因而世俗世界建构的原则依据人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世俗世界不是自然的世界,而是非自然的世界,因而非自然的世界也非道的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世俗世界的有限性阻碍了人本真的存在方式;而作为世俗世界的人,有其存在者的感性特征,如形体、语言甚至社会性,世俗世界的知识、语言和形体成为人通达道的壁垒,因而存在于世俗世界的人有着形体有死、是非有分和贵贱有序三层有限性。因此,世俗世界的人若要得道,也即认识和成就自身,则需要突破世俗世界的视角,而观之以道。宁静和虚空是道的本性,也是人的自然本性,要达到个体的虚无和宁静,需要通过心斋和坐忘的功夫实现,包括了若干过程: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櫻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首先是外天下。将世俗世界置之度外;第二,外物,依据道而消解物与我的差异;第三,外生,不执著于自身的形体生命;第四,朝彻,通过物我两忘而洞彻对道的认识;第五,见独,洞见道的通与一;第六,无古今,消解个体存在的时间之维度;第七,入于不死不生,人得道,按照道的方式理解自身,与道同在。那么,个体如何以道的方式存在于世俗世界之中。《庄子》将个体以道的方式生存的状态称之为“游”。首先,游是人在世俗世界中自由的游戏,而非彷徨无措的游荡。“游”的思想在《庄子》文本中多有出现,历来被视作《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游”被理解为“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也被理解为“消极混世”。通过上述考察,《庄子》所表现的是个体的价值在外在世界中得以实现,个体与外在世界的依存关系,在开篇《逍遥游》中,便表达了这一思想: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鲲鹏的自由状态实质上是个体与世俗世界交互的结果。也即是说,作为世俗世界的生命个体,世俗世界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反之,如果没有世俗世界作为背景和存在的基础,个体生命无法独立存在。《庄子》将人与世俗世界的关系比喻作鱼和水的关系,以忘的方式否定自身与世俗世界的关系:“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据郭象《注》:“死生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故谓之朝彻也。”据成玄英《疏》:“夫至道凝然,妙绝言象,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睹斯胜境,谓之见独。故老经云寂寞而不改。”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文集》(第四卷,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页。哲学研宄编辑部编,《庄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年。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是因为,对于人而言,世俗世界与道一起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忘”并非采用极端的现实方式回避问题,而是获得个体与世俗世界的平衡与协调,正如足履相适合,腰与带相适合:“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然而忘本身只是通达道的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得道:“莶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因此,否定忘的行为本身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逍遥境界:“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因此,人在不断的否定自身的现实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也在向道不断接近,直到物我两相忘时,人的存在方式与道重合:“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因此,游是人道合一、天人合一的状态。《庄子》将这种得道者称为真人。真人尽管不同于世俗之人,却也在世俗世界之中,《庄子》将其分为五类,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道引之士,这五类人尚未得道,也即尚未成为真人,因而无法超脱生死。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依道而行。道无为而无不为,因而无为而无不有: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所以,作为得道者的真人,不借助于人为的手段(有待),而是无为而游(无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以,作为得道者的真人一定是超脱生死之人,真人不但超脱生死,而且超然物外,乘物以游,真人超出了世俗世界的时空之限,游于无穷: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絛然而往,脩然而来而巳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也正是在上述逍遥游的境界中,真人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一方面,对时空之限的突破使生命个体的自由精神得以解放,另一方面,道对于人的本真意义也全面展开。结论实质上,虽然在个体不断否定自身在世俗世界的有限性的过程中,《庄子》经历了柏拉图式的精神转向,然而对于世俗世界的人而言,作为事实的有限性是无法避免的,价值世界才是可能的归宿。人虽然身处事实世界,人却可以观,也即跳出自身视域认识外在世界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可以观之以道。对于人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世界呈现给人的方式,怀特海这样描述道:有限性是存在的,除非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无限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对照来源于下列基本的形而上真理,即每一种存在物都包含着对某种由各种视角构成的无限阵列(其中每一个视角都表迗这种存在物的一个有限特征,不过任何一个有限的视角,都不能使一种存在物摆脱其与总体性(的本质联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n系,无限的背景总是作为未经分析的理由而存在一一即这种存在物的有限视角,为什么会具有它实际上所具有的这种特定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正是有限性的视角将我们一步步引向生死问题,在直面生死之时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并且,真正关注生命意义的是人的精神属性,所以生命的本真意义不在于个体生命的存在过程和存在形式,而是如何看待和评价生命。在事实层面人固有一死,而在价值层面,不朽是存在的,如古人有“立德”“立言,,“立功,,三种不朽的形式,这些形式均属于价值世界。对于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关系,怀特海将“不朽”和“必死”视作宇宙的两面,分属活动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将“必死”的事实看作活动的世界中的创造过程,活动的世界也即创新的世界,而价值世界则强调持续,是创造过程的目标,价值要保持它自己的不朽,就需要处在持续的激励和创造过程中:“价值世界和行动世界这两者是在宇宙的生命之中被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一来,价值所具有的不朽因素便进入了与时间性事实有关的、积极的创造过程之中。”这种过程在人的视域里表现为:“与事实有关的各种转瞬即逝的机遇,都具有把它们自身统一成为各种由人格同一性构成的系列的趋势”。怀特海的论述更清晰的展现了《庄子》关于“道通为一”观点:在活动的世界中,生生不息的宇宙依据行之而成的道,处在永恒不息的流变之中,万物有成有毁,人有生有死,个体与宇宙的关系是必然关系,也即宇宙是作为个体存在无法脱离的背景,而万物作为宇宙的具体内容。然而在价值的世界中,个体将生死理解为个体在宇宙演化中可能性的展开,可能性的展开以宇宙演化作为背景,从流变的事实世界向恒常不变的价值世界的回归。在人的有限性和价值世界的不朽性之间,是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者所从事的历史性的创造活动,亦即实践。实践是生死问题在时间中怀特海,艾彦译,《论不朽》,《世界哲学》,年第期。英】怀特海,艾彦译,《论不朽》,《世界哲学》,年第期。\n的本真的自我阐明。我们对生死问题的认识离不开在实践中不断地以价值世界的不朽来客服个体生存的有限,因此如果忽视了实践的维度,生死问题将因为其时间性的丧失,而变成一个僵死的形上问题。而以道观之本身即要求对生死问题按其本性来看待,而不是停留在某一种固定的人化的看法之中(俗)。因此,实践维度作为基于自然向人文的创造,是以道观之的境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考察,对于生死问题,离不开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不同与科学描述,作为哲学问题的生死更关注价值的层面,因此,如何评价生命和生死比生命和生死的概念更重要。《庄子》透过生死来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从天人、物我和群己三个范畴下,展幵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于按照自然本性生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也应自然而然,生命的本真意义来源于天与人的共融。\n参考文献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研宄所中国哲学史研宄室,《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北京:中华书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华书局,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三卷、第四卷),李维武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崔大华,《庄学研宄: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池田知久,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彭富春,《论中国的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毕治国,《死亡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柏拉图著,杨绛译,《斐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n19.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著,包利民等译,《自然与快乐:伊壁鸡鲁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卢克莱修,方书春译,《物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托马斯内格尔,贾可春译,《本然的观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三辑)“世界庄子研宄动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辑)“庄子研宄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n致谢论文从开题到定稿,并不顺利,哲学论文的写作充满挑战。之前所受的古典学训练与哲学研宄有很大差别,对于从故纸堆里走出来的我而言尚未入门,在导师的建议下,我选择精读一两本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如《人类理智论》、《第一哲学沉思集》和英文版《尼各马可伦理学》,渐渐对哲学思辨和论说方式有了宽泛的认识,之后对伦理学问题产生兴趣,在阅读大量伦理学论著的过程中,对于哲学问题的把握和论证有了初步了解。正如导师所言,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学习如何做研究的过程,而非正式的研宄过程。在写作论文期间,我反复阅读了《庄子》原文,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再从零碎的问题心得出发,渐渐深入思考,对论文进行反复修正,尽管如此,论文的结构和深度还是亟待完善。从祁连山到云梦泽,再到上海滩,始于江源,泊于江汉,止于江海,游学七载,恍如一梦。回首时,一个青涩纯朴的山里娃走过了他的家族所走过的最长的求学之路。至此,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高瑞泉教授的指导和鼓励,同时向刘梁剑、陈乔见、尚建飞诸位老师在写作和学习过程中的无私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此外,感谢父母、同窗、挚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