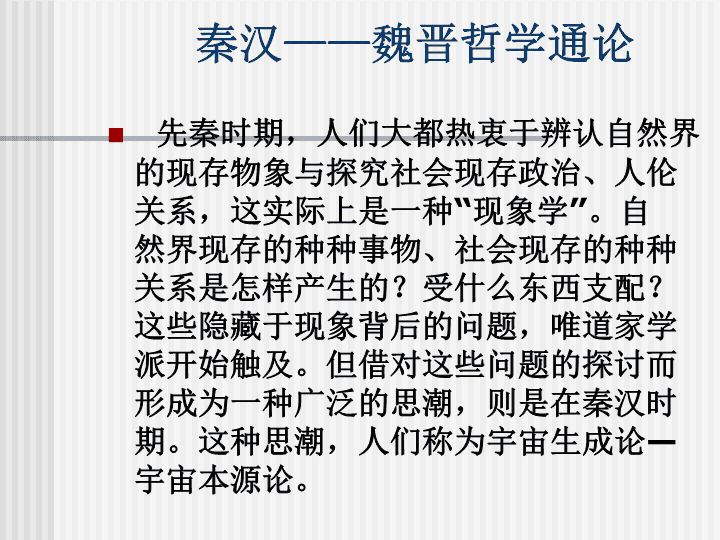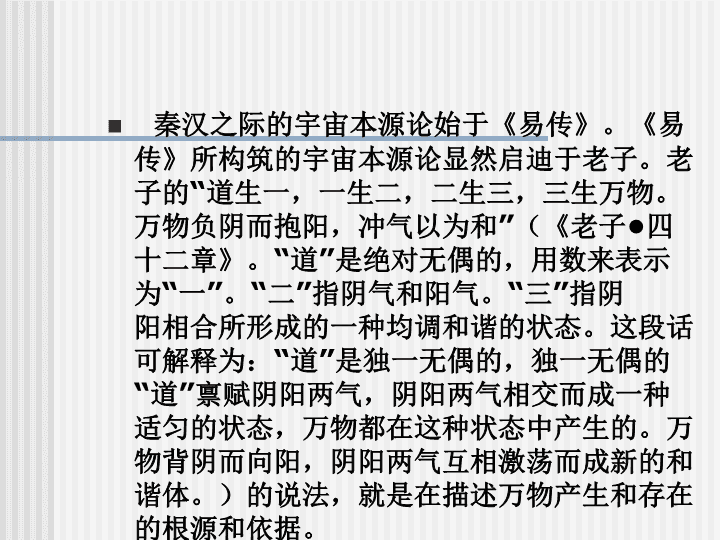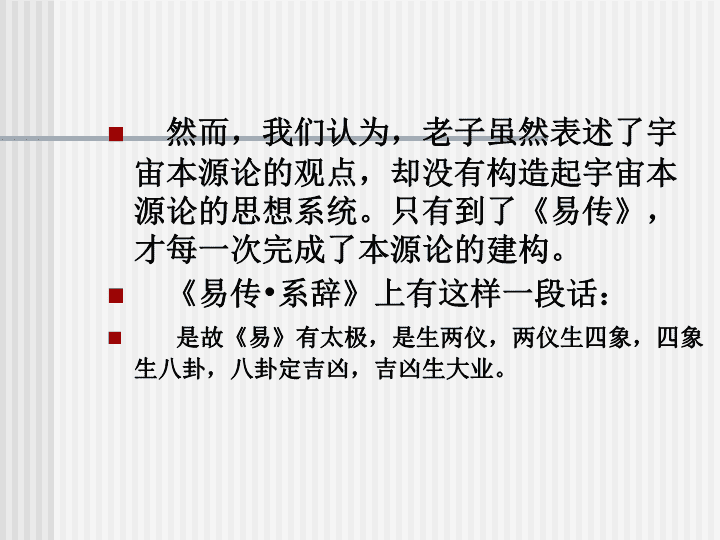- 147.50 K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秦汉——魏晋哲学通论先秦时期,人们大都热衷于辨认自然界的现存物象与探究社会现存政治、人伦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学”。自然界现存的种种事物、社会现存的种种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受什么东西支配?这些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问题,唯道家学派开始触及。但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而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则是在秦汉时期。这种思潮,人们称为宇宙生成论—宇宙本源论。\n秦汉之际的宇宙本源论始于《易传》。《易传》所构筑的宇宙本源论显然启迪于老子。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道”是绝对无偶的,用数来表示为“一”。“二”指阴气和阳气。“三”指阴阳相合所形成的一种均调和谐的状态。这段话可解释为:“道”是独一无偶的,独一无偶的“道”禀赋阴阳两气,阴阳两气相交而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都在这种状态中产生的。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的说法,就是在描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依据。\n然而,我们认为,老子虽然表述了宇宙本源论的观点,却没有构造起宇宙本源论的思想系统。只有到了《易传》,才每一次完成了本源论的建构。《易传•系辞》上有这样一段话: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n在这里,人们虽对“太极”的理解各异,但这段话的思想还是很明确的,它描述的是由“太极”而阴阳二气(两仪),由阴阳二气而春夏秋冬(四象),由春夏秋冬四时而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物(八卦),由这八物而产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很明显,我们从这种论说中可以找到老子的影子。但是,《易传》的整个思想旨归与老子极不相同:1)老子的产生万物的“道”是“与物反”的,要认识和体察“道”必须否定万物、涤除感知以复归于无;\n2)《易传》虽然也是为万物的存在寻找本源和依据,但是,作为万物存在本源和依据的“太极”与其所生的万物却具有类的同一性与通感性。《易传•序卦》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n这里,由天地而万物,由万物而男女,由男女而夫妇子女君臣等,这是一种正面的、顺向的“化生”关系。在这种“化生”关系中,生者与被生者是互相确认、互相蕴含,而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否弃的。但尽管《易传》的宇宙本源论思想已初具规模,却有几个理论上难题无法解决:首先,那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太极”怎么能够化生纷繁杂呈的万物呢?\n其次,按照《易传》的思想,一方面,性质相同的事物可以同类相感,性质相反的事物可以异类相荡,由此使整个世界生生不已、变化无穷;但另一方面,《易传》又称,由阴阳二仪交感所生的万物又呈现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的阴阳定位不变性,这不是很矛盾吗?\n再次,同类事物何以能够神妙地相互感应?异类事物何以能够相互推荡?这些难题,《易传》本身是通过将“太极”神化来解决的。在《易传》看来,正因为“太极”神秘莫测,“无方无体”,它才能造成这样一个既变化无穷而又井然有序的世界,万事万物的性质、样态及变化法则都是这神奇的“太极”的体现。由此,《易传》的宇宙本源论最终堕入了神学的迷途。\n《易传》开出的宇宙本源论思想,规定了两汉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不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道教的“神仙论”等具有多少差别,从理论上看,它们都根自于《易传》的理论系统,它们为克服《易传》引发的难题而各自建立的理论,又分别陷进了不同的理论缺陷之中: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主张“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n将宇宙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无形而可感的“气”,从而排除了那个既无确定性质又神妙无方的“太极”,似乎避免了《易传》的神学思辨,增加了理论的经验性和科学性。但是,由于董仲舒与《易传》同样地认为来自同一本源的宇宙万物都具有质的共同性与可通感性,他仍然不得不借助神的创造力才能解释万物的这种神奇的关系。在董仲舒试图依他所确认的宇宙万物的同类相感原则去广泛地说明自然界与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时,他的思想甚至不能不流为谶纬迷信。\n道教是产生于两汉之际的一种宗教,亦主元气本源论—宇宙生成论。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就称: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太平经合校》)既然万物由自然元气所生,那么,万物就是实在的,万物的生灭变化也是自然的、客观的。依此,道教的本源论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道教思想家由此却推出了“神仙论”。\n在道教思想家看来,化生于同一种元气的物既然具有类的共同性与相通性,那么由气化生的人通过练精保气的功夫修成神仙、回归本源也应当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样,道教的“神仙论”同样获得了理论上的基础。秦汉思想家通过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而建立起来的宇宙本源论—宇宙生成论,在为万物确立其存在的最终根源,将万物纳入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系统方面,的确比先秦大多数思想家来得深刻。\n但是,由于这种宇宙本源论给出的本源是外在于万物,并从万物之先、之上来规定万物的性质、样式和发展规律的,它本身就必然被神秘化、绝对化为一个不生不灭、妙应无方的至上实体。依照这一理论,万物的性质、特点和生灭变化不能由它本身予以说明,而只能通过对本源的回溯与回归才能获得完满的解释。这样,无论秦汉宇宙本源论具有多少合理性,它走向神学和道教在其理论上都是必然的。加之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推崇,这一演变过程就更为迅速。\n秦汉宇宙本源论造成的这种理论困境和现实迷误,在汉代就有古文经学派如王充(公元27—96年)等人起来反对。王充试图以其“效验论”突破秦汉宇宙本源论的局限,但是,由于他本人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突破宇宙本源论的框架,致使他在反对《易传》、董仲舒和道教随意运用同类通感的观点解释事物的存在与变化时,也不能从具体事物本身探讨其存在的根据,\n并认识其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而只能将这一切诉诸于外在于事物的、不可捉摸的偶然因素,从而陷入了命定论。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将外在于事物的至高无上的本源内置于事物自身。在贬斥儒家伦理道德和谶纬神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魏晋玄学做到了这一步。魏晋玄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秦汉宇宙本源论的思维框架。一般认为,魏晋玄学始于何晏(公元193?—249年)与王弼(公元226—249年)的“贵无”论虽然也主张万物由“无”而存在,但是,它与秦汉宇宙本源论却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n“贵无”论已不象秦汉时宇宙本源论那样,将本源置于万物之先、之上的位置,使它变成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并能主宰和支配万物的至上实体(无论这实体是“道”、“太极”,还是“气”),而是将万物存在的根据放置于万物自身之内,使它变成一个从事物内部给事物以规定性的内在根据或本体,它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也变成了“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n王弼所谓“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彖传注》)与“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等论说所申述的就是这种思想。这种从万物自身内部寻找其存在根据的理论就是本体论(或本质论)。这种理论克服了秦汉宇宙本源论产生的理论困难:\n1)既然生成、主宰万物的本源已不复存在,那么,秦汉宇宙本源论所导致的那种宗教与神学就失去了基础与前提;2)既然万物只能在自身内获得规定性,那么,就没有什么决定事物本质、特性的神秘莫测的偶然因素。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出现,实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大飞跃。\n但是,这不等于说何晏、王弼的“贵无”论没有理论缺陷。虽然“贵无”论实现了本体论的转向,但它并不能正确地对待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本体(本质)与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它在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同时,又极力贬低和剥落后者的意义、作用而抬高和提升前者的地位,甚至达到了“得鱼忘筌”、“得意忘象”的地步。这样,“贵无”论就很容易走向佛教般若学,因为它们两者在如下几方面都具有一致性:\n1)“贵无”论的本体“道”被极端地抽象化、绝对化以后,就成了毫无规定性的、空洞的“无”,而按当时人们对般若学的理解,作为绝对实体的真如也是超绝形象的“空”、“无”;2)“贵无”论的本体“无”与般若学的实体真如一样都是不生不灭、常住不变的;3)“贵无”论的本体“无”与般若学的实体真如都必须在否弃经验世界的基础上才能体认。\n事实上,般若学在魏晋之际得以流行,甚至发展出了“本无”一宗,也的确大大得力于玄学“贵无”论准备的理论土壤,许多般若学家就是直接用玄学“贵无”论的本体“无”来理解、解释“真如”这一实体的。何晏、王弼以后,魏晋玄学本体论演变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形态——郭象(公元252—312年)的“万有独化”论。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可以走向佛教般若学,也可以走向“万有独化”论,因为既然万事万物不能从先天的、外在的最高\n本源而只能从其自身获得本质规定,那么,所谓一般的、抽象的本体、原则等等就失去了意义,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万事万物自身。郭象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通过将具体事物升格为本体而形成其“万有独化”论的。与何、王不同,郭象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块然自生”的。同时,这种“自得而生”(《庄子•大宗师注》)的“有”又是“独化于玄冥之境”(《庄子•齐物论注》)的,\n也就是说,“有”是独自变化发展的。这样,“有”就具有“自有”、“自得”、“自本”、“自因”、“自化”等等特点。显然,郭象在这里旨在说明:1)每一个体(包括人)都是体用一如的绝对实体,认识了个体同时也就认识了本体,不必通过对个体的抽象、概括和超越而实现这一目的;\n2)作为个体内在根据的本体只存在于每一个绝对的个体之中而不存在于别的地方,个体就是本体的自足完满的体现。可以看出,郭象的“万有独化”论通过高扬个体而弥补了何王“贵无”论的“重本轻末”、“重体轻用”等理论上的不足。但是,由于没有联系(“万有”之间是各自孤立的)和发展(同一“有”的后一状态与前一状态毫无因果关连,它们都是“独化”的)的观点,对于个体的绝对化并不\n能使郭象走上新的理论维度,而只是将玄学推向了绝境——人对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无话可说了。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郭象的“万有独化”论却导致了佛教高潮的到来。魏晋时代的般若学无论多么精妙,但它把真如置于彼岸世界,认为众生只有通过累世修行才能证得“真如”、进入“涅槃”,获得解脱。这无论如何也会挫伤很多人念佛修行的积极性。\n加上成佛的前提——灵魂不灭论也仅仅是一个理论预设,并且不断受到人们的攻击与驳斥,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死后能否成佛的怀疑。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名僧竺道生(?—公元434年)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涅槃佛性”学说。\n他把处于彼岸世界的“真如佛性”内置于众生心中,倡“一切众生本有佛性”、“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注维摩诘经》),众生只要体认到自身本有佛性,即证得了涅槃。道生的佛学理论解决了众生能否成佛的问题,带来了佛教发展的高潮。这种一切众生(包括十恶不赦的“一阐提人”)悉有佛性和当下顿悟成佛的理论,在当时一度还找不到佛典上的依据。显然,道生在理论上似乎主要得力于郭象的“万有独化”论:\n1)郭象主张每一个体都是体用相即、体用一如的,这种思想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变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佛性说;2)郭象认为人们只要“纵心直往”,就能与绝对本体“有”“冥然契合”,这实际上就是“顿悟成佛”的另一种说法。显然,如果说佛教的“般若学”与玄学“贵无”论相契合的话,那么,佛教的“佛性论”则与玄学“贵有”论也是相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