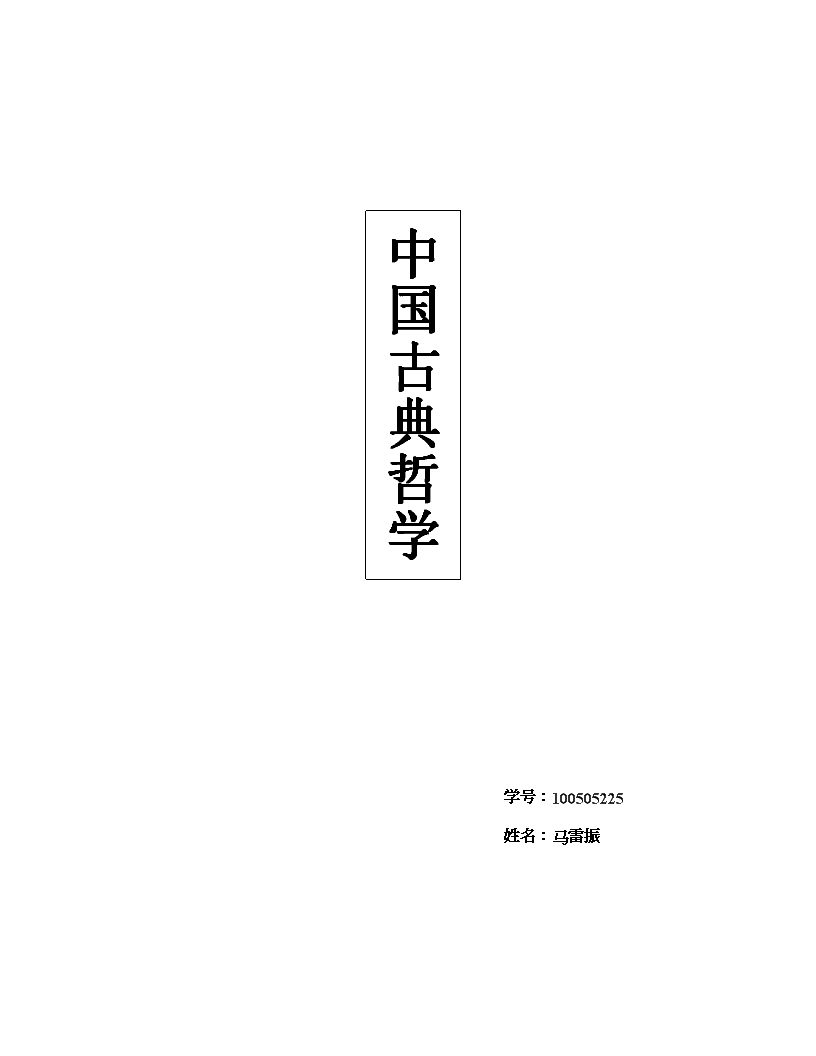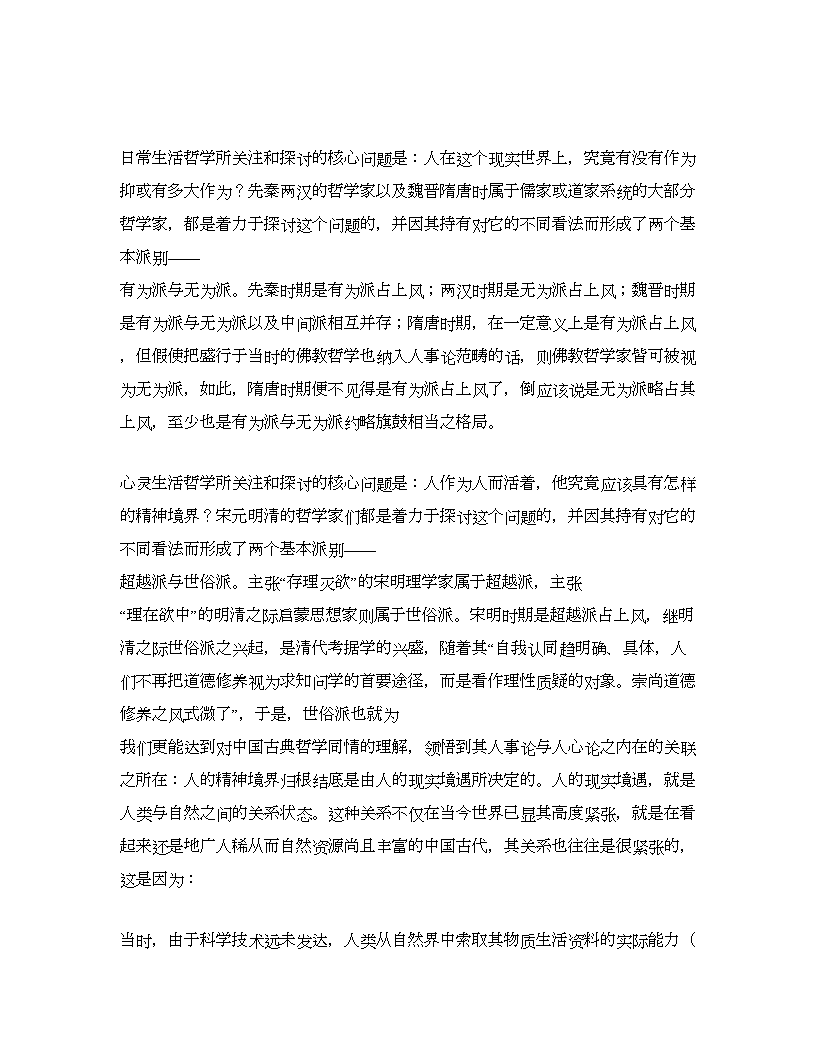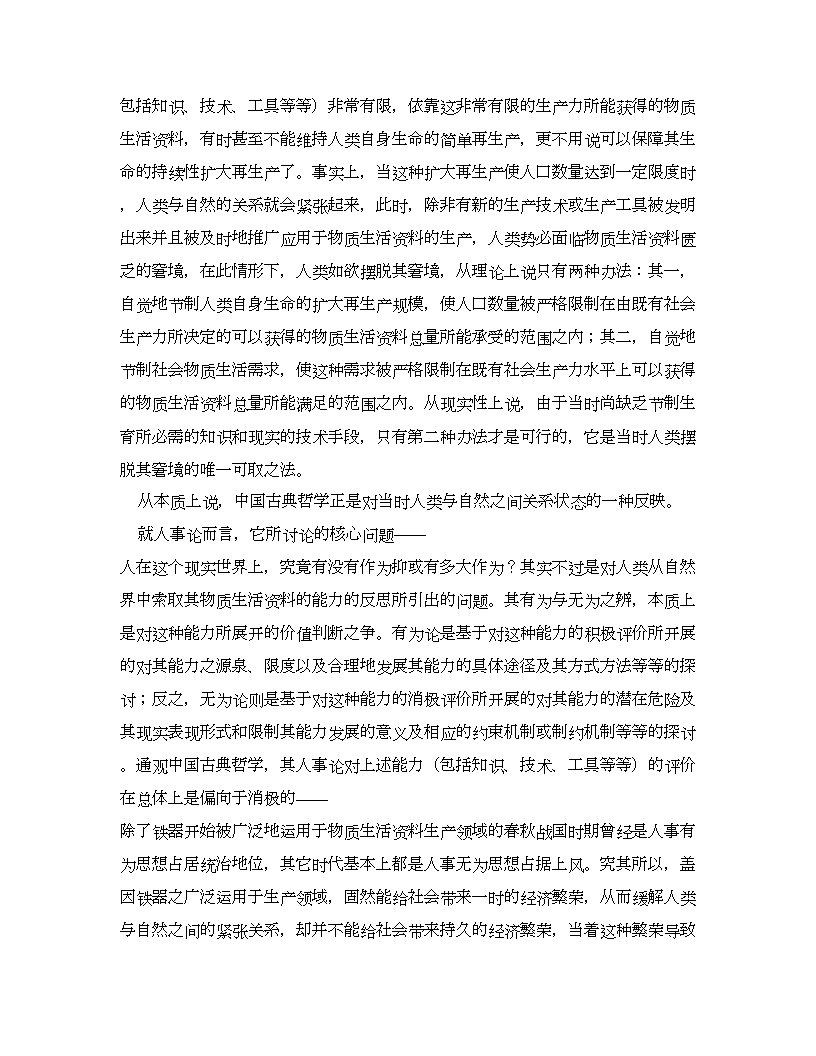- 28.50 K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中国古典哲学学号:100505225姓名:马雷振\n日常生活哲学所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作为抑或有多大作为?先秦两汉的哲学家以及魏晋隋唐时属于儒家或道家系统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着力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并因其持有对它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有为派与无为派。先秦时期是有为派占上风;两汉时期是无为派占上风;魏晋时期是有为派与无为派以及中间派相互并存;隋唐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是有为派占上风,但假使把盛行于当时的佛教哲学也纳入人事论范畴的话,则佛教哲学家皆可被视为无为派,如此,隋唐时期便不见得是有为派占上风了,倒应该说是无为派略占其上风,至少也是有为派与无为派约略旗鼓相当之格局。心灵生活哲学所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作为人而活着,他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宋元明清的哲学家们都是着力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并因其持有对它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超越派与世俗派。主张“存理灭欲”的宋明理学家属于超越派,主张“理在欲中”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则属于世俗派。宋明时期是超越派占上风,继明清之际世俗派之兴起,是清代考据学的兴盛,随着其“自我认同趋明确、具体,人们不再把道德修养视为求知问学的首要途径,而是看作理性质疑的对象。崇尚道德修养之风式微了”,于是,世俗派也就为我们更能达到对中国古典哲学同情的理解,领悟到其人事论与人心论之内在的关联之所在:人的精神境界归根结底是由人的现实境遇所决定的。人的现实境遇,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不仅在当今世界已显其高度紧张,就是在看起来还是地广人稀从而自然资源尚且丰富的中国古代,其关系也往往是很紧张的,这是因为:\n当时,由于科学技术远未发达,人类从自然界中索取其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包括知识、技术、工具等等)非常有限,依靠这非常有限的生产力所能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有时甚至不能维持人类自身生命的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可以保障其生命的持续性扩大再生产了。事实上,当这种扩大再生产使人口数量达到一定限度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此时,除非有新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被发明出来并且被及时地推广应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势必面临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窘境,在此情形下,人类如欲摆脱其窘境,从理论上说只有两种办法:其一,自觉地节制人类自身生命的扩大再生产规模,使人口数量被严格限制在由既有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可以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总量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其二,自觉地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使这种需求被严格限制在既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可以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总量所能满足的范围之内。从现实性上说,由于当时尚缺乏节制生育所必需的知识和现实的技术手段,只有第二种办法才是可行的,它是当时人类摆脱其窘境的唯一可取之法。从本质上说,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对当时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状态的一种反映。就人事论而言,它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作为抑或有多大作为?其实不过是对人类从自然界中索取其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反思所引出的问题。其有为与无为之辨,本质上是对这种能力所展开的价值判断之争。有为论是基于对这种能力的积极评价所开展的对其能力之源泉、限度以及合理地发展其能力的具体途径及其方式方法等等的探讨;反之,无为论则是基于对这种能力的消极评价所开展的对其能力的潜在危险及其现实表现形式和限制其能力发展的意义及相应的约束机制或制约机制等等的探讨。通观中国古典哲学,其人事论对上述能力(包括知识、技术、工具等等)的评价在总体上是偏向于消极的——\n除了铁器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领域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人事有为思想占居统治地位,其它时代基本上都是人事无为思想占据上风。究其所以,盖因铁器之广泛运用于生产领域,固然能给社会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从而缓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当着这种繁荣导致人口增长并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再度紧张起来。此时,在未有新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出现的情况之下(按:自春秋末期至清代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中,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领域,一直都是以简单铁制工具加牛耕为主,而未有比这更先进的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来取而代之),要改变这种状态,唯有两种可选的办法:或者变革社会制度,通过重新调整社会关系来增强社会生产力;或者变革社会观念,通过树立新的生活观念来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使这种需求被严格限制在既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可以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总量所能满足的范围之内。选取前一种办法的是人事有为论者;选取后一种办法的则属于无为论者。此外,当然也有共取其两种办法者,但他们也不外乎是前二者之间。中国古典哲学中人事无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不过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上,人们的思想重心不是偏向于考虑如何增强或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是偏向于考虑如何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对于该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而言,那就是意味着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观要求),努力使这种欲望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而勿使其任意膨胀,这是一个自觉的精神活动过程。显然,要使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既有待于社会的教育,又有待于个人的修养。前者作为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国家政府组织来保障其工程的实施,汉代名教之治的推行和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及与之相应的学校教育,以及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的扶持和利用,就都是当时国家为开展社会教育所采取的政府组织行为——\n以其最终目的而言,都不过是为了达成对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有效节制。中国古典哲学在汉唐时期的种种表现,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由政府所主导的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方式方法等问题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理论探讨以及在此过程中从儒、释、道三教中各取所需地对它们的思想加以实用主义的改造而提出的种种不同的见解和学说。宋代以后的哲学则是着力于探讨与社会教育密切相关的个人修养问题,其根本目的和汉唐哲学一样,也是为了达成对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有效节制,只是相对而言,汉唐哲学比较强调社会规范(包括伦理规范和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外在节制作用,亦即重视对人的客观行为的制约,而宋以后的哲学则比较强调人的德性对于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内在节制作用,亦即重视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制约。(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兴起以后则逐渐转向强调人的知性的作用,不再重视人的德性的作用。)由于物质生活需求的降低不是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是必有其限度,故寻求其合理的限度,就成为偏重于探讨如何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中国古典哲学的首要任务。对此,儒、释、道三家原本各有其所立的合理限度——儒家以“礼”为限度,道家以“自然”为限度,佛家以“戒律”为限度,而且它们原本主要是用于制约人的客观行为的准则,但是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则通过会通儒、释、道而将“礼”、“自然”、“戒律”融于一体,由此形成了所谓“天理”。“天理”(“性”或“本心”)不仅是理学家为节制人的社会物质生活需求所设定的人的精神活动所不可逾越的限度,同时也是理学家为人们自觉地限制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所设定的人的精神活动所应追求的境界。就其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所不可逾越的限度而言,“天理”是对于人而言具有必然意义的“天道”;就其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所应追求的境界而言,“天理”是对于人而言具有自由意义的“人道”。故“天理”乃是天人合一之道,它意味着必然与自由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天理”概念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观:人的精神活动(物质生活需求)有其一定的限度,必然是这种有限的精神活动的合理界限,自由则是合乎必然的精神活动。这种自由观表明:自由所给人带来的快乐本质上不是肉体的,而是心灵的;不是感性的快乐于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理性的快乐于物质欲望的自制。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价值,即为生活的快乐而追求自制的生活。对快乐的自制生活的追求,在原始儒家那里表现为提倡“克己复礼”的“归仁”;在原始道家那里表现为提倡“为道日损”的“法自然”;至于合儒、释、道为一的理学则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原始的儒道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哲学,故儒家提倡“克己复礼”的“归仁”,最终是要在客观行为上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n;道家提倡的“为道日损”的“法自然”,最终也是要在客观行为上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而本质上作为一种心灵生活哲学的理学,其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则是为了达到主观精神上的“乐循理”。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生活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自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