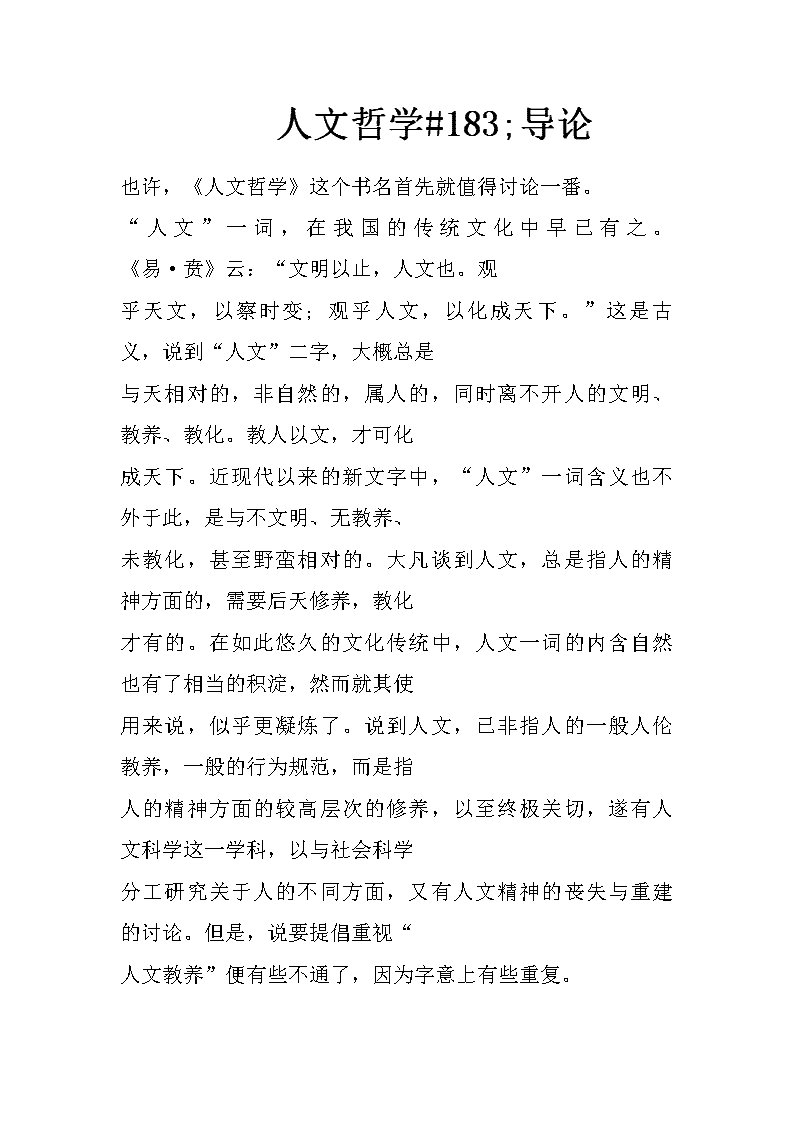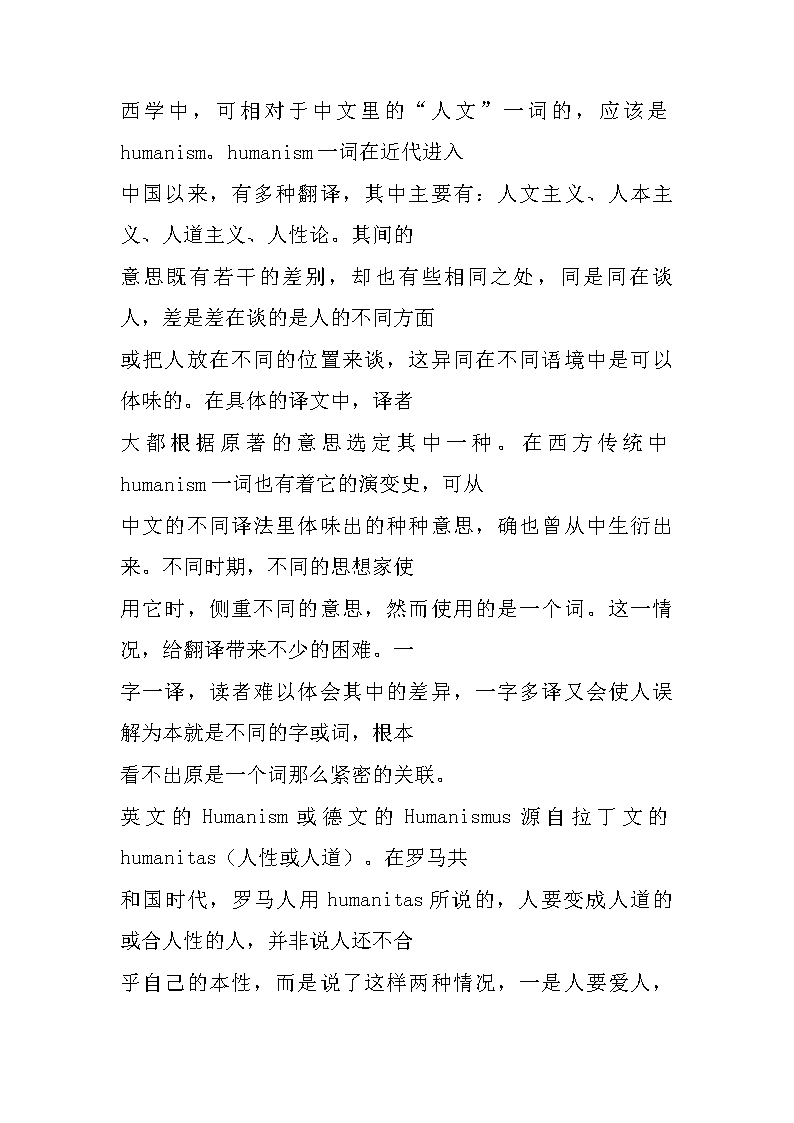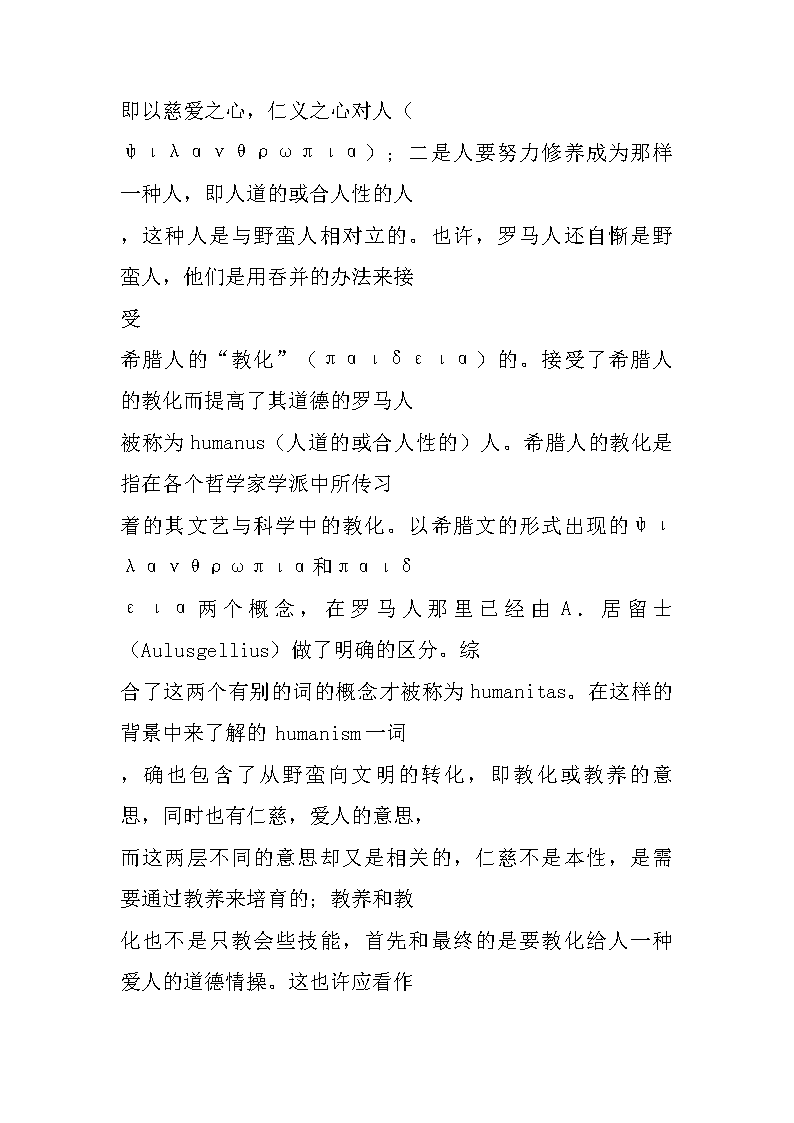- 90.50 KB
- 2022-08-1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人文哲学#183;导论也许,《人文哲学》这个书名首先就值得讨论一番。“人文”一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古义,说到“人文”二字,大概总是与天相对的,非自然的,属人的,同时离不开人的文明、教养、教化。教人以文,才可化成天下。近现代以来的新文字中,“人文”一词含义也不外于此,是与不文明、无教养、未教化,甚至野蛮相对的。大凡谈到人文,总是指人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后天修养,教化才有的。在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人文一词的内含自然也有了相当的积淀,然而就其使用来说,似乎更凝炼了。说到人文,已非指人的一般人伦教养,一般的行为规范,而是指人的精神方面的较高层次的修养,以至终极关切,遂有人文科学这一学科,以与社会科学分工研究关于人的不同方面,又有人文精神的丧失与重建的讨论。但是,说要提倡重视“人文教养”便有些不通了,因为字意上有些重复。\n西学中,可相对于中文里的“人文”一词的,应该是humanism。humanism一词在近代进入中国以来,有多种翻译,其中主要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其间的意思既有若干的差别,却也有些相同之处,同是同在谈人,差是差在谈的是人的不同方面或把人放在不同的位置来谈,这异同在不同语境中是可以体味的。在具体的译文中,译者大都根据原著的意思选定其中一种。在西方传统中humanism一词也有着它的演变史,可从中文的不同译法里体味出的种种意思,确也曾从中生衍出来。不同时期,不同的思想家使用它时,侧重不同的意思,然而使用的是一个词。这一情况,给翻译带来不少的困难。一字一译,读者难以体会其中的差异,一字多译又会使人误解为本就是不同的字或词,根本看不出原是一个词那么紧密的关联。英文的Humanism或德文的Humanismus源自拉丁文的humanitas(人性或人道)。在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人用humanitas所说的,人要变成人道的或合人性的人,并非说人还不合\n乎自己的本性,而是说了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人要爱人,即以慈爱之心,仁义之心对人(ψιλανθρωπια);二是人要努力修养成为那样一种人,即人道的或合人性的人,这种人是与野蛮人相对立的。也许,罗马人还自惭是野蛮人,他们是用吞并的办法来接受希腊人的“教化”(παιδεια)的。接受了希腊人的教化而提高了其道德的罗马人被称为humanus(人道的或合人性的)人。希腊人的教化是指在各个哲学家学派中所传习着的其文艺与科学中的教化。以希腊文的形式出现的ψιλανθρωπια和παιδεια两个概念,在罗马人那里已经由A.居留士(Aulusgellius)做了明确的区分。综合了这两个有别的词的概念才被称为humanitas。在这样的背景中来了解的humanism一词,确也包含了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化,即教化或教养的意思,同时也有仁慈,爱人的意思,而这两层不同的意思却又是相关的,仁慈不是本性,是需要通过教养来培育的;教养和教化也不是只教会些技能,首先和最终的是要教化给人一种爱人的道德情操。这也许应看作\nhumanism的原初含义,而这样来看的humanism便与中文里的“人文”、“人道”、“人本”这样一些词的意思相合,因而译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还都较合适,并无不通的地方。当然,在后来的西方哲学中,尤其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humanism这一概念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在这一概念下来谈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然而总不出“人”的事情,便是humanism。因为我们会问:那么人的事情是什么?大概世上的一切事情,只要是人知道的,人能够取为谈资的,都是与人有关的,属人的,一句话,就成为人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只要是由人来谈的,只要是从人的角度来谈的——然而哲学又就只是人在谈,就只能是由人来谈,也只能是从人的角度来谈,我们还能设想由别的什么来谈或不从人的角度而从别的什么角度来谈哲学吗?——那么所谈的事情就肯定都与人有关,都是人的事情。或许,我们还不能这么广泛地来理解所谓人的事情。不然,整个哲学就都成了humanism,\n成了“人文哲学”了。“人文哲学”或humanism所说的人的事情,应该是专指以人为中心论题,仅就人自身而言的事情。即使是这样,“人文哲学”的范围也已经非常广泛了。人有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外在生活方面,人也还有其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意识的、心理的内在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的诸多方面来谈人,而各个方面对人的研究和探讨,在哲学分化为各种科学学科后,已然成为各学科的主题。留给哲学的也许只有“人”这个概念,无论从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方面来理解,或从个体的还是整体的方面来认识。人,是哲学的永恒题目。哲学,是人的永恒事业。只有有了人,才有哲学,哲学是属人的。只有有了哲学,人才真正成为人,哲学是为人的。一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人的,它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与人有关。因而根本上可以说,哲学只关心人。在西方,从雅典德尔斐神殿上铭刻的箴言“\n认识你自己”,到康德的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说的都是人,说到的世界都与人密切相关,若是与人全无关系的外部世界,构不成哲学的对象。人首先是为了生存才与外界打交道,才去认识和研究世界和外物的。人在研究外物时,只是因了人自身的原因或目的才有了关于世界的某一方面的知识的哲学性的把握,人们把这称为某某哲学其实并非是关于某某的,实在是关于人的,是人对自身认识的总结。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处,希腊人其实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人文哲学思想。海德格尔说我们在罗马碰到了第一个人道主义时,他其实已经说,这种人道主义是接受了希腊的教化才出现的。在希腊人那里,也许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像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那样明确地把人摆在如此绝对中心的地位。他的格言是我们都熟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如此极端的表述,几乎让我们觉得再作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然而正是这种明白无误,不仅使他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倾向表现得淋漓尽\n至,而且也把他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立场标示得再明确不过。因为他还说过,事物对任何人来说,就是它向他所呈现的样子,对你对我都是一样的真实。他的这种人类中心论和相对主义当然地受到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的激烈反对。苏格拉底就认为,人是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的,即使聪明的人作为尺度要比愚蠢的人好,但是他也还是不完善的,因而还是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完善的,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人只有在如下的意义里,才能以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事物:即他不仅是一个认识心灵的人,而且是一个公正的人,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哲学家,他不仅总是不断地检验他自己,使自己不断完善起来,向神的完善性趋近:而且也总是不断地以种种智力对话来检验别人,并号召每一个人努力工作,以使自己的灵魂完善起来。这样看来,一方面,苏格拉底既没有把人摆在像神或神性的善所居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占据他的哲学的中心地位的也并不只是神或神性的善,而是人对神和神性的善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作为一\n个人的真正人性、完满性和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表现出一种为了服从德尔斐神的要求而履行自我检验和自我认识的宗教义务,因而他专事探讨个体的人。柏拉图对德尔斐神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作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使希腊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这种解释弓!引出了一个不仅不同于前苏格拉底思想,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苏格拉底方法之局限的问题。柏拉图主张,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我们的眼光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的人,而应该把这个问题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平面上去。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所经验到的现象是如此多样、如此复杂、如此矛盾,以至我们几乎不能清理它们。因此我们不应当在个人的生活中,而应当在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中去研究人,理清人的种种问题。柏拉图并没有改变人与神的位置,却大大地扩展了人的问题得以展开的视野和范围。希腊思想中的理性因素决定了希腊人对人的有限性的不信任。他们,总是要在这种有限性之外去寻找一种绝对可靠的、永恒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认识。即使是在上述柏拉图的那种\n大大地扩展了的视野中,问题最后也是要归到外在的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上。那是人为自己的认识所设置的一个活生生的现象的投影。有如神的生活只不过是人的生活的投影一样。所关切的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却要以神的观念来口答。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观点大概是柏拉图的视野的进一步的扩展和观点的进一步的延伸。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因为事实上,人并非世间的最好的东西,人的实践的智慧(practica1)和政治也不能代表最高种类的知识。因为这最高种类的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和关于神所知道的事情的知识,我们人类的最高的善就是在我们自己和神的这种知识的统一中被发现的。而这种善又是我们人类必须以尽可能经常的行动和实践来参与的事情。我们把这种最高的善称为“幸福”。所谓幸福,当然是人的幸福。然而人的幸福也是要以神的知识为尺度的。而这种神的尺度却又是进入了我们人的心灵之中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一方面,不是人,而是神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更严格他说来,\n所谓神性的心灵却是在人之中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通过组织在自己的沉思的心灵生活周围的生活实践和行动,把神性的心灵吸纳或同化到自己的内心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希腊哲学的顶峰。这一哲学达到了希腊人的理性所能达到的最为充分的形态。后来晚期希腊的哲学,即使是反叛,也只不过是其变形的一种。伊壁鸠鲁哲学中关于原子的偏离运动,不应被看作只是对德莫克里特原子论的一种补充,而是在对待个体的人的自由的观点中的一次革命,这一意义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阐发。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革命,也还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哲学表述方式范围之内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哲学基本上是整体地接受了希腊思想的概念。如果说,希腊哲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开始出现概念化的倾向,那么在罗马人对希腊思想经过翻译的生吞活剥的接受和继承中,哲学思想的概念化及其概念含义的单一化、固定化,几乎扼杀了希腊哲学中原本所有的思想创造活力。罗马人虽然通过西塞罗首先使用human\nitas这个术语而成就了“第一个人道主义”,但是他们对人的看法几乎完全抄袭了经过希腊化所流传下来的希腊思想中的人的概念。罗马人也把人看作anima1rationa1e(理性的动物)。这不仅是希腊文ζωονλσγονεχον的拉丁文译法,而且在罗马的意义下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定义。罗马人所谓“合人性的人”(homohumanu),即是符合这样的概念定义的人。若不符合这个定义,便是不合人性的人。这一定义在罗马人那里被当作人的一般本质而在对人的研究中成为当然的前提。但是,在罗马人看来,人所特有的理性是一种修养,尤其是一种希腊式的在文艺和科学方面的修养。由于罗马人是在与晚期希腊人的教化的相遇中来理解的,因而通常总是就希腊的晚期形态来看希腊人,而对晚期希腊形态本身又总是以罗马人的眼光来看的,这样一种修养,在罗马,便演度为一种技巧,一种论辩术或修辞学(rhetor)。这样一来,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便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技巧,所谓合理性的人便是具有这样一种技巧的人。即使我们推而广之地来说,也不过\n是一些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成为合人性的人。这样的有关人的定义显然是过于狭窄了。二事情也许就是这样的,对于人的定义是最困难的。这世上也许没有比人自身更难于认识的了。人对于外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认识,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却要难得多了。对于外物,人只需以“直观”的方式向外去看;对自身,人却只能以反思或反观的方式来“照看”。于是,对于人来说,观照自己的最易行的方式就是把人自身投射出去,在自身之外,立起和自身一样而又能用以反观自身的偶像——神。人把自身的所有现实性和可能性都寄托在这个投影上,希望能从这个投影中真正看到并看清自己。当然,神的观念并非只是人用以观照自身的“对像”。神本来就是人对自身的有限性的一种直接的否定。人不仅把自身的所有可能性都投射到神的观念中去,而且把因自身的有限性而不能达到的所有可能性和\n完善性都赋予了神。人不仅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就实际而言,并非像神话和宗教的观念所言,是神创造了人——而且人还把自身实际上所不能够或尚不能够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自己创造的神的观念中,尽可能地使神这个原本虚幻的形象丰满起来。而神的这种丰满和完善本身就宣示了:这是人之所不能。即使当人想要实现某些原本不能的愿望时,也还要借助神的力量——其实这一现象掩盖了如下的基本事实:归根到底,不仅是神的力量,就是神的观念本身也都是人创造的。这种情况,在那些原始的自然的宗教中也不例外。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的精神自身的悲哀。精神本就是人有可能超出自身之有限性的唯一力量,或换言之,精神本就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然而,超越本身就是对人的有限性之外的那个“不”或“非”的肯定,同时也就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否定。这首先是因为人对自身的有限性的不信任造成的。相对于人自身的有限性来说,\n神成为人只能景仰和神往而不可企及的超然之物。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不仅从神那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之所不能,甚至因从神那里感到了对自身的严重威胁而恐惧。神成了人羞辱自己,扭曲自己,恐吓自己,控制自己的一面“魔镜”,人在这面魔镜里变得越来越渺小、可怜,以至丑陋、罪恶得不堪人目。从近代以来的传统观念看来,西方人的整个中世纪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无所不能的神的威慑力的统治下的黑暗时代。基督宗教的一神论确定之后尤其如此。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犹太教的一神论逐步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多神论宗教——就某种意义而言,希腊和罗马的,尤其希腊的诸神,虽都有着一种超人的能力和品格,却都具有某些人所具有的气质、情感和性格,甚至缺点和怪癖,似乎也就更接近于人性,因而也就更可爱得多——尤其经过了自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一直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正统经院哲学体系的确立,经过了一系列对上帝的信仰的论证,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唯一的,然而又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念的实在性和真理性,在经院神学范围内和经院哲学的层\n面上,获得了似乎具有逻辑上和概念上的严密性的充分论证和绝对确定。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人是相对于上述这样一种上帝的观念而言的,人只不过是上帝的造物而已。人构不成当时的哲学的中心论题,虽然哲学在那时仍然是人在做的,是人在讨论上帝的观念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但人却不能在其中占有中心的地位。经院哲学也谈人。然而,经院哲学是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谈人的。按照基督教义人不仅是上帝的造物,而且是负有原罪的,此生此世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只有当肉体消亡时,上帝才能将人的灵魂拯救进入天国。因此此生此世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只有赎罪与等待。对于人来说,有意义的不在人生的此世,而在来世。人生此世的一切,都在于为了来世能够受召进入上帝的天国。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这是“启示的真理”,与人靠理性把握的真理不同。他并不否认人有理性,也不否认人能把握理性的真理。然而理性的真理不仅不同于启示的真\n理也不能与启示的真理相冲突,人凭理性是不能把握启示的真理的。人所能把握的理性真理都来自人的理性的本质之光,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不可靠的,会犯错误的,因而只能相对地保证理性真理的确实性。启示的真理则是超于人的理性之上的完美无比的,只有凭上帝的启示才能达到的。启示真理的确实性于上帝,上帝的全能保证了启示的真理的绝对确实性。也许人可以借助自己的理性,借助哲学来认识上帝,讨论上帝,神学也许还需要凭借哲学来发挥。但是,这只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容易接近和体悟上帝,使上帝以及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在人的心灵中更清晰些。然而,这样做却不能达到启示真理的绝对确实性。这种确实性只有在上帝的启示下,凭信仰才能获得。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体系中,人的有限性在与上帝的这样一种关系格局中以十分奇特的方式被确认下来——人是不完满的,也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达于完满。在自身所设立的偶像面前,人以一种被迫的冷静,以至委屈的心态,承认了自身现世的有限性。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自欺欺人?\n当然,中世纪的西方虽是正统的经院哲学体系占了主导的地位,却也不只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之外,还存在着诸多的异教和异端思想流派。就是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相当多的不同观点的争论长期存在。活跃在14世纪上半叶的威廉·奥康对其前辈圣·托马斯·阿奎那和邓·司各脱都有尖锐的批评,虽然这两位大师在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和神学的理性化都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理论论证在概念和逻辑上的繁琐,使奥康无法忍受。奥康对他们的哲学批判显示了那一时期经院哲学内部的重大转折。奥康极力反对经院哲学的繁琐逻辑,强调对个体存在物的直观的重要性,以此来否定上帝的存在对于把握客体的必要性。他在强调对个体事物的直观的同时,指出人的世界对于神的世界的相对独立性,指出了伦理和道德法则的两种可能性,即上帝建立并须经启示才赋予人的道德法则和由人的理性而非启示产生的临时性的、次级性的、非神学性的伦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以及后来的巴黎奥康主义运动对经验科学的重视也表现了神学内部的理性主义成分的不断增长和有力抗争。\n近年来,由于大量有关中世纪教会和修道院内部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人们对中世纪西方精神生活状况的看法有了较大的改变。人们看到,中世纪的西方教会,一方面有其压抑人类精神之创造性的相当长时期的负面记录,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资料说明,中世纪的教会和修道院成为西方精神生命得以延展的唯一场所,以至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都源出于教会内部,而科学学的发展也得益于经验科学在教会中的长期积累。也许,由此便得出结论,对中世纪西方教会给以充分的正面肯定,还为时过早或失之偏颇,然而中世纪并非像那些反对它的人们所描绘的那般黑暗,那时的人们也并非像后来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野蛮和愚昧到一味地用神来作践自己而毫无抗争,却是历史的事实已证明了的。或许,就我们眼下这本书的主题——人文哲学而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及其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比起正统的经院哲学来更具有意义。神秘主义大都具有泛神论的倾向,他们虽仍无法取消上帝所居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却由上帝无处不在的信条出发,认为\n上帝即在万物之中,万物便皆有神性,进而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上帝,人人都可与上帝直接沟通,因而人人都可以是神圣的。在对基督教义的不同信仰方式和解释方式中,人与上帝的位置和关系都有微妙的变化。这种思想与后来的宗教改革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中世纪的思想中人无疑并不占有中心的地位,然而,也并非完全没有了人的声音,尤其并非没有人的努力抗争的声音。情况的复杂并不是可以一言以毕之的,作任何的结论都应该十分地小心。作这种小心细致的考察显然不是我们眼下这篇短短的绪论能够完成的。但是,进一步地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对于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的精神生活而言,中世纪究竟是怎样的?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断裂?还是在西方人的精神基因中已然保留有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所添加的遗传密码?进而,人类精神生活在已经经过的几千年中究竟是如何延续和生长的?今后又会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为我们当前以至今后的精神生活拓展必要的空间,使其能更自由地生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