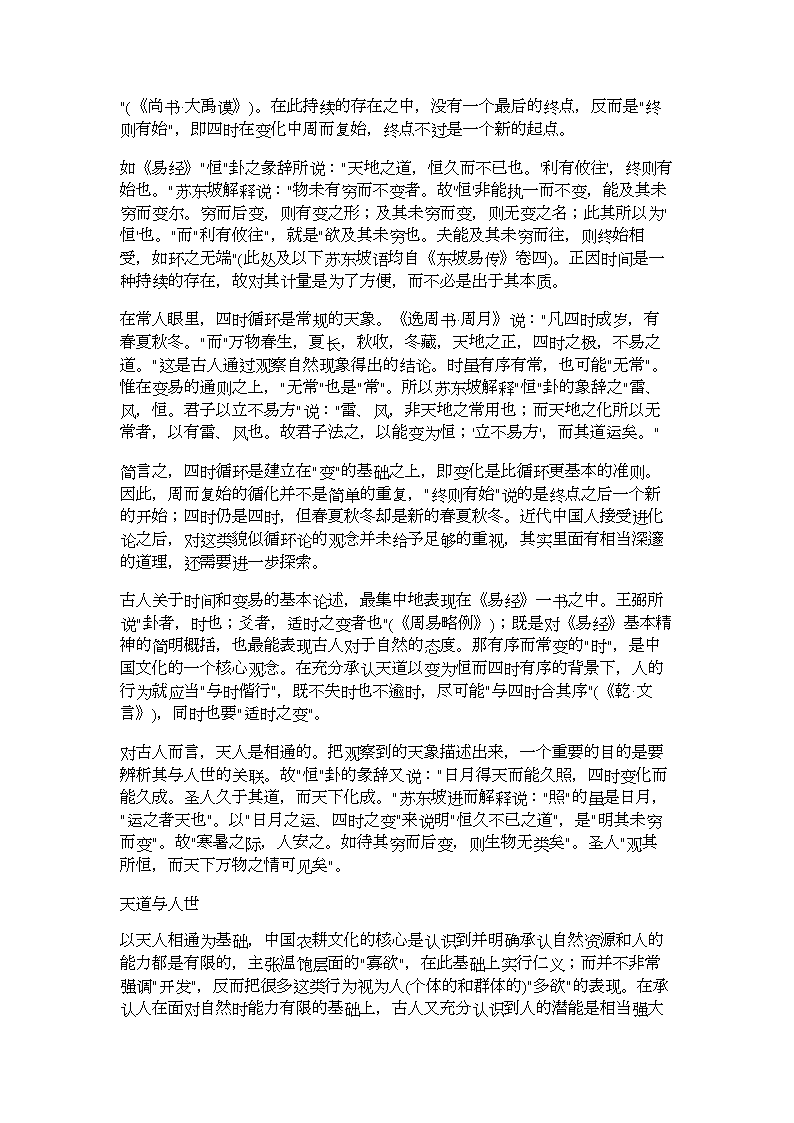- 16.67 KB
- 2022-08-18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农学论文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摘要:由于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多年来,传统本身成为一个不那么正面的负担,农耕文化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人们说到农耕文化,如果不加以贬斥,也往往带一点抱歉的意味。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中国的农耕文化,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不多。已有的论述并不少,但能形成共识,可作为进一步探讨基础的见解,似乎也不多。在举国媒体都关注日全食的前一天,我恰在成都参加一个农耕文化的研讨会。大约几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遇到日食月食一类事,还会针对"天狗吃月亮、吃太阳"一类传统说法进行科普教育。如今科学知识普及,至少媒体都知道这是月亮绕行地球时遮住了太阳。在日月的神秘性被剥去后,几百年一遇的天文奇观也就成了"自然产业",被相关人等当作商机好好地开发了一回。若回到几百年或几千年前,恐怕人们没有这么大胆。老百姓对太阳月亮是尊敬而爱护的,遇到天狗出来,就要大家鸣锣敲鼓而攻之,把它给吓回去。且天狗敢于出来作乱,可不是什么好事,人们都要有所防范。受到天狗侵犯的日月,似乎也不宜多看,尤其小孩子看了据说是要吃亏的。这些见解,现在都知道是"迷信"了。不过里面隐伏着一个不那么迷信的思路,即自然与人生息息相关。这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到今天也还有启发性。由于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多年来,传统本身成为一个不那么正面的负担,农耕文化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人们说到农耕文化,如果不加以贬斥,也往往带一点抱歉的意味。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中国的农耕文化,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不多。已有的论述并不少,但能形成共识,可作为进一步探讨基础的见解,似乎也不多。从很早以来,至少从有文字到大约数十年前,中国基本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可以说,农耕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从全人类和长时段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农耕文化时代产生的基本思想。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工商业文化,似尚未形成什么足以称道的贡献。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颇有其独特的地方。时间与变易敝友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授提示我,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与西方相当不同,与我们现在的认知也很不同。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不必是一个目的明确、可计量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走向(在近代西方进化论兴起之后,又增添了越来越进步的涵义),其本质在于变易,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所谓"时乃天道\n"(《尚书·大禹谟》)。在此持续的存在之中,没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反而是"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此处及以下苏东坡语均自《东坡易传》卷四)。正因时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故对其计量是为了方便,而不必是出于其本质。在常人眼里,四时循环是常规的天象。《逸周书·周月》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而"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这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时虽有序有常,也可能"无常"。惟在变易的通则之上,"无常"也是"常"。所以苏东坡解释"恒"卦的象辞之"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说:"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简言之,四时循环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即变化是比循环更基本的准则。因此,周而复始的循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终则有始"说的是终点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四时仍是四时,但春夏秋冬却是新的春夏秋冬。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对这类貌似循环论的观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里面有相当深邃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古人关于时间和变易的基本论述,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一书之中。王弼所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既是对《易经》基本精神的简明概括,也最能表现古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那有序而常变的"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充分承认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有序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就应当"与时偕行",既不失时也不逾时,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同时也要"适时之变"。对古人而言,天人是相通的。把观察到的天象描述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辨析其与人世的关联。故"恒"卦的彖辞又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苏东坡进而解释说:"照"的虽是日月,"运之者天也"。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来说明"恒久不已之道",是"明其未穷而变"。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圣人"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天道与人世以天人相通为基础,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认识到并明确承认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张温饱层面的"寡欲",在此基础上实行仁义;而并不非常强调"开发",反而把很多这类行为视为人(个体的和群体的)"多欲"的表现。在承认人在面对自然时能力有限的基础上,古人又充分认识到人的潜能是相当强\n大的(不论性善性恶)。人一旦"多欲",采取进攻性的举措,触及的方面可能是很多的,在态度上甚或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包括自然,也包括人本身,最后可能危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从天子到庶人,其所作所为都要因时、顺时、随时,"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礼记·月令》)。人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榨取甚至破坏自然。所有人,包括帝王在内,其行为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但以不超越自然为限度。所以古代特别警惕"人主"的"多欲",因为那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敬天但以人为本,不一定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如果略作理想型的表述,在这样的社会里,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君主是天之子,他在人间代替天执行天道;但天道是否真正得到贯彻,却表现在老百姓方面,所以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君主了解民视民听的一个方式是"采风",即通过搜集各地的民歌民谣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也由此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否仍代表着"天命"。"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关键的特色。经过孔子诠释的夏商周"三代",被推崇为黄金般的理想社会。正因为天道是"终则有始",所以理想社会可以在远古的"三代",但需要改善的却是当下的人生。历代士人都以做"天下士"为目标,他们的关怀必须广及"天人之际",而其始终想要澄清的"天下",仍是这凡俗的人世---要让"三代"的秩序重现于当世,变无道的社会为有道的社会。传统农耕文化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即大部分的人家居耕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女子基本不外出,至少不鼓励其外出(女权主义者可能看到歧视,但也未必不是出于善意,譬如对弱者的保护);男子可以有外面的事业,但也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考虑。实际的现象是,男性中并不真正务农的一部分常常外出:商人追逐十一之利,当然频繁外出;当兵也是"事业"之一途,可能远到边塞,但不受鼓励(贵族时代除外,那既是义务也是特权);在很长的时间里,读书做官被视为"上进"的正途,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今日所谓城市为官。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军人亦然。商人多是只身外出,家人仍定居,往往还在家乡置地以为保障,甚或借此转变身份。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其实劳动的分类和分工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而"男耕女织"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从西周开始的礼制,天子亲耕藉田、后妃亲蚕,成为一种必须的象征性仪式。到宋代苏东坡还曾描述"苍龙挂阙农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的热闹。天子亲耕的仪式虽然只是一个象征,但对农耕的特殊尊重,已表达得非常清楚。\n如果进一步进行"劳心"和"劳力"的区分,则劳心者或许可实行"代耕"的方式。孟子就承认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但认为"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自主能力,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性。所以一般人是无恒产即无恒心,惟有士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他进而提出,如果士君子能使国家"安富尊荣"、人民"孝弟忠信",则即使"不耕而食",也不算尸位素餐(《孟子·尽心上》)。仔细体会孟子的意思,只有那些学养高到可以超越经济支配的人,并对国家人民有具体的贡献,才可以享受"不耕而食"的特例。对无恒产则无恒心的一般人而言,当然就应"耕而食"才对。所以他明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一对应的比拟,清楚地表明"仕"不过是一种"代耕";孟子的整个立论,仍建立在重"耕"尊"耕"的基础之上。沿着这一思路,后来衍伸出"笔耕"、"舌耕"一类的表述,反映着很多实际"不耕而食"者对"耕"的尊重。进而言之,"仕"既是士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其追求的目标,却不必是士之常态;大部分读书人毋宁说长期处于一个为出仕而持续准备的过程之中。在一个农业文明中,文化不能没有根,且必须扎根于土地之中。文化与土地的关联,是农耕文化的一个基础。天子尚且要亲耕,读书人自不能疏离于耕作和土地。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汉书·艺文志》),到后来,象征着与土地关联的"耕读",成为中国一个持续了至少两千年的核心观念。耕读也是四民之首的"士"赖以维持其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象征。如身历清末废科举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自诩其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这恐怕更多是一种理想型的表述,刘家上一代主要经济收入就来自他在外经商的父亲,刘大鹏自己入仕不成,也不得不像大多数未能做官的读书人一样以"舌耕"为生,出任塾师,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但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与刘大鹏相类,很多读书人实际不"耕",或不怎么"耕",但仍要维持这一认同,以示未曾疏离于土地和农耕行为。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最迟大约在汉代,中国人已经在思考西欧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思考的那些基本问题,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假如套用西方"生产"和"分配"的概念,近代西方人的结论似偏于前者,而早年的中国人则偏于后者;即在充分承认物质有限并且不侧重开发的基础上,特别重视"分配",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所谓重农抑商,既是一个基本的倾向,也是农业社会的习惯思维。古代本有"工贾食官"(《国语·晋语四》)的传统,如孟子所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孟子·公孙丑下》)。因此,工匠贾人多近于官奴,身份很低贱。而工贾之事也是鄙事、贱事,贵\n族既不愿参与,大概也不能参与。秦汉时诏令律条中常将贾人与罪人、赘婿等同列,作为卑贱而国家可征发的社群,就是上述传统的遗存。但春秋战国本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贵族体制的崩溃带来思想和行为的解放,使一些商贾有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身居相位。而孔子也可以用"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来解释其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这里当然有谦逊,但若世风不变,这样的谦逊恐怕说不出口)。不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在周秦诸子之中仍相当普遍。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但这更多是特指以"末业"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略近于今日所谓"脱贫"。也就是说,贫寒者可以借"末业"致富,若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的,就不宜如此了。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抑商"政策,但对商的"抑制"并不是全面的,而仅是相对的。即并不阻碍商人发财甚或发大财,但不能不限制商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在生产力并未充分发展时(如上所述,古人本不主张"发展"得太充分),把社会资源进行有区隔的分配,特别是将名、利、权三者进行大致明晰的分疏,使各有所得,是古人充满智慧的处理方式。类似的措置长期得到贯彻,但也不是一刀切,仍能关注特殊区域的行业特色。如清代商人之家在科举方面受到不少限制,但也有专门分配给工商业地区的科举名额,四川的犍为就是其一;在这些地区,商人子弟所受限制就无意义了。对商的警惕的确是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古人一方面充分了解并承认商的本质是求利,即使惟利是图,或也不算违背其"职业道德";在此基础上,更注意到与商相关的思想行为扩充到其他领域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故以发财为目的之商业作为是可以允许的,其行为模式和思想风尚却受到限制,不得推广。这一顾虑是有理由的,至少就当年的社会伦理言,商业行为模式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考虑其他方面的轻重缓急。这一点,也算是成功商人的吕不韦请人编成一部《吕氏春秋》,就说得非常清楚: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n安土重迁与农耕的紧密关联,在这里反映得相当明晰,其中既有今日所谓经济的考虑,也有昔人特别看重的文化因素---落叶就要归根,"死处"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可直接影响其行为。当然,这些具体思考都建立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之上,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社会,但其思路很清楚,就是农业和商业各有其附载的行为模式和思想风尚,不能仅从直接获"利"多少的物质角度来计算,还要考虑今日所谓社会和政治的成本与后果。很多年后,蔡元培仍以类似的理念来办大学。他主张区别"学"与"术",即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两者在学理上"虽关系至为密切",却"有性质之差别"。教学上也应予区分,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则独立出去。因为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而后者的培养目标则是让生徒"学成任事"。两方面"习之者旨趋不同",对学风有实际的影响。各科兼设的结果,使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会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蔡先生的主张虽未被后来的校长所采纳,但其思路却与早年重农抑商的想法相近似。致力于天人的双赢近代西力东渐后,农耕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后来更衍生出许多"非农"甚至"反农"的观念和言论,迄今仍较流行,甚或越来越流行。有些观念反映出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如前些时候出现的"毒奶粉",就被有的学者归咎于农业文明,说成是中国商业文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一个社会上发生了在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期间不曾发生的事,常规的思维似乎应该反思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些社会变化与新的社会行为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等等。但一些学者几乎恰好是反其道而言之。这样说的好像还不是一两人,有些在本专业是很不错的学者,也非常诚恳地相信这一点(我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人)。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反思。"毒奶粉"不过一例,今日还有大量制贩假药等伤天害理的行为,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遵循《吕氏春秋》和蔡元培的思路,出现这类现象,更可能是在发展非农业经济的同时,改变了与农耕文化相伴随的行为方式;即商业文明的好处还没学到,又已把农业文明的优点抛弃了。近代形成的反传统思路有一个特点,国家或社会出了问题,却并不像后来的套话所说那样"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而是先把责任推给古人或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之所以会成为非农耕文化行为的替罪羊,既体现出这类推卸责任的反传统思路已成为某种惯性思维,也说明我们对农耕文化的了解已经非常不足了。近年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与农耕文化渐行渐远。如"随时随地"在今日是一个常用词,其本意却有着非常意味深长的哲理。朱熹曾发挥程颐"君子顺时"的观念说,所谓"顺时",要达到"如影之随形"的程度。"夏葛冬裘,饥食渴饮,岂有一毫人为加乎其间\n哉?随时而已。时至自从,而自不可须臾离也"。学者若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则"时食而饮、时葛而裘,毫厘之差,其应皆忒,则将以何为道"(《朱文公文集·答范伯崇书》)?时间如此,空间亦然。安土重迁的原则,也可以反映在饮食行为上。用今天的话说,吃东西最好"随时随地",而不宜逆时逆地(后者可以尝鲜,却不必经常吃)。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吃反季节、远距离的蔬菜水果,越来越提倡假日外出活动以代替家居休息,同时又越来越愿意生活在不受四季影响而冬暖夏凉的室内。这些都是朱子所说的"人为"因素,除室内的冬暖夏凉的确更舒适也显得更"必要"外,其余多是温饱之余的补充。这些不过是最近才"形成"的生活习惯,若按农耕文化的标准看,都是违背自然常规的,也离"道"日远。我自己就很愿意享受冬暖夏凉的科技成果,当然无意提倡返回更原始的生活方式。问题是,侧重温饱之余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够普及,以及可以持续多久?更基本的问题是:地球给人类准备了那么多资源吗?人多远虑,然后可以少近忧。我有个外国朋友就在忧虑,地球的资源是否能让60亿人都过现在欧美"发达国家"所过的生活?就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人口还在与日俱增,地球迟早会不堪重负,人类总要面临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的难题。自从农耕文化被否定后,以"人定胜天"的精神改造自然得到充分提倡。这一精神当然给人类带来很多正面的回馈,但也已导致了一些"战胜自然"的过分举动。有一首歌很乐观地唱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然而如今黄河时常断流,长江也已被污染到变质,家里盘着的两条龙都出了大问题,这个局面还不够可怕吗?我们也许在"与天奋斗"的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如今恐怕不能不比从前更敬天,适当收敛对自然的进攻精神,与天和谐共处,庶几获致天人的双赢。我们常常听到农业文明/文化、工业文明/文化和商业文明/文化的这类说法,我不知道人类文明或文化是否确可以这样划分。假如可以这样划分的话,这些文化各自如何界定,如何区隔,估计也难有定见。不过,有西哲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既然有不少人这样说,可以假设这样的分类有其道理。对这些文明或文化,个人无意在其间作什么价值判断。人类的历史太悠久,有文字以后也已经好几千年,我们生活在这长期积累之后,只要把历史视为思想资源而不是精神负担,就可以有足够的智慧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类文明取长补短,产生出一种相对均衡、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都能长期和谐共处的取向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农耕文化对自然资源和人类能力有限性的认识,不仅应认真反思,也的确是可以汲取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