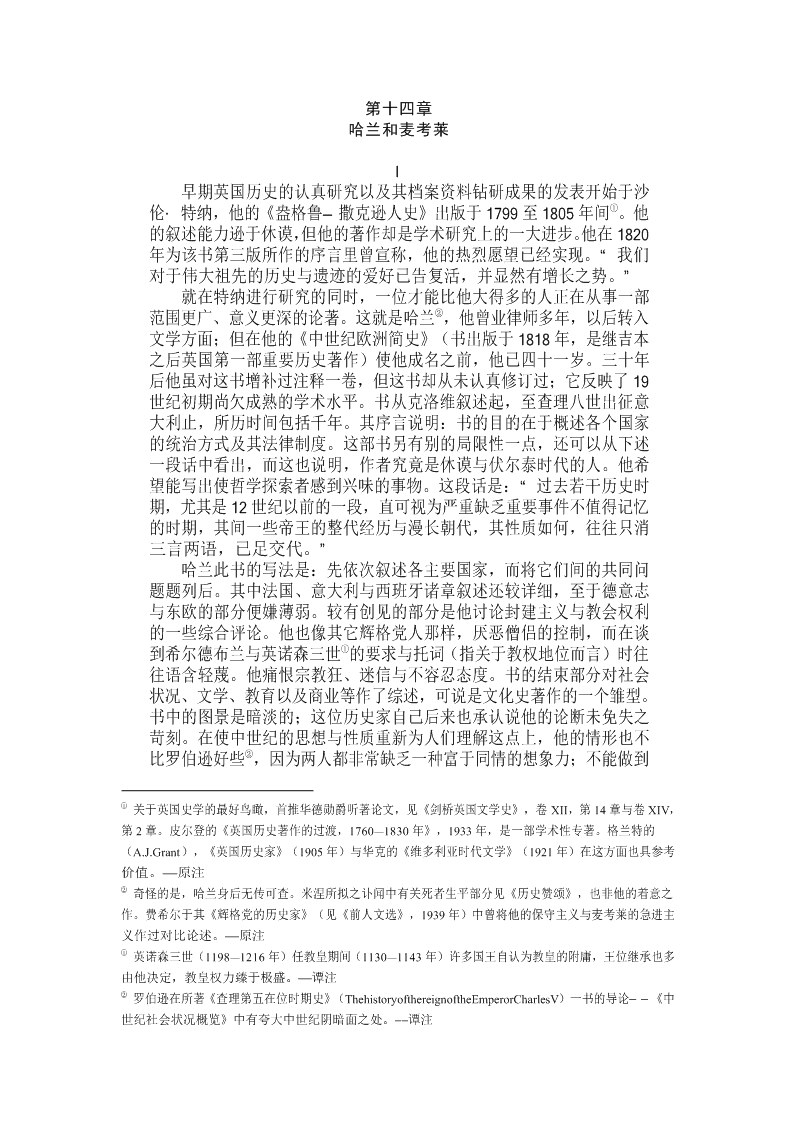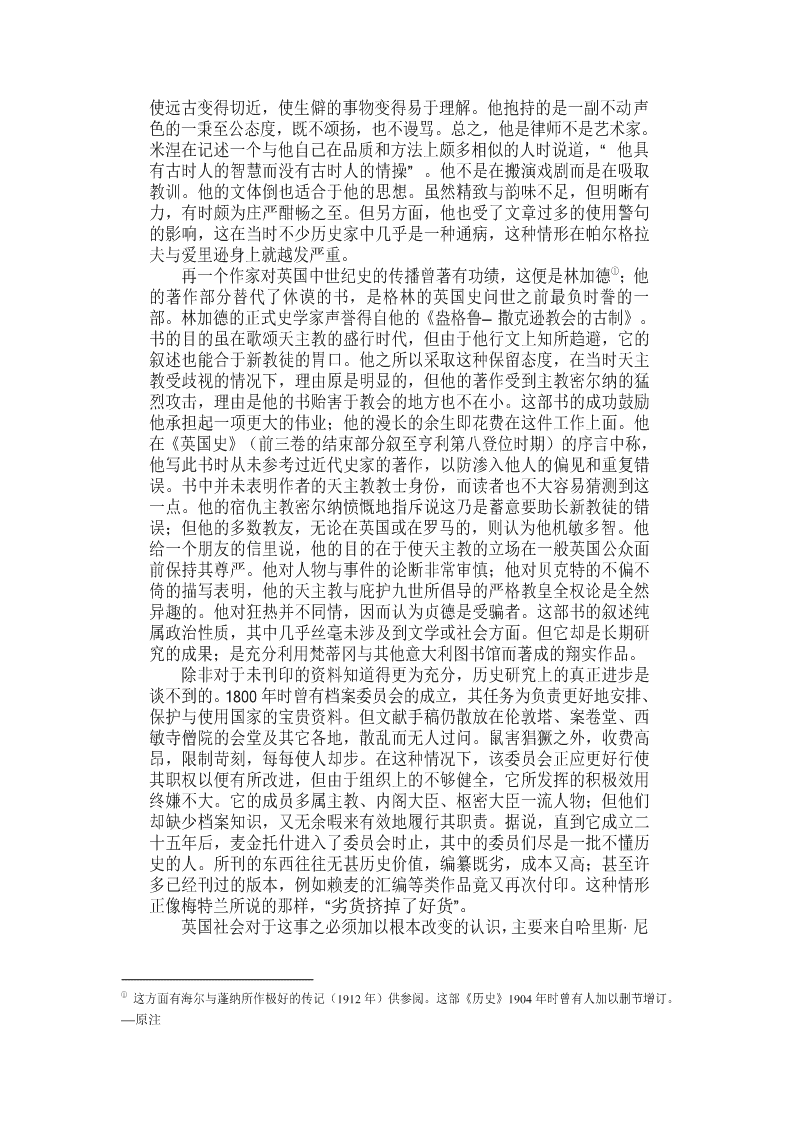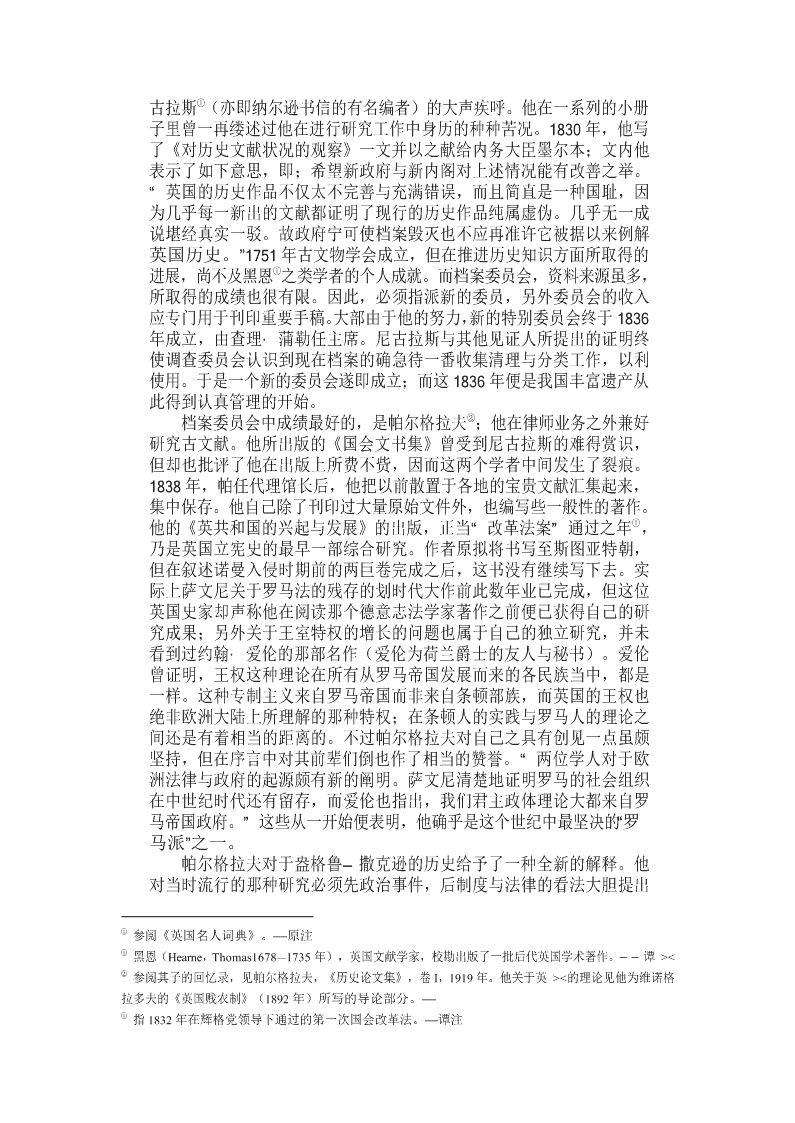- 748.78 KB
- 2022-08-18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第十四章哈兰和麦考莱I早期英国历史的认真研究以及其档案资料钻研成果的发表开始于沙①伦·特纳,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史》出版于1799至1805年间。他的叙述能力逊于休谟,但他的著作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大进步。他在1820年为该书第三版所作的序言里曾宣称,他的热烈愿望已经实现。“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历史与遗迹的爱好已告复活,并显然有增长之势。”就在特纳进行研究的同时,一位才能比他大得多的人正在从事一部②范围更广、意义更深的论著。这就是哈兰,他曾业律师多年,以后转入文学方面;但在他的《中世纪欧洲简史》(书出版于1818年,是继吉本之后英国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使他成名之前,他已四十一岁。三十年后他虽对这书增补过注释一卷,但这书却从未认真修订过;它反映了19世纪初期尚欠成熟的学术水平。书从克洛维叙述起,至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止,所历时间包括千年。其序言说明:书的目的在于概述各个国家的统治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这部书另有别的局限性一点,还可以从下述一段话中看出,而这也说明,作者究竟是休谟与伏尔泰时代的人。他希望能写出使哲学探索者感到兴味的事物。这段话是:“过去若干历史时期,尤其是12世纪以前的一段,直可视为严重缺乏重要事件不值得记忆的时期,其间一些帝王的整代经历与漫长朝代,其性质如何,往往只消三言两语,已足交代。”哈兰此书的写法是:先依次叙述各主要国家,而将它们间的共同问题题列后。其中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诸章叙述还较详细,至于德意志与东欧的部分便嫌薄弱。较有创见的部分是他讨论封建主义与教会权利的一些综合评论。他也像其它辉格党人那样,厌恶僧侣的控制,而在谈①到希尔德布兰与英诺森三世的要求与托词(指关于教权地位而言)时往往语含轻蔑。他痛恨宗教狂、迷信与不容忍态度。书的结束部分对社会状况、文学、教育以及商业等作了综述,可说是文化史著作的一个雏型。书中的图景是暗淡的;这位历史家自己后来也承认说他的论断未免失之苛刻。在使中世纪的思想与性质重新为人们理解这点上,他的情形也不②比罗伯逊好些,因为两人都非常缺乏一种富于同情的想象力;不能做到①关于英国史学的最好鸟瞰,首推华德勋爵听著论文,见《剑桥英国文学史》,卷XII,第14章与卷XIV,第2章。皮尔登的《英国历史著作的过渡,1760—1830年》,1933年,是一部学术性专著。格兰特的(A.J.Grant),《英国历史家》(1905年)与华克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1921年)在这方面也具参考价值。——原注②奇怪的是,哈兰身后无传可查。米涅所拟之讣闻中有关死者生平部分见《历史赞颂》,也非他的着意之作。费希尔于其《辉格党的历史家》(见《前人文选》,1939年)中曾将他的保守主义与麦考莱的急进主义作过对比论述。——原注①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任教皇期间(1130—1143年)许多国王自认为教皇的附庸,王位继承也多由他决定,教皇权力臻于极盛。——谭注②罗伯逊在所著《查理第五在位时期史》(ThehistoryofthereignoftheEmperorCharlesV)一书的导论——《中世纪社会状况概览》中有夸大中世纪阴暗面之处。——谭注\n使远古变得切近,使生僻的事物变得易于理解。他抱持的是一副不动声色的一秉至公态度,既不颂扬,也不谩骂。总之,他是律师不是艺术家。米涅在记述一个与他自己在品质和方法上颇多相似的人时说道,“他具有古时人的智慧而没有古时人的情操”。他不是在搬演戏剧而是在吸取教训。他的文体倒也适合于他的思想。虽然精致与韵味不足,但明晰有力,有时颇为庄严酣畅之至。但另方面,他也受了文章过多的使用警句的影响,这在当时不少历史家中几乎是一种通病,这种情形在帕尔格拉夫与爱里逊身上就越发严重。①再一个作家对英国中世纪史的传播曾著有功绩,这便是林加德;他的著作部分替代了休谟的书,是格林的英国史问世之前最负时誊的一部。林加德的正式史学家声誉得自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古制》。书的目的虽在歌颂天主教的盛行时代,但由于他行文上知所趋避,它的叙述也能合于新教徒的胃口。他之所以采取这种保留态度,在当时天主教受歧视的情况下,理由原是明显的,但他的著作受到主教密尔纳的猛烈攻击,理由是他的书贻害于教会的地方也不在小。这部书的成功鼓励他承担起一项更大的伟业;他的漫长的余生即花费在这件工作上面。他在《英国史》(前三卷的结束部分叙至亨利第八登位时期)的序言中称,他写此书时从未参考过近代史家的著作,以防渗入他人的偏见和重复错误。书中并未表明作者的天主教教士身份,而读者也不大容易猜测到这一点。他的宿仇主教密尔纳愤慨地指斥说这乃是蓄意要助长新教徒的错误;但他的多数教友,无论在英国或在罗马的,则认为他机敏多智。他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他的目的在于使天主教的立场在一般英国公众面前保持其尊严。他对人物与事件的论断非常审慎;他对贝克特的不偏不倚的描写表明,他的天主教与庇护九世所倡导的严格教皇全权论是全然异趣的。他对狂热并不同情,因而认为贞德是受骗者。这部书的叙述纯属政治性质,其中几乎丝毫未涉及到文学或社会方面。但它却是长期研究的成果;是充分利用梵蒂冈与其他意大利图书馆而著成的翔实作品。除非对于未刊印的资料知道得更为充分,历史研究上的真正进步是谈不到的。1800年时曾有档案委员会的成立,其任务为负责更好地安排、保护与使用国家的宝贵资料。但文献手稿仍散放在伦敦塔、案卷堂、西敏寺僧院的会堂及其它各地,散乱而无人过问。鼠害猖獗之外,收费高昂,限制苛刻,每每使人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正应更好行使其职权以便有所改进,但由于组织上的不够健全,它所发挥的积极效用终嫌不大。它的成员多属主教、内阁大臣、枢密大臣一流人物;但他们却缺少档案知识,又无余暇来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据说,直到它成立二十五年后,麦金托什进入了委员会时止,其中的委员们尽是一批不懂历史的人。所刊的东西往往无甚历史价值,编纂既劣,成本又高;甚至许多已经刊过的版本,例如赖麦的汇编等类作品竟又再次付印。这种情形正像梅特兰所说的那样,“劣货挤掉了好货”。英国社会对于这事之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的认识,主要来自哈里斯·尼①这方面有海尔与蓬纳所作极好的传记(1912年)供参阅。这部《历史》1904年时曾有人加以删节增订。——原注\n①古拉斯(亦即纳尔逊书信的有名编者)的大声疾呼。他在一系列的小册子里曾一再缕述过他在进行研究工作中身历的种种苦况。1830年,他写了《对历史文献状况的观察》一文并以之献给内务大臣墨尔本;文内他表示了如下意思,即;希望新政府与新内阁对上述情况能有改善之举。“英国的历史作品不仅太不完善与充满错误,而且简直是一种国耻,因为几乎每一新出的文献都证明了现行的历史作品纯属虚伪。几乎无一成说堪经真实一驳。故政府宁可使档案毁灭也不应再准许它被据以来例解英国历史。”1751年古文物学会成立,但在推进历史知识方面所取得的①进展,尚不及黑恩之类学者的个人成就。而档案委员会,资料来源虽多,所取得的成绩也很有限。因此,必须指派新的委员,另外委员会的收入应专门用于刊印重要手稿。大部由于他的努力,新的特别委员会终于1836年成立,由查理·蒲勒任主席。尼古拉斯与其他见证人所提出的证明终使调查委员会认识到现在档案的确急待一番收集清理与分类工作,以利使用。于是一个新的委员会遂即成立;而这1836年便是我国丰富遗产从此得到认真管理的开始。②档案委员会中成绩最好的,是帕尔格拉夫;他在律师业务之外兼好研究古文献。他所出版的《国会文书集》曾受到尼古拉斯的难得赏识,但却也批评了他在出版上所费不赀,因而这两个学者中间发生了裂痕。1838年,帕任代理馆长后,他把以前散置于各地的宝贵文献汇集起来,集中保存。他自己除了刊印过大量原始文件外,也编写些一般性的著作。①他的《英共和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出版,正当“改革法案”通过之年,乃是英国立宪史的最早一部综合研究。作者原拟将书写至斯图亚特朝,但在叙述诺曼入侵时期前的两巨卷完成之后,这书没有继续写下去。实际上萨文尼关于罗马法的残存的划时代大作前此数年业已完成,但这位英国史家却声称他在阅读那个德意志法学家著作之前便已获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另外关于王室特权的增长的问题也属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并未看到过约翰·爱伦的那部名作(爱伦为荷兰爵士的友人与秘书)。爱伦曾证明,王权这种理论在所有从罗马帝国发展而来的各民族当中,都是一样。这种专制主义来自罗马帝国而非来自条顿部族,而英国的王权也绝非欧洲大陆上所理解的那种特权;在条顿人的实践与罗马人的理论之间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不过帕尔格拉夫对自己之具有创见一点虽颇坚持,但在序言中对其前辈们倒也作了相当的赞誉。“两位学人对于欧洲法律与政府的起源颇有新的阐明。萨文尼清楚地证明罗马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时代还有留存,而爱伦也指出,我们君主政体理论大都来自罗马帝国政府。”这些从一开始便表明,他确乎是这个世纪中最坚决的“罗马派”之一。帕尔格拉夫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研究必须先政治事件,后制度与法律的看法大胆提出①参阅《英国名人词典》。——原注①黑恩(Hearne,Thomas1678—1735年),英国文献学家,校勘出版了一批后代英国学术著作。——谭><②参阅其子的回忆录,见帕尔格拉夫,《历史论文集》,卷I,1919年。他关于英><的理论见他为维诺格拉多夫的《英国贱农制》(1892年)所写的导论部分。——①指1832年在辉格党领导下通过的第一次国会改革法。——谭注\n异议。“法律史乃是最能说明英国政治史的有力的线索。民族的性格主要取决于其法律。”他谈起法律时总是一副极为恭谨的态度。“立法者的职能及是人类所能行使的最高职能。立法是一种义务,它必将使有关的人担负起异常重大的责任。”英国君主政权乃是从罗马君主政权派生而来并受到其条顿实践限制的。其中罗马的成分使我们免于成为一盘散沙;而条顿的成分则使我们摆脱专制政体。在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司法制。英国的州、百户村与市镇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同时也是政治团体。社会机构就是这样而一直曾是这样,尽管其间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与王朝更替。罗马帝国时期,入侵的蛮族只改①②变了它的“维兰制”的形式。不列吞人语言的消灭并不能证明不列吞人的消灭,这也犹如高卢地区凯尔特人语言的消灭不能说明凯尔特人已被法兰克人所消灭。至于丹麦人与诺曼人的侵入的遗迹就更要少些。中世纪的英国乃是建立在罗马基地上的。帕尔格拉夫的这些著作立论大胆也有新见。他这个历史延续性的信念,是以他对社会状况的惯性力(Visinertiae)的认识为依据的;他虽说才气横溢,学识渊博,但却未免武断和太多幻想。他是处处只见罗马,而闭眼不见条顿遗迹。他对资料的安排也极不好。书的第一卷从各个罗马皇帝的章节开始,而第二卷名为《证据与例举》却不恰当,叫作“拾遗补阙”或更合适一些(这后一标题乃系《爱丁堡评论》为其代拟)。帕尔格拉夫后期巨著《诺曼底与英国史》在某些方面是他的一部续编。当时,关于该公国的历史尚未出现,而他也讲过没有人能够编写这部历史,除非是编者能掌握住此中的关键。“现在一般人对中世纪时代,尤其对中世纪的基督教,攻击甚烈,说它完全沉浸在黑暗与野蛮状态之中。”但是一方面中世纪与基督教从新教徒与理性主义者那里遭到的贬抑固然失之公允,它们从糊涂的卫道者们手中蒙受的损害也并不小。如果说一副不偏不倚的态度乃是作好这件工作的第一条件,那么第二条件便是对罗马影响的清楚认识。“想要真正理解中世纪与近代的重要理论关键便是,一切权力导源于罗马与欧洲各国的继承性二点。”因此这位史家的第二部著作,也正像他第一部那样,不过是他关于罗马主题的老调重弹而已。书从加洛林帝国的历史详细叙起,而后谈到诺曼人在罗洛①定居诺曼底前的情形。二卷专述早期各公爵;三卷的叙述迄诺曼征服②止。四卷叙述鲁夫斯的统治并讨论了征服的结果。但这书因作者逝世于1861年而中断;故征服这段历史未能写出,但作者对征服一事性质的看法早已阐述得十分明显。与梯叶里完全相反,他把征服看作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这位英国人对诺曼人的一片热情,恰和那位法国人对撒克逊人的看法不相上下。他书中说明,当时土地的转移并不如梯叶里所说的那样,但种族的融合则比梯叶里所认为的更加迅速。所有法律上所进行①“维兰制”(Villeinage)一般认为即农奴制。近代学者对其形成与发展尚有争议。我国学者通用音译。——谭注②不列吞人(Britons),罗马入侵前居于英国南部的凯尔特人之一支。——谭注①罗洛,领洗后改名罗伯特,北欧诺曼人的首领。加洛林王朝查理三世于911年将后来的诺曼底大部分土地封赐与他。——谭注②鲁夫斯,即威廉二世,征服者威廉之次子。1087年嗣位,暴虐无道,1100年暴卒。——谭注\n的改变,并非是威廉征服者的事而是亨利二世的事。帕尔格拉夫的著作在细写诺曼各公爵与在纠正梯叶里对征服的谬误看法等方面是有成绩的,另外他的书还有下述一个优点。正因为他发现了罗马帝国并非终止于476年,于是他抓住了进入中世纪史的钥匙。在开首的一章里他写道,“罗马的残暴行为(数量之大令人不解),它的种种罪恶以及它对上帝的极端仇恨,等等,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没有人比他更加佩服罗马的政治天才。他著作中的最好部分是关于喀罗林帝国和它后继者的叙①述。弗里曼说得很对,“在不出罗马帝国这个富于魅力的范围之外,他确实发挥出了他的最高才能。”然而这部著作的缺点却比它的优点更加明显。帕尔格拉夫的文字饶舌噜苏、太好使用格言和堆砌词句。所以他得到惩罚是:他的书无人阅读;他的历史研究的成就也几乎久被遗忘。他的第二个缺点是他对资料的使用缺乏批判能力。不错,他推翻了曾将梯叶里陷入迷途的虚构的英②葛尔夫的著作。但他自己对待价值不同的资料也是一视同仁。再有,他的重点几乎完全局限于制度与统治者方面,而对于整个民族生活则很少注意。他甚至比哈兰更好通过法律的眼镜来看问题。不过尽管有这许多缺点,他在这方面的拓荒者中仍应占有一个光荣席位。麦特兰曾以他那特有的生动笔法写道,“如果有一支大军前来,他完全可充任一位伟大司令官的。我们这里虽然不乏燕子;而且它们也都是很美丽的鸟类;但③德意志同样有过它的春天。”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历史从帕尔格拉夫身上有所获益,那④么得益于肯布尔的地方更多;肯布尔是英国的第一个日耳曼派,正像帕尔格拉夫是英国的第一个罗马派那样。在剑桥时,他曾是阿瑟·哈兰、但尼森兄弟、莫里斯、斯特林与米尔恩斯的友人,但未卒业即离校。那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行动而不在学问。他的妹妹范妮写道,“他的心思时间往往被一种热情所萦扰,以至损害和几乎排除其他一切研究。”他崇拜边沁;赞成无记名投票、撤消国教,还有其它一些先进建议。一句话,“他对政治上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1830年他曾和几位朋友同往①西班牙去帮助托利约斯的注定要失败的事。在这悲剧性的冒险结束后,他置身于条顿语言学的研究,在格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盎格鲁—撒克逊的宪章;然后据以重新构制出早期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他的《古文书汇编》收入文献达一千五百件之多,按年②代顺序排列,自厄脱尔柏特的改宗至诺曼征服止,主要是从大学与教堂等图书馆搜集的。不少这类文献前此已曾由赖麦、黑恩及其他学者刊印①见《爱丁堡评论》,1859年4月。——原注②英葛尔夫(Ingulph)—英人,克洛兰(Crowland)寺院的住持,据说《克洛兰>院史》即出自他的手笔。他死于1086年。帕尔格拉夫力图证明这部所谓“历史”,只是一部小说,可能系13或14世纪时僧侣所写。——译者<③希腊谚语:“孤燕不成春”。——译><④参阅《英国名人词典》。范妮·肯布尔的《少女时期的记录》(1878年)中常>起他。另参阅维诺格拉多夫的《英国贱民制》的精彩导论。——原注①1830年,西班牙将军托利约斯举行反对国王斐迪南七世的起事。——谭注②厄脱尔柏特,肯特国王,于597年皈依天主教。——谭注<\n过,但在可能范围内,这些都是经他重新录出的。他曾得意地说过,“这里开放给语言学家、法学家与古文物学家的这份知识宝库所将产生的结果,必远远超越我国与我们时代的界限。”这些宪章对不动产法、占有性质、以及国王、贵族与教会的权限等等颇能提供资料;同时其中遗嘱部分在家庭对动产与不动产的安排处理方面也能告诉我们许多知识。但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仍在大量收集的资料上面,而不是对资料的处理。麦特兰曾说,“肯布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即使按照他那时候的标准,他也够不上一个良好的法律文献编辑家。”“英国人身上的最高贵部分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而来。尽管有着各色各样的影响,我们和我们祖先之间,还是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肯布尔的伟大著作正是在这种十足的日耳曼主义的精神下写成的。《英国的撒克逊人》一书出版于1849年,曾经题献给女皇。书的描述主①要以自己的《文书汇编》与索普的法律汇编为依据。实际上这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叙述,而是本论文集;内容讨论了制度、阶级与一些其它问题,每篇文字独立成篇。社会的每个方面几乎尽行涉入,其中关于异教徒一章并对入侵者的文化背景作了概述。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望见工场的尘埃,但它的卷帙中却充满着新资料与新见解。通过考察地名,部分地帮助他证明,条顿人的征服在定居地有史可查以前早已开始。他同意帕尔格拉夫的主张:入侵者不费力地征服了凯尔特族,而且没有消灭他们;但它认为当时社会制度的根基则是由入侵者所携来的“马克公社制”。由于入侵者人数比较少,他们只分掉了所征服的土地的一部分,其余土地则以公社土地的名义仍留在居民手中以供来日之用。封建主义的产生正是因为这批保留土地落入了少数豪强之手。这时自由人已不复能够获得新的土地,而只能从领主那里谋求生计。土地乃是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在自由社会时代是如此,在庄园制取代它们之后也无不如此。无论不列吞人还是罗马人都不曾在他们后裔的生活上或制度上留下痕迹。说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本质上及是属于条顿的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他关于社会结构的描绘却有严重错误。例如“马克公社制”便决不是定地的通例,而只是个别现象。至于把族有地看作不占领但凭托管的认识也纯属一种虚妄。但另方面,他对宪章的熟悉却也使他能够对法律领域中的各个方面问题均能有所阐明。虽然他的书更像一部百科全书,而不大像历史,但它支配了英国的学术达一个世纪之久。经康拉德·摩①勒介绍入德国后,他对研究中世纪制度的德国学者产生过持久的影响。II②林加德关于中世纪英国初编诸卷的成功稍逊于他后出的几卷;后者①书名《古代英国的法令与条例》(AncientLawsandInstitutionsofEng><规章。——谭注①摩勒(Mourer,GeorgLudwig,1790—1872年),德国研究古代和中世纪>耳曼社会制度的著名学者,在探讨马克公社的历史方面作有贡献。——谭注<②林加德于1806年出版《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古制》,后在1819—1830年间>版《自罗马首次入侵至1688年威廉与玛丽即位时期的英国史》\n把历史一直叙述至1688年革命。他对自己在书中不大拿见解一事所提的理由是,“我对一些事件的动机、起因等有时无知,对一般所说的历史的哲学缺乏体验,因为这些在我看来实无异传奇的哲学,因而在权威默不作声的地方,我宁愿让读者们去自行判断。”在叙述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起源时,他承认教会内部存在着严重弊端,并谴责了那项反对亨利八世的教令,认为这是蓄意报复,而将教会领导权凌驾于国家领导权之上,只会败坏人民的精神和导致消极的服从。他对任何地方出现的虐政暴行都毫不偏私地加以谴责。“玛丽统治时期的最大污点莫过于她对宗教改①革者的残酷迫害。结果弄得人心恐慌,期盼着一个能有立法的清明时代。”在论述玛丽·斯图亚特时,他不表示自己站在任何一方;至于对伊丽莎白,他的立场也几乎同样不够明朗。按新教徒的说法,她的治下非常幸福;按旧教徒的说法,这个时代便是民族遭劫。但是他虽对这整个时代不作判断,他倒也说过这位女王缺乏果断、偏私易怒,并暗示她私德败坏。关于斯图亚特朝的诸卷,同样是这副过于谨慎的味道。“现在有人怀疑我可能有时受到宗教偏见的左右。流露这种怀疑当然一点都不费事,只是我不了解他们发现了什么这类重大错误。”他宣称劳德与他的仇人都是“同样顽固、同样自以为是、同样毫不容忍。”查理一世的被弑是“对王室的一个可怕教训,说明它必须注意舆论发展,善自节抑,以勉副臣民的合理要求。”但是在论及胜利的清教徒时,他却忽而措辞②激烈,大异平日。例如他骂威克斯福与德罗厄达的征服者是“无情的野蛮人”,而克伦威尔本人则是盛气凌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这人竟把掩盖真情视作人类智慧的完美境界。书的第八卷出版于1830年,结篇时对詹姆士二世进行了一番审慎的辩护。林加德的书是论述英国史上两个重要世纪的第一部近代著作。他的宗教态度是属于法国高卢教派的;而他的政治观点则属于辉格党。约翰·爱伦在《爱丁堡评论》中曾多次对他加以攻击,指斥他掩盖和歪曲事实。哈兰称颂他的锐利与勤奋,但惋惜他根深蒂固的偏见。爱里逊也说他是一个有党派偏见的人,但没有人比他更善于掩饰他的偏见,他的偏见不在其所言,而在其所不言。骚塞对他宗教改革各卷的评论意见使他扩展成了他的《教会书》。这时林加德的语调逐渐变得较为率直。他承认道,因为他必须在新教徒中间取得信任,所以他著作的初版里态度极为谨慎;现在即已取得信任,他才把起初回避的刑法等问题也一并载入。他把“新教徒思想上对天主教理论的革命”归功于他的著作。由于新教的需要,他对原书作了修改。1851年当他八十岁时他很高兴生前能看到自己书的节本与几种文字译本的问世。第一部具有国内外意义的近代英国史著作,是哈兰的《宪政史,自(HistoryofEnglandfromtheFirstInvasionbytheRomanstotheAccessionofWilliamandMaryin1688)八卷。——译者①玛丽在位期间(1553—1558年)一贯迫害新教徒,至1555达于极点。是年,被烧死的新教徒约三百人。——谭注<②威克斯福(Wexford)地在爱尔兰东南部,德罗厄达(Drogheda)在爱尔兰>北部,两地1649年时均遭受过克伦威尔军队的蹂躏与屠杀。——谭注\n亨利七世登位至乔治二世逝世》。书写于托利党的优势尚未衰落之时,因而它无异一篇政治宣言。骚塞在《季刊评论》发表的一篇辛辣的论文①里曾指斥过“它的狠毒、傲慢、不公与乖张气”。实则,哈兰属于辉格党的极右翼。他厌恶政治与宗教的暴虐,但对于群众的智慧也无信心;“改革法”虽出于他的友人之手,也因过激而不能为他接受。他的著作是对都铎朝与斯图亚特朝专制政治的一种持续的攻击和对1688年原则的一番歌颂。于是休谟的影响被打了下去,17世纪的托利见解也被普遍放弃。正当“改革法”开始了一代辉格党政治的同时,哈兰也开始一代辉格党史学。他的影响的增长还与他语气的温和以及文体的谨严有关;他的文章曾被人比作公家文书或法官判词。②哈兰颂扬了“那位冲破罗马羁绊的伟大君王”的功绩。然而,他书里的亨利仍是一个有才而凶横的君主,“属于忿怒上天所树立而为卑顺①的臣民所难耐的无数暴虐君主之一”。他看不起克兰麦。他对玛丽的迫②害行为的谴责也并不比他谴责她妹妹严惩天主教徒的行为更加厉害。都铎王室的人都专横暴君;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垄断权问题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公众舆论才开始发挥作用。宗教改革是由世俗、自私的人们所进行的一场有益的运动。在一个爱好法治者看来,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几乎是同样可恶的,但在他们的臣看来,斯图亚特朝的压迫似乎更加难于容忍。哈兰对作为一个宗教运动的清教并没有什么同情,但他对律师与乡绅反抗王朝的侵犯权利的作法却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没有一个专制政府在文字上遭受过这样令人晕眩的严重打击。林加德曾温和地谴责③过开头两个斯图亚特君主的顽固;葛德文也曾痛骂过他们的专制主义。④但哈兰对斯特拉福的背教、劳德的不容忍以及其主人的不可悛改的不忠⑤实态度严厉斥责,却产生了远为深刻的效果。艾撒克·狄士累利力图为詹姆士与查理挽回名誉的作法,并未使舆论受到影响。哈兰虽以英国历史家所未曾有过的力量与权威来讲话,他所发表的判断仍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不过他也决不是对民党的行动乱加恭维的。他倒更愿意只将斯特拉福永远放逐。他认为查理作恶的权力在1641年时已告结束,因而无再使用武力之必要。他对处死劳德与国王的作法是不满的。日后的研究成果表明,哈兰的名著当中恰恰是这一部分最欠完善。在他看来英国当日已有一部明确的宪法可加破坏,而斯图亚特朝的开首两个国王便是这种破坏者。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如休谟;后者认识到这两个英王也大有可争辩的余地,因为先例所指示的方向并不一律。国①哈兰对这项攻击不胜痛恨。能阅斯迈尔斯《约翰·墨累》,卷II,第263—264页。——原注②指倡导英国宗教改革的国王亨利八世。——谭注①克兰麦,(Gramner,1489—1556年)在亨利八世与其后天主教徒西班牙公主离婚时任坎特布里大主教,支持国王与教皇决裂。——谭注②指伊丽莎白女王,她和玛丽均亨利八世所生,为同父异母姊妹。——谭注③葛德文在所著《英吉利共和国史》(HistoryoftheCommonwealth)中严厉谴责斯图亚特朝诸王,特别是查理一世残民以逞的暴行。——谭注④似指斯特拉福任爱尔兰副总督时既压迫天主教徒也压迫清教徒。——谭注⑤艾·狄士累利著有《查理一世的生平及其统治述评》(CommentariesontheLifeandReignofCharlesI)共二卷,1851年。——谭注\n会享有着立法与控制物资的实权,但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领导权却一向属于王权的职能范围。王座特权不是法律的仇敌,而是一个补充权,包括法律所未曾特殊规定的事项;在君主与国会的多番决战中,合法权利绝非仅是永远属于后者一方。这位辉格历史家对“共和国”与“护国主政府”的好感并不比他对斯图亚特的专制政治多些。麦考莱便说过,“他①是一个绞刑法官。他的黑冠是经常能派用场的。在那长长的名单当中,难得有哪一个能逃得脱判决及其执行,尽管他们都不缺乏品德的证明与宽恕的保举。”他承认克伦威尔使英国再度成为一个强国的功绩,但作者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拿破仑式的自私暴君,并慨叹他“吸吮了一种昏乱狂热的渣滓。”另一方面,他对保守的1688年革命加以祝颂,而他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形成了辉格党政治理论的一种古典解释。此书在详述了威廉时代新订宪法的运用后,略谈了继他之后三个朝代的情况。《宪政史》是英国历史著作中的一部巨制,曾被大学采用为课本,国会中经常为人引用,维多利亚年轻时就和她丈夫一起熟读过此书,把它看作一本政治指导。这部书还在基佐的主持下被译成法文;并得到了全世界爱护宪政自由的友人们的无形接受。①如果说哈兰是辉格党历史哲学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麦考莱则是它的最著名而又最雄辩的解释者。我们要读通哈兰的三卷《宪政史》是得费一番气力的。书中的议论阻塞了叙述,法律与政治的学说掩盖了人物;但任何人却能够顺利地阅读麦考莱即使有人害怕阅读他的大部头《英国②史》,他也不难从他十余篇精采的论文里滤出他的见解。他们两人一道对一般人看法的形成起到过决定作用,直到后来兰克与加迪纳才把17世纪的历史提到超出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之上。③正像提尔华尔与小穆勒那样,麦考莱也是一个特别早慧的人。他开始编写《通史》和著文作诗的时候,正是其他孩子还在幼儿园阶段。他难于忘记,正象别人难于记忆那样。一次,他竟开出一张一百年来“剑桥数学甲等生”的一张名表,连他们的试期与所属学院也都全部注出。他说,任何呆子也能够把坎特伯雷里的大主教们的名字倒背如流。他一④⑤次说过,如果《失乐园》、《天路历程》或《查理·格伦狄逊勋爵》的所有版本全部被毁,他也能把它们全部默写出来。他对政治的兴趣发①英国法官宣判死刑时戴黑冠。——译者①参阅屈维廉的古典传记,1876年;乌礼逊的一卷,见《英国文人》,1882年;R.C.俾替,《麦考莱爵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人》,1938年。评传方面计有:摩莱《杂文》,卷II,1877年;李斯廉·斯提芬《图书馆内札记》,卷II,1892年;巴佐特《文学研究》,卷II,1878年;赫伯特·保罗,《人与书》。麦克维伊·内皮尔《通讯集》,1879年,集中所收资料丰富。——原注②此书全名为:《詹姆士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II)五卷,1849—61年。——谭注③小穆勒,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JohnStuart1805—7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谭注④《天路历程》为英国传教士兼文学家班扬(JohnBanyan1628—1688年)所作之著名宗教寓言小说。——谭注⑤《查理·格伦狄逊勋爵》为英国小说家黎吉生(SamuelRichardson1689—1761年)所作之小说,查理·格伦狄逊是书中的男主角。——谭注\n生得较迟,但并非不够浓厚。在克拉时,那些常到他父亲家访问的福音主义者尽是些托利党人,但后来在剑桥时他却逐渐厌恶起托利政府,因而出校后他已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人。他最早出版的作品中古典与近代①的题材都有。罗马与雅典杂记以及那本精妙的《考莱与密尔顿关于内战的谈话》,已显示出他文章的气势与流利。1825年在他的密尔顿论发表于《爱丁堡评论》后,大家觉得一颗最明亮的巨星已经升起。他驾驭知识的娴熟、引喻的丰富与语言的敏捷有力都是惊人的。杰弗雷说道,“我越想越想不清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那种笔调”。辉格党的这个大机关报不仅招收来一名有才干的论文家,而且也获得了一个有力量的新兵。他以拥护《失乐园》的作者的同样热情来拥护作为政治家的密尔顿。于是这位今后将一生从事于破坏斯图亚特朝名誉的作家遂向该王朝发出了第一炮,而克伦威尔也被置于与华盛顿和玻利瓦尔并列的地位。如果说这篇文章对于政治与风尚等严重问题未免自信过度的话,这个缺点当时的人也几乎未曾注意到,那个世代的人们是惯于谩骂的。四年后,麦考莱在一篇题为《历史》的论文里就他自己对于历史家的任务的认识作了说明。他宣称,想要作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家,也许是智力上最稀有的成就。在科学上,诗歌上与演说上是有不少的完善作品的,但没有完善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不过是一位可喜的传奇家。修②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洞察力很强的专家,但思想很不深刻。普鲁塔克颇有③稚气,波里比阿文章枯燥。李维对真实性漠不关心,其严重程度为历史家中所罕见。塔西陀是古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与最伟大的戏剧家,但他却不可凭信。近代历史家们对真实的观念较为严格,在综括推论方面也较优越,但他们的偏见却往往引导他们歪曲事实。休谟的著作是一大堆①诡辩。骚塞是英国国教的文人,林加德是罗马教的文人。吉本恨教会,密特福恨雅典人。他们忙于争辩,而忽略了叙述的艺术。事实仅仅是历史的渣滓。理想的历史家不仅必须懂得怎样画,还必须懂得怎样绘;不仅必须掌握人类的行动,还必须掌握人类的文化。这套主张在他的《史论》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其中有些具有永久价值,另一些只是因为文章不错才幸免湮沉。他最好的文章是关于17、18世纪的英国历史论文,而其中关于哈兰的论文是早写成的也是最重要的。在评论的掩护下,麦考莱乘机对托利党人关于英国历史的解释大加攻击。他对克兰麦的指斥几乎和对“傲慢的背教者”斯特拉福的指斥同样严厉。他宣称,查理一世一生充满虚伪,并说,他对他臣民自由的仇恨曾是他行为的指导原则。他一笔扫除哈兰对长期国会行动所作的重要批判。他自认他对劳德,“一个可笑的老顽固”,比对我们历史上任何其他人物都抱着更多的十足轻视态度。他谴责内战在它的早期阶段的半心半意的进行:只是到1649年它的最后一幕时,他才发出抗议之声。虽①考莱(Cowley,Abraham,1618—1667年),英国诗人。——谭注②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所著《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对后代思想、文化与史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谭注③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122年),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家,著有《通史》,不仅记罗马帝国的扩张过程,兼叙地中海沿岸各族的历史,并发扬了修昔底德的注重客观公正和求真的精神。──谭注①骚塞,罗伯特(1774—1843年),英国桂冠诗人、历史家。——谭注\n然他不是清教的爱护者,但他关于克伦威尔的性格与政策的有力颂赞却为卡莱尔铺平了道路。复辟时期的黑暗图景引向了1688史》,不仅记罗马帝国的扩张过程,兼叙地中海沿岸各族的历史,并发扬了修昔底德的注重客观公正和求真的精神。——谭注年的光荣革命,不过说到光荣,也只是威廉一个人“光荣”。论罕普登部分地讲述了同一范围,不过文笔更有节制罢了。詹姆士一世的描写,是这个历史家写得最坏的一篇;①关于无污点的英雄的描写则显示出他对这个人的崇拜;他和威廉两人在他自己的情感中都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关于玛金托希的论文则为这次革命提供了理由充分的辩护。关于贺拉西·华尔波尔与查塔姆的研究表明:他关于18世纪的知识殊不亚于他关于17世纪的知识。他从印度归来后②所写的论文更有分量但论战性质不强。论腾普尔是他最成熟的作品,而再论查塔姆则是人物肖像的一篇杰作。几年后他为《英国百科全书》撰写的庇特传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决不是篇篇论文都达到了这样的高度。③麦考莱对于斯图亚特朝以前的知识是不足的。论柏力便写得平庸;至于论培根一篇则是他一生中最明显的失败。如果说这篇关于培根哲学的讨论以及这篇文字对理想主义的讽刺和其间流露的庸俗功利主义严重地打击了麦考莱的思想家的声誊,他的那篇政治叙述,(按指论柏力的那篇——译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哲学家被抬高到太不合理的程度,而那④⑤位政治家被贬抑到不公平的程度。虽然几年之后斯佩丁把钟摆太过分地推到另一方向,但这至少是对这位论文家的明显不公道的一种揭露。麦考莱自加尔各答返回后不久所著成的两篇关于印度的著名论文属于他最动人的作品。他埋怨说,任何学童都能指出欧洲史上主要战役的日期,但许多英国人对自己民族在亚洲赢得立脚地的种种胜利战役的名①称,竟也茫然无知。在这两篇论文中,《克莱武》虽不够出名却写得较为确切。这个离开办公案桌而前往战场指挥军队的青年,曾赢得普拉西战役于是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终因被其国人控告盗用公款,而致自刎。其人其事,充满着为麦考莱所喜爱的色采与传奇。《华伦·哈斯丁斯》把这个大总督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总督一方面同他的行政院冲突,另一方面同印度土王冲突;一番经历饶有趣味。增强英国权力所施的诡②③计、同敖德的贵妇们所进行的勾心斗角以及南科马的陷害案,一件接①按即克伦威尔。——译者②腾普尔(Temple,SirWilliam1628—1699年),英国外交家、散文家。曾促成英、荷、瑞典缔结反法同盟,促成奥伦治亲王与玛丽公主的婚姻。复辟时期拒不接受查理二世的任命。——谭注③柏力(Burleigh,W.C.1520—1598年)亨利八世及伊丽莎白两朝历任要职,主张开放贸易,废除了一些专利事业。——谭注④斯佩丁(Spedding,James1808—1881年),英国历史家,致力于研究F.培根及其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著有《佛兰西斯·培根的生平及其书信》(LettersandthelifeofFrancisBacon)七卷(1861—1874年)。——谭注⑤他的《评论家夜话》,共2卷,1848年,其中载有一篇系统攻击《论文》的文字。——译者①克莱武(CliveRobert1725—1774年)英国将军,为英国奠定独占印度的局面。——译者②哈斯丁斯任总督后将一切地方权力收归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拿瓦布给与年金。当时敖德的拿瓦布年幼,由其父后宫妃嫔照料,于是哈斯丁斯乘机从贵妇们手中掠夺土地和财富。——谭注③南科马亦译难德·拘摩罗(NundKuma),孟加拉封建主。因不堪哈斯丁斯的勒索,对他提出控告。哈斯\n一件地迅速发生。画面上重新呈现出富饶东方的魅人景象、奇风异俗与绚烂色采。这位超人的魔术般的巧思乃是西敏寺厅的大审案和柏克的雷④霆般的报复攻击的前导。虽这些描绘是作者画廊中一幅最夺目的艺术品,它却是一幅非常失真的画像。哈斯丁斯的出名虽有赖于麦考莱,但他的名誉却还有待它人的辩护。麦考莱关于欧洲大陆历史的知识是有限的;因而当他写这方面的著作时,他笔下就不那么自如了。他的论马基雅弗里与其说是历史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论文。他关于西班牙继位战争的描写,因为插入安妮女王会议室的内幕消息而显得内容丰富。但他关于兰克《教皇史》的论文则完全徒有其名。他把教廷利用种种新运`动之技巧拿来与造成卫士力的错误的莽撞的迂腐态度相比,而殊不知罗马因未能避免掉宗教改革,失策①更大。他论腓特烈大王的文章是他最坏的著作之一。关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讽刺描写,其根据是威廉美那的回忆录,他使用时丝毫没怀疑过②③回忆录很不可靠。他说,这个国王最好把他描为摩洛赫与帕克之间的混血儿。麦考莱此文著于兰克的《普鲁士史》问世之前,因为我们很难因他对这个普鲁士行政制度的创立人之重要性未能认识而予以指责,但他却完全应当能够对蕴藏在那个粗暴外表之下的优点稍有察觉。再有,关于腓特烈大王的描写也几乎同样不够真实。他被描写成一个坏心肠的人,一个无忌惮、无信仰、无慈悲的暴君。称之为暴君,正是不理解“开明专制主义”,而这主义正是19世纪中的突出特征之一,它完成过很多有益的改革。如果说麦考莱并未发明史论这种体裁,那么他初看见它时它是砖造①的,而他离开它时,它已是云石造的了。他的文章在尘埃厚积的《爱丁堡评论》里面简直像钻石一般地闪闪发光。我们只要把他的稿子与锡德②③尼·斯密士、杰弗雷或布鲁姆的比较一下,马上便可看出新旧文体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麦考莱史论为17、18世纪所完成的工作,殊不下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为15世纪所完成的工作。麦考莱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一个到澳洲的旅行家曾记载说,他看到每个移民的书架上都有的三部书便是,《圣经》、莎士比亚与《史论》。他旧时读书的学院礼拜堂的自己纪念铭文上刻着:“他这样地写作,使历史可愉快地阅读,如小说然;”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本能打动各个种族的人们的著作,一定是有其特殊的优点的。他的引力的秘诀即在:他是④从来写史人中最有魔力的讲故事者。他曾被称为史学上的鲁本兹。他的丁斯买通孟加拉高等法院以伪造文书图谋判乱罪将拘摩罗判处绞刑。——谭注④在哈斯丁斯受指控期间(1788—1795年),时任议员的柏克对他多次进行弹劾。——谭注①关于德人的忿懑,参阅豪塞《文集》卷I与巴斯·雷蒙《英人目光里的腓特烈二世》,《演讲集》卷I。——原注②摩洛赫(Moloch)——古腓尼基人所供奉的火神,以人身为祭品。——译者③柏克(Puck)——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好恶作剧的妖怪。——译者<①拉丁成语:“Latericiamaccepit,maroreamreliquit”(他接下砖城而遗下><。——译><②锡德尼·斯密士(1771—1845年),英国国教教士,散文家。——谭><③杰弗雷与布鲁姆,均系辉格党刊物《爱丁堡评论》,创刊初期的主编。——谭><④鲁本兹(Rubens,1577—1640年)——荷兰大画家,名作有:《耶稣自十字架><》(“DescentfromtheCross”)\n画像萦回于记忆之中,仿佛我们曾在舞台上亲自见过一般。在表达的生动上,他足以与卡莱尔、摩特莱与米什莱比肩。1830年他进入议会后乃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演说家,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哪个历史大家能象他这样地懂得议会政府的精神。戏剧能力而外,他兼备着无穷尽的学识,因而他遂能以千变万化的生动笔法来增强他的叙述。虽然戏剧本能、政治生活经验以及无限知识都有助于他写成卓越的史论,但它们成功的决定因素,仍在文章。对于一个读惯了沉重庄肃文体的世代,他的迅畅、精采、明净的散文,简直象一个渴饮者的一掬清泉那样。不过这文体有时对演说比对论文更为适合;这种光华四溢的雄辩,时时会变得浮夸而迫人。繁词缛句,叠床架屋,致使人们有不堪重压之感。在他论密特福的早期论文中关于雅典文化的一段颂赞,原是一篇惊人的演说文学,但一旦印成白纸黑字,读起来便会感到令人作呕。阅读麦考莱仿佛象在清爽的空气里快步疾走一样——令人无限兴奋,但却不是一种适宜于任何体质或任何生活时期的运动方式。从这些史论的轻松精神、充溢自信与丰盛浮夸的词藻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年青心智的产物;因而它们对于初露才华的青年人们也就感染最强。关于麦考莱无所不知的说法纯属一种神话。他的知识宝库虽说是惊人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缺陷。他对古典文学的精熟是可观的,但关于中世纪时代,除但丁与佩脱拉克而外,他却几乎毫无所知;既使对英国史的伊丽莎白前期,他的修养也是不过是有普通教养的水平。关于大陆国家的成长,他熟悉的程度非常有限。他精通近代英国文学与拉丁族的南方文学,但对德国文学便所知甚少。他对于宗教与哲学思想的知识更是异常有限。就在他编写他自己著作的时候,他对创造了历史科学的那种耐心研究精神竟然毫不了解,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个缺点则是他的政治偏见。他的史论大部是以评论形式出现的,其主要目的则在传播某种主张。如果以评论专业学者论文的标准来应用于他的论文,那对他是不公道的。我们不该以评断科学论著的标准来评断一篇政治宣言。在他那里,中立性或超脱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忠实地相信:辉格党的原则是政治智慧的全部内容。直到他生命终了时期,他仍然是一个1832年时的人。所以这位最出色而又最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便同时又是一位最不够分量的历史学家。《史论》的第三个缺点则是它们的那种铁鎚般的粗暴的文风,正象一个颇以自身的膂力为快的巨人那样,他好发出使人晕眩的打击。一位敬佩他的朋友麦金托什曾说,他的缺点恰在他对他的对手们的才能与性格不能给予适当尊重。墨尔本也说过,他但愿自己对任何事情有点自信,正象麦考莱件件事情都很有自信。1843年《史论》重印时,其中某些带触犯性的词句曾作了一些削删或缓和,但这项簸扬工作却做得不够严格。在评论博斯伟尔的著作出版时,他很高兴乘此机会对一个政治反对①派进行猛攻:他写道,“我把克罗克打得鼻青脸肿。”他晚年时曾公开与“圣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图”(“Crucifixiono><①克罗克见第十二章释注。此指麦考莱所作《克罗克刊行的博斯威尔著〈约><〉》一文对克氏的抨击。——谭><\n②忏悔过他对老穆勒的攻击,但却很少由于良心上受到这类谴责而感到不③④⑤安。不论在论骚塞、萨德勒、巴勒尔与罗伯特·蒙哥马利的文章里,都充满着咆哮的谩骂。他爱用夸大词句。腓特烈大帝的诗,是“神人共厌的”。我们正是由于劳德的鲁钝而容易忘记他恶毒心肠。他甚至以阅读那勒兹的《柏力传》与踩踏轧机相比,认为后者更加愉快轻松。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说,深浅分寸就都谈不到了。勒那说过,“真理即在分寸”;但对麦考莱来说,真理有时完全可以换成一句有力语言或响亮词句。他的最后一个弱点便是,他对于有些的思想类型与性格类型缺乏一定的洞察能力。他的豪爽脾气与率直性情使他难于理解复杂个性。他对于自己的时代思想的终极性——“历史上最开明的民族的最开明的世代”——过于相信不疑,以致使他不能深入了解其它时代的思想。卡莱尔曾简洁地说过他,他是“一个有魄力,真正有力量的人,但不幸他没有圣洁的思想。”他键盘上的音调是很少的,他的感情经验的范围是异常有限的。他对于被剥夺者们的强烈不满或神秘者的渴望都是不同情的;他还公开蔑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的一切理论。麦考莱既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预言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通情理和有文化的庸人。麦考莱在大学时期所写的关于威廉三世的论文表明,这位救星的性格对这个年轻的辉格党人曾产生过深刻印象;而关于哈兰与玛金托希的论文,也曾热烈地表达过他的景仰之心。1838年,他计划编写一部英国史,自复辟时期叙至乔治四世逝世,而次年他已动手编写。1841年当墨尔本政府下台时,他曾表示:他希望能够长期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以便把他叙述的历史一直叙述到安妮女王死时为止。但这工作比他所预想的要庞大得多。他放弃了替《爱丁堡评论》的撰稿工作,辞掉了剑桥大学近代史的讲座聘请,以便以全副精力投入这项著述。当1859年死神突然来袭的时候,他的叙述还没有达到威廉统治的末朝。1843年他《史论》的重印表明了他读者数量的可观;而“无穷尽的需要”也鼓励了他加紧他的更加沉重的劳动。1848年在《英国史》的开首两卷销行时,他傲然自得地写道,“我甚至时常想到2000年乃至3000年”。他在写给马克维·内皮尔的信中说,“我是不会感到满意的,除非我写出的东西能在几天之内替代了年轻淑女们桌几上的最新时髦小说。”这种雄心实现了。①自从《威弗利》出版以来,从来还没有过一部书有过这种盛况的。书译②即詹姆士·穆勒(1773—1836年),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鼓吹功利主义。麦考莱抨击穆勒的论文有:《穆勒论政治的文章》(Mill’sEssa><谭注③萨德勒(Sadler,M.T.1780—1835年),政治经济学家,下院议员,著有《人><》一书。——谭注④巴勒尔(Barére,deVieuzac1755—1841),法国政治家,曾任救国委员会><著有《回忆录》。——谭注⑤罗伯特·蒙哥马利(1807—1855年)英国诗人。麦考莱对他们作品的评议,><《骚塞关于社会的对话》(Southey’sColloguiesonSociety),《评萨德勒的〈人><〉》(Sadler’sLawofPopulation),《驳萨德勒的申辩》(Sadler’sreftationrefa>①威弗利(Waverley),原为司各特第一部小说《威弗利》中主人公名,嗣后成为斯各脱小说全集总称。\n成各文明国家的文字;荣誉从外国学术界里似潮水般地涌来。除了他的宿怨克罗克在《季刊》里发表过一篇激烈的攻击文外,各个学派的评论者全都异口同声一致称颂。爱里逊虽指出过它的片面性,但也誊之为一部高贵的书。这项成就也是完全应得的。虽然整个来说《英国史》不如他的《史②论》精采,却是一个远为伟大的重要成绩。这著作属于他的思想更趋成熟时期的作品,在那里旺盛的精力与一种清新而可喜的成熟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这时宣称,英国对于它历史上的两个政党,都有其需要。这里,不论学识与准确性都提高了。他慢慢地写,在收集与编排资料方③面都花费了无限辛苦。为他作传的外甥写道,“他的心神始终不能安定下来,直到每一段文字都能以一般警语结束和每一句子都能似流水般地顺畅。”他从他读者的欣赏里找得了酬报,而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很少阅读其他书籍的。有一个集会上曾通过一项对他表示感谢的决议,因为他“写了一部工人都能读懂的历史。”一个在印刷所工作的读者告诉麦考莱说,他在这两卷里只有一处措辞不能在一瞥之下抓住意思,他对于这句话特别感到满意。二十年的研究工夫才写成了同样长时期的一段历史。虽然这些书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片断,但它还是自吉本以来在英国语言中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我的目的不仅要叙述政府的历史,而且要叙述人民的历史,要探索实用与装饰技艺的进步,描写宗教派别的兴起与文学爱好的变化,以及描绘历代的风尚习惯。”那论述1685年时英国状况的有名的第三章为戏剧提供了背景。如其说《史论》显示了一种罕见的概括能力,那么《历史》的成功却有赖于更为宽阔的活动余地。但他在方法上的缺点是:他的方法只能应用于一个短暂时期,而对于这个时期来说,资料却丰富得容纳不完。在对英国复辟时期以前历史的一番简描之后,接着是关于查理二世期间的精采一章以及关于全国情况的一个综述;在这之后,详细的叙述便从詹姆士二世的登位时期开始。故事是一连串夺人心目的场面:开始①②于蒙穆斯的冒险与血腥巡回裁判所(BloodyAssizes),历史遂以对大③④学的进攻、七个主教的遭审、威廉的登陆与詹姆士的逃亡为其高潮。关于詹姆士二世诸卷,是在快到1848年时写成的,结束部分对于1688年革命作了一番尽情的赞颂。“这是一次严格防御性的革命。在几乎每句言论与每件行动上都可以看出它对过去的深刻尊重。由于它在所有的革命中是最少强暴性的,它在所有革命中便是最有益的。为了法律的权威,为了财产的安全,为了我们街道的和平,为了我们家庭的幸福,我——译者②最佳版本为斐司的版本,1913年,斐司的遗著《麦考莱的英国史》(1937年)是一部杰作。——译者③屈维廉著有《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LifeandLettersofLordMacaulay)。——译者①蒙穆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1685年率军潜往苏格兰,自称国王。兵败,被杀。——谭注②蒙穆斯失败后,英王组织巡回法庭审处作乱者,备极残酷,因有此称。——谭注③詹姆士二世压迫新教,向国教势力强大的牛津大学施加压力,没收学院财产,企图建立天主教神学院。——谭注④1687年,詹姆士二世颁布信仰自由公告,命于教众中宣读。以坎特布里大主教为首的七主教吁请收回成命,因而被捕受审。——谭注\n①们除对掌管国家兴亡的上帝感谢之外,便应感谢长期国会、代表国会与奥伦治·威廉。”七年后,叙述威廉三世的两卷续出。饱经人世沧桑变②幻的英雄壮志,冷峻的外表背后对他妻子、对本廷克和对凯佩尔的一副缱绻柔肠以及他如何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置之于新教欧洲的利益之下的精神;这一切错综交织起构成了一幅麦考莱所绘过的最惊人的形象。在与这伟岸的形象对比之下,甚至最好的政治家,无论辉格党的还是托利党的,都不免显得矮小和偏私。他为这两卷所作的准备工作,甚至比前此几卷所做的还要艰苦。“我首先要通过阅读与旅行,来获得关于威廉统治时代的完备知识。我必须考察荷兰、比利时、苏格兰、法国各地。我③必须查遍荷兰与法国的档案。我必须察访伦敦德里港、波印河、奥赫里④①②③④姆、利默里克、金萨尔、那慕尔,再次访问兰登与斯坦扣克。我必须翻阅百种千种小册子。”他日记里这样记下的计划,竟一一忠实地执行了。《历史》一书的生动性很多是与他对书中涉及到的各地有直接了⑤解一点密切有关。全书不少部分固然精采,其中伦敦德里之围与葛伦科⑥大屠杀的叙述,就尤其写得绘声绘色。关于国家公债的起源、英国中央⑦银行的创立与出征德利安等部分也都篇篇是精心之作,能够当作短篇专著来读。《历史》是对1688年革命及其主要发动者的一篇颂歌。更富批判精神的新一代虽然接受了麦考莱关于1688年的恩惠的说法,但对这场戏中的扮演人们则颇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搁下其史笔不多几年之后,近代⑧史学家中最称伟大的一位便部分地涉历了这同一范围。兰克争辩说,麦考莱把查理二世时的长期国会的功绩都推给了辉格党,但这个党却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另外兰克还把托利党人通通写成极端僧侣主义者与极端君主派的作法提出争议。托利党人曾主张对法开战,并安排过玛丽与威廉的婚事,而这两件事都是辉格党人所反对的;另外,托利党人还准备限制詹姆士的权力,而这事和他们的反对者所做的也并无两样。他们对抵抗的权力谈得确实不多,但当危险迫近教会与宪法的时候,他们却也同样愿意奋力加以保卫。麦考莱在谈到詹姆士时自始至终是一派①代表国会(ConventionParliament)——英国两次非常国会,以其非由国王命令召集,故称,一次为1660年时蒙克将军所召集;另一次为1689年时为赐王冠与威廉与玛丽而召集。——译者②本廷克勋爵是威廉宠信的荷兰籍将军;凯佩尔子爵是威廉宠信的海军将领。——谭注③波印河,在爱尔兰东部。1690年7月,威廉军在此击败詹姆士军。——谭注④奥赫里姆,在爱尔兰。1691年7月,威廉军在此击败詹姆士军。——谭注①利默里克,1691年10月爱尔兰抵抗威廉的军队在此地投降。——谭注②金萨尔,爱尔兰滨海市镇,詹姆士二世自法来英,在此登陆。——谭注③那慕尔在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境。为1692—1695年间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激烈争夺之地。——谭注④兰登、斯坦扣克,均在西属尼德兰境内。1692、1693年法国先后在此两地击败英军。——谭注⑤伦敦德里是17世纪初英国殖民爱尔兰时所建的城市。1689年4至7月,拥护威廉的军民被詹姆士军围困于此。——谭注⑥威廉即位后,苏格兰高地葛伦科部落首领麦唐纳未及时宣誓效忠。1692年英军诛杀麦唐纳及其部众多人。——谭注⑦德利安地峡,在苏格兰北部。1695年威廉计划移民前往定居,遭到强烈反对而作罢。——谭注⑧对于这两位历史家的讨论,见努尔登的论文《兰克与麦考莱》,《历史杂志》,卷XVII。——原注\n轻蔑嫌憎的口吻,这种描写也是无法让人完全接受的。至于威廉的形象,则又因聚光过强而弄得面目失真;他的洗刷葛伦科污点的企图,也是一个失败。对优点缺点夸张过度以及对某种类型人物缺乏理解能力的毛病在《历史》中又有重现。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个卑劣恶毒的怪物”——守①财奴、放荡之徒、卖国贼、暗杀凶手。约翰·帕泽特曾对这幅画像作了一个深入的分析。依他的话来说便是,在那里,“文献被隐瞒,日期被窜改,无耻之徒的论调被充作纯洁和无可非议的证据而列出,那些久已遗忘的,措词恶毒的匿名诽谤竟又跃然纸上。”那个袭击布雷斯特计划②的泄漏,被说成是“他所有几百件卑鄙行为当中的最卑鄙的一桩”,但③是这个计划路易十四早就完全知道。公爵也被描成一个泼妇,既无才④干,又无品格。乔治·福克斯在他早期史论的拙劣笔调下被骂得一塌胡①涂。他对潘恩⑤的论述激起了“公谊会”的正当愤怒。亚敦挺身而出,②对丹第的受攻击作过声援。巴宾吞对麦考莱笔下的僧侣阶层的品质与社会地位的描写发表过一篇详细答辩。麦考莱太好把他那时代一些小册子与传单内记载的东西当作证据。穆勒在谈到关于威廉三世的各卷时,曾③说它们不失为有趣读物,但非正确的历史。“他对效果的追求往往言过其实,对所描写的许多人物歪曲过度,以致许多人的成就都变得无法解释。他与格罗特是多么不同;格罗特才气稍逊,但叙事简朴真实,反而更吸引人,另外还因为格罗特不求惊人而力图理解和说明。”卡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四百次的再版也不能给这些书带来永久价值,其中往往缺乏深意,不过徒逞辞令而已。”这些非难不免过苛,但麦考莱对于他的题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掌握却是有限的。他关于1688年革命的④描写过分拘泥于岛国的观点。他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关于三国同盟、⑤⑥⑦多佛条约、巴利隆与反对派的谈判以及立兹尉克的和约等等,但在这些地方他却把握不住事情线索。于是,兰克的全欧观点再次补充了这个前辈的不足。最后一项批评意见我这里还须提出。麦考莱长于描写而短于说明。像他这样对思想感情的内心世界毫无感受,对漂浮在事件表面的背后实质完全不肯费力探索的人,求之于第一流的史学家中,委实不①《新检视》1861年,这是一部叙述有力而又饶有趣味的作品。——原注②1694年7月英军计划偷袭法国布雷斯特,因泄密未果。——谭注③女公爵,似指查理二世的情妇露易莎(Lousisa)。她是法国人,由路易十四介绍入宫,深得宠信,受封朴茨茅斯女公爵(DuchessofPortsmouth)。《英国史》专门描写了她在查理二世临死前的行为。——谭注④乔治·福克斯(1629—1691年),英国“公谊会”(“贵格派”)的创立者。——谭注①亚敦(Aytoun,W.E.1813—1865年),苏格兰诗人,爱丁堡大学修词学教授。——谭注②丹第子爵,名约翰·格拉汉,复辟王朝将军。1684—1685年奉命率军镇压迫害苏格兰的护教者。1689年5月在苏格兰以詹姆士二世名义进行复辟活动。——谭注③穆勒《通讯集》,卷I,第188—189页,1910年。——译者④三国同盟,1668年英、荷、瑞典缔结的反法同盟。——谭注⑤杜佛条约,1670年英法订立的瓜分荷兰的密约。——谭注⑥巴利隆为法国驻英大使,秉路易十四之命在英国贿买反对派,扰乱政局。——谭注⑦立兹尉克和约,1697年9月英、法、荷、西所订有关英、法、荷领土及英国王位等问题的条约。——谭注\n多。哈兰与麦考莱的共同努力曾使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摆脱了休①谟的支配,但托利主义却又找到了艾利森这个新的拥护者。他写道,“鉴于局势的发展会在我们国内引起一场社会与政治的巨大动乱,因而动念②著述一部法国革命时期的欧洲历史。多年以来遍及全国的革新狂热、社会上流行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空洞思想以及政府采用这些意见时的轻率态度——这一切已都使我对前途产生悲观。”此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33年,第十卷1842年。书的序言对他自己的政治与宗教哲学表述得异常坦率。“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对人们有什么重大启示的话,那便是潮流的危险性;因为投身于政治革新浪潮的人已经被卷入其中”。幸而人们的愚蠢行为受到了一个巨大力量的制止。“行动者们在一个看不见的力量之下受到制服,这力量恰恰把他们的罪恶与野心变成了伸张天理正义的工具,因而使道德最后战胜邪恶,整个人类得到拯救。”这段话完全是那种不肯妥协的托利主义精神。法国革命乃是一个混乱的爆发,无论其原则还是结果都纯粹是破坏性的;正象其它激烈的暴乱那样,势必自食其果。“自从路易十六死去之后,转而扶持秩序与宗教的趋势已在全世界上开始呈现。”这种维护者之一,便是乔治三世。“他从未在少数有头脑的人中失去威信。书的结尾部分还用了上百页的篇幅讨论道德问题。“民主政治在一个古老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它不是毁掉社会,就是毁掉它自己。”这部被它的著者天真地称之为促进保守派立场的巨大努力的《欧洲史》,成了托利党的圣经;该党在改革国会的初期曾从这部书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滋补剂。然而,使这书获得世界声誉达三十多年之久,却并非靠它的托利主义。艾利森自己曾把这个成功正确地归之于他的题材的特别诱人和他在这个领域内的优先地位。读者对书中的种种陈腐议论完全能够将就,因为这部著作乃是关于近代史上最多事之秋的一段历史的第一次综合叙述。一时英、美社会的书斋中很少书架上不备有这位苏格兰官员的大部卷头;它的译本还把他的见解传遍全欧。但民主潮流的高涨与公正的历史研究的发展,终使他的名声衰落下去。《欧洲史》的续编叙至路易·拿破仑政变,但不如它的正编富于戏剧兴趣。作者1867年死后不久,这部《欧洲史》已经逐渐扫进旧书铺内积满尘埃的角落里去了。艾利森巨型剧中的一个场景,却另由内皮尔根据很不同的资料,更①②详细地作了叙述。他的《伊伯利安半岛战史》一书是英文中一部最好③的军事史,编写时曾得到过威灵吞与苏尔特二人的帮助。但书中所流露的偏见却和艾利森或麦考莱的书同样明显。“西班牙人曾大胆提出,而人们也都相信:半岛之得到拯救乃是出自他们之手。我反对这种说法。”①见《自传》,2卷,1883年。——原注(一译爱里逊)②书名《法国革命时期欧洲史》(HistoryofEuropeDuringFrenchRevolu-tion)十卷。——谭注①关于因这部书而激起的大量著作,参阅《英国名人词典》。——原注②此书全名为:《1807—1814年伊伯利安半岛及法国南部战争史》(HistoryoftheWarinthePeninsulaandintheSouthofFrancefromtheYear1807totheYear1814),六卷,1824—40年。——谭注③苏尔特(Sout,Nicolas-Jean1769—1851),法国元帅,伊伯利安半岛战争的法军指挥官。——谭注\n他宣称,西班牙覆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它那迷信的朝廷与残忍的僧侣阶层相结合。他们暴虐固执,愚昧矜夸,他们在战争里所表现的极度残暴简直是人性的一种耻辱。另一方面,法国人则激起了作者的钦佩,他们是那样英勇,以致只有英国军队才能够打败他们。虽然他也指责拿破仑的欺诈与暴虐,但他还是认为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最了不起的统帅和最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对苏尔特以及其它法国将领公开地表示①了钦佩。书的主角是约翰·摩尔勋爵,连葡萄牙人也获得了称颂。然而②作者的强烈情感并没有影响到他军事叙述的价值。他对亚尔布拉及其它他参加过的战役与围攻的描写,比他的唯一真正对手金拉克对克里米亚③战争的描写要更生动些。这是一部军人的著作;在他看来,战争是世界的规律;所有生物,上至人类下至虫豸,时时都在斗争。除了哈兰与麦考莱、艾利森与内皮尔的著作——这些书已传诵全世界——之外,还出了许多有用的历史著作;这些书的对象主要是学者而④非一般读者。詹姆士·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便是一部难读的书;麦考莱在1833年议会辩论中曾记这本书是“自吉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称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书的内容系关于辽远地域,叙述详尽,语调严峻。这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在叙述这个以种姓与传统为基础的社会时,他的①同情心是不太丰富的。正当威廉·琼斯勋爵在社会上对印度文化掀起了热潮的时候,穆勒对印度各族的法律制度、风习、艺术、宗教与文学的叙述方法,实在无异于一股刺骨的冷风;不过他对东印度公司及其代理人的评断也同样不少宽假。在谈到他的“浩繁的卷帙”时他的态度倒也谦逊,他认为他对印度缺乏直接知识——而这正是公正态度所必不可少的——这点,往往使他下笔不易恰合分寸。他的同情与想像也都不够。《印度史》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丰富资料和它的分析能力。它被列入当时的经典著作之一,因而为它的著者在印度部中赢得了一个席位。三十年后,这部书经过贺拉西·威尔逊的改订与续写,仍然是此后几十年内的标准著作,并被采用为印度文官候补人员的一种课本。另一方面马②克斯·穆勒声称,这部著作对印度所遭遇的某些最大灾难,是负有责任的,即使威尔逊所加的注释可作为它的解毒剂。哈兰与穆勒时代的作家再也没有像威廉·科克斯那样地不倦于出版③新资料。他所写的华尔波尔传、马尔巴罗传与柏兰传迄今还是研究18世纪者之必不可少的著作,而他关于奥国王室与西班牙波旁朝之大部头④历史著作则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他完全缺少叙述能力与文学①约翰·摩尔(1761—1809年),在葡萄牙对法作战的英国统帅。——谭注②1810年5月英军击败法苏尔特军于亚尔布拉。——谭注③金拉克著有:《入侵克里米亚》(InvasionofCrimea)共八卷,1863—1867年。——谭注④参阅贝因《詹姆士·穆勒》,1882年与李思廉·斯提芬《英国功利主义者》,卷II。——原注①琼斯勋爵(Jones,SirWilliam1746—1794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第一个娴熟梵文的英国学者。曾将一些著名的印度典籍译成英语。1784年创建“孟买亚细亚学会”。——谭注②见《印度所能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第二讲,1882年。——原注③亨利·柏兰(1695?—1754年)是1743—1754年间的英国首相。——谭注④第一部书名《奥地利王室史,1218—1792年》(HistoryoftheHouseAustria,1218—1792年),共四卷,1893—1895。——谭注<\n本领,但他却是一个勤恳的编辑者;他的著作构成了才隽之士从中汲取资料的仓库。更为通俗的则有斯特里克兰的《英国女王传记》与泰特勒的《苏格兰史》,虽然它们也是根据手稿资料的广泛研究写成的,而后者则是在华尔脱·斯各脱的怂恿下编写的。还有一部富有思想性的综合著作——《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史》,这是由马蒂诺写成的;此书迄今仍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是由一位渊博多闻的当代人编写的著作。\n第十五章提尔华尔、格罗特和亚诺尔I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著作的一般性研究,在英国比在任何其它国家更为普遍,因而古典时代第一部多少带有几分学术性质的历史遂出①自一个英人的手笔。当吉本发现他友人密特福是一位希腊文学的爱好者时,曾建议他编写一部希腊历史。这部著作在开始编写时并未涉及到当代的问题;其第一卷出版于1874年。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历史家却利用过他的著作来打击辉格党人与雅各宾党人。对于那些艳羡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并强调它们的制度是最适合于培育幸福的人们,他的回答是,那种认为这些制度在它们起源的国家里曾经确保过繁荣康乐的假设,及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在那里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是谈不到的,统治者间的关系主要是争权夺利,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其中最好的城邦斯巴达则干脆不去标榜什么民主。在密特福看来,民主实即专制;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宪法便是世间出现过的最好宪法。他对波斯人、迦太基人与马其顿人的好感是甚于希腊人的。他对僭主们备致颂扬,但对于民主派与民主活动家的任何不利的流言,则欣然接受。他天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方,而指斥狄摩西尼是懦夫与无赖。弗里曼写道,“密特福是一个不高明的学者、一个不高明的历史家和一个不高明的英文作家!虽然如此,我们觉得对他还是有些眷念的。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位揭示出希腊社会的生动现实及其所具实际意义的极有声望的作家。”①麦考莱则声称,几乎所有近代的希腊历史学家都剥夺了希腊人的个性特点,使之成为单纯的类型,但这一严重缺点密特福倒能避免。但他的唯一优点也就在这里;而就连这个优点也多少是他那漫无节制的党派心理所带来的结果。这部书的成功主要由于他的政治偏见。当时的托利党人引用它,正象在三十年后他们引用爱里逊那样。1824年时麦考莱写道,“密特福享有着巨大并且与日俱增的声望。他在历史家中间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几乎无可动摇。他本该在他第一卷出版时就受到攻击。但现在要来拦阻他声誉的发展已属一种近乎绝望的作法。”这篇攻击性的文章颇使辉格党人称快;但对于一个业已确立的声誉则很少影响,于是那经过作者修订的再版便又在1829年刊出。但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已不远了。“改革法案”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与这个历史家观点全然异趣的新时期,而同时另外两部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宽容精神的希腊史的问世,迅速变成了有力替代。在攻击密特福的同时,麦考莱表达了他所想望的真正的希腊史的出现;它不仅包括希腊的政治,而且包括它的社会、艺术与文学,以便使近代世界能认识到它从希腊所承袭到的遗产。数年之后,在各国语言中第一部堪称具有学术价值的希腊历史著述遂由提尔华尔发表。他在获得①参阅他的兄弟勒兹达尔爵士的回忆录,见1837年版,卷I。在马哈斐为度律伊的《希腊史》英译本所作的导论里,可以看到马对密特福及其他后继者的若干有趣评论。——原注①《密特福的希腊史》,见《杂文》。——原注\n①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资格之后,曾经担任大法院的律师多年。1827年时他被授圣职,复回三一学院,在那里他参加朱里安·哈尔翻译尼布尔著作的工作。他接受约克郡一笔王室领地圣俸,并于1840年擢升圣大卫主教。当他受邀为拉德纳《百科全书》编写一部希腊史时,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书的第一卷于1835年出版,第八卷1844年出版。修订与扩大版出于1845至1852年间。书的作者表示他对该书所受到的欢迎感到十分满意,认为他的原意不过是“使希腊史的著作在某些方面比原来的情形稍胜一筹。”由于他在发表意见上的拘谨,兼之风格与热情不足,他比较缺乏吸引人心的艺术,但他那精粹的学术水平与稳健的识见,曾使他成为那些悉心研究希腊历史者们的良友。著作的开篇包括,希腊世界的地理概述,它的早期种族情况,以及关于它的英雄时代文化的描写,等等。与相信荷马史诗中人物具有真实性的密特福不同,这位尼布尔的门生则仔细地对传说与历史加以区别。他的雅典黄金时代的概述部份,具有冷静、清晰与就事论事的特点,但缺少风格与应有的气氛。他从没有考察过希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愿望。马拉松战役的描写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伯里克利时代的艺术与文学所占的篇幅则嫌过少。叙拉古的斗争描写缺少了它应有的某种①悲剧情调;而亚尔西巴德也失掉了他的不少光辉。在提尔华尔眼光中,除了苏格拉底之外再无别的英雄。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战后雅典内部局势的一章乃是一篇四平八稳的总结。“他们浮薄、狂热并且常常是不公平,但他们同时也能慈悲为怀和对人怜悯。”腓力与狄摩西尼之间的斗争则描写得详尽而又公允。后者在他看来,是“善良而又伟大的”——比福西昂要伟大得多,因为福西昂虽然在个人方面具有高尚的品格,但却成了征服者的奴隶。而腓力虽然肆无忌惮而又好搞阴谋,但并非完全没有宽大胸襟。从来很少有历史家对于亚历山大的目的与事业采取过这样宽厚的看法。“他的雄心,在那些颇足以使之变为高贵与纯洁的次要目的中几乎已长成为一种为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的征服是大大有利于被征服者的。但是亚洲从他的功绩所感受到的赐福,在希腊却几乎不为人知。“在许多重大方面,它的状况已变得每况愈下。”书的结尾为大事述略,直至希腊由于科林斯的毁灭而变为罗马行省为止。提尔华尔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他博采众长,吸取了博赫奥弗里·穆勒、韦尔克尔、德罗伊曾、克累散与洛贝克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人都是在将古希腊的文明揭示给近代人方面著有成绩的。他的见解也与他的学力相称。豪吞爵士是一个交游很广的人,但当他被问起谁是他所熟识人中最杰出人才时,他竟毫不踌躇地回答说是“提尔华尔”。书的缺点是在消极方面而非在积极方面。剧中人物显得象影模糊,另外也给人以陈旧剧目的感觉。至于要使那种雅典民主起死回生,并把世人的①参阅他的《通讯》,1881年,和提尔华尔(J.C.Thiriwall),《康诺普·提尔华尔》,1963年。关于评传,参阅《爱丁堡评论》,1876年4月号(由普兰普脱所作)和克拉克,《在剑桥与别处的老朋友》,1900年。他在黎德的《豪吞勋爵传》,1890年,常被提及。关于德国对英国古典学者的影响,参阅杜克洪,《德意志历史主义在英国》,1950年。——原注①亚尔西巴德(公元前451—404年),雅典将军,以雄材博学见称于时。415年率舰远征西西里。在围攻叙拉古城之时,雅典政府命其回国受审,于是投奔斯巴达。——谭注\n注意力集注在它的辉煌成绩上面,这项工作就有待于一个才能更为出众的同代人了。①早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格罗特便已开始了希腊史的系统研究,1826年他在论述密特福的一篇文章里已经拿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在承认希腊民主政体中种种缺点的同时,他提出,我们必须对这些作出公正论断。“我们只须把它们和任何其它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踌躇地宣称它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它们为良好行政所提供的安全保证远远不够这一点,我们完全承认,但是寡头政治与君主政治则是对此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安全保证。”他对密特福的下述论点一一提出反驳,诸如:希腊的议会是反复无常的,民主政治是不够稳定的,富人的赋税过重等等,并严厉批评了他学术研究上的种种重大谬误。格罗特的结论是,“十分明显,一个历史家如果在转述具体史实上尚且如此脱离根据,那么他在任何一般性的论断方面便更加不会有多大信实可凭。如果希腊历史将来被人以认真信实的态度重写之后,我们敢于断言,这位作者的声誉必将一落千丈。”这个年轻银行家此时早已熟悉边沁与老穆勒,并被认为是那个为数不多然而颇有影响力量的哲学急进派中的一个很有前途的新兵。当1830年辉格党在长期失势后重掌政权的时候,他决定参加议会;并于1833至1841年间充①②任伦敦议员。他与洛巴克与摩尔兹威司一道,努力引导格雷与墨尔本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更前进几步。这是一桩既饶趣味又有价值的生活经验,不过他并无意于长此继续下去;因而到1841年辉格党失势时,他就又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年后,他甚至脱离了银行;从此专心致志干他的《希腊史》的编写,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46年,第十二卷于1856年。他的学问本有基础,又得益于“德国学术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帮助。”他事先精详地研究过其它文明的早期历史。他是一个修养有素的哲学大家,因而古希腊思辨哲学中的种种玄妙之处在他丝毫不是困难。另外他又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坚决信奉者,热烈地同情希腊各城邦为实现民主所作的努力。最后,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经验还有助于使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体会到希腊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所企图解决的种种问题的真实性。这部著作从探讨早期希腊的传说开始,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其在关于希腊传说与早期历史的一篇文章里已经作过说明。任何想使传说合理化的企图都不可能获得鉴别真伪的结果:它们不过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的幻想的创造物。这个态度支配了《希腊史》的开始两卷。“据我所知,再也没有比把这些模糊时代及其人物的一些所谓证据掂来掂去更加今人丧气和更无益处的了。如果读者责备我没有帮助他,如果他问我①参阅格罗特夫人《乔治·格罗特的个人生活》,1873年,和贝因的格罗脱《次要著作》(MinorWorks)导论,1873年。关于专家的评价参阅白尔曼《论古代与现代》,1895年;勒尔斯《通俗论文》,1875年;龚佩士《论文与回忆》,1905年;弗里曼《历史论文》,第二辑,1873年。——原注①格雷(Grey,CharlesEartof1764—1845年),辉格党改革家,1830—1834年任首相,在其任内通过了第一次议会改革法。——谭注②墨尔本,一译梅尔波恩(Melbourne,WilliamLamb1779—1848年),辉格党政治家,1834,1835—1841年两任首相。——谭注\n③为什么不揭开幕布展出图画,那么我将引用画家宙克息斯的话回答他说,幕布即是图画。”如果格罗特不是看到神话在显示人类的萌芽思想方面具有相当意义,他是不可能以那么多的篇幅来叙述传说的。随着科学的宇宙观的发展,许多神话逐渐被当作寓言看待。他对于古代传说与神话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并利用了最近德国的研究成果。书中关于史前期希腊的论述是以荷马诗篇的分析作为结束的。他在荷马撰著说与沃尔夫和拉赫曼的民谣说之间,采取了折衷说法,宣称《奥德赛》很有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另方面《伊利亚德》原系关于阿喀硫斯的纪事诗,后来其它次要情节也都连缀上去。这些诗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约有二百来年系靠人们的记忆流传下来直至庇士特拉图时代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式样。书中的“历史期希腊”(HistoricalGreece)部分,开篇时首先对地理情况作了扼要介绍。接着作者叙述了斯巴达的政体;不久又接触到了索伦,他已经是历史家们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了。行文到此,亦即到了希腊开始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的时候,作者通过对小亚细亚、腓尼基人、亚述人与埃及人各章的叙述,综观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在这样地描绘了一幅政治地图之后,他略述了地中海区希腊殖民地的建立。书的核心是以克来斯特尼的改革为开始的雅典民主政治。他宣称,改革运动在人民中间迅速兴起。“它的积极原因则是人民主权的这个伟大新观念,即是主权属于自由平等的公民全体的观念。这个观念产生了电流一般的迅速效果,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思想、情绪、动机与才干”。这种兴奋鼓舞的状态一直维持喀罗尼亚战役之前五十年左右,这时雅典人已降至其它希腊城邦的一般水平。“主要因为民主政治不大适合于大多近代读者的胃口,于是他们总习惯于从这种思想的最乏光采的表现方面去观察问题,正如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我们却须要,按伯里克利的讲法那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波斯战争表明,雅典人不仅能说而且能做。但他们对于胜利的将军则小心提防。格罗特很惋惜米太①雅第在马拉松战役后的失意,但却认为他的耻辱是咎由自取。反复无常②并非是雅典人的一般属性,他们对尼细阿与福西昂的态度便曾始终不渝。只要他们的首领忠心于雅典的时候,他们也是忠心于首领的。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宪法达到了它的异常完备的形式。克来特尼斯扫除了出身所造成的差别,并减少了以财产为基础的等差。至于其余法律上各种没有资格现在也已消失。雅典这时已由一个主权的会议来进行治理;这会议由全体公民所组成,并从中选出一切国家官吏。这个政府第一次以法律代替暴力,是世界上所曾出现过的最好政府。它的理想性质(即使不是它的真正实践,)曾在伯里克利的不朽演说中得到了光辉的表述。这是合乎理性的自由的黄金时代。“我们从这里所读到的这种宽厚容忍精神是目前各个国家中都见不到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伯里克利本人,而一旦他不在之后,衰落便立即呈现。“他的清③宙克息斯(Zeuxis约公元前464—393年)——希腊画家,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译者①米太雅第以在战争中未能占领派各斯岛受到惩罚不久病死。——谭注②尼细阿,雅典保守派领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力持和议。公元前421年主持与斯巴达签订了“尼细阿和约”。——谭注\n廉公正的政治品德、他的谨慎与坚定在整个希腊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在那里这些品质本来是难得的,而它们集于一身就更属罕见。”格罗特并非看不到雅典人的缺点。他非难了那些给他们的战争带来玷污的残暴行为;他谴责说他们在阿吉纽萨海战后处决一些将领是违法①行为,虽然他相信这些将领是有罪的。在称颂尼细阿的清廉时,他补充说,这种品质在希腊政治活动家中间是罕见的。他严厉指斥了西西里远征。但另方面,他却认为雅典人在不止一个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责备。他对贝壳流放制作了解释辩护,认为这是一种替代弹劾与死刑的温和办②法。他拥护克利温,反对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与修昔底德的恶意。关于诡③辩派与苏格拉底诸章可为书中最具创见的部分。正像“律法师”与“法④利赛人”那样,人们对诡辩派的印象是他们的反对者替他们而留下来的。“据我所知,历史上很少有人遭到这样苛刻的对待。他们横遭了他们这个恶名的惩罚。”他们的任务曾经是教导青年如何思维讲话与行动,训练他们如何执行公民的义务与责任。他们乃是道德家而非哲学家,他们属于一种行业而非属于一个教派。我们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证明他们产生了坏的影响,或者他们流行的时期就是一个道德衰败的时期。他痛斥那种认为雅典品质堕落的说法为纯属无稽之谈。“我认为,雅典人不论在政治上在道德上均已较过去大有进步,他们的民主政治在这件事上是颇著成效的。苏格拉底自己也是一个诡辩家或大众的教师;他与其余诡辩家的不同仅在于,他公开讲授,拒不收费与具有传道士般的热情。说他是一个好人不等于说他们便是坏人,或者说他的教诲便比他们的教诲更为有益。他的同时代人是不曾像我们那样地透过柏拉图雄辩滔滔的金色雾霭来看待他的宗教革新者无论在异教时代或基督教时代都从来不曾得到过仁厚对待的,只有雅典人才可能那么长时期地容忍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已经不复是这出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但希腊文①明之灯却依然如往日那样光辉灿烂。格罗特对伊巴密嫩达的景仰是说不尽的。他认为,这位著名的底庇斯人政治才干虽然逊于伯里克利,但军事才干则有过之;他是唯一堪与之比拟的重大人物。这位历史家对亚吉②③西劳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而他对于提摩利温——那个古代的华盛顿——的经历行事则不胜低徊留恋。雅典本身不乏高贵的公民,但他们却无力避免其自身的覆灭。她曾受到暴力征服一点决不应成为我们应当拜①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于阿吉纽萨群岛大败斯巴达舰队。战后有八名将军以不关怀遇难水兵之罪受审,六人被处决。——谭注②克利温,雅典民主派领袖,继伯里克利之后执政,主张对斯巴达作战,在安菲波利斯之役(公元前422年)中战死。——谭注③“律法师”(Scribes)——古代犹太神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保护旧礼教者。——译者④“法利赛人”(Pharisees)——古代犹太的一个宗派,以严格遵守法律与圣法生活为特征。——译者①伊巴密嫩达,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之一。公元前371年,以新的战术在留克特拉城附近大败斯巴达军,予伯罗奔尼撒同盟以重大的打击。——谭注②亚吉西劳,斯巴达国王,于公元前396年多次大败波斯军,但未能巩固其战果。——谭注③提摩利温,科林斯的执政者。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迦太基入侵西西里。提摩利温率军赴援,击退迦太基人并在该岛宣布民主宪法建立了温和的寡头政治,然后撤军。——谭注\n倒在其征服者面前的理由。他承认她的复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公元前360年时的雅典人似乎是已经衰老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平和安稳、安土重迁的文雅公民。”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福西昂的影响确实是一个致命伤。如果不是他,雅典完全足以挫败腓力,而不致使之变得那样强大无敌。格罗特虽惋惜福西昂的政策,却承认他的个人方面的巨大优点。但他在狄摩尼西身上则深激赏那种道德与智慧的结合。正如伯里克利体现了雅典全盛时代的精神代表,同样,狄摩尼西则是希腊世界衰落时期的主要光荣。希腊民主政治正是由于忽略了他的忠告,才使自己在喀罗尼亚的战场上遭到暴亡。格罗特对腓力的描写是具有敌意的,但在根本上却无不公道之处。腓力是一个良将,不过他也幸而没有遇到过能力卓越的希腊将领的对抗。他并非没有文化修养,但他缺少稳健节制,对于妇女保持着东方人的看法,并常因嗜酒而失了体统。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则远远比他恶劣得多。这个曾经受到特洛伊曾的歌颂与提尔华尔赞美的国君,在格罗特看来,正像在尼布尔的眼中那样,不过是个有些才具的野蛮人,他的能力只是在于破坏。他那不可控制的强烈冲动是从他野蛮的伊庇鲁斯族(Epirot)的母亲遗传来的。他把底比斯夷为平地的作法即使在那个残暴的时代也是一件没有先例的残暴行为。他对菲洛达斯与帕米尼奥的杀①②害显出了他的无情无义,而杀死克来图斯又表明了他的难驾驭的激情。战争与征伐不仅成了他生活中的正事,而且成了他的乐趣。他的侵袭亚洲正像阿提拉的进攻欧洲那样。在大流士死后,他也摆出了那套豪华的架子,一切采用了波斯王的习惯。“他不是要希腊化亚洲,而是要亚洲化马其顿与希腊。”他所建造的“城市”仅仅是设了防的前哨站,借以保持占领地的服从。在他一切的建设中,只有亚历山大城尚处繁荣状态。如果说希腊曾经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药地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发展、商业的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如果这个征服者寿命再长的话,他也许会要征服掉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包括罗马在内。但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干尽了坏事。“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用。”狄摩西尼因避免死于马其顿人手下而饮毒自尽。而亚加亚同盟——那个“从希腊自由的枯树上所发出的柔条”,从来没有达到枝繁叶茂的地步。在一切构成希腊伟大的事物中,唯有各种哲学派别算是幸存了下来。《希腊史》这部著作获得了异口同声的赞颂。他的老同学提尔华尔有一次曾说过,“格罗特正是一位编写希腊史的最好人选”。他在阅毕第一卷后写道,尽管他所设想的目标颇高,但它还是大大超过了他的这个标准。“它提供了一种真实保证,这是在这个题目上我们的或任何其它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的。它使我感到相当满意的是,他的见解除了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一般与我自己的见解没有多大分歧的。”在起首四卷出版后,提尔华尔承认他自己的成绩“差得很多”。“我已很①菲洛达斯系腓力手下的大将帕米尼奥之子。父子二人以涉及所谓阴谋案为亚历山大杀害。——谭注②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在一次宴会上将其密友,救命恩人克来图斯杀死。——谭注\n满足于我著作所获得的暂时性的成功与作用,并能为了一切最崇高的目的而毫不虚假地甘愿它被替代。”他们两人也能相互佩服,因为格罗特也曾宣称,如果提尔华尔的书能够早出几年,他很可能根本不去动笔了。格罗特的《希腊史》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它的笔调虽缺少色采与优美,但很少著作能够给人以这样一种坚实的思想力量。他表明,在希腊史经过密特福的介绍而渐为人知的时候,他已开始计划撰写这部著作,其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较公正的解释。在他看来,“希腊人乃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天性中潜伏的智力上点燃起火花的民族”。而他的著作正是一种对他们感激与景仰的热烈颂辞。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一个作家在使世人认识到希腊对政治家与公民的重要性方面,做过这样重大成绩。弗里曼也完全会作出这类说法,即阅读格罗特的著作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正当其他作家在宣扬这个哲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之母的时候,格罗特则遗憾地说,她在文学上的光荣未免掩盖了她在政治上的伟大。她的最高的成就,她对人类的最宝贵的贡献,乃是政治自由。以这种角度观之,希腊的历史,尤其是雅典的历史,开始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勒尔斯写道“他是第一个给了我们一幅希腊图景的政治家。”穆勒也宣称,几乎没有一个重要事实,在他重新对之检视之前,曾经为人们所透彻了解。①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讨,迈锡尼文明的出土,以及《政治学》的发现,已经推翻或部分改变了格罗特的许多结论,但是不管我们如何需要阅读别的著作,至少格罗特的部分著作总是必需读的。他的序言表明,他已察觉到了历史家所可能碰到的陷阱之一。“尽管整个希腊世界显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都不得不根据为数有限的文件来作论断,而这些文件却是太偏于雅典方面的了。”虽然抱着这种警惕,他的书还是关于雅典的太多而关于希腊的太少。由于这个缘故,希腊早期与后期的历史的叙述也都受到影响,而其中一些小的城邦并未得到应有的篇幅。他对僭主的仇恨,使他昧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僭主的统治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适应某种需要的结果。他也忽视了雅典城邦的若干缺①点。瑟曼写道,“格罗特驳斥了那些加在雅典民主身上的不少指责,缩小了其他指责的分量,解释了并删减了那些无可称颂的事情。但是,我们虽然乐于同意他关于雅典人所说的一切优点,这并不能使我们对于他们的民主所作的论断有所改变。甚至雅典人民也渐渐体会到它的种种不良后果”。不过他的偏见究属为害有限一类的。弗里曼宣称,“他的著作使人觉得他的道德品质甚至比他的智慧品质更可尊敬,因为他所提出一些事实往往恰好反驳了自己的结论。当我们阅读他的种种议论时,我们感到他的话不像一个法官的判词,而像一个律师的辩词,但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位律师来作辩护也自是一大佳事”。另一个明显的缺点则是他对经济影响的忽视。他没有看到在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所逐渐扩大了的鸿沟。由于他把自己的叙述在公元前4世纪时作结,这样便可免于对自己歌颂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考究,而这种结果当时已呈现得非常①《政治学》(Politicia)——亚理斯多德的名著;1890年在纸草文献背面发现,1891年出版英译本。《雅典政制》是此书的最重要部分。——译者①《格罗脱所述雅典宪法史》,博山奎的英译本,1878年。——原注\n明显。最后,麦考莱对于亚历山大的事业所形成的概念则是根本错误的。把他看作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人,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马其顿王朝与希腊血统原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其顿宫廷上渗透着希腊的影响,而亚历山大,这个亚理斯多德的门生,曾是一个希腊文学的热烈爱好者。希腊文明通过他的征伐而传至近代世界,其作用之大殊不下于通过罗马。梅里韦尔讽刺地指出说,格罗特恰恰是在他的故事开始有趣的时候,突然中断了他叙述。弗里曼也编写了①一部关于希腊联盟的历史,其书证明,希腊人的政治本能曾怎样适应了那个业已改变了的环境。Ⅱ英国关于罗马史的批判研究是从翻译尼布尔的著作开始的,他的享②名主要有赖于托玛斯·亚诺尔。没有一位英国学者曾以他那样大的愉快来欢迎尼布尔的修订本各卷;也没有人以更深厚的尊敬来看待这著作;她还亲去波恩访问了书的作者。他写道,“这是一部以非凡的天才与学识所著成的作品,对我来说可谓广扩视野,顿开茅塞”。他之所以计划要编写一部罗马史,并非因为他存心要和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赌赛,而是因为那部书在英国不易受人欢迎。尼布尔死后,他比以前更加积极于重述尼氏的某些结论和续成他的著作。亚诺尔的雄心便是模仿尼布尔的研究方法,“去亲自实践一下他的那个正确怀疑与正确相信的卓绝技艺”。他曾以适度的谦逊态度处理了他的工作。他写信给哈尔说,“至于说任何人可以作为尼布尔的一个适合的后继者,那是荒谬的;但我至少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即我对他的一切成就有着不可限量的崇敬,并愿试图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种种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亚诺尔的《罗马史》第一卷于1838年出版,内容包括罗马侵入高卢前的时期。其中的传说部分系用古语写成,以示其仅属稗史类型。在罗马国王的故事里,他只找到了很少材料属于历史事实。在他著作的这一部分里,文笔是亚①诺尔的但精神则是尼布尔的:甚至连后者对于歌谣的大胆假设也都被他接受了过来。第二卷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第三卷所述内容接近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末期,但于1841年书接近完成时,著者突然去世。亚诺尔的书的运气,正象他老师的书那样,仅以残编遗世。他的早逝注定使他这部史书的价值不超过尼布尔的改编: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他必将表明他有能力独立进行一番事业。他具体描绘一个国家的生活的能力远比他重新构制出一个早期文明的模糊轮廓更要适合的多。他的才力随着工作的前进而日益增长;因而他的第三卷便已优于第二卷,正如那第二卷曾优于第一卷那样。他的朋友哈尔在文章中说,他最杰出的才干便是他对地理的独特眼光,因此他在看到一幅地图时所感到的愉快正象一个绘图爱好者在看到一幅拉斐尔的作品时所感到的那样。由于这项才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兴趣,他遂能够解释汉尼拔的军①书名《希腊、意大利联盟政府史》(HistoryofFederalGovernmentinGreeceandItaly)1863年。——谭注②参阅史坦莱,《托玛斯·亚诺尔的传记与通讯》,1844年。——原注①参阅上文第二章。——译者\n事行动。他那出色的文体轻快、流利、而又富于色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类题材里找到了再适合不过的表现机会。但可惜的是这位描绘迦太基伟人形象的非凡妙手,竟尔天不假年,未能得以叙述革拉古弟兄的命运乃至罗马共和国末期一段历史,这实在是文学上的一大损失。他关于罗马史的一个早期草稿的后半部曾作为续编刊出,多少作为那未成诸卷的一种弥补。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表出了作者对凯撒的公平谴责。“就道德性质而言,通观全部历史也几乎找不出一幅更加畸形的图景。从来未曾见过任何人这样无缘无故地搞出这样大量的人间灾难。”他关于奥古斯都的描写也几乎是同样严峻的,因而这部著作构成了一篇对凯撒主义的激烈控诉。亚诺尔历史概念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乃是一个神定的过程,而人则是一个道德动物,他对自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他对那种认为支配私人关系的道德律不适用于统治者的行为的辩解,是嗤之以鼻的。在他看来,罪人的地位愈高,则他的罪过也就愈大。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辩护手段的理由。这一道德标准他在罗马史的各卷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后1841年当他以钦定讲座教授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授课的过程中则更加强调了它。在这些一度曾享盛名的演讲里,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位历史家而是一位神学家。历史那是通过完成上帝的使命,借以说明他的光荣。“我们已是生存在世界史的末季之世。我们即是世界的最末一批后备兵员——世界的命运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不能勇于承担,上帝的事业甚至有不能完成之虞。”尼布尔的时代统治了一个世代之久,而亚诺尔便是他的最后一名使徒。1855年,出版了康华尔·留伊①斯的一部著作,这书指斥了尼布尔的推测方法,也否定了他关于早期罗马史的重新阐释。留伊斯的怀疑主义不免有些超过限度,但他倒底也揭露了尼布尔基础的不坚实性。几年之后,尼布尔的时代遂告一终结,而被蒙森取而代之。当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在尼布尔与亚诺尔的著作中被认真研究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探讨则迟至这个世纪的中叶之前几乎完全受到忽略。1840①年梅里韦尔为“实用知识传播协会”撰写了一本关于帝国的篇幅不大的书,但该学会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前已经瓦解。1845年他对这座“永恒之城”的访问增加了他的兴趣,因而1850年时他的《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史》开始出版。书的序言特别提到,“在我们近代著作里,特别缺少关于罗马史上最有兴味的一段时期的任何完整的叙述”。他补充说,他之所以编写这书,主要因为亚诺尔未编写过。虽然他自称是亚诺尔的“崇拜者与朋友”,但他的政治立场则是与亚诺尔根本不同。开首两卷从第一次三头政治叙起至凯撒之死为止,凯撒的事业被视作以后四个世纪历史的前奏。“这个帝国政治的继承人沿袭共和国这位最贤明政治家所规划的路线而发展至伟大而稳定的局面。”他在书的后一版序言里曾写道,他原应该从革拉古兄弟叙起。“这会表明,罗马社会有在君主制基础上完全重建的必要。罗马寡头政治确为文明世界所曾经历过的最糜费不赀的虐政。只是为了使百余户家族得以肆无忌惮地互相攻击,互相残杀,便让大多数人呻吟于愁苦与屈辱之中。寡头政治必须消灭,而破坏它的①书名《早期罗马史之可靠性的探讨》(InquiryintotheCredibilityoftheEarlyRomanHistory)。——谭注①参阅《自传与通讯》,1898年。——原注\n正是他们本族的恩人。”梅里韦尔是强权政府的崇拜者;当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发动政变时,他曾指出,他也会采取同样作法。他承认凯撒私人生活是腐化的,但他的公共事务上则是做了有益的工作。书的下两卷专写奥古斯都这个“天才”。他不认为早期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坏皇帝是确实有的,但大体上他们还是受着元老院的约束,而他们的联合统治曾给罗马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幸福。“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个政府在①恪守法律这件事上,比得上奥古斯都至珀蒂纳克斯时期的帝国政府。”②不过他虽然对于那些罗马皇帝并不过苛要求,他却并没有想要为提庇留加以粉饰,或把罗马社会加以理想化。他承认罗马存在着一个日趋专制的发展倾向,不过他提出罗马人对此倒也容易忍受,理由是他们自己便也是专制者。在朱里亚王朝倾覆以后,叙述渐趋草略。全书终止于马卡③斯·奥理略,一方面为了避免与吉本出现争赛,另方面也是因为罗马帝政的立宪时期至此已告结束。梅里韦尔的著作是在一个没有其竞争者的时期中写成的。它的学术性是很强的,叙述也清楚而有力。他是一个坚决而热情的帝国拥护者。④⑤他揭露了塔西陀、斯韦托尼和狄翁,书中缺乏公允的地方,并向读者⑥提出:他们也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很久才动笔的。他把克劳第从冤枉的⑦轻蔑中挽救了出来,并认为吉本所给予安托尼朝的崇敬实则应当归于法⑧①雷维朝时期。另外,杜密善本人在开始统治时期曾是一个改革家。如果说亚诺尔常以过高的标准来论断统治者,那么梅里韦尔对人类本性的要求则不免过低。他对于帝国外表的煊赫功绩印象过佳,以致他对其内部的腐朽糜烂注意不足。他把凯撒与奥古斯都说成仿佛是人民党派的首领;而殊不知他们不过是在腐败的寡头政治的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统治,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波拿巴家族之类所建立的那种假民主的专制政权。这部著作之失掉权威,并非因为它被后来同一题材的著作所取代,而是因为它根据单纯局限于文献方面资料。就在他编书的时候,蒙森及其门生们已在他们的《拉丁碑铭集》(‘CorpusInscriptionumLatinarum’)里打下了关于帝国的更深一层的知识基础。①珀蒂纳克斯(Pertinax,PubliusHelvius)公元193年为元老院所立,同年被军团暗杀。——谭注②提庇留皇帝,公元14—34年在位期间帝国发生过两次军团大暴动及意大利奴隶起义,旧贵族所代表的共和派残余势力也图谋推翻现政权。为维护君权,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派遣耳目,刺探情报,严刑峻法,锄除异己。——谭注③马卡斯·奥理略,公元161—180年在位。——谭注④斯韦托尼(公元75—160年),罗马帝政时期的大史学家,有《罗马十二帝本纪》流传至今。——谭注⑤狄翁(Dion,Cassius约155—240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历史家,著有《罗马史》80卷,记建城至公元229年之事,今存十九卷。——谭注⑥克劳第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时期进一步巩固君权,完善官僚政治,扩大帝国版图。——谭注⑦安托尼朝,自公元138年安托尼·庇护即位至193年孔茂德之死,凡四帝五十五年。——谭注⑧法雷维朝时期为公元69至96年,凡三帝,27年。——谭注①杜密善,法雷维朝末帝,公元81—96年在位。——谭注\n第十六章卡莱尔与弗劳德Ⅰ在整个19世纪前半个世纪中,英国作家中除麦考莱外,再没人象卡①莱尔那样给过历史研究以重大的推动。那位英格兰辉格党人曾利用历史来辩解他的政治信仰,而这位苏格兰喀尔文教徒则利用它来说明他的道德教诲。他早年悉心于德国文学的研究,直到中年初期,才开始了范围更加广阔的活动。他的论文《论历史》出版于1830年,代表了他的初期思想。他宣称历史乃是无数传记的精英,强调了卑贱者在创造文明上所②作出的贡献。“在那赢得坎尼与特拉息米战役的人与那第一个为自己铸成一把铁铲的无名穷人之间,究竟谁对人类的恩惠更大呢?所有战役与战争骚动,不过象旅馆的喧嚣那样,转瞬即逝。法律与政治宪法本身,并非我们的生命,而不过是暂供我们栖宿的屋舍而已。甚至只有过是屋舍内的光秃墙壁而已;而屋内的一切主要家俱却件件是一批久被遗忘了的艺师工匠的成绩;他们自一开始起就共同教导着我们如何思维如何行事。”新的更高尚的事物正开始期待于这位历史家。“自古以来,经常有人指出,史家每每过于偏爱论述元老院、战场,甚至国王厅室而忘记了远离这些场所之外的思想与行动的滚滚洪流正在滔滔奔腾不止,就在那成百成千个流域里面一个蓬蓬勃勃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盛衰荣枯,与某次战役的胜负全然无干。”这个时期,他日记中对司各脱《历史》的批评意见,也表露过同类主张。“奇怪的是,一个人记录了一个淫荡少妇与乖戾蠢才私奔被炸的故事,竟自以为他便是在编写民族历史。”两年以后,在一篇题为《传记》的论文里,曾这样地提出问题即,历史的全部目的是否即在传记;并在带有见解的第二篇文章《再论历史》中,更加强调了历史的道德价值。“历史不仅是最切要的学问;它简直是唯一的学问,其它一切尽在其内。它是真正的纪事史诗,是普遍的神圣经典。”但在卡莱尔真正写起历史时,历史却成了伟人的传记而并非芸芸众生与无名氏们的记录;他中年与晚年时期潜心写成种种的论著,恰恰是他在1830年时要别人提防的那种东西。①待到卡莱尔提出他的《补衣裁缝》的论点时,他业已与18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潮很少联系,但他的兴趣所在却始终是朝向那时代。他关于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论著代表了他对这些“哲学家”/PGN0525.TXT/PGN>的①弗劳德的四卷集传记、阿勒克·威尔逊(DavidAlecWilson)的六卷集传记,卡莱尔的《回忆录》与通讯以及卡菜尔夫人的《通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迦涅特(1887年)与尼科尔(1892年)还编写了他的略传。最好的评传为:摩莱,《杂文》,卷Ⅰ;昆威,《卡莱尔》,1881年;马松,《卡莱尔》,1885年;李思廉·斯提芬,《图书馆内札记》,卷Ⅲ。罗伯特森(J.M.Robertson)的《近代人文主义者》中一篇有关文章,1895年,也是一篇有力的论战文字。——原注②特拉息米战役,公元前217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于意大利北部之特拉息米湖。——谭注①《补衣裁缝》(SartorResartus)——此书以谈论服装为题泛论宇宙和社会,暗示虚浮的风俗与习惯,官场仪节无异于陈旧的服装,不仅掩盖了社会的本来面目而且窒息了社会有机体的呼吸,发表于1833—1834年的《弗拉散杂志》(FrasersMagazi-ne)。——译者\n①②评价;他关于卡略斯特洛与“钻石项鍊”的论文阐明了旧制度的黑暗角落,而他关于米拉波的描写则跨进了新时代的门限。这一批出色的论文,是他对历史的初步贡献,也是他日后杰作的前导部分。1837年他的③《法国革命史》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全国声誉;这是19世纪上半期英文历史著作中(麦考莱《史论》除外),至今还为人广泛阅读的一部书。它的优点是独特的。首先,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一个读惯了哈兰的冗长论文、爱里逊的夸大笔调与麦考莱铿锵有力的文章的世代里,一部洋溢着热情与诗味的著作的问世实在是一件启人心智的事。通过一种高度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量,他竟使读者对他书中景象的感受和他本人④同样真实。他说过,“这事在我头脑中已经一清二楚,我也不想对它再多作什么调查研究,现在主要的是如何把我所了解的种种以大量的各种彩色绘饰出来,这样远远望去,简直如声势煊赫的巨焰烈火一般。”这书是英国历史著作中最带史诗性的一篇纪事。它在作者的心目中决不仅仅是一部事件实录,此书体现了他最深刻的道德与宗教信念。读者所听的乃是一位先知召唤罪人进行忏悔的激越呼号。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曾对他的妻子说过,“我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有多大价值,也不知道世人如何对待它;但是像这样从一个活人心底直接涌现出来的火热作品,百余年来,实为仅见。”他写给约翰·斯脱林的信中说这是一部粗犷强悍的书。“这是一部从我灵魂深处倾泻出来的书,它产生于黑暗、疾风与痛楚。”读者对他的一些伟大场景的描写将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袭击巴斯底狱,向凡尔赛进军,联盟节庆典,向瓦伦逃亡,法王的审讯与处死,吉伦特派与丹敦,夏洛特·科代的短暂一生的悲剧,罗伯斯庇尔的倾覆——这些景象都是我们毕生难忘的。在描写恐怖与希望、炽烈热情与兽性狂暴等气氛的渲染力量方面,米什莱而外,再没有任何作家比得上卡莱尔。他对于书中主要人物品格的洞察力,也是同样惊人的。洛威尔曾说,许多历史家所描绘的形象不过像塞满着砻糠的布娃娃,但卡莱尔的人物则异常真实,用针来刺要流血的。虽然他象当时的其它历史家一样,对吉伦特派颇有误解,但他笔下的法王与王后,米拉波与拉斐特,以至丹敦、罗伯斯庇尔、马拉的形象,却不需要修改。“材料虽①欠充分,但态度异常公正”——这是屈维廉博士对该书的评语。那时,卡莱尔还没有尊崇那种有损于他后期著作的英雄崇拜主义。他既不同情于旧秩序也不同情于新秩序;他往往站在党争的呐喊之外来注视人类灵魂中的剧烈斗争。卡莱尔为英语世界阐明了法国革命,他绘出了一幅迄今仍不褪色的鲜艳图景;但这书也有它的严重缺点,其中一些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些则由其他的洞察力不够,他关于这时期的知识太有限了。他放弃①卡略斯特洛(Cagliostro,1743—1795年)——意大利眼科医生与骗子手。——译者②”钻石项鍊”(TheDiamondNecklace),指法国史上牵涉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的钻石项鍊事件(1783—1785年)。——译者③参阅夫勒契与洛兹版本,附导论与注释,1902年。见阿尔杰的卡莱尔的错误附录一文,见《巴黎,1789—1794年》,1902年。——原注④指法国革命。——译者①《历史上的偏见》,见《自传与其他论文》,第74页。——原注\n了对克罗克所收藏的大量书册的探索,原因是他不能在书架上自由查阅。关于档案的研究也未开始,而他从未曾想到过该这么做。他的主要资料不外:《箴言报》、布舍与鲁的《议会史》、拉克勒德尔与梯也尔的记载以及几本回忆录。书籍所由建立的根基如此单薄,大量错误的潜入也就毫不足奇了。在一篇关于《革命史》的论文里,他曾尖锐地攻击过梯也尔缺少正确性,但他自己的正确性也不无可以指责之处。他竟把下面这类传说,信以为真,例如索布勒叶尔女士饮过一杯血(1800年后①②③的传说),“复仇号”的沉没(巴勒尔的虚构),卡佐特的预言(实④系事后所编)以及吉伦特派的最后晚餐(诺第安的捏造)。再如巴巴鲁⑤(不是布佐)倒成了罗兰夫人精神上的情人。但是他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向瓦伦逃亡的那一节。由于他把一百五十英里的距离搞成了六十五英里,同时使逃亡者所乘坐的车又大又笨,一件精心预谋的冒险简直成了一桩注定要失败的儿戏。其次,他的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画册。导论诸章对于此后即将发生的种种灾难既根本无意于说明,而全⑥书以1795年葡萄弹的爆炸事件作结,也收得过于突然。法国与欧洲的关系没有重视,而地方情况则全被遗忘。一些无足轻重的情况,如南锡①兵变,叙述得极详细,但是宪法与经济上的重大问题却反被略去。他在终卷之前早已厌倦,所以靠近结尾部分便写得比较草率。读者往往弄不清这场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并也不了解一个阶段怎么过渡到另一阶段。抬高戏剧性成了降低历史性。第三个缺点则更带基本性质。卡莱尔对他所叙述的事件的性质,并不能正确理解。他把这整个民族写成由于痛苦与压迫而走向疯狂,而且从一开始起便认为这场巨变必不可免。因此,他把这个革命看成是纯属破坏性的,是“对恶魔及其所作所为的一次卓越反抗”,是将古老法国的腐朽封建制度付之一炬的熊熊烈焰。他对弗劳德说过,“如其不是借助于法国大革命,我将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这个误解还不单因为他把法国革命从18世纪欧洲各种运动割裂开来。正如他的朋友玛②志尼在一篇深刻的书评中所指出,他缺乏人群的概念。“他看不到一个民族里面的任何集体生活或集体目标。他所看到的只是个别人物。所以①索布勒叶尔,革命前为残废军人宫总管。1792年8月被捕。据说其女为挽救父亲,声称:他们不但不是贵族而且仇恨贵族,并饮了一杯贵族的血水以表明态度。——谭注②卡莱尔书记述了“复仇号”在1794年6月1日海战中被击沉,船员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英勇赴死的情节。——谭注③卡佐特,侯爵。1792年8月被捕,其女陪同入狱,不肯离去,感动了看守,暂获释。十天后,法庭判以谋反罪处死。——谭注④1793年10月30日夜,在狱中的吉伦特派首领二十二人得知已被判决后,有一人自杀,一人服毒,余众歌唱叫嚣,通宵达旦。——谭注⑤巴巴鲁,大革命初期为马赛区议员;布佐,山岳党,国民公会议员。罗兰夫人,是吉伦特党核心人物罗兰(曾任议员、内政部长等职)之妻,1793年11月被处决。——谭注⑥1795年4月1日(萌芽月十二日),巴黎市民走上街头,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遭到政府军的开枪镇压。——谭注①1790年8月,驻南锡的瑞士卫队及法军二团叛乱,同年为布依耶侯爵平定。——谭注②《约瑟夫·玛志尼的生活著作》,卷Ⅳ,第110—144页,1891年。——原注\n在他看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因果联系。”法国革命乃是19世纪的直接根源,在它的恐怖的背后还滋育着一种更加宽广的生活种子,它作出过带有永久性的建设性的工作,它汲取过旧制度里面的不少观念与倾向——这一切他都是不理解的。卡莱尔要我们观看的是“神③的曚光”而米什莱欢呼的则是民主分娩阵痛。没有人能够理解法国大革命,直到他认识了它的双重性质。卡莱尔是最伟大的演出家,但也是最渺小的解说人。他称自己的著作是“几个世纪以来一部最狂暴的书,一部狂人所写的书”。人们对这书的态度可说是毁誉不一。华兹华斯扬言苏格兰人是写不了英文的。哈兰声称,此书的文体令人生厌,使他不能卒读。普雷斯科特写道,整个这部书,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十足可鄙的;他这样极力去渲染那自然已经过事渲染过的东西,实在是很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书赞颂之声却更响。穆勒誉之为那种自成规律的天才作品之一;金斯利称之为近代独一无二的纪事史诗。不少完全不是一派的批评家们,如杰弗雷与阿诺德、斯特林与萨克雷等人也都一律承认书中的天才。骚塞曾把这书读过六次。作为一部散文的纪事史诗,它的地位是无可攻击的,但它的权威性却早已失掉。在“法国大革命”一时在社会上还不够出名的期间,他的友人马铁努等人曾帮助卡莱尔举行公开演讲,以增加他的收入。卡莱尔作过四个专题演讲,其中最后一讲,也是最好的一讲即《英雄与英雄崇拜》获得了出版机会。他关于穆罕默德、但丁、莎士比亚、路德、克伦威尔与诺①克斯的人物研究,激起了听众很大热情。每篇演讲都是一场布道。他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在我听众中间,从主教到各种各类的人们都有。②我老实告诉他们,这个可怜的阿拉伯人身上也自有他的种种优点,大大值得他们学习;或许他们比他还更好自作聪明。”他已经习惯于对一般常人的德才加以轻视了。弗劳德也证明这点说,“世上的芸芸众生在他看来尽是一批可怜虫,感情上可怜,智慧上也可怜”。正像加尔文派神学家们那样,他认为优秀者人数很少。一旦离去了牧羊狗,羊群就要走入迷途。这时他所尊崇的已不复是民族的无名恩人,而是那种能够推翻社会制度,为后人开辟道路的能力非凡的英雄人物。英雄的创业行事要按照事实,而承认这种永恒真实便是敬奉上帝。正义的事业必然获胜——从这个论点出发,势必要得出获胜利的事业亦必是正义的事业的结论。康威曾为他求情说,卡莱尔所崇拜的并非武力而是功业,亦即是拨乱反正。这话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对为达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如何却是太不关心了。他1832年时把自己宣称为“一个急进分子与一个绝对主义者”,但这个绝对主义者却很快吞噬了这个急进分子。出现在《英雄》一书中的未成熟价值学说,不仅影响了而且也损害了他不少后期著作。③“神的曚光”(theduskofthegods)意即世界的最后毁灭。据北欧神话,洛基(Loki)是不断制造纠纷与祸害之,最后他被十条铁链系于岩石上面;据说,他将继续被系着,直到神的曚光出现时止,那时,他将挣断他的铁链,天空将消逝不见,地面也将被海水淹没。——译者①诺克斯(Knox,John1505?—1572年)苏格兰新教教士,卡尔文派宗教改革家,与玛丽·斯图亚特的宗教迫害作过坚决的斗争。——谭注②指穆罕默德。——译者\n①在《过去与现在》里,领导权的概念在住持参孙身上带着它很动人的外②表,但在关于巴拉圭独裁者法兰西亚博士的论文里,这个概念却显露出了它最可憎的面目。所谓“诚实”的人,便是对横在他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坚决铲除,毫不留情的人。卡莱尔对独裁一事,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究竟效验如何,从来也没想到过应当调查调查。尼采的这位先驱者忘记了穆勒的一句言论所包含的至理名言:老师如果代替学生做了一切功课,学生便永远也没进步。在《英雄》里,克伦威尔被描写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人”。当1822年卡莱尔阅读克拉伦敦的著作时,他已计划研究英国内战,并写了一批人物札记,这些作品曾在他死后出版。《法国革命》出版后,他再度拾起了清教时代的研究。他对那必须跋涉的“无边无岸的污水湖沼”满腹抱怨。1840年他在日记簿中写道,“我已看出,关于那个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混乱时期——那块葬满死狗的墓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好编写的。可是我对自己说,一个伟大人物确曾埋葬在这块荒芜的瓦砾堆之下。”他同亚诺尔博士一起参观过纳斯卑战场,并亲临过当年曾经发布过历史性命令:“抛弃你的无聊事,出来吧,先生”的伊利大教堂。最①后他决定范围不超过收集克伦威尔的通讯与演说,这样范围小了,计划也就迅速实现。的确护国主义从来未曾有过一个知心朋友。对于王党,他是一个嗜血的人;对于共和派,他是一个背教者;对于休谟一类怀疑派,他则是一个“狂热者”。麦考莱崇拜他,但却不了解他。卡莱尔有志为他作品中的主角的性格与政策作点剖白。关于前一点,他的成功是无可争论的。克伦威尔在大约两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全部曲解与诽谤至此在卡莱尔的手下得到了洗刷,允许了他为他自己申辩作证。詹姆士·摩兹雷与邱契曾宣称他们完全未能信服;但他们在这点②上则几乎是孤立的。福斯脱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了改变,而现在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再也不会相信护国主曾是什么伪君子或狂热者了。这位历史家一生中最可骄傲的成绩便是给英国的一大伟人恢复了名誉。但另一方面,他关于克伦威尔政策的解释,则说服力不大。他首先认识到宗教因素在这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但他却未能对那个在政治上要求自治的力量进行正确衡量。由于他本人对代议制度便毫不重视,他对这种制度何以会成为热烈追求的对象一点也就始终未能理解。这样,他不去追溯克伦威尔在种种局势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变化,而把他自己的专制信仰归到克伦威尔头上。后来的《克拉克文件》表明,这个超人之走向最高权力绝非出于自愿,他曾怎样诚恳地企图与议会合作;他怎样深①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1843年)一书中,描绘了12世纪英国一修道院在住持参孙管理下安定繁荣的生活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社会的混乱劳动者的贫困进行对照,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自己的历史与道德观点。——谭注②法兰西亚(1756—1840年),神学家、律师,曾领导巴拉圭独立运动。1814年起建立独裁政权。对外锁国,对内致力于破除宗教迷信,扶植农业和教育。——谭注①参阅斐司(Firth)为洛马斯版本(Lomasedition)所作的导论,1904年。威尔勃·阿波特的巨型版包括有新资料,出版于1937—194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共四卷。——原注②参阅摩兹雷(J.B.Mozley)《论文》,卷Ⅰ,1878年;和丘契,《偶谈》(Church,OccasionalPapers),卷Ⅰ,1897年。——原注\n信不疑慈善的专制政体的脆弱性。卡莱尔从来未曾认识到,以刀剑维持的政府,即使是好政府,也是不如没有的。他认为时代已失去了它的常态,遂有英雄出而匡正。他肆意讥笑拉德罗与凡纳,正象蒙森肆意讥笑西塞罗与庞培那样。他认为: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人民议会没有统治的能力。实际上,这只说明了个人政府在近代英国已不可能存在。在编辑的技术性工作方面,卡莱尔是完全不胜任的。他把《乡绅文件》——这本是他的书出版后作为恶作剧而伪造的一部文件——信以为真,并不去查究其根据,也未曾看出这里面充满着多少现代词语。他很少费力去寻找最好版本,往往任意篡改原文,并把一些演说词的用语弄得太近代化了。这作法对于一位专业学者的声誉是会很不利的,但卡莱尔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使他主角生动活跃起来,至于技术问题则很少注意。如果按照格林的恭维说法,这部著作显示了古董专家的渊博与诗人的才华等特征,那么它同样也露出了剧场中人的全般表演本领。谁也不能否认,他帮助了读者去想见他所描写的那个人物,并且也不时地使一些隐晦不明的段落变得具有意义。尽管批评家们把它骂得体无完肤,这①部克伦威尔大著仍不失为一部神奇之作。其中丹巴之役与这位英雄之死等段落都是文学上的杰作。《通讯与演说》也不愧为一部经典作品,罕有其匹,堪称两个同属伟大甚至并非完全不同的人物的一座合碑。长期沉浸于克伦威尔研究的结果加强了卡莱尔的一个信念即,实际行动家是构成历史的骨干。他对英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暗淡。他同时代人所宣称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是退步。他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科学。“改革法”乃是一个失败。议会正是国家的弱点,而不是它的长处,是工作的障碍而非它的工具。随着他对议会政府的信仰的日益减退,对仁慈专政者的崇拜也逐渐抬头。《论近世》一书的作者对于过去的18世纪往往不胜其怀念之情,因为那个世纪虽说是一个宗教的怀疑时代,却不失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统治的时代。1852年他曾参观了腓特烈大王的战场,这事标志着他最后的也是最可惊的历史工作的正式开始。在②他《英雄》的演讲里,老佛里慈尚未曾出场;而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他曾指出,“我对于他从来未曾看得过重”。但是他却宣称大王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君王。如果说大王缺少参孙修道院院长或克伦威尔式的信仰,他至少信任事实和接受工作的福音。如果说他欺骗过别人,他却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①当卡莱尔的巨著问世的时候,腓特烈的事迹在英国还属比较陌生:麦考莱的第二篇论文对他来说非但不是帮助,反而成了障碍。另外他也未曾从他的德国先行者们那里获得多大帮助,这些人,他曾粗暴地斥之②为“愚昧糊涂的蠢物”。普罗伊斯曾收集过关于大王的大量资料,兰克①1650年6月,查理二世在苏格兰登陆,同年9月3日克伦威尔大败勒士利统帅的苏格兰军于丹巴。——谭注②老佛里慈(OldFritz)为对普王腓特烈大王晚年的昵称。——译者①指《腓特烈二世传》,1858—1865年出版。——译者②关于早期作传者,参阅辛策,《历史与政治论文》(Hintze,Historischeu.PoliticheAufs■tze),卷Ⅱ。至于德人的权威作品,参阅克劳斯克(Krauske)的《麦考莱与卡莱尔》,《历史杂志》,卷CⅡ。——原注\n也曾简述过他的政策与行政;但却从没有人重新构制过他的人格。而这个正是卡莱尔给他自己规定的工作。关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全部描写,也许恰是他全书中最成功部分。这位仰尊上帝、俯事庶民宵旰辛勤的缄③默行动家,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史家。吸烟议会上的种种喧闹的取乐,对于这个卑夷宫廷虚矫的历史家非但不觉厌恶反而成了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年轻的腓特烈似不如他那粗鲁的父亲更合他心意。卡莱尔对于作诗吹笛等事的兴趣并不比威廉更大,但是当这位主人公以一个实行家的面貌出现时,他则开始对他敬意有加。他对于普鲁士索求西利西亚的理由之正确与否虽然兴趣不大,但他对这个决定的果敢与行动的疾迅却赞不绝口。他在《克伦威尔》里已充分显出他作为一位军事历史家的本领。1858年时他的再次访德,更把那里战场上的每一细节深深铭刻在他的顽强的记忆之中;他对这些战役记叙得如此精详准确,简直成了德国军官们的教科书,直到普鲁士总参谋部编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为止。但另方面,对于介于两次大冲突中间之十年改革与复兴这一段成效卓著的整个①时期,他所提供的却不过是简略纲要。1763年当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烈的统治仅仅不过一半时期,以后的二十三年期间他仅用了半卷书的篇幅便草草叙过,而且主要限于叙述他的外交政策。至于在财政改革、土地资源的开发、新工业的计划以及法律的合理化等方面所作的不绝努力,卡莱尔很少谈到,甚至略而不提。曾经帮他编写这部著作的助手亨②利.拉金曾说:卡莱尔原拟编写一部关于腓特烈重建其王国的相当完备的著作,因为他认为这是腓特烈事业中最关重要而又最富教育意义的教训;但这书的篇幅已超出他所预计的范围,另外他已经筋疲力竭了。再有,他认为,生动的图景是不可能根据官方报告与统计数字而构制出来的。《腓特烈》一书对知识的增添不多,但其间却不乏绚丽的段落,曾被比之为历史著作中的最称规模巨大而又花样繁多的展览箱。卡莱尔夫人是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但她也说这是她丈夫的最好著作。它无论在布局、幽默和刻划人物方面都显示了一种迄未减退的气势。爱默生也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警辟之作。书中关于伏尔泰在波茨坦的种种妙语逸事的记载最是他的精采段落,而他关于欧洲统治者们的描写也都属于他的最佳文笔。书出之后,不胫而走,甚至超过《法国革命》或《克伦威尔》并被立即译成为德文。当他开始他的著作时,很少人曾梦想到德意志未①来的戏剧式的变化;当他结束它时,俾士麦的铁鎚已经第一次敲下了。一个新兴强国的惊人的崛起,激起了人们对于造成普鲁士之伟大的创造者的兴趣;卡莱尔作为一位历史家与作为1870年德意志立场的拥护者的双重功绩使他荣获了连腓特烈自己也垂涎不置的“功绩勋章”(Order“PourleMérite”),但是这部书对于读者是太长了,正如对书的作者③吸烟议会(TobaccoParliament)——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朋友集团之绰号。他们和他常在晚间集合,一边吸烟,一边讨论国事。——译者①指自1745年第二次西利西亚战争结束到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之间的十年。——谭注②《卡莱尔》,1886年。——原注①此书最后一卷(第六卷)于1865年出版,前一年2月普鲁士对丹麦开战,次年6月,普奥战争爆发。——谭注\n太长那样。书的主角似乎远没有他所想像的那般气概非凡。他在写给凡哈根的信中说,他在这书里只能找到辛苦与悲哀,并说,“我与你们的腓特烈鬼知道有半点相干?”但事实上,老佛里慈在某些方面却是一位②比他所想像的更加伟大的君王,因而科塞的杰作反而留下了某种为这位英雄崇拜专家所未能表达出的印象。卡莱尔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不愧为最伟大的英国历史肖像画作者。迦③凡·达菲讲过,卡莱尔的习惯是把他所要进行描绘的人物的图像一张一张挂在帷幕之上。这位“圣人”讲道,这能使人物的形象经常呈现眼前;我们必须在心中先对一个人物有了清楚印象,才有可能使读者也能看清他。但是作家虽能以无比清晰的目光详察个别人物,却竟闭眼不见群众的根本存在。他晚年时甚至对贫苦无知的人们流露出某种迹近轻蔑的言④论。他的《射击尼亚加拉》相当粗暴地表达了他对1867年时工人阶级⑤的看法。他曾颇带几分正经地对武尔兹力说过,他真希望他能把议会的大门锁闭,把议员们都赶出去。在美国解放黑奴的问题上,他站到了南方一边,并和州长爱尔一起反对西印度黑人。他的全部哲学便是:普通凡人只能交由他们的主子去管教惩治。当一般英人已经变得更加乐观和民主的时候,他却变得更加反动和消沉了。Ⅱ①卡莱尔的主要门生与作者弗劳德是按他老师的精神来研究历史的;在他完成的著作里辉煌的优点与刺目的缺点不可分地糅杂在了一起。一位曾把弗劳德称之为民族历史家的著名比利时批评家指出过,他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无人知道,他的书也没有一本被翻译过。“他是十足②英国式的,充满着激情、狂热与排外主义。”他的研究是在牛津运动的赞助之下开始的。当纽曼着手编写圣徒传记丛书的时候,曾拉过赫勒③尔·弗劳德的幼弟作自己的助手,并对他发过如下的进军令:“证据不足时,则应以说理代之;而当证据有力时则易于取信”。弗劳德的选题④是关于艾尔弗雷德的一个同时代人圣尼奥特,并曾以下述话语作结:“这便是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不止一切”。他在圣徒传记这个朦胧领域的跋涉终于使他成了几分怀疑主义者,因而1845年他虽然②德国史学家R.科塞写的《腓特烈大王传》(共二卷,1893—1903年)是一部名著。——谭注③《与卡莱尔谈话》,(ConversationwithCarlyle),1892年。——原注④尼亚加拉(Niagara)美国大瀑布名,书名意味着危险。——译者⑤指对1867年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扩大选举权斗争的看法。——谭注①参阅赫伯特·保罗的精采著作:《弗考德传》,1905年;萨罗利亚,《论文,第一集》,1905年;斯基尔顿的《瑟力的席间闲谈》。腓特烈·哈里逊《坦尼森、拉斯金、穆勒等》,1899年;阿尔杰农·塞西尔《六个牛津思想家》,1909年。——原注②牛津运动是英国国教内部反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倾向的运动,因其在1833—1841年间发端于牛津大学,故名。——谭注③赫勒尔·弗劳德(HurrellFroude,1803—1836年),“牛津运动”的首领之一。赫勒尔是史学家安托尼·弗劳德(JamesAntonyFroude1818—1894年)的长兄。——译者④圣尼奥特(?—877年),相传曾为国王亚勒弗烈德的顾问,后隐居虔修,徒众甚多。——谭注\n被授圣职,他的信仰却逐渐动摇。1849年他所著《信仰的天罚》一书的公开焚毁,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研究员职位受到撤消后,他离开牛津去了伦敦。正是在这个倒运时刻,他遇到了卡莱尔;这使他转入了一个新的信仰。他的史学与文学论文使他迅速成名,而他关于伊丽莎①白时代海员的一篇文章鼓舞了《向西去啊?》的精神。凡是亲身经历过牛津运动的人不可能不联想到宗教改革。在纽曼的所有门生中,以异常强烈的轻蔑口吻来谈论宗教改革者的,再无过于赫勒尔·弗劳德其人,但是当他的幼弟开始亲自研究16世纪时,他吃惊地察觉到原来亨利八世当年在世时曾经深得民心。当他准备编写一部关于英国反对罗马的斗争详史的计划在他心中初步定型时,他获得了卡莱尔的热情鼓励;后者不久之前在一本《论近世》的小册子里已严谴过耶稣会徒,并把罗马教会视作天宇第一号的大骗局。弗劳德的《英国史,自1529年至伊丽莎白逝世止》一书的前四卷所引起的震动之大,仅次于麦②考莱的著作。“高教会”运动曾使宗教改革家很失人望;辉格党人如哈兰与麦考莱等便曾抨击他们的谄媚态度。弗劳德为亨利与宗教改革所作的辩护是建立在最阔大的基础之上的。基于他的罗马教会当时和历来都是人们心智的奴役者这一深刻认识,他对那些曾经动摇过其权势影响的人们是充满着由衷的感谢的。他认为休谟的下述论点都是不正确的,例如说,英国的民众曾像东方奴隶那样,或者,英国议会除了它同意英王的政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理由来支持他。从这个角度观之,则所谓专制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英王既然陷入在这场生死斗争之中,他势不能不动用一切可以进攻与防御的武器,而人民也赞赏他的行动。宗教改革乃是我们历史上的最重大不过的事件。这不是敌对教条之间的冲突,而是要解决英国应自己统治还是被僧侣统治这个问题的斗争。英国与罗马的决裂是英国日臻伟大的开端,是它为人类自由与思想真诚而进行的斗争。他毫不踌躇地承认,有很多好人站在错误的一方,但是那些相信正确一方获得胜利的人们,则应当感激他们的拯救者。弗劳德并不满足仅仅表明亨利八世的胜利是对我们民族的拯救。他深信,这位英王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他相当真诚,而并非那么残忍、自私和淫乱。他坚持认为,英王的离婚乃是出于真诚的顾虑,①②即是,安妮·博林与凯瑟琳·霍华德确曾犯有通奸罪,而他的臣民正③和他同样盼望能有嫡出的男继承人。在处死安妮的翌日即与简·西摩结婚一事及是“当时出于职责需要的一种官方行为”。他并不爱她,但是①弗劳德的文章:《十六世纪的英国海员》(EnglishSeamanintheSixteenthCentury1895);《向西去啊!》(WestwardHo!—1855)为金斯利(见本书541页译注)所作小说,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与西班牙在海上和美洲角逐的故事,讴歌英国海外掠夺的先驱者的业绩。此后,这个标题常被用为鼓舞不列颠臣民进行海外扩张的口号。——谭注②高教会(HighChurch)为英格兰教会中之一派,主张维持僧侣的要求,并重视宗教的外表形式与仪节等。——译者①安妮·博林,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王后。1533年亨利与原配西班牙公主离异,和她结婚,教皇不予批准。此事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导因。1536年安妮以奸淫罪被处死。——谭注②凯瑟琳·霍华德是亨利八世的第五位王后,1540年结婚,1542年被处决。——谭注③简·西摩,亨利八世第三位皇后,1536年结婚,数年后病故。生一子,即爱德华六世。——谭注\n“在一个突然而又悲怆的必要情势之下”他和她结婚了。弗劳德又根据①②下列理由来辩护对莫尔与费希尔的处死:他们准备勾引外国军队入境以使国家陷于内战状态。在这些迅速决定的措施里,国王是在执行民族安全受托者的职责。解散寺院也是必要的,因为这般人不仅是罗马的卫戍站,而且他们严重败坏风纪;况且没收所得不仅入了朝臣腰包,而且也用在了教育与国防方面。除去麦考莱这一仅有的例外,弗劳德关于亨利八世的诸卷,是19世纪中叶英国所产生的最精采的历史著作。书中所涉及问题的广阔,著名人物的生动描写,强有力的国王的具体形象,在在都很引人注目。弗劳德,这位天生的小说家往往善于以最简朴的方法来产生效果。读者好象乘着一叶扁舟驶过晶莹的水面。没有一个英国作家具有这样浅易、流畅③而明晰的笔调。但是,尽管受到金斯利学派好战的新教徒的热烈欢迎,这部书也引起了尖锐的批评。《爱丁堡评论》便对这位历史家的道德概④念给予了接二连三的攻击。很难想象,他曾看到过英国法官的嘴脸;他关于亨利八世的解释,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怪论。他天真地认为,1529年时的议会是自由选举的,而其实,它只是由各郡的郡长所指派的。他丝毫未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来没有哪个审判官或陪审官曾使一个王家公诉案中的牺牲者得以无罪开释。他竟抓住法令的前言来充作公众的舆论的可靠证据。全部著作受到了武力崇拜的毒害。《评论》的批评者下结论道,“卡莱尔由于树立了突出和危险的例子而损害了一本原来可以成为很好的书,对此他应负很大的责任”。柏根洛特曾宣称他根本不懂历史。保利与兰克则拒绝接受弗劳德对于这个朝代的解释。斯塔布斯在关于亨利八世的卓越演讲里也声称他决不能接受弗劳德关于英王的见解;弗里德曼在关于安妮·博林的论文里证明,当时的议会不过是一个陪衬。弗劳德关于爱德华与玛丽的几卷则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角色而显得平淡,但它们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关于克兰默纯系一名谄媚者这个观念,现已不复存在,而消除这一看法上,弗劳德是功绩特著①的。他最早说明了萨默塞特的形象,他的宽大理想和他对老百姓的同情。玛丽是相当真诚的,的确她在解释那个可恨的宗教上未免太有点忠②诚过度了。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提醒了英国人天主教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和怎样完成了它的信仰转变。所以,玛丽的统治期间尽管有着它无法的形容的恐怖,却是不易觉察福祉;而这统治的教训必须永远不再重演。著作的后半部或大半部主要用于叙述伊丽莎白。就写作技巧论,尽①莫尔(More,SirThomas,1478—1535年),世界名著《乌托邦》的作者。因拒绝向“至尊法案”宣誓,被处死。——谭注②费希尔(Fisher,John1439—1535年),罗彻斯特主教,以拒绝向“至尊法案”宣誓被处死。——谭注③金斯利(Kingsley,Charles1819—1875年),英国文学家、神学家,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1864—1865年曾与纽曼进行论战。——谭注④1858年7月。——原注①1547年爱德华六世嗣立,年幼,其叔萨默塞特公爵摄政(1547—1550年),施行了一些较为宽大的政策。——谭注②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伦敦广场名,曾用作烧死异教徒的场所。——译者\n管其间不乏精采段落,但它已逊于前面诸卷,因为这里弗劳德向读者提供了过多资料。不过,在这点上他倒也并非情无可原,因为这几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于西曼卡斯档案的,而他则是第一个探索这些档案的英国史家。正像他早期对亨利八世的厌恶,在深入调查之后曾经转而变为同情,同样,他少年对这个女王的忠诚至此也化为某种轻蔑。他不相信关于她个人人品方面的某些谣言,但她的事迹过去却从来未曾受到过精密考查,而它们是经不起考查的。他写道“柏利与沃尔辛厄姆的信件最后消除了那迄今萦绕于我心头的一个偏见即,她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却是一个有才干的妇人。她统治的伟大成绩乃是因为施行了某种并非来自于她但倒受过她不少限制与阻挠的政策的结果”。这个历史家把伊丽莎白从宝座拉了下来,但却把她的首相捧了上去。他以毫不缓和的语调宣称:“柏利乃是伊丽莎白与英国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功臣”。我们关于这个大政治家的不倦努力的全部知识都是从弗劳德那里得到的。柏利是一个持重胜过才华的人,遇事往往要经过长期考虑才能见之行动。而他也竟得到了四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考虑,借以把新教建立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这出戏剧中的若干苏格兰场景写得极其精采,但也极不可靠。①而同时书中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三十年则一直抱无情的敌意。她的异母②兄,即摄政墨累却又被写成一位屹立于一群自私自利的阴谋家中间的清③白无瑕的骑士。《银匣信件》被全盘接受了;这个严肃的新教道德家在揭穿那个天主教罪人的假面具时感到了一种正义的喜悦。这故事的主角是诺克斯,即一个合乎弗劳德自己心意的人;他拯救了宗教改革。书中爱尔兰的各章,则以其千篇一律的恐怖事件而使读者生厌。西曼卡斯档案与柏利文件的摘要确实过于浩繁了,以致这位历史家在叙完无故舰队之后竟搁笔不再往下写去。这倒是一个聪明的作法。现在卷帙已多达洋洋十二厚册之巨,而所叙不过六十年之事。况且,这部著作究竟是一盛满冲突矛盾的戏剧,因而从艺术上讲,它也未尝不应该在欢快的凯奏声中宣告收场。就实际效果而论,这个从1529年起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开始①的斗争便在1588年结束了。用弗劳德的话说,棋手在将近终局时,已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扫而空。这部著作的长处及其弱点现在一般已有公论。它是关于我们历史上两个最重大时期的最早的一部(而且是迄今唯一的一部)独力完成的详尽纪事。它使得宗教改革的发动者们重新获得了生命,并以无数激动人心的叙事篇章丰富了英国文学。弗里曼在《星期六评论》里所发表的攻击文章并没有多大分量。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敢说,我从无休止地攻击弗劳德中竟获得了对于那个时代仿佛知之颇多的虚名。但人们要攻击弗劳德并不需要多大知识。实际上我对于16世纪是茫然无知的”。他对弗劳德对他的主角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加以指责,这一点乃是正确的。他埋怨弗劳德忽略了考查王室与议会以及与朝廷的关系也是①指玛丽于1553年即王位至1587年被处死,在位约三十四年。——谭注②墨累,James于1564年起兵击败玛丽,立其子为苏格兰王,自任摄政。——谭注③见上文第十章。——谭注①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受到教皇驳斥之时,主持国政的红衣主教武尔塞对此事态度暖昧,1529年被免职。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此后英国海上霸权的基础。——谭注\n有理由的。他提请人们注意校对上的粗疏与细节上的差错等等,也都不算出格。但他在1870年在这部书出齐时所下的最后论断,却超出了批评的公正界限,这话是,“弗劳德先生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全部著作便是四卷聪明的奇谈怪论与八卷宗教书册。它之所以不得享有历史美名的原因乃是:事实方面的极度疏忽与辨别是非的完全无能”。这个被批评者曾向《星期六评论》提过挑战,要求请两位有资格的专家来核对书中任何上百余页的引证,尽管没产生效果。他在写给斯基尔顿的一封信里说,“在十二卷中我承认有真正错误五处以及细小疏忽约二十处,例如i上未加点,t字上未加划,而怀有最大恶意的人所发现者,不过如此。几年后,弗里曼在发表关于贝克特的几篇论文时,又责备弗劳德说他“对英国教会,无论改革的或未改革的,都怀有疯狂的仇恨”,并指斥他具有“一种天生和不可救药的怪癖;而这个怪癖使他无法对任何事情作出精确的陈述”。对这篇首次署了名的攻击文章,弗劳德给了郑重的回答,指出他的批评者所寻出不过是几处细小的印刷错误而已。弗里曼的恶毒攻击只是损伤了他自己的名誉。《诺曼征服史》的作者往往避去手稿文献,而弗劳德的大部资料则取自档案。在抄录那些往往字迹模糊而又用几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时,差错乃是无可避免的。他是一个特别粗心的抄写者与校正人,对于完整引语与他自己的节略引语往往并未标清。但故意的篡改则是没有的事。在他的想象杂文:《火车站侧线》里,他曾对自己遭受的伪造指控作过声辩。斯基尔顿,即梅特兰与玛丽·斯图亚特的作传者宣称,弗劳德对真实具有热烈的尊重。斯基尔顿虽然不能接受他的全部结论,但他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朋友的非凡辛劳与坚实可靠。和弗劳德研究范围大体相同的安德鲁·朗则宣称,虽然别的历史家也许在立意上不如弗劳德忠实,但别人的失误也同①样并不这么严重。布鲁尔甚至惋惜地说,在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早期生活的叙述里面,几乎没有一句陈述是正确的。在编辑卡莱尔《回忆录》修订本时,埃利奥特·诺顿在弗劳德的版本开首的五页中即作了一百三十处的更正,并宣称,在他所校订这部《传记》中,几乎其中每个字母印刷上都有错误。另外,在他的游记诸卷也显出他的记忆力是多么的不可靠。他在细节上的粗心虽是一个严重过失,但是使他不得进入第一流历史家行列的原因却是由于他持论不够公允。波拉德曾申辩说,弗劳德对于亨利八世的看法并不象他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夸大,但是他的心智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则缺少冷静与洞察能力。他一生的主要任务局限在对罗马教会的斗争。在完成了他对宗教改革的辩护之后,他又在新的一章中继续着这同一斗争。在他大胆地为都铎王朝的暴虐进行辩解之后,他进行了甚至更加乏味的工作,即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进行辩护。就连他的作传者赫伯特·保罗,一位对他抱有同情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每当天主教与新教发生冲突时,弗劳德总是本能地,几乎不自觉地站到了新教一边”。他的这种偏见在后期甚至比在前期著作里更为令人讨厌。①托马斯·克伦威尔(约1485—1540年)英国政治家,青年时代在法国军中服役,返国后历任议员、亨利八世朝大臣。1539年受命监督“至尊法案”的实施,大肆进行迫害活动,后因未支持国王与安娜离婚,被处死。——谭注\n在18世纪的英国政府已不再有这样的托词即,英国是为了它的肉体与灵魂而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的。《爱尔兰的英国人》中所表现的正是卡莱尔的精神。虽然他也喜欢爱尔兰的农民,而且也觉得在克里(Kerry)那里钓钓鱼,真是其乐无比,弗劳德却沾染了他老师对这个民族的轻蔑观点。他在写给斯基尔顿的信中说,“我已对我那本关于爱尔兰的书产生了厌恶。这会使那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也讨厌我,虽然我并不希望其如此”。在他的目光里,爱尔兰人是一个劣等民族,而天主教则是一种退化的偶①像崇拜。在叙述到格拉顿议会时,他竟与那些最狂热的托利党人站到了②一边。格拉顿乃是被狂热的民族情感引入了迷途,而克莱尔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谴责了1793年时在选举权上对天主教徒所作的让步,赞成对③④菲茨威廉的召回,称颂奥伦治会社并为国王反对恢复天主教徒的公民资格喝采。在弗劳德眼中,杀死天主教徒不是罪行的讥讽不是没有一定理由的。这本书无异一篇奥伦治会社的宣言,其目的在于表明调和政策的愚蠢。当葛拉斯吞提到有人认为爱尔兰人犯有双重的原罪时,他心中所指的人中即包括有弗劳德在内。虽然这部书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但它在道德上则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有毒害的。他不听从柏克的警告,竟把控诉的目标指向了整个民族。卡莱尔对这部反映了他自己偏见的书是喜欢的,但它的权威很快就被莱基推翻。当他以蒙森的笔调撰作了一篇对凯撒的热烈赞颂并编写了卡莱尔的①传记之后弗劳德在晚年时期又回到16世纪,著成了亚拉冈的凯瑟琳一②卷,这表明他并没有再学到什么新的,也没有忘掉什么旧的。他很失望他对亨利八世的解释未被接受,并伤感地说,要改变群众的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的意见却看不出有什么地方须要收回或改变的。他并不标榜公正,他是相信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与他议会的立法乃是近代世界的大宪章,而所争求的东西则是人类的自由。凡是相信正义能战胜错误的人,便无需为下述那些勇毅之士的所做所为而感到面红,这些人或从讲坛之上或从议会室里,或在断头台边或从火刑柱上而为人类赢得了今日已堪称世界之法则的精神自由。他继弗里曼之后,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所作的三种讲演(内容系特兰托会议、16世纪的海员与伊拉斯姆的信件)同样表现着那种充满战斗精神的新教思想。弗劳德结束了业余历史家的时代。他的一些伟大场面的描绘直堪与麦考莱的媲美,腓特烈·哈里逊曾把他比之为李维与弗鲁瓦萨尔;但是他在思想上还不及①格拉顿(Grattan,Henry1746—1820年),爱尔兰温和的反英派,要求爱尔兰独立及解放天主教徒。1775—1800年间是爱尔兰议会的首脑,1798年协助英政府镇压爱尔兰起义。——谭注②克莱尔(Clare,JohnFitzgibbon1749—1802年),爱尔兰政治家,自1784年以来是爱尔兰政府的指导者,一贯反对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反对改革,反对给予天主教徒政治权利。——谭注③菲茨威廉于1794年底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支持格拉顿的政治纲领,次年3月被调离。——谭注④奥伦治会社(OrangeLodgesorClubs)——北爱尔兰的一个反对天主教旧教拥护新教的秘密社团纪念奥伦治·威廉而得名。——译者①书名《凯撒传略》(Ceasar,ASketch),1870年;《托马斯·卡莱尔前四十年史》(ThomasCarlyle,ahistoryofthefirstfortyyearsofhislife)共二卷,1882年,《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的生活》(ThomasCarlyle,ahistoryofhislifeinLondon)共二卷,1884年。——谭注②书名《亚拉冈的凯瑟琳的离婚》(TheDivorceofCatherineofAragon),1891年。——谭注\n卡莱尔,另外他所做过的工作甚至有推倒重来的必要。他从没有认识到,历史家的责任既非颂扬也非谩骂,而是对复杂的过程与矛盾的理想冷静地进行解释。\n第十七章牛津学派Ⅰ在麦考莱·卡莱尔与弗劳德的著作成千累万本行销的同时,更加严①密的史学方法开始被应用到研究上面。斯塔布斯早在就学时期便已着手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学习,并利用假日研究其本乡内尔兹巴勒郡旧法院的案卷。到他进入牛津大学时,他已对查询中世纪文献的方法十分熟悉。二十五岁时,他在埃塞克斯接受了一个牧师职位,就在那里,在此后十六年平静的岁月中,他颇余暇研究,竟成了当时英国最高的中世纪专家。他第一部著作追述了数百年来英国主教的接续情况。《英国宗教实录》曾得到一些学者赏识,推为一部有功教会历史的重要贡献,迅速成为这方面的必备参考书之一。他的谨严学风使他成了当时档案委员会出版物的一位严峻的批评家。他指出,公家资金往往浪费在次要文献的刊印上面,而当时权威资料却很少受到选录。另外,对于编辑者的责任的观念也是狭隘的。当忏②悔者爱德华传记出版时,他写道,“我遗憾地看到在这些出版物里,关于语言的东西竟成了编者注意的中心”。这种编辑标准不少在这位批评者自己的手中果然得到了提高。1875年,案卷部主任罗密里爵士,得财政部的准许,进行了关于中世纪末期之前英国资料的校订版本的刊行工作,这件事主要由达夫思·哈第来主持,他对于《英国史的资料与文献》的研究是一部具有经久价值的作品。斯塔布斯立即自荐参加这项工作,但直到1863年,这位编辑大家方才得到委任。在此后二十五年的长期内,他确曾以种种既以技术见长又富于历史学识的杰作丰富了《卷帙丛书》,可谓开英国中世纪历史资料研究的先河。他具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各方面必备条件——古体文的精通、广博的学识与冷静善断的性情。他的最早①一卷:《理查一世行程》出版于1864年;他的最后一卷,即《马姆斯②③伯里的威廉》的结束卷,出版于1889年。他关于邓斯坦的一卷,为这位英国杰出教士洗刷了种种诬陷,而关于早期安吉文朝的诸卷则都附有历史导论,在这里他对许多统治者的个性特征第一次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描绘。这些洋洋大观的序言中所显露的高度文才是和它们的渊博学识同样惊人。他是在资料的直接印象下进行编写的。1866年时他说过,“我①参阅《威廉·斯塔布斯通讯》,胡登编辑,1904年;梅特兰,《英国历史评论》,1901年7月号;《季刊评论》,1905年1月号。赫伦·卡姆,《七十年后的斯塔布斯》,《剑桥历史杂志》,1948年,第129—147页,总结了此后的批评意见。——原注②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谭注①理查一世(在位:1189—1199年),即王位后,参加第三次十字军,返国途中为奥地利公爵所俘,1194年被赎出。——谭注②马姆斯伯里的威廉(1095—1143年),马姆斯伯里修士,编有自萨克逊人入侵至1128年的王朝历史。——谭注③圣邓斯坦,(924—988年)坎特布里大主教,10世纪英国寺院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曾被指控为排斥异己和滥用威权。——谭注\n正在凭借天赋来撰写我的亨利二世。除非我感到一切不啻出自我的自身,我便简直写不下去”。正当斯塔布斯全身沉浸在编年史的时候,他忽受其母校之聘,担任了近代史讲座教席,时为1866年。格林曾就这件聘请事于《星期评论》撰文表示欢迎,认为此事足堪与剑桥之聘请名小说家来作教授或牛津之擢升大哲学家去讲教会史等相媲美。的确,他乃是第一位堪充此任的积学有素的历史学家。这个新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讲里很坦率地说明他对自己职务的看法。“近代史的研究,是神学之外精神上所可能受到的最彻底的宗教训练。正是基督教赋予了近代世界以统一性,而同时使之与过去时代的陈死事物一刀两断。”但是他的政治与宗教信仰却从未干扰他的工作。演讲最后表示,他希望能够帮助建成一个历史学派,以期在这项共同任务上与外国的学者通力协作。斯塔布斯在他在牛津的二十年间一方面忙于授课,一方面忙于《宪①政史》的编写。他给自己规定的责任极重,但是他的许多最精采的篇章也多成就于此时。他在辞去讲座后,曾把自己认为有出版价值的讲义刊印了出来。对于这个历史家,我们从《中世纪与近代史讲义》里所获的印象要比从他的任何其他著作所得的更为完备。他那浩博的知识与多样化的题材虽也引人瞩目,但那种轻盈的笔触,生动的人物刻画,幽默诙谐与欣快活泼,同样也很动人。他关于亨利二世宫廷上文学与学术以及关于亨利七世与八世等的卓越论述,都不失为他的辉煌论著中的杰作。他死后又陆续刊出过讲义数卷,但这些对他的声誉已无重大增益。他的主要兴趣仍在宪政方面。他说过,作为一个文明民族,它的学者仅对雅典罗马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而对自己祖先的体制风习则一无所知,这并非一件值得嘉奖的事。在受牛津之聘的第二年,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将就宪政史作十八篇讲演,从塔西陀起讲至亨利二世止,并且已经写好大部分讲稿。这些讲稿曾于其死后出版;有趣的是,现在发现了这部名作的初稿。他的下一步骤为1870年出版的《宪章选集》(SelectCharters),书出后一时成为其他时期或国家的同类著述之楷模。书前的导论部分以至简峻的笔墨概述了迄爱德华一世止的宪政历史。弗里曼颇称赏此书,誉之为“无论学问之笃粹与识见之卓越,均无愧当今一流学者手笔的一部著述”。通过头等重要史料的选择——法律与宪章、条约与编年史,等等,——他使早期英国史的研究变为一种生动的现实,其中他所作的种种扼要阐释对法律与惯例的许多模糊处颇能不乏新鲜。尤其经过多番修订,这部《宪章选集》尽可视作《宪政史》的一部可靠注释资料。斯塔布斯的杰作开始问世于1874年,书出后立即被公认为属于英语语言中六七部历史巨著之一。书中所涉领域之广,远过于书名所示范围。它实际上是自朱里安·凯撒至都铎王朝登基止的一部英国史,是关于我民族生活的第一部权威论述。书中在外交、经济状况或军事细节等方面失之简略;但它包括了教会、国家、法律、司法、行政与财政。梅特兰说过,没有一部关于宪法发展的著作曾经写得这么鲜明具体。“当我们①全名《英国宪政的起源与发展史》(TheConstitutionalHistoryofEnglandinItsOriginandDevelopment),三卷,1874—1878年。——谭注\n亲眼看到各种典章制度在我们周围生生灭灭的时候,作者却使我们一刻也忘记不得,这一演进与解体的过程没有一处不是依赖人们的具体行为组成。”凭借着把带分析性与带叙述性的各章交替排列的作法,他作到了使社会结构的研究与民族运动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正确地认识到,重建宪法发展的主要路线是他的最大任务,他却从来不使读者忘记一个民族的生活之网的编织是何等千头万绪。斯塔布斯的著作是处理中世纪整个英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爱好法律:人们曾说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法官。他在牛津的一位同事布赖斯教授便说过,斯塔布斯与弗里曼和格林不同,他对法律问题有着巨大兴趣,并非常善于掌握这类事物。《宪政史》的第一卷叙述至诺曼征服止,是书中最少创见与经久性的一部分。关于那个时期的资料本极匮乏而又难于解释。梅特兰在三十年后写道,“在绘出那块荒漠地域的准确地图之前,很多调查研究者很可能已经暴骨沙碛。值得怀疑的是,他曾否充分觉察到他所穿越的地带的险恶性。”另一方面,他的法国批评者珀蒂-迪塔伊与贝蒙则埋怨说:他的结论往往小心翼翼,他在文献不足的时期面前往往显得踌躇莫决,并且回避困难问题,不作结论。不过谨慎从事也许倒是聪明作法。他非常熟悉魏茨与格奈斯特、摩勒父①子、布伦纳与索姆的著作,有时还对他的德国向导步趋过甚。在他的英国前辈中,他把肯布尔看得最高。1859年时他曾称誊肯为“我的学术楷模”。1866年他又写道,“我很抱歉我对于帕尔格拉夫不敢信任。肯布尔也同样往往成为他自己的理论之累,但我认为他的一些看法倒还包含着较多意义”。斯塔布斯是英国社会依赖于条顿基础说的信仰者;他接受摩勒关于“马克”公社的理论。但揭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复杂性的工作,原是属于下一个世代的;他不应因为他未能预见他们的研究成果①而过受苛责。他也不应因为他和所有维诺格拉道夫以前的学者们同样误解过族有地的性质而受到严厉指斥。但是到了诺曼时代他则站立在了较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时史料已很充分,问题也不似过去那么棘手。待到他叙述至亨利二世及其子嗣时,他已进入佳境,这里的任何一条僻路曲径他都无不熟悉。由于他对这个时期十分烂熟于胸,所以他遂能在短短六周之内为某个通俗丛书写成一个关于金雀花朝的出色简编。正是在这里,他的笔下最为稳妥,他的人物刻画也最为生动和令人信服。甚至在14、15世纪时期,亦即那个“阴暗、凋敝、无所作为的时代”,他也能巧妙地使情节的兴味保持不衰。他夸大了封建制度的混乱,承袭了那种认为《大宪章》是一个觉醒的民族所作的功绩,而非男爵们为要保持其自身特权而产生的结果的传统错误看法。另外对爱德华一世的称颂也失②之溢美。但在第2、3卷里却很少有重大错误。书结尾处载有他对中世纪末期的社会与政治影响的一篇评述,为他综合能力的最高表现。在《宪政史》的种种优点中,最突出的是他持论公允。在政治与宗教见解上与他很不相同的梅特兰曾说过,“阅读斯塔布斯的著作乃是一①摩勒(Maurer,GeorgLudwigvon1790—1872年)及其子康拉德(Kon-rad,1823—1902年)均为德国的法学历史家。——译者①维诺格拉道夫(SirPaulVinogradoff,1854—1925年),俄国法学家及历史学家。——译者②参阅坦普尔曼《爱德华一世及其历史学家》,见《剑桥历史杂志》卷X,第1期。——原注\n种司法上的训练”。不过斯塔布斯在著作以外发表意见却是相当直率的。他在1859年表示支持奥国,评论过那些“糟糕的意大利人”。他在1863年指斥过“那些可恶的波兰人”,并讥笑过加里波第到英国的访问。布赖斯记载,他拒绝过会晤一个单一神教的牧师;这位教授还得意地对牛①津的听讲人说,他曾如何从格林手里把一本勒南的书丢到了字纸篓里。②他任圣保罗教堂的牧师时,曾庄严地焚毁过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著作。他还嘲笑过弗里曼为土耳其虐政下的牺牲者而代抱不平的过度热情。由于厌恶清教,他不赞成格林对17世纪斗争所作精彩叙述。他自称他已浸沉在了僧侣与保守的原则。然而,这个反动成性与偏见强烈的人在判断很久以前的是非时,却能作到完全不偏不倚,一秉至公。他还十分得意地自诩说(而这话也一点不假),谁也无法据其大著来评断他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他曾因为赞成兰开斯特派与议会政府友好和因为对较有权的约克派态度严厉而遭过谴责。他在一次牛津演讲里曾说,他的任务并非要把人们强行分作辉格或托利,而是要使辉格成为善良聪明的辉格,与托利成为善良聪明的托利。他的书中没有虚美溢恶之辞。他宣称,最高的正义只能表现在对犯错误者与迷路者的最深刻的同情上面。他没有重蹈那个曾使弗里曼陷入其中的迷途,即把盎格鲁-撒克逊制度加以理想化;另外在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问题能持论公平。珀蒂-迪塔伊在③他的三卷更正性与补充性的著作中因为这事对他颇感钦佩,甚至竟认为斯塔布斯的书大有自由主义倾向。他宣称:斯塔布斯实际上属于那个赞成选举改革与政治机构完善化的新的一代,并且受了德国爱国主义学者所宣扬的原始德意志制为人类尊严与独立泉源这一见解的影响。斯塔布斯在他那篇颇具深意的前言里曾说过,“制度史的精熟掌握甚至初步熟悉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有着它特有的观点与语言。它以完全不同于武器的虚假闪耀的真正光芒来阐明人类的功绩与品质。如其人们必须引诱方才前去研究真理的话,那么它所能给予的引诱是微弱的”。题材的庄重严肃以及其中许多论点的隐晦费解等特点都使《宪政史》一书颇不易读,但它的文体却清晰而有力,若干章节甚至达到了很高境界。在其长达二千页的巨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芜词赘语,因而受到举世学者的共赏。作者曾称,他的第一卷在德意志所受到的称颂与理解比在英国还多。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在德国有更多的人能够认`出它的分量。他访问过戈丁根的魏茨,但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①友则是属于稍年轻一代的。保利,这位研究中世纪英国的历史家,在他的著作出版时曾为他写了书评。他和李伯曼的友谊甚至更要密切一些,后者称他为研究中世纪英国的最大历史学家,而这位牛津教授也称颂李①勒南,见本书第二十五章。他的著作《耶稣传》、《基督教的起源》,试图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看待,扫除其神秘性,被正统神学家视为离经叛道的作品。——谭注②H.斯宾塞(1820—1903年),有名的英国哲学、社会科学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搬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谭注③《对斯塔布斯著作的补充研究》,1908—1929年。——原注①保利,R.(1823—1882年),德国著名史学家,曾受业于兰克和达尔曼,后留学英国,《英国史》(GeschichtevonEngland)共三卷,是他的代表作。——谭注\n②伯曼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巨著为“一部内容精彩、极具价值的作品”。他在外国获得过多种荣誉;到处被尊为以谨严著称的历史学派的领袖人物。陶特与朗德即是他最著名的门生。1884年斯塔布斯接受了支斯脱郡主教职。他在牛津的临别演讲里宣称,他不打算放弃过去的研究,希望出版《不列颠宗教会议》(BritishCouncils)的第四卷,并完成他出版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著作的工作,甚至再出一部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宪政史大纲。在这些计划中,仅仅第二项得到实现。他的新职务使他相当烦恼,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留在书房里面;所以,我们也就失掉了一部修订本的《宪政史》。他不想压缩这部书的篇幅,他在后来各版里所作的更动也都非常有限。他以从不衰竭的注意力追踪着一些年轻人的研究活动,但却很少认真吸取他们的成果。当赫伯特·霍尔指出他在关税记载中的错误时,他作了纠正。他接受了维诺格拉道夫关于族有地的解释,但还主张有某些公地的存在,虽然对自己的说法提不出什么根据。他在一条注释内提到了朗德关于骑士仪式的论述,但他的原作却仍留着未改。梅特兰在他逝世时写道,“我们觉得我们曾经有了一个国王,而现在则没有了。”他补充说,再没有一个英国人曾经把从素材搜集与具体叙述到推论概括这一历史家的全套过程这样完备地向世人举授无遗。他的教导与榜样曾使牛津蔚为系统学习与研究的一大中心,但他不是一位渊深的思想家。当巴克尔的著作出版时,斯塔布斯曾说过,“我不相信历史哲学,所以我也不相信巴克尔”。他也不接受弗里曼关于历史统一性的看法,以及一些从①莱辛获得的更加富于哲理的概念,这些主教坦普尔在其著名论文《人类的教育》曾作过阐述。斯塔布斯是他所在时代的英国最大历史学家,在将德国学术研究方法介绍入我国这点上,他的功绩是任何他人所难比拟的。Ⅱ①虽然弗里曼的年纪比斯塔布斯稍长,但对后者一向以师视之。他们二人与格林一起形成了一般所称的牛津学派;格林曾把他最著名的书奉献给“我在英国史上的师长们”。但是弗里曼与斯塔布斯无论在气质与观点上都很不相同。斯塔布斯冷静而沉着,而弗里曼则是一个英雄崇拜者与宣传家。斯塔布斯的文章扼要简洁,而弗里曼的文章则详尽枝漫。前者是一个极端保守者,后者则是一个好战的急进者。他们著作的范围也不相同。斯塔布斯毕生专攻中世纪英国,而弗里曼则对雅典、罗马、②③亚琛、君士坦丁堡、卢昂与温切斯特等也都同样谙熟。1841年他进入②李伯曼,F.(1851—1925年),德国中世纪史、法制史专家,精研英国古代史,《盎格鲁-撒克逊法律》(DieGesetzederAnglo-Sachsen)一书(共三卷,1898—1916年)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谭注①坦普尔,F.(1821—1902年),英坎特布里大主教,自由主义思想家,社会改革家。长期从事教育与教会工作,认为宗教与教育是改善劳苦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谭注①参阅斯蒂芬斯,《弗里曼的传记与通讯》,共二卷,1895年;布赖斯,《现代传记研究》,1903年;贝蒙,见法国《历史评论》,卷XLIX;约克·鲍威尔,《札记》,1906年。——原注②亚琛,今西德,北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省之一城市,为查理大帝、鄂图大帝陵墓所在地。——谭注\n牛津大学时,纽曼的影响正还极盛,他的兴趣被吸引到宗教建筑学方面,并一度摇摆于建筑行业与牧师职业之间。但世俗历史渐渐成了他的主要兴趣所在;参加过关于诺曼征服的影响的论文奖金竞赛,忙于阅读梯叶里、林加德、帕尔格拉夫的书以及编年纪事等著作。他第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建筑学史》抨击过一些忽视历史的考古学家。不久以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窗格细工的著作,书中附有自制插图;一两年后,他还参加过一部关于圣大卫咨礼拜堂历史的合编工作。他对建筑学的爱好仍然存在,但此时他对建筑的重视主要已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而是因为它们足资作为以往时代的见证。弗里曼既具有独立的研究方法,遂决心终身致力于史学。在取得学位后的二十年间,他曾以大部分时间潜心于古典世界的研究,特别是希腊世界。他把希腊沦为奴役状态视为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并梦想重新①发现古君士坦丁堡。他还以近代希腊语言写信和演说,歌颂过芬雷并与②特里库匹斯结成了持久的友谊。对于那种说希腊人是杂种的嘲笑,他的回答是,希腊的血缘并不比我们的血缘更加混杂,而他们的民族性格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他对近东基督徒所抱有的热情,正如他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同样强烈;他极力反对克里米亚战争,认为这是企图支持野蛮虐政。他计划编写一部《联邦政府史》,从希腊叙起,中经瑞士与尼德兰迄美国止。书仅完成一卷,但这个巨型片断对希腊史上最少为人了解的③篇章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他对希腊于其失掉自由后所组织的联邦的详尽研究,迄今还是必要的参考。书的第二卷叙述瑞士;在察访瑞士后,他宣称从心底爱好瑞士。他在关于英国宪法的著名演讲里反映了他对瑞士各州那种简朴民主的极大热情。弗里曼在专攻古代世界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对后来时期的注意。1865年,亦即当他四十三岁时,他决心成为研究诺曼征服时期的历史专家。在宗教改革之前,我们历史上的这个重大事件从来不曾有过认真的研究。梯叶里这方面的著作缺乏谨严性,立论也多不够可靠。帕尔格拉夫则在叙述至“征服者”之前便已死去。那时,斯塔布斯也还未曾开始编写他的《宪政史》。《诺曼征服史》自盎格鲁-撒克逊英国与在法国的诺曼人的定居等简况开始叙起,诺曼诸公爵的叙述在书中是极具精彩的部份,而关于丹麦诸王的研究也第一次显露了他们的动人之处与重要性,但作者的叙述到忏悔者爱德华时,文笔才开始纵横驰骋起来。这里①的主角是葛德文;在将他从他的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时,弗里曼把他与西蒙·德;蒙福尔并列,尊之为“伟人”,并在他的墓碑上写下诔辞。对③温切斯特在罗马占领时代为英国第五大城,艾尔弗雷德王以后为韦塞克斯首都,中世纪为羊毛贸易重要商埠。——谭注①芬雷(GeorgeFinlay,1799—1875年)——希腊史学家,著有《希腊史》(1844—1861年出版)。——译者②特里库匹斯(Tricoupis,1788—1873年)——希腊作家与政治活动家,著有《希腊革命史》。——译者③参阅伯里为该书1893年版所作序言。——原注①葛德文,10世纪末丹麦国王卡纽特(Canute)统治时期最强大的伯爵。1036年卡纽特死后,葛德文家族扶植爱德华为王。1051被放逐。次年,向伦敦进军,国王屈服。1053年死。——谭注\n②于哈罗德的描写,甚至比对他的父亲更多谀词。在诺曼人与撒克逊人的斗争中,他寄同情于后者。他对威廉的伟大处感触很深,但所描写的形象,虽然确切周到,却缺少生气与文采。他的征服对于整个民族生活所带来的动乱,远比想像的要少得多。尤其是作为英国的光荣与骄傲的自由宪法,并未受到严重干扰。民主成份并未被完全淹没,那保卫自治政府神圣原则的贤人会议,曾于1085与1086年开过。这部书乃是热情的辛勤成果。作为一个崇尚政治自由的人,他自以为他在条顿民族中间,特别是在自己的祖国之内找到了它。一个德国的批评家宣称,“人们不免要认为,昔年撒克逊族的血液今日依然纯净地①在他的血管里流转着。”他说,他会欣然在哈罗德的麾下战斗于森拉克的。尽管书的篇幅极大,它还是勃勃有生气的。这座广厦是建造在坚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格林誉之为学术研究之一大奇迹。他的学识不仅表现在书的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每卷的无数附录内,其中有不少属于具有高度价值的评论。他的第二大优点则来自他对所写事件的发生地点的熟悉。他是英国历史家中最早认识到地理位置与历史遗迹的确切知识在重现历史上的重要性。他的《诺曼底与缅因记行》完全可作为《诺曼征英史》的诠注来读。“征服者”及其夫人的生地墓地,其所居城市、其赢得声名之战场及其所建造的城堡与教堂等等,——这一切有形可见的遗迹均有助于以使其人其事重现在我们眼前。弗里曼关于诺曼征英在历史上地位的看法不无可以訾议的地方。在反对梯叶里在这个问题上的灾难时说,他过低估算了动乱的范围并过分夸大了种族同化的速度。由于立意建立所谓连贯性,他对证据往往过于轻信,另外对“征服者”晚年所召开的贤人会议给予了过分民主的解释。他对征英前后宪法中的民主成份也有夸大之嫌。他写道,“我们一般归功于‘征服者’的那些法律与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在许多情形下却是属于亨利二世的。”但这样一来却未免把过多的创造性归功于那个安茹王②朝的君主,亨利二世发展了他父亲亨利一世的一些观念,但与他父亲的差别并不很大。弗里曼对于征英结果的论述,比较缺乏完整性,因为他忽略了民族生活的若干重要部门,特别是关于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对国王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该书的主要弱点。它是政治的论述,而不是人民生活的描写。格林在《星期六评论》所发表的一系列率直的批评文章中,正确地指出了弗里曼在道德与思想的同情上面①的某种狭隘性。“他略而不谈宗教、思想与社会状况。他赞赏集合在贤人会议里的人民,但却从不带领我们去看看那些自由民的屋宇或农户的茅舍。关于我们祖先的实际生活、风习、好恶,书中没有提供我们任何东西。它实际上不过是一卷史学翻案文章。”这个批评虽然严峻,但基②本上则是正确的。在弗里曼看来,唯有行动才是历史,而在这范围之内,②哈罗德二世,葛德文的长子。1066年1月爱德华卒,哈罗德被推选为国王。同年,诺曼底公爵侵入英国,哈罗德战死。——谭注①森拉克,在海斯汀斯附近。1066年诺曼底威廉击败哈罗德的海斯汀斯之战,亦称森拉克之战。——谭注②即金雀花王朝。——译者①重印于格林的《历史研究》,1903年。——原注②比较保利的批评意见,德国《历史杂志》,卷XXXVII。——原注\n不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他也都能毫无疏漏。在叙述“征服”本身的第三卷内,一切详情细节概在欢迎之列;但是其中一些较小战役与叛乱的记叙却和那些决定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同样详尽无遗。他缺乏斯塔布斯与格林所具有的那种选材本领。弗里曼关于编年史的知识是无所不备的,但他对手稿缺乏审辨能力并且没有学过古文字学。他在索谋利兹城自己的藏书室里写作时,所依据的尽是刊印的资料,但就是这些,他也未作到充分利用。因为缺少法律或社会结构方面的兴趣,他对宪章的重要性并未能充分认识。他的《末③日审判簿》一章的写法是肤浅的。朗德关于弗里曼属于过了时的学派的提法,并非没有根据。他没有作出什么发现,因为不去研究手稿而要有所发现是不可能的。他不懂得,制度与经济状况的重要性殊不亚于帝王将相的盛衰陵替。至于书中的细小毛病则为刺目的条顿系词语,某些中意的词句使用得过于频繁,用字的不够雅驯,例如“不公正”,“非法”,①“大量的”,等等。在他与朗德关于哈斯丁斯战役的激辩中,他所下的②判断也是对他不利的,好在这事尚无重大影响。尽管有着这种种来自“作为”与“不作为”的过失,这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经久意义的作品。《诺曼征英史》还有一部关于威廉·鲁弗斯的著作作为其补编。虽然鲁弗斯的统治时期不长并且比较平静,他还是用了两大巨卷来加以叙述。编年史上所记载的每桩事实现在又都被重新转录到这位历史家的卷帙之中,许多地方还附赘着冗长的议论。保利曾指责他对那些仇视鲁弗斯的僧侣所加给的诬蔑也都一概接受,不过要想能证明这些诬蔑之误也是办不到的。当斯塔布斯接受了主教职后,弗里曼当然被选作他的继任者。除了他关于希腊与诺曼英国的巨著外,他还出版了重要著作《近代欧洲历史地理》一部,有关萨拉逊人与奥斯曼人的论文与讲稿三卷、《英国宪法》与《比较政治学》以及某些历史名城与地区的许多研究论著。正如斯塔布斯那样,他对讲授他聘约上所规定的一些课程兴趣不大,并每每慨叹英才的缺乏,但在完成教学任务上还是不遗余力的。他首先讲授了《历史研究法》课程,作为开端,而后讲授5与8世纪欧洲概论以及《欧洲史上的主要时期》史纲。奇怪的是,这位讲近代史的皇家教授对于近四个世纪的历史竟很少了解,因而他的大部分题目都是关于中世纪的。他晚年时期所致力的问题与他讲课的范围距离很远。他对诺曼英国的研究,燃起了他对一个也曾由诺曼国王统治过的美丽岛屿的兴趣。一个时期中,他曾想编写一部诺曼人在西西里岛上的历史,但不久他又认为他必须把历史继续追溯上去。该岛的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的冲突之地。它应是非洲还是欧洲的一部分呢?“迄今还没有人把这段历史的整个经过视作对世界史的一种贡献。我愿读者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的著作。这里是帮助我们认识武断划分的愚蠢的再好不过的材料;而这种划分常把历史的研究弄得空洞而没有意义。”他愿拟把这段历史叙述至腓特烈二世死亡时止,但这注定是办不到的。他从来不懂得如何对材料进③评《历史研究》,《十九世纪》杂志,1898年,12月号。——原注①原文为unright、unlaw、mickle。——译者②参阅《季刊评论》,1892—1893年,与施帕茨,《哈斯丁斯战役》,1896年。——原注\n行压缩,因而当他去世时,他的四大巨卷也仅把内容叙述至公元前3世①纪初期。他宣称他在《诺曼征英史》中虽然阐明了许多事实,但在西西里早期的历史中却难于找出一个绝对新颖的事,霍尔姆已经把这个题材②研究得详尽无遗了。他自己的贡献主要限于他对此岛的知识方面。他的热情简直是冲决一切的。他说,“希腊语是语言课中最高贵部分,希腊史是世界史中最有教育意义的部分”。所以,每次重读修昔底德,这位“最伟大的历史教师”的作品,总是其乐无穷,他并论证了自己早年时所作的种种判断。“至于叙拉古的民主,正如雅典的民主那样,我们有格罗特可作为我们的老师。而经过多番体验,我愿再次强调,提尔华尔迄今还没有人能胜过,甚至格罗特超不过他。”这部著作从论述西西里历史的特征一章开始。整个全景的描述广阔宏伟,西西里与其它岛屿的比较部分也具有启发性:但书中重复之处过多,引喻也有时非但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徒乱人意。其后紧接着的一段关于岛屿自然特征的描写属于他的最好文章,而叙拉古城的建立一节中,在写到该城在历史上的地位时,作者有机会写下一篇华丽辞藻的专论。叙拉占与迦太基、意大利的战争叙述过于琐屑,令人生厌;但关于雅典远征的细致叙述,读者则不会有任何意见。第四卷叙述至亚伽多克勒的暴虐止,在他死时尚未完成,后由其女婿阿瑟·伊文思整理出版。这部著作被译成德文,并受到霍尔姆的热情嘉许。阿道尔夫·鲍尔也声称,自格罗特以来,在论述古代的英文著作中,没有一本著作显示了这①样博大精深的学识。这是一部宏伟的未竟之篇,的确它正如《诺曼征英史》那样,不免失之冗长,但也充满着那种洋溢于其全部著作之中的特殊感人力量。弗里曼的中心理论便是历史的统一性。从早期希腊到罗马帝国,再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与近代欧洲,其间不存在任何中断;这种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正是他对历史思想与历史教育的一大贡献。但是,斯塔布斯在他一次演讲里他花了一定时间反对他朋友的这种哲学。他宣称,古代、中世纪与近代历史的分别研究会有好处的。在行动的世界里是存在着连续性,但在思想与情感的世界里,即在这个弗里曼知之不多,注意得较差的世界里,却存在着巨大的裂口。我们现在还可提出一项更有分量的批评意见。自弗里曼发表他的理论以来,历史家的眼界已大为开阔。而他的视野则局限于欧洲。但希腊已不能视作是文明的起点,因为古代东方的发现已使我们的看法有所改变。再者,尽管一再强调古代、中世纪与近代世界应当并重,但他的历史观念却是纯属表面的。《诺曼征英史》中包括了一章关于古代建筑的论述,《西西里史》中也用了几页篇幅来①论述早期希腊文学以及亥厄伦与品达和埃斯基勒斯的关系。然而,正像腓特烈·哈里逊所埋怨的那样,十分之九的人类历史却对他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老友布赖斯宣称,“他性格的基调是,他对自所喜爱的人们、①书名《远古以来的西西里史》(HistoryofSicilyfromtheEarliestTimes)共四卷,1891—1894年。——谭注②霍尔姆著有《西西里古代史》(GeschichteSiciliensimAltertum)共三卷,搜集原始资料颇为丰富。——谭注①鲍尔,A.《希腊史研究》,1899年。——原注①亥厄伦(Hieron)——叙拉古僭主;在位时期是公元前478—467年。——译者\n事物与地方等等,热情洋溢;而对于那些素不关心的事情,则几乎冷若冰霜。他把历史看成了单纯政治事件的纪录。他不仅自己对宗教、哲学或社会状况一概不感兴趣,而且还认为别人感觉兴趣是件怪事”。他对英国与西欧的教会与城堡的知识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历史家都多得多,但据说,他只去看过一次画展,而这次还是被格林拖去的。他对柏拉图、希腊悲剧家们与莎士比亚虽毫无爱好,但却喜爱英国的古老歌谣,称颂司各特的小说和欣赏麦考莱的短抒情诗。观念的世界对他是不存在的。历史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事件的纪录,因而他只承认它的继续性,而不承认它的有机的进化。不过他的偏见还没有使他陷入卡莱尔与弗劳德的狂热地步,因为他是厌恶暴行的。他夸大了葛德文与哈罗德的德性,但他从来不为一个坏人掩饰罪过。格林虽然感到《诺曼征英史》一书中有许多地方该受指责却也承认这书的崇高品德。指出“书中洋溢着对人民自由的强烈热爱和对一切残暴与非正义行为的深恶痛绝。如果说其中也有英雄崇拜的话,这种崇拜则不是对野蛮暴力的怯懦崇拜”。弗里曼心中最值得景仰的对象乃是提摩勒翁与华盛顿一类人物,因为他们很懂得放下权力。尽管存在着种种偏见与局限,他在历史学家与历史教师中仍然占有极高地位;任何学派的读者在他生气勃勃的篇章中总可以吸取到一定教益。Ⅲ①格林虽然从斯塔布斯与弗里曼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比他们两人都更能富于创见。当他还是儿童时,他已在他牛津的家宅附近的教堂内探索事物,摹拓黄铜铭文。二十二岁时开始着手著作,编写了一系列关于18世纪时期牛津的论文。他那流畅、秀丽的风格此时已大体形成;这座古城以及大学中的神权论派导师与喧闹的大学生的情景形象,在他笔下写得极为精妙。二十四岁任神职后,他曾在穷苦人中间工作过九年。他后来常对人讲,他在伦敦东部贫民区的经历对于他的著述事业大有帮助,因为在那里他获得了对群众的真实兴趣。1862年他在索美塞特考古学会上所宣读的一篇关于邓斯坦的论文,成了他一生事业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那里他遇到弗里曼。这个年长的学者对这篇论文——“为一个崇高而受到诽谤的人所作的崇高辩护”——很感惊奇,因为文章表明,作者不仅长于叙述,而且长于举证。自此弗里曼感到他有责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去为小格林到处说项”。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后格林去世为止,尽管他们各自的历史观点很不相同。弗里曼讨厌格林的想象式的方法,而这个年轻人则惋惜那个年长者只注意单纯事件。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着许多共同兴趣,并乐于在国内外互相来往。弗里曼慨然承认他从那位杰出的友人处获益匪浅。“我从格林城市史的研究方面,得益最多。他那善于抓住城市地形与历史上主要特征的才华是使人惊奇的。在这方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一年后,格林与斯塔布斯在访问他们的这位共同朋友时初次见了面。这位教①参阅,《格林的通讯》,斯蒂芬编辑,1901年;布赖斯,《现代传记研究》,1903年;约克·鲍威尔,《札记》,1906年;摩诺《画像与遗著》,1897年;艾迪生,《格林》,1946年。——原注\n授的性格不很开朗,因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斯塔布斯对格林的著作和他对英国史的功绩仍然非常激赏,并且一遇机会便对他不吝赞誉。他最初想起撰写《英国人民简史》的念头开始于1869年。那时,即使是关于英国史上的明显的事实也缺少较好的新式史纲可以凭据,至于它文明的发展情况就更找不到像样的综合论述。1874年《简史》的问世是历史学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英语世界第一次获得了一部关于自己过去世代的系统连贯而又令人满意的记载。书的主角成了人民;只有这样,英国的历史才能完整地得到说明。国王的事迹被归入到他们的适①当地位,这里鼓角之声开始敛息。乔叟比克勒西战役占据了更多的篇幅。王朝尽管经历了无数更替,战也打了不少,但人民始终还是人民。这种解释历史的方法,现在虽已不觉新奇,却主要是格林的功绩。他虽不是最早发明这个方法的人,但他却是最早以一个大国的历史来阐明这个理论的人。过去历史家曾企图把金字塔立在它的顶端之上,而现在则把它放在了它的基础之上。他的著作还具有传记式的生动趣味与史诗般的连贯剧情。格林书的结构布局固然出色,它的实际贯彻也很良好。由于他巧妙地归并了时代,删去了繁冗的细节,加之文笔生动,并对生活的各方面——不仅政治,而且兼及社会、宗教与艺术等等给予了同样注意:这样,他遂能在一卷的范围之内重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无论在英国或在别处,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从这一事实,也可想见这项成就具有多大困难。他与传统的第一个不同,便是在历史的分期上,不是按朝代或王朝来划分,而是按它们的主要特征来划分。他的归并时代,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尽管他以爱德华四世为新君主制度的开端的作法受到过严厉指摘。他与传统的第二个不同是,他对战争外交等仅作简述,而不详叙,这样,叙述的重点便从具体行动与军事场面转到了内部发展,从而倾其全力于那些足以显示或影响国民生活的人物、书籍、观点与理想等方面。他在写给弗里曼的信中说,“很可能,当你看到玫瑰战争只用了七页,①而科勒特、伊拉斯姆与摩尔只用了十五页的时候,你也许会要咋舌。但是我越是把我们的整个历史通盘进行考虑,我就越发觉得,它的政治历史完全是它的社会与宗教的历史所形成和产生出来的,虽然关于这方面,你是不免要嘲笑我的。”他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在中世纪方面,而《简史》中的这一部分也大体上写得最好。亨利五世这一类单纯实行家从作①②者所激起的注意,远不如艾尔弗雷德或约翰·保尔,朗兰或卡克斯顿等人。书中他强调了市镇的所起的影响,讨论了黑死病的经济后果,并指出了玫瑰战争与社会和经济改变的关系。在他的书写成前不久,他回顾他整个工作时说过,其中关于新学术(NewLearning)、农民起义与城①乔叟(约1343—1400年),英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著《坎特布里故事》为传世名篇。——谭注①科勒特(Colet,John,1467—1519年),神学家、教育家,曾游学意大利,将人文主义思想传入英国,为《圣经》注疏之学开创了新路。——谭注①朗兰(Langland,William约1332—约1400年)诗人,14世纪有名诗篇——《农夫庇尔斯》据说是他的作品。——谭注②卡克斯顿(Caxton,William约1422—1491年)英国第一位印刷家。——谭注\n市等部分,是他所写过的最好作品。在进入到近代史的领域之后,他所熟悉的程度便较差了。但其中宗教改革诸章仍然具有高度价值。斯图亚特朝的章节则稍有逊色;18世纪对施展其专长所提供的机会,比以前任何世纪都更少些。这部著作以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而终篇。《简史》立即获得了成功。自麦考莱以来,没有哪部历史著作曾经这样迅速售出。虽然弗里曼提出过这书的相当部分必须有较高知识程度才能读懂,它还是被许多学校采用作读本与程度较高学生的指导书,成千上万不同年龄的人们第一次对其祖国的历史开始产生了学习兴趣。这本书见解的新颖与学识的广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另外,书中笔调的清新与其中所洋溢的朝气,这在一个已是死期不远的肺疾患者来说,尤属难能可贵。英国历史不再是一本陈年旧历,而是英国人民这个生气勃勃民族的发展历史。的确这部书可谓才人之笔。而这点恰是作者的两位老师所望尘莫及的。不过成功尽管相当成功,它却仍然难逃批评。格林自己写道,“整个书的靠前部分,我见到散文家难免的特性,处处暴露出短篇的小品文作家的那种行文倾向,纤巧文风,敷衍连缀,把乏味部分忽略过去,等等。我是通过写作而学会我的行业的。”在这样的一部著作里,错误乃是无可避免的。斯塔布斯对此说得最为清楚。“正像别人一样,他有时也犯错误,但这些无论对事情的真相或议论的力量都并无影响。”也有人指责说书中在民族发展的叙述上有党派偏见。布鲁尔,①亦即研究武尔舍的历史专家,曾在《季刊》里指斥它是一篇民主宣言,它理想化了人民而轻视了他们的统治者。詹姆士一世被描写成了一个不道德的丑角、懦夫与酒徒;查理一世成了贪婪与卑鄙的化身;乔治三世成了浮夸、自私与残忍的君主。同样他对英国国教也怀有异样的敌对情绪。他认为战争不过是屠杀,并认为,战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毫无疑问他是具有天才的,但他的同情看来不是寄予秩序方面而是寄予动乱方面。“在历史课本的外衣掩盖下,他在政治与宗教方面散播了不少十分过激的见解。对全书旨趣与所讲内容,我们提出郑重抗议。”虽然布鲁尔的批评意见未免过甚其词,但他在看出其“左派”观点这点上则是不错的。格林的这种自由主义倾向的确与年俱增,他属于最早的英国地方自治派。他爱护和尊敬格拉德斯通,衷心同情人民的疾苦②与理想,并对在教会与政府中那些压迫人民的人,深为憎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任何冲突中,他总是站在后者一方。他对弗里曼坦白说过,“我将继续爱护自由,爱护那些为我们争取得自由的人们,至死不渝。”因而他能以深厚的同情心来叙述1381年的农民起义和热烈地支持国会反对斯图亚特起初二位国王的斗争。他没有很好去理解王党的立场,这一点加第纳已开始加以阐明。在论述美洲殖民地的反抗方面,他也缺乏象勒基所表现的那种宽广胸襟。尽管如此,但持平而论,这部书还是不能称之为充满党派偏见的。在许多场合下它还是非常明显地不偏不倚。他对新教与旧教的殉道者能一视同仁,而对他们的迫害者则一概严峻谴责。他对庇得与福克斯都能公正相待。这部书并非是对英国民族①重印于布鲁尔,《英国研究》,1881年。——原注②比较格林夫人在耶稣学院匾额揭幕典礼上的演说,见《泰晤士报》,1909年6月7日。——原注\n的狂热赞歌,也不是对英国政策不顾是非的辩护。他以道德的原则来检验政治,因而对政府在对待爱尔兰、苏格兰、印度、美洲与法国的政策上能够无所畏惧地加以谴责。布鲁尔提出了另一项指责。“社会上对于历史的需求——那种希望把历史写得生动,引人,精彩的需求,已经使这种货色应运而生。这个引诱力是巨大的,格林也往往抵抗不了它。他具有这样一种天然的倾向,即以他的丰富而狂热的想像来提供他那些冰冷而无色彩的资料中所缺乏的戏剧性细节。”在他的友人里面,也间或可以看到类似的温和指责。布赖斯曾说,“想象的能力乃是他的心智与写作上的主要而突出的特征。在这部著作的较早版本中有时便出现过那种为了生动而不顾准确的情形。他的判断能力有时竟为其才华的光辉所掩蔽。”他通过形象色彩的角度来看问题。《爱丁堡评论》中说,“他的文体的缺点是,通篇过于敷彩着色,以致有时使人感到单调,甚至生厌。这种感觉恰与我们在过久翻阅一本画册后所产生的厌倦相似。”但另一方面,斯塔布斯则称赞他在“情节叙述上的惊人的质朴与优美”,这与上述批评适成一种对照。当《简史》正以各种文字的版本成千累万地销行时,格林决意对英国的命运重新进行详述。他以非凡的毅力投入了这项工作,因而,待到1880年时,他的四巨卷本《英国人民史》已告完成。这部“大书”的篇幅约为原来“小书”的一倍,但体系与方法仍和以前一样。作为英国史的导论来说,除了在以前出版的“小书”外,它可说优于任何其它著作,但是问题在于这书是否有编写的必要。这部书与前一部的间隔过短,以致无暇纳入新的研究成果以纠正过去某些问题的论断,因而遭受到和以前同样的批评。加第纳指责他惯于忽视宪法方面问题,特别关于17世纪①时船税、恩税以及其它一些有争执的问题。虽然业已身染沉疴,但格林仍以大无畏英雄气魄投入了新的工作。他很惋惜地说,“民族形成的时期”在一般人们中竟还几乎毫无所知,而其间的种种斗争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只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争。他所已经完稿的《英国的形成》与未经他修订的《征服英国的遭侵》包括了他的一些最好作品。教长史坦莱有一次曾对他说过,“我看你越来越有过趋彩绘的危险。请注意这点。我自己是有同病的。”这次他接受了这个警告。他在攫取景物特征以及这些在历史发展上的影响方面,具有一种稀有的能力。他熟悉英国,热爱英国;1880年时他和他妻子便合出过《不列颠群岛地理》一书。他对于全国地貌、古物遗迹、森林、沼地与道路等的这方面确切知识,在编写“英国的形成”时曾起到过有益作用。他的无数地图第一次把英王国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疆界描绘清楚。除了对外族的入侵与内战的详尽研究外,他还特别另辟一章来叙述征服者的定居问题及其文化与制度。他不同意罗马文化继续论,而赞成弗里曼的主张,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是极其民主的。在继爱格柏之后的《征服英国》部分中,他以绚丽的色调描绘了艾尔弗雷德与卡纽脱,并重申其对葛德文毫无好感的评价。克莱顿在读了格林与弗里曼的书后写道,“格林与弗里曼之间的分歧是很大的。弗里曼企图使你了解每一细节的作法是孤立的,或是附以19世纪背景。他虽一再申说,而你还是不懂。在《形①恩税(Benevolence)往时英王借名献金,从民间勒捐的税金。——谭注\n①成》与《征服》中则不然。整个全景是生动的。”1883年格林的去世(死时年仅四十六岁)是对历史研究的一个沉重打击。在讨论选择什么作铭词时,他曾说过,“你们知道人们将会怎样说我吗?他们会说,‘他弥留之际犹不忘学问。’”格兰特·达夫曾说,如天假以年,他会成为从吉本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布赖斯也相信,许多人会把他放到几乎与麦考莱并列的地位,因为他虽然才力稍逊,但却更为聪颖,和同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认为格林的身上颇有吉本之风,这即是‘在那些足以支配民族命运,引导帝国航程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力量与关系方面,既能备极周详,熟谙精审,又能胸襟博大,高瞻远瞩。’①克莱顿的《传记》,卷Ⅰ,页264,1904年。——原注\n第十八章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Ⅰ正当弗劳德埋头于都铎王朝的研究时,一位才华虽然稍逊但却更加①信实可靠的历史家也正在以斯图亚特王朝为其毕生研究目标。加第纳值得赞美的地方即在于,他是第一个以全部知识与冷静识见对我国充满危急与争论的一段时期进行了叙述的人。可能除斯塔布斯的《宪政史》外,他的著作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上最坚实而经久的成绩。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经完全根据其时代的纪录作出考查以发现那个时期事件的真实情况。王党与辉格历史家只不过见到了他们所愿见的东西。兰克的巨著也才刚刚出版。加第纳常常指责基佐的《英国革命史》只从查理一世开编,理由是,关于詹姆士一世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整个斗争实属必要。②加第纳著作的开首两卷出版于1863年,内容包括这个统治时期的前半段时间。在将近四十年的长时期内,这项工作始终不松不紧地进行着。他曾立意要叙述到复辟时期,但在叙述至1656年时,他死去了。他的著作乃是第一部根据详尽研究大量公私案卷资料而著成的作品。报章书册也曾广泛加以征引。至于各类回忆录,则不论其作者如何著名,也仅仅视作第二类资料而不当成头等资料。试把加第纳著作中一章的附注与以前著作的附注比较一下,便可看到这方面的进步。终于法官把所有事实摆在了面前,然后对之加以正确处理。辉格党关于斯图亚特开头两个国王统治时期所作的解释,自哈兰与“改革法”以来本已非常流行;现在加第纳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他对议会曾站在未来方面以及詹姆士与查理政策的失败正是好事则从未加以怀疑。他的创见,并不在于他对这个巨大冲突的结局作出过什么判断,而在于他对当时主要的活动家的描绘,在于他对当时的不同政策与过去实践和传统的关系所作的估计。他沉着地说,“在这个充满着复杂动机的世界里,一个政治或宗教信条的正确并不能成为据以辨别一个人的高贵与卑鄙的标准。”如果说历史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使其剧中的角色变得可以为人理解,那么加第纳确实无愧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家。他的完备知识与平和气质往往能够使他了解某些他们彼此之间还不能互相了解的人们。他能象斯拍定一①样,清楚地看出培根理想的宏伟之处,也能象麦考莱一样,很尊重科克①参阅《全国名人传记词典》(弗思作);约克·鲍威尔所作评传见《英国历史评论》,1902年4月号;《两位牛津史家》(格林与加第纳),见《每季评论》,1902年4月号。乌瑟对他的无偏袒态度的攻击,见《对加第纳历史方法的批判研究》(1915年),对此弗思曾作过答复;见后者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919年)。——原注②加第纳穷毕生之力研究英国革命史,写成的专著三种:一、《自詹姆一世即位至内战爆发时期英国史》(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ItotheOutBreakoftheCivilWar,1603—1642)共十卷。二、《大内战史》(HistoryoftheGreatCivilWar,1942—1949)四卷。三、《共和国及护国政府史》(HistoryoftheCommonwealthandProtectorate,1649—1660)共四卷。——谭注①科克(Coke,Edward1552—1634年),詹姆士一世朝任大法官,反对征收献金被更职。与议会反对派有密切联系。”权利请愿书”大部分出于他的手笔。——谭注\n与庇姆。他从来不会使读者忘掉在英国的缔造这件事上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他和辉格传统的分歧首先是在关于詹姆士一世的看法上。过去作家对于詹姆士的看法主要不出回忆录与稗官野史范围,而一般人的看法则①从《尼格尔的命运》中来。麦考莱描写过詹姆士的容貌和强调过他的怪癖,但加第纳在这些外表方面则谈得不多。他摈弃掉那些关于他嗜酒与淫乱等等传说,指出,这个君王与一般书上所说的那个丑角很不相同。“就其本意来讲,他很希望能做到办事合理,执法公正,引导臣民日益臻于承平熙和之境,防止以宗教为外衣掩饰派系私忿。他个人的思想一般也较明敏犀利。他可惜缺乏谋略,另外对于他自己肯定能成为英主的非凡才能自恃过高。”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并为日后革命与灾难的直接肇因。对詹姆士之子的描写,则与流行传说的出入不大,虽然作者对他也有微词。“[查理一世]缺乏想象力实在是他的诸种过失之源。由于他自以为动机纯洁,遂一向把人们区分为两种简单类型——那些同意他的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即可以欢迎的善类与须要摈弃的歹徒。在对待后一类上,他以为使用欺诈手段也是对的。而这善恶两类,他都有先例可援。在15世纪时,议会特权曾占优势。而在16世纪时,王室特权又占优势。新世界的精神是站在议会一边的,但同时到处还存在着有力的君主政体。关于开明专政是最好的政体这个信念,不仅为统治者们自己所信奉,而且也曾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士所主张。詹姆士在他登上英国王位之前便曾以书面形式有力地表述过这种见解。培根也曾诚实地相信,一位哲人国王的统治要比人民代表的统治贤明得多。对于这种开明而敬畏上帝的专制理想,加第纳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同时认为詹姆士与查理固然过于庸碌而无法实行之,另外这种体制也只适合于尚未成熟的人民。英国在财富与文化方面正在一往直前,政治自由的新思想已经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因而个人统治,过去在伊丽莎白的强有力的手里虽曾似乎合理,现在在詹姆士这里则显得不够自然了。况且,英国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业已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而告终。国内争论的尖锐化,完全起于政治方面以外的原因。货币购买力因为从西班牙属美洲矿场来的贵金属的大量增加而急剧下降,另外赋税已不复能够适应国家的需要。于是经费的增加引起人们的怀疑,因而要求对其开支进行严密的监督。引起事态恶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这两个国王采取了“高教会英国①国教”的种种作法,而这些在不少清教徒看来几乎与罗马教难以区别。这种疑虑之续有增加还因为,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不愿以英国的全力投入新教方面,以及他们对天主教国家维持了友好关系。查理和法国公主的结婚暗示着城堡的钥匙已交付了敌人。加第纳证明,这两个国王确曾为新教徒;他们拒绝直接卷入大陆战争旋涡的这项政策乃是正确的。他认为,欧洲政治对议会下院来说成了一个没有线索的迷宫。这部著作中一个极有价值的部分即是书中第一次说明了詹姆士的外交政策指出这个①《尼格尔的命运》(FortunesofNigel)——英国司各特所著小说。按尼格尔为苏格兰一位年轻而骄傲的领主,曾赴英格兰劝使英王詹姆士支付对其父亲庄园的债款,以免这个庄园遭到破产。——译者①注见前第十六章。——译者\n政策在执行上虽不免笨拙,但在设想上却并不乏政治家的风度。关于磨擦的第三项原因,颇具新意。最使群众激愤的事情,莫过于这两个国王①对白金汉的宠信;辉格党的历史家早已把他描成一个典型的宠臣,自私自利、虚浮而又无能。加第纳对他的描写不象兰克的描写那么充满赞扬,但认为他还具有爱国思想。“不过,如果对他不以宠臣而以大臣视之,那他就不论在这个国家或在别的其他国家都得归入特别无能一类。”加第纳指出,他即不接受议会行政执行权说,也不接受君权神授说,因而斯特拉福的参加政府决不能说是背教行为,并声称他是一个培根的继承者,一个具体而微的黎塞留。他的主要过错在于,他不能认识到伊丽莎白的制度已经过时,以及稳固的宪政大厦不能以查理作为它的基础而建造起来。虽然加第纳不承认对英王的专政改革与背叛国教的指责,但他却也相信个人统治制度已行不通,并且日趋衰落,而国王的缺乏权谋与轻视妥协,都更使这种制度显得特别令人讨厌。另一方面,虽然他象任何辉格历史家一样,对议会领袖们的品质评价颇高,但他却觉得他们的眼界②在某些方面却比这两个国王还更狭窄。他在讨论1625年的冲突时指出说,“我们虽极力想找出一些虚心接受新思想的痕迹,或者他们所生存于其间的世代与以往的世代在观念上有何不同,而终归无效。”他对科克的思想意识的分析表明,科克与他的国王至少具有同样的保守心理。其次,要说那些赞成王室特权的法官便是谄媚行为,实际上也并无根据。许多先例也是互相矛盾的,忠实的人们对此也尽有其不同的看法。他虽然承认劳德的热诚与善意,他在总结里却强烈反对他的政策。这个大主教是一个忠诚的新教徒,但当清教徒们看到他们朋友遭尽禁锢与残害的时候,也就难于相信这点。对宗教犯罪的报复性惩罚是比任何别的事情更容易激起群众的愤慨。“星法院”本来很少审理政治案件,但现在却赢得了专制政治的工具与罗马化政党的机关的恶名。他严峻指出,极力想把那种不要任何政治自由的意识培养成为一代人们的思想风气。在长期国会的早期阶段里,这个历史家是反对宫廷的;他把内战爆发的主要责任放在了国家身上。庇姆在为国会要求行政控制权上,是打破先例与①传统的;但这项要求只是在未能获得可信任的大臣之后,在他确信没有别的办法可终止个人统治制度之后。方才正式提出的内战爆发以后,国王身上的品质,亦即反复无常,终于驱使他走向灭亡。加第纳在精细研究外交档案之后证明英王曾经不顾一切地去恢复他的权力,妥协当时已属没有可能。由于他深刻理解到查理确已走投无路,因此对他的处死也就不再加以责备。到了克伦威尔(加第纳即是他的后裔),我们又遇着了新的问题。“他是一位勇敢可尊敬的人,时刻希望尽其所能,把他自己的同胞引入和平与正直的道路”。加第纳把他描写为一个具有善于随机应变倾向、①白金汉公爵(1592—1628年),詹姆士及查理两朝的大臣,一再煽动对法国及西班牙作战,丧师辱国。——谭注②1625年6月查理一世召开第一届议会。议员要求罢免并惩办白金汉,国王不允,解散议会。——谭注①庇姆是长期国会中操纵下议院一派的首领,他们强迫国王接受政府必须信任代表国家福利的议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解散议会等议案。——谭注\n温和稳健,甚至保守的人,对于周围盛行的平等主义很不放心,他之走向最高权力并非出于自愿,他深感任何不基于议会同意的统治都将是缺乏持久性的。克伦威尔解散残阙议会的作法,正是作为回复到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步骤。在获得最高权力后,他的最诚挚的愿望便是要变军事独裁为一个文治国家。加第纳他自己虽对克伦威尔一生诚实这点深信不疑,但他宣称别人把他看作一名伪君子也是自然的事。关于克伦威尔的为人及其事迹,他在福特讲座中题为《克伦威尔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在哥比尔丛书内附有插图的专文中所发表的意见比较成熟。从没有一位历史家对克伦威尔的高贵品质与崇高理想给予过这样公允的论述,但关于他才干的评价则稍失严苛;对于他的政治风度也批评得比较尖锐。就将①才论,克伦威尔比不上蒙特罗斯。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政绩及其外交政策也都有所谴责。“清教在他的内心仍然极具影响,但尽管如此,至少就外交政策来说,政治的物质方面,亦即世俗方面,还是占着上风”。他明白:护国政府由于克伦威尔处境的固有困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是少数派,因而他只能以武力来维持自己。军费的开支浩大,一个代表性的议院很有可能拒予拨款。从他们那里我们所得到的悲伤印象是,一个好人正在和厄运挣扎,而他的建设性的工作终归无成。“因而不可避免的结论必然是,克伦威尔在他所拆毁的地方并没有完成什么称得起建设的工作;没有一项护国政府的法令在复辟时期不是被彻底扫除,从此再无恢复希望。”加第纳曾被恰当地说成是一个涤除了所有刻薄与窄狭性的清教徒。②有人认为,他与伊尔文派的关系曾使他比较能够理解各种教派在信仰上的那种高超境界,但从他的书中谁也说不出他究竟属于那个教会或党派。在许多作家矢志于复燃或煽起宿仇旧恨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位法官而且还是一位和事佬。他的最高功绩即在他能以同等的深刻见解为近代人说明了王党与议会派的各自立场,但他的著作也还有许多其它优点。他根据在西班牙与其他各国的调查研究所作出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实在是我们历史上各个时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关于财政方面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境地。作为一位军事历史家来说,他的才干曾使他《内战史》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关于共和国与护国政府的著作表明,他对于海战竟也是同样熟悉。除了一项短缺之外,加第纳具有着为他行业所必需的一切工具——缜密的心智、镇定的情绪、对性格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观念的理解本领。而这项短缺即是他短于文笔。如果他再兼具了这种魔力,他那高贵的著作是肯定会成为有名的经典之作的。他的笔下太缺少优美与特色,但是我们仍不时可以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在他那副谨慎的外表之下悸动着。可能斯特拉福的审讯与处决诸章是他最好的文笔,那些关于不可避免的覆灭的暗示之笔是极具感人力量的。他曾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对两个危急世代中的事件加以叙述;他所成就的业绩已是如此彻①蒙特罗斯侯爵(Montrose,JamesGraham,Marguisof),王党将军。1644年6月潜入苏格兰纠集武力多次击败长老会军,一度占有苏格兰大部分土地。——校者②伊尔文派(Irvingites)以苏格兰神学家爱德华·欧文(EdwardIrving,1792—1834年)命名的教派,否认“原罪”教义,宣扬耶稣即将再临人间,被指控为异端。他死后才成为教派。——译者\n底,因而这一时期似已再无必要以同等宏大的规模来重做一番。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对文化、经济状况与社会生活等叙述得过简而对之多所责难。他毕竟履行了那个首先须要完成的责任,并打下了基础,从而使别人得以从那里继续其建造工作。他过着一个学者的平凡生活;安心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重视全世界其它历史学家们的成就,既不好名也不好利。由于一心忠诚于他给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所以当弗劳德死后牛津大学聘请他继任钦定讲座教授的职位时,他竟固辞不就。他为《全国名人传记词典》编写了他所熟悉时期的条目。在三十年长期中,他始终担任着卡姆登学会的会长职务,为学会编辑过十二卷著作。他还接替克赖①顿担任《英国历史评论》编辑。当杰勒德神父著论提出炸药阴谋乃系由②罗伯特·塞西尔所组织,其目的在于毁坏天主教和巩固其自身的地位时,加第纳当即为其主要论点提供论证。在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中,他是最能把历史著作的责任感提到一个较高标准的人,而且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在我们民族各时期中最为令人满意的著作。对他史学见识的最好赞语便是,属于他自己领域内的唯一对手的弗思,在许多问题上也达到了与他大体相同的结论。Ⅱ③加第纳曾以毕生之力从事于一个世纪的研究,但莱基的研究则广泛地涉及过去各个时代。因为出生于南爱尔兰的家庭,他曾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过神学;但在二十一岁时他出版了一本论述当代宗教倾向的没有具名的著作,书中流露,教会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他最早而又最强烈的兴趣是他祖国的历史与文学。他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写道,“他研究过大演说家们的不少讲演并能背诵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心中装满着爱国党派的诗文,对于《谁怕谈1798年?》的作者,他怀着无限景仰。爱国主义简直成了他的独一无二的情感”。他的这种少年狂热在他的《爱尔兰舆情的领导者》里得到了尽情的渲泄。不成熟的印记暴露在它的全部篇章;尾声部分吐放着火热般的民族主义,但书中不少文章并非没有气势。作者没有公开他的姓名,结果只售出了三十本。这本书的失败使他的精力转到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方面。他的那种博览群书、游踪甚广以及他对巴克尔的景仰等特点,使他走上了一①条特殊的研究路子,其中一项成果即是他的《理性主义史》。这部著作既是一位思想家的书,也是一位学者之作。虽然书的作者彼时不过二十②七岁。乔治·埃利奥特曾以相当的篇幅评论过书的种种缺点,但它仍然是每个研究人类心理演变者的一部必读著作。四年后他的《奥古斯都至查理曼时代的欧洲道德史》出版,标志着作者更大的进步。书中所表现①炸药阴谋是一个图谋炸毁议会的计划。1605年,因被告发而事败。——谭注②塞西尔,即索尔兹伯里伯爵(1563—1612年)曾任詹姆士一世的首席大臣。——谭注③参阅其妻所作《对莱基的回忆》,1909年;与奥克缪特《莱基传》,1945年。——原注①此书的全名是《欧洲理性主义精神之兴趣与影响史》(HistoryoftheRiseandInfluenceoftheSpiritofRationalisminEurope),1865年。——谭注②她的这篇文章曾重刊于其《论文集》。——原注\n的学识更加广博,编排更加精巧,也更富于文采与气势,因而毫不奇怪,它也始终是它的作者的最称得意之作。坦尼森对此书的评价是,“一个青年人而能写出此书固堪称奇,任何人能写出它来也堪称巨著。”但当这位诗人接着说这证明书的作者具有着真正的天才时,他却不免言过其实了。莱基的心智是批判性的,但非创造性的。理性主义的稳定而又无可抗拒的前进的图景曾经引起过广泛的惊恐。在这后一著作,概述伦理理论的一篇导论中,作者表明他不赞成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近代世界中知识的进步在道德领域内是不会产生什么损害的。他关于理性主义与道德的研究论著曾经传遍世界,而这些书的成功也是应得的,因为它们乃是凭借深入行动的幕后以扩大历史的概念的最早的著名尝试。下述这封有趣的信足以说明其作者的意图。“这两部书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意在按照历史方法以检查若干神学主张的价值。第一部是关于把这些主张强加于世的历史。第二部是关于其衰退过程的历史。它们是属于一个很小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维科,中经康多塞、赫德尔、黑格尔、孔德等加以继承,而以巴克尔为其最后的伟大代表。这些作家的特征是:他们不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传记、事件或图景,而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有机整体”。三十岁时,莱基已由其在思想发展方面的论著而赢得全欧声望,但他的后半生时间则以之治近代政治史。弗劳德已经占据了16世纪,加第纳正在专攻17世纪,惟有18世纪尚属空缺。斯坦诺普关于18世纪大部①头历史著作,虽不失为认真而有益之作,但却缺乏广度与色彩。莱基的雄心则在写出一部包括这个时期中的生活、政策、制度、倾向等在内的综合研究。他大量压缩传记、军事与党派利益的篇幅以腾出地方来论述国教派与非国教派、农业、制造业、商业、出版业、社会状况以及宗主国对其附属国的关系等等多方面的问题。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分八卷于1878至1900年间问世后,立即取得经典著作的地位。在后来的版本里,他把关于爱尔兰的诸章从英国的诸章分开,因而这部书尽可看作由两个独立的部分所组成。英国部分诸卷还不能说是一部论述18世纪的①全部历史。它的叙述虽延止于1793年大战的爆发,但关于乔治三世登位前的时期,则仅仅是个概要。关于辉格党自革命时期以来发展情况的论述不无相当兴味,但作为一部宏大规模的历史来看,这部著作则只涉及到乔治三世最初三十三年的时期。莱基也具有一些加第纳的那种对争执的双方都能正确理解的优点。他对于美国战争的叙述即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典范。正是关于这一部分,阿克顿在写给作者的信中说道,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教训要比好久以来一般书中所提到的完备得多。如果书中有什么主角的话,那么这个主角既不是查塔姆,也不是庇得,而是柏克。阿克顿又说,查塔姆是不少伟人当中江湖气特别浓厚的一位,他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沾染了一种不轻的浮夸习气。而另一方面,柏克与福克斯则为了他们的原则而作出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牺牲。书中最成功的部分首推①斯坦诺普,P.H.英国伯爵,历史家,著有《英国史》两部,第一部为1701—1713年史,共二卷(1872年),第二部为1713—1783年史,共七卷(1858年)。——谭注①指1793年2月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宣战,英、西等国长期的反法战争开始。——谭注\n②那几乎可称之为离题漫谈式的两大章:第一章系关于卫斯理的功绩与宗教思想的情况的论述;第二章为对法国革命起因的分析。但在全部著作中最具创见而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则是有关爱尔兰的部分。在开始编写18世纪历史之前,他曾对他的《公意的领导者》一书进行过改写,删去了其中浮夸词语,但保留了它的民族主义观点。在着手撰作这部大作时,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对爱尔兰历史上的这个重大时期进行一番详尽缕述,主要是由于弗劳德著作的出版所引起的。莱基的妻子写道,“他对弗劳德所鼓吹的那一整套不容忍精神及其资料引用方法,可谓反感已极”。经他在都柏林城堡档案库内进行长期探索之后,他揭①示了格拉坦议会、1798年叛乱与“联合”等的历史真相。这项研究工作他做得十分彻底,以致以后已无需重做。这些著作在价值上可与加第纳关于17世纪斗争的叙述比美,代表着他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关于爱尔兰的诸卷,正像他的英国诸卷那样,也仅仅略述了18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不过在这里可以原谅的地方要稍多些。史实的复杂性随②着义勇军的出现与1782年独立立法机关的建立而日益加大起来。这个议会虽是由新教徒选出的新教立法院,但它却似乎受到某种正常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对天主教多数派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它对英国方面的忠诚也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它的主要代言人格拉坦也许是当时的最高尚的政治人物,因而各卷中对格拉坦的人品、政策与天才始终赞不绝口。1793年所采取的巨大的前进步骤便是把选举权给与天主教徒;斐兹威廉爵士的派遣似乎也是为了预示更多的让步。在关于他的政策及其召回的争执上,莱基毫不踌躇地站在了总督一方;在此后那些恐怖的岁月里,他也毫无保留地谴责了盲目的镇压行为。他争辩说,正是由于政府的严酷与卤莽政策才把群众驱赶到反叛阵营,而合理的让步本可能使他们保持忠诚的。他认为,1798年的叛乱已使“联合”成为无可避免,①但对完成联合所使用的方法,则几乎与格拉坦同样不胜愤慨。他的耐心研究使他终于揭露了这个肮脏事件的全部线索。他不否认克莱尔的能力与卡斯尔雷的手腕,但宣称,爱尔兰的不受收买的整个知识界则是反对②过这项措施的。他的书中多处说明,“联合法”之与普通法的关系正如戒严法之与民法的关系。正当莱基忙于格拉坦国会的研究,“自治法案”的争执在国内爆发。他那半被遗忘的著作《爱尔兰领导者》又被搜索出来当武器用,但他却②卫斯理(Wesley,Johnl703—1791年),传教士,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此派对英国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并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谭注①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于1791年组成“爱尔兰人联合会”。1797年6月该会在洛尔发动起义,次年6月被镇压。1801年英议会通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法案”。——谭注②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后,爱尔兰各地新教徒纷纷组成义勇军。他们愿以武力抵抗法国的入侵,但要求英政府废除损害爱尔兰工商业利益的法令及允许爱尔兰议会独立。1782年,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压力下被迫承认爱尔兰享有独立的立法权。——谭注①英国为了通过“联合法案”,用一百万镑以上的巨资和封赐爵位的办法来收买爱尔兰议会议员。——谭注②“联合法”,1801年1月通过。规定爱尔兰与英国合并,爱议会并入英议会,取消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力,天主教徒仍然没有参政权。——谭注\n毫不踌躇地站在格拉德斯通的反对派方面。他传记中发表过的信件清除③了关于他前后不一致的指责。他曾欢迎过1870年的土地法;他对像他友人加万·达菲与奥尼尔·道特那样的“自治派”也怀着极大的尊敬,④但他对巴涅尔及其一伙则非常厌恶。他对他爱尔兰同胞的能力的强烈不信任态度充分表现在1880年的一封怪信里。“我想你不久即将看到,各方面会产生这样一种强烈舆论即爱尔兰即使对它目前所享有的这点代议制度也是不适应的;那按印度方式组成的政府也许会成为一种必要制①度”。他也不喜欢他自己政党所通过的1898年《地方政府改革法》,曾说他“但愿它不造成巨大灾难就好”。自治法案的冲突使他搞起了政治,并且进入议会。他对未来抱着悲观的看法;在1893年最后的一天,他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道,“这个世界在我看来似乎已经变得非常衰老而又惨淡”。正是在这种悲观主义的影响下,他撰写了《民主与自由》,这是对政治与工业世界里新近趋势的一篇激烈攻击。这部书纯粹是一部充满党派怒火的作品,其中关于爱尔兰的部分牢骚尤大,但是他对爱尔兰历史的说法则迄无改变。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主要用在进一步扩充那部曾于1861年出版并于1871年修订过的著作。书中的格拉坦仍被称为一位在忠实于英国的精神下为其国家的进步而作出崇高努力的政治家。这部书详尽地讨论了斐兹威廉的召回;这是根据罗斯伯里爵士与阿什伯恩爵士在他们的近作庇得传记里所提出的新解而写成的。他承认这个总督在作法上不无失误,但却强调庇得在罢免一位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所信赖与爱戴的长官这事上则犯了一桩无可补救的错误。第二卷专门论述奥康内尔。在委婉地承认自己缺点的同时,他却深信他的诚恳用心与爱国忠悃。实际上莱基对那种尊重财产权利,反对暴动,效忠于英王的民族主义并无异议。试想一位以为格拉坦议会作声辩而大大著称的学者,现在于其生命将终之际,复这位爱尔兰的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撰就一部成熟的甚至多情的传记,这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吧。Ⅲ①虽然西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比起其同时代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更来得狭窄些,这却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兴趣不广。自从他开始出版李维《罗②马史》第一卷的有批评的版以后,他曾以《请观此人》(EcceHomo)作者的身份而声名大噪,另外晚年期间他还写过一部优美的歌德事略。他最早的历史著作是他的《演讲与论文集》,出版于1870年,亦即在他接③该法令规定佃农在他所租佃的土地上享有可以变卖的产权,对被无理驱逐的佃户给予补偿,对购置土地的佃农给予贷款,远未满足佃农的基本要求。——谭注④巴涅尔(ParnellCharlesStewart1846—1891年),自1877年以来为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谭注①此法案的主要精神是将爱尔兰郡议会的权力交与由各郡地主组成的委员会之手。——谭注①参阅普罗特洛的回忆录(载于他的《英国政策的成长》卷首,1895年);坦纳《英国历史评论》,1895年7月号;费希尔的文章见《双周评论》,1896年8月号;阿道尔夫·勒因:《西莱,关于这个历史家的研究》,1912年。——原注②此书的副标题为《综述耶稣的生平与业绩》(ASurveyoftheLifeandWorkofJesusChrist)是一部耶稣传。——谭注\n替金斯利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后一年。他的就职演讲曾专门论述了政治学的讲授问题。为什么须要研究历史呢?那答案是,因为历史是政治家的学校。“我们的大学乃是,而且必须是,一所政治家的巨大培养所。没有至少起码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政治感到合乎理性的兴趣,而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也就不会对政治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这条明显的真理之所以很少为人认识,乃是因为一般人往往误以为历史只讲辽远的过去。他提请青年们注意近代史的研究,因为“下一代的立法者与政治家势将出自他们中间。”也正是在近代史方面产生出他的三部主要历史著作。他的最早也是最大的著作是他的《斯泰因的生活与时代,或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与普鲁士》一书。他的计划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拿破仑的历史,从而说明拿破仑与其敌人之间所争执的原则。普鲁士在耶拿灾难后所完成的建设性改革这一伟大事业,当时尚少为人所知,而斯泰因在英国还仅仅是个空名。书中新的发现不多,因为西莱没有查阅过手稿,但已刊印的资料他都见到了。他的论旨是,德意志的这场改革所引起的深远的影响殊不下于法国,但却不曾带来恐怖。这个变普鲁士为一①个近代国家的问题,大体上系经斯泰因所解决;故西莱依照豪塞的先例,也将他比之为杜阁。虽然英雄崇拜的事不适合于他的严肃性情,而传记式的细节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却毫不讳言地对这位大政治家的勇敢与明智不胜景仰,因为斯泰因的名字已无异其民族独立与内政改革的象征。西莱对拿破仑与世界帝国的思想毕生怀着憎恶心理。他把善与恶的原则——民族性之于世界霸权——的斗争体现于斯泰因与拿破仑的身上。他指责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年,以及在此后的1809与1812年都该打而不打。如果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那年曾参加了俄奥两国作战,结局可能另是一种情形,但在1806年他便陷于孤立了。如果他在1809年与奥联合作战,他本来可能扭转局面。如果他对1812年惨败后的拿破仑进行侧面夹击,完全可以免掉莱比锡与滑铁卢的几场血战。西莱从未怀疑过这个平庸国王的爱国心,但这事的后果却主要应由别人承担。斯泰因之外他特别推崇费希特,他对费希特的那部激发壮志的《告德意志人民书》非常欣赏。西莱的著作在那些曾经引起农奴制的取消与城市自治的建立这一系列划时代的变革方面向英国读者提供了最好的总结。在造成普鲁士复兴的诸种因素当中,沙恩荷尔斯特与格奈塞瑙的陆军改革,柏林大学的创立,尼布尔的高贵性格以及洪堡弟兄的教育工作等等,都起到过相当作用。《斯泰因的生活》并未成为一部非常流行的书,但是它的价值是每一个肯去阅读的人都会看到的。对英国说,这部书主要在于它写出了一位大政治家生平及其英雄时代。这位历史家曾经满有理由地表示过,他的书的篇幅之所以这样浩繁,并非由于文笔的芜漫,而是由于内容丰富,对德国说,书也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是关于这个政治家的第一部合用的传记;过去佩茨所编的斯泰因巨型传在对他的①德国史学家豪塞(Hausser,Ludwig1816—1867)在所著《1786—1815年德国史》中对斯泰因有较详细的论述。——谭注\n①描写上每失之晦涩。所以直至下一世代马克斯·勒曼的专书问世以前,西莱这书始终享有相当地位。如果说这书也有缺点的话,那便是关于拿破仑的描写。他在为《英国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拿破仑传略》中,以及又一次暴露了他不能认识这个人的伟大。这在据此而重新出版的增编中都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人物有何伟大完全不能认识;他的品格与政策只能招他嫌恶。如果说《斯泰因》未曾获得它应得的成功,西莱的第二部著作则带来很大的补偿。《英国的扩张》不仅史学史上而且在政治史上也都占有一席地位,因为书的出版恰值英国对殖民地与帝国等兴趣渐浓的时候。据他讲,我们在一阵尚非充分自觉的情况下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思想上仍然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欧洲北岸之外的一个岛国。这种岛国特点对我们的历史家大有影响,他们过于重视了18世纪的议会纠纷,而未能看到我们的历史已更多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而本土则较少。他有两个讲座内容都谈英国对加拿大与印度的征服问题,清楚地分析了英帝国的形成与对法冲突之间的关系。“自路易十四时起至拿破仑时代为止,这一时期中英国的主要斗争乃是为了占取新世界”。西莱惯以对主要因素投射强烈光照的手法来增加其叙事效果,善于从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孤立的事件中间揭示其内在联系,进而使读者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而达到相同的结论。他爱好全景式的观察、综合性的概括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的一个门生写道,“他讲述一个世纪比讲述十年时期更为擅长。他心智的整个趋向是重大事件启发性的论述而不是显微镜下的细节考查。他的方法是天文学式的。他惯于以望远镜横扫整个天空”。这部书的主题非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独出心裁,但他却是第一个说明这个主题的人。虽然《英国的扩张》成了英帝国主义者们的《圣经》,此书的精神却决非对帝国本身或帝国所由建成的方法的过度狂热。虽然他也强调了这个趋势的重要性,但究竟这事值得高兴还是只能引起遗憾,他却留下未说。“巨大不等于伟大。如果我们在规模上的不过保持第二位而在道德与智慧上却能够跃居首位,那就让我们宁可牺牲单纯物质上的规模数量吧。”他对白人的殖民地与对印度是显然有所区别的;认为对印度的占有增加了我们的负担而不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他并不认为帝国版图的庞大足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或者它的异乎寻常的统治天才。此书所引起的是思考而不是得意,它所强调的也是我们继承下来的负担的沉重而不是它的光荣。正像马汉的《历史上的制海权》与奥利弗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书那样,西莱的书并不仅是科学探讨,而更主要是政治理论。西莱一生的最后十年主要用于研究英国的外交政策。正如对他教益最大的兰克那样,他也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国与国之间的生活与关系。他自己的著作一向主要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他也特别喜欢演述威廉与马尔巴罗时代的英国外交。他为此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擅长于摄取其中精华。他最初计划即从1688年开始叙起,但后来感到非常需要某些导入的部分,遂把书的起点一步步向上倒推。最后,他从伊丽莎①勒曼所著为《斯泰因男爵传》(FreiherrvonStein)共三卷1902—1905年。——谭注\n白登位讲起;但由于死亡提前到来,仅仅叙述了威廉三世时代。这些残稿构成两卷小书,于其死后出版。他的《英国政策的成长》追述了一个强国的形成以及大陆上宗教与王朝的斗争对这个岛国的国策所起的影响。他写道,“英国人的眼睛总是过多地盯在议会上面;英国的历史一向颇有简化为单纯议会史的倾向,因而几乎所有的英国史学大家在论述外交关系上都往往不能达到他们自己的应有水平。”他的志愿是要在英国产生一种相当于德国特洛伊曾的作品,但他自称他的书仅是一部论文而非一部历史。在台前受人注意的为伊丽莎白、克伦威尔与威廉三世等人,这些人曾使英国能在后来18世纪一开始就屹立于欧洲列强之林。这部书丝毫没有炫耀博学的痕迹。书中绝少引证,一切详情细节统统退居背后。但这部书在流畅与透辟上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是其它书籍所远远不及的。他那驾驭事实的本领是出众的,尤其成功的地方是他能使读者充分感到欧洲在外交上的统一性。这部书的开篇部分系关于哈布斯堡族成长历史的研究,其中一些章节中英国几乎很少提及,但不需多久各条线索复又交织合拢起来。他认为,一国命运之有赖其世界地位的程度往往甚于其制度本身。弗思婉惜地说,书中一些思想虽颇大胆新颖,但事实有时却有牵强之处。概括乃是一个危险的方法;西莱有时把事件结果过多地追溯到外交因素上去了。西莱著述的数量虽然稀少,但却质量颇高。他的作品在问世之前往往经过反复推敲;他最痛恨懒惰的思考、草率的句法与粗糙的研究。他非常藐视那些卖弄词藻的作家,他曾因为指斥卡莱尔与麦考莱为走江湖的而触怒了少壮派乔治·屈维廉。史实正像一位律师办案那样,总是务使其种种理由最后汇集于一点。他的结论往往被强有力地铁锤般敲打入人们心中,使人无从误解或遗忘。虽然他故意把过去生活中的广阔地带排除于历史家的视野之外,但没有曾经这样热心地宣传过历史在指导与影响现实上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历史既具有意义也富于教训,而历史家的主要职务则在于去发现这些意义与教训。正是这种与当前问题的直接联系才使《英国的扩张》赢得其非凡的成功。在历史荣誉考试制建立后,他曾提出将政治学列为其中主要科目。他的朋友普罗思罗在他死后写道,“在他看来,历史细节除了作为概括的依据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在论述历史时,他一向抱着一个确定的目的——解决某个问题,确定某项原则,以便引起研究家的注意,或对政治家有所裨益。不带有概括的论述对他是没有什么兴味的”。他自己也说,政治如果没有历史来开拓其境界便难免流于庸俗,而历史如果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流于单纯的词章文学。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实际教益并筹建一门政治科学。他还在自己家中特设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班。这的确是一种殊可敬佩的志行。但是这种旨在教诲的历史,尽管其立意非常符合科学和非常富于启发性,却也有其严重弊害。再有,他在强调研究近世历史的卓越作用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今天不仅是昨天的结果,而且是过去无数世代的产物。Ⅳ\n①克莱顿正象西莱那样,最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外交技术与会议室内的秘密。两人都惯以兰克式的冷静与超脱态度来从事其工作,两人也都重视行动胜过于思想。他的试笔习作阶段是在牛津度过的,在那里他讲演过中世纪史与近代史,并编写过关于罗马、西蒙·得·蒙福特与伊丽莎白时代的通俗读物。这些初级作品的成功使他在接受诺森伯兰郡恩布勒得学院牧师职后,开始从事其较重大的著作。他热爱意大利,曾编写过关于伊尼阿·锡尔维以及其它意大利题材的论著。1877年他对一位友人说,他正在忙于一件他准备作为其毕生事业的工作,即编写一部从教会大分裂起迄特棱特宗教会议时止的教廷史。“我的书将不是论战性或宗教性的。其目的为论述当时较重大的政治问题,内容包括意大利的历史及其艺术文学,并进而对全欧的历史加以综述。它将填补密尔曼的书与兰克的《教皇史》之间的一段空隙;前一项著作在接近结束处是太杂乱无章了。我的目的乃是要将前者的描绘技巧与后者的博大政治观点融合为一”。他以高度的积极态度研究了教廷史。他写道,“一般新教对宗教改革的事实真相往往歪曲过度,以现在罗马天主教用以令人改宗的一个最好方法便是向那些肯于聆听的人们证明他们对于历史上某些事实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没有整套理论,没有什么历史哲学,也没有想要证明或驳倒什么的愿望。他的志愿不过是聚集资料,以便绘出宗教改革之前与宗教改革时代的整个图景。从来的宗教史是很少以这样一种精神来研究的;这部著作确实现了其作的“有光无热”的理想。①《教廷史》开首两卷于1882年出版,内容叙述至15世纪中期。书中表现的广博学识与公平态度得到承认,并为他赢得了剑桥大学宗教史教授的职位。他的邻人与意大利史的同好霍奇金在回顾他与克莱顿在其编写这著作过程中的交往时证明说,克莱顿曾举出过历史书籍编写所应遵守的原则。克莱顿曾说,“我一向喜欢紧密依据我的资料;而他的著作也表明了他曾怎样严格履行了他的职责。书中有关资料的讨论属于该书极有价值的部分。的确,这部著作甚至可说因为在材料处理上的过趋谨严而受到影响。这个时期的种种阴谋,教皇与伪教皇斗争的过程等等,在书中都得到了详尽的叙述。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的胡斯运动与宗教会议在改革教会上的一番壮举等等的描写,这部书很有可能是沉闷乏味的,甚至会象书的作者半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是十分沉闷乏味的。至于这许多教皇,其中除尼古拉五世与庇护二世外,几乎都非常缺乏个性。但这事并不怨他。他说过,“当事情本身就乏趣时,你也只有跟着乏趣。”但是这部著作却在国内外的学者中间赢得了颇大声誉。尤其使他满意的是,他的这种公平美德竟也获得了罗马方面的承认。阿克顿这位在他看来唯一能够评断其书的人,也称誉他的这种公允态度,但却认为他对宗教会议运动的评价未免偏高,另外指出他对思想的发展注意不足。其实克莱顿倒更希望从自己一方多听到些不同意见,因为他的原意便在于“廓清新教徒们在对待其所谓福音主义精神的成长上的精神误解。”①参阅其妻所编著的《曼德尔·克莱顿的生平与通讯》第2卷,1904年;理查·加尼特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1901年4月号;戈斯《画像与札记》,1912年。——原注①全名《教廷史:从教会大分裂到洗劫罗马》(HistoryofthePapacyfromtheGreatSchismtotheSackofRome),共五卷,1882—94年。——谭注\n他的最值得一提的成绩是在第三、四卷中关于文艺复兴早期诸教皇的论述。他爱好写绚烂色彩与杰出人物,这使他给这个意大利教皇时代罩上了一层特殊迷人的色彩。书中关于学术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毫无保留的赞美,但在有关那些曾使教廷成为巨大的世俗权力的教皇们的论述方面则遭受了严峻的批评。要知道,想让他去满口仁义道德,痛心疾首般地向着那些头戴冕旒的罪人去历数其罪状,这他是干不来的。他写道,“我现在正忙着写波尔查家族,这滋味,活像天天呆在一个地方警察局中办事那样很不好过。但我的任务并不在表明教皇们在罗马怎样过活,①而在要表明他们怎样影响了欧洲”。他不想多写洛德里戈·波尔查在道德上的重大劣迹,而尽量给他凑上几条一般优点。他在出书之前还写道,“亚历山大身上的种种弥天大罪乃是出于一般人想为16世纪时意大利的衰败寻找一只替罪羊的心理。他是有不少罪孽的,但还罪不至此。”他之所以蒙受特殊恶名,主要倒是因为他还没有再犯伪善这条。克莱顿指出道,“许多好人并不一定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好,而坏人也未必便像一些好人所认为的那样邪恶,”对人的要求从来不应过苛。但这新出的两卷则使得阿克顿颇形愤怒。“他往往不是力图去证明一个案情或去探求什么结论,而只是冷眼旁观地驰骋于种种是非激战之①场,既不判断,也不决定,徒然戴着一双白手套而已。”在这位严肃的天主教道德家看来,教廷的堕落乃是一出可耻的悲剧。“历史科学的任务,正在坚持以道德作为衡量人和事的唯一公正准则,同时也是一切真诚人士所能同意的唯一准则”。他的第二个批评意见稍有普遍意义。阿克顿认为这种以生活与行动来代替思想与法律的作法“减轻了他自己的负担”。这不过是一句委婉责备,暗示他的论述是表面的因而是肤浅的。克莱顿重场面而不重问题,重叙述而不重思考。这个重要批评意见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一次有意义的信件往来,其间阿克顿更着重申述了他的看法。“我不能接受你所提出的那个准则,即我们对教皇与国王的批判须不同于其它人们亦即先从一个偏袒的假设出发,认为他们不可能有错。如果真要有任何假设的话,那倒恰恰相反,那是不利于掌权者的,而且其权力愈高,这种不利也就愈大。”克莱顿对此的答复是他不赞成把历史变成伦理科学的一个部门。那些视异端为罪恶的人可以指责为思想上的错误,但未必便是道德上的罪行。“历史给我所提供的英雄不多,所记载的善行亦少;但历史上的这些扮演者也正像我这样的人一样,都不过是权力之欲的受惑者。余也何人,敢妄訾前哲?其实,他们也不过罪在不知而已。”阿克顿所指责的这些特点,在他著作的最后一卷。(亦即从利奥十①世登位至罗马城遭劫掠为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突出。><由于他的宁静性格很适于处理纷争繁杂的时期,但他的思想却太偏于入世类型,因而往往未能很好把握宗教改革时的问题。如果引用理查·加尼特的妙语来说便是,“他对15世纪学术的爱好往往胜于16世纪神学。对他来说,①洛德里戈·波尔查(RodrigoBorgia,1431—150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2年登位。——译者①按英国惯例,当巡回法院没有犯人时,执行吏即以一双白手套捧送法官,以示无讼。这来源于英国古代审判时不准戴手套这一习惯,故以手套交给法官即表示他无需开庭。——译者①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1527—1529年,皇帝查理五世军队掠夺罗马。——谭注\n意大利人胜于德意志人,政治家胜于战士,学者胜于先知”。这书开首②的两章,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与刘希林争论,也都是以他对文化的那种宿有的热忱著成的。正如人们天生便有柏拉图派与亚理斯多德派之别,因而他们也就天生有的爱好路德有的爱好伊拉斯姆。克莱顿是站在伊拉斯姆一边的。这部书中虽也不乏某些精采段落,但对他的声誉却未见有多大提高。对于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他没有认真作出什么说明。无论关于对罗马教廷的不满,对教会世俗化的愤怒还是关于道德家、布道者与讽刺家所提出的抗议,他却谈得很少。一场巨大变革在15世纪时即将发生本已是一件明显事实,但这次改革的来临在他的书中却仿佛突如其来。他开始这段叙述所用的字眼也是怪的;“路德所发动的宗教叛乱象晴天霹雳一样突然降临”。他摈弃了新教徒的那种认为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传统观念,而认为宗教改革以分裂教会统一的作法出之,殊为基督教国之莫大不幸。不过他也宣称,路德所提出的诸种要求亦均在教会可予应允之列。“对于迫使路德走上反叛一事,教廷实应负其责任。”书中的这位改革家确实显得异常平淡无奇。在天主教徒看来,他不过是个大胆的坏人,在新教徒看来,是个大胆的好人,而在克莱顿看来,是一个不觉走上而非被迫走上叛乱的人。路德是克莱顿书中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大人物,而他也未能充分认识路德的伟大。他也部分地觉察到自己这个问题。他在写给查理·利的信中说,“我所写的路德部分我自己也不满意。科尔德是赞赏它的,但认为对路德必须从宗教方面来进行理解,而我自己却主要是以政治方面来论述他的”。这个德国学者的批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克莱顿称,他尽量采取当代政治家的目光来观察问题;他关于沃尔西的专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是他最感熟悉的世俗世界。他对群众的生活与思想以及宗教改革家的火热信仰都是缺乏洞察力的。不过《教廷史》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仍不失为一部名著。虽然书中并无新的发现——因为克莱顿未曾探索过档案这个朦胧世界——但对已刊出的资料则能做到巧为利用。他的公正是显著的,文笔也清楚而饶有趣味。在论述那些他能深感同情的人物与运动时,无论在描写上在解释上他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书的缺点主要在于对宗教生活中的重大经验相对说来往往漠不关心。1891年他的第五卷大部分行将告成之际,他受到了主教职的任命,而这项任命对他的历史著述确实是个致命损失,正象斯塔布斯的情形那样。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为《剑桥近代史》的首卷所撰写的简要导论,文中他把文艺复兴视作近代史的开端。②刘希林(Reuchlin,Johnn;1455—1522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曾提倡过希腊文的近代读音法(即刘希林读音法);关于犹太圣经问题他曾与科伦的多米尼克派发生过激烈争论(1510—1516年间)。——译者\n第十九章阿克顿与梅特兰Ⅰ①阿克顿的家世使他自出生之日起即投入到本国以外的环境里:他的祖先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曾任过那不勒斯王国的首相,并属于德意志的达尔堡旧族;而这个环境又因他母亲与格兰维尔爵士的结婚而更形扩大。因为未能进入剑桥大学,他转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曾在窦林格尔家住过六年之久;德林格尔为天主教学术界的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对于阿克顿的一生中起过最有力的影响。嗣后阿克顿以非常的毅力投身于教会②史的研究,凡是见过他的人深为他那过人的渊博知识所折服。离开慕尼黑后,他到柏林聆听过兰克与博赫的演讲,并去美国作长途旅行,他还伴随其继父参加过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由于痛感当时德国思想界的生动活跃与他本国天主教会的思想僵化,他下定决心要把近代学术研究的酵母输进英国。在杰出的改宗者辛①普森,亦即坎皮恩传记的作者的帮助下,他曾利用《漫游者》月刊来论②述欧洲的思想运动和讨论历史、政治与哲学方面的问题。自童年时起,他已广泛涉猎过多种文字著作,摘录其重要段落并将摘要排列在箱笈抽屉之内。二十三岁时他开始建立他那宏大的藏书楼;这是他生平第一得③意的事,后来这些藏书转予了剑桥图书馆。他的工作的确是一番辛苦挣扎。因为按他的主张,最重要的并非仅是学问本身,而是在于揭示真理的神圣性,信仰的权利,以及政治与宗教绝对主义的罪行。他非常渴望能获得纽曼的支持,但这位最伟大的英国天主教士对于《漫游者》月刊④⑤言论过激的讨厌程度并不亚于对曼宁与华德的蒙昧主义。在回答一封①他的著作汇编,附有以前未曾刊印过的通讯,将由贺力斯与卡脱整理出版。参阅赫伯特·保罗的回忆录,刊于《阿克顿给曼丽·格拉德斯通讯》前面,1904年;《自由的历史及其它》(1907年)的导论(菲吉斯与劳伦斯作);《爱丁堡评论》,1903年4月号;普尔《英国历史评论》,1902年10月;布赖斯《现代传记研究》,1903年;《传记年鉴》(1905年)中布伦纳哈塞特女士所作部分;《英国名人词典》中菲吉斯所作部分;赫伯特·费希尔《阿克顿的历史著作》,《每季评论》,1911年7月;格兰特·达夫《略谈过去》,卷Ⅱ,1903年;拉利《阿克顿语录》,1942年;大主教马修《阿克顿的成长时代》,1946年;格特鲁德·希米尔法布《阿克顿关于自由与权力的论文》的导论(波斯顿,1948年);巴特菲尔德《阿克顿爵士》(历史学会从书),1948年。关于他思想的详尽分析,见乌尔里克·诺亚克的3卷集:《历史科学与真理》,《天主教活动与自由精神》及《自由的政治保证》,1935—1947年,以及法斯纳克特,《阿克顿的政治哲学》。——原注②参阅伯恩哈特·冯·迈尔《经验谈》(Erlebnisse),卷Ⅰ,第12章,1875年。“每逢我回忆起与这位青年的一番交往,总是不胜欣悦,因为彼时他早已广有学识,邃密德国学术”。——原注①坎皮恩(Campion,Edmund1540—1581年),牛津大学出身,知识渊深,曾任修词学教授。1573年加入耶稣会,1581年以谋叛罪被绞死,为英国第一个以身殉道的耶稣会教士。——谭注②参阅加斯奎《阿克顿爵士及其交游》的导论,1906年;《加斯奎与阿克顿-辛普森通讯》,见《剑桥历史杂志》,1950年;威尔弗里德·华德关于华德(W.G.Ward)与纽曼的传记。——原注③参阅特德,《书籍收藏家阿克顿爵士》,英国科学院议事录,卷Ⅰ。——原注④曼宁(Manning,H.E.1808—1892年),神学家,初为新教徒,1851年,皈依天主教,极力宣扬教皇绝\n批评有关庇护五世的论述的信里,阿克顿的语调是忧郁的。“关于科学的权威性与真理圣洁性,一般舆论从来很少单纯为此而予以承认的。我们的目的在于鼓励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无私的真理爱好。但可惜这项原则在一般天主教刊物中均未见认真采纳”。在这个月刊被禁出后,他创办了《国内外评论》季刊来进行这种活动。这位新的编辑在第一期出版时写信给纽曼说,“只有一件事你也许不会喜欢听,这即是保罗三世曾有过一个儿子,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一个侄子。我深深感到,这事必须公之于众,因而我不得不指出这中间包含着有意的说谎。”及至1864年时他的上级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最后他只有屈从于权力,停出《评论》。阿克顿在这六年期间〔1858—1864年〕所写的东西不论在数量与范①围上都是颇为可观的。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在他死后曾进行重印。除关②于詹姆士·得·拉克洛什的研究与对巴克尔的一篇抨击文章外,这些论文大都直接间接与天主教会及其反对者们有关。在最早的一篇论文《对于教会的政治考虑》里,他叹息宗教动机已为政治见解所替代,认为这种情况导源于新教国家之僭窃教会的职能。罗马教廷在保守派眼中被认作是一种政治危险,在自由党人方面则认作是自由的敌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宗教体系在任何其它领域之内,正象在教义的领域之内那样,作好斗争准备。”中世纪时代乃是一个“我们为人类以后所享受到的一切幸福与所完成了的一切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基督教的信仰观念,需要一个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而教会不能容忍任何不承认这项自由的政府。教会乃是国家专制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因而教会便是自由与信仰的保护人。绝对专制的君主制曾是教会的最大敌人,但理性主义的民主制也是一个同样的危险。宗教改革曾是“近代的大规模背教运动”,对它清算的日子终要到来,正如过去对于异教曾经到来过那样。但是英国“在它背教的运动中尽管对宗教犯过偌大过错”,它在政治制度内所曾保存的天主教精神却比在任何其它国家的情形要好得多。阿克顿对意大利1860年后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颇为忿慨,曾写过一篇论述加富尔之死的辛辣文章,认为他所寻求的乃是国家的伟大而非人民的自由。加富尔1859年对奥国的进攻被称为是一桩不可宽恕的事件,他①与教会的敌对态度则是一场灾难。“皮埃蒙特法律与政府同教会自由的不可调和性,乃是足以引起教会世俗权的丧失的一个真正危险”。几个月后他在评论窦林格尔的新书《教会与诸种教会》时,复以教会世俗权为主题著过一篇长文。正象他的老师那样,他宣称新教是注定要灭亡的,“是一个无组织的教会,其教义已处于解体之中,其牧师对之已感绝望,对权威立说。——谭注⑤华德(Ward,M.G.1812—1882年),牛津大学出身,在母校任教。1844年发表《基督教会的理想》一文触怒国教当局,被剥夺学位与教职,改奉天主教。——谭注①参阅A.W.肖为王家历史学会所编的传记集,1903年,以及拉利与希米尔法布的著作。——原注②詹姆士,得·拉克洛什(1647—1669年),政治骗子,自称英国查理二世的私生子,未获承认,后皈依耶稣会。——谭注①加富尔任皮埃蒙特王国首相时,颁布法令取消天主教会特权,解散修道院,重新分配神职人员收入,被教皇逐出教门。——谭注\n而只是在它与罗马教廷敌对时才是团结有力的”。首主教的职权于基督的教会乃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样的职权,这副机体势将分裂为无数你争我夺的小单位。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反对信仰自由的剧烈行动,因为否定教皇必将直接导致君权神授的作法,这正是路德所制造出来的。教皇国的政府诚然是需要改革的,但那里却既没有专制主义也没有精神腐败。在题为《新教徒的迫害理论》一篇精采的论文中,他进一步把战斗勇猛地推进到敌对营垒之内。他重复道,新教业已将那尚能对国家万能加以节制的唯一权威扫除尽净。宗教改革者在这样一个宗教统一性已经消逝的时代里,依旧传播和实行以死刑来惩罚宗教错误实已丧失其任何借口。但阿克顿对天主教所施行过的迫害却没有说过一句谴责的话;在评论戈尔德温·史密斯的《爱尔兰史》一篇论文中,他曾对人们说罗马教廷是迫害者的这个指责进行过辩解。他认为,中世纪的迫害是有其理由的,因为当时的种种教派尽是一些革命党派,天主教对于那些并不属①于其教会的人是从未迫害过的。在评论黑费勒的《希梅内斯传》一篇长文章里,他抨击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压制了宗教思想并支持了绝对专制政治,但却说这对消除罪恶颇曾有益。尽管《漫游者》月刊具有着战斗的天主教精神,怀斯曼还是公开抨击过它,指出它“在对待一些一般心目中认为神圣的人或事上缺乏审慎与恭谨的态度,往往逼近错误深渊的最危险的边缘,另外它一向所爱好的种种天性、倾向与动机恰恰是非天主教的而非天主教的。”阿克顿在他的新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火气旺盛的答复,辩护了自己的忠诚与独立性。“近代社会迄未提供过自由的保证,进步的工具,以及达到真理的手段;而对于真理我们却抱着漠视或怀疑的态度。”这篇辩护没有能够与他的批评者们达成和解,因而他的名文《与罗马的冲突》便是《国内外评论》宣布其停刊的搁笔之作。“目前并不缺乏那种脱离宗教而谈科学或脱离科学而谈宗教的刊物。《评论》曾经试图结合二者于一道。刊物所标举的原则将不致随其停刊而消逝,正相反,它将于适当的时期重新获得其必然的辩护者与胜利”。但纽曼的信件则认为,这次引起不满的却主要由于辛普森而非阿克顿,但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个人主义者,在一个强调神圣权力的教会里,其处境必然是艰难的。诚然罗马教廷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在英国得到过这样一位辩护士,但是英国的领袖们对于以德林格尔及其门生为代表的德国学术的怀疑却愈益滋长。纽曼、曼宁与华德早已离开他们曾受洗礼的教会,因为它向“自由主义”投降;他们不愿让恶魔进入他们所皈依的教会。1869年当安布罗斯·圣约翰朝见庇护九世时,教皇对他谈起过①那些本质上并非天主教的人们,阿克顿即属于此种类型。这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还为一个叫做《时报》的周刊撰写社论;周刊创立于1867年,但只存在了一年时期。之后,他又按照自由派天主教的方针帮助改组了《北英评论》。在这里刊出了他关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长篇论文;文章反驳了那种为教会开脱责任的企图。“当我们看到真实性乃是能够赋予历史以尊严与价值的唯一美德时,这类东西将不复为人编写了。”这位①希梅内斯(1436—1517年)西班牙人,红衣大主教,1506,1517年两任摄政,痛恨异端,曾处决异教徒数千人。——谭注①华德,《纽曼传》,卷Ⅱ,页167。——原注\n辩护家正在发展为历史家。②当梵蒂冈宗教会议来临时,阿克顿曾与他的老师一起阻挠过它的实现,因为他觉得这事对自由与教会都将极为不利。他将全部报告自罗马③寄给德林格尔;《奎利那信件》便是大部分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的。反对会议的召开失败后,他在《北英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给一位德国主教公开信》以及另一篇文章。信中阿克顿将其中少数派在早期阶段的豪言壮语与他们在紧要关头的缄默无言作了对照,宣称,为了对其自身的名誉负责,他们必须抵抗到底。而在那篇文章中他详述了宗教会议的起源、问题与过程,指出如若不是因为教皇受了耶稣会的控制,它原可成为讨论改革的会议。但是不论诉诸启示还是诉诸传统,诉诸理性还是诉诸信仰,结果概未生效。近年来,几乎每个真正为天主教服务的作家迟早总要蒙受耻辱或遭到怀疑。罗马教已在天主教中占了优势。会上教皇无谬论的突然提出便是一个阴谋。阿克顿关于一个容忍而有学术性的天主教的理想的最后失败,使他的余生一直笼罩了一层阴影。他所梦想的教会截然不同于庇护九世与曼宁的教皇全权论,正如哈纳克的新教主义之不①②同于斯珀吉翁的“基要主义”。他与德林格尔一样,拒绝参加“老天③主教会”,但他仍受到这胜利派的怀疑;曼宁便不止一次地请求他说明其立场。他感到他将被驱逐出教,并对格拉德斯通说过,现在所剩下的④问题只不过是这打击什么时候到来。不过他并未受到烦扰,因而终身保持了一个虔信天主教徒的身份。使他感到宽慰的是,他后来发现1870年会议所要求过并得到过承认的那个极大权力,在他有生之年尚从未被使用过,但他对教皇全权论精神的厌恶心理则迄无改变。赫柏特·保罗曾把他比诸萨毕;但如其说他在对教廷的关心上不如萨毕,他对宗教的兴趣则要比这位伟大的威尼斯人浓厚得多。阿克顿代表其教会所作的最后①发言是他1874年写给《泰晤士报》的一系列信件,内容系答复葛拉斯吞对“梵蒂冈主义”的攻击。在反驳关于天主教徒既效忠于一个外国统治者便不可能再效忠于自己国家这个论点时,他提出,尽管教皇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其有国君废黜权,英国天主教徒却从未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②梵蒂冈宗教会议是在1869—1870年间召开的。1870年7月梵蒂冈会议重申“教皇无谬论”并宣布关于信仰和伦理的决定,企图将教权置于政权之上,将信仰与伦理扩大到政治领域。——谭注③1870年8月,德国一些天主教神学家、教授在纽伦堡集会,对当年7月梵蒂冈会议所颁布之教皇敕令,提出异议。次年3月,德林格尔发表《奎利那信件》(LettersofQuirinus),被逐出教会。奎利那为罗马七丘之一,借以指罗马。——谭注①斯珀吉翁(Spurgeon,CharlesHaddon,1834—1892年)——英国浸礼会派教士,一个坚定的喀尔文派,不相信近代的圣经批判,反对因受浸礼而可得到复活的说法,曾每周出版他的布道讲演(后集成五十卷)。──译者②原文为Fundamentalism。──译者③“老天主教派”(OldCatholics)──指反对1870年梵蒂冈会议宣布的“教皇无谬论”的天主教徒。他们的目标不是根本改革教会,而是恢复古代天主教制度,因而获得此名。这一派以德国为基地,法、奥、意、瑞士等国都有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译者④曼宁曾称他为格拉德斯通的邪恶的守护神;(阿克顿与格拉德斯通私交甚笃,在宗教问题上意见又常相左,故云。)参阅珀塞尔《曼宁》,卷Ⅱ,第434—435,490—491页,1895年。——原注①重刊于《阿克顿爵士的通讯》,卷Ⅰ,第119—144页,1917年。——原注\n会进行叛乱行为。在他的后期著作里信条主义(Confessionalism)已完全不见了。阿克顿在早年时期便曾计划完全根据原始资料来编写一部《自由的历史》。1877年时他作过两次讲演,足以说明他自己思想的倾向。讲演一开头便说,“宗教而外,自由一向是善良行为的动机与罪恶坏事的通常借口。”他所理解的自由是,保证任何人得以进行其自认为在责任上应做之事,而不受权威、多数、风俗与舆论的压力。“我们据以测验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标尺便是看其中少数派所享有的安全程度的多寡如何”。据此则希腊与罗马的自由很少,因为那里个人完全要听命于国家。基督的格言,“把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正是对绝对专制主义的否定与自由的开端。在中世纪时代,正是由于教会的抵抗,欧洲才没有堕入拜占庭式专制主义。从世俗与宗教权力的冲突里兴起了公民自由,因为政教双方都不得不逐渐承认了人民的主权。如果说古代的政治是以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绝对国家为结局,那么中世纪时代则是政治权力受到了代议制与教会的限制。但这个过程遭到了马基雅弗里与宗教改革家们的阻挠;他们恢复了绝对专制的理论。但英美两国对自由进行了拯救。一年之后他在评论厄斯金·梅的《欧洲的民主》这篇杰出的文章中所讲的也基本上是这个问题。“古代民主政治即使在其黄金时代,也只是部分与虚假地解决了人民政府的问题。”基督教输入了一些民主思想,但却未见施行。民主政治的复兴,既非由于基督教教会,也不是由于条顿国家,而是来自它们之间的冲突。在强调指出路德拥护消极服从的原则后,他宣称,利尔伯恩是懂得真正民主条件最早的一个。民主政治在欧洲的胜利及其影响却是有赖于美国。“在那里,民主政治在严防其软弱与过度的情况下,达到了它最完善的境界。”他指责法国大革命给民主政治注入了不可和解的仇恨宗教心理,并认为,它的平等理论恰是自由的大害。文章的结尾部分讨论了联邦制、比例代表制以及其它关于自由的保证问题。历史的教训便是,自由的唯一希望即在权限的分散。但《自由的历史》却始终没有写成,甚至没有正式开始,因为这项工作在他看来是人的力量所达不到的。1869年格里哥罗维在他的日记簿里写道,“阿克顿正在使全世界到处供给他资料,但我担心他非被这汗①牛充栋的材料淹没不可。”阿克顿说德林格尔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总是不愿意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来进行写作,而对于他,资料却总是不完全的。”德林格尔也说过,如果阿克顿在四十岁前写不出一部巨著,那他也就永远写不出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布赖斯在他的一段相当出名的话里说道,“二十年前的一个深夜,他在他自己戛纳的书房里,曾向我说明过关于这样一部自由的历史应该怎样编法,甚至怎样使之成为全部历史的中心线索的意见。他不过谈了六七分钟,但那谈话却是像一个受了灵感的人的谈话;他仿佛是从高空的某个山巅之上望尽了①脚下人类进步的辽远曲折的道路,从史前混沌的息米立亚人岸边的朦胧阴影一直到光焰较强但仍然闪烁不定的近代。他那滔滔的雄辩是壮丽①《罗马日记》,页340,1910年。——原注①息米立亚人(Cimmerians)——据说为太古时代住于黑暗中的怪民族。——译者\n的,但比这雄辩更为奇伟的则是他那洞悉一切的惊人想象;它通过一切事件并且就在一切时代之中窥见了那些道德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时成时毁,但却始终不停地转化;它们曾经形成并一再形成着人类的制度,并曾经将其瞬息万变的能量转化形式赋予了人类的精神。这情形恰似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在一道阳光的照射之下而骤然闪烁起来。我从未曾从其它别人的口中听到过这样的精采议论,甚至从他自己的口中也再没听到过”。②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对写作的新刺激。阿克顿久已愿望能有一种类似聚贝尔与摩诺所创立的那种大型刊物,因而表示支持这个新杂志。他所写过的一篇最精采的文章《德国历史学派》即在《评论》的创刊号上登出;这篇文字受到了它的第一个主编克莱顿的热烈欢迎,认为这种文章足以使杂志的声誉在全欧洲确立起来。他提出了那些潜伏于那个世纪历史研究底层的种种观念,把历史研究与全欧洲的政治、宗教与经济思想运动结合在一起。文章中所表现的学识、见解以及那意味深长的笔调等等也都同样非常突出。其次是他论述德林格尔的一篇长文,为纪念他那位九十余岁老师的逝世所作。文中提到“他曾比以前学者更大规模地使用归纳法以此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他为基塞布勒希特所写的悼词,文虽不长,却很好地表出了这位历史家的性格与成就。阿克顿所写的书评也和他自己的论文同样出色。他为利的《宗教裁判所史》与布赖斯的《美国共和制》所撰的书评与这些书中所论及的那些经典作品多能相称。他对下列一些稍次要著作的书评——例如弗林特《法国的历史哲学》,克莱顿有关教皇的著作,布罗格利关于马比荣的研究,莫尔斯·斯提芬斯《法国革命史》,西利的《拿破仑》与布赖脱的《维多利亚时代》等等,——其中处处不乏识断,因而使其评论颇具经久意义。他的笔调也愈来愈变得警辟含蓄,读后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是从一个在学识上高于当时其他人水准之上进行写作的。他的稿件构成了《评论》最初十年期间最突出的特征。在《十九世纪》杂志里,①他还评论了关于乔治·埃利奥特和霍顿爵士的传记和赞扬过塔莱朗与托克维尔所写的回忆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柏德出版《君主论》所作的长篇导论,文中他追述了马基雅弗里的理论在各世纪里被有意无意采用的情况,并遗憾地认为,马基雅弗里并非一个业已消逝的形象而是一个长在的与现实的势力。他于1895年在西利死后,受聘担任为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一事曾引①起过人们非常的注意。虽然一般人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大名,而他也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但在近四十年来他早已是学术界的一位显赫人物;曾在本世纪中最大宗教冲突里起主要作用;他与政治家们的熟悉程度丝②参阅克莱顿的《传记》,卷Ⅰ,第11章,1904年。——原注①乔治·埃利奥特(GeorgeEliot,1717—1790年),苏格兰人,将军。1775年任直布罗陀总督,抵御西班牙对该城的围困达三年之久(1779—1782年)。霍顿爵士名米尔恩斯(MilnesR.M.1809—1885年),英国政治家、诗人,初为保守党人,后改入自由党,在反对谷物法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爱好文艺热心扶植作家和出版事业。——谭注①参阅波洛克,《阿克顿爵士在剑桥》,《独立评论》,1904年10月与《近代史讲义》导论(菲吉斯与劳伦斯作),1906年。——原注\n毫不下于欧洲学者。而且他也确是当时英国人中间最有学问的人。他作为半个德国人,受过一些德国教育给剑桥大学带进了国际的气氛。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教授不能不是一件奇事,但这个选任却是大有道理的。剑桥大学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教师能够这么善于启发其学生进行研究与思考,或者这么愿意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兴趣。他在就职演讲中的一②些提法乃是这两座著名学校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开首的几段讲话里,他捣毁了他的前任曾用来束缚他自己并企图束缚其学生的枷锁。“政治与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并非是等同的。我们的领域则超出于政治事务的范围。我们的任务在于注视并指挥思想的运动,而这些思想乃是政治事件的原因而并非它们的结果。”人类所关心的事务,首推宗教,其次便是自由,而二者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从历史的范围与内容转到那应该支配历史研究的精神时,他强调指出了道德法典的圣洁性。“我劝告你们永远不要使道德的通货贬值,而要以那支配你们生活的终极准则来审察别人;另外不容任何人与任何事逃脱那个永存的处罚,这即是,历史有权对作恶行为所施加的处罚。”“如果说我们由于把握不定而必然常常出错,那么,我们有时宁可失之过严而不可失之过宽。”“如果我们降低历史上的道德标准,我们在教会与国家中将愈加不能维持这个标准。”有人担心他会掩护他的教会,但当人们看到他对宗教在教导人们为善这件事上失职时所宣布的异常严厉的判决的情形,这种疑惧也就涣然冰释。他在写给克莱顿的信中说,“在判断人物与事件时,①道德应走在教条政治与民族的前面”。他躬行了他所宣示的主张;他在其王家教授的身份上,从来未曾写过或说过一句表示其教会派属的话。阿克顿在那里讲授过两门课程,其讲义曾于他死后出版。那部近代史课讲义概述了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前夕的一段历史。这门课原是为普通大学生讲的,因而内容当然包括了许多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但我们觉得他的性格还是反映在书中不少严肃的论断上面,另外在许多地方也都不乏新解。虽然这部书主要叙述的是事件而非思想,但它的主要论旨仍是人类向着有秩序的自由不断前进的情景。“要想阐明近代政治中的这种千头万绪的复杂状况,我们除了有向完整与确实的自由发展与自由人具有天赋权利这些思想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其它线索。”他大胆地宣称,信仰从权威中的获得解放便是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他对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南特诏令、以及对英国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论家们,等等——这里不过略举一二,——所作的评论,足以充分表明自由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是何等丰富。在活动家中间,威廉沉默者与华盛顿得到了他的行为善良的奖誉,但大多数著名的统治者,自查理五世至腓特烈大王,却得不到他多大赞许。当人道的进步被视作进步的量计与标尺时,宗教与种族的成见便会降至其适当地位。他的法国大革命课程的讲义却更有趣味与更有代表性。这里阿克顿所讲述的乃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题目,一个思想与行动错综交织②这种主张曾受到利与普勒希特的反对,见利《历史的道德价值》,《美国历史评论》,卷Ⅸ,与兰普勒希特《德意志历史科学杂志》,1898年。——原注①参阅一封有趣的信,见克莱顿的《传记》,卷Ⅰ,第13章与希米尔法布的《传记》,第357—373页。——原注\n在一起的运动。一个简短的撮要是表达不出这样一部精彩著作的全部力量、文才与丰富的思想的。其中的第一讲“革命的先驱”的特色是书中给了费内隆以特别显著的地位,指出“费内隆是最早能够看穿宫廷上的①种种虚伪浮夸作风与察觉到法国已走上崩溃道路的第一个人”。费内隆深深感觉到绝对权力乃是一副毒药,而唯一的解毒剂则是宪法。而那些继他之后的哲人们仍是在继续他那捣毁专制权力的工作;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尤其是卢梭)真正想要或者懂得政治自由。“那个使思想转化为行动的火花乃是由《独立宣言》所提供的。”书中关于美国的影响一讲也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他从美国政论家文中所作的种种摘要以及由于他对柏克早期哲学所作的讨论,而主要由于他对这场伟大的斗争所作的论断。“他们〔美国人〕的冤屈是难以证实的,在范围上则是琐细的。但如果说一方面是利害关系,那么,另一方面还有着一项显著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竟是这样神圣,这样清楚,以致绝对要求人们牺牲其生命、家庭及其财产。他们认为自由是这样神圣的一桩事业,所以他们必须以全社会的存在作为孤注以防止自由的最高权利受到那怕极小的侵犯。”而每当阿克顿谈到自由的时候,他的语气之间总是带有感情的。法国理论与美国实践的结合导致了1789年的事件。《陈情书》所提出的要求是封建制度与专制政治的取消而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泰纳曾把大革命中的人物描绘得相当阴森可怖,但阿克顿则认为,他们都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人,其中很多人的能力与性格不过稍高于普通标准,但米拉波与西哀士则是具有天才的。“我们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除非我们能看到它也是符合于一般规律的,而并非特别出奇与特别例外,因为不少别的场面也是同样可怖的,也同样有不少的坏人。”他把造成改革运动退步的主要责任推委于宫廷。法王自己是情愿前进的,但他却受到了坏主意的顾问的包围,其中尤为恶劣的便是那个王后。在谈到《人权宣言》时阿克顿是热情扬溢的。“提出《宣言》宣告了关于人类义务并非都可归因于契约、利益或武力的这一理论的胜利。这区区一纸的分量实超过无数座图书大楼与拿破仑的庞大军队。”但是它也有一个重大缺点。它为了平等而牺牲了自由;它把国王的绝对专制换成了议会的绝对专制。在国民议会还完全没有来得及去处理那些最紧要问题之前,欧洲列强早已开始对革命进行了威胁。逃亡者从边境上阴谋反对着新秩序,而国王王后则从推勒里宫中进行对抗。向瓦伦的逃亡顿时向法国表明,国王乃是背弃允诺,言行不一的。阿克顿与奥拉尔在政见与宗教上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却一致认为,迫使革命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则是宫廷与外国的勾结。但另一方面,那个为国王所痛恶的“教士法”也是一个致命的失策。国民议会实际优于立法议会,而立法议会又优于国民公会。他对王朝的倾覆,不胜惋惜,对9月大屠杀、国王与王后的处死以及恐怖政治等颇多谴责,但却认为这一切也都自有其原因。暴力统治始于边境危机的尖锐化而终止于这种危机的解除。处在那个威胁要把革命及其①费内隆,生平见第一章译注。他在为路易十四的王孙所写的读物《死人的谈话》及小说《黛雷马克》中谈论治国之道,借古讽今,抨击时政,发抒己见。——谭注\n一切成果统统毁尽杀绝的布伦斯威克宣言的面前,一个专制政府乃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吉伦特倒台而由雅各宾派上台,而这派的人物更为恶劣,而且更加不顾什么自由,但他们却懂得怎样捍卫祖国。丹敦的行为遭受到了严厉遣责,我们唯一能为他缓颊的话不过是:他还没有坏到罗伯斯庇尔的程度。在下面这句十足的攻击话里,这位演讲者对一群掩饰真象之徒曾经横加讥笑。“佩戴宝剑的强人之后尾随了一批拿着海绵的弱者。”不过这场革命尽管有它的种种恐怖,却是为人类解放事业所作的一番伟大努力。“人们梦寐以求的最好事物乃是宗教与自由;而并非逸乐或繁荣,也不是知识或权力。但是宗教与自由的道路上却都涂染了无穷鲜血。”在阿克顿受聘的几个月后,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主编一部综合性①的近代世界史。他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的职务本身使这事成为义不容辞,另外也因为任何人都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充分表达他自己对处理历史的看法。”他在一篇详细的备忘录里说明了他的编辑计划。“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撰稿者必须懂得,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另外谁也不能在还未检定作者名单之前便能够说出,哪里哪里②那位牛津主教的叙述告一段落,而下文开始由费尔贝恩还是由加斯奎、①李伯曼或哈里森继续执笔”。在检视了各国大批包括有新资料的刊物后,他宣称,一位勤恳的研究者会必将发现他自己往往不断被历史文献中的经典著作所遗弃、阻碍和误引。“在我们这一代中十分完善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的,但我们却还能够处理传统的历史著作。”他以特别愉快的心情期待着《近代史》后面诸卷的出版:认为这些卷帙将因改为含有从书本中所得不到的秘密而更趋富赡。“某些私人刊印的回忆录并非是绝对不可能获得的,另外城市中还有不少年迈的人们头脑中充满着秘密的东西。”他晚年期间在剑桥所写的论文《普法战争的原因》足以说明,那些以创造历史的人物身上所可获得的材料是如何丰富地深藏在一个人的脑袋之中。布赖斯指出,“他一直是在搜寻那密室的钥匙,而把前厅楼梯只看作装饰罢了。人们有时不免要发生怀疑,他是否对幕后的事物重视过多,但他却曾在那里看到过许多正在酝酿中的历史。”这位主编拟定一张撰稿者的名表,并征得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意,但1901年春他突然中风,因此不得不辞去这项职务。1902年时他即死去,距第②一卷出版前没有多久。正象马克·帕蒂森那样。他把相当巨量的未曾用过的知识带进了坟墓。亨利·西季威克常说,不管你对什么事情懂得的如何之多,阿克顿却肯定知道的更多。德拉弗莱曾因发现他居停主人书桌上“各式各类的每本新书都加满批注”而惊异不已。托尔马契也说,格拉德斯通每逢在①参阅剑桥近代史的缘起、撰写者出版,1907年。——原注②费尔贝恩(Fairbairn,A.M.1838—1912年),苏格兰神学家。加斯奎(Cas-quet,F.A.1846—1929年),英国天主教主教、史学家。——谭注①哈里森(Harrison,J.E.1850—1925年),英国史学家、古典学家。——谭注②马克·帕蒂森(1813—1884年),英国神学家,多方面的学者,对教育、文化、政治均有研究,逝世前,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完成。——谭注\n谈话中遇到什么疑难地方总是停下来说,“这事我们得请教阿克顿爵士。”当然对这些赞词我们不能理解得太死。他对科学便完全不懂,对于纯文学与艺术也很少关心,而只是在中世纪后期与近代世界史方面才是出奇的渊博。但另一方面,广泛的书本知识而外,他还具有对人的宏富知识。他接触过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政治与学术界中不少起过重大作用的知名之士。早年他曾经是平民院的议员,后来又充任贵族院的议员。莫利爵士的文中记载道,格拉德斯通总想和他更多地交往,而《给曼丽·格①拉德斯通的信件》中也表现了这位学者对这个政治家的热烈钦敬。阿克②顿作为格列里温俱乐部的成员,非常熟悉英国社会的上层人物。在国外③④不仅德林格尔与度蓬卢,甚至象勒南与泰纳或蒙森与赫尔姆霍斯这样人物,也都乐于与他结交。他常常今天晚上与梯也尔一道进餐,明天晚上在布罗伊公爵席上作客。连腓特烈王后也都是他的好友之一。他的一个忠实的门生写道,“与阿克顿交,即是与全欧最有文化的人士来往。在他那深沉的音调里仿佛可以听到历史的语言。”他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深入理解当前现实的基础,而且是德性的学校与人生的指导。“史学的伟大任务在于发展,改善与加强信仰。”历史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历程,思想与理想的形成与运用的纪录。而自由则是一个种族在其前进与上升的行程中的标记、目的与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构成人类历史之网的主要思潮与心理状态往往不下二、三十种。对这一切,每个严肃的人都应当有所了解,无论是关于它们的优点缺点还是关于它们的原因、结果与关系。而其中的多数不是属于宗教性的,便是宗教的替代物。”他曾为一个“受过教育并具有常识的”青年拟过①一张包括有上百种著作的必读书目。他还以一段崇高的语言说明它的目的,“即在使他的心灵日臻完美与打开他各方面的眼界,即在使他的认识达到其时代的水平,从而能够理解那些曾经造成我们今天世界甚至今后仍将支配这个世界的种种力量,即在使我们能够防范对猝然而来的外部事件发生惊慌和对内心之中错误的经常的缘由以有力的纠正,即在给予我们以最强烈的刺激与最可靠的指导,使我们的思想具备有力量、充实、透彻、诚恳、独立、高尚、慷慨、沉着等等优点,从而懂得克服错误与赢得真理的方法与法则,以及我们对事物进行取舍的充分理由,并更好地理解制度的起源、优点与活力以及做了错事的人们的良好动机;另外还在于使我们不为文采与才华所迷惑,因而使其中每一本书都足以可成为一种新生活的开端”。在阿克顿看来,历史家不仅是事件与意识形态的解释者,而且是道德的捍卫者。他宣称,“道德法典的不容伸缩的完整性,在我看来乃是历史的权威、尊严与效用的秘诀。”他认为自基督教兴起以来,过去的人们也和今天我们同样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基督教信仰过①比较,曼丽·德留,《阿克顿爵士留给自由派的遗产》,《乐观派》杂志,1908年1月。——原注②格列里温俱乐部(Grillion’sandtheClub)系伦敦著名文艺俱乐部,成立于1813年,成员多属知名人士。——译者③度蓬卢(1812—1878年),法国奥尔良主教。——谭注④赫尔姆霍斯,H.L.F.(1821—1894年),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自然法学家。——谭注①参阅克莱门特·肖特,《阿克顿爵士推荐的佳著百种》,《帕尔·马尔杂志》1905年7月。——原注\n去便是我们行为的指南针,此外我们再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指引我们。他在评论莫尔斯·斯提芬斯时写道,“我们对于人物与党派的判断乃是从他们所达到的最低点来开始的。作为此事最低点的凶杀对于我们的衡量基础具有极大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的零点作为开始,所有对腐败、虚伪或叛逆的谴责都将没有意义,而道德与历史也必将分道扬镳。”同样他对超人及其崇拜者也是厌恶的。卡莱尔去世后,他在写给曼丽·格拉德斯通的信中说,“弗劳德而外,我认为他是最可憎恶的历史家。”他这一系列的警语,包括他对历史家的一些劝告在内,处处吐放着一种严肃气氛,可能会使西斯蒙第与施洛塞尔感到满意。“判断不应按照一种体系的正统标准来进行,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在哲学或政治方面,而是应按照是否能促进信仰的优美、完整与权威这个标准。”“最大的罪孽是杀人罪。同谋者并不比凶手好些,而策划者便更坏。”“系人勾当不止可以通过毒药或刀剑进行,它还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通过貌似正义但又有利可图的战争,通过诬告等进行。”历史教导研究者们要寻求并讲述全部真实,坚持证据,反对模棱两可的言语与消除偏见。历史家须是一个不为世俗权势、功利或谄谀所动的审判官,一个主持正义公道,为人昭屈雪冤的人。他对他那年迈老师的冷淡超脱态度曾深表惋惜。1879年时他写道,“德林格尔对于事物差异的根源,往往只知道到思辨性体系里去找,到知识的缺陷里去找,而唯独不到道德原因方面去找;在这点上他与我之间存在着一条完全无法接通的深阔鸿沟。他对人性中一切罪恶是避眼不看的。”阿克顿这种顽固态度:即他拒不承认道德风尚也正象别的事情那样可能发生改变直到其弥留之际方才有所转变。他①的儿子写道,“在几乎是我们最后的那次谈话里,他郑重地教诲我不要象他过去所做的那样草率地判断别人,但要尽量宽恕人们的弱点。”这种至死仍在学习的态度确实是这位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志职的人的一个很好总结。Ⅱ①英国制度研究者当中最杰出与最有创见的历史家梅特兰><以史学作为其终身工作之前原是学法律的。1879年,二十九岁时,他就英国不动产法的改革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显出他对布伦纳及其它外国法学家的著作相当熟悉;这篇文章引起了波洛克爵士的注意,成为双方友谊的开端。波洛克勋爵在其友人死后写道,“我是一个法学家;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远远超出一般课本的更多的历史批判知识,他是不可能理解英国法律的。”他找到了梅特兰这个气味相投的人,因为他们对古往今来都感兴趣。1884年他在牛津遇到了维诺格勒多夫,于是又开始了第①给《泰晤士报》的信,1906年10月30日。阿克顿的这些先知式的言论受到巴①参阅费希尔,《梅特兰》,1910年;史密斯《梅特兰的两篇讲演稿》,1908年;波洛克勋爵《每季评论》,1907年4月;维诺格勒多夫,《英国历史评论》,1907年4月;《塞尔登学会》,卷XXⅡ,1907年;《剑桥大学报道》,1907年7月22日。关于国外对他的评价,参阅贝蒙,《历史评论》,卷XCⅢ与《法律季刊评论》,1907年4月。另外《剑桥杂志》1950年12月号中载有过一篇极好的百年纪念论文。——原注\n二个著名的友谊关系。“那一天决定了我的一生。”在一席谈话的鼓舞之下,梅特兰去了档案局。这件事的结果便是他的《格罗斯脱郡的英王公诉状》这一著作。格罗斯脱郡为他的生地,他曾认为这个地方乃是13世纪早期英国生活的写照。同年他被聘为剑桥大学英国法律特菲尔德的反对,《辉格党的历史观》,第6章。——原注史讲师,于是放弃了他的律师方面业务。他的第二个尝试则更加与这位俄国学者直接有关,后①者在《雅典娜》杂志上曾论述了英国博物馆内的一部手稿,内容为亨利②三世时代几百件判例,认为这手稿显系为布雷克顿所编或别人为他所编,曾经他加过注释并在他的那篇名文写作时充分采用过。梅特兰的研究证实了他友人的假设;他的《布雷克顿的笔记》一书曾于1887年出版。这些判例经过出色的编辑后,不仅帮助说明了当时的法律概念与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生活也极具启示。一年后,他被聘为英国③法唐宁讲座教授。他的就职演讲的标题为《为什么法律史尚未编写》,他在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指出,因为这事在传统上一向与其它一切研究相隔绝。我们的档案无论在数量上与连续性上都是独特的,这中间蕴藏着人们梦想不到的宝物。“法律文献往往是关于社会与经济史、关于道德史或关于实际宗教史方面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证据。这些广阔、富饶的历史地带却往往使历史学家裹足不前,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法律性质太强不易把握。”法律必须视作民族生活的一部分,而通过法律所表达的种种思想必须加以恢复。“一部法律的历史必然也是一部思想的历史”。一般历史家往往不具备法律方面的详细知识而一般法律家又常严重缺乏历史观点。为了沟通这个困难,他遂担起这项近乎终身的工作。《英国法律史》曾于1895年出版;虽然名为波洛克与梅特兰的合著,实际上主要出于后者之手。书前长达二百页的导论篇是对英国史的一个宝贵贡献。他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几乎是纯属日耳曼式的。即使凯尔特的习惯在条顿征服后尚有留存,它的痕迹已经无从寻素。另外也没有什么真实证据足以表明,罗马制度在条顿族侵入后曾经延续下来,或者曾有助于英国法律的形成。在法律领域内一切属于罗马或罗马化的事物,都可以后来输入的东西中得到说明。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文献内,一切罗马的东西都只是宗教方面的。在后来的年代里,某些罗马的形式与成语乃是从法国渗入的。直到诺曼征服以后,罗马成分,亦即由诺曼公爵们所袭用的法兰克政治制度内所包含的罗马成分,才真正有大量地传入英国。另外也只是直到12世纪中期,当博洛涅重新兴起了关于查士丁尼法典的研究后,这个潮流才开始大量涌入;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即又开始呈现退落。自爱德华一世以来法律方面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我国的法律从未象在德意志那样被罗马成份的整批输入所消灭。13世纪,亦即法德两国法律的古典时期,曾得到过欧洲大陆学者们的彻底探索,①原文为Anthenaeum。——译者②布雷克顿(Bracton,E.?—1268年),英国法学家,对英国法律与审判记录进行系统整理写有专著。——谭注③唐宁讲座教授(DowningProfessor)——乔治·唐宁勋爵在剑桥大学所创设的法律讲座;担任这个讲座者叫做唐宁教授。——译者\n但欧洲的法律则只有在认真研究了各种体系之后方才能作到充分理解。“我们必须一个个弄清那些将用以比较的事物,然后才能拿它们进行比较。在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上我们已经着手担任了其中一小部分。”这两位作者的研究范围虽然实际上仅限于法律史方面,但他们偶尔也讨论到宪法上的问题。“我们感到,那些致力于中世纪时代私法研究的人们,即使从一些政治事件当中也每每能窥出若干线索,而这些,对于那种由于其素养关系只习惯于或只懂得从政治方面看问题的人们,则往往会视而不见。”同样,这部书有时也会撇开教会的体制不谈,而涉入到教会法的领域之内。书的两大卷中很大部分系对安吉文朝法律的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各色各样的租赁权、社会阶级、各类审判权、契约与继承权、婚姻法、刑法、程序法等等。虽然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概述里面有些部分必然专业性较强的,但这由于文笔的灵活以及其中牵涉到的民族生活范围较广,这部书倒也并不枯燥。1898年的第2版内还增入了关于前撒克逊时期,亦即罗马时代一章,内容颇具启发性。两位作者原打算以《末日审判簿》的研究来充实他们对金雀花朝法律的概述。“我们想迫使《末日审判簿》吐出其蕴藏的秘密的唯一希望,以及我们想让盎格鲁-撒克逊土地册成为一件意义明确的东西的唯一希望都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彻底弄通安吉文朝时代的法律。”但是这本“秘录”的研究却受到了耽搁;《末日审判簿与嗣后》一年以后方才出版,仅由梅特兰单独具名。这个论题要远比金雀花朝法律的整理困难得多,但他的尝试则是在这方面研究中成绩最卓越的一个。早在1883年时西博姆业已出版过《英国的村社》,由于书中对中世纪农业的生动描写、书中所体现的广博学识以及在农奴制起源的资料上的巧妙的处理,曾使书出后产生过深刻印象。西博姆以大家熟悉的中世纪后期的庄园制为起点,通过《末日审判》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由此而上至于罗马占领时期的逐步追溯从而找到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罗马大农庄乃是庄园的最早来源,而村庄则是拉丁族的产物而非条顿族的产物。于是,马克公社的理论立即垮台;一个时期之内,好象他的进攻已把日耳曼派从战场上扫除净尽。但是这个新理论实际上却是和那旧理论同样不够严密的。它所采用的一系列证据,乍看起来虽很完备,但其中充满着很大缺陷。许多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属于另一方面的事实则完全被他忽略。西波姆不仅在其得出的结论上,甚至在他的思想习惯上很象斐斯特尔·得·库朗热,他具有一种善于把事物描绘得鲜明突出的稀有本领。维诺格勒多夫关于“维兰”制的经典著作,(梅特兰曾誉之为英国法律史上的最为杰出的伟业)不久便证明了英国社会结构并非如西博姆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这位英国学者所看到的无非是从罗马时代以来一脉相承而来的一个单一制度,但那位俄国学者从中所见出的却是非止一种类型,而是一个随其时代与地点而变化的各种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复合体。维诺格勒多夫对农奴制的罗马起源说的否定主要以《末日审判簿》以后的事实为依据,而梅特兰的根据则是他对《末日审判簿》本身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庄园与领主制并非罗马田庄产生的后果;英国自由农民愈在过去人数愈多;自由村庄过去即曾存在;英国在诺曼征服时代还只是部分庄园化;真正的庄园制度只是迟至12世纪时方才出现。那时各种庄园的性质不一,在这里面有着为数不少的自由租地农,以及不同程\n度的自由。我们的村社属于日耳曼来源,起初包括那些占有土地的克尔①(Ceorls)与他们的奴隶。这个自由阶级由于后来领主司法权与封建制度的增长而受到压迫。自由的村社乃是农业单位而非政治单位。它没有议事会与法院,而法律也没有承认它的地位。梅特兰的这篇论著,以至轻快的笔调论述极繁难的问题,毫不费力地推翻了英国农奴庄园制单一性的概念。一年后,梅特兰发表了第二篇专著,亦即《市镇区与市邑》属于福特讲座书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根据牛津与剑桥的资料来探讨市镇起源与特权问题的一部著述。这里他的任务又是反对过分简化。他倾向于接受刻特根的一种理论,即市邑(borough)起源于郡的炮台(countyfortress)。市镇区(township)连同它的市场、法院与炮垒逐渐变成市邑或特权市镇(privilegedtown)。在诺曼征英之后,许多市镇曾请求并获得过类似的特权,但没有一种假说可以解释通各种情况。例如,剑桥便没有领主而只有国王。书中讨论了法团观念,这是梅特兰所喜欢谈的一个概念,认为这是形而上学、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基尔克曾说明过法团在中世纪生活里所占据的重大地位:信托会或友谊社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个真人,既非国家的创造物,也不是一个①虚构。梅特兰在1900年翻译过基尔克关于法团理论的一章,并在所写的一篇精彩导论中对这个概念作了说明与发挥。梅特兰第三部专著则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英国法律史》曾扼要地叙述过僧侣的法律地位和讨论过异端与妖术这类宗教上的罪行,但未曾研究过宗教法。当梅特兰开始在这个领域内进行研究时,斯塔布斯曾是这方面最伟大的实际上亦即唯一的权威,后者曾以此为题在牛津作过演讲,并为宗教法院王家委员会编写过一本备忘录。斯塔布斯主张,宗教法在其得到英国教会批准之前在那个教会里是不具约束力的;梅特兰由于研究了林伍德(坎特布里大主教下的一名职员)1430年所编的《大主教区》而抛弃了斯塔布斯的看法。其它一些教科书中也都载有着类似的写法;但他的著作证明,英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服从教会法的。于是,那种认为英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罗马之外和宗教改革在英国未曾产生过多大变革的传统说法也就立不住脚了。《英国宗教法》在某些范围内曾引起过震动,甚至不满,但它的结论则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他在《剑桥近代史》第二卷里关于伊丽莎白的《宗教处置法案》与苏格兰的宗教改革的描述,也是极具价值的作品。以前很少注意16世纪的历史,但他很快掌握了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在不过短短的一章的篇幅①里,他异常透辟地阐明了伊丽莎白的宗教处置法案,由于他一贯善于把握和分析半法律半政治的概念,因而完全能深入到宗教改革妥协的核心。亨利八世的盎格鲁——天主教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继之而来的则是“长久的伊丽莎白和平”。“这个和平的出现乃是整个局势得到普遍改①克尔(Ceorls)是盎格鲁-撒克逊早期(5至7世纪)的自由农民。——谭注①书名:《中世纪政治理论》(PoliticalTheoriesoftheMiddleages),摘译自基尔克的名著《德意志社团法》。——谭注①1559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肯定教会最高权力属于国王,否认教皇的权力,并规定以《公共祈祷书》为作礼拜的唯一合法依据。——谭注\n善的一种结果,是与稳定的币制、费用低廉但效能颇高的政府、民族的独立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复兴等等密切相联系的。”在这样地忙于论述与调查研究的同时,梅特兰还在他1887年所创立的塞尔登学会上化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在这个学会在他逝世之前所出版的二十一卷刊物中,他便编辑过不下八卷。其第一卷树立了以后诸卷的楷模。《英王公诉状选辑》的导论,说明了13世纪前半期王家法院分院之间的纷歧问题。《庄园法院公诉状选辑》追溯了私人法权的衰落过②程。《布雷克顿与亚速》衡量了布雷克顿对罗马法与意大利学术的继承关系,而在这方面梅因曾走入迷途。在以塞尔登学会的刊物来阐明某些具体问题的同时,他还提醒国人注意这个方面那些几乎完全为人忽视的大量资料,因为这对英国法律史的知识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过去那种以为不用年鉴也能写中世纪英国史的作法是何等奇怪。”正是因为他过去曾探索这些“年鉴”,致使《英国法律史》未能续写下去。他以极大兴味投身于这项研究,并高兴地发现到这些在帮助弄清法律与行政制度的各个方面具有多么大的启示作用。他从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开始,完成了三卷。他毫无困难地揭示了一些他称之为欧①洲最早的“辩论”的独特价值。他关于法文文献的翻译是语言学上的一个出色成绩,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帮助确立了英法两国的法律用语。他在死前生病时期的几个月内仍忙于这项异常艰辛的工作。梅特兰死时年仅五十六岁,这是学术界的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在不过二十年期间,他奠定了英国法律史的基础,另外对其中若干部门也都制定出详尽计划。他曾使他的门生与同事,其中包括玛丽·贝特森,在这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著作与功绩受到了人们充分的肯定。维诺格勒多夫称他是一位天才。在斯塔布斯与加第纳还在世的时候,阿克②③顿便称许他为英国最有才干的历史家。戴西把他与布莱克斯通与梅因并列。在德国,他的著作得到人们的认真研读。李伯曼说他曾把档案的尘埃变成了黄金,布伦纳也说他使英国一脱其孤立状态而汇入欧洲思潮的中流。基尔克则认为他是自己思想的天才诠释家,也是法团研究上的一个同道。类似的赞语还来自法美等国的史学和法学家。这种普遍赞美的原因主要由于他一身兼备各类优点的稀有结合。史密斯写道,“自吉本以来,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地既长于科学又长于文学,既是分析家又是艺术家,集斯塔布斯与弗劳德之长于一身”。他既有才气又极谨严,既善想象又能勤勉。不唯在业务的具体技术方面醇然无疵,甚至在法律与惯例等赖以表达的概念的洞察力上也属罕见。斯塔布斯在制度的分析方面可谓鲜有其匹,但梅特兰在说明这些制度所由体现的概念上则较他犹胜一筹。由于他善于从法律程序与羊皮纸的背后发掘出人的因素,他把法律与生活联系了起来。他按最广泛的方式解释了历史。“人们在行②亚速(Azo约1150—1230年),意大利法学家,波伦亚大学教授,著有《法典大全》(SummaCodicis)。——译者①指“日耳曼派”与“罗马派”的辩论。——谭注②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W.1723—1780年)英国法学家,曾任律师、法官、女王法律顾问,著有《英国法注释》(Com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共四卷。——谭注③梅因(MaineH.J.S.1822—1888年),见本书第二十七章。——谭注\n动上与言论上的成就,尤其是他们在思想上的成就——这便是历史。”法律的历史实即思想的历史,但这种思想不是指抽象的思想,而是那种在活人中间起着作用的思想。他的鲜明而优美的文体也反映了他的机敏与活泼的精神。他善于随手举出近代的相类事例来体现一个概念或解释某种行动。他的伊丽莎白“宗教处置法案”一章表明,他在叙述方面完全可能作到和他在解释制度与思想方面那样同等成功。他关于《英国宪法》的早期讲稿处处闪耀着机智与轻快。他在里德讲座(RedeLecture)所作的《英国法律与文艺复兴》中则以寥寥无几的粗放笔墨表出,当罗马法业已进入德国与苏格兰之际英国曾经如何确保其本土的法律。他写东西虽然文笔敏捷,且无斧凿痕迹,而笔锋所至,无不使篇页生辉。波拉德经一再考虑后说过,他不仅是他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英国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至于其它众多英国学者的辛勤成就,这里只能作一个简述了。以只手之力而毅然完成中世纪史的叙述者则为詹姆斯·拉姆齐爵士。他所苦①心孤诣编写的数卷一直叙述至都铎朝的开始。他的著作在创见性与文笔上并不见长,书的价值主要来自他对已刊资料的审慎研究。朗德主要阐②③明了诺曼诸王的制度,而泰特的书则系关于早期诸自治市的状况。凯特·诺尔盖脱进一步研究了英王约翰与亨利三世早年的历史,这是继她④在格林的提示下所成的金雀花朝诸卷之后的续作。关于后期中世纪的历①史以韦里所编的亨利四世时期部分发掘最为透彻。布鲁尔曾将自己为亨②利八世公文所作的很好前言汇集为两巨册,这样遂将这段统治的历史叙述至沃尔西舍的失败时期,书中也揭示了他的伟大之处。波拉德对16世③纪历史的研究结果,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老练成熟的专著方面。英国海军①拉姆齐爵士所著中世纪英国史有以下五种:1.《英格兰的奠基,英国千二百年史》(FoundationsofEnglandorTwelveCenturiesofBritishHistory,B.C.55——A.D.1154)共二卷,1898年。2.《金雀花帝国,亨利二世、理查一世与约翰三朝史》(AngevinEmpireortheThreeReignsofHenryⅡ,RichardⅠ,andJohn.A.D.1154—1216),1903年。3.《宪法的起源,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两朝史》(DawnoftheConstitutionortheReignsofHenryⅢandEdwardⅠ,A.D.1216—1307)。1908年。4.《兰开斯特王朝的创业,爱德华二世、三世与理查二世三朝史》(GenesisofLancasterortheReignsofEdwardⅡ,EdwardⅢ,andRichardⅡ,1307—1399),二卷,1913年。5.《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英国百年史》(LancasterandYork,acenturyofEnglishHistory,A.D.1399—1485),共二卷,1892年。——谭注②朗德(Round,J.H.)著有《封建制的英国,十一、二世纪历史研究》(FeudalEngland:historicalstudiesoftheXIthandXIIthcenturies)一书(1895年初版)。——谭注③泰特(Tait,T.)与巴拉德(Ballard,A.)合编有《英国自治市特许状》(BritishBoroughCharters,1216—1307)一书。——谭注④凯特·诺尔盖脱(KateNorgate)有关金雀花朝的著作名《金雀花朝诸王治下的英国》(EnglandundertheAngevinKings)共两卷,1807年。有关亨利三世的专著为《亨利三世的青少年时代》(MinorityofHenryⅢ),1912年。——谭注①韦里(Wylie,J.H.)所著书名《亨利四世治下的英国》(EnglandunderHen-ryⅣ),共四卷,1884—1898年。——谭注②布鲁尔(Brewer,J.S.)所著书名《亨利八世朝:自即位至沃尔西之死》(ReignofHenryⅧ,fromhisaccessiontothedeathofWolsey)共两卷,1884年。——谭注③波拉德(Pollard,A.F.)有关16世纪的专著有:《1547—1603年的英国》(England,1547—1603年),\n④史的研究与普及应首推约翰·劳顿勋爵与朱利安·科贝特勋爵,而前者还是海军档案学会的创立人。斯佩丁一生致力于培根著作的搜集与其名⑤誉的维护。大卫·马森则以密尔顿为枢纽来对他的时代作包罗万象的综⑥述。弗思以下列一系列工作阐明了17世纪中期的各个角落:编订出版《克拉克文件》,勒德洛的《回忆录》及许多其它新旧资料;撰写《全①国名人传记辞典》中有关条目与克伦威尔及其军队的专著,并将加第纳的英国史续至护国主死时为止。关于复辟时代则有克里斯蒂所著的沙夫②③茨伯里传与福克斯克罗夫特小姐对哈利法克斯的研究。18世纪时期的主要政治家们也逐渐有了他们的传记作者。西奇尔为④博林布鲁克编写了一部极有气势的申辩书;巴兹尔·威廉斯第一次提供⑤⑥了查塔姆的详细传记;菲茨莫里斯爵士为其祖先谢尔本作了辩护。乔治·屈维廉爵士继其对福克斯的早期生涯所作精彩简述之后,又回至其⑦主角的晚年时期,实际上把这部传记写成了一部美国战争的历史。约⑧翰·莫利关于柏克的传记与论著已成为英国政治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亨利八世》(HenryⅥ),《托马斯·克拉麦与英国宗教改革》(ThomasCrammerandtheEnglishReformation),《护政大臣萨默塞特治下的英国》(EnglandunderProtectorSomerset)等。——谭注④朱利安·科贝特勋爵(JulianCorbett)关于海军史的专著有:《德雷克与都铎朝海军》(DrakeandtheTudorNavy,withahistoryoftberiseofEnglandasamarintinepower),《德雷克的后继者》(SuccessorsofDrake),《英国在地中海上》(EnglandintheMediterranean,astudyoftheriseandinfluenceofBritishpowerwithintheStraits,1603—1713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EnglandintheSevenYear’sWar,astudyincombinedstrategy)等。——谭注⑤斯佩丁(Spedding,J.)所著书名《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平与书信》(LettersandtheLifeofFrancisBacon,includingallhisoccassionalworks)共七卷,1861—1874年。——谭注⑥马松(Masson,D.)所著书名《密尔顿传》(LifeofJohnMilton,narratedinconnectionwiththepolitical,eccesiasticalandliteraryhistoryofhistime)共六卷,1859—1894年。——谭注①弗思(Firth)所著书名《克伦威尔的军队》(Cromwell’sArmy,ahistoryoftheEnglishsoldierduringtheCivilWar,theCommonwealthandtheProtectorate)。——谭注②克里斯蒂(Christie,W.D.》所著书名《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传》(LifeofAnthonyAshleyCooper,firstEarlofshaftsbury),1888年。——谭注③福克斯克罗夫特(Foxcroft,H.C.)所著书名《乔治·萨维尔的生平与书信》(LifeandLettersofGeorgeSavile,firstMarquisofHalifax)两卷,1898年。——谭注④西奇尔(sichel,W.H.》的书名《博林布鲁克及其时代》(BolingbrokeandHisTime)共二卷,1901—1902年。——谭注⑤威廉斯(Williams,B.)所著书名《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传》(Lifeofwil-liamPitt,EarlofChatham)共二卷,1913年。——谭注⑥菲茨莫里斯爵士(Fitzmaurice)所著书名《谢尔本伯爵威廉传》(LifeofWilliam,Earlofshelburne,afterwardsmarquessofLanodowne)共三卷,1875—1876年。——谭注⑦屈维廉(G.O.Trevelyan)于1880年出版《福克斯早年的历史》(EarlyhistoryofCharlesJamesFox),继之写出《美国革命》(AmericanRevolution)一书,最后,以(乔治三世与查理·福克斯》(GeorgeⅢandCharlesFox)作为记述美国革命史的终篇。——谭注⑧莫利(J.Moley)著有:《埃德蒙·伯克,历史的研究》(EdmundButke,ahistoricalstudy),1867年,《伯克传》(Burke),1879年。——谭注\n①霍兰·罗斯关于拿破仑与皮特的传记则体现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福蒂斯丘异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陆军的命运并对其政治上的名声表示了绝大②的轻视态度。斯宾塞·沃尔波以一位温和的辉格党人精神编写了珀西瓦③④尔与约翰·罗素勋爵的传记,以及自1815至1880年间的英国史;这一系列著作横跨了整个19世纪时期。赫伯特·保罗编述了维多利亚时代⑤后期的历史。英国素以官方政治传记众多著称,其写法继承了格雷维尔⑥《回忆录》的传统,主要以揭示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的动机与筹划为目的。英国18至19世纪之间社会经济的过渡情况则从韦伯夫妇、劳伦斯⑦与巴巴拉·哈蒙德等人的研究中获得较好的说明。苏格兰历史的编写则①有伯顿·安德鲁·朗与休姆·布朗。爱尔兰的历史仍属一个争端较多的②地带。格林夫人尖锐地指责了英人对中世纪时期爱尔兰的贬抑观念;这项挑战的答复人为奥彭。巴格威尔从统治种族的立场讲述了16、17世纪③的爱尔兰史。利顿·福基纳的惨死使爱尔兰史的领域内丧失了一位自莱基以来最有修养的学者。①罗斯(H.Rose)所写的传记为:《拿破仑一世传》(LifeofNapoleonI)共二卷,《威廉·皮特传》(LifeofWilliamPitt)。——谭注②书名《英国陆军史》(HistoryofBritishArmy)共十三卷,1899—1930年。——谭注③珀西瓦尔(Perceval,S.1762—1812年),英国政治家,反对解放天主教徒,1809—1812年任首相,遇刺身死。约翰·罗素勋爵(1792—1878年),辉格党领袖,1831年提出议会改革法案,1865—1866年任首相。热心学术,编辑刊行了C.J.福克斯和托马斯·莫尔的回忆录与书信。——谭注④沃波尔(S.Walpole)著有:《约翰·罗素勋爵传》(LifeofLordJohnRussell)共二卷,1891年;《1815年大战结束以来的英国史》《HistoryofEnglandfromtheconclusionoftheGreatWarin1815),共五卷,1878—1886年。——谭注⑤书名《英国近代史》(HistoryofModernEngland)共五卷,1904—1906年。——谭注⑥全名《格雷维尔回忆录:乔治四世、威廉四世及维多利亚女皇三朝杂记》(Grevellememoirs,ajournalofthereignsofKingGeorgeⅣ,KingWil-liamⅣandQueenVictoria)共八卷,里夫(Reeve,H.)主编,1874—1887年。——谭注⑦S.韦伯夫妇有关18、19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著作有:《教区与州郡》(TheparishandtheCounty),《贵族领地与自治市镇》(TheManorandtheBorough),《英国济贫法政策》(EnglishPoorLawpolicy),《工业民主》(IndustryDemocracy),《近代实业问题》(ProblemsofModernIndustry),《英国工会运动史》(TheHistoryofTradeUnionison)等。J.B.哈蒙德夫妇的有关著作见本书《导论》译注。——谭注①伯顿(J.H.Burton)著有:《自阿格里科拉入侵至肃清詹姆士二世党叛乱时期的苏格兰史》(HistoryofScotland,fromAgricola’sinvasiontotheextinctionofthelastJacobiteinsurrection),共八卷,1867—1870年。——谭注安德鲁·朗(A.Lang)著有《罗马占领以来的苏格兰史》(HistoryofScotlandfromtheRomanOccuption),共四卷,1900—1907年。——谭注休姆·布朗(H.Brown)著有《苏格兰史》(HistoryofScotland),共三卷,1900—1909年。——谭注②见格林夫人所著《爱尔兰的缔造与毁灭》(TheMakingofIrelandandItsUndoing,1200—1600,1908)。——谭注③格林夫人(Mrs.J.R.Green原名AliceStopfordGreen)著有《爱尔兰民族》,《爱尔兰国史——至1014年》(HistoryoftheIrishStateto1014年)奥彭(Orpen,G.H.)著有《诺曼人统治下的爱尔兰》(IrelandundertheNormans1216—1333),共两卷。巴格威尔(Bagewell,R.)著有:《都铎朝治下的爱尔兰》(IrelandundertheTudors)共三卷;《斯图亚特朝及空位时期的爱尔兰》(IrelandundertheStuartsandDuringtheInterregnum)共两卷。——谭注\n在近时英国学者关于外国史方面的著作中间,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占有着极高的地位。经过多次修订后,这部书已成为全世界研究者了解中世纪欧洲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部指导著作。霍奇金的《意大利及其入侵者》,由于其叙述的本领以及论题所具有的浪漫趣味,也赢得了④其应有的声望。这位英国的达恩给阿拉列与查理大帝之间的漫长的几世纪注入了生命;英国历史书中很少有哪部著作能象他在描述西奥多里克的哥特王国及其遭到查士丁尼军队的毁灭等场景时那样富于魔力。另外一些虽不很出名,但却颇有价值的史学著作为,豪沃思的《蒙古人史》,阿姆斯特朗的《查理五世传》,马丁·休姆关于西班牙的卷帙繁多的著①②作以及华德关于三十年战争与汉诺威选侯领的研究。威廉·亨特勋爵③一生曾致力于印度史的研究。赫伯特·费希尔研究了拿破仑在德意志的④⑤行政制度;奥曼重述了半岛战争的故事。金莱克的多卷本《克里米亚战争史》,曾一度为人们所争相阅读,而现在已几乎被遗忘。法伊夫编写过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清晰概论,时间自法国革命时期至柏林会议止⑥⑦。在近时著作中间,乔治·麦考莱·屈维廉论述加里波第的著作则由于书中的鲜明色调而赢得热烈欢迎。吉本与格罗脱所兴起的那种由有学问的史家所形成的优良英国传统一直绵延不绝,这对学术与文学都产生过无可估量的益处。《维多利亚英国诸郡》还在慢慢陆续出版;英国地名学会的刊物也在不断填补着我们关于早期英国知识中的缺项。而《剑桥近代史》一书中则载入了英国与外国学者的某些最为成熟的作品。④达恩(Dahn,1834—1912年)——德国政论家、历史家与诗人。曾任尼斯堡与布勒斯劳大学的法学教授。——译者①马丁·休姆(M.Hume)有关西班牙史的专著有:《西班牙:从伟大到衰微,1479—1788年》(Spain,itsgreatnessanddecay,1479—1788年),《西班牙腓力二世》(PhilipⅡofSpain),《腓力四世的宫廷》(CourtofphilipⅣ;Spainindec-adence),《近代西班牙》(ModernSpain,1788—1898年)等多种。——谭注②华德(Ward,A.W.)的有关专著有:《三十年战争中的奥地利王室》(TheHouseofAnstriaintheThirtyYearsWar),《反宗教改革》(TheCounterReformation)等。——谭注③亨特(W.Hunt)勋爵著有:《英属印度史》(HistoryofBritishIndia)共二卷,1899—1900年,《女皇的印度及其他,论文集》(IndiaoftheQueenandOtherEssays),1903年等,主编《印度的统治者》(丛书)(RulersofIndia)共二十八卷。——谭注④费希尔(H.Fisher)的专著名《拿破仑治国方术之研究》(StudiesinNapole-onicStatesmanship),1903年。——谭注⑤奥曼(Oman,C.)的专著名《半岛战争史》(HistoryofthePenisularWar),共六卷,1902—1922年。——谭注⑥书名《欧洲近代史,1792—1878年》(HistoryofModernEurope,1792—1878),共三卷,1880—1892年。——谭注⑦G.M.屈维廉有关加里波第的著作是:《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Garibal-di’sDefenceoftheRomanRepublic),1909年;《加里波第与千人军》(GaribaldiandtheThousand),1909年;《加里波第与意大利的缔造》(GaribaldiandtheMakingofItaly),1911年。——谭注\n第二十章美国Ⅰ关于美国历史文献方面的认真研究始于贾雷德·斯帕克斯,他最初①的工作是收集华盛顿的著作。华盛顿已发表的书信散见于许多书籍之内,另外大量文件从未为人见过。起初,华盛顿的家族曾计划出版一部②他的私人文件选辑,因而不允许斯帕克斯去查阅弗农山庄上的珍藏案卷,但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的劝告下,他们没有继续坚持。1828年斯帕克斯并查阅了伦敦与巴黎的档案。他的著作于1834至1838年间按十二卷出版,不仅使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的性格与活动充分为世人所③知而且提供了美国史上这段关键时期的第一部详尽记载。书的重要性立即获得了人们的承认。基佐主持了该书法文节略本的翻译,并在书前冠以这位英雄的精彩事略一篇,同时,劳默尔也准备出其德文版本。斯帕克斯的勤劳虽然到处得到了承认,但他在执行编辑责任方面却未能逃脱批评。马洪爵士指责他抽去了那些对美国官员不利的文字段落;其它的人也指责说他窜改与润饰了某些信件。斯帕克斯答复说,如果说他曾略去了若干信件,那只是因为这些的内容已在他所出版的书籍中刊出过。对另外一些批评者他的答复是,由于华盛顿遗留下的很多文件有几种草稿,而他在年老时期曾修改过他的早期信件,所以他觉得有责任按其最后形式来进行刊印;而且他对原文的更动部分仅仅限于抄录者的明显笔误方面。但这个申辩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其中有少数文字段落的删略乃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另外若干文字上的改动则是无可原谅的。如果说斯帕克斯不是一个理想的编订者,另外在草稿上的重后期轻前期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他的真诚用心却是无可指摘的。他还在政府的指示①下出版过十二卷文献,阐明美国革命时期的外交政策;并且收集过富兰②克林与莫里斯的著作。他的《美国传记丛书》载有传记六十篇,其中颇有些篇即出于他的手笔,涉及到美国史的全部领域。斯帕克斯也是另一个领域内的先驱者。1839年他被聘在哈佛大学任教席,这事那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承认历史讲授在大学中的地位。早在1861年他去世之前,他已被公认为美国历史学界中的耆宿。①参阅亚当斯(H.B.Adams),《贾雷德·斯帕克斯传》,共两卷,1893年。关于一般论述,参阅J.F.詹姆森《美国历史编纂史》,1891年;巴西特《美国历史家的中部集团》(TheMiddleGroupofAmericanHistorians),1917年;迈克尔·克劳斯《美国史学史》,1937年;《关于美国史学的马库斯·W.杰尼根论文》,哈钦森编辑,1937年;H.E.巴恩斯,《历史编纂与历史科学》。见《二十世纪美国》,纶塞克编辑,1950年。——原注②弗农山庄,在弗吉尼亚州,是华盛顿的产业。他卸任总统后,息影家园,死后安葬于此。——谭注③书名《华盛顿的生平及其著作》(TheLifeandWritingsofGeorgeWa-shington)。——谭注①书名《美国革命中的外交通信》(CorrespondenceoftheAmericanRe-volution),1830年。——谭注②莫里斯(1752—1816年),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曾任美驻法大使。属联邦派,以思想保守著称。——谭注\n①班克罗夫特标志着美国史学的成年,他最有资格担当起其民族历史家的称号。这位哈佛大学出身的青年人在拿破仑战争后平静的岁月里游历了欧洲;在柏林他聆听过黑格尔、施莱尔马赫萨维尼、博赫的讲演,在戈丁根听过黑伦的讲演,并访问过歌德。他虽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却是属于杰斐逊民主派。1826年他在7月4日纪念美国国庆的一篇演说中讲道,“人民之声对于我们便是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神谕;而这个,我们还当承认,就是上帝的纶音。”他在1835年所发表一篇题为《人民在艺术、政治与宗教上的职务》的演说,是对人民群众的另一篇颂歌。“真正的政治科学是尊重群众的,应当谦恭地听取下层人民的呼声。”他怀②着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开始了美国史的编写,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34年。“殖民地的精神自一开始起即在要求自由。美国在人类平等权利的实践与保卫方面都曾着了先鞭。”这里没有军队,没有公债,宗教是自由的。知识的传播无比普遍。在班克罗夫特所描绘的图画上见不到一点阴影,另外书中没有提到过奴隶制。在这里我们呼吸到的是杰克逊时代的那种轻快的气息。当然,对于最后造成这个完善境界前此各个世代的种种功绩也都应当受到一定的表彰。第一卷便是叙述早期的冒险航行与居留地的;并以《清教教义的性质》一章作结。在这书看来清教教义的唯一缺点即在它的不容忍态度,但这点也出于防御的考虑和带暂时性的。这些“移民祖①先”从未曾企图改变过别人的信仰,而只不过保卫其政体免受别人攻击。“这不过是像笼罩在清澄河流上的一股浓雾。”他们的法律除对已婚妇女的堕落的规定外,一般则是温和的。美国人过去能有这样一个黄金时代也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书出之后,当然受到热烈欢迎。班克罗夫特所表达的是一个新生民族的思想,同时也表现这个乐观时代的一切自足思想与饱满情绪。因为这部书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对民主政府与美国宪法的坚强信念的影响。这著作也在旧世界里引起了注意。年迈的黑伦自戈廷根写道,“我平生所感到的最大快事之一,便是我多少帮助培养了这位美国历史家。”书的第二、三卷叙完了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也②是以这同样的赞颂口气写成的。罗杰·威廉斯被称誉为宗教压迫的反对者。乔治·福克斯及其教友派的描写部分则极富感情,潘恩的名誉也得到了有力的辩护。班克罗夫特嫌恶任何形式的宗教控制;他骄傲地宣称,教士手段未曾从旧世界里迁来。在叙述迫害女巫的流行风气时,他感到遗憾;但却同时提醒读者,这种风气并未延续过久。“罪恶的自私自利性质往往会导致其自身的灭亡,支配人间的仍是上帝。”1854年他在《关于人类进步的演说》中宣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保障来自于上帝与人类同在一起。“天意决计不会不认我们这个民族。一个专制魔王的①参阅豪(Howe)夫人,《班克罗夫特的生活与信件》,2卷,1908年与奈(Nye)的《乔治·班克罗夫特》,1945年。——原注②书名《发现美洲以来的美国史》(Histor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fromtheDiscoveryoftheAmericanContinent),简称《美国史》共十卷,1834—1875年。——谭注①“移民祖先”(ThePilgrimFathers)——指1620年乘“五月花”号至美洲的一百零二名清教徒。——译者②罗杰·威廉斯(约1603—1683年),英国出生的新英格兰新教教士。因持与英国国教不同的观点,被逐出马萨诸塞州,创罗德岛殖民地。——谭注\n脚步踏毁不了一种思想。世界是不可能倒退的。”用富兰克林·詹姆森的生动语言来说,他的早期诸卷都是投的杰克逊的票。1838年,卡莱尔在感谢作者赠给他的第二卷时写道,“书的某些部分使我联想起约翰·穆勒的《瑞士史》,一本见解最为大胆的书。但你的理论方面使我感到不够满意,你的说教气味太浓了些。”虽然卡莱尔不是一位什么反对说教性历史的人,但这个批评却是很有道理的。书中的哲学思想是幼稚的;那些在五六十年前曾赢得赞扬的品质,到了现在已成为非常不合乎近代胃口的东西。但这本书却具有坚实的价值,而且越到后面越有价值。美国人往往以能向这位民族历史家提供他们个人回忆与家庭信件而引以为荣。他自己到柏林查阅过普鲁士外交部的档案。帕斯夸尔·德加扬戈斯帮他在西班牙查档案,另外他的友人与助手帮他在海牙、巴黎与维也纳等地替他做搜寻资料工作。在十二年的政治生活与在伦敦大使馆的工作之后,他复于1852年出版了第四卷。在整个十年中,前三卷叙述至1748年,而后七卷则叙述美洲殖民地与英国的争执与独立国家的创立。书中他对英国的政策的批评是严峻的。他说,“1774①年的惩治法令瓦解了两国之间的精神联系。大不列颠对人类自由进行了挑战。自由在欧洲与在英国本身都受到了威胁。而举兵起义则是殖民地对全人类的进步的有力维护。”英国本应当让美国独立的,因为她那强壮的子孙已经成年。这是一场残酷与违反自然的战争,不过这事的后果对两国都很有利。随着和约的签订,英国也抛弃了自己的凶恶作风。而美国方面则能够对英国政府与英国人民有所区别。它对于母国的敬爱依然存在。一个民族在没有社会动乱的情况下竟诞生出来。《独立宣言》,亦即杰斐逊的那篇不朽之作,表达了正义与公道的永恒原则。上帝的援助是自始至终可以看到的。书中与英冲突的部分带有一般爱国主义历史著作的通常缺点。那种把殖民地居民说成是个个满腔神圣火焰,誓死捍卫自由的描绘不过是一种梦幻。当时殖民地居民对这场斗争的热情实际上是如何微薄,一些无聊的嫉忌心理是如何常见,甚至整个这番事业曾经如何濒于失败,这一切都只好留待下一代人去叙述了。那些效忠于英国的人不过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书中对法国的帮助未曾给予足够的肯定,而德国义勇军的作用却得到了过分高抬。另外书的注意力过分局限于新英格兰一地。因而后面诸卷遂引起了尖锐的争辩。一些在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者的后裔乃出书揭露该书对待他们的祖先不够公平。虽然作者曾作了种种有力答辩,但不少的批评意见却是正确的。这部书颇有叙述支蔓,偏重词藻与故作精炼的缺点。为了要叙述德国人的帮助,他竟一下追溯到“民族大移动”的时代。连篇累牍的陈腐议论妨碍了叙述的正常进行。卡莱尔对他说,对于人所熟知的事情的起源,他每每论述得过多。这部著作虽然一直迟至1874年时才全部完成,但始终不脱其初期的种种特征。杰克逊依旧是他最心爱的政治家。当班克罗夫特以驻柏林公使衔再去德国时,兰克曾问他道,“你知道我在上课时怎样对学生谈到你吗?我对他们说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他听了这句内①指英政府颁布的封闭波士顿海港,取消马萨诸塞自治条例、新驻营条例、司法权条例和魁北克条例等五项法令。——谭注\n藏批评的表面恭维稍稍吃了一惊,然后说道,如果他的书中有着民主思想,那主要由于题材,而不由于这历史著作者。但尽管在见解与编写上有这种种缺点,这部书却不失为一项卓越的成就。这是关于美国殖民时代历史的第一部详尽系统的叙述。书中载有从新旧大陆公私档案所搜来的巨量原始资料。他认识约翰·亚当斯、麦迪逊以及其他许多历史的创造者。冯·霍尔斯特曾说,“每个美国历史家必须以班克罗夫特为起点来前进”。后面诸卷在编写技术方面有所改进。编写的速度减慢了些,搜索的范围更广了些,摇旗呐喊的喧闹声也稍小了些。美国人通过痛苦的经验得知,新世界也未能把旧世界的一切艰难与缺陷完全避掉。①1882年时班克罗夫特以八十有二的高龄续成论述美国宪法的形成二卷。这是他多年的宿愿至此终于得偿。为此目的,他走遍了十三州大部分档案馆,研究了奥、荷、法、英各国公使的报告。此书对华盛顿的②伟大善良赞颂不衰。麦迪逊被誉为宪法的总设计师,但对汉密尔顿的评价则未能恰如其分。他检视了宪法,觉得确实很好——对秩序好,对自由好,对每个公民的个性好,无异是力量与灵活的奇异混合物。这部论著最后对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形势作了简要对照,前者仍呻吟于虐政之下与处在革命的前夜,后者已进入了理想之乡。“在美国,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亲王,没有贵族的新民族已经崛起。他们比以前任何一个共和国的人们都更笃信宗教、更有教育,更加纯洁和具有更加宁静的心智。在他们生存的幸福初期,他们便把公理认作自己的行动指南。”班克罗夫特的这种把清教式的美国理想化的作法在帕尔弗雷身上又得到了重复,他所编写的《新英格兰史》叙述至独立战争爆发时止。由于他对殖民地居民的敬仰过甚,对他们为政治自由所作出的功绩感戴过深,因而势必对问题缺乏分析。他虽尚未为不宽容的态度喝采,但总是尽量为之开脱。他曾深入挖掘过英国的档案;他以前历史家谁也没有这样细密地研究过新老英格兰清教时代紧张时期的相互关系。虽然他声望不如班克罗夫特,但却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詹姆逊曾声称他的书是整个殖民时期的一部唯一佳作。另一位历史家希尔德雷思则使用了较多的批判性方法,他的写作时间虽早于帕尔弗雷,但在精神上却属于下一个世代。他编写《美国史》的明确目的即在减少那种已被班克罗夫特弄成风气的歌功颂德作法。希尔德雷思告诉他的读者说,他的目的在于提供“我们祖先的不加修饰的画像”。这种试验的结果见之于书的第二版的序言。“我对于这个充满着神话式的纯洁与德行的地域与黄金时代的揭破,已大大开罪于人,特别是新英格兰人。”他大胆地宣称,1789年前的时期大半属于神话的领域;他那充满怀疑主义的著作正象一股凛冽的北风,吹散了①许多爱国主义的传说。例如,在班克罗夫特看来,萨伦巫术案至多仅是一件令人遗憾的失误而已,但希尔德雷思则在无情地缕续了这个事件之后,宣称这乃是足以判定这个社会无异一个野蛮社会之无可争辩的证①书名:《美国宪法形成史》共二卷。——译者②麦迪逊(Madison,J.1751—1836年),法学家,历任大陆会议代表,制宪会议成员,对宪法中的中央政府结构与权力的规定,提出了方案,主张建立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1807—1817年任总统。——谭注①萨伦(Salem)——美国马萨堵塞州海港,在17世纪后期为“巫术狂”的中心;那里在1692年有十九个妖巫被处死刑。——译者\n据。他著作的第二部分叙至1821年,在这里,他开辟了前人未历之境,开始对早期的各届总统提出了批判性的评述。美国的历史学家,正如美国政治家那样,是分为联邦派与民主派的。班克罗夫特的英雄是杰斐逊,但杰氏在希尔德雷思看来不过是一个群众煽动家罢了;他宁可去爱好汉密尔顿,同时也沾染上了他后者轻视一般人的观点。他很少去查阅官方或私人收藏的资料,他的文笔拙劣,但是他那种比较实际的叙述方法则对美国人是一个教育,即是,他们也必须以其他国家那种同样的批判精神来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关于美国历史的科学性的探索研究则是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内才开始的。美洲殖民的最早权威记述为哈佛大学著名的图书馆长贾斯廷·温泽所主编的一部集体著作;这部《叙述与批判的美国史》首卷叙述了美洲本地土著,以下各卷追述了欧洲人的探险与移殖过程,最后以美国的建立终篇。其中关于资料来源的批判性论文、详尽的注释以及所附插图与地图等等都使这部著作获得某种独特的重要性。出于主编手笔的诸章属于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本人即是早期殖民地历史与制图学方面的专家。其次马卡姆叙述了比萨罗征服秘鲁的经过与南美洲的解放。但另方面,书中对英国殖民在与其母国冲突前后时期的历史,则讲得很少和缺乏系统。马卡姆著作的最后一卷杂叙了有关赫德森湾公司、北冰洋探险、英王统治下的加拿大与西班牙属美洲等问题。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叙述性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为高年级学生所编的辅导书,内容总结了百年来新大陆殖民事业的成就。另有一个不甚成功的集体合编的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富翁休伯①特·豪·班克罗夫特的提倡下所著成的巨型汇编;他也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家。他自中年时期退出出版业后,曾以大量资金从事书报手稿的购置与地方记录的抄写工作。他派了一个俄国人去阿拉斯加,又派了几个西班牙人到墨西哥,访问了老开荒人,记录了他们的回忆。他聚集了异常宏富的图书,以作为详尽研究中美与西美等地的基础。根据这些资料,洋洋三十四巨卷的《太平洋沿岸诸州史》遂在他亲自主编下由他的一批助手修成。虽然这些书由于充满文献而很有用处,但缺少历史著作的较①高的质量。它们很象贝德克尔或墨里所编写的一类指南书籍,那里作者的姓名性格都不见透露,读者在那里查到的只是图表事实。书的叙述自中美诸州开始,而后转向北方,经墨西哥、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直至俄勒冈、华盛顿、不列颠哥伦比亚与阿拉斯加。遗憾的是,这批资料上的无价之宝竟完全委之于档案保管部门。由奥斯古德与比尔执笔的殖②民时期部分还写得较具客观精神。《美国政治家》这部出色丛书包括自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至内战的结束这段时期。其中大部分书都有较高水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1912年)中曾叙述和辩护过他的文学方法。比较科甘《休伯特·豪·班克罗夫特》,1946年。——原注①贝德克尔或墨里所编的旅游向导书。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分册发行,内容包括各大洲,大国、重要地区、历史名城,介绍其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谭注②《美国政治家》,莫尔斯(J.T.Morse)主编。第一辑共三十二卷,1898—1900年出版,第二辑共八卷,1905—1917年出版。——谭注\n③平,个别书籍,尤其是卡尔·舒尔茨的《克雷传》,甚至具有经久价值。在关于早期各届总统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亨利·亚当斯所编的关于④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巨型论著。他的九卷本论著是他根据在新旧世界长期的调查研究所著成,内容清楚地叙述了美国政府在十六年多事之际的内①政外交政策。麦克马斯特所编的巨著,包括从革命到内战这个时期,也②是有用之作。但在钱宁的大型著作《美国史》出版后,班克罗夫特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已经不复有参考价值。至于离我们较近的历史最重要的为福特·罗德斯所编的‘1850年妥协以来的美国史’,内容主要叙述关于解放黑奴问题斗争的重要年代。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也憎恶黑奴制;因而对于它的取消感到喜悦;但他对那些似乎是为了维持这制度而作战的人们,却也不加责备。开首二卷描写这个风潮的酝酿过程,后面三卷叙述这个冲突本身。他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战双方都不曾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许多北方人对黑奴本不关心;而很多南方人,包括李将军在内,也同样认为黑奴制是不对的。事实上,北方是为了维持美国统一而战;南方则是为了要求分离的权利而战。作者对李将军高尚③与石壁杰克逊的勇敢所给予的赞颂之热烈,甚至有过于南方人。不仅对于这些军人,就是在对待政治家上作者也是同样毫不严苛;杰斐逊·大卫斯竟被称之为一位可敬的敌人。书中林肯的描写不愧是一篇具有判断④与观察力的杰作。林肯两位秘书尼古拉与海的包罗万象的著作于1890①年出版,但林肯的独特性格反被十大本的浩繁卷帙所淹没。罗兹的书则取消了林肯头上的光轮,不承认他具有军事天才,并婉转地纠正了一般对其智力的夸张说法。但这位总统虽有所失,也有所得。当我们看到他也在竭力抵制其自身的诱惑与在困难之中反复探索时,他反而显得更近乎人情和更加可爱了。林肯比任何人更能清楚地看到,这战争必须宣布为目的在于保卫联邦统一的战争而非为了反对蓄奴制度,并依此原则进行。如果依照了极端“取消黑奴制派”的引导,他只会给他所保护的双重原则招来灾难。罗兹原拟把自己的叙述写至1884年;那一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的当选总统一事表明,南方与北方的旧分界线业已消失。后来,③克雷(Clay,H.1777—1852年),美著名政治家,曾任参议院议员,国务卿,在南北冲突中持调和主张,力图避免内战。——谭注④亨利·亚当士编著的书为《美利坚合众国史(杰斐逊、麦迪逊总统时期)》,(Histor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uringtheadministrationofJeffersonandMadison〕),共九卷,1889—1891年。——谭注①指麦克马斯特所编的《美国人民史:从革命到内战》(Historyof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fromtherevolutiontothecivilwar),8卷,1883—1913年。——谭注②《美国史》共六卷,1905—1925年,起殖民时代止于1865年。——谭注③石壁杰克逊(1824—1863年)原名Jackson,ThomosJonathan,美国内战中南方陆军将军,骁勇善战。1861年7月21日以少敌众解庄士敦(Johnston)将军之围,获得了“石壁”(“Stonewall”)的称号。——谭注④尼古拉(Nicolay,J.G.)与海(Hay,J.)合著有《阿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ahistory)一书,共十卷。——谭注①指罗兹(J.F.Rhodes)所著:《1850年妥协以来的美国史》(HistoryoftheUnitedStatesfromtheCompromiseof1850),七卷,1895—1906年。——谭注\n当他逐渐接近于自己的目标时,他认识到,他并不需要写这么多,决定在1877年打住,因为当时最后一次围绕黑奴问题的总统竞选已告解决,最后一批军队已从南方撤出,而南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办法来处置黑人问题。最后描述重建南部时期历史的两卷也显出同样的冷静态度。他对②③安德鲁·约翰逊与布莱恩的写法比较严厉;强调指出了格兰特的无能,并认为他的统治是美国行政腐败的高潮。罗兹的著作标志着自班克罗夫④特以来美国学术研究上所迈出的行程。粗俗的得意精神与民族傲慢这里已不复见;年轻的一代已开始懂得尊重人们的某些动机,尽管这些动机所造成的行动曾受到过世人的一致谴责。Ⅱ①就在美国人开始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同时,华盛顿·欧文却把他的目光转向了旧世界。他本质上是一位四海为家的人,能够随遇而安,并容易感受各种影响。虽然他主要是一位小品文作家与幽默作家,而非历史学家,但他在美国史学史中的发展上却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文学生涯始于1809年,他假托尼克博克的名字所写的《纽约史》主要描写荷兰人在新大陆的占领,其中事实与幻想、幽默与讽刺交融在一起,书出之后,轰动了整个美国。几年之后,他乘船去到欧洲,在那里他留居了十七年。②他的《见闻杂记》的出版,其中载有《吕伯大梦》一篇,使他在新旧两个世界中都备受欢迎。他对旅行与传奇的嗜好使他于1826年去了西班③牙;两年后,他出版了《哥伦布传》书系根据纳瓦雷特所搜集的资料,加上他在马德里与塞维尔的研究结果而成。这是关于这位伟大的发现家第一部带学术性的叙述;书以作者素有的纤秀文笔写成,史学与文学的爱好者读来都能感到兴味。由于书的声誉传布极广,因而作者立即把它编成节本,以防美国的抄袭者。书中的叙述也许有些渲染过甚,但却是以诗人之笔来写梦想家的一部很好作品。翌年,欧文出版了《格拉纳达征服纪》;这部书他认为是自己的最好作品。正象他在写荷属美洲滑稽史时曾经假托过一个杜撰的古董家之口那样,这里他也编造了一位西班牙高僧来记述摩尔王国的倾覆。虽然背景尽属虚幻,却包括很多事实,复由于作者对格拉纳达知之极详,内①容赤颇充实。之后,他又续成关于红堡的《杂记》一卷,其中景物描述②安德鲁·约翰逊,林肯遇刺身死后继任美国总统(任期1865—1869年),主持重建南部的工作。执行偏袒奴隶主,图谋恢复奴隶制的政策。——谭注③布莱恩,J.G.(1830—1893年),民主党人,1863—1876年任议员,以不关心公共利益及牵涉格兰特总统不名誉案件受到弹劾。1881—1891年任国务卿。——谭注④参阅沃尔夫·豪的《罗兹》,1929年。——原注①参阅欧文(P.M.Irving),《华盛顿·欧文的生活与通讯》,共四卷,1862—1864年,和沃纳的著作,见《美国文人》,1884年。——原注②《吕伯大梦》系一虚构的故事,记一荷兰移民吕伯在卡茨启尔山小■,沉睡二十年的奇遇。——谭注③纳瓦雷特(Navarrete,1765—1844年)——西班牙航海家与作家,曾奉命搜集有关西班牙海军史的文献。——译者①红堡(Alhambra)——13世纪摩尔王在格拉纳达建造的卫城与宫殿。——译者\n与传奇轶闻纷然杂陈,使作者的幽默与情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不绝出入于这座古城之间,颇能得其地之精神,因而使他自己的姓名竟与该城造成不朽的联想。“我们只要凝神思虑一下这块美妙的住所便不能不对当年设计这座人间乐园的人们的天才和诗情深致赞美。他们确实无负于他们的美丽国土。他们不仅英勇地赢得了它,而且慷慨风雅地享用了它。在这里,智慧豪侠、彬彬有礼、诗情雅趣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我不禁要说;他们甚至是从来唯一无负于这块国土的民族,我但祝愿他们能再度从非洲渡海前来重领此地。”1832年欧文回到美国时已是一位闻人;十年后,他复被派赴马德里任公使。他原拟编写一部墨西哥征服史,但由于得知普雷斯科特业已从事此事而作罢。他晚年潜心于编写《华盛顿传》。他对于调查研究素少兴趣;因而历史学家的一番重任他有时遂力有不逮。但在轶闻与传奇的轻松文学范围内,则是无可匹敌的。作为美国文学的创始人与西班牙魅力的发现者,他的声誉也是不可动摇的。关于西班牙的历史,华盛顿·欧文不过触及了它的光耀的外表而已,①普雷斯科特才深入掘发了它的基础。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留下过一件极不愉快的回忆,这便是一次偶然事故竟使他一目失明,另一只眼也受到无可补救的损伤。于是阅读成了经常困难,甚至无法进行,但由于好学情殷,生理上的缺陷也阻挡不住。就他后来的工作来看,奇怪的是,在他大学之后长期旅欧期间并没有把去西班牙列入他的游程之内。彼时他的兴趣主要在法国与意大利文学。直到1824年他的友人蒂克诺在哈佛大学讲西班牙文学时,他的注意力才转到了那个国家,自此他的名字遂与该国密不可分。在考虑了若干历史题目之后,他决定编写斐迪南与伊萨伯拉统治时代的详史。他的财产使他有可能聚集起极其可观的资料,他还从马德里的美国公使处获得大批书籍手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都得要人读给他听,所以这部书至1837年出版时,所历时间凡十年。虽然华盛顿·欧文在他之前已撷尽史料中的菁英,普雷斯科特的卷帙较之他那位杰出的国人并不多让。他的画面更加阔大,他的学识更加深广,甚至文笔也无逊色。半岛之上各个文明间的冲突,新世界的发现,阿拉冈与卡斯提尔联合建成单一强大王国的过程,以及那里两国统治者的性格,宗教裁判所的肇始——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家借以成名的绝好题材。斐迪南在他的笔下是一位贤明而有成就的统治者,尽管他的性格冷酷自私。伊萨伯拉为全书的女主人公,在心智与感情上同样高贵,可谓一位具有男人头脑的完善妇人。她的唯一缺点是在宗教上缺乏宽容态度,但这也属于她时代的过错。普雷斯科特唯有在谈到宗教裁判所时情绪相当激昂,这种情形在他那平静的篇章里是较罕见的;但他却能对天主教完全不存偏见。他的笔下的希梅内斯虽刚愎而专制,却是一位颇具威仪的人物;哥伦布则是一位无所畏惧而又无可指责的英雄;绰号“大队长”①的贡萨尔伏,有时虽也难免使用欺骗手段,却也是个长处很多的人。除①参阅蒂克诺《普雷斯科特传》,1864年;奥格登的著作,见《美国文人》,1904年,以及佩克(Peck):《W.H.普雷斯科特传》,1905年。另一篇较好杂记,见塞科姆《秘鲁征服史》导论,《人人丛书》。比较《蒂克诺的生活、通讯与日记》共二卷,1876年。——原注①贡萨尔伏(Consalvo,diCordova1453—1515年),职业军人,初为摩尔统治者服务,后投效那不勒斯斐\n人物的详尽描写而外,这位历史家对于政事文学,风尚习俗,也给予密切注意。在撰写这部著作漫长年月里,普雷斯科特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才力来真正写好这样一个巨大题材。另外他的国人是否会对这样一部详细论述感到兴趣。但这种疑虑不久即涣然冰释。丹尼尔·韦伯斯特宣称,一颗彗星已经以其全部辉煌突然显现天际。帕斯夸尔·德·加扬戈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学者们的共同朋友,在《爱丁堡评论》发表了一篇热②情的称颂文章,而著名的《手册》作者福特也在《季刊》上著文加以赞扬。荷兰爵士称这书为自吉本以来历史著作中一部伟著。基佐与米涅也对之赞不绝口。书被译成不少国家文字,堪称美国第一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历史著作。《斐迪南与伊萨伯拉的统治时代》也是无愧于其声誉的。这书虽还够不上十分精彩,但允称作者的最为坚实之作,迄未为人胜过。以后各版中由于新资料的继续补充,书的价值也不断有所增高。尤其是1841年刊印的第三版;通过加扬戈斯的帮助,所得“天主教国王”的通讯手稿大大丰富了书的内容;这些都是在打开萨拉戈萨修道院时找到的。当然这书也不是每个部分都是无懈可击。格兰纳达复亡前阿拉伯①政体与文化那部分概述便主要是依据孔德不扎实的研究所编成。他所描②绘的伊萨伯拉形象便未免渲染过甚,虽然它比柏根洛特的那个专制伪善者形象更接近于实际情形。贾斯廷·温泽认为他对哥伦布的描写词多溢③美。另外在宗教裁判所的叙述上,他对洛伦脱过于轻信。但那个时代的著作当中却很少有哪部书能够这样不须大改便可足敷今日学者之用。从写斐迪南与伊萨伯拉到写对新世界的征服,其间只是一步之隔。普雷斯科特雇用了助手去西班牙图书馆内抄录其中有关墨西哥与秘鲁的手稿。加扬戈斯从英国博物馆寄给他不少抄本,而加尔德龙亦即西班牙驻墨西哥的公使,则从当地替他搜集文献;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文人。④书中对于蒙特祖玛的王国的一番盛大铺叙,虽不免为其人祭的残酷所掩,却为入侵历史提供了一篇出色导论。而他关于科尔特斯从海岸向内地的进军的描写构成了他笔下一节最动人的题材。这个首领的一幅威风凛凛的形象占据了舞台的整个中心。这位西班牙“征服者”虽然毫无怜悯顾惜,他们所推翻的帝国则更残酷无情。《墨西哥的征服》是普雷斯科特的最出名的著作。它不论过去现在,它一直是一切爱好冒险与传奇的老幼读者爱读的书。书中关于进军、战役与围攻都城的描写真可与麦迪南二世,一度为西班牙驱除法占领军,夺回那不勒斯。——谭注②福特(Ford,Richard,1796—1858年)——英国人,曾在西班牙长途旅行,1845年出版《西班牙旅行手册》。——译者①孔德(Conde,JoseAntonio,1765—1820年)——西班牙东方学家,著有《阿拉伯统治西班牙史》,现在历史学者对此书一般已不重视。——译者②柏根洛特(Bergenroth,GustavAdolf,1813—1869年)——出生于东普鲁士,死于马德里。以研究西班牙塞曼卡斯档案中有关英国的历史著称。——译者③洛伦脱(Llorente1756—1823年)——西班牙教士,曾任宗教裁判所要职,著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批判史》。——译者④蒙特祖玛(Montezuma1480?—1520年)——墨西哥的最后皇帝,为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ez,Herhando1485—1547年)征服,1520年饿死。——译者\n考莱的辉煌篇章比美,直接打动着每个儿童的心灵。少数批评者曾指责他对入侵者过于宽容,但这位历史家在谴责他们的行动的同时,却没有因为他们不曾走在时代的前面而对之加以呵叱。他在自己的日记簿里写道,“永不破口谩骂;这是非历史的、非哲学的与有失忠厚的。”他的特点是一般尽量少加评论。天主教人曾称颂这书对其教会的态度公允;昆西·亚当斯则认为,从书中不易看出作者是新教徒还是旧教徒,是君主派还是共和派。老作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对他的好评尤其使他感到特别愉快;他认为洪堡是“我的著作所遇到的最有资格的批评者。”华盛顿·欧文的评语也同样充满着赞美。但书中最严重的错误则不曾为人注意到。当考古学揭示了阿兹台克人墨西哥的真相后,蒙特祖玛国家的文明已证明远非如以西班牙编年史家为依据的普雷斯科特所曾想象的那样灿烂。《秘鲁的征服》也是一个缺乏吸引力的题目。皮萨罗的才具也比不上科尔特斯;而他的恶魔般的残暴行为则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地方。再如“征服者”之间的内战,也破坏了整个事件的戏剧性的统一。他悻悻然地认识到他的题材不过是次要题材,而那些匪帮的种种冲突不过是起于分赃不均。在墨西哥问题上,他的同情完全属于西班牙人一方,而在秘鲁则反对西班牙人。书中关于当地古文明的叙述是他著作中的另一特别薄弱部分,后来克莱门茨·马卡姆的调查研究证明情形完全是另①外一种样子。1842年,福特力劝普雷斯科特编写腓力二世传,认为这里“几乎是一片处女地”;这个历史家在顺利实现他的计划之前,预先搜集了大量资料。米涅为他在巴黎弄到种种文献的抄本,加扬戈斯则不仅深入到伦敦与锡曼卡斯的档案库内进行发掘,而且取得了阿尔瓦家族与其它重要家族中所珍藏案卷的阅览权利。这部著作于1849年开始编写,开首两卷①于1855年出版。对外方面,为西班牙与英国的争雄,尼德兰境内的战争、土耳其人的失败等;对内方面,摩尔族的叛乱,宗教裁判所的统治,唐卡洛的悲剧等;这一切都是足以吸引一位具有世界声望历史学家进行一试的有趣题材。由于他的死亡,书只叙述至1580年,但已完成的三卷,虽非完壁,仍然颇有可观。按腓力时代的思想来判断腓力,作者认为仍应对他给以宽恕甚至嘉许。热情的莫特利写道,“你天生具有一颗公正的心”,但他私下对他的妻子说,普雷斯科特的腓力实在未免把那个令人可憎的人物写得过分文雅高贵了。他一项突出成绩便是使这个面目狰狞的天主教统治者变得可以为人理解。在编写腓力的同时,普雷斯科特特别腾出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记述腓力父亲的晚年景况。曾经一再有人劝他编写查理五世的历史,但他认为罗伯逊的著作已十分翔实,因无重新缕叙之必要。不过,他倒愿意补记一些关于这个皇帝禅位之后的修道院生活。他从那些为他抄送的锡曼卡斯文献里早已了解了他的特点,另外利用了已见于他《腓力二世》的第一卷中许多材料;书成于1851年,但1854年才出版。在这期间,真象已为至少三位历史家揭示出来。一位锡曼卡斯的档案管理人编辑了一部①克莱门茨·马卡姆著有:《秘鲁史》(HistoryofPeru,1892年),《秘鲁的印加族人》(IncasofPeru,1910年)等书。——谭注①书名《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史》(HistoryoftheReignofPhilipⅡKingofSpain)。——译者\n有关该皇帝退隐的记事,其中附有大量档案摘要。这份手稿他死后曾为法国政府所购得,送至巴黎外交部,从此即被束之高阁,直到斯特林-马①克斯韦尔于1849年参观尤斯特后,方才用它编成《查理五世的修道院生活》出版(1852年);这部书的成功引起米涅与盖查也去追寻这个线②索。这三者的著作颇曾有助于普雷斯科特于1855年所编的纪事,但他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新的补充。另外罗伯逊的那部旧作经过这一大批新材料的增补后,也开始获得了新的生命。普雷斯科特是一位最称杰出的业余历史家之一;他的著作在19世纪中期曾培养了全世界对历史的兴趣。但是他的注意所及主要是具体生活方面而非思想方面。他具有编写庄严纪事的才干,很懂得如何选择适当的题材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但他有时不能批判地使用自己的资料,也不能像一位富于哲理思想的历史家那样,经常留意社会的演进问题。另一方面,格罗脱、麦考莱、卡莱尔、弗劳德、班克罗夫特、莫特利等往往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当成政治与宗教的宣传工具,而普雷斯科特的书中则很少带有那些英雄崇拜与党派偏见。他自居于政治生活之外,无意扮演一位先知或道德家的角色。如果说这种谨慎态度曾使他的著作缺乏活力,那么至少这些书籍也不至如一些群众口号那样不久就又过时。正当普雷斯科特长年埋头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际,他听说一个年轻的本国人正在研究尼德兰的叛乱问题。他鼓励后者继续前进,把资料借他使用并为他将出书的事作了宣扬。《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于1856年的①出版使他很感满意,因为编者终能不负所望。莫特利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正象班克罗夫特与普雷斯科特,他属于自幼早慧一流人物;还在哈佛时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已看出他的前途不凡。他在班克罗夫特任校长的一所学校里念过德文,立志要以班氏为自己今后的学习榜样。其后入戈丁根大学,与俾士麦结下终身的友谊;两人转入柏林大学后,曾经共住一室。返国后,莫特利决定写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史。“我并不是先有修史念头,然后再去四下寻觅题目。我的情形是,问题找上我来,拖住了我,甚至把我深深卷入其中。”1851年他出国赴欧洲后,便全身投入进比、荷、德等国的档案库之中。他说起过他当年在地下室内从六七种不同文字的黑字对折本中发掘材料的情景,周遭一切阴暗肮脏,简直像煤井下面那样。但他却又接着说,如果他不是因为希望能使某些人们借此变得更加良善聪明,他也决不会这么长久地在地下室中枉费苦心了。但他终于在这中间找到了一位毫无个人野心,德勇兼备的伟②大人物。足堪与华盛顿匹配。莫特利还尽量使自己对其剧中的具体场景十分谙熟。在谈到布鲁塞尔的大广场(Grandeplace)时他写道,“我常去其地,因为那里便是我的剧场,这里曾经搬演过多少人间悲剧与庄严①尤斯特(Yuste〕——西班牙的修道院,即查理五世退隐所在地。——译者②米涅著有《佩雷斯与腓力二世》(AntonioPerezetPhilippeⅡ,1845)一书。盖查(L.P.Gachard,1800—1805年),法国史学家,自1831年起供职于比利时档案馆,辑有腓力二世有关尼德兰事务的通讯集。——谭注①参阅霍姆斯,《莫特利》,1878年;《莫特利的通讯集》2卷,1889年,以及《莫特利与他的家庭:附信件》,1910年。——原注②指的是尼德兰革命的领导者奥伦治亲王威廉(沉默者威廉)。——谭注\n故事,我对这些地方久已熟识,恍如我自己也在此地弄到一分家私似的。”经过十年不间断的努力后,他的著作终于1856年以自费在伦敦刊出。正象普雷斯科特那样,这位无名作者遂也一举成名。弗劳德在《西敏寺评论》里宣称,这部书势将在历史经典著作之中占一席位,另外以描绘之生动而论,则近代史家中除卡莱尔外,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温德尔·霍姆斯甚至把他比诸鲁宾斯。在他本国内,他立刻跃居于与班克罗夫特、欧文与普雷斯科特诸大家比肩的地位。基佐曾为这书的法文译本撰过一篇导论,荷兰档案馆馆长也亲自监督荷兰文版的出版。这个题目的确是精选得来的。历史上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时刻,近代自由发展史上这样具有头等位置的一章,过去不过出之于一些文人之手。莫特利的作品,无论在其感情的炽烈与文笔的诱人等方面,都比普雷斯科特所写的东西更高出一筹。另外,这本书的写成曾根据了既广阔而深厚的研究。在业余历史家时代的产品之中,能像这样大量利用当代文献的著作,并不多见。他在写给霍姆斯的信中说,“我每天都去档案库里工作。这里我陪伴着我的蠹鱼同事们啮食着那些霉烂的桑叶,以便我们以后能吐出丝来。现在居然能够见到奥伦治·威廉、埃格蒙、亚历①②山大·法尔内斯、腓力二世、红衣主教格兰维尔等人的亲笔签名,实在是莫大的幸事。”这部著作充分表明作者不愧为本世纪中杰出的文章妙手之一。他的作品既无班克洛大的浮夸,也不像普雷斯科特那样生硬,足以代表美国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书中不少重大情节的描写,不论爱格蒙与和伦之死还是来登城的保卫战与沉默者威廉的遇刺,都无愧为英文散文中最宏伟的篇章。这位视自由为宗教的摩特莱对于自己立志要描写的斗争,往往能把全部身心投入进去。他曾对他的父亲说,他因为能够“称心如意地投入到阿尔瓦与腓力之中”而感到满意。书出之后普雷斯科特写道,“值得庆贺的是,这样一场重大革命的讲述工作,终于假我们国人之手而完成;而这场革命与我们自己的革命在许多方面都颇有类似之处。”他对荷兰人叛乱的看法是,这是一场夺取自由的斗争,一次神圣的战争,正象他那世代每个美国人看待十三州殖民地的叛乱那样。腓力是剧中的十足反派人物,阿尔瓦是他凶残的代理人;而沉默者威廉则是自由的英勇卫士,他曾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在莫特利看来,正如在弗劳德看来那样,那个以宗教裁判为其象征的天主教不过是奴隶者与顽固派的宗教;新教才是自由人的信仰。这种狂热的偏见,在半个世纪以前虽然极为自然,但在我们今天的冷静头脑看来却已变得不好接受。甚至在这部书刚才出版时,基佐已经婉转指责过它的偏颇,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新教信徒,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偏颇因为过分明显,也许不致造成不利。普雷斯科特也说他对待腓力的态度过苛了些。勒登霍夫与其他旧教的作家则把莫特利所捧上宝座的几位英雄都一一拉了下来。实际上,以弗鲁因与布洛克为首的荷兰历史家们自己在对待其先人的态度上反而比这位美国卫士还更严格一些。今天,我们仍能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地欣赏那些炽热文章,①亚历山大·法尔内斯(AlexanderFarnese1545—1592年),1579年起任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谭注②格兰维尔(Granvelle1517—1586年),西班牙红衣主教,政治家,曾任哈布斯王朝枢机大巨,1559—1564年任尼德兰总督马格丽特的首席顾问。——谭注\n但它的魔力则已无存了。莫特利的编写大纲包括自尼德兰独立战争至1648年共和国的受到承认这段时期。书的第一部分刚刚才将出版他已进入《统一的尼德兰史》的编写。“我的画面很广阔,但我却没有找到一个中心英雄人物来使这些情节具有统一性和变得有血有肉。因此我担心这部书必然要枯燥乏味和不够生动。”英国参加了这场斗争;那些联合的国家也曾使得西班牙的国力大受损伤。但起义各省区的命运始终长期悬而未决。法尔内斯是①一个可畏的仇敌,而新教徒由于失掉其可爱首领也蒙受了损失。莫里斯的将才超过他的父亲,但却缺乏政治本领与个人魅力。如果说这本书必然不如头一部那样受人欢迎,那原因倒也不在作者。他第一次探索了伊丽莎白后期的外交政策;但她的声誉并不曾因此而有所提高。此书的开首两卷在兴味方面几乎并不逊于他先前的一些著作;但三、四两卷中外交斗争占据了过分篇幅。他写道,“我说不清我的最后两卷是好是坏;我只知道这些是真实的——但这点并不意味着它们便一定有趣。”②他原希望把那部书叙述至三十年战争,因而《巴涅味特传》的编写便只能算是离题而不是一种续编。这里所叙述的不再是荷兰反对西班牙与日内瓦反对罗马的斗争,而是关于荷兰内讧的龌龊故事。他在海牙发现了巴涅味特一生最后几年期间的亲笔信件;而这些信件写得那么潦草,以致没人想去阅读它们。这项宝物的发现遂成了他这部著作的基础。他很想使这个人们很少知道的人能够见知于世,并称他为“欧洲新教的内阁总理”。但他自以为能比巴涅味特的国人〔荷兰人〕更公平地处理这个带有极大争执性的问题的信念则是错误的,因为他的英雄崇拜倾向再次使他成了一个偏见很强的人。站在单一神教信仰者的地位上,巴涅①味特当然要支持宽容主义教派(Latitudinarians)来反对喀尔文教派。而这两派中的每一派都自称是代表着民族的宗教。在七个行省中,只有②两省属于阿明尼乌教派;所以巴涅味特主张各省应有决定其正式信仰之权。当莫里斯占据了其中一个教会时,巴涅味特征集过一队雇佣兵。“执政”(statholder)获得了“三级会议”的支持,因而巴涅味特经过虚伪审讯后即遭处决。由于深信他的爱国心并同情他对铁一般的喀尔文教的憎恶,莫特利尊他为一位爱国者与殉道者;但另方面,莫里斯看来则是一个曾把他自己的无辜敌手驱上断头台的残忍武夫。他的前几本书虽然在荷兰曾受到欣喜若狂的欢迎,《巴涅味特传》则激起了尖锐的批评。格罗恩·凡·普林斯脱勒,亦即《奥伦治通讯集》③的编辑,对此曾撰写过长篇答复。这部书在基佐看来虽是一部为宗教与政治自由而作的伟大历史申辩书,但在这个喀尔文教历史家看来则是对①莫里斯(1567—1625年),沉默者威廉之子,有将才。其父死后,率军于佛兰德等地区大败西班牙军。——谭注②巴涅味特(Barneveldt,Johanvandden或Oldenbarneldt,JohnVan,1547—1619年)17世纪初与以莫理斯为首代表大贵族利益的奥伦治党对立的商人贵族政党领袖。——谭注①宽容主义教派是查理二世时出现于英国新教内部的教派。这一教派既反对高教会,也反对清教,不重正统的教义教规,故有“宽容”之称。——谭注②阿明尼乌教派是17世纪初兴起于荷兰,与喀尔文教对立的教派,后传入英国及北美英殖民地。——谭注③《那骚的莫里斯与巴涅味特》,1875年。——原注\n其民族英雄的一种侮辱。他把莫特利对喀尔文教的政治价值的所作的证明的话与其对该教的信条和哲学所说过的轻蔑论调作了一番对照。他补充说,这个单一神教信仰者没有注意到这种福音主义的宗教。巴涅味特的处死,并非是由于莫里斯而是由于一般民众,民众曾起来保卫合乎圣经的宗教以反对阿明尼乌的虚伪基督教。莫里斯只不过保卫过“归正会”①与中央政府的权威,使之免受攻击而已。他本无意将巴涅味特置之死地,虽然他很可以制止这事的发生。当然莫特利对于“执政”显然有些不够公道。但莫里斯也决不如格罗恩所说的那样无辜。布洛克认为,巴涅味特的过失来自他的刚愎自用与缺乏容忍态度,但他的处死是一宗冤狱。“双方都有罪过,但执政的一方则罪过更大。”莫特利在他最后一部书出版后的第三年上死去了。他虽没有实现其全部计划,但所作成绩之大已足使他不朽。他肯定了尼德兰反西班牙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在这件事上的认识与表达的深切程度而言,没有哪个美国历史学家能及得上他。自由乃是他的毕生热爱,此外他还使其读者体会到今天的种种文明无一不是建立在过去斗争与牺牲的基础之上的。②与普雷斯科特和莫特利那种一举成名的情形不同,帕克曼的取得名声则是经历了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正象霍姆斯所戏称之为新英格兰的婆罗门阶级的其他成员那样,他也是波士顿人和哈佛出身。上学时期他曾爱读库柏的小说。他对法英争夺北美洲问题,在大学时已感兴趣,他常利用假期去参观旧战场。1843年亦即在他二十岁时,他已开始致力于这项直到1892年始告完成的毕生之作。他访问了西北美洲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部族,曾在一个叫苏的乡村住过好多星期。他在那里的经历以后载入他的第一部书《俄勒冈记游》里面,这书虽然清新生动,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他的《庞蒂亚克的阴谋》是他进入史学界的第一部书,但运气同样不佳。在沃尔夫胜利并将法国从加拿大逐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1763年印第安人的起事。庞蒂亚克是印第安人的最后一个酋长;在他的覆灭之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帕克曼由于熟悉这些战场与幸存的部族,因而能够将其祖先的生活与制度原般再造出来。当时少数有眼光的批评家已注意到他那活泼的文风与驾驭材料的本领,而他自己也没有因为未得鼓励而中断这项自行承担的任务,但长达十年之久却曾因病重而不能进行吃力的工作。他在寄居印第安人期间曾经备尝艰苦,以致损害了他的健康;另外他的眼睛也弄得象普雷斯科特那样不大抵用。《庞蒂亚克的阴谋》对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来说仿佛只是一个附录而①不是它的一篇绪言。当沃尔夫与蒙特姆的最后斗争已是人人皆知的时候,法国人在加拿大的殖民情形外界还很不了解。他的《新世界中法国①“归正会”(ReformedChurch)——喀尔文派的教会。归正意谓新教经过宗教改革而复归于正确的基督教。——译者②参阅法纳姆,《帕克曼传》,1900年;塞奇威克的著作,见《美国文人》,1904年;韦德《弗朗西斯·帕克曼》,1942年;《季刊评论》,1897年4月,以及西孔勃《庞蒂亚克的阴谋》的导论《人人丛书》。他的日记分为两卷,于1947年出版。——原注①1759年9月沃尔夫统率的英军与梦坎姆统率的法军激战于魁北克,英军获胜,占领魁北克,为征服加拿大奠定了基础。——谭注\n的殖民先锋》记述了佛罗里达的胡格诺殖民地及其遭到西班牙人残酷消②③灭的经过,并接着叙述了卡蒂埃在圣劳伦士河的探险与尚普兰在魁北克建立殖民地等情况。两年后关于耶稣会传教士的一卷,写出了那批教士的忠诚献身精神;这些人挨受着种种难言之苦,甚至牺牲性命去帮助休伦人与易洛魁族摆脱其蛮荒状态。这位清教自由思想家对天主教传教士所作的那一番赞颂,在他的这套书中尤其令人感到激动,第三部著作①主要记叙拉·萨尔的英勇壮举,即以一条法国的堡垒线来连接加拿大与密西西比河口,借以包围英国的殖民地带。第四部叙述加拿大的旧日制②度,绘出了法国治下的一幅黑暗图景。第五部记弗隆特纳克的功业,一个个才调回出群伦的杰出总督,既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也是这位史家心目中的英雄。帕克曼现在已把这段历史叙述到了1701年,但他(这时他的年事已高)没有继续下去,而是一跃而翻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梦坎姆与沃尔夫之间的紧张斗争。两位指挥官的种种壮志豪情与这场争端的巨大规模给这个冲突带来了史诗般的特征。最后,他以《半世纪以来的冲突》一书连结了这个缺口。他的名声传播很慢;因而当菲斯克在1880年一次伦敦演讲里宣称他是美国史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对英国听众还很陌生。的确,他在其国人中间,是无出其右的。西奥图·罗斯福曾把自己的著作《西部的赢得》题献给他。“我们中间那些曾经久居边境的人们认识到,你的著作乃是所有关于新社会建立方面史学著述中的最佳典范。”哈特称他为最伟大的美国史作家。戈尔德温·史密斯则把他比之为美国的塔西陀。他的题目,虽然不如西班牙帝国或荷兰共和国那样容易引起广泛兴趣,较少动人,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序幕。殖民地当时没有力量驱走法国人;但当法国势力一旦被逐出后,殖民地便有了反抗英国的可能了。帕克曼对欧美档案的研究是深厚的。他对上演这出戏剧的那座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十分熟悉,并且能够摆脱党派偏见,虽然法属加拿大人仍认为,他对他们不够公平。他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乃是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起初虽稍偏于华丽,却变得越来越朴素和有力,他的描写文章也属于美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他的勇武气质也使他适合于描写危急惊险场面。他一生对强有力者与勇敢行动怀有敬意。他之所以能够渡过重重困难,全靠他的一副钢铁意志,读他的书时决想不到这一切竟是一个病夫所作。他痛恨懦弱,轻视“取消蓄奴制派”和不相信民主政治。他的友人及其传记作者写道,“他天然生就一副军人的脾气性格,喜欢为战斗而战斗,为战斗所唤起的毅力、勇敢与力量而战斗。”他从未曾宽恕过教友派,因为他们拒绝对印第安人作战。他曾渴望能参②卡蒂埃(Cartier,C.J.1491—1557年),法国海员,曾三次探测至劳伦斯河。——谭注③尚普兰(Champlain,S.de约1567—1635年),法国探险家,在圣劳伦斯河以南创建了殖民地——魁北克。——谭注①1679—1682年法国探险家拉·萨尔完成了从密西西比河上游至墨西哥湾入口处的探测,以法王的名义占领了河谷地区。——谭注②弗隆特纳克公爵系法属新法兰西总督,在任期间在安大略湖上建弗隆特纳克堡(1673年),频频唆使印第安人侵袭新英格兰。——谭注\n加内战,但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图书室内也尽有机会来一示他的勇敢的。在帕克曼业已搁笔不作的时候,一颗新星在史学领域冉冉升起。这即是马汉。他被聘为新港海军学院讲师后不久认识到,海权的影响从来①还未为人认真地考查过。对于海军史上若干重大方面受到忽略一事,在英国这样一个头等海军强国中尤其明显。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出版于1889年,此书开首便讨论了影响海上实力的诸种条件,如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与人口的范围、人民的特征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等等。海洋本身实即一条巨大的公路,或更正确些说,一片广阔的公地。欧洲二百多年来的历史,实际上大部分便是西方列强争夺海上控制权的斗争史。马汉从查理二世与荷兰的战争叙起,强调指出了英国商业利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所牵涉的范围;从这次战争中英国遂以地中海区的一大列强而雄视海上,并使直布罗陀海峡与马洪①②港都尽人其掌之中。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没有海军,沃尔夫的成功便不可能;因为正是这批海军才开放圣劳伦士河和阻止了法国援军的到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海权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舒瓦瑟尔曾加③强过法国的舰队,这样再联合上西班牙的舰队,其实力与英国的海军相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英王乔治三世遂未能攻下大西洋沿岸,因而也④未能有效地对付叛乱。而最后,由于德格拉塞在切萨皮克湾上的出现,而迫使约克镇不得不投降,并使英军面临崩溃。这本著作的非凡成功使书的作者继续写了下去。他的第二部著作接着于1892年出版,追述大法⑤兰西战争的历史,他认为这次战争是英国的一次商业战争。他反对麦考莱对皮特的攻击,因为作者认识到海上控制乃是问题的关键,不利局面在特拉法加海战以后业已成为过去。“那些为〔法国〕‘大陆军’所从来不予重视的远航大洋、经历风暴的军舰,现在则站列在她自己及其世界霸权之间。”大陆封锁政策原意在于毁掉英国,但它对法国所造成的损失反而更大,因为英国的枢密院命令连同作为对此命令之答复的柏林与米兰命令,大大地破坏了中立船只的运输;这事使法国受害最深,因为他最需要这些中立运输船的帮助。马汉继而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多事年代中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①身上,“一个最能总结和体现海权所包含种种可能的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由于天才与机缘的妙合而成为英国海军的具体化身。”书中所包含新①参阅泰勒,《马汉将军传》,1920年。关于他开首两部著作的一位专家评论,参阅《英国历史评论》,1893年10月。——原注①马洪港,西班牙米诺卡岛上的港口。——谭注②沃尔夫,J.(1729—1759年),英国将军。1759年9月13日在魁北克之役中战死,数月后英军击败法军,夺得魁北克。——谭注③舒瓦瑟尔,E.F.(1719—1785),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历任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在俄期间扩充海军,改革陆军。——谭注④德格拉塞(DeGrasse,1722—178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海军司令。——译者⑤书名《海权对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帝国的影响》(InfluenceofseaPoweupontheFrenchRevolutionandEmpire,1793—1812)。——谭注①此为马汉的第三部著作,书名《纳尔逊传,大不列颠海权的体现》(LifeofNelson,TheEmbodimentoftheSeaPowerofGreatBritain),1897年。——原注\n资料并不很多;它的新奇之处主要在于对纳尔逊功绩所作的论述与说明。他指出纳尔逊的长处在于他的行动的敏捷;这个并非由于临时的英明措施,而是来源于战斗前审慎考虑的结果。马汉的主要目的是要衡量一下这个人的功绩,“只消提起他的名字,便会使人不仅想起他的人格或他的事业,而且想起他的伟大力量。”但是他也要揭示这个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把他的本来面目从他的身外盛名之中分解出来。在关于纳尔②逊对待那不勒斯共和派的态度这场激烈争论中,他也为他的行动作了有力辩护。“虽然他也有着我们人类的共同弱点,但他却遗给了我们一种足以垂之永久的赤胆忠心的典范。”他第四种关于制海权影响的著作③论述了1812年的战争;这次战争起于英国在与拿破仑激烈斗争期间所推行的某些政策。这部著作由于分析了导致这场冲突的种种原因而价值极高。他指出,在英国人的眼中看来:第一英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权利强制它的侨民为其服务,不论他们住在哪里;其次英国当时所从事的斗争乃是一场生死的斗争;第三它之忽视国际法,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取得胜利。而另一方面,美国对那些有损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加以抵制,也是完全合理的。马汉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能以不同于流俗的眼光来观察某些问题。他书中包含的新材料并不很多,而其中某些专门性的讨论还会使一般读者感觉厌倦。有时他对海权的因素在某一具体结果的决定作用方面,也有强调过度之处,而对其它因素则考虑不足。他虽不是海军史的最早专家,但他却是第一个能充分认识到海军史的广大意义,并使非专业的读者也能对之感到兴趣的人。他不愧为这方面学派的创立人,因为对于制海权的研究,无论在旧世界和在新世界里,目前都正在大力开展着。另外,他的著作是不仅具有着史学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有着政治意义。他力图使美国认识到发展自己海军的重要性。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他便说明过美国独立曾经多么有赖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舰队。他在所作的法拉①格特传记里又一再提起海军在北部的胜利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他的著作对于德皇甚至比对英国政策的决策人所造成的印象还深,这点已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可说是一位历史家而兼充历史的记录者与创造者的另一著例。美国现在这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几乎主要限其自己本国。历史学家的精彩客串时代业已成为过去。现在正式学历史的人都要横渡大西洋到柏林或莱比锡去学专门技术。今天美国的历史家在回顾殖民地时代①时已不复有那种崇高非凡的感觉,同时哈奇森总督的种种高贵品质与对英效忠派的一番真诚用心,也都获得了人们的充分承认。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严峻地批评了马萨诸塞州史上“冰河期”间在宗教上出现②1798年冬法军进驻巴勒摩,至次年1月占领了整个那不勒斯。当地共和派举行起义,建立了共和国。英军登陆后,共和派战败投降。6月,纳尔逊来到该城,否定了双方和约,逮捕起义者,许多人被处死。——谭注①法拉格特(Farragut,1801—187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海军将领,有卓著战功。——译者①哈奇森(Hutchinson,Th.1711—1780年),1771—1774年任马萨诸塞州总督,效忠英国,认为英政府有权向殖民地征税。1774年离美,财产被籍没。——谭注\n②过的不容忍主义,另外对班克罗夫特与帕尔弗里的“忠孝主义”学派也很不客气。另一位史家特纳还从威斯康星的高地开始,叙述了美国中西部疆界西移与其移民的过程。如其说今日美国在世界史学上的贡献尚不如普雷斯科特、莫特利、帕克曼等人当年那样气势宏阔,那么至少令人在学术上的成果则更为坚实牢固。②帕尔弗里(Palfrey,J.G.1796—1881年),美国第一代史学家,著有《新英格兰史》(HistoryofNewEngland)五卷。其书歌颂新英格兰先辈,词多溢美,缺乏历史批判精神。——谭注\n第二十一章诸小国在大多数国家里,历史研究都是伴随着民族感情的复兴而来,但在①②波希米亚,却是历史研究创造了这种感情。1620年白山战役后开始的瘫痪状态,持续了两百年。那时,文字表达不再使用捷克语;它的地位已被德文和拉丁文所取代。在奥属地区内出版的任何书籍必须经过两道检查手续,一是代表政府,一是代表教会。教育事业掌握在耶稣会会士手里。可是,由于五个学者的努力,这个国家从长期的昏睡状态中被唤醒了。在18世纪末,杜布鲁斯基开始激发起对波希米亚文学的兴趣。科拉出版那些充满热爱斯拉夫人情感的短诗汇编,容曼编写了一部波希米亚文学史;萨法利克刊行了他的《斯拉夫古文物》。但其中最最著名的是帕拉茨基;他是最伟大斯拉夫历史家,波希米亚民族意识的倡导者。他的父母属于路德教派;他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传统精神下成长起来。他受教育于普雷斯堡,却经常宣称,他不是德意志文化的产儿。杜布鲁斯基把他介绍给那些对波希米亚历史感兴趣的贵族;这些贵族不久之前曾在布拉格建立了民族博物馆。以前,捷克人自己对这个机构很少表现热情,而奥国官吏则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它。在帕拉茨基大胆声称,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应责怪公众而应责怪主持人时,斯腾堡伯爵,即这个事业的领导人回答说,要使波希米亚民族起死回生,已为时太晚了。这个青年学者反驳说:没有人曾作过这个尝试。1828年他创办了一份该博物馆的杂志;他研究的初步成果总结在关于早期波希米亚历史家的一卷著作里。帕拉茨基在察觉到城堡档案库内储藏着丰富资料以后,就决心要以研究整个波希米亚历史作为己任。他被聘任为领薪俸的史官;虽然这项聘任在维也纳被否决,但议会得被允准支付出版费用。受到这样的①鼓励后,他开始编写他的著作;第一卷在1836年出版,叙述斯拉夫人在波希米亚的移殖。由于充满爱国的狂热,他把早期捷克人的文化和品德理想化了。在叙述到胡斯的时代,此书才表现出民族的重要地位;但那个似天启般地激动他同胞的篇章,也恰好是在维也纳引起最大愤怒的部分。在德意志和天主教的刊物上,胡斯和他的信徒被歪曲为野蛮的宗教狂信者,但帕拉茨基指出:捷克人的仇敌的残暴比捷克人更甚,他还②说明了瑞日卡和普洛科比阿的伟大。他说,胡斯在法庭上的勇敢连他的①关于诸小国近时的历史研究的最好概述,见《历史与历史家,1876—1926年》,共二卷,1927年,和《近代欧洲若干历史家》贝尔纳多特·E.施米特编辑,1942年。关于波希米亚,参阅吕差伯爵:《关于波希米亚历史家的演讲》,1905年,和《波希米亚文学史》,1899年;塞顿-华生:《捷克与斯洛伐克人的历史》,1943年,莱热:《斯拉夫研究》,卷Ⅱ,1875年;马萨利克:《帕拉茨基关于波希米亚人民的观念》,1899年。——原注②1620年11月,天主教联盟统帅梯里在白山战役中击败新教联盟领袖,捷克国王腓德烈。从此,捷克沦为德国的属地,天主教恢复了在该国的统治地位。——谭注①书名《波希米亚史》共五卷1836—1867年,布拉格版。——谭注②瑞日卡·杨(■i■ka,John约1360—1424年),捷克民族英雄,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统帅。普罗科比阿,即普罗科普(Brocop,Andrew),胡斯运动领袖、继瑞日卡任塔博尔派统帅,屡立战功,1434年5月战死。——谭注\n反对者也不得不赞佩,这一说法,曾引起检查官的挑剔。帕拉茨基宣称,“天主教会看不见勇敢,所看见的只是出于极端愚昧的傲慢和顽固”。这个历史家向维也纳提出了一个英勇的抗议。“我不相信,天主教有必要来无条件地谴责胡斯的任何行为和思想,来删除任何有利于他的情节。检查官所希望的,似乎就是这样;但我宁可丢开我的工作,放弃我的历史研究也不愿这样做”。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删去了书中的若干段落,并把检查官所增加的字句插入书中,作为出自自己的手笔。在对一个大学者这样无理强迫后不久,爆发了1848年革命。因为警察检查出版物的做法已被撤消,这个历史家又恢复了那些被删除的部分,并改掉了插入的字句。现在他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全民族的人物。他主持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会,并当选为出席维也纳制宪会议的代表。在绝对专制政治复活后,他回到他的研究岗位;但十年后,在缓和政策开始时,他被任命为终身贵族。关于法兰西斯·约瑟夫将在布拉格被加冕为王的诺言使他在晚年感到高兴,因为他未能预见到这项诺言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帕拉茨基原想把历史写到1620年这一个不幸的年分,但他终于决定只写到1526年哈布斯堡族的登位。他从天主教检查官所受到的经历已够使他感到不愉快。那个哈布斯堡族尊严保卫者会使他实际上不可能叙述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而且,他的资料浩繁,甚至按他有限的计划也需要写成十卷的篇幅。著者原是以德文写的,1848年后,它同时刊印两种文字的版本;在改订时,它的早期诸卷也译成捷克文。帕拉茨基的功绩是:重建一个国家的历史,发现并利用大量新资料,阐明中世纪中欧历史上许多模糊的地方。关于胡斯派的诸卷构成了该书的核心。赫尔斐写了一部相反的传记,但帕拉茨基的最固执的批评者是霍夫勒;霍夫勒从慕尼黑被派到布拉格来和他抗衡的。帕拉茨基轻而易举地表明:霍夫勒的著作。虽由帝国印刷局刊印,却几乎是无价值的,因为它十分缺少批①判性;他不懂捷克文,也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巴赫曼在19世纪末期也研究这同一范围的历史;他宣称,帕拉茨基的著作现已没有什么价值,但这个严厉的评断只适用于该书的第一卷。帕拉茨基误信了那些伪造的《刻尼金和夫手稿》,即9、10世纪的歌曲;这些手稿显示出一种不受条顿影响的高度的本地文化。他把斯拉夫人理想化,借以对抗德意志人对捷克文化的蔑视;他还主张,波希米亚的文明,在12和13世纪时不亚于任何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除外)。所以他的著作,不仅是一项学术上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个唤醒被压迫民族的号角,要它抬起头来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它的过去时代的。帕拉茨基的毕生的劳绩鼓励了人们阅读并编写波希米亚的历史。而②他的最著名的门生托米克毕生致力于编写布拉格的历史。他的这本著作虽在波希米亚境外不大为人所知,但是在重要性上却仅次于他老师的著作;因为这本著作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他在布拉格担任大学教授四十年之久,做过1881年创立的捷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又是一个政治家和议员;所以,他在他国家的精神生活上起过领导的作用。①《波希米亚史》,卷I,1899年。——原注②参考勒革的关于托米克的文章,见《捷克文艺复兴运动》,1911。——原注\n③他的十二卷著作在1855到1901年间出版,把历史叙述到1609年止。这部著作比起属于浪漫主义时代的帕拉茨基的著作,带有较多的批判性而较少词藻修饰。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却能描写出一幅15世纪天主教会的黑暗图景,并承认胡斯的诚实和高尚的雄心。波希米亚的第三位①著名的历史家,是安东·京德利;他不同于他的同时代的前辈:出身于一个异族通婚的家庭,能摆脱种族的偏见。他的德国父亲只能讲德语,而他的捷克母亲能讲德、捷两国语言。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叙述波②希米亚兄弟会,旨在开始深入研究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他埋头于布鲁塞尔、海牙、巴黎和锡曼卡斯的档案中。在锡曼卡斯,他找出了出乎意料的宝贵文献。他写道,“我所收集的文献,一半是完全新的,而另一半则使我们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来说明已知道的事情。我常常为此欣喜若狂。”返国后,他担任布拉格大学教授和档案馆长;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还监督波希米亚议会议事录的出版。他在回来后出版的鲁道夫③二世的统治史,阐明了历史上的一个黑暗角落。随后,他发表了关于三④十年战争的历史四卷,叙述到1623年止。这时,他突然中断,转而编写了一部关于这次战争的通俗历史;它是部分根据他为王太子鲁道夫讲授时的原稿而编成的。然后他出版了两部专著:关于瓦伦斯坦在1625到⑤1630年间的经历和关于柏特棱·卡波尔的生活。京德利是一个最公平的人。虽然他信仰天主教,但他的宗教见解是不能从他的著作中推测出来的。他揭露帝国内各新教王公在政治上的无能,他也拒绝从王朝的或教派角度对斐迪南二世的歌颂。虽然他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什么迷信的尊敬,但他认为华伦斯坦是皇帝的一个叛徒。他的德意志气质大于他的捷克气质。当布拉格大学分成为德捷两部分时,他选择了德意志分部。①几乎毫不足怪,匈牙利史学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民族自觉的热情,不仅要在马扎尔人的故事里寻求匈牙利人要求自治的理由,而且在多难之秋还可寻求力量的源泉。因此,历史学者对历史概论的注意甚于对某一问题和时期的耐心探究。直到马萨里出现,匈牙利历史学才打破了窄狭的爱国主义框框儿。他关于匈牙利人民发展史的通俗简编和关于②约瑟夫二世时代的匈牙利的较大著作,可以代表马扎尔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虽然意大利统一的概念开始于拿破仑时代,但这个国家的破碎河山却鼓励了区域史的研究:托斯卡纳人一般研究托斯卡纳史,威尼斯人研③书名《布拉格市史》。——谭注①参阅华德的文章,《英国历史评论》,1893年7月号。——原注②书名《波希米亚兄弟会史——至1609年止》,两卷,1857年。——谭注③书名《鲁道夫二世及其时代》,共两卷,1862、1865年。皇帝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1576—1612年)是天主教势力扩张和竭力排斥新教的时期。——谭注④书名《三十年战争史》,共四卷,1869—1880年。——谭注⑤柏特棱·卡波尔,特兰西瓦尼亚王公。1613—1619年间与反哈布斯堡王室的欧洲贵族结盟提高了该邦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并使该邦成为匈牙利的文化和民族感情的中心。——谭注①参阅法勒格勒,《匈牙利史学评价稿》,《历史杂志》,第XIX卷和《历史综合评论》第Ⅱ卷。——谭注②书名《匈牙利史》,1911年;《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匈牙利》第三卷,1882—1888年。——谭注\n③究威尼斯史,那不勒斯人研究西西里和南意史。在拿破仑垮台后几年时期中,最引人注意的两个历史家所写的历史著作是富有强烈的政治气味④的。在法国革命的早期,博塔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曾被逮捕,后来他追随法军充当医生。他的主要著作:《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意大利史》是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宣言。意大利被描述成外来野蛮人的牺牲者,无论过去或现在;他大声疾呼意大利应享有独立生活的权利。他曾亲眼看到过他所描写的许多场面;他的生动笔触使这部著作成为很受欢迎的①书;热烈的爱国精神还有助于在反动时期使民族观念历久不衰。科莱塔的《那不勒斯王国史》,在大法兰西战争前期中期与后期,具有更大的重要性。1798年他参加了反对法国人的战争,但他也知道波旁王朝的腐败;因此在法国革命军队入城的时候,他也不感到遗憾。他在国王约瑟夫和缪拉时期曾担任过文武要职。他参加了1820年革命,并担任陆军部长;在立宪运动被镇压后,他被禁锢于奥国。两年后,他获准在佛罗伦萨城,在那里他编写了他的这一杰作。该书是对波旁统治的一个严肃的长篇控诉状。虽然他憎恶纷乱和革命,但他说明:这种情况由于政治腐败,已成为不可避免。他对于缪拉统治的阿谀描写,使波旁复辟更显得暗淡无光。科莱塔曾被比拟为塔西佗,因为他力图再现后者的高傲的抨击。这样的一部书是不能在意大利出版的,但它的日内瓦版本却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找到了归路。在意大利,象在英国和法国一样,对过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②小说和戏剧所引起的。《许婚》于1827年出版,是根据对17世纪伦巴底的认真研究而写成的。虔诚的曼佐尼虽然有心要使教会处于有利地位,但他对当时生活和思想的描写是相当真切的。这部意大利最伟大的历史小说,是大批后来出现的小说的原型。尼科利尼在《普罗奇达的约①翰》里,颂扬了西西里晚祷事件;并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尔德》里对教廷进行攻击。属于相似类型的有:切萨雷·巴尔博的《菲耶拉莫斯卡》②和《尼科洛·德拉皮》。意大利的戏剧、小说与诗歌在1825—1850年间似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大有助于刺激民族发展的自豪心理;而这种心理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促进了认真研究意大利历史的倾向。这类著作中③的第一部,是特罗亚关于早期中世纪的汇编。这个那不勒斯学者曾长期研究卡西诺山及其他寺院的档案。他的《中世纪时代的意大利》虽然是一部卷帙浩瀚且有残缺的著作,不过它对研究意大利史的发展,却极为③参阅克罗齐,《十九世纪意大利史学史》,共两卷,1921年。——原注④参阅帕韦西奥,《卡洛·博塔》。——原注①参阅卢察尔,《论意大利的智力演进,1815—1830年》,第198—2l4页,1906年。——原注②《许婚》(IPromessiSposi)系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曼佐尼(Man-zoni,1785—1873年)的著名小说。——译者①1282年8月31日,西西里人民在巴勒摩举行了反对法国统治者的起义。这次行动以晚祷钟声作为发难的信号,故有此称。——谭注②这二部书并非切萨雷·巴尔博所作,而是另一位意大利政治活动家阿泽利奥(Azeglio)的作品。——译者③参阅马约基,《特罗亚》,1876年;德尔朱迪切,《卡洛·特罗亚》,1899年;和马克·莫尼埃,《意大利是绝地吗?》第Ⅱ章,186O年。——原注\n重要。从穆拉托里以来,没有人曾这样彻底地考查过档案;他的巨大文献汇编使编写伦巴底王国的历史有了可能性。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的任务是:纪述事实——这是一种粗浅的历史,不配与维科和赫德的著作相提并论。”这种谦逊的意图——目的既不在于哲学,也不在于艺术——并未妨碍他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显示伦巴底人是一些野蛮人和暴君,教皇则是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文明的保护人。该书指示出意大利应通过梵蒂冈以实现复兴的道路。特罗亚对历史的态度获得他的那不勒斯同乡,即有学问的卡西诺山寺院修道院院长〔托斯蒂〕的共鸣;他欢迎彭茨和蒙森,勒南和格雷戈④罗维乌斯来到他的山顶上的图书馆。托斯蒂曾以编写关于他所主持的寺院的历史而知名;他关于卜尼法斯八世的论著维护了这个著名的教皇极权论者,称之为人道和意大利的卫士。他赞扬教会是代表精神而反对暴①力;他从教廷和卫尔夫派的背后看到了民主和民族性。他在1848年出版了《伦巴底同盟》,那是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编成的。该书献给庇护九世;它表彰教皇为意大利反抗侵入者之领导人。“我以为这些篇章作②为一项神圣礼物来献给圣座。请还给我们亚历山大三世的旗帜。时机已至,人类正在等待您。”托斯蒂是属于不妥协的卫尔夫派。他认为意大利诸共和国的文明已达到为其他地方诸君主国家所不能攀登的高峰。意大利属于它的公民,而其他国家则属于它们的统治者。他以这样的思想来欢迎革命的年代,因而后来的反动时期使他深感失望。卡西诺山寺院被军队占领,寺院的住持逃去了。当法军的刺刀破坏了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短命的罗马共和国,并恢复了教皇统治时,关于教廷代表自由和独立的这个梦想,就化为泡影。③费拉里是一个才气远过托斯蒂的作家;但他们两人关于意大利历史的概念在若干方面是一致的。他于1840年离开本国;他的主要著作是用法文写的。他的《意大利革命》于1858年出版,是从西罗马帝国的倾覆到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垮台止这一时期的生动概述。他宣称,每个作家都寻找某种统一国家的原则;有些人求之于教廷,有些人求之于城市。事实上,所有争执的党派都是在不同名称下属于卫尔夫或吉伯林派的。所以,在1000—1500年间发生的七千二百次革命和七百次大屠杀,只是这两个党派间的斗争。教皇与皇帝仅仅是象征而已。他的著作暗示:意大利历史上的流血和混乱状态都是真正的好事。他肯定说,意大利人自己从未愿意以这种狂热的生活来换取宁静的生活,因为这种永恒的沸腾情况是他们创造性成就所由产生的条件。西斯蒙第悲叹他所崇拜的自由之弊病——无秩序状态,但费拉里则不然:他以玫瑰花冠戴在这种状态的头上。他的著作缺少准确性和严肃性,因而克罗齐称他的思想为非历史的;但是他却空前大胆地重新展现出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心理。④参阅勒南,《道德与批判论文》,1859年。——原注①卫尔夫派,意译为教皇派,它是12至13世纪间佛罗伦萨的大资产阶级政党,长期与吉伯林(意译为皇帝派)争权。1250年,卫尔夫派获胜,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谭注②教皇亚力山大三世(1159—1164年在位),在任期间竭力维护教会独立,多次与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和英国的亨利二世进行斗争。——谭注③参阅勒南论文《意大利革命》,见《道德与批判论文》,1859年。——原注\n①南意的最大学者是西西里的阿马里。他初期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著作内的政治低调。他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史》于1842年出版,详细地叙述了这次叛乱,但尽管它长达千余页,它的作者却是一举成名。这部著作在他生前曾刊印过八版,并译成为好几国文字。在记述法国人被逐出的时候,他和他的读者都会想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该书是一部严肃的论著,对资料的批判是非常彻底的,但它的主题和它的成功使它受到了怀疑。阿马里因此被免职,并被传唤到那不勒斯去,但他却以为巴黎较为安全。后来他回到巴勒摩,任职于1848年的临时政府,在立宪运动崩溃后,他再一次避难于国外。在流亡时期,他在巴黎各图书馆内研究阿拉伯文手稿。他的六卷《穆斯林在西西里》,是近代意大利少数突出的历史著作之一,因为它阐明中世纪时代的黑暗角落,并填补了罗马与诺曼征服时期之间的空隙。在“千人义勇军”解放西西里后,他回到他的出生的岛上,担任了几年新王国的教育部长;死时年八十三岁。南意少数分散在各处的学者在不利的情势下进行他们的研究,而在北意各邦学者们却进行了更有成果的活动。在北意第一个最著名的学者①是切萨雷·巴尔博,虽然他并不是皮得蒙学者中最渊博的。他以编写历史剧和小说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政治活动所得的结果是放逐;他寓居巴黎,用其闲暇时间编写了《意大利史》,其中两卷于1820年出版。好多年后,他自认,他从青年时代就梦想要编写自己国家的历史,但他的叙事也象特罗亚一样,只写到了伦巴底人的末期。可是,这本著作虽然几乎只是一部关于战争和侵入的编年史,它却作为第一部由意大利人所作的关于意大利早期功业的总结而受到欢迎,书中虽然缺乏更崇高的品质,但却以其洋溢的民族情绪而稍微得到补偿。1845年他为一部都灵百科全书匆忙编写的《意大利史概要》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声望。他的教训是:幸福有赖于独立地位,外族统治是民族精神的毒药。巴尔博象特罗亚和托斯蒂一样,把教会描述成民族独立的堡垒,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萨伏依王族的功绩。在其他举国知名的皮得蒙学者中间还有:斯克洛②比伯爵和科皮,前者著有意大利立法史,迄今还是必不可少的书;后者一生从事于续编穆拉托里的编年史。更重要的著作是利塔伯爵的《望①②族》,其中第一编专述斯福尔扎家族,于1819年出版。他死于1852年,在这以前,他已写完百余个名门望族的历史;其中有:维斯孔蒂族、③伊斯特族、美第奇族、贡扎加族和本蒂伏利奥族。在利塔以前,意大利的家史都是一些伪造的东西。查理·艾尔贝特因其王族先人之缺点被揭①参阅托马西尼《历史著作与批判》1891年;德棱堡《一个阿拉伯学家的小品文》;安科纳,见《阿马里》卷Ⅱ,1896年;和精装本:《阿马里诞生百周年纪念集》,1910年。——原注①参阅列梦,《同时代的人们》卷Ⅰ,1862年。——原注②参阅列梦,《传记小丛书》,1878年。——原注①斯福尔扎家族的祖先是意大利佣兵队长F.斯福尔扎与米兰大公之女结婚,于1450年夺得米兰公国的统治权。——谭注②参阅列梦,《同时代的人们》,第Ⅱ卷。——原注③继斯孔蒂家族于14世纪中叶两度统治米兰;伊斯特族,奎尔夫系的分支是15世纪长期统治费拉拉的家族,美第奇族是长期统治佛罗伦萨和托斯加纳的世家;贡扎加家族,是意大利北部的望族;本蒂伏利奥族是1462—1506年间波伦亚的实际统治者。——谭注\n露而发怒;这个历史家还受到奥国和皮得蒙的出版检查的为难。④切萨雷·坎图与巴尔博属于同一学派,即在19世纪前半期支配意大利历史学的自由天主教学派。坎图在伦巴底起着相似的作用。然而,他的影响不限于他的本省之内,因为没有人在以意大利史教导意大利人方面,写过这样多,并参加过这样多的活动。他的关于14世纪的历史小说:《马格里塔·普斯泰拉》(MargheritaPus-terla)赢得了很大声望;他关于17世纪伦巴底的论著获得过曼佐尼的帮助;这本著作原意是作为《许婚》的注释。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编写《意大利全史》;书分十二卷,叙述罗马建城到克里米亚战争止这一时期的半岛命运。关于宗教和文学、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论述使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坎图行文冗赘,见解肤浅,不能深入观察历史成长的过程,但他却具有通俗化的艺术。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几十年中,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精神上的首都。托斯卡纳政府也象其他政府一样,是反对思想自由的,但在那里的警察的活动较少,检查制度也不大严苛。19世纪中期,在他的公民中间,卡波①尼伯爵以其学识、热诚与资财,为促进意大利历史研究所做的贡献比他的任何同胞都多。象巴尔波和坎图一样,卡波尼也属于自由天主教学派。在英国时,他曾痛感巨型杂志的重要性,想望以《爱丁堡评论》作模型,创办一种意大利杂志。后来,他得维厄苏的帮助而实现了他的计划;后者是一个侨居佛罗伦萨的有文化的热那亚人。1821年《文汇》杂志开始出版;迫于检查制度,编者大体上只限于文学的论题;虽然如此,它却成为意大利学术研究的荟萃之所。二十年后,这两个人采取了一个更重要的步骤,创立了《意大利历史文库》(ArchivioSto■icoItaliano)。起初,它主要是刊印文献,但很快成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评论,并长久存在而能看到大批区域性杂志的诞生。在半个世纪时期内,卡波尼的住所是国内外学者的集会地点。他虽然是大公爵的顺民,也主张在教皇领导下实现意大利联邦计划,但他兼容并蓄,不同那些倡导更大胆的解决办法的人们进行争执。在近代意大利学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托斯加纳人梅森那斯;尽管他中年失明,却从未丧失研究的热诚。他的终身工作是:编写他出生的城市和国家的早期历史。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断断续续地编写,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即延迟出版。到1875年该书出版时,它已不能满足那个较多批判性的时代的期望了。象巴尔波和坎图一样,他也是始终显出对卫尔夫派的强烈同情。②关于威尼斯的历史,在好多年中都是从达律的著作来研究的,但当他的著作出版的时候,有两个学者正在该城内做研究工作,并打下了更①深入观察的基础。1824年,《威尼斯碑铭集》第一卷出版;奇科尼亚为此书曾长期艰苦地工作。由于这些研究成果,他的著作才胜过了达律。塞缪尔·罗马宁,特里雅斯特的一个犹太人,于1821年移居威尼斯,经④参阅塔巴里尼,《历史的批判研究》1876年。——原注①参阅列梦的精彩传记,《卡波尼》,1880年。——原注②达律,法国史学家,有《威尼斯共和国史》1819—1821年。——谭注①参阅列梦,《传记小丛书》1878年。——原注\n②过几年的探索,在1853—1861年间出版了他的根据文献编成的《威尼斯史》,全书分成十卷。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新资料,而且在于它有论断;这些论断驳倒了达律的许多指责。这两个历史家的最大分歧点,是关于这场戏的最后一幕。那个法国人〔达律〕把共和国的倾覆归咎于它的腐败,而罗马宁则认为:它只是在武力压迫下才屈服的。在意大利王国建立的同一世代或稍后一个世代的历史家中间,最著③名的是维拉里。1827年,他出生于那不勒斯,1849年移居托斯加纳,并在佛罗伦萨找到了他的终身工作。在十年期间他努力编写萨沃纳罗拉的传记;他根据对后者的著作和书信的研究,写成了第一部关于这个先④知的详细论著。他从未动摇过他的信念:即这个大布道师本质上是属于天主教的;他不愿使世界屈服于教会;他是意大利最光荣的思想家、英雄和殉道者之一。《马基雅维里传》是他们的更大的更重要的著作。1827年,麦考莱曾写道,“在马基雅维里的目的实现以后,他的坟墓和名字将受到尊敬”。这个预言应验了。维拉里作为一个统一意大利的公民,以感激的心情回顾了它的先知之一。他发现马基雅维里著作中的一贯思想是要看到国家的统一,不受外来的控制。这本传记的观点虽然不是完全新的,但它却是以挑战的姿态出现的。卡波尼在不久以前曾指责这个《君主论》作者;外国学者还侮蔑他是意大利诈术的典型。但维拉里由①于重建历史背景而有可能作出公平的论断;后来,托马西尼的学术性著作也证实了这个赞许的评断。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关于佛罗伦萨最初二百年历史的研究》,在1893年出版,并在1904年大部经过改写。该书是一组论文,以描写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作为终篇。他对自己侨居的城市之爱护热情,有时竟打破了这个学者的审慎态度。“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佛罗伦萨看来是一星电火,照耀着世界”。在19世纪意大利历史家中,只有他不仅能获得欧洲的声望,而且获得欧洲的公众。在政治领域之外,弗朗切斯科·德圣克提斯的《意大利的文学史》占得首位。19世纪西班牙产生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之所以知名,倒不是由于写得②好,而是由于选题好。洛伦托的《宗教裁判所史》具有一种揭露内幕的辛辣气味。他是马德里宗教法庭的秘书,趁波旁王朝被逐,裁判所暂停活动的时机,借助官方文献未编写它的历史。该书于1817年以法文刊行,不久,出西班牙语版,曾被译成几国文字;它增加了信奉新教的和自由的欧洲对宗教裁判所的憎恶情绪;但书中资料的引用是武断的,因而引用本书时须极其审慎。几乎同样著名的,是康突的《西班牙阿拉伯人史》。在一个关于阿拉伯文知认很少的时代,康突被认为是掌握着研究阿拉伯史的钥匙。这个历史家被约瑟·波拿巴指派为马德里图书馆长,后来同法国人一起撤退到巴黎,直到1819年才回国,然后去世。他的著作在他死后立即出版,被译成几国文字,在一个世代里一直是一部权威著作。②参阅《死者小传》(Necrologia)由波里多里作,见第10卷内。——原注③巴尔达塞罗尼,《维拉里传》,1907年。——原注④书名《萨沃纳罗拉的生平及其时代》,1859—1861年,共两卷。——谭注①托马西尼著有《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及其著作》一书。——谭注②参阅敌对的分析,见赫斐尔,《希梅内斯》第XVⅢ章,1844年。美国宗教裁判所历史家H.C.利也揭露他的滥用数字。——原注\n它的权威由于帕斯夸尔·达·加扬戈斯的精装本:《马卡里的穆罕默德王朝》的刊印而第一次受到打击。但直到1849年多泽《西班牙政治和文学史研究》出版后,它才被证明是一座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康突所知的阿拉伯文,几乎只限于字母。“他以无可比拟的厚颜,编造了几百个日期,虚构了几千个事实,而冒充它们是翻译出来的。更正这些差错,①揭破这些谎言,比清扫奥吉亚斯的牛棚还要困难”。这个伟大的荷兰阿拉伯学家在他的《研究》和后来出版的《西班牙穆斯林史》里,驱散了僧侣传说的烟雾,从而使关于中世纪西班牙的批判性的历史有可能出现。他的最轰动的成绩,是重新展现锡德的真正性质和他历尽沧桑的一生。在复辟时期的起初几年,也出现了关于西班牙君主国英雄时代的第一次认真的研究。王家历史科学院开始这个巨大工作:《未刊文献汇编》;它的出版现已超过一百卷:没有一个小国能够以这样的一种综合性著作或以这样早开始的著作而自豪。此书出版后,学者们才开始认识到锡曼②卡斯的民族档案库的重要性,并从那里汲取了许多材料。在18世纪,罗伯逊要求在那里为他的《美洲的征服》查考文献,但被拒绝;直到1843年盖夏尔才进入这个在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小村庄,抄写了腓力普二世的信件。在他之后少数外国学者也去过;他们都埋怨在那里所碰到艰苦的物质条件。柏根洛特和穆伦布勒歇尔来自德意志;京德利来自波希米亚;得·列瓦来自意大利;弗劳德和加第纳来自英国。柏根洛特在档案库花了十年光阴中最好的部分,损害了健康,并死于热病。在朝谒过这①个神殿的少数西班牙人中,有拉富恩特;他是第一部详细而又完备的西②班牙史作者。他的著作分为三十卷,在1850年到1867年间出版,赞扬西班牙君主国和教会。尽管他摈弃了旧编年史中的许多谬说,却没有充分的勇气拒绝一切谬说。他的笔调冗赘,象大多数南欧历史家一样。书中叙述的每一部分都已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被修正;该书并已被《西班③牙通史》所代替。这部通史是在卡诺瓦斯指导下由历史科学院成员编写的,于1892年开始出版。这个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是一个学识渊深的学者,他的《腓力四世》诸卷,显示出他在研究和叙述两方面的才能。这部汇编中最出名的部分,是丹维拉-科利亚多所写的关于主张改革的统治者查理三世之附有文献的著作,后者是波旁朝最好的国王。科学院所编的历史,是西班牙史学上最重要的成绩,但也出现了其④他有价值的著作。阿尔塔米拉,即英国读者所知道的《剑桥史》的一个⑤撰稿者,所写的关于西班牙文明成长的书,是以任何文字所写的书中最①奥吉亚斯(Augeas)——希腊神话中伊里斯王。他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曾清扫过牛棚。赫尔克里斯曾决河一天之内洗净它。——译者②关于这些档案的历史,有一篇很好的记载,见《历史评论》,卷XCⅥ。比较卡特赖特,《古斯塔夫·柏根洛特》,1870年。档案库现已移至塞维利亚。——原注①参阅他的《西班牙通史》,卷XXX中的详细传记。——原注②书名《西班牙通史,从远古至现代》。——谭注③此书共十八卷,1892—1899年出版。——谭注④参阅《历史综合评论》,卷Ⅵ·Ⅸ。——原注⑤书名《西班牙历史与西班牙文明》,1900—1911年。——谭注\n⑥①好的叙述。丹维拉-科利亚多撰作了关于民政权的论著;该书虽强调立法和行政方面,但它也几乎是一部西班牙史,从斐迪南和伊萨伯拉到1812②年宪法止。费南德斯·杜罗关于无敌舰队的著作,揭示了这次出征的西班牙方面的情况。西班牙近代学者中最伟大的是梅嫩德斯-佩拉约,他在五十六岁时去世,是对欧洲学术界的一个打击,他比国内外任何其他作③家更好地阐明了西班牙思想的发展。他关于西班牙异教徒的巨著,讲述了一段凄惨的故事;该书出版时,他才二十六岁。他的西班牙科学史和美学思想史以及他的无数文学论文,接触到了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佩雷斯·加尔多斯是西班牙的沃尔特·司各脱;他的历史小说是任何历史概论所不能忽略的。他的《民族历史中的插曲》叙述从特拉法加战役起的国家命运之变幻,分成四十卷;它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反拿破仑的反叛、斐第南七世的专制和卡洛斯派战争的残暴。古与今的对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葡萄牙那样鲜明,在任何国家中对过去的膜拜没有象葡萄牙那样缺乏识别力。在那里,认真的历史研究④是从1846—1849年间埃库拉诺德卡瓦略第一部著作〔《葡萄牙史》〕出版而开始的。读书四卷虽然几乎只涉及一个世纪,它很快就刊行了三版,但它不仅引起了注意,而且引起愤怒。他在序言里大胆宣称,爱国主义是历史家的一个坏顾问;他擦去了传说的镀金;至于若干古代传说,他连提也不屑一提。他表明:葡萄牙的历史并不象设想的那样英勇、光荣和独特。他由于强调摩尔人血缘的大量混入而损伤了他的同胞的最敏感之处。葡萄牙所引以自豪的少数几个学者都欢迎这部书,认为它是说明实际情况的一个忠实尝试;但许多批评家则攻击他是为外敌收买了的卖国贼,渎神者和路德教派。他尖刻地宣称,他本应该表明每一个葡萄牙人都相当于三个西班牙人,两个法国人,本应该相信那些通俗的传说和老妇的虏诚谎言。他的同胞的愚顽使他感到非常不悦,因而他未完成他的著作。在决心中止他所编的历史后,他转到另一个几乎同样容易激①动人心的题目。他关于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成立的巨著,是完全根据未曾用过的法令和信件编写的。它比洛伦特的著作虽然范围较狭,不大出名,但却是一部更坚实得多的著作。骚泽有一次曾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是一个谋财害命的机构。这项控诉经过埃库拉诺的研究而得到了证实;他称自己所叙述的故事是一出犯罪的戏剧。他这第二部著作引起了强烈的敌意,以致使这位沃尔脱·司各脱的老崇拜者转到历史小说方面去了。他的《攸立克》是关于摩尔人毁灭西哥特王国的故事;它由海涅译成德文;并以节本形式刊印了法文版。埃库拉诺虽然受到他大多数同胞的漠视,却在他的门生的忠诚和景仰中得到了一些补偿,可是没有一个门生能达到老师的水平。⑥参阅《近代欧洲若干历史家》,施密特编,第一章。——原注①书名《西班牙的民政权》,六卷,1885—1886年。——谭注②书名《卡斯提尔-阿拉贡王国联合后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共九卷,1895—1903年。——谭注③书名《西班牙异教史》,共三卷,1880—1881年。——谭注④参阅多林格尔,《科学院演讲》,卷Ⅱ,1889年,和巴克斯曼,见《历史杂志》,卷Ⅸ。——原注①书名《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与确立》共三卷。——谭注\n②在瑞士也象在葡萄牙一样,直到传说的迷雾被驱散,民族传统从属③于批判性探究时,才有可能作认真的历史研究。科普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完成了偶像破坏的工作。在卢塞恩担任历史教①师的时候,科普曾编辑供学校使用的约翰内斯·缪勒文选,他对这部“不朽”著作的热情颂赞,表明他内心中原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当他从事编写关于卢塞恩加入邦联五百周年纪念论文的时候,他的信仰才开始转变。他转到查阅档案时才发现:那些由缪勒天真地抄入他书内的楚第的故事,大部分是后来的虚构。他决心不接受任何没有早期证据的遗闻轶事。这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了瑞士历史的研究。他下一步的工作,是编辑一卷文献,在1835年出版。按照他的新说法,盖斯勒和退尔都不复出②现了。因而他使读者感到惊讶,但他的批判的洞察力使他扬名国外。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决心叙述瑞士邦联的开始。关于奥国虐政和残>暴的众所周知的故事被斥为无稽之谈;奥国人看到他对哈布斯堡·鲁德福的辩护时,感到喜悦。象这样没有爱国偏见的一个历史家,当然在国外可以得到极大的赞赏;但是魏茨和伯默尔惋惜道,这样重要的一部著作竟写得这样坏;前者是最大的中世纪史专家,后者是作者最亲密的朋友。现在瑞士人已不再是从他的著作中,而是从那些吸收了他研究成果的课本中来阅读瑞士的历史。然而,爱国精神大部分渗入了研究各个州的领域,因为那以本州自豪的心理,是每个公民的本性。在促使过去时代感兴趣的各种影响中,还有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的小说。1830年,即独立的比利时诞生那一年,开始了一个热烈的历史研究①和写作的时期。比利时的历史家一般以刊印资料,而不是以精彩叙事见长。他们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于紧要的16世纪时期。盖夏尔以其漫长生活之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的正是这个时期。盖夏尔生于法国,少年时期来到比利时;1831年被派为新王国的档案总管。他刊印了沉默者威廉与腓力二世的多卷通讯集,这使对这两大敌手的研究有了可能。虽然他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刊印资料,但他也编写了一本关于唐·卡洛斯的专著,一部18世纪比利时的历史,以及若干卷论文。刻文·德·勒登霍夫较为著名而远少批判性,他的《法兰德尔史》是在比利时出现的最大的叙述性著作之一。由于他的爱国热情,他轻率地投入了法国与城市公社之间的斗争漩涡。他的缺少判断力在他最出名的著作:《胡格诺与乞丐党》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这部著作是以好战的天主教的观点编写的,因而它把莫特利所描绘的图颠倒过来。他厌恶沉默者威廉,并辱骂他的支持者。1830年成功的反叛是朱斯特所选的研究领域。他关于“比利时君主国的开国元勋”的许多专著具有持久的价值,因为他使用了国王利奥波尔德、施托克马、凡·得·韦耶及其他有功于比利时独立的政治家的私②参阅冯·韦斯,《瑞士史学史》,1895年,和费勒,《十九世纪的瑞士史学》,1938年。——原注③鲁托尔夫,《科普传》,共三卷,1868年。——原注①参阅亨金,《约翰内斯·缪勒》,共二卷,1909—1928年。——原注②盖斯勒(Gessler,Hermann)与退尔(Tell,William)——瑞士史中的传说人物。据说盖斯勒系奥国驻瑞士的行政长官,在1307年为威廉·脱尔射死;后者被称为争取瑞士独立反对奥国统治的民族英雄。——译者①参阅波特文,《比利时文学史》,卷Ⅳ,1882年,和《比利时全国传记集》。——原注\n人文件。在最近一个世代里,还兴起了一个使用法、德大学的专门方法的历史学派。由于这两个世代的认真研究,比利时最著名的历史家比伦②才能编写出关于他国家的批判性的历史。①格劳秀斯和荷夫特的国家〔荷兰〕密切地注意它的光荣历史。盖夏尔在比利时所占的地位,在荷兰则是由格罗恩·凡·普林斯脱占据。他②毕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刊印1688年前的奥伦治家族的档案。他是加尔文派教徒,王朝的热诚拥护者,因此他的论断不无可议之处,但他的导论③④和说明,确是对历史的一个真正的贡献。弗莱因的声望更大;他是兰克的一个缩影;如果他曾编写过大部头著作,他的声誊会流传得更广;但大著作是否会象他源源不断出版的那些收录他研究成果的专著那样有⑤用,还值得怀疑。他的最著名著作:《八十年战争的十年时期》(1588—1598年),于1857年出版,使他获得了莱登大学荷兰史教授的位置。他叙述的是沉默者威廉死后的关键时期。无论在学识、论断或文采方面,它都被认为是荷兰最完善的历史著作。他的论文和研究报告集十卷,主要涉及16和17世纪,是研究荷兰史上光荣时期的最可信的指南。弗莱因在莱登大学的接班人,是他的门生布洛克;后者的《荷兰人民史》提供了第一部关于民族发展的综合而又有批判性的概述。它在民族历史方面立即取得了地位,并享有译成英文、德文的荣誉。荷兰民族生活的各方面——政治和社会、宗教和文学、工业和商业——都受到注意,作者还不时停下来纵览全面形势。书的最后一卷是描述18和19世纪的,它为近代史上很少为人所知的一章提供了可喜的图景。赫鲁恩·范·普林斯特勒尔在前一世代所树立的榜样,由雅比克斯和科伦布兰德继承;他们刊印了关于奥伦治家族后期历史的多卷集资料。①丹麦历史研究的创始人是阿伦,即第一部丹麦近代史的作者,这部著作的法文译本曾长期是外国学者的独一无二的指导书。他的《北欧三王国史,1497—1536年》,虽然内容仅是总结已知的事实,却是他长期探索的成果。服索厄选择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史作为题目。从丹麦的②太古时代起,他追述了诺曼人到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过程,继之,③他概述了丹麦对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征服。他的著作译成为英文和德文,②书名《比利时史》(HistoiredeBelgique)共六卷,1900—1926年。——谭注①参阅布洛克的杂记《荷兰的历史编纂》,1924年。——原注②书名《奥伦治-奈梭亲王未刊书信档案》,共二十七卷,1835—1917年。——谭注③参阅马开,《荷兰的宗教思想》,第一讲,1911年。——原注④参阅布洛克的颂赞,《宣传研究》(VerspreideStudien),1903年和拉克法尔,《历史杂志》,卷XCVⅢ。——原注⑤“八十年”,指自1568年尼德兰革命爆发至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西班牙承认“联省共和国”这段时期。“十年”指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舰为英国击溃至1598年。西班牙对法国胡格诺战争干涉最后失败。——谭注①参阅斯腾斯特鲁普,《十九世纪丹麦的历史编纂》,1889年,和乔根生,《十九世纪丹麦的历史研究》,1943年。——原注②英译本书名《记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AccountoftheDanesandNorwegiansinEngland,ScotlandandIreland)。——谭注③英译本书名《丹麦人征服英格兰、诺曼底史》(TheDanishConquestofEnglandandNormandy)。——谭注\n在一个世代里是北欧海盗的主要知识来源;由于插图丰富,它引起了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研究的兴趣。斯腾斯特鲁普在他的基础上,但使用了较多批判的方法,编写了关于诺曼人的巨著;它的后面各卷显示出,斯堪的纳维亚影响在英国的遗迹比一般曾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关于丹麦人④的历史,现在可以阅读在1897年开始出版的那部集体著作,其中有斯腾斯特鲁普、弗里德里希、欧斯拉夫、爱德华·霍尔姆及其他宿学之士的撰稿。①瑞典历史研究的创始人是盖吉尔;他是教授、诗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83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他国家的通史。该书略述中世纪时②期后,就放宽幅度来描写古斯塔夫·瓦萨,而后详细讲述古斯塔夫·阿③尔道夫的事业;并以他的女儿克立斯提那的退位结束。这部著作成为一个全民族的财富,译成为好几国文字。后来他的门生卡尔逊继续编写;④加上了第5、6卷,但在完成查理十二统治史以前即死去。弗律克塞尔,即瑞典的弗赖塔赫,由于编写《瑞典史故事》而使历史研究通俗化,在这方面,他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作家为多。该书于1823年开始出版,第46卷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完成。虽然这部著作越到后面学术性越强,但它始终没有达到高度的学术水平。在活着的瑞典学者中间,没有人在重要性和影响上能与哈罗德·赫耶纳相提并论;他现任乌普萨拉大学的盖吉尔和卡尔逊讲座教授。近代第一个挪威历史家,是鲁德福·凯塞尔;他的著作以及他在克立斯提尼亚大学的演讲引起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古代和中世纪史的兴趣。他最杰出的门生明希曾帮助他的老师刊印挪威古法律,他本人也挖掘出大量资料。明希的主要著作是《1397年与丹麦联合前的诺曼人民史》八卷集;该书是挪威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巨著;其中对社会和文化的注意不少于对战争和政略。他的研究也不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他是在罗马城研究文献手稿时死去的。他是条顿语言学专家;格林也承认他的才识;他关于语言、神话学和历史的演讲引起了对诺曼文明的广泛兴趣。亚历山大·巴格所选的研究领域是关于“北欧海盗”活动的时代;萨斯批判地论述了在丹麦统治下挪威历史的屈辱时期。①②俄国第一个本民族的历史家是卡兰姆津。在叶卡特琳娜和保罗时代,他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有一些世界主义的倾向,但后来他认为俄国是独立于并优越于西方国家的另一个世界。他在这种“斯拉夫本位主义”(“斯拉夫派”)的精神下着手工作,少谈它的野蛮状况,并在他的叙述中加上了幻想的浓墨重彩。他未来著作的基本论点已在一篇《古④书名《丹麦王国史》,共八卷,1897—1907年。——谭注①参阅尼尔逊,《盖吉尔》(ErikGeijer)1902年。——原注②古斯塔夫·瓦萨即古斯塔夫一世。在位期间(1523—1560)加强王权,支持宗教改革,宣布王位世垄。——谭注③克立斯提那于1654年退位,查理十世,古斯塔夫嗣立。——谭注④盖吉尔与卡尔逊编写的通史,名《瑞典史》,共七卷,1832—1908年。——谭注①关于卡兰姆津的评论,见赖因霍尔德和瓦利舍夫斯基编的《俄国文学史》和培品,《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思想运动》,第4章,1894年。马佐尔,《近代俄国史学大纲(1939年)是最好的概论。——原注②以前译喀德林。——译者\n代与近代俄国》论文里提出;他赞扬专政原则而攻击立宪理论。有种种原因促使他的庇护人亚历山大一世放弃自由主义,并导致斯彼兰斯基的③④倾覆。这本书也是原因之一。《俄罗斯国家史》,分为十二卷,在1816到1829年间出版。他把俄罗斯早期的一些国王描写成专制统治者,而把那个使俄国人摆脱鞑靼统治的伊凡三世说成是理想的君主。他的书一直被称为专制政治的史诗。教会是王座的砥柱。“信仰是国家的基本力量之一”。普希金把这第一个史官说成是古俄罗斯的哥伦布,索洛维约夫称赞该书是雄壮的诗篇。的确,他是在几乎没有海图的洋面上航行,但无论在学术性和论断方面,他都没有达到高水平。他文字优美,但缺乏批判能力;他接受权威而不予鉴别,对人民的生活很少注意。①俄国第二个鼎鼎大名的史家是索洛维约夫。他使卡兰姆津的著作被束诸高阁。他的〔《俄国通史》〕第一卷于1851年出版;以后每年出版一卷。1879年他死时,第29卷已几乎准备付印。卡兰姆津叙述到1611年,索洛维约夫则叙述到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代。他仔细探究档案;他的著作是对于已有知识的一项总结,也是它的一项增补。虽然他充满尊重古代的浓厚情感,但他认为俄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是自然而又值得称赞的。在答复卡特柯夫和莫斯科“斯拉夫派”的文章里,他主张:俄国人是欧洲人;没有什么欧洲的东西对他们是陌生的。他强调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必要的;并表明这项改革怎样自然地从过去演变而来的。他能够理解并同情自由派和“斯拉夫派”的理想,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还把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考虑在内。他的俄国史简编负有盛名,该书只有一册,于1859年出版。它的法文译本使外国人能估计它的作者的成绩。老一辈的历史家们被克柳切夫斯基代替了;他是俄国最大的历史家,在莫斯科多年从事卓有成效的活动后,他被说服修改并出版了他②的讲义。他不想在详述政治和战争方面同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较量短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外交;他擅长于叙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还有大量的资料从公共档案以及伏朗佐夫和其他大家族的档案中涌现出①来。得·马腾斯花费了四十年时间来编辑俄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从而使编写俄国外交史成为可能。很少有人利用这样积累起来的资料来编写综合性的著作,这部分地是由于实施出版检查条律的缘故。瓦利舍夫斯②基关于帝王(从伊凡雷帝到保罗)的精彩传记获得了欧洲的读者。比耳巴索夫原来打算编写十二卷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著作;但其中大部分被砍掉了,那是检查条律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失。这部著作除了它的大量参考书目外,迄今还是手抄本。赫鲁晓夫斯基用乌克兰文编写了乌克兰③斯彼兰斯基,米·米·(1772—1836年),于1808年后受沙皇亚历山大之命,草拟改革方案计划实施立宪,并限制地主对农民的专横统治,遭到大农奴主反对,于1812年被流放。——谭注④此书只出版了十一卷,其笔十二卷因作者逝世,未能完成。——谭注①参阅克利尔的献辞,见《历史杂志》,卷XLV。——原注②书名《俄国史教程》,共五卷,1904—1922年。——谭注现有英文译本,分为五卷。参阅《近代欧洲若干历史家》,施密特编,第9章。——原注①马腾斯辑有《俄罗斯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汇编》共15卷,圣彼得堡,1874—1909年。——谭注②瓦利舍夫斯基撰有:《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共二卷、《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奇》共二卷、《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代》,共三卷,均有法、英文译本。——谭注\n③史的巨著;这部著作类似帕拉茨基的波希米亚史。俄国的历史研究还由于驱逐或流放著名学者而遭受了损害。维诺格拉多夫避难于牛津。米留④科夫,研究俄国文化的自由派历史家,在被剥夺他的教授位置后,参加了政治活动。沙皇统治下阴沉的蒙昧主义高压在历史研究之上,正象它压着民族生活的其他各个部门那样。波兰历史家,象波希米亚历史家那样,是在屈从外国政权检查律的限制下进行写作的。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可以用勒勒威尔的经历作为例⑤证。在维尔纳任历史教授时,他已鼓起他的学生的爱国热情,因而在取缔秘密结社时他失去他的职位。1830年革命爆发后,他当选为民族政府的一个成员。革命失败后,他逃亡巴黎,再转到布鲁塞尔,在那里消磨了他最后的三十年生活。他的《中世纪的波兰》不足之处在未能看到档案;这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在早期波兰史中所看到的人民的影响比它们实际存在的要多。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学识和爱国精神在他的故国仍被人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纪念着。密茨凯维支的诗①篇,克拉舍夫斯基和显克维支的爱国小说,则比任何学究气的历史家都更有力地唤醒了民族的兴趣。除了在波希米亚外,历史研究没有比在希腊产生过更大的影响。在逐出土耳其人后,希腊仍处于穷苦和愚昧的状态中;因而有教养的希腊人只能以追念它的古典文明作为慰藉。但正在这个解放的时候,有一个巴伐利亚人叫法尔麦拉耶,否认了希腊人的人种继续性,从而使学术界深感惊讶:他宣称,近代“希腊人”实际上是斯拉夫人。希腊人痛恨这项攻击性的论断;他们欣然看到霍普夫、芬莱、辛开森和赫茨堡对他这种怪论的反驳。帕派里哥波洛斯以希腊生活的无间断的连续性作为他的著作的论旨。1837年当雅典大学创立时,他由于答复法尔麦拉耶的文章及其他历史论文而获得了希腊史教授的位置。在1865—1876年间,他出②版了他的〔希腊〕历史,其中包括了他毕生研究的成果。象其他“民族性”历史著作那样,它具有一种申辩书的缺点,即强调希腊人的文化和英雄主义,而夸大其压迫者的罪恶。在他的简明的《希腊文明史》中,他重申自己的主张;该书的希腊文版和法文版于1878年同时出版。他宣称,外国学者几乎不能认识到近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西欧过去使希腊受了委屈,现在它必须帮助这个小国合并所有希腊血统占优势的地区。希腊的学生和教师们对他们国家的史诗的传统,都③书名《乌克兰民族史》8卷,1898—1917年。——谭注④米留柯夫,巴·尼·(1859—1943年),俄国史学家,立宪民主党首领。流亡国外后出版有《俄国史》,共三卷,(1932—1933),《俄罗斯文化大纲》,共三卷,1942等书。——谭注⑤参阅尼采曼,《波兰文学史》;摩斐尔,《波兰》,章XⅢ,和腾平斯基、哈勒基和汉德尔斯曼,《波兰史学》,1933年。——原注①密茨凯维支(1798—1855年),波兰革命家,诗人。所作叙事长诗《塔杜施先生》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年),波兰小说家、历史家,著有历史小说及研究波兰古文化的论文。显克维支(1846—1916年),波兰爱国志士、文学家,其代表作是描写17世纪波兰人民反异族侵略斗争的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谭注②书名《从远古至现代希腊人民史》,共五卷。——谭注\n①是充满热情的。比克拉斯宣称,“现在希腊人所具有的无论在形体或智慧方面完全属于希腊性质的特征,都是我们民族的活力强度的一个光荣②证据”。在青年一代希腊作家中,没有人能象安德雷亚德斯那样闻名于西方世界;他是东南欧财政经济史的主要权威。在罗马尼亚,研究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家若加,是无与伦比的。在巴尔干国家中,近百年来的战争和革命造成了不利于安静的教学和研究的环境。①《关于基督教希腊的七篇论文》,1890年。——原注②安德雷亚德斯(Andrèadès,A.M.1876—1935年)的代表作有《希腊经济发展史》、《英国银行史》等。——谭注\n第二十二章古代东方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纪录的历史的发轫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是走向基①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据有纪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Ⅰ古埃及遗迹的发现,开始于1798年拿破仑的远征。对这个古国一知半解,来自它分散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方尖碑和木乃伊,以及游记中所引述的事情;但对于它的生活和艺术、宗教和科学的兴趣却早已丧失。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卷帙里,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更重要得多的是:一个法国军官在尼罗河口罗塞塔为造工事而挖坑时发现的一块损坏了的石板;这块石板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就是罗塞塔石碑,①铭文内有公元前197年的一项关于赐给显赫者托勒密以荣典的祭司令,②用希腊文、埃及圣书体[正体字]和民书体[俗体字]写成,提供了一把理解古埃及历史和文明的钥匙。但是谁能用它来开锁呢?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和瑞典人阿刻布拉德首先进行这项研究;他们猜出了俗体字中的几个字母,并认明在两种碑文中有似乎相当于专名的几组单字。他们认为,铭文不会完全是象形文字,因为一个外来的专名不能以一个形象来指示;但他们拈出了专名而不能确定它们的组成部分。另一次较成功的尝试是由托马斯·杨,即光线波动说的创始人所作出的;他认出了那些相当于n、f、p、t、i的音符。用马斯伯乐的话说,杨看到了乐园的景色,但从未走进那里。③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在学术史上谁也不象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象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①参阅达姆斯特泰尔:《法国的东方研究》,见他的《关于东方论文》,1883年;霍格思:《资料与考古学》,1899年;希尔普勒希特:《圣经地区的探索》1903年;《剑桥古代史》,卷Ⅰ,第3、4章,1923年;凯尼恩:《圣经与考古学》,1940年;法因根:《来自东方的光明》,1946年;西兰:《众神、坟墓与学者》,1949年;丹尼尔:《考古学的百年》,1950年。沃利斯·巴奇《尼罗河与底格里斯河畔》,1920年;舍斯:《回忆录》,1923年以及皮特里:《考古学的七十年》,1931年,都是有用的。——原注①显赫者托勒密(PtolemyEpiphanes,约公元前210—181年)——埃及王托勒密五世(在位期约公元前203—181年),——他免除僧侣团体的捐税,因而祭司为之立碑颂扬。——译者②埃及圣书字(Hieroglyphics)——通译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有三种字体:圣书体(正体)、祭司体(草体)、民用字(俗体)。圣书体多半用在碑铭上,祭司体多半写在草纸上。圣书体起源最早,民用字最为晚出。三体之名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译者③参阅哈特尔本的《大传记》,共2卷,1906年。——原注\n①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②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③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④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⑤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⑥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杨贬低他的劲敌的成绩,但商博良却能毫无困难地指出,他的字母除了5个符号外都是错的。西尔韦斯特·德·萨西赞赏他的门生的成功,但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轻蔑的攻击却成了最高的颂赞;因为商博良1822年的《给达西埃的信》和1824年的《圣书字体系纲要》所宣布的发现,似乎是出乎人力之外的。他被聘为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但1826年他回到巴黎,担任埃及博物馆保管人。当时,他已研究过宝贵的都灵纸草卷;这纸草卷列举了埃及国王的名字,直到拉美西斯二世1828年,在法国和托斯卡纳政府支持下,他和洛塞利尼同到埃及游览。这次游览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但1829年当他回到巴黎时,已经为他设立埃及考古学讲座。他只发表了他的就职讲演,于1831年死去,年四十一岁。商博良在使古代东方重现于近代世界方面,作出了最伟大而又最早的成绩。他的《埃及古迹》即他旅行的成果,在他死后出版;接着又出版了他的《埃及文文法》和《埃及圣书字字典》。他的最高功绩是译解了圣书字。他没有完全掌握埃及俗体字;这一个难关最后是由布鲁格希攻破的;掌握这种知识并不是迫不及待,因为埃及最重要的铭文都是用圣书字写的。①科普特,原意为阿拉伯人对埃及原有居民的称谓,后来指信仰科普特派的基督教徒。科普特文采用希腊字母,但吸收了六、七个埃及民用体字为希腊文之“埃及”变体,一般用于宗教仪式。——谭注②柏勒奈西(公元前28?—70年),犹太女王。——谭注③克娄奥巴特拉(公元前63—30年),古埃及女王,以其美艳博得恺撒与安东尼之欢心得拯救其国。克死后,埃及乃为罗马所灭。——谭注④花边(cartouche)——(埃及)王及神的名字周围所加之轮形(常用于纪念碑上)。——译者⑤埃西斯,古埃及主神之一,丰收女神。具有很大的神通,法老被认为是她的儿子。——谭注⑥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事业。——译者\n①莱普西乌斯在埃及学上又跨进了一大步。从戈特弗里德·赫尔曼学习了正确的方法后,他进入戈丁根大学内奥特弗里德·缪勒的学术讨论班,决定研习语言学的考古方面,而不学文法方面。他觉得需要了解整个古代,所以去听黑伦、埃瓦尔德、博赫和博普的讲课。他的博士论文①的选题是《攸古比铜牌》(EugubianTablets);就是15世纪在谷俾奥地窖中所找出的七块铜牌。铜牌上的铭文原是一种意大利语的最古文献,所以它们使解释翁布里亚人语言有了可能,并阐明了他们的仪式和宗教。这些铭文已由奥特弗里德·缪勒在关于埃特鲁斯坎人的著作里分析过;正是由于这个可爱的老师,莱普西乌斯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那里。他使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缪勒达到的水平;他证明了他对释解未知语言的本领。在巴黎一年,他完成了他的学生生活,在那里他听过勒特伦的讲课;后者对商博良的许多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他被本森邀请到意大利去,本森希望他研究埃及语言。在接受邀请之前,他决定考查一下商博良的著作是否建造在坚实的基础上。他考查的结果是使他满意的;他突然悟到在埃及学方面大有可为。他先学习科普特文,然后钻研埃及俗体字和圣书字。本森和洪堡象父亲般地关心他,并从柏林科学院为他领到了一笔补助金。罗塞利尼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送给他;他还被准许查阅商博良的手稿。在遍查巴黎的资料后,他去查都灵的珍藏,首先是关于埃及国王名表的纸草卷。本森相信,他已经找到商博良工作的继承者。当时本森正在计划编写《埃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书,因而切望获得这个年轻学者的协助。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两人之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1837年莱普西乌斯发表了他的《给罗塞利亚的信》,证实了商博良的主要发现,并摈弃了批评他的人使用的方法。开放这个宝库的大门,成为让大批业余研究者涌入的信号。他的功绩在于坚持应用严格的批判原则,扫除幻想和空论。1842年,他写出了《帝王书》(BookofKings)草稿;他在游历埃及后,对该书加以补充。他还研究神话学;把混乱的众神排成有秩序的等级。在第一次游览都灵时,他已认识到:在纪念品、木乃伊和纸草卷上的宗教文献大部分是属于一种被他指称为《亡人书》的著作。为了理解神话学,显然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1842年,他出版了都灵纸草卷摹本;虽然这是一种后期而又有差错的摹本,但它继续保持它的地位,直到四十年后那维尔出版了它的最好的原文。当莱普西乌斯请求本森替他设法得到游历埃及的资助时,这个公使同意尽力为之。洪堡支持了这项申请;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登基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柏林大学还为他设立了埃及学讲座。于是一个私人旅行计划发展成为科学考察队的计划。1842年底,莱普西乌斯在埃及登陆时,已经学到欧洲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穆罕默德·阿里准许他自由发掘,而且表示普鲁士王需要什么,他就赠送什么。考察队送回本国的古物和石膏模型约有一万五千件,包①括来自孟斐斯的三座古墓,来自底比斯和斐利的圆柱以及方尖碑、雕①参阅艾伯斯;《理查·莱普西乌斯》,英译本,1887年。——原注①谷俾奥(Gubbio)——古称攸古比,意大利中部古城,1444年在该城发现的九块青铜板,刻有翁布里亚人祭祀丘比特等神之祈祷文及仪节,对研究古代意大利宗教具有重大意义。——译者①斐利,在第一瀑布附近,今阿斯旺水库区,有托勒密二世所建埃西斯庙,庙前有巨大塔门及圆柱,柱上\n像、石板、纸草卷和其它无数古物。这个考察队继续工作了三年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故事,由它的领队记述在他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西奈半岛通讯》里。他长期逗留在孟斐斯,探究古王国,发掘了百余座坟墓,把十二王朝与十八王朝分开,确定了喜克索人入侵的日期,并研究了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斐利的铭文,使他能够确定托勒密朝诸王的顺序。他①最早研究了尼罗河流域第一瀑布外的地区,他参观过麦洛伊,并发现了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他在底比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赞赏埃及十八和十九王朝统治者的丰功伟业。在游历西奈半岛后,他满载宝物返国。他的收获超过了他的最高期望。于是,他被聘为柏林埃及博物馆馆长,实际上他是这个博物馆的创始人;普鲁士王还拨了经费出版他的研究成果。该书分十二巨册刊行,约有图版千幅。他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古迹集》是一座极其丰富的铭文、地图、略图和画片宝库,其中很多是彩色图。页边还注明地点和朝代,但未附释文。《帝王书》的编写,开始于他的埃及旅行之前,出版于1852年;因此它几乎是一部必备的姐妹篇。用艾伯斯的话说,《古迹集》必然永远是研究埃及学的最基本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坚固的编年学基础,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埃及史。莱普西乌斯的论著:《埃及人的编年学》于1849年出版;它不仅是根据对②古文献的研究,而且企图恢复曼涅托的佚著;曼涅托是托勒密王朝的历史家,他的片断摘要散见于后来的历史家著作里。虽然莱普西乌斯不想编成一部叙述性著作,但他坚实地勾画出埃及史的轮廓。他在晚年从事于不间断的研究和旅行。1866年重游埃及时,他发现了卡诺帕斯碑,那是用圣书字、民用字和希腊字写的长篇铭文;它证明按相同的原则来释解罗塞达碑及其他铭文的方法是正确的。七十岁时,他出版了《努比亚文文法》;这项工作在他游历埃塞俄比亚后就已开始进行。在该书的导论里;他广泛地论述了非洲的民族和语言。1884年,七十四岁,莱普西乌斯死去,他一生忙到最后一刻,名满世界学术界;他对埃及学所做的工作,除了它的创立人外,比任何人都多。他的审慎的方法和精确的学识使他的著作特别坚实。除了布鲁格施外,那些继续他的工作的德国大学者:埃贝斯和杜密坎、埃曼和维德曼,都是他的门生。马伯乐在他死时写道,“莱普西乌斯是我们英雄时代的最后残存者之一。他长期以来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我只希望,在我死时,人家认为我为我们的科学所做的工作能等于他所做的一半。”①在莱普西乌斯从他的第一次考察旅行返国后不久,马里埃特被罗浮博物馆派到那个和他的名字永远联系着的国家去。几个星期后,他发现有一条立着一百四十一座狮身人面像的大道,通往孟斐斯附近的塞拉比尤姆(Serapeum)即奥西里神庙。神庙已经毁灭,但还有许多巨型地窖有铭刻。——谭注①一译梅罗伊,为古代埃塞俄比亚首府。——译者②公元前3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祭司曼涅托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部。其书久佚,公元1至4世纪罗马作家约瑟夫·弗拉维优斯,优塞比乌斯书中有简短摘录。传世的片断中有三十个王朝法老名表,并附有依年代记载的日期,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谭注①参阅马伯乐的《传略》,见马里埃特:《杂文》,卷Ⅰ,1904年,和查姆斯:《埃及》,1891年。两人都是他的知交。——原注\n留存,在那里埋着神牛石像。他还找出六十四座坟墓和无数铭文及艺术品,包括从十八王朝到托勒密王朝时期。于是他挖出基泽的狮身人面像神庙。1853年,他回到巴黎,意图出版他所发现的全部记载。他虽然很快把它们分类成编,但他太缺少学者的修养,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只出版了一篇简述。1857年,他被埃及王指派为古物管理委员,并在布拉克建立了博物馆。他在孟斐斯和萨卡拉找到了几百座坟墓,挖掘了①阿拜多斯城遗址,在登得拉和伊德富探索了托勒密朝的诸神庙;并清查②出底比斯附近山中的默狄涅-哈布和特尔-埃尔-贝哈里的宫殿。虽然他的技术粗糙,他却是第一个、又是最大的发掘家。他认为这个博物馆是他的最大成就。他知道在那里最能表现自己的特长,所以拒绝接受法兰西学院埃及学讲座的聘书。他的忠诚的朋友和同行布鲁格施说过,“马里埃特与其说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诗人。他不擅长译解圣书字,他也很了解他的翻译不太可靠。他自己承认,他绝对没有这门科学的语言学方面的才能,因而深自慨叹”。马里埃特是与商博良、勒普瑟并列的第三个埃及学大家。他的最高成就是揭示了古王国,关于这方面,他已被正确地称为哥伦布。在萨卡拉,他发现了第六王朝的陵墓;并找出了古王国最早的长篇宗教文献;而《亡人书》是属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他证明:古王国的艺术和文明决不是原始的,而是高度发展的;它本身就是许多发展时代的顶点。达姆斯特泰尔写道,“马里埃特所要进行的斗争,不仅是对未知的东西,而且是对自然界和人们。他胜利的三十年是同疟疾、愚蠢、冷酷和偏见的无休止的而又猛烈的冲突年代。他必须使用非凡的外交手腕,迫使这些持有的宝藏愚昧的人了解它们的价值。发现的垄断权使埃及的古迹避免了愚昧的那种彻底的破坏,而另一世纪的旅行者和古董投机商是会造成这种破坏的。”在他死时,埃及王赐给花岗石棺以殓其遗体。“他长眠在他的博物馆的入口处,即由他的天才所恢复的四千年历史的进门处,由从塞拉比尤姆神庙移来的四座狮身人面像保卫着。”①商博良死后出现了许多幻想的空谈;法国埃及学直到鲁热才又开始沿着坚实的路线前进。鲁热被委派为卢浮博物馆埃及古物保管员,这说明他的学术性专著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并在1860年接任了埃及学讲座。在他长期游历埃及时,马里埃特作他的向导。虽然他的名字既不与轰动的发现又不与综合的论著相联系,但他对科学的埃及学的贡献,已被一些有资格下判断的人列入了最高等级。另一个更出色的语言学家是布鲁②格施,德国的第二个埃及学大家。1848年,他的《埃及俗体字文法》的出版,使他一跃而跻于学者的前列;腓特烈·威廉四世按照洪堡的意见派他到埃及去译解俗体字铭文。当塞拉比尤姆神庙区被发现的时候,他正和马里埃特在一起,并和这个发掘者之王结成了终身友谊。可是,他①阿拜多斯,在上埃及尼罗河西岸。在这里发现了塞提一世所建奥西里神庙,拉美西斯二世所建之庙及走廊上的书板(TabletsofAbydas)。——谭注②默狄涅哈布的宫殿是反映埃及艺术暂时复兴的第二十王朝时代作品。特尔-埃尔-贝哈里有十一王朝,十八王朝的庙宇。——谭注①参阅马伯乐的杂记,见鲁热:《杂文》卷Ⅰ,1907年,和瓦隆:《颂赞》卷Ⅰ,1882年。——原注②参阅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和旅行》,1894年,和纳维勒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n和莱普西乌斯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有时甚至公开敌对。洪堡是他们两人的朋友和赞助人;当他企图为这个年龄较轻的学者获得柏林博物馆长的职位时,莱普西乌斯宣称,这个位置应给他本人,否则他将辞去教授职位并离开首都。但他对布鲁格施的最大著作:《圣书字和俗体字字典》则表示赞赏;并声称,在埃及学上再也没有象这样的著作。艾伯斯是他们两人的朋友和门生;他宣称,布鲁格施在译解埃及语言和研究其演变方面,远远地领先。爱德华·迈尔宣称,就天才、广博和推测本领说,他可与商博良比肩。莱普西乌斯限于研究铭文,而布鲁格施则大胆地处理手稿。布鲁格施主要是一个语言学家,但他却首先认真地企图根据同时代的纪录来编写埃及历史。他宣称,莱普西乌斯已经做到了一个人根据曼涅托所能做到的事情,但古文献却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这个托勒密朝的祭司是不可信的。该书附有大量的铭文和纸草卷的译文。关于古王国和中王国,叙述得不很详细,但第一卷以一半篇幅专述那个伟大的十八王朝的故事;通过他的手笔,这个王朝才得以被研究者充分了解。这部著作享有盛名,但由于它引录原文过多和任意作出假设,是不能完全使人满①意的。第三个和马里埃特有联系的学者,是杜密欣。当这个大发掘家[马里埃特]掘出阿拜多斯的塞提庙时,他并没有停下来详细考察它收藏的宝物。不久以后,杜密欣在他第一次游历埃及时在那里的墙上发现有一张埃及国王名表——塞提和他儿子拉美西斯二世对其列祖列宗献祭的名单。这张保存完好的名单就成了埃及编年学的主要基础。马里埃特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是马伯乐,他的博物馆和埃及古物管理员的职位是由后者接任的。象商博良那样,马伯乐在学校时已经显示出爱好圣书字的倾向。1867年,他碰到马里埃特,正时后者正在为展览会的事情留在巴黎。那个有名的埃及学者给了他两篇新发现而又困难的文献去研究,而这个自修的学者把它们翻译了出来。1869年,23岁,他被聘在新成立的高等学术研究院讲授埃及文;鲁热死后,马里埃特还为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内那个被人垂涎的讲座。1880年,马伯乐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埃及;这一团体后来发展为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他留在那里,①直到马里埃特去世。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开掘出一座萨卡拉金字塔,它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宗教文献。他的最轰动一时的发现是:1881年他找出了从十八到二十一王朝陵墓以及塞提、拉美西斯二世、三世和图特摩斯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堆积在底比斯附近王公山谷中的一个洞穴里。他曾监督博物馆移到开罗,并刊印了它的目录。他是在法国普及埃及学的第一人。过去,商博良和鲁热的著作太难懂,而马里埃特的报告则太简略,都不能赢得广大的读者。马伯乐则不然:他是探险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家,因而他关于东方人民的长篇和短篇的历史著作,最先明显地展示东方的图景。马里埃特去世前,埃及学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由法、德两国人进行的;而现在轮到英国人来插手了。1883年,英国设立埃及探测基金会,它标①参阅艾伯斯:《埃及研究》,1900年。——原注①萨卡拉在孟菲斯附近,即马里埃特发现塞拉比尤姆与狮身人面像之地。马伯乐在此地第五、六王朝金字塔内部墓室发现了大量宗教经文以“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之名发表。——谭注\n②志有组织的研究的开端。在它的早期,主要活动者是弗林德斯·皮特里;他第一次游历埃及是在1880年。他从三角洲开始,发掘塔尼斯,即《圣③④经》上的琐安,并根据它的早期希腊文铭文证实瑙克拉提斯;铭文显出那个以前未曾想到过的有三百年历史的希腊殖民地。不久以后,又发现了第二个希腊城市达夫尼。然后他转到发雍,住在哈华拉做研究工作。在发雍他进入金字塔并发现了一座陵墓以及许多宝物,包括从宝石到儿童玩的娃娃。在他看来,任何发现,那怕是极微小的,也是重要的。他①确定了米立斯湖和“迷宫”的地点;探索特尔·厄尔·阿马那,即宗教改革家埃赫那吞(图坦喀门的岳父)建立的短命城市。约在公元前1380年,他放弃底比斯以求摆脱祭司权力的控制。1887年,有一个农妇偶然看到若干只破碎木箱,里面藏着几百块公元前14世纪巴比伦楔形文泥版,包括埃及王及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之间的通信;经过温克勒编辑后,这些通信为古代东方史专家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有些信件已被英国博物馆收买。1905年在开罗以北20英里处,又发现了一所喜克索人的大营。皮特里的一系列附有插图的专著包括埃及各部分的发掘地点,直到西奈半岛;这些专著证明了他工作卓有成效。作为一个挖掘家,皮特里的地位可与马里埃特和马伯乐并肩;他参加的集体著作:《埃及②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写的有权威的记载;其中开首四卷是他执笔的。③美国参加埃及学研究较晚,但布雷斯特德是一个才识超群的学者。法国的埃及学研究的崇高传统,是由勒维荣和阿梅利诺继续的:前者研究埃及的法律,后者研究它的道德和宗教思想。兰布洛索根据纸草卷和④铭文详细地评述了托勒密朝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艾伯斯编辑了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医学巨著,叫做艾伯斯纸草卷;这部著作是他在底比斯找到的;他还编辑了通俗图解的纪述。在《埃及公主》及其他小说里,他描述了埃及历史上的许多场面;这些小说已遍传全世界。厄曼,即莱普西乌斯在柏林的继承人,除了他的巨著:《埃及文字典》外,还为埃①及人的生活和思想描绘出有学术性的综合性的图景。②19世纪最后二十年期间的主要事件,是揭示埃及的起源。1895年,③当马伯乐出版他的叙述著作时,故事是从第四王朝的金字塔建造者开始的。现在我们不仅发现了埃及的一些古王朝,而且发现了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的埃及。奇异的陶器和燧石早已为人所知,但直到德摩根系统地②他的早年发现,总结在《十年的埃及发掘》,1892年,关于这方面的全部故事,叙述在他的《考古学的七十年》,1931年。——原注③琐安(Zoan)——即塔尼斯(Tanis),尼罗河三角洲上荒芜了的古城,喜克索人曾建都于此。——译者④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希腊城。——译者①米立斯湖与“迷宫”始见于希罗多德《历史》著录。——谭注②《埃及史》全书六卷,1898—1905年。——谭注③参阅C.布雷斯特德:《研究古代的先驱:J.H.布雷斯特德的故事》,1947年。——原注④参阅艾伯斯:《我的生活故事》,1893年,和爱德华·迈尔:《论学杂著》,1910年。——原注①厄曼还著有《古代埃及人的生活》(1885—1887年),《埃及宗教手册》(1905)等。——谭注②这方面的成绩已由金(King)和哈尔极好地总结在《从新近的发现来看埃及与西亚》,1907年。——原注③指《古典东方民族古代史》(HistoireAnciennedesPeuplesdesl’orientclassique)。——谭注\n探究阿拜多斯和伊德富之间的原始墓地后,才发现曾有过一个石器时代。皮特里曾暗示过,这些墓地与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的利比亚的侵入者有关系;而现在他也改变了主张,按照陶器来划分埃及史前时代的阶段。这个原始文明的发现使人们从一个新的配景里来看埃及的历史。关于埃及起初三个王朝的历史,我们也是新近才知道的。那些可能属于塞姆族出身的侵入者,聚集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两个中心;亥拉康波里斯诸王终于征服了北部,并建立起第一王朝。这里,又是从坟墓得到了说明。由于德摩根、阿梅利诺、皮特里和奎贝尔在阿拜多斯和亥拉康波里斯的努力,我们在古代史上才增加了这个新篇章。孟斐斯城是在第一王朝时代建立;而迁都该城,则是在第三王朝时代;对这片广阔地址的系统探索,是由皮特里开始的。努比亚的麦罗埃的发掘是属于埃及史的另一端的。虽然关于埃及古史已有惊人的进步,但还残留两段空白。在第六王朝以后笼罩着一片黑暗;直到十一王朝的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这帷幕才揭开。同样,中王国崩溃后,舞台又变得一片黑暗。关于喜克索人我们虽已知道一些,但这方面的消息还是微乎其微。我们从曼涅托知道:他们的文化是低下的。他们遗留下来的是使人憎恶的回忆。可是,他们所造成的破坏的痕迹却一点儿也没有被发现过;他们曾使用圣书字,并崇拜埃及的神。大家都同意,他们是从亚洲来的;但他们是属于①贝督因阿拉伯族,还是一个与赫梯人有关的小亚细亚种族呢?由于这两个黑暗时期的存在,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朝代纪年依然未能确定。皮特里按照传统的计算法,把第一王朝日期放在约公元前4300年时,而厄曼、爱德华·迈尔和布雷斯特德都主张它的日期约在公元前3400年时。对于这两个极端的看法,马伯乐都不同意。Ⅱ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第一步,是译解旅行家们搜集到的铭文。译解楔形文的钥匙,从①波斯诸王在波斯波利斯和苏萨的铭文中可以找到;而这些铭文已有卡斯②登·尼布尔的抄本。1802年格罗特芬认明波斯波利斯铭文的三种文字是①曼涅托认为喜克索人是腓尼基人或阿拉伯人。现代学者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塞姆人或塞姆人与胡里特人的混血种。——谭注②参阅希耳普雷希特:《圣经地区的探索》,1903年;巴奇:《亚述学的兴起和发展》,1925年;肯尼恩:《圣经和考古学》,1940年;和丹尼尔:《考古学的百年》,1950年。简略的总结,见于达姆斯特泰尔:《关于东方的论文》以及霍梅尔、罗杰斯与爱德华·迈尔所编的历史著作。——原注①波斯波利斯,在今设拉子东北,为古波斯王大流士所建都城。17世纪初意大利旅行家在此摹写了所见楔形文符号,1765年德国旅行家K.尼布尔拓下了波斯、埃兰、巴比伦三体铭文。苏萨,古埃兰首都,公元前645年为亚述所灭,后又归入波斯帝国版图。1884—1886年法国考察团在此发掘出埋沉地下的大流士宫殿及记有大流士功业与宫殿建筑的铭文。——谭注②卡斯登·尼布尔(KarstenNiebuhr,1733—1815年),德国旅行家,著名史学家B.G.尼布尔之父,东方\n波斯文、米太文和巴比伦文,发现大流士·喜斯塔普斯和他的儿子薛西斯的名字,并认出了若干字母。1836年,柏努夫和拉森又认出了另外几③个字母,但决定性的胜利是由亨利·罗林森赢得的;他是译解楔形文的商博良。1835年,当游历波斯时,他在哈马丹看到了两块楔形文碑铭,并认出了波斯诸王的名字。于是他就看格罗特芬的研究成果,并宣称,在他所说的三十个字母中有二十二个是错误的。1838年,他出版了贝希④⑤斯敦波斯文铭文开首两段的译文。于是柏努夫把自己哈马丹铭文的论⑥文送给他,其中包括若干个不同的解释以及关于矰达语的研究论文,这种语言虽比铭文晚出,却是波斯语的古体文;他帮助于罗林森掌握了波斯语的语法结构。1838年,罗林森开始与拉森通讯;他们两人发现,对于几乎每一个字母双方的看法都是一致的。1844年,罗林森被任命为驻巴格达政治特派员后,立即出发到贝希斯敦。罗塞达碑包括希腊文这把钥匙,但大流士的铭文上的三种书体都同样是未知的。而且罗塞达碑文能舒舒服服地加以研究,而这项布告却是镌刻在离地三百英尺高的陡崚石壁上的。波斯楔形文流行于波斯;巴比伦文流行于巴比伦,而米太文不止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克服无限困难,他抄下了波斯文和米太文,但巴比伦文他起初抄不到。他的前辈们曾试图译解的波斯文是最容易的;他也集中他的主要注意力于这方面。他使用哈马丹铭文中所译解的喜斯塔普斯、大流士和薛西斯这三个名字作为钥匙,试译全部铭文。译文和他的论文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奥佩尔是最有权威的判断者,他在1895年宣称,在罗林森之后,波斯楔形文解释这片田野里只能再检一些落穗了。然后,罗林森转到巴比伦文字;这种文字难得多,因为有几个符号代表同一字母,使用的字体约有三百个。并且,关于波斯文书体,他已有前辈研究过,而关于巴比伦文①书体则没有。当莱亚德的宝物从底格里斯河顺流运到巴格达时,他取得了铭文的抄本,并注意到亚述泥版书体与贝希斯敦的巴比伦文铭文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在1847年他第二次旅行到那里;他本人不能攀登崖壁,就雇了一个库尔德族青年进行摹拓。铭文几乎已经剥蚀了一半,因而只能揣测,但他总算设法摘取到主要之点。1849年,他返回英国后,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纪录的文章。十年后,有人发现了一个圆柱形土器,刻着关于提格拉—帕拉萨一世的编年史约八百行。这个圆筒送到罗林森、奥佩尔、塔尔博特和欣克斯处;他们的译文实际上都是相同的。于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虽然甚至今天还有若干字体未能确定下来。卢休森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米太文的铭文,但波斯和巴比伦文的铭文已经被他掌握了。他的晚年大部分消磨在学家,1761—1767年在阿拉伯调查考察。——谭注③公元前516年,波斯王大流士于巴格达附近贝希斯敦悬岩上刻石纪功,碑文以古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三体书写。——谭注④哈马丹,波斯西部城市,古米底亚国首都,公元前549年为波斯王居鲁士所毁。考古学者在此发现了居鲁士的铭刻。——谭注⑤矰达语,古波斯语。——谭注⑥参阅C.罗林森:《H.罗林森勋爵》,1898年。——原注①莱亚德(A.H.Layard,1817—1894年)英国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译者\n英国博物馆内,拼凑并翻译泥版和石碑上的片断文字;并在乔治·史密斯和平奇斯帮助下,为博物馆董事会编辑巨型汇编:《西亚楔形文铭文》。1904年董事会还派遣它的两名职员去重拓贝希斯敦铭文;1907年,出版了它的确定版本。把亚述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首先应该归功于施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德利奇两人。前者是艾华德的门生,于1872年出版他的《楔形文铭①文与旧约全书》;它是第一次详细讨论对犹太人历史的新见解。在那个时期,他开始在耶拿大学讲授亚述学,不久从那里被聘到柏林大学。在这以前,德国学者曾倾向于轻视这门新科学;在施拉德尔开始写作以前,②古什密德曾表示他的怀疑态度。这个亚述学家帮助东克尔刊印他的《古③代史》新版;当后者受到古什密德挑战时,他立即给予援助。于是古什密德从东克尔掉转矛头,在他的《德国的亚述学》里对施拉德尔开始猛攻。他宣称,施拉德尔是一个热情的人,但缺少严格的语言学训练和批判的本能。这个批评者比那个柏林大学教授学识更渊博,智力更高强;他的锋利的攻击好象马队冲锋一样。他确实揭露了若干易被攻破的结论;他进攻的结果是教会别人更谨慎;但他所列的罪状夸张太甚;他闭眼不看越来越多的已确定的事实。施拉德尔在他的最大著作:《楔形文铭文与历史研究》里给予答复。他虽不善于争辩,但他的书由于学识充实而获得了信任,于是学术界不复怀疑,亚述学的基础已很好地并认真地奠定下来。在他死前好久,他的最大门生德利奇的正确的语言学方法已经使这门学科不会再受到攻击。在柏努夫、拉森和罗林森从事译解楔形文的时期,挖掘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的工作也开始了。1842年,当波塔到达摩苏尔任法国领事的①时候,他接到法国政府关于挖掘柯萨巴的训令;结果他发现撒玛利亚征服者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很多遗迹送回巴黎,在那里它们构成了最早的亚述博物馆。关于一个丰富而强大的文明的揭示,激起了全世界的兴趣,②庞大有翼的石牛还引起了公众的热情。波塔首开风气,莱亚德继踵于后。1840年,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旅行时,以贪恋的目光看着那些土山;1845年,他率领探测队到摩苏尔附近的宁罗德地方,掘出了亚述伟大统治者的宫殿和宏伟纪念物,这些古物现存英国博物馆。然后他转到库米尼克,即古代尼尼微,在那里他又掘出西那基立布的宫殿;它墙上的雕刻显示出西亚古文明——服装和风俗、打猎景象和船只,国王的事业和政治。在那里王家图书馆藏有各种关于天文学和占星学、纪录和年谱、圣歌和咒语、行政和国务报告的泥版文书。在这些宝物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亚述洪水故事的记载,那是1872年由乔治·史密斯译出的。继亚述的惊人发现后,很快就进行了发掘更古老更偏向南边的巴比伦文明遗址。莱亚德掘开巴格达附近尼普尔的土山。罗林森探索了那久①参阅爱德华·迈尔的杰出杂记:《小品文》,1910年。——原注②参阅吕尔的杂记,见古什密德:《小品文》,共五卷,1894年。——原注③东克尔(MaxDuncker,1811—1886年),德国历史家,著有《古代史》共九卷。——译者①柯萨巴,在伊兰北部,今为农村。1843—1845年波塔在当地废墟上发掘出萨尔贡二世宫殿,其壁上浮雕,镌刻了国王的事迹,后又发掘出镌有带翼牡牛的城门,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谭注②除了他的杂记外,参阅他的《自传与信件》,共二卷,1903年。——原注\n已被认为“巴别尔塔”的比尔斯·宁罗德。洛夫特斯在华喀,泰勒在乌尔,进行发掘工作;奥佩尔率领法国探测队到巴比尔。但他们很少看到大理石和石头的遗迹,也找不出宏伟的遗物,因而西方人的热情被浇上了冷水。而且这一地区住着无法无纪的愚昧的部族,并常常遭受水淹。另一方面,从尼尼微泥版中逐渐清楚地看到:亚述的大多数文献仅仅是巴比伦原著的抄本;当世人再注意于巴比伦区时,轰动的发现即将出现。①1877年,法国驻巴士拉领事德萨泽克开始系统的挖掘。由于决心探索南②巴比伦或称迦勒底,他选择了特洛即古代的拉加西域,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二十余年,直到他死亡为止。他发现的东西由卢浮博物馆东方古物管理人厄泽加以鉴定和描述。在波塔和莱亚德揭示出亚述的奇迹以后,任何亚洲的发现在重要性上都比不上特洛地方的发现。那些被罗林森称为前塞姆族时代的古文献,曾在尼尼微图书馆被找出,洛夫特斯和泰勒也在稍南的地方偶然发现过类似的铭文;但从史学角度,在特洛发现了苏美尔人和几千块泥版文书,其中大多是帐目。美国的普姆佩利探测队在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阿瑙城的发掘,还提示了这个种族的可能的起源;这个种族有复杂的语言、灌溉体系和高度发达的艺术。从收集到的闪长岩石像,可以想见约在公元前2600年拉加西王古狄亚统治时代的丰功伟业。拉加西的铭文还证明它与阿拉伯、西奈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有贸易关系。1901年,当德萨泽克死时,他已写出了历史上的新篇章。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对亚述统治者萨尔贡和西那基立布的宫殿,曾惊叹不已,但这些古迹与特洛的大量古物比较`,似乎都是属于比较近代的。当认识到巴比伦文化,包括书写术在内,大多是塞姆族从苏美尔人承袭来的时候,人类经历的链条就加长了。在德萨泽克忙于发掘特洛时,1886年一个美国探测队在彼得斯和喜尔普勒希特领导下被派到巴比伦城南五十英里的尼浦尔。再没有什么地方曾发现过这样多的铭文;几千块碑构成了神庙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些纪录发掘结果的许多长篇巨帙,为我们关于北巴比伦的知识作了最重要的增补。最有趣的发现是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传说,它比亚述和犹太人的叙述还早几百年。在晚近时期,德国东方学会(创立于1898年)发掘①了巴比伦的使人扫兴的遗址;科尔杜威的图案曾试图重建它的光荣古迹。虽然在无石头的巴比伦城未曾找出象波塔和拉雅德发现的那样动人的古迹,但文化的证据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而且重要得多。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②动全世界;法典是在1901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这个法典①特洛地方的探索已由喜尔普勒希特描述。后来时期的挖掘,总结在金和哈尔,《从新近的发现看埃及和西亚》,1907年。——原注②德萨泽克误认特洛即拉加西,直到1953年才得到小雅各布森的纠正,小丘希巴才是拉加西城邦的首府。特罗为古代的吉尔苏城,隶属拉加西城邦。——谭注①科尔杜威(Koldewey,Robert,1855—1925年),德国考古学家,发掘巴比伦古迹的领导人。——译者②除了他的大批报告外,参阅他的简略总结:《探测队在波斯的历史和工作》,1905年。1891年,在南波斯参观苏萨时,他看到四个大土山,于是建议法国政府向波斯王购买发掘波斯古迹的独占权。这项工作于1897年在苏萨和其他地方开始进行——原注\n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在波斯、帕提亚和阿拉伯统治的遗迹里,德摩根还发现了大批可以显示埃兰早期历史的铭文;在那以前,只是从巴比伦和亚述的纪录里模模糊糊地知道埃兰。在苏萨出土的古物,占着卢浮博物馆的两个大厅。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期间重新进行了亚述的发掘工作。尼尼微开发未尽的旧址,也再一次被挖掘;安德累考查了舍尔加特,即位于摩苏尔和巴格达间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古城,在那里他找出了亚述城旧址,即亚述国家的最早的首都。对于该城,德国东方学会也已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这样,我们才知道亚述成为强大国家以前的情况;当时它还是在巴比伦总督统治下的一个行省。为了揭开乌尔的秘密,也已作了初步的尝试。当东克尔在他的《古代史》中提供关于古代东方的最早的综合论述①的时候,乔治·罗林森在他的著名长兄和乔治·史密斯帮助下,也用英文编写了一部类似的著作。他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叙述了迦勒底、亚述、巴比伦、米太和波斯的地理与历史、宗教与风俗、艺术和科学;接着,还出版了关于帕提亚、萨桑朝或新波斯帝国和腓尼基的著作。和东克尔一样,他也不懂东方语言,但他的论述却是具有学术性的。他对文化给予较多的注意;书中的插图也构成一个新颖可喜的特征。马伯乐的《古代东方各族人民史》简编第一版于1875年刊行;20年后,他更详①细地叙述同一范围的故事,出版了精装本三卷。虽然只有关于埃及的历史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的,但这部著作却仔细论述了古代帝国的功业。最后,爱德华·迈尔在他的大著:《古代史》里,以一个大师的手笔描写了巴比伦的最古的文明。该书于1884年初版;1909年二版;第二版与其说是改订本,不如说是新著作——因为在这两版中间的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在温克勒给赫尔摩特的《人类的历史》所撰写的著作②③里,和金所编的关于巴比伦文明史的出色著作里,都使用了最近二十年期间的发现。现在我们已能够试验性地、轮廓式地再现出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特征。爱德华·迈尔相信:塞姆族在苏美尔人之前已占领了这个地区;这个主张虽然得不到普遍的同意,但这两个敌对种族究竟在什么时候进入两河流域,两个部族都在那里留下了痕迹,还是不能确定下来。这个地区看来曾长期分裂为许多城邦——基什、拉加西、乌尔及其他城邦——它们的命运和相互关系经常在改变着。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代,萨尔贡似乎是一世之雄,不仅因为他们是阿喀德和苏美尔的统治者,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扩张到地中海岸的帝国的创立人。萨尔贡的大厦被埃兰人推翻了,但当侵入的浪潮退却后,巴比伦城成了一个辉煌而强①即亨利·罗林森(SirHenryRawlinson,1810—1895年),见上文。——译者①即《古典东方古代民族史》。——谭注②温克勒(WincklerH.为《人类的历史》丛书所撰的专著名《古代西亚》(Dasal-teWestasien)。——谭注③金(King,L.w.)氏著有《苏美尔与阿卡德史》(HistoryofSumerandAkkad),《巴比伦史,自王国创建至波斯征服》(HistoryofBabylon,fromthefoundationoftheMonarchytothePersianConquests)。——谭注\n大的帝国中心。在交替的诸王朝中,我们了解最多的,是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第一王朝,汉穆拉比就是它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他的细密的法典外,大量的官方信件、司法判决和法律文献都显出一种非常近代性的文明。亚述是从附庸逐渐升到独立地位的;关于它的历史,早期诸章薄弱,而后期诸章则详细。如果说温克勒判断它是“一个军事强盗国家”过分苛刻,无论如何它的文化远低于那个终于被它推翻了的衰朽的帝国。一直有人在说:巴比伦对古代东方的影响正象罗马对欧洲的影响一样。在法律和科学、宗教和艺术方面,它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犹太人从古代东方所受到的影响已被揭示出来;这不仅引起兴趣,而且若干集团里引起了震惊。根据铭文的显示。洪水的故事只是许多抄袭中的第一种;虽然学者们对犹太人所受影响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没有人否认,古老的宗教对年轻的犹太教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的。Ⅲ在最近的轰动一时的揭示古代东方的发现中,有关于公元前第二、三千年代克里特岛上一个高度文明的发现。在埃及和巴比伦,知识的界限被延伸到古代;而在克里特,象在迈锡尼那样,一个未知的世界得以重见光明。关于古代世界的一个最著名的故事确定了它古代的基础,因此浪漫的兴趣就更浓了。故事是这样:密诺托即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怎样在迷宫里吞噬从雅典七年一次献来的童男女;提秀斯怎样加入了这些牺牲者中间;阿里哀德尼即米诺斯的女儿,怎样钟情于提秀斯,因而授他一把宝剑和一条绳索;前者用以杀死密诺托,后者用以引导提秀斯退出迷宫。这个故事是每个希腊儿童都熟悉的,并且刺激了几个世纪的幻想。要探索那个被荷马称作“大克诺萨斯”的古城是施里曼的雄心之一,但这项发掘工作,还要等到土耳其人的被逐出和一个英国富翁的出①现。阿瑟·伊文斯在雅典看到了一些刻有一种不知道的书体的印章,就在1895年购买了克诺萨斯旧址的一部分,又在1900年购买了其余的部分。他对这项工作已有准备,因为他对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具有包罗万象的知识。在他发掘的第一期,他出土一座前迈锡尼时期的王宫,规模远远超过泰林斯和迈锡尼的王宫,并有壁画作装饰,证明一种高级文明的存在。贵妇们所穿的精致的低领长袍几乎和现代的夜礼服分辨不出来;一个法国学者不禁惊呼,“这些简直是巴黎的妇女服式”。一块图样美妙的游戏盘还证实这个印象:那里的文化比迈锡尼文化要丰富得多。那些捉牛的壁画——抓住冲撞的牛的角,并跳过它们——及其他证据,表明牛在人民生活和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多么重要。王宫下层的分支错综纷复,使人可以想到迷宫是在这个建筑之内,而不是在它外边。1900年,经过九周的工作后,为东地中海早期历史开拓了一幅重要性无可估①阿瑟·伊文斯勋爵的传记,由他的异母姊妹琼·伊文斯编写的,很精彩。全部故事,由发现者本人叙述在他的《米诺斯王宫》,1921—1935年。伯罗斯,《克里特岛的发现》1907年;格拉斯哥:《米诺斯王朝》(Minoans),1923年;和彭德尔伯里:《克里特岛的考古学》,1939年,都是有用的总结。——原注阿瑟·伊文斯青年时代经营造纸业致富,由于企业需要进行水文地质探察,对考古产生兴趣,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谭注\n计的新前景;后来几年的探索证实了这个黎明时期的期望。虽然约在公元前1400年,王宫遭到劫掠和焚毁,但它的结构和内容还留下相当多,从中可以想象出当时米诺斯首都的生活。那里缺少防御工事和战争题材的壁画,由此可见,它当时觉得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这和泰林斯与迈锡尼的坚厚城垣以及埃及和亚述的军事标记形成了一个显明的对照。在克诺萨斯的开创工作鼓舞了人们对岛上其他部分的探索。意大利的学者们探索斐斯托斯和哈吉亚·特里达,在前一地方有一座值得骄傲的壮丽宫殿,在后一地方附近有一所乡村别墅。哈立特·倍德在谷尔尼①亚发现了一座城市;雅典的英国学校在帕莱奥卡斯特洛发现了另一古城。虽然铭文至今仍不可理解,但现在我们已有可能以陶器为主要线索勾画出克里特早期历史的轮廓。古代的残余片断暗示有一些比米诺斯文明更早的殖民地。米诺斯文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可再分为三段。克诺萨斯宫殿在中米诺斯的第三段开始建造,而在米诺斯晚期的开首两段完成。它在完成后,很快就遭到破坏。斐斯托斯和哈吉亚·特里达二者同时毁灭表明:米诺斯的整个文化约在公元前1200年同遭浩劫,也许是迈锡尼人造成的浩劫;而迈锡尼人本身则是被厄基亚人驱逐出来的。米诺斯曾在一个时期中继续出产艺术品,随着多利安人的侵入而出现黑暗状态。在[埃及]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它和埃及交往频繁,这一事实可由两国内不断增加的大量证据获得证明;但埃及的编年学直到十八王朝才可以有定论,所以,我们还不能确定米诺斯文明的较早阶段之精确界限。阿瑟·伊文斯勋爵同意那些缩短埃及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因而他指出米诺斯早期约在公元前3400年。但无论如何,克里特岛上的发掘揭示出至少两千年时期的历史。米诺斯文明是希腊文化的渊源之一;在它的贡献中包括字母,腓尼基人仅仅是把这些字母加以简化而已。如果我们要寻求欧洲文明的开路先锋,最好求之于最早的海上主人翁,即米诺斯克里特的统治者。①赫梯的文明是最后被揭示出来的文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旅行家曾报告过:看到了在小亚细亚他们无法确认的遗物和读不出的铭文。《旧约全书》提到过的一些事使人想起在以色列的最早时期已有很多国际交往,但我们从埃及史上还获得了更多的说明。我们有拉美斯二世与克塔国王之间一项条约的埃及文抄本,这是历史上最早以文字记载②的条约;他们在泰勒阿马尔奈信件中被提到过。亚述的记录也说到过喀梯人:他们约在公元前1100年及以后的若干时期是叙利亚北部一个强盛的部族,直到公元前717年萨尔贡二世谈到他结束了他们独立地位时止。③另有一些证据来自亚美尼亚的凡城铭文,这些铭文一部分已被译出。根①帕莱奥卡斯特洛(Palaiokastro),在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在那里发现米诺斯中期和晚期的古城遗迹。——译者①爱德华·迈尔:《赫梯帝国与文化》,1914年,提供了一部良好的概论。考利:《赫梯人》,1920年,和霍格思:《赫梯诸王》,1926年,是有用的斯威希讲稿。所有已往的论著,都已被加斯敦:《赫梯人的领土》,1927年所替代。——原注②泰勒阿马尔奈(Tell-elAmarna),尼罗河畔的交通站,位在底比斯与孟斐斯的中间;在那里,1887年发现重要古文献。——译者③凡城(Van),古城,在凡湖东南岸。——译者\n据这些资料可以确定,赫梯人在被亚述并吞之前的千余年间曾在叙利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东部建立过一个重要的强国;他们起初是好战的,侵略的,后来从事商业,变为富饶的国家;他们同附近部族有过密切的政治和贸易关系。近年来,由于研究他们的遗址,这种证据已大大地得到补充。乔治·史密斯在幼发拉底河畔杰拉卜卢斯(据猜测,就是卡尔捷密士)曾看到雕刻品,于是英国博物馆就在那里发掘,找出的铭文据称是赫梯文。对博阿兹柯伊山岩上的遗迹及小亚细亚各地山岩上的其他雕刻进行研究后,塞斯于1880年宣布:曾存在过一个能与埃及和亚述比肩的赫梯大帝国,它的版图从托罗斯延伸到爱琴海岸。1884年,一个英国传教士赖特出版了他的《赫梯帝国》,这是关于这个题目的第一部著作,它讨论了《旧约全书》中的证据以及埃及和亚述的证据。塞斯首先试图译解铭文,但梅塞施米特,即赫梯法典的编辑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宣称,在两百个已知的圣书字中,只能对一个符号作明确的解释。后来,匈牙利人赫罗兹尼作了最大胆的尝试。①虽然赫梯的语言还无人能懂,但探测和发掘已有了迅速的进展。在北卡帕多基亚的博阿兹柯伊所做的工作最重要;1906年,柏林考古学会和近东学会在温克勒指导下所组织的联合探测队,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探索。属于公元前14世纪的二万块泥版文书——从泰勒阿马尔奈信件以来,关于成文记录的最轰动的发现——是在王宫废墟中发现的。它们是用赫梯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写的,最后总会提供出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北叙利亚的萨克泽吉西,即最近由加斯敦所发掘的地点,是很重要的。1911年,英国博物馆开始发掘卡尔捷密士,即帝国在北叙利亚地区的首都。辛泽里和泰勒哈拉夫则由一个德国探测队查勘过。所有这些北叙利亚的遗址都显示出受到亚述很大的影响。埃及的克塔战士图画和赫梯雕刻的图画极其类似。加斯敦曾试验性地概述了帝国的历史;他主张:赫梯帝国分两大时期,前一时期的中心在博阿兹柯伊,后一时期的中心在卡尔捷密士。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主张。在最近以前,对小亚细亚的发掘主要局限于希腊化时代和希腊—罗马时代的遗址。特洛伊城由于时隔太远,不能对半岛的一般历史多所阐明。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设想:希腊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大多是有赖于腓尼基人的。但从移民运动的日子以来,推罗人和西顿人的声名已经消歇了。阿瑟·伊文斯表明:克里特书体是独立于,而且肯定早于腓尼基书体;关于腓尼基艺术遗迹的种种新发现都证实了这种艺术平庸无奇的印象。现在没有人再同意佩罗特的信念:塞浦路斯仅仅是一个属于腓尼基的艺术附庸。我们看不到公元前9世纪以前腓尼基文物或货币,直到更后时期它才有文字,虽然《旧约全书》和荷马的诗篇表明他们在较早时期已有文明。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提供东方文化的人。所以,赫梯帝国的发现使小亚细亚的历①史有了意义和次序,并说明了东方影响的传播。从它的废墟上兴起过弗①1906年德国考古学家自赫梯首都带回数以千计的楔形文泥板,赫梯文字研究自此开始。1915年匈牙利学者赫罗兹尼将大部分泥板解读成功。赫梯人早期所用象形文字在1946年于西里西亚·卡拉小丘(Karafepe)发现了腓尼基字母和赫梯象形文字的双体铭文,终于获得解读。——谭注①参阅何伽茨的精彩演讲:《爱奥尼亚与东方》,1909年。——原注\n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权力。前者曾强烈地激发过希腊人的想象,并留下了宏伟的遗迹;后者是希腊与东方之间最后一个环节。对萨迪斯的发掘是由美国人在1910年开始的。伍德没有触动过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圣殿的更深的地层,何伽茨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则显示出东方的丰富影响。虽然东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米诺斯人和腓尼基人传到希腊的,几乎可以肯定,主要路线是经过陆路而非海路,这条道路是穿过赫梯帝国的广阔领地的。阿拉伯半岛也许是塞姆族的摇篮。世界上很少地区象这个半岛那样精心地保守其秘密。它的腹地还未被参观过,自然界和当地人联合起来警告闯入者要他们小心生命危险;但卡斯敦·尼布尔和布克哈特、伯顿和帕尔格雷夫、道蒂和本特总算掀开了这块面纱的几个角。直到19世纪①②最后三十年,阿莱维和格拉泽尔才勾划出阿拉伯南部早期文明轮廓。③在几次旅行中,他们探索了萨那周围的地方,收集到几百张铭文;这些铭文已刊入《塞姆族铭文集》。格拉泽尔的《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的历史和地理》奠定了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亚述的资料已经稍微扩大了一些从犹太和古典作家的引证中得到的片断知识;但这些阿拉伯铭文却使人们看到了公元前千年时期的一个伟大的文明。铭文中大部分是还愿文;少数有历史性的铭文也并未注明日期,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头④绪。从中可以找出四个文明王国,人们对其中两个王国即舍俾安人和密⑤尼安人王国已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关于前一王国,即《旧约全书》上的⑥示巴,铭文可上溯到约公元前800年,指出它的各个时期、统治者和首都,并揭示它的神话和宗教。关于密尼安人王国,我们所知较少。19世纪中期以前,对伊斯兰教的兴起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项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由魏尔开始的,他是德籍犹太人,在德萨栖指导下学过阿拉伯文。他根据在欧洲可以见到的最早资料,编写了先知的传记;他更重要的著作:《哈里法史》则是细心意译阿拉伯史家已刊印的和未刊印的著作,据以编成的。第二步是施普伦格尔迈出的,他的巨著[《穆罕默德的生活和教训》]迄今还是有用的。关于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半岛上宗教运动的概述和关于《古兰经》的详尽分析,是该书的明显特征;他自豪地说,他为理解《古兰经》提供了钥匙。对于这个宗教的创立人,他很少赞赏:他叱责他眈于肉欲,说他柔弱而又有歇斯底里症,并否认他的天才。米尔同意他轻视[穆罕默德]的意见;米尔的长篇和短篇传①格拉泽尔(GlaserE.1855—1908年)奥地利考古学家,曾三次赴阿拉伯调查,发现伊斯兰教以前的铭刻千余件。——谭注②参阅鄂图·韦伯:《格拉塞在南阿拉伯的考察旅行》,1909年,和何伽茨:《阿拉伯半岛深入记》,1904年。——原注哈莱维(Halévy,J.1827—1917年),法国东方学家,长期在也门一带进行考古发掘,获得有关亚述、巴比伦的宗教资料甚多,对巴比伦文字的起源也有研究。——谭注③萨那,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谭注④现译萨巴人。——译者⑤两王国均属塞姆族,在阿拉伯南部。铭文为古阿拉伯语,一度流行于半岛西南部及埃及,今已消亡。——谭注⑥示巴(Sheba)——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古国。——译者据《旧约·创世记》第十章,示巴是挪亚的后代拉玛的儿子。——谭注\n①记,第一次为英语世界提供了关于伊斯兰教兴起的可信的论述它们都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成的。下列著作对于早期穆罕默德教的历史和背景也②作出了宝贵贡献:德哥杰主编的达巴利著作的纪念版,坎塔尼亲王的《伊③斯兰教编年史》,韦尔豪森关于前伊斯兰教阿拉伯的专著④以及内尔德①克和戈尔德则尔关于《古兰经》的专门论著。《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于1908年在莱顿城开始出版;其中有托马斯·阿诺德爵士及其他主要的阿拉伯学家的撰稿。②关于重建古波斯史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1754年由昂克蒂尔·迪佩罗采取的;二十岁时,他出发到印度,去求袄教的神圣经卷。他应募当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兵士,经过四年的战争和疾病后,终于达到他旅行的③④目的地苏拉特。他在帕尔西人中间呆了三年,学习矰达语和钵罗婆语,并研究他们的宗教仪式。1762年,他带着手稿回到巴黎;1771年出版他的《矰达语阿维斯陀经》译本,附有关于帕尔西人风俗和仪节的叙述。社会上有些人指斥这部著作是近代的伪造品;有些人斥之为荒谬绝伦;关于学术史上这个最英勇事业之一的重要意义很少得到承认。所以,这项发现似乎始终劳而无功,直到矰达语研究的第二个创始人出现。比尔努夫首先是一个梵文学家,但对印度的语言和文明的研究促使他研究矰达语;他认为这种语言是古波斯语。他很快发现,昂克蒂尔的译本很少帮助,因为他所从学的人们既不太懂矰达语,也不太懂钵罗婆语;神圣经卷在中世纪时已译成这些语言。柏努夫的功绩是:根据神圣经卷之一的梵文译文,使自己摆脱了近代帕栖人的窳劣的学术研究。他的《雅斯①那注释》确定了古波斯的语言和宗教二者的真正性质。他相信波斯诸王的语言不会与神圣经卷有实质的区别,所以他把注意力转到了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碑铭;他对它们的解释远远超出格罗脱芬已有的成就。在他死后,波斯研究是由德国学者而不是由法国学者继续进行的,但古什密德和内尔德克都是在柏努夫的基础上重建波斯史的。②关于古印度的研究是由于威廉·琼斯爵士、科尔布鲁克和博普的语言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在研究梵文时,琼斯很快察觉到它同拉丁和希腊①米尔(Muir)著有《穆罕默德传》(LifeofMohammadfromOriginalSources)共四卷,1858—1861年,《哈里发王国兴亡史》(TheCaliphate:ItsRise,DeclineandFall),1896。——谭注②穆罕穆德·伊本·查瑞尔·达巴利(846—932年),阿拉伯著名史学家。著有《编年史》记自远古至回历302年(公元914年)之事,广搜文献,博采旧闻,内容详赡,是穆斯林世界的第一部通史,有法译本四卷。——谭注③韦尔豪森著有:《法利赛人与撤都该派教徒》、《以色列史序论》等。——谭注①内尔德克,T.著有《古兰经史》(GeschichtedesKorans,1860),戈尔德则尔著有《穆罕默德研究》(MuhammedanischeStudien,1889),《伊斯兰教讲座》(Vor-lesungenüberdenIslam,1910)等。——谭注②参阅达米斯特脱:《法国的东方研究》,第一章,《关于东方的论文》,1883年。——谭注③帕尔西人系公元7、8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印度的袄教徒的后裔。——谭注④钵罗婆语,流行于公元3至8世纪的古波斯语,多用于书写袄教经典。——谭注①《雅斯那》,为袄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中的一篇,收有祈祷文及宗教仪规等。——谭注②参阅本斐:《东方语言学史》,1896年;达姆斯特泰尔,《法国的东方研究》,第二章;马克斯·穆勒的关于科尔布鲁克的论文,见《一所德国工场的琐记》,卷Ⅱ;勒夫曼:《法兰士·博普》,共二卷,1891—1897年。——原注\n文的相似处。在他留居印度充任法官时期,他建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翻译了梵文文学的选本,并写了关于古印度许多方面的论著。虽然他的学术造诣并不深广,但他的热情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他的工作的继承者是科尔布鲁克,即欧洲的第一个梵文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是在印度担任法官。为了阅读印度法律书,他学习了梵文;1805年,他出版一篇关于《吠陀经》的论文;这是第一次关于它们的可靠叙述。他还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他的精确的翻译和分析适切地纠正了那些业余研究者的狂想空论。如果说英国学者迈出了揭示古印度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由德国学者接替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精彩论文:《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指出了梵文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博普的功绩则在①于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阅读《摩诃跋罗多》和《乌尔斐拉》时,他震惊于梵文与哥特文之间的酷似之处。他计划编写一部比较文法:《梵文与它的女儿们》;1816年,他出版了《动词变位法体系》;这本书确立了梵文同拉丁文、希腊文和波斯文的关系。继这项成功之后,他编写了一部梵文文法;他以其晚年撰作了他的最大著作:《比较文法》。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阐明了印欧语系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一道探索的光照亮了未经记录的经验的广阔空间。梵文一旦被彻底了解后,很快就对重建古印度的文明作了尝试。拉②森最先从事综合性的论著;他是挪威人,曾受教育于波恩大学;在1847③—1862年间,出版了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论。他的著作涉及[印度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欧洲人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历史、文学和艺术、宗教和风俗。虽然范围过于广阔,以致不能使每个部分都有权威性,但是拉森的巨著确实大大推进了研究工作。在重建古印度史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布赖恩·霍奇森所找出的佛经。1821年到尼泊尔任助理驻扎官后,他④借助于一个印度学者,获得了庙宇所藏经卷的主要手稿的抄本。他的结⑤论并不全都正确,但他作为佛教研究创立人的声誊却是稳固的。他把得到的经卷分给六个图书馆,使之各有充分的数量,足以对佛教进行综合研究。最大部分的经卷落到巴黎,引起柏努夫的注意;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印度佛教研究导论》,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的。人们对亚洲宗教中这个最有吸引力的宗教一直在作着认真的研究。塞纳尔和其他少数学①者对佛陀的存在提出挑战的企图已告失败。奥尔登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②③来研究的可靠成果。马克斯·穆勒的《东方经卷汇编》使英国学者可①乌尔斐拉(Ulfilas,约公元311—383年)——哥特人的主教,译《圣经》为哥特文。这里指他的译文。——译者②参阅《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③书名《印度古文化》。——谭注④参阅威廉·亨特,《布赖恩·霍奇森传》,1896年。——原注⑤霍奇森著有《佛教文学与宗教图解》(IllustrationsoftheLiteratureandReligionofBuddhists),1841年。——谭注①塞纳尔在《论佛陀传说之特点及其由来》(EssaisurlalégendedeBuddha,soncaractèreetsesoringines,1882)一书中对佛陀是否存在提出了疑问。——谭注②奥尔登堡总结性著作名《佛陀的生平与学说及其徒众》,第五版,1906年。——谭注③《东方经卷汇编》(SacredBooksoftheEast),共五十一卷,1875年开始出版。——谭注\n以自行判断,在宗教范围内亚洲对西方究竟能提供多少教益。佩罗和齐毕士编的《古代艺术史》,插图精美;由于考古学迅速进步,这部著作中有些部分已显得陈旧,但它对于研究古代东方的整个区域依然保留其价值。布林克利的《日本和中国》共十二卷,于1903—1904年间出版;它是第一部关于远东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论。\n第二十三章希腊和拜占庭Ⅰ由于奥特弗里德·缪勒的早死,搜集古史资料的工作落到了两个年①轻人身上。东克尔的《古代史》在普及古史知识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它的第3、4卷是专讲希腊的,但只叙述到波希战争。到晚年,他又回到古典的世界,重写这本著作(从1860年以来未曾修改过),并增加两卷,叙述到伯里克利的死亡。他的关于希腊的各卷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他的学识,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观察力。在东克尔看来,一个国家的至上需要,是保卫自己防御袭击的力量。他的英雄是地米斯托克利,即“阿提喀权力的创立人,所有希腊人中最有远见和力量的人”。他虽然承认伯里克利个人有其卓越之处,却否认他的军事能力,并指责他的政策。伯里克利使雅典成为自由的和光辉的,但他却未曾使它有保卫自己宝库的力量。②恩斯特·库齐乌斯的研究方法与这种政治研究法迥然不同;库齐乌斯由于受到奥特弗里德·缪勒的演讲和友谊的影响而转到古典时代的研究。这个年轻的戈丁根大学生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听他演讲,是一个无可估价的特权;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教师。他思想清晰、演讲的生动文雅和知识的丰实,每天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迷住,鼓起我对他所复活的科学感到的新热情”。1836年,他作为家庭教师伴随布兰迪斯和他的家眷来到雅典;1840年,当他的敬爱的老师到那里游历因而丧命的时候,他充任向导。库齐乌斯在最后一刻还和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从事那项作为这次旅行的目的的事业。缪勒死后,他回到德国;1844年,他在柏林一些著名的人物面前作了关于阿克罗波利斯的演讲,因而一举成名。这个英发的青年学者成了王太子腓特烈的导师,柏林大学的讲师。①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伯罗奔尼撒的历史地理,这是以他亲自从这个地区所得的知识和对文献和遗物资料的彻底研究为根据的。1853年,在欢迎库齐乌斯加入普鲁士科学院的时候,老学者博克热情地表示了他的赞扬。“我费了一生精力所做的,是考证并精选细节,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基础。但你看到了这块地方本身,即图画的框子”。这篇②演词读起来好象一首《主啊》颂;难怪这位年轻学者觉得这是号召他去显示出那浮现在这位大师心目中的希腊文明的统一性。1856年,库齐乌斯受聘担任戈丁根大学奥特弗里德·缪勒讲座;次③年,他开始出版他的《希腊史》。这本书与蒙森的《罗马史》属于同一部丛书,它是要总结现有的知识,以供有文化的公众阅读。他写给他的①参阅海姆,《马克斯·东克尔传》,1891年。——原注②参阅《恩斯特·库齐乌斯通讯中的生活杂记》,1903年;格尔策,《同恩斯特·库齐乌斯的旅行和谈话》,见《小品文选辑》,1907年;弗里曼,《历史论文》第二集,1873年。——原注①书名《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共二卷,1851—1852年。——谭注②即四回(Simeon)的歌颂(NuncDimittis),开首有“主啊”语故名。——译者③全书三卷,1857—1867年。——谭注\n门生王太子说,“这本书不是为学者,而是为所有爱好历史的人编写的,它是一本供阅读的书,没有什么注释或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片断摘引”。对于这项工作,他是非常合适的。他是希腊文明的热情崇拜者,也是通过温克尔曼、歌德和赫尔德林的眼睛来看它的。他把浪漫派的理想主义与批判学派的精确研究结合在一起。首先,他十分熟悉这块地方本身,以及它古代光荣的遗迹。另一方面,他对希腊史的政治方面很少感到兴趣。这些品质反映在他的《希腊史》里,使这部书获得声誊,也使它的权威受到了限制。他以综合地论述这个地区作为开端;他承认自然界所起的作用,这种写法为后来的历史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年老的洪堡写道,“我一行行地阅读了你的第一卷。你关于这个地区的概述,是一幅极好的自然图画。”库齐乌斯指出,半岛位于欧亚两洲的边界上,这使它的交通便利;很有利于它的发展。象东克尔一样,他拒绝格罗特对僭主的敌对看法,也不赞成他对克利斯提尼的赞佩。他擅长描写属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和文明。《希腊统一性》的一章。评述了那些把希腊世界的分散部分联成一体的纽带——竞技和神谕、文学和艺术。关于德尔斐和奥林比亚等圣地的描写,显出他亲临目睹得来的知识。他本人笃信宗教,因而比大多数历史家更加认真地考虑希腊人的宗教。他关于波希战争的纪事平淡无奇,但《和平年代》一章则是本书的精华之一。在其他任何历史著作里也没有这样生动地体现出伯里克利时代的魅力。对于格罗脱,希腊意味着民主政治;对于库齐乌斯,希腊则是文化的代表。雅典文明是人类的一宗不朽的财富,也是人类精神的春天。他不同意关于马其顿人是野蛮人这种见解,主张腓力是懂得尊重希腊文化的;可是他把德摩斯提尼与伯里克利并列,虽然前者的工作是为人力所不及的。在德摩斯提尼鼓舞领导下的起事,是自由希腊的最后大事业;书的叙述止于喀罗尼亚战役。著作的弱点,在于论述行动方面。柏纳士指示说,他叙述事物(res)比叙述功业(resgestae)要成功得多。这一种气质上的缺陷是学殖修养所不能弥补的。他的诗人气质使他从来不很注意制度、战争和党派。他在描写文化方面胜过提尔华尔、格罗脱和东克尔的程度,恰等于描写政治问题上落后于他们的程度。虽然该书的声誉主要是由于它描述文化得来,但甚至这一部分也未能免受批评。他本人属于第一批游历过这块有魔力的地方的人们,这个鲜明的印象从未衰减,希腊在他的书中看来是一颗精美的宝石,而不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威拉摩威兹谈到过书中婉约、哀伤的语调,谈到过他对美景消逝的悲痛以及残破城市所引起的伤感。他的文体流畅而又精炼,整个著作使人感到的是文雅而不是力量。本森适当地称之为一部有启发性的书。它是根据最近研究之完备知识而编成的;它的真正成绩,在于为德国提供了第一部关于希腊历史的详细概述;但它不能象蒙森的著作那样使竞争者裹足不前。库齐乌斯的晚年部分是用于考古学的研究方面。他和王太子的友谊使他能够获得物质帮助来完成他发掘奥林比亚的工作;这项工作曾由温克尔曼提出,并在1829年由法国探测队开始。发掘工作在1875年着手①进行,并得到丰硕的收获,包括普拉克息特利①的海尔梅斯半身像在①海尔梅斯,古希腊商人的庇护神。——谭注\n内。他最后的重要著作是关于雅典的历史概论,追述这个城市在各个时代的命运。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传教师。他宣扬希腊的光荣与美丽;他的通俗论文和演说集成许多卷,把这个看法传布到极广大的读者中去。他的《历史》的大量销售可以抵消专家们对它的冷淡态度。1881年,他讽刺地写道:“当看到一本易读的书而它的作者的眉毛上没有出现汗珠的时候,德国的大学者就要耸起肩膀来了。”他深信:关于希腊文明的知识,不仅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对性格发展也是一个帮助。只有希腊给人类以和谐的自我实现的教诲。他从未真正宽恕格尔策,因为后者以全副精力来研究拜占庭帝国。没有任何历史家比这个学者更加专心致志地对待他的工作;他是在最高精神形式下的希腊主义的大祭司。在提尔华尔和格罗脱、东克尔和库齐乌斯之后,希腊历史领域内似乎只剩下编写专著的余地了,但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施利曼的发②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早期希腊历史的论述。七岁时,施利曼看到特洛伊城大火的图画,就想参观这个古城的遗址,并说道,那里的堡垒不会全部消逝的。十岁时,他写了一篇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拉丁文论文。他父亲的穷困使他不得不在十四岁时自谋生活,直到三十四岁他才开始学习希腊文。四十一岁时,他变为富翁,因而放弃了营业。1870年,他开始发掘希萨里克即特洛伊城遗址;1874年,他出版了《特洛伊城古迹考》。学术界嘲笑他,因为他天真地想指实《伊利亚特》诗篇中所描写的东西和建筑物;他认为这诗篇是实录;他还混淆了那些累积起来的不同地层①。他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而他的缺点只有学者才知道。他在特洛伊的工作遭到土耳其政府的阻挠,于是他转移注意力于迈锡尼,在那里他发现古代国王的坟墓,其中藏满黄金及其他饰品。在拍给希腊王的一个电报里,他宣布他已找出阿加米农及其家属的坟墓;但经过仔细研究后才看出:他所发现的古物并不属于同一时代;而且这些遗骸的数目与性别也与传说不符。然而,他所发现的究竟是阿加米农的还是其他国王的遗骸这一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他毕竟已揭示出一个消逝了的文明。②下一步,他在奥科美那斯又发现了所谓米尼亚斯宝库,并挖出迈锡尼附近的提林斯城堡。1890年,当施利曼逝世时,他已名满天下。在二十年内,他使三个城市出土,揭示了迈锡尼文明,并给考古学研究以一个无可估计的推动。他对希腊满怀着浪漫的依恋感情。他娶希腊女子为妻;他的儿子命名为阿加米农,他的女儿为安德洛玛刻,但他缺少进行科学发掘工作所需要的训练和耐心。他认为迈锡尼人就是荷马诗篇中的亚该亚人。后来,还是由其他学者来指出,迈锡尼文明是属于前荷马时代的;并由他的晚年同事多普费尔德来证明,赫克脱和阿溪里的城是第六个而非第二个城。②参阅舒赫哈尔特,《施利曼的发掘工作》,1891年,和埃米尔·路德维希,《特洛伊的施利曼》,1931年。——原注①他误认其所发掘的希萨里克遗址的第二层为特洛伊城。直到1932—1938年美国考古学家布勒根确定了其第七层a才是特洛伊城。——谭注②米尼亚斯(Minyas)——[希腊神话]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的国王,米尼亚人所由得名的始祖,以其财富著称。——译者\n③施利曼是一个先锋,一个“征服者”、一个天才的业余发掘家,如果说他的考古发掘显出浪漫式发掘的可能性,那么他的错误则强调指出专业知识的需要。施利曼的发现给希腊历史提供了最宝贵的新资料,但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它的,是1891年由肯尼昂发表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治制度的论著。越来越多的铭文和草纸卷、遗址的探索、无数艺术品的恢复以及古①代东方文明的重建;这一切都鼓励人们重新写一部希腊历史。部索尔的大部头著作(《希腊史》)于1885年开始出版。该书主要用力于详尽评论希腊史的资料和近代研究成果,而不着意详细叙述它的历史。作者称②它的第二版为一部新著,因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a)的发现已使单纯的修订不能解决问题。他的著作精密地论述了关于迈锡尼文明的资料,并表明荷马的世界是出现于较晚时期,而又较为简朴。作者对于历史时代城邦的建立和雅典帝国的兴亡,给予慎重精密的讨论。他还坦率地宣布,“我编写的历史,是为研究用的而不是供阅读的;就引人入胜来说,它并不企求与库齐乌斯或东克尔的著作分庭抗礼。”该书的大半篇幅是注释。③④霍姆的著名历史,是大不相同的;他也象库齐乌斯一样,是为有修养的公众写的。他宣称,他的愿望是要总结成果并区分事实与假设。“希腊人并不是总能想出最好或近于最好的行动路线;但他们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人类,即力求臻于至善境界的人们。”他在斯巴达与雅典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摈弃了库齐乌斯关于德尔斐影响的夸大说法;他主张神谕所宣示的东西,很少创见或先见,它仅仅是批准已经决定的事情。他尊敬地米斯托克利的天才;否认他是一个卖国贼。他认为伯里克利是一个大政治家,与梭伦并驾齐驱并继承其事业;但这种强烈的敬佩并未使他闭眼不见伯里克利的缺少军事才干。到了公元前第4世纪时,他认为雅典人已到了衰败阶段,但他宣称,马其顿人按广义说是希腊人。“喀罗尼亚战役对被征服者和对征服者都同样是光荣的。”他声称,如果德谟斯提尼获得成功的话,希腊会继续受到波斯的旧压迫,而且,各城邦会仍然处于内战状态。亚历山大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在他的成就中,好事大大超过坏事。第四卷即结束的一卷,叙述到奥古斯都,它第一次企图作出关于政治衰落时代的综合论述。霍姆的著作既充实而又有学术性,没有企图作出什么奇巧的议论或宣传。他没有象德罗伊曾和东克尔那样的政治的天性;关于文学和文化各章写得平凡。对于经济现象的论述也是不够的。可是,该书仍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从古币所吸取的资料,多为它的任何对手所不及。他写道,“在援引古币学时,我感觉有巨大的魅力。从这些古币的研究中,比从许多费力的典籍考证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关于西西里的几章具有任何其他希腊史所望尘莫③扎洛蒙·赖纳赫的用语。——原注①近时的研究总结在鲍尔的《希腊史的研究》,1899年,和克罗尔,《最近二十五年来的考古学》,1905年。——原注②第二版,1893—1904年,共三卷。——谭注③书名《希腊史,从历史的开始到独立的丧失》共四卷,1886—1894年,柏林版。——谭注④参阅《考古学的传记年鉴》,1901年。——原注\n及的权威。在全书中,所有举例性和批判性的注解都是精彩的。它的英译本已替代格罗特和库齐乌斯的著作,而成为学生和教师的手册。几年以后,那个在罗马长期担任古代史讲座的著名学者贝洛赫,编①写了一部与霍姆的历史大不相同的历史。这部历史虽然不太适合初学者,但对高年级学生和学者却是有更大的鼓舞作用——大胆、打破成规,并对传统提出了震动人心的挑战。他按照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写;所以他认为希腊不是民主政治的发明者,也不是美的明镜,而是科学的母亲,理性的拥护者。“我们的整个近代文明是建立在希腊的基础上的。从那里生发出那些使我们值得活下去的好东西——我们的科学、我们的艺术以及我们的知识和政治自由的理想。”他宣称,一切文明的进步归根到①底是知识的进步;这句话好象是从巴克尔墓中传来的声音。第一卷叙述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总括叙述比不上他的前辈那样详细。他对于希腊早期历史是完全抱怀疑态度的;他把多里安人的侵入事件看作是学者的虚构。但希腊的历史虽被删略很多,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却得到了特别的注意。他长期研究过历史的经济方面;他对希腊和罗马人口的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而又有成果的领域。他埋怨说,希腊的经济史从博赫以来一直受到忽视;他的关于社会转变、贸易、工业、城市的成长、人口、物价的上升以及其他主要问题的诸章,是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他对雅②典民主所作的高度批判的估价,已在他的一部引人注意的专著里宣布过。他把伯里克利称做一个操纵会议的能手;这个名称在他的笔下可并③不是一个褒词。地米斯托克利和西门曾使雅典帝国达到高峰,而伯里克利未能使之保持这个地位;他的遗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贝洛赫与格罗特相同,替克里昂说了一些好话;但除这一点外,他与格罗特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不同意关于希腊人的腐化是对斯巴达作战所引起的这个思想,因为公元前第5世纪的道德水平原是低落的。相反他们由于科学运动的发展而具有更多的德性。索福克勒斯和希罗多德还天真地信迷信,而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已显出科学思想的萌芽。贝洛赫对于雅典帝国既然不抱多少敬佩之情,所以也就不为它的覆亡而洒泪。地方本位主义使希腊各城邦不能单独或联合地负起一个国家的首要责任,即自卫。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因此喀罗尼亚战役给希腊带来了统一,即优秀的希腊人求之已久而未获得的统一。地方自治仍被留存,因为腓力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主人。贝洛赫主张: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觉得自己是属于同一种族,因而反抗决不是一个民族运动。他们都讲希腊语,只是有方言上的分歧,他们由于种族关系而紧密地联系着。希腊人把马其顿人看作野蛮人,只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而这一缺陷很快就被弥补了。虽然这个历史家把独立希腊的众所周知的故事尽快讲完,但他却留下大量的篇幅叙述那个越来越扩展的希腊文化的①书名《希腊史》,共四卷,1893—1904年。——谭注①巴克尔认为西方文明进步的关键在于知识,在于掌握知识的程度,知识发展的方向与传播的范围,见所著《英国文明史》,参见本书第二十七章第二节。——谭注②书名《伯里克利以来的阿提喀政治》,1884年。——谭注③西门,雅典保守贵族上层领袖,曾多次远征,击破腓尼基舰队和波斯陆军,公元前460年左右执政,后被放逐,451年返国。——谭注\n帝国;这个帝国开始于亚历山大的远征。他对于亚历山大的统帅和政治家地位评价不高。亚历山大之要求神权,是东方对征服者所发生的第一次反作用,是使最自由的人民走上拜占庭主义道路的第一步。正在开始他的全部功业时,他死去了,但他已推动起来的各种力量继续起着作用,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关于亚历山大用宝剑所开辟的新地区的精彩论述,占了一大卷的一半篇幅;包括贸易、币制、银行、人口、财政、社会、教育、宗教、科学、文学和艺术。他写道,“世界是属于希腊人了,但他们能够保持住它吗?”第四卷即末卷对这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开始了一个阴郁的时代,连贝洛赫也无法写得生动。爱德华·迈耶一生从事古代史的广泛研究;他关于希腊的著作占据①了这类论著的大部分。“无论古代或近代历史为了历史的伟大任务,只有在它觉察到它的世界性的时候,才可以有办法。”希腊历史的真正性质,只在把它和地中海地区各族人民联系起来论述的时候,才能被掌握,几个世代以来学者们的无稽假设也才能被扫除。他宣称,欧洲的历史开始于爱琴海上,他关于早期地中海地区各帝国的知识使他提出的关于迈锡尼文明的论断具有特殊的权威。虽然这种文明并不存在于西部希腊,但它的陶器和坟墓却在意大利、西西里和撒丁尼亚都已有发现。在小亚细亚唯一的迈锡尼大城是特洛伊。迈锡尼艺术带有浓厚的东方性,但整个看来,它的文化本质上是属于希腊的。他承认多里安人的侵入迈锡尼,但他提出一个疑问:他们是一起来的,还是逐步渗入的。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相当众多,足以淹没当地的人口。迈锡尼文化到处逐渐消逝了,因为它已经过了时。关于多里安文明,现在所知甚少;我们必须根据荷马的诗篇和象斯巴达这一类的残余来重建。这个时代的光荣是史诗。荷马诗篇是几个世纪编写的成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编辑和统一而定形的。希腊中期最重要的成绩是地中海地区的殖民事业和逐步赶走腓尼基人;关于这个过程,我们没有什么资料,但它们的遗址本身就是明证。梭伦是第一个希腊政治家,他的人格是我们所知道的;他的重要性也比克来斯特尼要大。迈尔关于波斯帝国的知识是其他研究希腊史的专家望尘莫及的;他以这样完备的知识来描述这个帝国的兴起。他关于公元前第5世纪雅典的描写在许多方面近似贝洛赫的描写。他宣称,地米斯托克利是最伟大的雅典人:在他以后,出现过大事业,但没有持久的成功。暴民是一个残暴的主人,正象一个毫无慈悲心,最反复无常的专制魔王那样;它对从米太雅第和地米斯托克利以下的人所遭受的不名誉谴责是要负责的。雅典没有真正的政府,他经常苦于无政府状态。伯里克利的政治家风度,比不上地米斯托克利,因为他具有较多的理想家的气质。“从他[伯里克利]的伟大处所产生的平衡力一旦消失后,激进民主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缺口已在他的脚下出现,而他只是推迟了这个破裂。伯里克利和任何别人都不能制定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稳定的对外政策。雅典的命运也就是希腊的命运在腓力使用武力之前,这个民族的力量已经在内部冲突中消耗净尽了。“当希腊文化达到它的最高峰并成熟为世界文化的时候,这个民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失掉。它已经①迈耶的代表作为《古代史》(GeschichtedesAltetums)共五卷,1884—1902年。——谭注\n破碎了,任何人可以俯拾那里的断片。”迈耶的叙述停止于伊巴密浓达,但他对马其顿远征所要下的论断已经显然可以看出。迈耶的批判性注释包括了关于资料和近代研究成果的完备的记载。虽然政治事件是放在首要地位,他对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宗教也同样是熟悉的。他的著作是完①全以独立研究为基础的;这一事实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它的第一卷讨论了早期历史上的问题;第二卷讨论了公元前第5世纪历史上的问题。他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研究论著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宣称,希罗多德的政治偏见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并主张:他的目的是要拥护雅典霸权,正象普鲁士学派拥护普鲁士霸权那样。另一方面,他对修昔底德景仰得五体投地,他根本不理睬对他的公平性的指责。“演说①词是他著作的神经中枢,也是他的艺术和所有历史艺术的顶峰”。根据新发现的资料重写希腊史的工作主要是由德国学者进行的,但其他两种尝试也值得注意。杜律伊在完成罗马史的著作以后,使用铭文②和考古学编辑了一部希腊史。这部著作并不企求进行深刻的或有创造性的研究,但它以动人的形式作出了有学术性的总结。他在这里比在罗马史著作里作的政治论断为少,但他对希腊民主政治的看法比在德国所流行的看法较有好感。在格罗特以后第一部由英国学者所写的重要[希腊]③历史,是伯里的作品;而且伯里是唯一企图利用大量新资料的人,这部比较简明的总结既有科学性,又有通俗性,是一篇出色的导论。作者并不想详细描述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宗教,他大体上只限于政治方面,叙述到亚历山大逝世止。很多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写成专著的;对于这一规则,希腊史也不例④外。在活着的学者中,没有人对希腊文明所提供的知识象维拉默维茨那①样多。他关于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专论阐明了文学和宗教的历史。他的巨著:《亚里士多德与雅典》是根据《政治学》再现了雅典的国家制度。他的无数专著和演讲还阐明了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者以迈耶和维拉默维茨作为向导,是不会走入迷途的。随着迈锡尼文明的发现,自然地就出现了活跃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个文明是属于荷马和多里安以前的时代,但关于迈锡尼人属于什么族这个问题,还是未获定论。就大胆启发方面说,李奇微的著作:《希腊的上古时代》,是无与伦比的。霍尔曾宣称,迈锡尼人是亚该亚人;与他不同,李奇微主张:佩拉斯吉人是希腊的原始居民,也是迈锡尼文明的创始人;他们后来相继被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征服。荷马问题继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肯定的结果还是未能确定。霍姆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荷马①此书全名为《当前的古代史研究》,共二卷,1892—1899年。——谭注①修昔底德在他的书中记载了约占全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篇幅的历史人物的演说词,用以反映人物的个性,也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这是他的编纂方法的一大特色。——谭注②书名《希腊史》(HistoiredesGrecs),1887年。——谭注③书名《希腊史——至亚历山大大帝逝世止》(HistoryofGreecetotheDeathofAlexandertheGreat),1900年。——谭注④参阅他的引人入胜的自传,英译本,1930年。——原注①维拉莫维茨著有《荷马研究》(HomerischeUntersuchungen,1884)及欧里庇得斯剧本《赫拉克里》校注等。——谭注\n曾否存在过,他是什么人,或者他写了什么。”沃尔夫所定的[荷马诗篇]写成文字的世纪太晚了,而拉克曼关于它是歌谣汇定集这个理论,也同样站不住脚。安德鲁·兰格重申荷马诗篇的统一性的立场,而吉尔②伯特·墨莱却从相反的观点上来生动地描述希腊叙事诗的兴起过程。贝拉尔根据地理知识和对腓尼基人的探索,写了一篇关于奥德赛诗篇的有③启发性的概述。荷马与梭伦之间的时期还是不清楚的,因为在波希战争之前很少铭文,但斯巴达城的发掘已表明多里安人首都要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富于艺术性。我们已远远离开了库齐乌斯的美学观点;现在根据粮食供应问题来讨论雅典帝国。齐默恩描绘出公元前5世纪雅典共和国的①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幅灿烂的图景。我们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完全用雅典的眼光来看希腊,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雅典帝国倾覆以后的时期,这个转变大部分是由于德罗伊②曾的有魄力的人格。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于1833年出版。德罗伊曾所强调的,不是亚历山大的破坏方面,而是他的建设方面。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说成是一个更丰富的历史生活的开端。马其顿人是一个与希腊人有血缘联系的种族;德谟斯提尼是他国家的最坏的朋友。这个年轻的历史家在二十四岁时就已经几乎沉醉于他的英雄的光荣事业,他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对全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这本著作的后来版本里,浮夸的语调变得平和了,对资料的处理也有了更多的批判性;他具有类似蒙森著作的魄力和热情,因而迄今还有它的地位。在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德罗伊曾进而继续研究了他的后继者的命运。他写信给韦尔克尔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象我冒昧称做‘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他原想要概述这一整个时代,既写它的战争和统治者,又写它的文化和宗教,但它以政治史作为开端后,并未更向前跨进一步。因此,《希腊化时代历史》是一个气势逼人的片断,而不是他的梦想的全面概述。甚至德罗伊曾也未能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六位将领之间的斗争和竞争的故事写得有吸引力,但他使读者经常不会忘这个酝酿重大问题的时代的意义。后来,他在进行其他研究的余暇还对这本著作进行了仔细的修订,因而在历史著作中它还继续占有一个荣誉的地位。舍费尔在关于德谟斯提尼的缜密的专著里赞扬了这个大演说家的天才和智慧。尼斯的《从喀罗尼亚战役起的希腊史》则热烈称颂亚历山大大帝的性格和政治家风度;这是一部便于查考的政治性记事。另一方面,卡斯特在他的《希腊化时代史》里,虽然赞颂腓力的节制态度,但他把他的儿子描述成一个有疯狂野心的人,消耗精力于争取神权和征服世界的梦想。对于这些征服者的看法,虽然还有分歧,但现在却已认识到,喀罗尼亚战役并不是希腊史的终结,而是希腊化时代的世界使命的开端。至于同盟的故事,弗里曼关于联邦政府的著作至今还是无②A.兰格著有《荷马与史诗》(1893年),《荷马及其时代》(1906年)二书,墨莱著有《希腊史诗的兴起》(1907年)。——谭注③书名《奥德赛札记》。——谭注①书名《希腊共和国:五世纪雅典的政治与经济》(GreekCommon-wealth:PoliticsandEconomicsinFifthCenturyAthens),1911年。——谭注②参阅G.德罗伊曾,《J.G.德罗伊曾》,卷Ⅰ,1910年。——译者\n有出其右者。没有人能把亚历山大帝国的破碎河山叙述得饶有趣味,但①②贝凡关于塞琉古朝的著作和布歇-勒克莱尔关于托勒密朝的详细描写则对这一多事时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希腊制度是很多专著的论题,但由于各城邦的情况繁复,很难作出综合的概述,所以没有人试图③写出相当于蒙森的《宪法》的著作,而这种著作是维拉莫维茨认为最迫切需要的。研究希腊文化所需要的工作量比研究罗马文化要大得多。马哈斐关④于希腊生活和思想的研究著作是一部有用的导论,但为了充分处理各个部门,我们必须转向专家们写的著作。布兰迪斯出了一部深刻分析前苏①格拉底时期思想家的著作;海因里希·里特尔写了一部关于古代哲学的②概论,这本著作有无可责难的学术性和清晰的表达法;但是这两本书都③未能建立起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的逻辑联系。黑格尔在他的《演讲录》里首先企图完成的正是这个任务,这本著作应用辩证的方法来说明各学派的新陈代谢。但它并未企求专家研究的地位。他的解释虽然总富有启发性,但常常是武断的。策勒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他的《希腊人的哲学》于1851年出版,经过多次改订后它成了德国学术研究的光荣之一。在较近时期,冈佩茨的《希腊思想家》获得了几乎与它同等的声望。宗教研究是更使人望而生畏的。阿达尔柏·库恩和马克斯·缪勒主张:希腊神话是各印度—日耳曼种族的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它也主要是④太阳系的理论;这个论点现在已不复能找到支持者。在重述信仰的演变⑤这项困难工作上,没有任何学者比乌泽纳和迪特里希能显示出更敏锐的洞察力。铭文已使我们能对某些信仰作出更正确的估价,其中有些信仰⑥如对多度那·宙斯的崇拜证明只是注意于琐屑事情的。阿波罗不再是一①个多里安族的或甚至一个希腊的神,他已和吕西亚相揉合。法内尔对于②希腊各城邦的宗教信仰,作了百科全书式的概述。关于秘密祭礼的研究③也在大力进行。克罗策尔曾说,这些祭礼体现了许多神秘的真理,这种①书名《塞琉古王朝》(HouseofSeleucus)二卷,1902年。——谭注②书名《托密勒·拉戈斯王朝史》(HistoiredesLagides)共四卷,1903—1907年。——谭注③全名《罗马宪法》,1871—1876年,共三卷,参见下章第一节。——谭注④书名《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期到罗马征服》(GreekLifeandThoughtfromAlexandertotheRomanConquest),1887年。——谭注①布兰迪斯著有《希腊哲学发展史》(GeschichtederEntwickelungendergriechischenphilosophie),1862—1864年。——谭注②书名《希腊罗马哲学史》,1838年。——谭注③参阅策勒的《小品文》卷Ⅰ,1910年。——原注④太阳系,指太阳及所有绕太阳而旋转之星体。——谭注⑤乌泽纳著有《圣诞庆典》,1888年;第特立喜著有《宗教学文献》,1905年。——谭注⑥多度那,位于希腊北部伊皮鲁斯山中,有著名的宙斯圣堂。传说有来自埃及的鸽子降于橡树上,口吐人言,预告休咎。——谭注①吕西亚(Lycia)——古地名,在小亚细亚西南部。——据希腊学家研究,阿波罗神话与吕西亚有密切关系。阿波罗的称号及其母的名字,有吕西亚语根;他生于月之七日,而尚七乃是东方人的风习。——译者②书名《希腊诸城邦的宗教祭祀》(CultsoftheGreekStates),共五卷,1896—1909年。——谭注③克罗策尔(Creuzer,G.F.1771—1858年)普鲁士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译者\n天真的想法已被洛贝克驳倒,但很明显,它们提供了信仰所不能提供的情感滋养料,正好象基督教圣餐和神剧提供的是情景和仪式,而不是教义或神学。福卡特和赖岑施泰因、康福特和简·哈里森以无畏的步伐踏④进了那个被俄耳甫斯和狄俄尼索斯所支配的朦胧世界。罗德的杰作:《赛⑤姬》是一部论述希腊宗教各方面的最令人满意的专著,它追溯了永生概⑥念在各个时代的演变。托洛蒙·赖纳赫的多卷集著作,以精辟的创见评述了许多论题。弗雷泽还分析了波赛尼亚斯的证明。至于近代研究工作的详细结果,我们必须到罗舍尔的《神话学辞典》中去寻找。对艺术的研究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而得到迅速进步。佩罗和齐毕士对古代世界进①行百科全书式的概述,把希腊放在这种广阔的背景里来处理希腊。富特夫伦勒的富有魅力的著作《希腊雕刻杰作》和它大胆的探本穷源的分析,②③④曾激起研究的兴趣。克鲁瓦泽兄弟、克里斯特和马哈斐划出了文学发⑤展的线索。苏塞米尔关于古希腊后期文学的巨著以及罗德关于希腊小说的专著,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关于希腊历史的资料一年比一年增多起来。博赫的《铭文集》包括了八千张铭文;数字上只少于《阿提喀铭文集》;但它本身仅仅是柏林科学院在巴黎和维也纳帮助下所收集的巨大汇编的一部分。对它们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基希霍夫关于希腊字母的出色著作和乌尔里⑥希·克勒的研究成果。前者按照字母的形成来区分地点和日期。纸草卷⑦和陶器碎片使希腊化世界各部门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果实,尽管大多是在行政和文化领域,而不在政治领域内。现在发掘的技术已经完善;在雅①典,考古学学校的建立已可保证提供热情而且有水平的工作人员。法国人在欧摩尔的指导下,迁移了那个掩盖着德尔斐的村庄,并挖掘了提洛④俄耳甫斯,阿波罗之子,善弹琴,为音乐之鼻祖。传说,其妻死,俄耳甫斯入冥求之。冥司约以出冥前不得回顾,俄失约,其妻遂消逝。狄俄尼索斯,酒神、丰收之神,周游世界,传播葡萄种植之术。福卡特著有《希腊秘密宗教之起源与性质研究》、《希腊神密宗教》;赖岑施泰因著有《希腊的神密宗教》;康福特著有《希腊宗教观念》;J.哈里森著有《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等。——谭注⑤塞姬(Psyche)——[希腊神话]为灵魂化身之美女,相传,系山林川泽女神,因ﻀ锉话껉瘢–upid)所爱而得永生。——译者⑥书名《礼拜、秘密祭祀与宗教》(Cultes,mythes,etreligions)共五卷,1905—1923年。——谭注①指二人合著之《古代艺术史》(Histoiredel’artdansl’antiquité),共十卷,1881—1914年。——谭注②即鲁洛泽塞,阿尔弗雷德(Croiset,MarieJosephAlfred,1845—1923年)和鲁洛泽塞,莫里斯(Maurice1846—1935年)。兄弟,都是法国的希腊学专家,合著有《希腊文学史概论》(Manueld’histoiredelalitératuregrecque),1900年。——译者③克里斯特著有《希腊文学史,——至查士丁尼时代》(GeschichtedergriechischenLiteraturebisaufdieZeitJustinians),1880年。——谭注④马哈斐著有《希腊古典文学史》(AHistoryofGreekClassicalLiterature),1880年。——谭注⑤书名《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文学史》(GeschichtedergriechischenLiteraturinAlexandrinerzeit)共二卷,1891—1892年。——谭注⑥有一篇良好的通俗概述,参阅牛顿,《论希腊铭文》,见《艺术和考古学论文集》,1880年。——原注⑦维尔肯,《希腊纸草卷》,1897年提供一篇极好的纸草学概述。——原注①参阅米凯利斯,《19世纪考古发现》1908年;加德纳,《希腊史上的新章》,1892年;以及拉得,《雅典法国学校的历史》,1901年。——译者\n岛;该岛一直被称为希腊的庞贝城。美国人在挖掘阿耳戈斯的赫勒安神殿后,开始发掘科林斯城;雅典英国学校则探索斯巴达古城。希腊学者②们也积极参与了恢复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考古学会发现了阿克罗波利斯废墟上的前迈锡尼的遗迹,发掘了埃皮多勒斯和多度那,并完成了法国人在埃琉西斯的发掘工作。在爱琴海的彼岸,塞浦路斯岛上的文明遗迹已由切兹诺拉(一个美国领事)奥内法舍—里希特和迈尔斯发掘出来。在南俄坟墓内发现了宝石和珠宝饰品。关于西徐亚人的文化和希腊人从多瑙河口到高加索的殖民事业的早期历史,总结在埃利斯·明斯的四开本的宏伟著作:《西徐亚人和希腊人》里。多普费尔德完成了特洛伊的发掘工作,并证明它的最下层城址是属于前迈锡尼时期的。胡曼发掘了③帕加马城。霍加斯进一步发掘出以弗所城的阿耳特米斯庙;它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在1873年已由伍德发现。除了《政治学》外,近年来④还发现了巴克基利得斯和赫罗达斯的诗篇,萨福和品达罗斯的片断作⑤品、希佩里德斯的演词、狄奥波普斯的八百行作品以及米南德和欧里庇得斯的大批残稿。任何遗址出土的纸草卷也不象在法尤姆省的奥克西林克斯那样丰富;在那里格伦费尔和亨德是为埃及探测基金会工作的;他们使学术界处于欣悦期待的状态。虽然有时发现的东西没有什么重要价值;但它们总合起来,就真是增加了我们对一个古文明的知识;关于这方面,每一点消息都是珍贵的。Ⅱ19世纪,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很少有进展,比对东方帝国的兴趣复①②活更加重要的。拜占庭研究是在17世纪由杜孔日开始的,但在两百年时期中它撒播的种子并未曾发芽。18世纪对于整个中世纪时代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希腊帝国尤其显出不友好的态度。在伏尔泰看来,拜占庭历史是一系列可怕而又可憎的偶然事件;在孟德斯鸠看来,它是一连串叛③乱和背信的事件。他们的同国人勒博的巨著还证实了拜占庭是讨厌而又沉闷的国家这个通俗印象,并且加上一个不适当的书名:《下帝国》。更糟糕的是,吉本未能认识到它的真正性质和重要性。他写的君士坦丁和朱里斯,希腊历史家约生于公元前第4世纪。著有《希腊史》;米南德,公元前343?—291?,雅典喜剧作家。——译者安、狄奥多西和查②参阅西奥多·赖那赫所写的一章,见《演进中的希腊》,艾博特编辑,1909年。——译者③以弗所,在小亚细亚西岸,为古希腊人所建城市,上有阿耳特米斯(月神)神庙。——谭注④巴克基利得斯(Bacchylides)公元前5世纪与品达罗斯齐名的希腊诗人;赫罗达斯(Herondas),约公元前3世纪希腊笑剧作家、诗人。——谭注⑤希佩里德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演说家支持狄摩西尼,反对马其顿;狄奥波普①参阅迪尔,《拜占庭研究》,1905年;克伦巴赫,《拜占庭杂志社论》,转载于他的《通俗论文》,1909年;以及格兰德,《拜占庭史的研究》,1934年。俄国的贡献,总结于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卷1,第1章,1928年。——原注②杜孔日对拜占庭历史和史料的搜集和钻研,用力至勤,他参加了《拜占庭历史家著作汇编》的工作,还独立编辑出版了《中世纪和近代希腊文作家词典》,被认为是拜占庭史学的创立者。——谭注③勒博(Lebeau,Charles,1701—1778年)——法国历史家,著有多卷本《下帝国史》。——译者\n①士丁尼的几章是无与伦比的,但对希拉克略以后的历史,他的兴趣锐减;他带领一队黯淡无光的人物没精打彩地穿过舞台。它是“一个关于衰弱和愁苦的沉闷而又单调的故事”,描写一个腐败而又柔弱的国家,徒有一层文明的外表。吉本未能了解拜占庭对文明的功绩,以及它的许多人物的伟大之处。对希腊史的兴趣随着希腊独立战争和关于近代希腊种族由来的争论而复活起来。乔治·芬利,部分由于他与戈丁根大学的一个希腊同学的②友谊,决定游历希腊,去亲自判断希腊人的状况和战争的形势。1823年他在梅索朗吉昂和拜伦在一起。这个诗人说,“你年轻而有热情;当你象我一样地了解希腊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失望。”这项预言后来是应验了。当希腊完成独立后,他在阿蒂克买进了一块地产。“我失掉了我的金钱和我的工作,但我懂得了什一制怎样产生一种一个人无从反对的社会状况和教养习惯。当我浪费了我所有的一切以后,我的注意力转到学术研究上来。”他的终身事业是在1844—1861年间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他晚年致力于彻底改订这本著作,并继续叙事到1864年。他死后,③他的专著合成一部著作出版,书名《罗马征服以来的希腊史》弗里曼在1855年称之为吉本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在英文著作中最有创见的历史著作。克鲁姆巴克尔,即评论家之王,热烈地赞扬他关于希腊人性质的知识和他的叙事才能。芬利勇敢地选择了一个不通俗的题目,并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从古典希腊史专家搁笔之处开始,他从头至尾概述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并继续叙述了帝国覆亡以后四百年时期的历史。他虽然一直把希腊放在前景,却提供了一部关于东方帝国的相当完备的史纲。他表明,帝国政府所达到的标准远远超过中世纪时任何其他国家,并主张,它的人民的道德状况在圣像破坏者时代优于任何同等人口的道德状况,无论在当时或早些时候,无论在世界的任何部分。法律是高度发展的,秩序维持得很好,司法也执行得不坏,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帝国的财政压迫和停滞的中央集权制使帝国僵化了。这著作最新奇的特征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和经济状况方面。的确,他是一个研究法律和经济的学者,而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而且由于目睹了独立的希腊的种种弊病,使他追溯它们几百年来所产生的影响。他在写作时,对于希腊人民没有表示什么夸饰的同情。他叙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无动于衷,反而称颂穆罕默德二世,并宣扬土耳其人在他们征服时期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关于土耳其的统治他描绘了一幅丑恶的图景;其中的主要情节是他们把进贡来的基督教儿童组成土耳其苏丹的亲卫军。在叙述希腊独立战争时,他谴责了它的领导人,而赞赏人民的爱国心和坚忍精神。他对当代希腊的描写虽是高度批判性的,他却承认,希腊的进步已达到了力所能及的程度。①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在位。即位初期曾击败波斯,并夺回被他们夺去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这些地区在7世纪30、40年代又为阿拉伯人占领。——谭注②参阅他的简短自传,见托泽版,卷Ⅰ,1877年。关于他著作的赞颂,见弗里曼,《历史论文集》,第3集,1879年,和法尔麦拉耶,《全集》,卷Ⅲ,1861年。——原注③此书初版,1844—1861年,修订版七卷,1877年。——谭注\n①虽然芬利已指出法尔麦拉耶的很多证据带有推测性质,但首先驳斥关于①人口全盘移置的论点,还是霍普夫的著作;这本著作是以阿拉列的入侵作为开端。他的论著淹没于欧施和格鲁贝尔的《百科全书》之中,因而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可是没有别人象他做过这样多的工作,来把希腊中世纪时代的研究放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他的研究成绩被采入赫茨贝格所编的课本;后者的《希腊史》是从古典时代末期讲起,很有条理地总结了别人研究的成果。约在1870年时,长篇叙述的时代让位给专著的时代。在拜占庭研究上领先的,以前是德、英两国,而现在,由于法国人朗博出版了他的《君②士坦丁合法继承人》一书,而改由法国领先了。该书虽然只研究了一个统治者,可是它体现出关于拜占庭历史的一个确定的概念。他宣称,专政和行政集权制是必要的,因为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的局面;政教结合也是必要的,因为帝国只能以基督教来解除野蛮人的武装;它的统治者时常被迫使用贿赂和欺骗手法,因为他们所要对付的是粗野而又无信义的部族。“我们一直无情地对待它的罪恶,而没有注意到它的优点;而它必已具有这些优点,才能使它在西方帝国覆亡后还存在了千年之久。”他补充说,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必须应付象它所遭遇到的攻击。波兰具有研究拜占庭的历史家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包括俄文的知识在内,但他很少重一观点招致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但也促进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和人种学的研究。著有《摩里亚半岛史》(GeschichtederHalbirselMorea)。摩里亚系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古称。——谭注新涉足于这个使他成名的领域。他的领导地位后来由施卢姆贝格尔接替了;后者在以《拉丁东方的货币》专题论文获得声誉后,于1884年出版了他的精装的著作:《拜占庭印章学》。这本著作的内容由于附入千余幅插图而丰富起来;它对于圣像学、朝廷的显贵和仪节、帝国的地理和行政区划的研究,都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主要是借助于文物资①料编出了关于拜占庭统治者的专著;这部丛书附有丰富的图片,他也以②③此最为出名。丛书的第一本是专述福卡的,他把后者从利乌特普兰德的恶毒诽谤里拯救了出来;第二本是专述巴锡尔即“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的突出人品;最后一本是专述巴锡尔的后继者们。虽然这些传记只①法尔麦拉耶J.P.(1791—1861年),奥地利希腊史学者。主张古希腊人种,由于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断侵入,半岛已完全消失,近代希腊系一混血的民族。这①霍普夫,卡尔,(1832—1873年)德国学者,以研究中世纪史知名。主要著作有《希腊史》(GeschichteGriechenlands),1876—1878;《拜占庭与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derByzantinesunddesOsmanischenReiches),1883年;《中世纪雅典城市史》(GeschichtederStadtAthenimMittlealter),1889年。——谭注②君士坦丁合法继承人(ConstantinePorphyrogenitus)——东罗马帝国皇帝,即君士坦丁七世,公元912—959年在位。——译者①著有《十世纪拜占庭皇帝本纪》(UnempereurbyzantinauX■esiècle),1890年,《拜占庭伟人传》(L’Epopéebyzantine)共三卷,1890—1905年。——谭注②福卡,拜占庭皇帝,602—610年在位,残暴无能,为军队所拥立,为乱军所杀。——谭注③利乌特普兰德(死于972年),意大利主教,编年史家,于949、968年秉承皇帝奥托二世之命,出使拜占庭,著有《出使拜占庭记》,述其第二次出使经历。——谭注\n涉及了一个世纪的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驳倒了它是一个腐败国家这个传统说法。第三个致力于研究东方帝国的法国学者是第尔;他曾在雅典和罗马的法国学校受过训练。他开始时研究拉温那总督区和非洲的行政区,然后编写了关于查士丁尼和第六世纪文明④⑤的概论,该书附有丰富的图片。他关于狄奥多拉的单行本专著描写了一个意志坚强、智慧过人的妇女,她度过了一个坎坷多事的青年时期,①死后使皇帝眷恋难忘。他关于拜占庭艺术的论著是关于这一有魅力的领域的卓越的概述。在普及拜占庭历史方面,再没有人比他做过更多的工作;而他的工作也获得了报偿,因为他被聘担任为巴黎大学于1899年创②设的拜占庭史讲座第一任主讲人;该讲座,迦兰登关于昆尼南朝的著作虽然较少通俗性,却也具有同等的价值。③在英国,伯里关于9世纪以前的东方帝国的渊博的论述以及他编的吉本著作的校订版,为他赢得了第一流学者的地位。威廉·米勒和伦内④尔·罗德阐明了长期湮没的希腊中世纪时期,皮尔斯则重塑了1204和⑤1453年的悲剧。德国最大的拜占庭学家是克鲁姆巴克尔;慕尼黑大学曾在1892年为他创设了讲座;他关于拜占庭文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述是整⑥个拜占庭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卓绝的著作。它决不是一个关于诸作家的单纯分析性的书目,而是阐明了帝国的各个方面。他所创立的《拜占庭杂志》也是同样有价值的事情。扎哈里亚·冯·林根塔尔探索了拜占庭①的法律,这个领域是萨维尼不熟悉的。皮希勒追述了东方与西方教会的②③分裂;赫根勒特尔关于君士坦丁堡教长佛提乌的宏伟专著,说明了帝④书名《查士丁尼与六世纪拜占庭文明》(Justinienetlacivilisationbyzanti-neauVI■esiècle),1901年。——谭注⑤狄奥多拉,查士丁尼之妻。史称其出身微贱,以追求权势,凶残奸诈,意志顽强,明敏善断著称,对皇帝的施政有很大的影响。——谭注①书名《拜占庭艺术概论》(Manueld’artbyzantin),1910年。——谭注②即拜占庭史上的马其顿王朝(1050?—1460?)。迦氏书名《昆尼南两朝史》1912年。——谭注③伯里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后期罗马帝国史,395—800》,(HistoryoftheLaterRomanEmpirefromArcadiustoIrene,395A.D.to800A.D.),共二卷,1889年。《东罗马帝国史,802—867》(HistoryoftheEasternRomanEmpire,fromthefallofirenetotheaccessionofBasilI,A.D.802—867),1912年。——谭注④米勒著有《法兰克时代希腊史,1204—1566》(AHistoryoftheFrankishGreece),1908年;罗德著有《亚该亚诸王与摩理亚的编年史》(ThePrincessofAch-aiaandtheChronichesofMorea),共二卷,1907年。——谭注⑤书名《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第四次十字军故事》(FallofConstantinople,beingthestoryofthefourthCrusade),1885年。《希腊帝国之覆灭与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故事》(DestructionoftheGreekEmpireandtheStoryoftheCaptureofConstantinople),1903年。1202—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远征。——谭注⑥书名《拜占庭文学史》(GeschichtederbyzantinischenLitteratur),1891年。——谭注①其代表作为《希腊—罗马法律史》(GeschichtedesGriechisch-R■miscChenRechts),1856—1864年。——谭注②书名《东西教会分裂史》(GeschichtederKirchlichenTrennungzwis-chenOrientundOkzident)共二卷,1864—1865年。——谭注\n国的早期历史以及东西教会之间的关系。格雷戈罗维叙述了中世纪雅典④⑤的命运;勒里希特以毕生精力辛勤地研究十字军。海德关于东方诸国⑥商业的详尽论著成了经济史的古典著作;它说明了帝国的商业史和外人居留地的命运。欧洲地区的斯拉夫人对于帝国历史的兴趣也迅速增长起来,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不知道拜占庭的影响,斯拉夫人的历史是无法理解的。1894年,俄国学者们创立了《拜占庭评论》;1895年由乌斯宾斯基指导在君士坦丁堡创设了考古学研究所。关于拜占庭艺术的最有⑦创见的论著,是斯特尔齐戈夫斯基的著作;他是一个奥籍波兰人。拜占庭研究在19世纪后半期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但这个领域非常广阔,甚至今天它还是最有前途的历史研究领域,在尼布尔赞助下曾在波恩开始出版《拜占庭汇编》;但编辑得很粗劣,没有多大价值。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才可获得有学术性的资料汇编。没有任何著作比《秘①史》引起更多的争论,但一般人已接受了丹的见解:这本著作确实是由普洛科比阿所作。丹是研究民族大迁移的历史家,也是卓越的历史小说:《争夺罗马的斗争》的作者。1904年,国际科学院协会曾决定编辑关于希腊中世纪宪章汇编。现在,在巴黎和慕尼黑、莱顿和莱比锡、圣彼得堡、敖德萨和布达佩斯各大学里,都已设立了拜占庭讲座。由于两个世②代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拜占庭:它不是一个贫血的无生气的国家,而是一些大政治家和军人的母亲;当中欧和西欧陷入黑暗状态时它是希腊文化的故乡;是一千年期间基督教欧洲的屏障,是斯拉夫各种族的开化者;它不再是希腊的一个堕落后裔或罗马的一个不肖子,而是具有自己③个性的一个基督教国家。生气蓬勃的伊索里亚朝可与西欧的任何王朝分庭抗礼。弗里曼说得对:它在几百年时期中是世界上唯一的正规而有秩序的政府。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才能把这样一些复杂的地区和种族结合在一起。它的行政机构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最细密的制度;拜占庭宫廷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正象凡尔赛王宫对17、18世纪各国统治者的影响一样。旅行者和使节们对帝国首都的繁华景象惊异不已;他们感觉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比他们以前在国内所了解的更加复杂、有更高度组织的文明。可是,也没有从贬抑转到过分颂扬的另一极端这个倾向。东方帝国是一个官僚制的国家,在那里没有什么政治自由。在文学方面,它未曾产生杰作,对科学、神学和哲学,它也很少注意。只是在艺术领域③书名《君士坦丁教长佛提乌:生平,著作及希腊教会分裂》(Photius,PatriarchvonConstantinopel,SeinLeben,SeineSchriften,unddasgriechischeSchisma),共三卷,1867—1869年。——谭注④书名《中世纪雅典城市史》(GeschichtederStaatAthenimMittlelater),1889年。——谭注⑤勒里希特著有:《第一次十字军史》,《耶路撒冷王国史》,《十字军史纲》等书。——谭注⑥书名《中世纪东方诸国商业史》(GeschichtedesLevantehandelsimMittlelater),共二卷,1879年。——谭注⑦书名《东方或罗马》(OrientoderRome),1901年。——谭注①《秘史》为著名拜占庭史学家普洛科比阿(约公元500—565年)所作,记查士丁尼皇帝时代的内外大事及宫庭内幕。——谭注②由哈里森通俗地总结在他《里德演讲集》,1900年,重印于《在我的著作中间》,1912年。——原注③伊索里亚朝是利奥三世皇帝创建的王朝,利奥出身于伊索里亚省区,因而得名。统治时间717—802年。——谭注\n内,它具有创造性。比克拉斯说得很对,“基督教君士坦丁堡的使命,不是创造,而是挽救”。可是,它在早期中世纪的蛮族时代保存希腊文化,并防止它受伊斯兰教攻击,这也是有功于文明的。\n第二十四章蒙森和罗马史研究Ⅰ在尼布尔死后,罗马研究的历史大部是关于一个学者惊人活动的纪①录。特奥多尔·蒙森是石勒苏益格一个牧师的儿子,是三兄弟中最长者;他们都以研究古典世界而成名。他在基尔大学研究法律时,已将注意力②转向罗马;他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又由于奥托·雅恩的演讲而有所增加。他最初的著作:关于罗马社会的拉丁文专论与罗马部族的研究,赢得了学者们的注意;在二十六岁时,他已成为他那一行的专家。由于丹麦政府提供的旅行奖学金,加上柏林科学院的少量津贴,他游历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对他一生正如对兰克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他在永恒之③④城的活动中心,是那由本生与格哈德在1829年所创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在那里,他和该所的秘书亨岑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后者已经开始收集铭文的工作。在他关于罗马会社的专论里,这个年轻学者已表示要编辑一部拉丁铭文集的愿望。在1800年以前,已有十余部铭文汇编;但它们都包括一①些伪造品。拉丁铭文学的基础是马里尼奠定的;他关于古罗马十二祭司②团(FratresArvales)的著作(1795年出版)包括千件尚未为人所知的③铭文。他的榜样为其门生博吉西所仿效;后者重建了罗马执政官的年表(Fasti)。在同博吉西通过几次信后,蒙森前往他在圣马力诺的家中访问,并讨论拉丁铭文集的前途。柏林科学院聘请奥托·雅恩担任这项工作,而雅恩请他的旧门生帮忙。但法国科学院当时尚未放弃编辑铭文集的想法,博吉西又曾允许给予帮助。由于这一竞争,蒙森决定独自进行收集萨谟奈铭文的工作,于是按照博吉西的劝告,移居到那不勒斯王国。在南意长期漫游后,他重游圣马力诺,而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国。1852年,他出版《那不勒斯王国铭文集》并题词献给“导师、恩人与朋友博吉西”。在搜寻铭文时,他已注意古代世界的其他方面。他游历意大利的主要成果,除铭文集外是掌握了古代方言。他的《奥斯坎语(Oscan)研究》及跟着出版的《下意大利方言》,是对历史和人种学同样也是对罗马时代意大利语言的划时代的贡献。①最完备的记载,见哈特曼,《蒙森》,1908年。最好的评传是由下列的作家所写:纽曼,见《历史杂志》,第CXⅡ卷;卡斯特,见《历史季刊》,1904年;哈弗菲尔德,见《英国历史评论》,1940年1月号;卡米耶·朱利昂,见《历史评论》,第LXXXⅣ卷;奥托·希施费尔德,见《小品文》,1913年。吉兰的论文,见《近代德意志及其历史家》,1899年,该文过分强调他的政治思想。——原注②雅恩,O.,(1813—1869),德国考古学语言学家,基尔等大学教授,曾刊行多种希腊拉丁古籍。——谭注③原文EternalCity,罗马的别称。——译者④参阅米夏埃利斯,《德国考古学研究所》,1879年。——原注①参阅许布纳,《罗马铭文学》,见伊万·缪勒,《手册》。——原注②祭司团,由祭司十二人组成,主持每年5月奉祀大地女神(DeaDia)的典礼,以祈丰年。——谭注③参阅杂记,见博吉西,《全集》,第X卷,1897年。——原注\n蒙森回到基尔,赶上参加1848年的骚动事件。在汉堡的一次街道暴动中,他受轻伤,因而不能追随他的弟兄们参加反对丹麦的志愿军,但他得到机会协助编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即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由于同战争和革命的密切接触,他得以洞察那些创造历史的力量与热情,而他编写新闻的短期经验还发展了他的锋利的文风;这种文风正是他的《罗马史》之所以出名的部分原因。这次民族运动的失败使他不能再在荷尔斯泰因呆下去,因而他接受莱比锡大学罗马法讲座的聘书,在那里他同奥托·雅恩与莫里茨·豪普特密切交往。但是反动势力是大的;1851年,萨克森首相博伊斯特将这三位学者一起免职。于是蒙森接受聘请到苏黎世去,在那里从事收集瑞士铭文的工作,惟范围太小因而不久他即移居布雷斯劳。蒙森在写给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的一封信里说明他编写《罗马史》①几乎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我在青年时期,曾想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罗马刑法研究、法律文献的出版、《罗马法全书》的撮要,但从未想到过写历史。在莱比锡一次应邀作公开讲演时,我曾发表一篇关于格拉古弟兄的演说。当时,出版家赖默尔与希策尔也在座;两天以后,他们约我为他们编辑的丛书写一部罗马史”。他还写信给亨岑说,“现在该是写这一著作的时候了。现在比已往更加需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一个更广大的读书界”。一年以后,即1851年,他宣称,他处在这项工作的无穷尽的困难的重压之下。他最初的计划是要用两卷来叙述罗马共和国,用第三卷来叙述帝国,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只有在收集铭文以后才能叙述帝国。所以这三卷篇幅都用于叙述共和国。他并按照委托,以结果而非以过程来充实他的著作。在尼布尔的著作里,叙述的线索消失于议论的迷宫里。蒙森则不然,他所求的只是传统说法,用以证实或例解从制度与惯例残余所得的推论对于别的历史家所注意的问题,他一掠而过,而以概略的笔法重说古代意大利人种、制度与社会生活。完全的历史时期开始于皮洛士时代。他关于汉尼拔的论述,不如阿诺德的论述引人入胜;关于格拉古弟兄的描写,他也缺少同情。他以全力论述马略与苏拉,并以无比的魄力与灿烂文笔描写共和国的垂死挣扎。①《罗马史》很快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它给近代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它那准确的笔法,它那蓬勃的活力,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明色彩给每个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乎在同一时候,格罗特与蒙森各把雅典与罗马带入近代世界的认识与文化范围。普通读者欢欣地迎接这部著作,学者们也证明它的无懈可击的博学,可是有些专家却因看到老的假设已被抛弃而提出新的假设又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大为恼火。其他专家还埋怨它缺少沉着性与严肃态度。的确,②它是属于政论家兼学者的作品类型。拉比埃乌斯被看作是一个拿破仑的①《罗马史》共三卷1854—1856年。1885年出版第五卷,此书无第四卷,作者认为塔西陀的《罗马编年史》对这一时期已有记述。——谭注①关于英国人的评断,参阅弗里曼:《历史论文》,第2集,1873年。比较卡尔·彼得,《罗马史的研究》,1863年。——原注②拉比埃乌斯(Labienus,公元前98—45年)——罗马恺撒的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译者\n③④元帅;苏拉被看作是唐·璜;伽图被看作是桑乔·潘萨。我们可以看到容克地主与非常财政(hautefinance)。他写给亨岑的信里说,“关于使用近代语词有很多理由。我要把古代人从他们虚渺的宝座上拉到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把执政官看作市长的原因。也许我做得过火些,但我的用意是很对的”。还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是针对《罗马史》的最后一卷的。全书中没有任何部分写得象恺撒同他敌人斗争的故事那样有活力,因为这位历史家走下他的司令台而跃入了这场搏斗。庞培、西塞罗与伽图都被鞭挞,好象他们是一个可恨的政治派系的活着的首领;同时他们的偶像在舞台上支配一切,容光焕发、举世无双,无敌于天下;他是社会的救星。蒙森对不灵验的天使没有什么好感。他谴责庞培无论在好的或坏的方面都缺乏热情。哈弗菲尔德说,“他在1848年碰到过好多西塞罗;他们讲话漂亮而行动软弱”。他轻蔑地谈到元老院中老实的庸人。另一方面,恺撒是支配命运的人;他看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既不希望征服世界也不希望自己称帝。他的目的,是要复兴这衰败民族的政治、军事、道德与智慧。他论述恺撒的改革时宣称,这座改革大厦中的任何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一个人永垂不朽。施特劳斯评论说,“把恺撒理想化是多么无意义!一个历史家可以谴责,但不可谩骂;可以赞扬,但不可丧失分寸”。弗里曼叹息道,他是没有什么是非观念的。甚至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对他强烈的憎恶情感也感到遗憾。蒙森对于说他有所偏袒这项指责,毫不介意。他写道,“凡是象我一样从历史事件生活过来的人都开始看到历史的编写或创造不是没有爱憎感的”。他拒绝政治上的任何绝对标准并嘲笑正统主义。他宣称,“当一个政府失去统治能力的时候,它就不复是正统的;谁有力量推翻它,谁就有权利”。这些言论,在拿破仑三世听起来是音乐;当这个历史家在巴黎时,他邀请他吃饭;而后者则以自己的恺撒传相赠作为答谢。但蒙森很希望世人不要把他为恺撒辩护和为恺撒主义辩护混为一谈,因而在该书的第二版里,他说明了他的观点。罗马共和国是腐败的。恺撒的工作是必要而有益的,那不是因为它带来了或能够带来幸福,而是因为它的祸害较小。在不同的情势下,它会是一种僭取的政权。“自然规律是:最微小的有机体远远胜过最精巧的机械,按照同一规律,任何给大多数公民以自决余地的不完善宪法,也无限地胜过最合于人道而又最奇异的绝对主义;因为一个是活的,另一个是死的”。罗马皇帝维持国家的统一,并机械地扩大它的版图,同时它在内部却丧失元气而死去。很好,蒙森使这部著作实质上留在他原来的形式上,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那使它赢得世界声誉的特点。它是一部天才与热情的著作,一个青年的创作,并且今天仍和当初写它的时候那样新鲜而有生气。就灿烂文笔与持久力量而言,所有德文历史著作中,除了特赖奇克的《德国史》外,没有与它近似的。萨谟奈的铭文版本和那不勒斯铭文版本的优越性给每个学者以深刻③唐·璜(DonJuan)传说中的人物,是贪财、骄傲、美容颜、不信神、放纵类型的人物。——译者④桑乔·潘萨(SanchoPanza)——唐·吉诃德的仆人,忠心而饶舌,简朴、愚昧而富有风趣。——译者\n①印象。1853年柏林科学院给蒙森六年薪俸来编辑铭文集。1858年,他以科学院的成员身份被聘前往柏林,在那里他还担任讲座。于是他结束了他的漫游。这项工作范围极其庞大。远远超过博克的同样的工作;他需要一个能敏捷而又正确地工作并能鼓舞和管理同僚的人去承当。那大①型对开本的第一卷于1863年出版,包括蒙森自编的共和时期的铭文和亨岑所编的执政官年表。两位学者各自对于铭文的责任是:在可能范围内查阅原文,检视刊印本,解释地方与人物的引证,确定日期,并提示恢复断篇残简的方法。在他生前出版的二十册著作中,蒙森所编辑的约有半数,包括山南高卢、南意大利、多瑙河区和东方的铭文,每一部分都经过他的修订并带有他的特点。在这位大师的领导下,兴起一个铭文专家学派,准备在亨岑、德罗西及其他老专家退出队伍后继续这项工作。他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修订东方铭文的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内,他还计划出版第一卷的新版。他原来估计铭文集包括八万张铭文,但这个数字已经加倍,而新资料还在不断积累。新版与补编内刊入了最新资料;1872年所创立的《铭文杂志》并促进了新发现的资料的交流计划的讨论。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它阐明罗马公私生活的各部门——行政、城市、军队、赋税、宗教、艺术、社会状况与交通运输。哈弗菲尔德很适当地把它比作科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卡米耶·朱利昂还宣称,它是一个学者对有关过去的知识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这样地从事于一项要消耗平常人全副精力的工作的同时,蒙森还写了一系列专著,其中的每一部都标志着这一部门的一个时代。第一部,是共和时期的《年代学》,他在其中解决了已往几乎未曾涉及过的一个棘手问题。这部著作是属于开路先锋的性质;在他的作品中它最不经久但它所激起的争论却是富有成效的;佐尔陶正是根据二十五年的讨论结①果,建造了一座大厦大部分取代了他老师的建筑。第二部,是他的《货②币史》,于1860年出版。比前一部更为重要。在旅行意大利时,蒙森已开始他的钱币学研究,现在他试图包罗万象地综述一个广阔而大部未③经涉猎的知识领域。他雄辩地证实他的前辈埃克尔与博吉西的工作,但指出他们的著作并不完备。而且,他们只是作为钱币学家来写作,而蒙森则从未忘记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罗马币制所由产生的希腊-亚洲币制开始,追述币制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在从意大利到世界的发展,讨论各种货币的流通和使用时期、铸币权以及贸易和财政问题。他为德·布拉卡斯出版的法文译本评述了新发现的资料,他从来未曾有过时间来刊行这篇著作的修订版;(而现在它已过时了)。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注视钱币学的发展。他曾帮助创立《钱币学杂志》,支持《古币集》的出版,并和他在荣获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所接受的古币捐赠给它。①参阅希施费尔德的纪念演说,见《柏林科学院论文集》,1904年;哈纳克,《科学院史》,1901年;瓦尔青,《拉丁文铭文总集》,1892年。——原注①铭文集,全名《拉丁铭刻集成》(CorpusInscriptionumLatinarum)共十五卷,三十六册。——谭注①佐尔陶(J.Soltau)著有《古罗马人民大会的形成和它的组织结构》一书。——谭注②原名《罗马货币史》(GeschichtedesrómischenMünzwesems),1860年。——谭注③参阅肯纳,《约瑟夫·冯·埃克尔》,1871年。——原注\n在他从事《铭文集》的时期,他所写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罗马④公法》的专著。《公法》的篇幅,倍于《罗马史》;它被作者认为是他最大的成绩。象这样庞大而又详尽的著作是决不会受到普遍欢迎的,但它尽善尽美的学术成就却使历史学们又钦佩又望尘莫及。它也许是所有关于政治制度的历史专论中最大的一部。他宣称。“只要法理学忽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语言学又忽视法律,它们想要敲开罗马世界的大门就是徒劳”。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他既是法学家,又是史学家,他早已刊行《法律汇编》的最早的批判版,从那时起这个版本就成了每个法学家的指南。《公法》共有三千多页,每论述罗马政府和行政的整个过程与体系。每一句话都有论点与权威作为依据,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注释。它是一系列专题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制史。各种制度虽然是分别地研究的,但又是作为公法的有机体系的肢体来对待的。这部著作最有创见的部分,在于论述元首制方面。历史家们已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中已看出与旧秩序的剧烈决裂和一种新制度的创立,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毫无变动地继续了三百年之久。蒙森指出,他希望建立一种双头政治,并审慎地把大部分权力给元老院。元首职位不是世袭的。这个统治者只是第一公民,凭借享有终身权力和没有平起平坐的同僚而高于其他官吏之上。除了海陆军的指挥权与对特选省区的控制权外,新的权力逐渐加到元首身上,直到出现一个真正的帝国。他表明:这个制度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君主政体;它是放入旧框框内的一个新首长制;是基于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均势;是旧寡头政治与恺撒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妥协;绝对的独裁要到戴克里先时代才出现。这样看来,罗马是逐步从元首制演变到帝国的。在关于元老院的一卷里,他从另一方面叙述同一个故事。都有些人抱怨说:因为蒙森是一个法学家,他夸大了法律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这整个画面过分整齐和系统化。特别是他的双头政治理论受到批评。加德豪森认为他夸大了元老院的权力,过低估计了元首制有发展成为世界君主政体的倾向:罗马人相信他们是生活在个人统治下,这是比共和制度的若干残余更为有力的证明。十年后还有一篇附录,刊入一卷长达千页的著作《刑①法》内。在罗马法的广大领域内,再也没有象这一部分如此密切地与历史接近的了。这部著作概述从罗马历史开始到查士丁尼时代为止的官吏、礼仪、罪行的种类和刑罚;在他叙述的冗长过程中,他还阐明了罗马文明许多方面——道德、婚姻与宗教。当蒙森以恺撒之死来结束他的历史时,他打算用收集全部现存的铭文打下基础后,再继续写它。随着光阴的流逝,世人不复期望这部只有他能写出的著作,虽然他自己在很久之后才抛弃了这个念头。他在1877年所写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在他死后出版,1885年,那被称为《罗马史》第五卷的著作问世。他的《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的罗马行省史》,是②根据《铭文集》编写的。一个消逝了的世界,由于一个人的天才而得重④参阅贝尔奈斯,《罗马公法的论述》,《论文集》,第Ⅱ卷,1885年。——原注①参阅斯特罗恩-戴维森的出色分析,见《英国历史评论》,1901年4月号。——原注②参阅W.T.阿诺德,《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4月号,和博尔曼,《论古代和现代》,1895年。——原注\n现,因而有可能来评价帝国的真正性质与影响。在这以前的作家只能通过罗马历史家与讽刺家的眼睛来看帝国,他们把统治者放在图景的最前面。蒙森的成就是确定罗马城不是帝国;罗马君主的残暴与癖性,对广阔无际的整个罗马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微乎其微的。他的研究结果证明:首都耸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决不是典型的。塔西陀在蒙森以前的权威正如李维在尼布尔以前的权威一样。那被吉本视若神圣的传说,即关于第一世纪与第二世纪之间和关于提庇留时代与安敦尼朝时代之间的对照已被扫除。这个历史家宣称,各省在酷热的白昼之后享受了一个凉爽的黄昏,因为帝国最伟大的功绩是提供三百年的和平时期。他以西欧文明所由产生的稳定秩序的图景来代替关于专制腐败时代的传统说法;其次,他显示行政机构的正确性质。我们因而得知帝国的前进政策与缓冲政策、边境地区与附庸国家、军队制度、卫戍军、城市、赋税与贸易。的确,这部著作是一部不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帝国的地名词典。关于不列颠的一章,由于铭文稀少,必然是薄弱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西班牙的论述,也几乎同样是不充分的。但这一切只占全书中的极小一部分;除此之外,各章都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有些地区的铭文曾由他亲自编辑过,例如多瑙河地区与小亚细亚就是如此;关于这些地区,他做得最好。关于希腊的部分是以讨论它的腐化的原因为特色的,虽然内尔德克宣称他关于希腊化时代文化的描写过于黑暗。关于犹太人的论述,获得普遍的称赞。《罗马史》的传染性的轻浮气息,在这里已经消失;作者很不愿意渲染景色,而人情偏见也不复见。《罗马行省史》是关于政体的公平无私的研究,而不是一部热情与斗争的纪录。如果它曾总述行省政策与行政制度,讨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关系并评论社会与经济的力量,那将会更好些;但我们已能毫无困难地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公法》与《罗马行省史》的无比价值使人们更加为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始终未能使他的研究成果圆满完成而感到遗憾。我们本应该有关于历代帝王的一个令人叹赏的肖象展览,关于罗马法在帝国体系内地位的一个完善的说明和关于基督教的成长与受迫害的一幅精彩图画。这个历史家在晚年主要是从事古文献原本的研究。他最著名的出版物,是关于奥古斯都遗嘱的版本。遗嘱原文在罗马城已经遗失,但一份①几乎完善的抄本在小亚细亚的安西拉,于16世纪由布斯贝克发现。直到1861年法国佩罗考查队进行探索后,考订版才成为可能。根据抄本,蒙森把铬文刊印于《铭文集》内;并于1865年作为单行本重印。但仍然缺少希腊译文的一部分。1882年,休曼被推选来揭开那些隐蔽的部分;他把全部铭文制成一个石膏模型。依靠这个新资料,蒙森刊印新版,并附有修订过的注释。关于这个在罗马铭文中最著名铭文之起源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编辑者坚决主张碑文是在奥古斯都生前建立的,而别人认为,它是由奥古斯都起草而由他的继承人刻碑并附以必要的增补。蒙森参加《日耳曼史料集成》的管理部,并负责关于古代作家的部分,包括“民族大迁徙”的几个世纪。哥特人的历史是用出版齐丹斯与卡西奥②③多鲁斯的著作作为说明的,同时《教皇圣务录》、内尼斯及其他第四①即今安卡拉。——译者②卡西奥多拉斯(Cassiodorus,MagnusAurelius约480—约540年)东罗马官员,著有《哥特人史》十二册。\n世纪至第七世纪的较小编年史阐明了一个模糊时期。他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历史的黑暗过渡时期,必须从两方面予以说明;科学站在这个时期的前面,象工程师站在一条穿山隧道前面一样”。他最后的工作是出版《狄奥多西法典》,附有详尽的绪论。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一直扩大到罗马帝国淹没于中世纪时代的浪潮里。蒙森在组织式鼓励一切针对阐明罗马历史的工作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其中之一是探索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④的计划。1890年为这项工作成立了一个组织,创立了一份杂志以纪录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设立博物馆以展览所发现的文物。探索的结果,不仅阐明了罗马边境,而且阐明了它设防与防御的方法。他所深感兴趣的第二项工作,是《传记辞典》,这部辞典是在柏林科学院支持下由他的朋友兼同事德绍编辑并几乎是完全根据《铭文集》的。他欣然迎接这项新开辟的工作。当纸草卷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的时候,他已进入老年,但他的门生维尔肯证明,他是属于第一批看出这些褐色残片的重要意义的人。这一新科学接触到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属于罗马的埃及省有关。当一部《纸草卷集》的计划浮现于他的心头时,他帮助创办了一份专门杂志。他希望各国学者会联合起来做那些一个国家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庞大工作。其中之一,是编辑《拉丁语辞源》,即说明直到第6世纪为止的每个拉丁单词的历史。1892年,他力图联合德奥两国科学院进行这项事业,并草拟了联合的条例。但是柏林科学院虽然同意“辞源”方面的协作,却拒绝进一步的联合计划。这个决定使他深感失望,但他的努力已为国际科学院协会铺平了道路;协会于1901年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年迈的历史家的想象范围越来越广泛了。他的双目并未昏花,他的精力也未减退。他热切地注视惊人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揭示东方的古文明,并把希腊与罗马放入一个新的前景里。他的思想大部集中于新知识对旧知识的关系方面;他的最后活动之一,是提出一批关于文明社会的最古刑法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送给希腊、条顿、印度、穆斯林与犹太法律专家,旨在协调他们的研究的广泛成果。关于罗马的问题则由他自己作出回答。蒙森得以成为伟大历史家因素之一,是他对生活各方面的强烈兴趣①。这个最杰出学者,同时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与思想界的领导人。他明亮的眼睛与表情丰富的面容,显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性格的一切情感。他曾在1848年用笔来战斗,为了信念,他曾牺牲自己在基尔与莱比锡的职位。1861年,他以进步党成员的身分参加普鲁士议会。1881年,他充任帝国国会议员,参加由他的朋友巴姆贝格尔领导的急进党;当俾士麦提②出《保护关税法》时,该党脱离了民族自由党。他属于这样一批德国人;他们觉得德意志的统一使它担负着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使命;1874年,他在就任会长的演说里宣称,德国人不能满足于他们已有的成就。可是跟兰克一样,蒙森为他所形容的当时失去人性的趋势而感到沮丧。他对施其书残阙,有6世纪修道士乔丹斯所作摘要传世。——谭注③原文为LiberPontificatis。——译者①有一篇亲切的评论,见哈纳克,《论科学与生活》,第Ⅱ卷,1911年。——原注②1879年7月,德意志颁布了以保护农业与重工业为主旨的保护关税法。——谭注\n特克尔与特赖奇克所领导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的爆发而进行斗争。他指责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是谷物投机者和酒贩子。当他指称《保护法》为欺骗政策时,俾士麦对他加以迫害,但他随即被宣判无罪。他反对殖民运动,③认为它是侵略主义;反对泽德利茨学校法案,认为它是蒙昧主义。它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他抵制在科学、文学与艺术方面侵犯自由的一切措施。④他的最后的政治声明,是对1902年农业税率的猛烈攻击。1903年他八十六岁时在睡眠中死去,一生勤于学习并从事教学,直到最后一刻。蒙森与兰克一起并单独跻身于19世纪第一流历史家之列。兰克的著作几乎完全是属于叙述性的,蒙森则不仅以叙述大师而且以制度解释者以及铭文与文献的编纂者而博得盛名。他们两人在多产和把批判技术与综合想象相结合方面,彼此相似。两人都是为几代好学青年所尊敬的大师;两人都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声誉确立,无可匹敌。蒙森著作的出版时期持续达六十多年。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没有不成熟的东西,而在他后期的著作里也没有衰退的迹象。只有他能做到对一个古典文明的完全融会贯通并使之重现于世,那是自斯卡利吉尔以来学者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罗马史在蒙森以前正象欧洲史在兰克以前一样。“他接受的是一座①砖城,而遗下了一座云石城”。Ⅱ蒙森的两个同时代德国人所编写的罗马历史也是享有盛名的。彼得②著作的第一版于1853年出版,第二版是在〔蒙森〕《罗马史》已震惊世界之后刊行的。他属于尼布尔学派,对这位伟大历史家也进行批评,但他否认说他是比较保守的指责。他简略地叙述了关于罗马诸王的传说,警告读者这些传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接受传统作为追述宪法的形式与发展的指导。他的叙述只有在他可以利用波吕比阿的著作时,才渐渐变得详细起来。他赞扬共和时期的爱国、讲道德与有秩序的生活,但他也同意在格拉古弟兄之后已出现衰败。他对最后几次政治斗争中的诸主角之估计,是公正而又宽和的。他指出说,“我们不能责备西塞罗没有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看出共和国注定要灭亡的”。他承认恺撒的统治是贤明而良好的,但他否认他有复兴国家的力量。“我们看到罗马极盛时代——就是布匿战争时代——的景象,不能不生起景仰之心”。但罗马人的征服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又由于一个世纪的内战,守法的精神荡然无存。旧罗马性质的废墟被奥古斯都与提比留进一步破①坏,并被加里古拉、克劳第与尼禄任意践踏。③原文为ZedlitzSchoolBill,指教育大臣泽德利茨提出的法案。此法令允许波森及西普鲁士各级学校使用波兰语,还规定发还“文化斗争”中没收的天主教会经费,允许天主教的一个教团在德国恢复活动等。——谭注④1902年通过了恢复一度降低的农产品课税率。——谭注①原文为Latericiamaccepit,marmoreamreliquit。——译者关于一般论述,参阅克罗尔,《最近二十五年时期的古代研究》,1905年。《古代研究年鉴》于1906年开始出现。——原注②彼得(Peter,KarlL.1808—1893年),撰有《罗马史大事记》。——谭注①见第十五章注。提比留,加里古拉(在位:37—41年),自封为神,令臣民崇祀;克劳第(在位:41—54\n②伊纳的著作,更为著名;他专心致力于共和时期,因而对这一时期的叙述更加详细。这部著作于1868至1890年间断断续续地出版,在某些方面,它是为了非难蒙森而写的;对于后者他原是不抱好感的。他的雄心是要步阿诺尔的后尘。他写道,“如果阿诺尔完成了他的著作,又如果这著采入了最新资料,我可能就不会写我的书了”。他的愿望是要概述现有的知识而不是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他关于早期罗马的叙述带有③尼布尔与施威格勒的鲜明痕迹。他心目中没有什么英雄;他为罗马人的残暴而感叹。他宣称,“我被指责对待罗马不公平,其实不然;但我对待希腊与迦太基是公平的,因我记起罗马历史家并不是一向讲实话的,他们获得了世人的听信,因而使所有反对的声音寂寂无闻”。在叙述共和国末期时,他认为个人统治的建立已成为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恺撒与庞培互争雄长,但他们未曾真正改变过历史的进程。“共和国的覆亡不是由于恺撒的决定或野心。如果恺撒早死,共和国仍然会找到一个主人。他毫不感情用事,而是以庄严崇高的精神来解决问题”。虽然这部著作缺少魄力与创见,但它不偏不倚的语气倒使它成为那些已厌恶蒙森的明显偏见的读者所最喜爱的书。①②③在德国以外,拿破仑三世思想开明的大臣杜律伊所写的历史是最宏伟的作品。这部著作的最初两卷在1843—1844年间出版;第三卷和第四卷虽然在1850年时已经写好,但因书中盛赞恺撒和罗马帝国而搁置下来,直到〔拿破仑三世夸台后〕1872年才出版。关于早期几个世纪的历史,他依靠尼布尔和施威格勒;而关于向帝国过渡的见解,他预示了蒙森的看法。他在1880年写作时,他指出,共和派只不过是一小撮寡头,他们在征服世界后不知道怎样统治。在共和国倾覆后,虽然有一百个家族遭受损失,但八千万人口却获得了好处。杜律伊在晚年所写的几卷里,充分利用铭文,也同意蒙森关于帝国有功于文明的意见。在详述起初两个世纪的罗马社会时,他认为罗马各行省的健康的生活与首都的腐化生④活恰恰形成对照。他把历史叙述到狄奥多西的死亡为止,这样,他就完成了唯一的一部从头到尾详细叙述的罗马史。作者在后来的版本里还补充了插图,因而使它更受欢迎,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杜律伊也是法国史和希腊史的作者;虽然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帮助的向导。近来,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企图写一部关于罗马的详①细记载。他的《罗马史》,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总结蒙森以来研究成果的年),扩大专制权力,削弱元老院实力;尼禄(在位:54—68年),凶残好杀,以残酷手段消灭政敌和鱼肉臣民。——谭注②伊纳(Ihne,w.1821—1902年)著有《高卢颠覆以前的罗马史》(RometoItsDestractionbyGauls)。共八卷,1808—1890年。——谭注③施威格勒著有《罗马史》(RoimischeGeschichte)。——谭注①参阅拉维斯,《维克托·杜律伊》,1895年。——原注②书名《罗马史》(HistoiredesRomains),全书共七卷。——谭注③杜律伊并非路易·拿破仑的亲信,这位皇帝读了他的《罗马史》后,欣赏其才学,于1861年任命他为公共教育大臣。在职期间杜律伊对法国教育多所改革。第二帝国崩溃后,他重返史学界。——谭注④狄奥多西(大帝)以395年卒于米兰,帝国自是分裂为东西二部。——谭注①原文为StoriadeiRomani,全书共四卷,起远古,止于公元前2世纪30年代。1907—1922年。——谭注\n尝试。他在怀疑主义与轻信态度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他充分论述古代意大利的种族与那里的希腊人。在回想起尼布尔所爱好的一个观念时,他相信在罗马曾有大量诗歌存在过;从诗歌派生出传说;甚至有些古老②的民歌也可以尝试从传说中重新编出。海特兰关于共和国的概论,旨在公正的叙述;他抛弃同行研究者的奇谈怪论,但也并未提出自己的论点。在描写盖约·格拉古和苏拉、西塞罗和恺撒时,他表示出他并不依赖于蒙森。他虽然承认恺撒工作的必要性,但并不等于赞成他的品质或谴责那些拥护一个毫无希望的事业的人们。有些人选择罗马史上特殊的问题或时期来进行研究,他们已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关于前罗马时期意大利的知识,由于考古学、人种学与语言学的联合工作,而正在慢慢地增加起来。关于自然条件的影响,③尼森第一次作出了彻底的研究。在库齐乌斯以前,希腊史专家对于希腊半岛的自然特征一无所知;同样,尼布尔、施威格勒甚至蒙森对于罗马的自然条件也很少注意。尼森关于山岭、河流、海岸、自然资源与气候的研究,给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埃托雷·帕伊斯在关于布匿①战争前的西西里与意大利的著作里,显出他完全怀疑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并认为《执政官年表》是伪造的文献。他更相信考古学、语言与地方名称的证据。《罗马史古传说》是他的一部较大著作的附录,讨②论在罗马广场所发现的文物。他相信,许多传说仅仅是关于罗马七丘的③神秘的化身。自奥特弗里德·缪勒关于埃特鲁斯坎人写了很精彩的概况以来,发掘工作一直在稳定地进行,因而他们的宗教、艺术与社会状况现时已相当详细地为人所知。可是,他们的起源与种族关系仍然悬而未决,他们的语言仍然难于解释。人们埋怨蒙森未曾探讨过他所用资料的价值,对这些资料的批判分析是由尼森开始的;尼森对李维(《罗马史》)第四个“十书”与第五④个“十书”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考查了这个历史家的著作与人⑤品。他的研究结果比一般所接受的结果消极性较少,但受到彼得的攻击;彼得认为李维的著作旨在激励爱国心与道德而不在作出严肃的历史⑥叙述。然而尼森的结论获得了尼茨的支持;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尼茨被称为尼布尔学派的最后一人;的确,他属于尼布尔学派而不属于蒙森学派。尼茨还写了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它的未完成的部分,由他的讲稿补②书名《罗马共和国》(RomanPoldie)共三卷。——谭注③《意大利地理》两卷,1883—1902年。——原注①书名《古代意大利、中意、大希腊、西西里、萨丁尼亚之历史与地理的考察》论文集。——谭注②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罗马城包括七个山丘。罗马城和罗马国家的建立过程,即是以巴拉丁山丘为中心,逐渐联合其它部落的过程。——谭注③书名《埃特鲁斯坎人》,共二卷,1828年。——谭注④李维的《罗马史》共一百四十二卷,以全书久佚,仅有前“十书”及第二至第五个“十书”传世。以每十卷(书)为一辑(“十书”)。——谭注⑤卡尔·彼得(1808—1893年),德国罗马史专家,以搜集整理古罗马历史文献见称于世。——谭注⑥K.W.尼茨(1818—1880年),德国罗马史,中世纪史专家,兰克的门人。——谭注\n①充后,在他死后出版。遗著有力而有创见,使人为他未曾写完这部完备的概论而感遗憾。蒙森的主要兴趣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尼茨却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经济因素,强调农民同商业和运输业的新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共和国末期的场面较之所有以前或以后的世纪更能吸引历史家的注②意,乔治·朗所写的一部详细叙述,虽然缺少特色,却是对以作者娴熟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并作出了公平的论断。四十年后,格里尼奇计划写一部包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和早期帝国至公元70年的历史的著作③。该书从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有价值的评论开始,主要讲述格拉古弟兄。提比留满足于社会改革,而盖约〔格拉古〕还要求政治与司法的改变。这两个人制订法律都未经过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为一个阻碍。第一次流血成了内战的开端。格里尼奇在完成第一卷后即逝世,那是对罗马研究的一个严重打击。其他英国学者对这一过渡时期的知识,也作出④了有价值的贡献。沃德·福勒关于恺撒的通俗传记。实质上是采用蒙森关于这个英雄的见解的。他宣称,恺撒具有高尚目的与真正的人性。当时罗马需要并愿望有绝对专制:城邦制已经衰竭,而元老院又自私又无能。虽然从法律讲他犯下叛国行为,但他当时需要一个合理政府,却证明他是正当的,而且没有哪个政治家曾做过这样有持久价值的工作。虽然他决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并有残暴行为,但他是和蔼可亲的。恺撒和西塞罗是这个时代最高贵的人物为西塞罗辩护的工作,由于斯特罗思-①②戴维森所作的传记与蒂勒尔所出版的《通讯集》,而被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恺撒的高卢战役和不列颠战役,赖斯·霍姆斯进行了无比透彻③④的研究。佩勒姆在他出色的罗马历史小册子与那些为他的听众所永远不会忘记的牛津演讲里,特别注意于共和国与元首制之间的关系。⑤自从蒙森以来没有任何著作象费雷罗的《罗马的盛衰》那样引起世界范围的兴趣。虽然它受到学者们的冷淡,它的力量与启发性却是无可⑥非议的。他在开始活动时是隆布罗索的一个门生,后来成了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研究古代世界,他找出共和国覆亡的原因,在于一个旧的农业和贵族的社会之一转入了一个新的商业时①书名《罗马共和国史》(Geschichtederr■mischenRepublic)二卷,1884—1885年。——谭注②书名《罗马共和国的衰落》(TheDeclineoftheRomanRepublic)。——谭注③书名《共和国后期与元首制初期的罗马史》(HistoryofRomeduringthelaterrepublicandearlyprincipate),1904年。此书只完成第一卷,记至马略重任执政官(公元前133—104年)止。——谭注④书名《恺撒与罗马帝国的创立》(JuliusCaeserandtheFoundationoftheRomanimperialSystem)。——谭注①书名《西塞罗传》(Cicero)。——谭注②《西塞罗通讯集》共五卷,1901—1915年。——谭注③霍姆斯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恺撒征服高卢记》(Caesar’sConquestofGaul),1899年,《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缔造者》(RomanRepublicandtheFounderoftheempire),共三卷,1923年。——谭注④指他写的《罗马史纲》(OutlinesofRomanHistory),1893年。——谭注⑤在最好的批评意见中有:柏斯尼尔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XCV卷及哈弗菲尔德,《蒙森以来的罗马史》,《季刊评论》,1912年10月号。克罗齐指责本书使意大利学术研究损失信誉,《意大利史学史》,第Ⅱ卷,第245—247页。——原注⑥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人类学家,法学家。——谭注\n代。迦太基覆亡后,财产如潮水般地涌入罗马,而财富导致奢侈风气的增长与需求标准的提高。贫富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了。外交政策与内政的演变是取决于财富分配的改变的,而剧中的个别演员却无可奈何地沿着经济改变的潮流随波逐流。这样看来,在罗马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基本问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一场属于经济力量间的斗争而不是属于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共和国不是被苏拉或恺撒而是被“帝国主义”扼杀的。“伟大人物是历史性工作的工具或牺牲品,而对于这个工作,他们是不会觉察的;因为他们象他们的同胞那样,是我们所谓历史命运的玩物”。关于武人互争权力的旧想象,现在代之以人们同一种命运冲突的想象,而对这种命运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费雷罗在努力摹想古代方面比①蒙森更为大胆。他以早期共和国的罗马人比诸布尔人,以卢库鲁斯比诸②拿破仑,以恺撒比诸一个坦马尼协会的党魁,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比诸美国总统的权力。虽然这些及其他比拟使学者讨厌,但它们却受到一般怕读学术性作品的读者的欢迎。书中的叙述,在苏拉死后,开始变的详细起来。它的新奇点之一,是给卢库鲁斯以重要地位;他是“罗马史上最强的人”,使意大利从内战转到对东方的征服。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转向,因为很快又为分赃不匀而发生争吵。他指责蒙森对恺撒的狂热崇拜,他认为恺撒是一个道地的随机应变者。他是“为进行大事业而受着命运支配的无意识的工具”,但他从来未曾看到过自己事业的目标或探索过它的意义。他之所以在高卢作战,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作战;他也茫然不知高卢的征服会是欧洲历史的开端。他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未曾建设什么可以持久的东西。恺撒占据该书的前半部,他的外甥占据它的后半部。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蒙森过低估计了元首的权力,费雷罗却认为他过高估计了它。在他的笔下,奥古斯都被描绘成一个能力有限眼光短浅的人;起初是胆怯而又神经过敏,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思想与意志都有新发展。他不是恺撒的继承者,而是他的对立面。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一种君主政治,甚至也不是一种双头政治。他的愿望,是要把国家重新置于元老院控制之下,并给元老院以一个仲裁者的帮助,这样看来,他只是一个立宪共和国的总统;因而费雷罗称自己的著作为《奥古斯都共和国》。奥古斯都英明地主持了这个过渡时期。帝国既不是非常令人不快,也不是特别幸福的。这个历史家至多是说明了经济现象与政治演变之间的关系。他在研究人物与估计政治家的才能方面是才力不足的。他的机械哲学把历史归结为几乎是盲目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可是他否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宣称,罗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取决于风俗的转变,而这项转变是由于财富、开支与需要的增加而引起的,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①转变。“历史的基本力量,是心理的而非经济的”。这句话,是兰普雷②希特的语言也是他的精神。罗马历史的关键在于“野心和欲望的自动增①卢库鲁斯,罗马执政官、将军,在对米特拉达梯作战中屡立战功。公元前69年向亚美尼亚进军途中,部众骚动,公元前67年被撤换。——谭注②坦马尼派(Tammany)——以纽约坦马尼大厅为会集所的民主党的一派。——译者①参阅《从恺撒到尼禄的罗马史上的人物与事件》,1908年的洛维尔演讲。——译者②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历史观点,见本书第二十七章第二节。——谭注\n加”。东方和西方的混合既是罗马的光荣又是它的弱点。罗马的腐败状况已被大大地夸大。实际上它的财富和欲望的增加程度只是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娱乐和奢侈的欲望之增长,使智慧和道德,政策和制度都发生了改变。暴发户接替了贵族;而富人,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浮躁的、神经质的和悲观的。这种改变既是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是对它的惩罚。关于罗马帝国的完备的历史迄今尚未写出。蒙森的一个门生赫尔①曼·席勒曾作过临时性的尝试,但他用心写出的著作都缺少特点。伯里②编写了关于帝国头两个世纪的一篇简略而有用的撮要。泽克的六卷著作《古代世界衰落史》,论述罗马从戴克里先到公元476年止的政治与文化。在关于罗马诸帝的专著中间,加德豪森关于奥古斯都的生活与功绩③④的巨著,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亨德森关于尼禄的专著可作为反对塔⑤西佗的帝国概念的典型。格雷戈罗维以有趣的一卷论述了哈德良。根据铭文、古币与考古学所作的罗马行省的详细研究,已大有进展。奥托·希⑥施费尔德关于帝国行政制度的分析把新的细节加到他老师所作的描写⑦上。卡米耶·朱利昂关于罗马高卢的巨著,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哈佛⑧菲尔德一生从事罗马属不列颠的研究。奥地利法学家米泰斯根据纸草卷与铭文,写了一部学识渊博的专著,来论述东方省区从希腊法到罗马法①的过渡。虽然罗马的宪法史主要应归功于蒙森。但那些按照独立路线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路德维希·兰格在他的《罗马古制》②里,第一次对共和国的制度作了彻底的探索。他的审慎态度与蒙森的不顾一切与坚信不疑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蒙森的《公法史》企图把罗马政府描写成为一个有机体。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文章里,兰格为自己的考古研究法辩护理由是:如果遵循蒙森的指导,具体事实可能牺牲于法③理的对称之中。《公法史》还碰到另一个更加敌对的批评者,即马德维④格。这个伟大的丹麦学者,青年时期曾研究法律,但不久就放弃法律而转向研究拉丁文献原文。在他年老时期,因双目失明而不能进行心爱的①H.席勒著有《罗马帝国史》共二卷,1883—1887年,记事起恺撒遇刺至395年帝国分裂,系一部政治史。——谭注②书名《罗马帝国史》1893年。——谭注③书名《奥古斯都及其时代》(AugustusundSeineZeit)共二卷六册,1891——1904年。——谭注④书名《尼禄皇帝的生平与元首政体》(LifeandPrincipateoftheEmperorNero)1903年。——谭注⑤书名《哈德良皇帝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图景》,1851年。——谭注⑥书名《罗马帝国行政制度——至戴克里先朝》1905年。——谭注⑦书名《高卢史》(HistoiredelaGaule)八卷,1907—1926年。——谭注⑧哈佛菲尔德著有《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RomanizationofRomanBri-tain,RomanoccupationofBritain)等书。——谭注①书名《罗马帝国东方各省的国家法和民法兼论希腊法及晚期罗马法的发展》。——谭注②参阅纽曼,《路德维希·兰格》,1886年。——原注③兰格:《小品文》,卷Ⅱ,1887年。——原注④参阅内特尔希普,《演讲与论文》,第Ⅱ集,1895年。——原注\n⑤研究工作时,他口授他关于罗马宪法的论述。他宣称,忽略元老院与人民而先谈行政首长,就象在未打好基础之前先建造屋顶一样。蒙森是以近代理论来说明古代政治形式,而且他的有些假是牵强附会和凭空想出的。马德维格拒绝恢复那些概念的企图,可是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洞察各种制度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他是按照完全不讲宪法的性质的老方法来讲述帝国的。由于这部著作忽视铭文,奥托·施希费尔德在他出版以前就说它是过了时的而不予考虑。赫佐格在描写学派与法理学派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他的《罗马宪法的历史与体系》强调指出掌握罗马公法精神的必要性,但他不认为蒙森的著作已获得成功。与蒙森不同,赫佐格是按照宪法发展的年代顺序来全面地叙述它的成长的。〔罗马〕生活与文化已被辛勤地探索过,但由于资料的极端希少,重现早期共和国的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大胆的尝试是由菲斯泰尔·德·库朗热作出的,他从宗教方面提出关于罗马文明一个完备的解释。在他的《古代城邦》里,他宣称,家族的崇拜是这个结构的基石。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早期罗马社会是纯朴的。随着家族制度的解体,共和国也就衰落了,虽然菲斯泰尔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过份简单化了并企图用一把万能钥匙来启开这几个世纪的生活之锁,但他却非常有启发性地重现了古代社会。威索瓦与沃德·福勒也描绘了〔古罗马的〕宗教生活①与思想,虽然不很和谐,但说服力较强。还有三部以帝国文明作为题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弗里德兰德的《文明史》于1860年出版,立即成为一部欧洲的第一流著作。在著者死后,经过一批专家的修订,它迄今仍然提供关于从奥古斯都到安托尼朝末期为止的罗马文明之最完备的图景。稍后时期,出版了加斯东·布瓦西埃的极其吸引人的论著;他的《罗马宗教》讨论了东方信仰的传入、崇拜皇帝仪式的兴起与辛尼加的哲学②。他的后期著作《异教的终结》继续这项叙述。迪尔关于2世纪和4世①纪罗马社会的令人读着愉快的著作,是以它们的洞察力与学识著称,关于帝国的知识,也从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获得助益:例如勒南与哈纳克②③、纽曼与拉姆齐以及德·罗西关于坟窟的探索和居蒙关于太阳神崇拜的研究。没有任何部门比罗马城的考古学受到更为辛勤的培养。在法军占领⑤书名《罗马国家的宪法与行政》(DieVerfassungundVerwaltungdesr■mschenStaates),共二卷,1881—1882年。——谭注①威索瓦著有《罗马的宗教与文化》(ReligionundKuttusderR■mer,1902);福勒著有《罗马人民的宗教体验:从最早到奥古斯都时代》(Religiousexperie-nceoftheRomanPeoplefromtheEarlist,TimestotheAgeofAugustus,1911),《基督纪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的神道观念》(RomanIdeasofDeityintheLastCenturybeforetheChristianEra,1914)等。——谭注②辛尼加(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古罗马中斯多葛派哲学的代表人物。——谭注①迪尔著有《从尼禄到奥利略期间的罗马社会》(RomanSocietyfromNerotoMarcusAurelius,1904),《西帝国最后一世纪的罗马社会》(RomanSocietyinthelastCenturyoftheWesternEmpire,1898)等书。——谭注②勒南,见本书第二十六章,哈纳克研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著有《公元一至三世纪的基督教会及其扩张》,1904年。——谭注③纽曼辑有《罗马故物》一书。拉姆齐著有《公元170年以前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罗马帝国东方省之历史与艺术的研究》等书。——谭注\n时期,费亚对古罗马广场遗址的部分发掘,给探索工作以必要的推动;在复辟时期,尼比和卡尼纳从事于重现这个古城的工作。本森的《罗马城志》和贝克尔在其《罗马古迹》里的精彩随笔,开始了有系统的论述。莫里茨·豪普特的门生约尔丹所编的《罗马地形学》,标志着自本森以后第一个有决定性的进步。博尼在广场与帕拉丁丘上所作的发掘;已产生轰动的结果。1876年创办了一份关于发掘工作的杂志;兰察尼与许尔④森并推广了取得的结果。对奥斯蒂亚的探索,已经开始。对庞贝的发掘⑤⑥正缓慢地向前推进,而它的丰富收获已由莫乌汇集。对赫库莱尼恩内的发掘,由于必须迁移一个村庄与打开坚实山岩所需之庞大费用而被延搁。发掘工作已大大增加我们所知道的古典艺术的遗迹;现在关于罗马雕刻是纯粹派生出来的这个传统概念,已被推翻。意大利内部迄今仍隐藏着许多秘密,“永恒之城”所有的考古学校正指望一个富有成效的竞①争前途。在半岛之外,最丰富的收获已在罗马非洲省的明珠提姆加德采集到。④奥斯蒂亚位于距罗马约一百六十里的台伯河口,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为罗马海军重要基地,后又发展为国际贸易城市。公元200年以来历经外族入侵,夷为废墟。1907年以来开始发掘,到1936年已有四分之一的面积出土。——谭注⑤莫乌著有《庞贝的生活与艺术》一书。——谭注⑥赫库莱尼恩,位于威苏维火山之区。初为希腊殖民地,后并入罗马,公元79年火山爆发被淹埋。——谭注①提姆加德,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罗马人在此建城。——谭注\n第二十五章犹太人和基督教会Ⅰ古代东方文明的重新发现和应用批判方法研究犹太《圣经》同时并①进,并促进了这一方法的应用。尼布尔的主要结论在17、18世纪已被预示,同样,研究《旧约全书》的若干成果也已由较早时期的个别思想②③家预见到。霍尔斯否认《五经》起源于摩西说,斯宾诺莎注意到它是混合物的这一特点。西蒙神父激起了博絮阿的愤怒,因为它暗示对《旧约全书》应该象对其他著作一样采取批判态度。1753年,当法国犹太学者阿斯特律克鉴别《五经》内用“伊洛欣”称神部分与用“耶和华”称④神部分的两种笔调时,这项批判研究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系统批①判研究的时代开始于J.G.艾希霍恩;他掌握了流行于戈丁根大学的历史研究精神。J.G.艾希霍恩他认为《旧约全书》诸卷具有东方文化特点,因而我们应按塞姆族的观念解释它们。同时,赫尔德企图以比较灵活的看法对待《圣经》而不那样呆板;他称《旧约全书》为以色列民族灵魂的镜子。J.G.艾希霍恩与赫德尔两人虽然结成亲密友谊,却各自独立地达到大体上相似的结论。许多年后,歌德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们两人,因为他们在犹太人的文学著作里开辟了一个美不胜收的园地。艾希霍恩的《旧约全书导论》于1783年出版,该书第一次全面地把批判方法应用于《圣经》的研究。他宣称,他是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工作。他只是间接地知道阿斯特律克的发现,并表明他曾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他把《五经》的组成部分按照称神为“耶和华”或称神为“伊诺欣”的译本进行分类,并指出《旧约全书》的许多卷曾经过几个人的手笔。如果说艾希霍恩是对《旧约全书》进行批判研究的创始人,那么他②的门生埃瓦尔德就是第一个犹太籍的历史学家。1835年,阿诺德在写给本生的信里说,“沃尔夫和尼布尔为希腊与罗马所做的工作,似乎对于①参阅切恩:《旧约全书批判研究的创始人》,1893年;达夫,《旧约全书批判研究史》,1910年。——原注②《摩西五经》(Pentateuch)——《旧约全书》之开首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译者③摩西,《圣经,旧约全书》传说中犹太人的领袖,率领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并创立制度。——谭注④伊洛欣(Elohim)与耶和华(Jehovah)是所谓摩西《五经》中用来称呼上帝的两个词的译音,其中耶和华一词也有学者音译为雅畏(Yahweh),因此三者所指的都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古抄本包含有两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其中之一种称上帝为伊洛欣,另一种则称上帝为雅畏。学者一般公认,《五经》中的这两种史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编成的,称上帝为伊洛欣的史料写得较早,思想内容较朴素原始,故事的叙述较多,乡土气味较浓。称上帝为雅畏的史料问世较晚,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历史知识背①J.G.艾希霍恩(1752—1827年),戈丁根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以所著《旧约导论》(1782—1783年)一书知名。本书第四章所介绍的法学家K.F.艾希霍恩是他的儿子。——谭注②最有权威的研究是由威尔豪森所作,见《戈丁根科学院成立150周年纪念论文集》,1901年。——原注\n犹太也非常需要”。米尔曼在1829年所写的《犹太景,思想内容较为精细成熟。作者在本章中所说的“theElohimandJehovahstrainsofthePentateuch”应理解为“《五经》中用伊洛欣称上帝(或神)的部分和用耶和华称上帝(或神)的部分”。在本章中作者也把耶和华和雅畏等同,多次通用。——译者人史》是有用的,因为它坚持研究《圣经》应该和研究任何其他历史著作同样进行;犹太人也应该作为塞姆人的一支来研究;但是尽管斯坦利声称这是德国神学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冲击,这项论述究属太简短,作者的知识又太肤浅,所以它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埃瓦尔德出生于戈丁根,并在那里度过他的大半生。他在求学时期已开始研究东方语言并拜艾希霍恩为师。由于他对语言学、神学和历史同样感到兴趣,1827年,接替他老师的讲座。他讲授梵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以及塞姆族语言;他以《希伯来文法》一书初露头角。他注释《诗篇》、《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他总称之为《诗卷》);这些注释表明:他的宗教洞察力和他的语言学修养是相得益彰的;他比他的任何前辈更能深入理解先知的真谛。埃瓦尔德在青年时代已计划写一部《以色列人民史》;在完成《先知》后,他即着手搜集半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于1843年首次出版,作者亲眼看到1864—1868年间第三版的发行。在长篇绪论里,他宣称,〔以色列〕历史著作中的空白可用诗歌与先知著作来填补;因为这些著作最能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第一卷叙述到摩西的死亡;他认为早期的历史是神话般的,但并不是虚构的。他把亚伯拉罕描①绘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并认为雅各同以扫的争吵可以说明希伯来人与阿拉伯部族之间的冲突。摩西显然是一个历史人物,是除基督以外最②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关于渡红海的故事是符合历史的,但不是奇迹。关于以色列人本身,这个历史家提供了一幅动人的但过分渲染的图画。他①们皈依上帝,在他的指引下勇气百倍。摩西律法最先宣布:上帝会拯救那些以精诚、服从与信仰上寻求他的人们。在这“光荣的远古时代”,对耶和华的信心,在战争中给予〔以色列人〕力量,并鼓舞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摩西以前,宗教是属于个人的私事;由于摩西,它也成为全民族的事情。埃瓦尔德关于早期历史的论述,是起刺激推动作用的,但失之于武断。象尼布尔一样,当他仅仅是在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时,②他的推测能力才常常获得称赞。在叙述到“列王”时,他是有更为可靠的根据的。他生动活泼地描绘扫罗、大卫与所罗门的形象。他把大卫描绘成一个英雄,并把他的人民理想化;他肯定说这些人民那时尚未腐化③堕落。他所描绘的以利亚,色彩鲜明。可是关于后来世纪的叙述,则不①以扫,据《圣经》传说系亚伯拉罕之孙,雅各为以扫之弟,因兄弟失和,雅各出逃。——谭注②指摩西率领犹太人来到红海,手杖一挥,海水让路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译者①据《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耶和华写于石版的各种律法。——谭注②《圣经·旧约全书》有《列王纪上、下》记大卫以后犹太诸王统治时期的历史。——谭注③据《圣经》传说,以利亚是公元前9世纪人,耶稣诞生以前以色列的伟大先知。——谭注\n如关于英雄时代的叙述那样逼真和动人。我们阅读埃瓦尔德的著作,可以测量那把19世纪中期与末期隔开的鸿沟。第一,他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从《旧约全书》本身取材的。在1865④年的修订版里,他叙述撒马利亚的征服时宣称,关于亚述人一般不太了解,不够一个历史家的研究目的之用。古代文明的发现与比较宗教这门新生科学,在他的著作里都没有得到反映。第二,犹太人始终被看作上帝的“选民”;他们虽然不免有严重过失,但在早期世纪里无论如何是和他们的特权地位相称的。而且他们的领导人物也被过分理想化了。最后,他没有想到法典起源于较晚的时期;威尔豪森认为他的《历史》比不上他的语言学著作的水平。“我不能承认他已象德·韦特或瓦特克那样启开大门或指出道路。他倒是一个学阀,以他的权威来阻止人们接受关于犹太史的真正解释。”普夫莱德雷尔宣称该书是一部说教式的小说,并指责作者阻碍对圣经的批判研究达一个世代之久。尽管有这些有意和无意犯下的过错,他的著作在史学史上还是占着一个显著的地位。他关于塞姆族的学识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能阅读他的著作而不感到犹太人的历史与希腊史、罗马史同样引人入胜。他的著作在英国曾受到热烈欢迎。斯坦利称之为杰出的作品,他的《犹太教会史讲义》就是以它为根据并利用这个作者的圣地知识写成的。我们关于《旧约全书》概念上的革命,是与威尔豪森的名字相联系的,并把埃瓦尔德的著作束诸高阁;这项革命原是由几个学者的独立工作准备起来的。按照威尔豪森的说法,德·韦特是“在这个领域内的历①②史批判研究之划时代的先锋”;他第一个注意到士师、列王和先知同③样是不知道摩西律法的,并主张,如果说《申命记》比约西亚王早的话,也早不了多少。但他早期著作的大胆假设,到他晚年就变得和缓了;所以,这个问题还要留给一个年轻的学者去解决。瓦特克的《圣经神学》出版于1835年;该书坚决主张以色列宗教也是从属于发展规律的。但使它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的,与其说是著作内的黑格尔哲学,不如说是关于①圣经诸卷真正先后顺序的发现。可是,关于祭司法典的后期起源说,还埋没于他的一卷又大又难读的著作里。他最大的成绩,是在诱使威尔豪森写出“我从瓦特克学得最多、最有收获。”当瓦特克在柏林宣布新思②想的时候,罗伊斯在斯特拉斯堡也达到类似的结论。他恍然大悟:《各先知篇》早于《律法篇》的出现,而《诗篇》又在两者之后。在摸索犹太人宗教发展的线索时,他碰到一个问题:据说在最早阶段的犹太历史③里,存在过完备的利未制度,而在《先知书》里则丝毫未曾提及它。罗④撒马利亚是以色列的京城,公元前722年为巴比伦王萨尔贡二世攻克。——谭注①士师是由选举产生的以色列部落领袖。——谭注②先知是所谓受神的启示而传达神的旨意或预言未来的人。早期的先知如撒母耳、以利亚等拥有封立国王的权力;后期的如以赛亚、耶利米等,都是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宗教领袖。——谭注③约西亚王,公元前7世纪时的犹太王。——谭注①参阅贝涅克所编的全传:《威廉·瓦特克》,1883年。——原注②关于《旧约全书》研究的发展,《罗伊斯与格拉夫的通讯》,是具有意义的。——原注③利未制度(Leviticalsystem)——《旧约·利未记》第18章所记载的“勿乱骨肉之亲”的制度。——译者\n伊斯的结论形成于1833年,所发表的十二篇论文中;这些论点是如此新奇,以致他不敢发表出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在他的《旧约圣经史》里把它们提出。他认为瓦特克的书看起来是如此令人生畏,以致他不曾阅读它;直到他的看法由他自己的门生发展以后,他才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问题上来。在他的听众中间有格拉夫,格拉夫的《旧约全书的历史诸书》于1866年出版,它是从早在一个世代前种植于他心里的萌芽成长起来的,后来被称为格拉夫的假设,并被采入杜姆关于《先知书》的权威著作;这部著作把《先知诸篇》作为犹太人的宗教发展之中心;但要推翻传统的错误观点,尚有待于更有威力的作品的发表。奎嫩关于《旧约全书》的研究使他赢得博学多才的学者名声;他的①《以色列宗教》出版于1869年,其中采用了格拉夫的假设。这位莱顿大学的教授虽然缺少埃瓦尔德的口才,却能激发起更多的信任。他否定犹太宗教异乎一般的起源论与独特的性质,拒绝《旧约全书》上的神迹,并宣称《五经》与《约书亚记》里的早期历史大部分属于传说。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时的资料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些传说才能取得可靠的根据。他宣称,由于按年代顺序重新排列《旧约全书》诸书,编写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史已成为可能。他从概述公元前第8世纪的宗教开始,再简略地回顾它的起源。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可能存在过。摩西确曾存在。“出埃及”可能发生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多神教不是一个革新,②而是“放逐”以前大多数人的信条。祭司立法是在放逐之后起草并记载下来的,起源于各个不同的时期,并经过不止一次的编订才最后定形。第三卷专讲犹太教,叙述止于耶路撒冷的陷落。奎嫩的著作连同它冗长的附录和注释,是一系列专论而不是一部叙述。但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解释以色列宗教的各个连续的阶段;关于这方面,埃瓦尔德是未曾掌握的。③威尔豪森在1876年出版他的《六经的编写》并在1878年出版他的《以色列史》以后,那些由瓦特克、格拉夫和奎嫩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及罗伊斯和拉加德在他们的演讲中所阐明的假设,不复是各个孤立的学者①的所有物,而成了公共的财富。虽然作为埃瓦尔德的门生起家,威尔豪森觉得《律法篇》与《先知书》属于不同的世界;他欢迎格拉夫假设的出现。在《士师记》、《列王纪》和《先知书》中,没有《律法篇》的痕迹,而在“放逐”后,它立即变得突出。这些事实,一见自明。摩西律法不是古代以色列历史的起点,而是犹太教历史的起点。《申命记》在约西亚时代的圣殿内被找到。《利未记》直到犹太王国覆亡后才被写②出;《五经》直到以斯拉时代才被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就有可能估计《先知书》的起源和意义。这一著作在全世界历史家与神学家中间曾引起极①参阅雷维尔《亚伯拉罕·奎嫩》1890年。——译者②“放逐”(TheExile)——指公元前597—586年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两度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之事,又称“巴比伦之囚”。——译者③六经(Hexateuch)——《旧约全书》开首六卷,即《摩西五经》与《约书亚记》的合称。——译者①威尔豪森的成绩被很好地总结于普夫莱德雷尔《自康德以来神学的发展》,1890年。比较罗伯逊·史密斯的评论,见《演讲与论文》,1912年。——原注②以斯拉,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伯来祭司,宗教改革家,由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进行改革。——谭注\n大震动。它从来未被续写过,在后来的重版上,采用了较合适的书名:《以色列史绪论》;但他为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篇《以色列与犹太史》概略;并在1894年出版一篇更完备的记载。威尔豪森的书使研究《旧约全书》的学者分成两个阵营,但大多数专家是站在他的旗帜下的。一般承认,只有他的解释,能使犹太人的宗教发展成为可以理解的。三年后,施塔德开始出版一部根据该书结论写的《以色列史》。这部著作是用高度批判的语气写的,甚至几乎是用雄辩的语气写成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于其他历史科学,因为它几乎被神学家一手垄断了”。但要促使这门科学发展,却需要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比较宗教研究者的帮助。在他的著作中,关于旱期以色列传统故事很少保留下来。关于侨居埃及的事情,他认为找不到什么证据,并宣称关于征服迦南的记载纯属传说。关于大卫时代,我们有了可靠的根据,但必须提防编年史家过分夸大的说法。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是弱小的,它的文化是原始的,描写中宫廷和圣殿的繁华只是一个神话。当时,叙①利亚分裂为许多小邦;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小邦的典型统治者。米沙王铭文的发现,揭示出摩押族及其部族神和与之相应的思想体系。在先知时代以前,没有什么一神教;崇拜祖先和信仰鬼神是普遍现象。“伊诺欣”与“耶和华”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微小的。由于吸取了威尔豪森的研究成果,施塔德在约西亚王时代以前找不出摩西律法的痕迹。他相信,“放逐”到巴比伦除了减少了宗教崇拜机会外,决不是痛苦的。这第一部批判性犹太人历史巨著的力量与学识,不能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书中的论战口气和经常强调传统的虚伪,却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欣赏。②在英国,威尔豪森见解的主要鼓吹者,是他的朋友罗伯逊·史密斯。他曾在戈丁根大学从拉加德学习塞姆人语言学的奥秘,1870年二十四岁时,他被聘为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东方语言与《旧约全书》教授。1875年他为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篇关于《圣经》的文章,因此③他被控为异端。对他的长期审判,曾象对科伦索的审判那样引起很大注意。这个教授最后被免除异端罪,但他的教授职位却被剥夺。他深信自己的批判原则,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对广大的听众发表演讲;后来这些讲稿是以《犹太教会中的旧约全书》和《以色列的先知》的书名出版。虽然论述是通俗的,但却是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大陆上的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创见结合在一起的。在被聘为剑桥大学阿拉伯文教授后,他写了《早期阿拉伯的亲族与婚姻制》和《塞姆族宗教讲义》,后者对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和塞姆族人氏族其他支系的信仰与仪式作了系统的比较。他指出:信仰是变幻无常的,因而难以注明日期;只有宗教的仪式是原始而又固定的。他的研究导致他拒绝关于塞姆族和雅利安人之间存在着基本差别的看法。这些著作中充满深刻的研究与精湛的分析。虽然不如他的①米沙王(MesaMesha)居于以色列以西的摩押部族之王。初臣属以色列,后背离,为以色列所擒。事迹见1868年发现的摩押碑。——谭注②参阅布莱克与克里斯托尔所作的传记,1912年。比较伯基特,《英国历史评论》,1894年10月号。——原注③科伦索(Colenso,JohnWilliam,1814—1883年)——英国人,南非那塔尔主教,宣称《五经》是在“放逐”后时期伪造的,因而被开普敦中心主教区逐出教会(1863年)。——译者\n早期演讲著名,它们却显出在英国也有这样一个研究塞姆族的学者,他在学识方面与洞察力方面,都可与荷兰和德国最有名望的学者不相上下。他的早逝对于《旧约全书》的研究和对于比较宗教这门新生科学,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①在法国,按照威尔豪森路线来批判地论述犹太史的工作,是由勒南开始的。在完成他的著作《基督教之起源》后,他回到那个使他成名的领域。他曾写过一部有学术性的塞姆族语言史,参观过有关犹太史的遗址,并劝告铭文学院编辑一部塞姆族铭文集。他宣称,“为了前后一致,我应该以我今天出版的书作为我的《基督教之起源》的开端,因为它们追溯那些把道德引入宗教的伟大先知。”他补充说,他由于感到寿数无常,他首先选择了他工作中最紧要的部分。但是在六十岁时,他看到自己身体尚健,于是勇敢地投入工作,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五卷犹太人民②的历史;它在这著作中虽不是最能令人信服的却是文笔最为流畅的作品。第一卷,叙述到大卫时期,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传说。勒南深信:传统说法包含宝贵的成分,即使不是属于事实的,也至少是属于气氛的成分。在这个朦胧世界中进行巡礼时,历史家需要有想象力。“即使我在若干点上的推测容有差错,我确信,我已领会那由上帝的呼吸即世界灵魂通过以色列人而完成的独特工作。”他提醒他的读者:他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关于历史时期前的社会和宗教的一个半想象的重现。关于下列事情,可以描出轮廓——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在埃及的流寓、在摩西或其他某个首领率领下的逃出埃及;但在大卫时期以前,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事实。要问什么事情曾发生过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只能描绘事情可能发生的各色各样的方式。每一句话都应包括“也许”这个字样。普通读者对本书的爱好远胜于专家对本书的爱好。奎嫩宣称,勒南不作资料的分析,好象没有航海图即扬帆开航一样,并埋怨说,他在接受资料与摈弃资料方面也同样是任性的。威尔豪森谴责本书与作者的名望不相称。罗伯逊·史密斯宣称,他关于族长制时代的重塑是全部错误的。史密斯还说,这些族长与游牧民族截然不同,他们近似于列王时代的大家族的家长。勒南相信塞姆人的一神教倾向也同样是无稽之谈;因为一神教只有在以色列,而且是由于先知才发展起来的。他还夸大“亚卫”与“伊诺欣”之间的差别;后者只是他幻想的产物。他把早期以色列人理想化,并相信他们已退化,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宗教思想却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得澄清和纯洁的。这样看来,第一卷尽管①文笔秀丽,却是五卷著作中内容最贫乏的部分。犹太人的历史时期据说是开始于大卫,即耶路撒冷和王朝的创立人。但勒南所描绘的形象失之暗淡模糊,正象埃瓦尔德所描绘的形象失①关于论述勒南的最好的著作,由下列作家编写:格兰特·达夫,1893年;舍叶尔(Séailles),1895年;达姆斯特泰尔夫人,1897年。达姆斯特泰尔,《勒南生活与著作的概要》。1893年,这本书是对研究塞姆族学者的一个专家的定论。——原注②书名《以色列人民史》(Histoiredupeopled’Israel),1887—1894年。——谭注①关于专家的批评意见,参阅罗伯逊·史密斯,《演讲与论文》1912年;奎嫩,《三条道路,一个目的》,见《论文集》,1894年。——原注\n之于过分绚丽多彩一样。勒南是不喜欢这个国王的;他相信,国王的权力已被传说夸大,并指出不能把《诗篇》算作是大卫的贡献。大卫被比②作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小王公或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首领阿卜杜·卡迪尔;他是一个残忍的国君,由他的宫妃包围着,依靠外国雇佣兵的支持,并缺少宗教与道德观念。所罗门是路易十四的缩影,聪明胜过他的父亲,但他是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关于这个分裂的王国,勒南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图景。时代是原始的;诸王是残忍的;耶和华又鼓励各种可憎恶的事情。他宣称,以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他以嫌恶的③心情描绘着他的野蛮的不容忍态度。亚哈看来是一个容忍而又开明的统治者。当时最重要的事件,是把有关族长与战争的传说写成文字,接着分别写成以“亚卫”称神的经文和以“伊诺欣”称神的经文;这些作品在很久以后又都汇总并入《五经》之中。勒南关于先知的描写遭到普遍的批评。他常常宣称,犹太人代表宗教,正如希腊人代表智慧;但虽然承认以色列的历史重要性有赖于众先④知,他却看出他们功过相等。阿摩司又阴沉又偏狭,狂热地以最后审判①日来威胁人们,劝告人们撕裂心灵以示悲伤而不仅仅撕裂衣服。何西阿象〔法国〕天主教同盟的一个传教士或一个〔英国〕清教徒劝世文作家②一样。以赛亚的名望大半由于他被认为是那个生活于“放逐”时期的更大天才所写的著作的作者。这个先知是他的人民的良心,但他也似一个颇似布道师的宣传家,一个颇似神学家的政客;他是卡尔文、诺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先行者。勒③南不能掩饰他对耶利米那过度不能容纳异己的态度的轻蔑;他叱责耶利④米是宗教迫害的首倡,是君主政治和国家的公敌。以西结使人想起维克⑤多·雨果的《惩罚集》和傅立叶的社会幻想。对道德标准的排他性成见,既无助于文化,也无助于民族威力;诸先知加速了一个民族的覆灭,而②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年),阿尔及利亚部落联盟首领,1832—1847年领导本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民族英雄。——谭注③亚哈,犹大王(约公元前874—852年在位),其妻左右国政,崇祀邪神,欲使国人从之。国中大旱,耶和华频频遣先知示警,图废立。外敌来犯,亚哈迎战,死于阵。——谭注④阿摩司,公元前8世纪时犹大小先知,其说教以上帝的裁判为主题,揭发尘世罪恶,预告灾难。——谭注①何西阿,以色列的小先知,阿摩司同时人。以夫妻比喻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其讲道简捷,充满狂热——谭注②以赛亚,8世纪中叶时人,被认为是《旧约》所记最伟大的先知和演说家。反对希伯来诸王干预邻邦事务,认为与亚述结盟后应守信约,对埃及不可依赖。——谭注③耶利米,公元前7—6世纪以色列先知。多次受到反对者的迫害,不断对本民族的罪恶发出警告。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后,对他颇为优礼,后定居埃及,据说约书亚王对偶像崇拜者发动迫害是受了他的影响。——谭注④以西结,公元前597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被俘,即于是年开始其先知生涯。其预言为谴责以色列的过失,指出充满希望的未来。——谭注⑤《惩罚集》是雨果所作的讽刺拿破仑三世的诗篇。诗中以小拿破仑和其伟大的叔父对比,呼吁上帝惩罚这个窃国僭位者,闪烁着要求报复的憧憬。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和三十二个时期,预言生活将由漫长的不和谐的境地进入和美的境界,充满幻想。——谭注\n这个民族又的确是没有政治才华的。可是,先知们具有不朽的重要地位。他们把一个部族的神灵转化为一个宇宙的正义主宰。他们为穷苦卑微者的事业而呼吁。他们是人类宗教的创立人,耶稣的先行者。早期以色列未曾有过真正的宗教。“伊诺欣”是空中的众神灵,“亚卫”是一个小世界的反复无常的专制魔王,他所索取的只是祭品,并非一颗纯洁悔悟的心。诸先知使渣滓化为黄金,并发展了伦理的一神教观念。没有人曾①以更大的热情写出第二个以赛亚,那个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先知。“我们同他一起站在一个高山之巅,从那里我们望见站在另一个顶峰上的耶稣,其间存在着一道幽深的峡谷。”从世俗国家转化为神权国家的过程,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前已经开始,勒南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追述,并未表示赞同。他严厉斥责《祭②③司法典》的无用,及其注释家枯燥无味的烦琐哲学。尼希米被说成是最早的耶稣会会士,他把耶路撒冷变为一座坟墓。《法律篇》是已发明的最可怕的使人痛苦的工具,是对诸先知传统的不可宽恕的背离;他们的工作只有靠基督来重新进行。精神被文字扼杀。关于犹太教的诸章,虽然包含很多有根有据的批评意见,对错误的驳斥却太多。他赞颂犹大④斯·玛喀贝斯的英雄主义,但以极其愉快的心情详细论述希腊化时代的⑤解放影响、对撒都该教派和《传道书》的有修养的怀疑主义以及希勒尔与菲洛⑥的宽大慈悲也倍加赞赏。构成希腊化时代气氛的是它的文化和文学、社会和思想、理想和迷信;关于它们的丰富多彩的论著,表明这个历史家虽然年老体弱,但他的手笔却仍然十分灵巧。他实现了他一生的雄心壮志,因为他的两部巨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布伦蒂埃证实说,“有普通文化的法国人对于古代东方、对于比较宗教、对于圣经的注解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勒南的。”他的成绩就在于唤起兴趣。关于继续与修正他的著作这项工作,要由更务实的学者们去完成。威尔豪森对以色列古代史的重新解释,一致地或无条件地加以接①受。老德利茨施悲叹道,如果威尔豪森是对的,那就不可能再谈论“律法篇与先知书”了。霍梅尔一度接受他的意见,后来又回到传统的见解。②在施塔德的反传统的著作出版后,基特尔立即对“囚虏”时期前犹太人①四大先知是: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与但以理(Daniel)。第二个以赛亚指但以理。——译者②《祭司法典》指《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27章中所记的犹太教宗教仪节、典章和条例。这部宗教法典是以色列人被俘至巴比伦以后逐渐形成的,但《旧约五经》却认定它在摩西时代就已存在了。——谭注③尼希米,犹太人,耶路撒冷失陷后,被波斯王任为犹太总督,重建圣城,恢复民族礼拜。——谭注④玛喀贝斯,犹太玛喀比族爱国首领,于公元前175—164年领导反对叙利亚人的起义,并一度占领了巴勒斯坦。——谭注⑤撒都该教派(Sadducees)——古犹太当权的祭司贵族教派,起源于所罗门时代的祭司撒都(Zadok),否认有复活、来世及天使等说。参见《新约·马可福音》12章18节至28节。——谭注①老德利茨施(Delitzsch,Franz’1813—1890年),德国著名神学家与希伯来语言学者,属于保守主义神学派。其子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850—1922年)被称为小德利茨施,亚述学家。——译者②书名《以色列民族史》(GeschichtederVolkesIsrael)共二卷。——谭注\n的历史提出相反的解释。虽然罗伯逊·史密斯认为这是对威尔豪森的见解的削弱而不予考虑,虽然对批判学派作出若干让步,他的著作仍是属于迪尔曼的保守主义阵营。他相信亚伯拉罕与约瑟,认为《十诫》是摩西所作,还在那些被其他学者称做添加部分而不屑一顾的历史著作里找出真正的传统的片断。这部著作是在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一个妥③协,而把《祭司法典》的主要部分归属于希西家统治时期,却使发展的线索陷于混乱。它的主要功绩,在于对资料的详细分析。威尔豪森的其他批评者,虽然接受《律法篇》编得较晚的说法,但他们却相信,它的若干部分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在实质上也远比他所承认的要早得多。蒙蒂菲奥里在希伯特的演讲中,根据近代的研究成果巧妙地提出了一个犹太人对犹太历史的见解。除一般性的历史著作外,出现了无数专著,为历史大厦添砖加瓦。罗伊斯、科尼尔与德赖弗提供了关于《旧约全书》著作的有用的概论。乔治·亚当·斯密的《圣地历史地理》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贡克尔研究了希伯来宇宙论的来源与性质。爱德华·迈尔分析了关于族长的传说,并评述早期以色列的邻邦。那个“放逐”后的时期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荷兰神学家科斯特斯曾声称:犹太人在居鲁士时代被释返国之说是神话,圣殿是由那些未曾被俘而留在本土的犹太人建造起来的。这项宣布曾震动一时。这个论点被爱德华·迈尔驳倒,他的《犹太教的起源》确定了《以斯拉记》里所引用的波斯文献是真实可靠的。切恩对“放逐”后的宗教生活描绘出一幅最好的图景。许雷尔的巨著《基督时代犹太人民的历史》,是关于犹太人三百年间的政治、宗教和哲学,以及文学和社会之概览,其中利用了铭文、纸草卷和古币的新资料。犹太人的历史从考古学研究所得的益处,比埃及或亚述历史所得的①要少得多。在耶路撒冷,没有发掘出辉煌的建筑物或雕刻品,铭文也极少。在其他地区的发现,对于《圣经》记载很少阐明。对这个地方的系统考察,是由爱德华·鲁宾逊和托布勒两人首先进行的。前者系美国一个希伯来文教师,他于183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次施行纪录。后者的七卷历史地形学相当于利克的希腊概览。1865年美国巴勒斯坦开发基金的创立和1878年德国巴勒斯坦学会的组织,提供了合作研究的机构。美国和德国在耶路撒冷还设立了考古研究所。弗林德斯·皮特里和布利斯考察了莱基什区,在那里发现了十一个约存在于公元前1700至1400年时期的古城遗址。舒马赫揭开了米吉多的若干秘密,我们关于撒马利亚的少①许知识也是从他获得的。塞林能够说明在他纳与耶利哥的富有成效的考察工作。麦卡利斯特详细地揭示了基色的历史记载,在那里有七个古城的地层可远溯到新石器时代。他的发掘工作的最有趣的结果,是恢复腓②力斯人的地位,他们是在两千年间所积累的文物中最有艺术性的作品的③希西家,犹太王,约公元前727—699年在位。——谭注①参阅神父樊尚,《按近时探索的伽南》,1907年;德赖弗,《斯威奇演讲》,1909年;布利斯,《巴勒斯坦考察的发展》,1906年;希尔普勒希特,《圣经地区的考察》,1903年;麦卡利斯特,《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发掘》,1925年;凯尼恩,《圣经与考古学》,1940年。——原注①他纳,伽南城镇,其王为约书亚所杀。遗址在米吉多古城东南五英里处。——谭注②腓力斯人,据《圣经》传说是居于今巴勒斯坦的好战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世仇。——谭注\n作者。现在,我们可以对巴勒斯坦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代,并看到这些穴居人渐渐被塞姆族侵入者驱逐的情景。耶路撒冷的部分发掘,已揭示出史前期的隧道与排水管网。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以色列与犹大境外。1868年发现了米沙的石版,即一般所称的摩押碑,它是用塞姆族字母刻③成的最古铭文,日期始于亚哈谢与约沙法时代。亚述铭文,包括萨尔贡与西拿基立的铭文,描写希西家时代对撒马利亚的占领和对耶路撒冷的围攻;这些铭文补充了《旧约全书》的记载。那些阐明巴勒斯坦在公元前14世纪的政治和文化的特勒阿马纳书板上的文字,谈到察比里人,有①些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希伯来人。那被讨论得很多的麦伦普塔的铭文于1896年被皮特里发现,其中包括以色拉尔(Isirar)这个名词,因而有些专家认为铭文指出,在巴勒斯坦有在麦伦普塔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但关于以色列人寄寓埃及的故事,没有找出任何确切的证据。1904年,发现了关于犹太人在埃勒凡泰尼岛(尼罗河上第一瀑布附近的一个岛)上的军事殖民地的纸草卷纪录;这个发现给公元前第5世纪以可喜的阐明。阿拉米文已经代替希伯来文;这些殖民者虽然崇拜“亚卫”却并不是一神教的信奉者。关于近时《旧约全书》研究之最突出的特点,是讨论犹太人承袭巴比伦宗教和文化的问题;但直到1902年〔小〕德利茨在柏林发表一次讲演后,这种关系才成了普遍讨论的题目。他的《巴别塔与圣经》,数以万计地销售,并断断续续地出版一系列论文来证实并发展书中的论点。他宣称,直到近世为止,以色列曾被看作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自成一个世界;同时,《旧约全书》被认为是关于古代东方的主要有权威性的典籍。但现在一个更古老、更浩瀚的文明已被发现,以色列的科学和宗教都源出于这一文明。特勒阿马纳书板显示出巴比伦文化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之间的优越地位;以色列人一开始就受到它的影响。洪水的古传说,当然会在经常受到水淹的地方兴起。创世传说,是属于巴比伦②的,造物主是马尔杜克神。关于禁果、蛇和失乐园的故事,出现于一个①巴比伦圆柱形土器上。虽然流行多神教,但关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却是普遍的。巴比伦文明的道德水平并不明显地比以色列的水平低,而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来自苏美尔人的一项遗产),倒是较高的。天文学以一小时分为六十分,一分分为六十秒,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发明的。犹太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的独创性并不比在科学和法律方面的更多。对于犹太人的创见之否定,引起传统看法的拥护者的激烈论战。最猛烈的回答,来自霍梅尔;他率直地宣布,在〔德利茨〕演讲中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他断言,以色列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德利茨关于巴比伦一神教的概念是错误的;《圣经》中的传说起源于迦勒底③亚哈谢,以色列王,约公元前844—43年在位;约沙法,犹大王,约公元前873—848年在位。——谭注①麦伦普塔(约公元前1225—1215年),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曾击退利比亚的入侵。相传,希伯来人在他统治时期离开埃及。——谭注②马尔杜克神(GodMarduk),按巴比伦神话,是万神中的主神。本为农神,也可能为一个太阳神;在阿喀德的《创世纪事诗》(EnumaElish)里作为一个风神。——译者①参阅本书第716—717页。——译者\n人而非巴比伦人。《五经》虽然不是摩西的著作,却是在他以后不很久写成的;迦南—巴比伦的影响只是出现在它的增补部分。不太固执保守的学者,也不大满意。基特尔宣称,这门科学是这样的年轻,所以传播些耸人听闻的怪事是不可避免的。巴比伦的宇宙论和《圣经》之间存在着基本分歧。巴比伦地区是信仰异教的,而《圣经》是属于一神教的。那些取自巴比伦的部分已经改头换面,而后来的形式要比原始概念具有更多真正的创见性。以色列已把渣滓变为黄金;巴比伦是一个资料源泉而不是一个模型。但是德利茨能站稳了他的立脚点,为他的中心论点提供新鲜例证,在这方面巴比伦的发掘使他获得了新资料。温克勒、杰里迈斯和齐默恩都同样地宣传犹太人继承巴比伦遗产这项见解:温克勒详尽阐明了巴比伦宗教的星象理论,后两人步武他的后尘。温克勒在他的《以色列史》里主张: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的传说,属于根据巴比伦占星术的体系。杰里迈斯在他精心写成的著作《从古代东方的新发现看〈旧约全书〉》中详细地证明了这项影响。他声称,巴比伦是在犹太人中间发现的所有最高概念的渊源;虽然以色列的公众是信仰异教的,可是领导人的信仰是对“亚卫”的纯洁崇拜;而这种崇拜原是来自巴比伦的。巴比伦的影响是这样地持久,甚至在《启示录》里也可以找到。温克勒与其学派的说法,不管多么怪诞,却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犹太宗教的由来。关于犹太人继承巴比伦遗产的实质问题,还不能贸然作出定论,但承认这一点已足以使早期以色列史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变化,并为世界宗教史提供一个新的背景。关于犹太人在《圣经》①以后时期的错综复杂的命运,格雷茨在他的多卷本著作里第一次作了充分的描述。Ⅱ19世纪的成绩之一,是新教徒的学术研究为教会史赢得了科学地位②。各种教派间的冲突从未平息过,信仰与不信仰间的搏斗也在继续进行,可是甚至在如基督教的起源与宗教改革运动这样引起争论的领域里,也已有了某些格局和定论。最早的详细叙述,是由马格德堡世纪派写的;他们热烈的新教情绪,使他们只看到从原始教会以来的不断退化,并在罗马教皇身上找出反基督的特征。巴罗尼借助梵蒂冈档案来编写出正式的答辩;他的宏伟著作迄今仍然有用。路德教会陷于顽固而僵化的形式主义;为了反对它,产生了虔诚派。1699年,戈特弗里德·阿诺德根据基督徒生活的价值无限地高于一个机械的正统这一信念,编写了《诸教会与异端流派的公平史》①。宗教改革运动,在开始时原是为反抗天主教会的世俗化倾向,但它也很快就同样走上歧途。象弗拉修斯那样,他虽承认日益加剧的退化趋势,①书名《犹太人史》(GeschichtederJuden),共十一卷,1853—1875年。——谭注②参阅鲍尔,《教会史编纂的时代》,1852年;黑德勒姆,《早期教会史的方法》,见他的《历史、权威与神学》,1909年;布拉特克,《教会史资料指南》,1890年;科尼比尔,《新约全书批判研究史》,1910年;尼格,《教会史编纂》,1934年;以及几篇传记,见《新教神学与教会百科全书》。——原注①关于阿诺德,可参阅里奇尔的《虔诚派史》中有趣的一章,第Ⅱ卷,1884年。——原注\n但他不是把责任只归于教皇统治,而是也归于所有那些使教会转变为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并使基督教僵化为教条的各种影响。基督的福音,主要是存在于异端派中间,他们是该书的主角;他们此仆彼起地对教权主②义进行反抗。在莫斯海姆的著作里,我们看不见弗拉修斯的宣传热诚与阿诺德的神秘虔诚。他以冷静的宗教热忱的语调来处理他的论题,写出了第一部属于近代世界的教会史。在他看来,教会是一种象国家那样的机构。他的论述基本上是根据史实的、政治的、世俗的。戈丁根大学的教授们把教会史联系到世俗事件,并不理会大量的传说中的细节,但他们对于辽远时代及其他思想形式缺乏洞察力。他们中间最有才干的斯皮③特勒轻蔑地称阿塔纳修斯为僧侣,称伯尔纳为专制魔王。在戈丁根大学,没有人懂得爱好教会史或尊重圣徒。浪漫主义运动把感情与幻想重新捧上它们的宝座。信仰的时代受到荣宠,而历史家注意追述基督教原则的实施甚于注意叱责罗马教廷。这个新精神在犹太人大卫·门德尔身①上得到了体现;他在十七岁时皈依基督教,并取名为奥古斯特·尼安德。②他被施莱尔马赫引入宗教哲学方面并研习伯麦与柏拉图的著作,因而他③觉得普朗克在戈丁根大学的教导太富于理性主义而不适合于他。许多年代后,他声称,“一个信仰的新生活已经觉醒;它开始鼓舞研究工作。生活与科学都谴责那种肤浅、无情的启蒙运动,因为它公开蔑视过去时代的伟大与光荣。”他很快就学会了爱护“教父”,但他满足于简朴的④虔信派教徒的基督教。1812年,在完成一篇论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的论文后,他撰写他关于朱里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次年,在二十四岁时,他被新成立的柏林大学聘任教会史讲座,他担任该职,直到1850年去世⑤⑥⑦为止。他关于圣伯纳德、诺斯替教、克里索斯托姆与特图利安的专著,一本接一本地迅速出版。1822年,他出版《基督教生活纪念品》,以一系列图片来说明基督教生活的精神与效果;1825年,他的《基督教会史》第一卷问世。教会史对尼安德意味着描写圣徒的生活多于叙述教条或制度的发展。作为施莱尔马赫的门生,他认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情绪的反映;它不同形式的种种表现,是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的。甚至对朱里安,鉴于他的真诚信心,他也同情地予以论述。他对教会作为一个伟大权力机构方②参阅霍伊西,《莫斯海姆教会史编纂》,1904年。——原注③伯尔纳(约1090—1153年)圣徒,法国西多教团修士,圣殿骑士团创建者。在神学上,反对阿贝拉派。曾发动并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一败涂地。——谭注①参阅沙夫,《奥古斯特·尼安德》,1886年;哈纳克,《演说与论文》,第Ⅰ卷,1904年;利希滕贝格,《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史》,1889年。——原注②伯麦,J.(1575—1624年),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秘主义者,认为对立物的冲突是按照上帝意志的宇宙力量,具有创造性价值。他的观点长期被斥为异端。——谭注③普朗克,G.J.(1751—1833年)、戈丁根大学教授,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谭注④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约150—约215年),希腊神学家,试图将希腊异教思想与基督教相结合。——谭注⑤诺斯替教(Gnosticism),1至6世纪间,以波斯、希腊神学和哲学来说明基督教教义的教派。——译者⑥克里索斯托姆(345?—407年)即圣约翰,君士坦丁大主教(398—404年)。——谭注⑦特图利安(约180—约230年),生活于罗马与迦太基之神学家,著述甚多,文笔优长。——谭注\n面不甚感兴趣;他认为教会的复杂机构与它的世俗活动,对原始基督教简朴纯洁来说是一种堕落。他的任务是强调指出敬神生活的美丽与芬芳,使对基督教男女圣徒的研究成为个人修养的工具。在叙述到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这项工作即由于他的逝世而中断。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对罗马和维滕堡所共有的遗产感激之情。虽然他始终相信基督教教条的真理,但他从来不热衷于攻击异端,也从来不主张教义的重要性可以离开道德结果而存在。由于相信基督教是一种神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他能从无数各不相同的形式中寻求它并找到了它。哈纳克称誉他为一个新教的本尼狄克派。全书的精神是极度和解的。他同情地对待教会的大人物,比起过去启蒙运动时的敌意来,这是一种使人感到舒畅的转变。但它也带着严重的缺点。虽然他强调个性的神圣性并抗议任何摧残个性的行为,但他所描绘的人物却流于单调乏味。所以,他描写意气相投的人物虽然取得成功,但描绘比较粗鲁的人物却有时失败。他认为圣徒比政治家好,学者与神秘主义者比行动家好。由于他厌恶教阶制的世俗方面,他看不见一个有力而常设的组织是必要的。并且,他象其他浪漫派成员一样,缺乏批判的本领。他原封不动地使用所找到的资料,从未认识到有责任确定这些资料的价值。尼安德做为一个教师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亚于他作为一个作家所产生①的影响。他的教室内挤满好学的学生;他的学术讨论班培养出一些继承师训并能青出于蓝的学者。他讲课时不仅对于他的论题充满热情,而且向学生灌注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他提出严重警告,要防止无论是以理性②主义形式还是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过度的唯智主义。虽然他不喜欢在他周围出现的批判精神,但他却反对从柏林大学逐出德·韦特;当被问到对于禁止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意见时,他表示反对这个禁令。的确,好战的正教领袖亨斯滕堡曾经指斥他只是半个信仰者。但在教会历史家中间,没有人比这个有学问而可爱的基督徒更有吸引力。虽然研究教会的历史需要更多批判方法,但忽略他的功绩也是不公道的。他对所有基督教徒发出了他的呼吁。默勒曾听过他的讲课,宣称他是第一个真正懂得教父的德意志新教徒,并称赞他对天主教教条与早期教派的惊人的理解。象夏托布里昂在法国那样,他挽救了基督教会,使之脱离启蒙运动的敌对气氛或半轻蔑的庇护状态。1826年,即尼安德的主要著作的第一卷出版后一年,费迪南德·克③里斯蒂安·鲍尔被聘任图宾根大学历史神学讲座。他站在另一极端并以不同的气质、方法与结果从事研究,但他所产生的影响持久得多,他为批判地论述教会史奠定了基础。虽然图宾根学派的论点很少被人接受,但当时它却给了教会史的研究以不可估计的推动力。鲍尔是一个符腾堡牧师的儿子,曾在图宾根大学研究神学。他关于《古代象征主义与神话学》一书使他获得那个担任到1860年去世时为止的讲座。他的讲稿构成①参阅伦茨:《柏林大学史》,第Ⅰ卷,第614—616页,1910年。——原注②唯智主义,主张一切关于现实的认识来源于智甚或理性的观点。——谭注③参阅泽勒的杰出论文,《F.C.鲍尔》与《图宾根历史学派》,《演讲与论文》,第1卷,1875年;魏茨泽克:《F.C.鲍尔》;马克·帕蒂森:《德国神学现状》,《论文集》,第2卷;普夫莱德雷尔:《康德以来神学的发展》,1890年;以及迪尔泰:《全集》第Ⅳ卷,第403—432页。——原注\n了他著作的基础;他以惊人的速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的作品,历时三十多年之久。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讲述教条的发展、《新约全书》诸书和教会史。虽然他早年生活中的主导影响来自施莱尔马赫,但黑格尔却逐步替代了后者。鲍尔的第一类著作以论述摩尼教和诺斯替教的专著作为开端,他并在其他著作里讨论赎罪理论和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些著作以其联结思想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技巧而著称。他的功绩,在于把规律和成长的概念引入教条的领域。“鲍尔擅长于追述那些贯穿于各个时代,深奥得人们不能理解的思想之进程;这在文学上是一件新①事物”。他象黑格尔解释希腊哲学那样,解释基督教教条的辩证发展。他的叙述是关于事实者少而关于思想者多。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耶稣复活的观念而不是耶稣复活的事实:他宣称,复活是否确有其事,这个问题不属于历史范围。宣布基督教是一个自然现象或是超自然的现象,不是历史家责任的一个必要部分。在第二类著作里,鲍尔致力于解决《新约全书》诸书的日期与著作人的问题。他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深信,研究《新约全书》必须和研究其他文献一样,对作者的人格和观点也必须予以考虑。早期学者曾把他们①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福音书》,而他是从保罗的著作出发的。他对于这个非犹太人中的伟大使徒的看法,支配着他关于早期基督教的见解:②他似乎认为,这整个时期的关键在于彼得和保罗之间的对立。他宣称,基督教不是一个完备无缺的启示,而是由那些逐渐发展起来的思想和倾向所形成的一个复杂体。他起初是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早期基督教徒认③定耶稣是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体现。正是保罗使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由于这个缘故,他和十二使徒分裂。保罗派普世宗教与彼得派犹太教之间④的斗争,使我们能够确定各卷经典编写的日期。《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书》清楚地反映出这项争执;因而它们是唯一真实可靠的使徒书信。有些著作中冲突缓和了,可以说这些著作的编写日期是从①阿克顿,见《德国历史学派》。——原注①保罗,原名扫罗。最初迫害耶稣门徒,后受启示,相信耶稣,传教于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成为非犹太人中的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许多篇章(如《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等)相传是他的作品。——谭注②彼得和保罗的对立,实质上是基督教是否将成为普世宗教(Universalreli-gion或Universalism)或只是一种民族宗教,即犹太教,两种思想的对立。彼得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七十三节),耶稣受难及复活后,在以色列人中布道,而无意于向非犹太人(外邦人)扩散。保罗则不然。他原是有名的开明派教法师迦玛列的门生,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改变信仰后就有志于改造犹太教,使之成为普世流行的宗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在这些方面:一、可否吸收外邦人入教?二、外邦人信教要不要遵守犹太教的教规?三、彼得不太重视教会的组织、典章、信条;保罗则热心于到处设立教会,并称信徒为“基督徒”,以别于一般的犹太教徒。四、彼得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应受到特别恩宠;保罗则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使基督教在教理上得以摆脱犹太教的狭隘性。以后,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基本上是按着保罗所定的基调发展的。——谭注③弥赛亚,希伯来女,为“受膏者”。古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时常在受封者头上敷抹膏油。自犹太危亡以来在犹太人中间流行一种说法,谓上帝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基督教产生后借用此说,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凡信仰他的人,罪可得赦,灵魂可升入天堂。——谭注④见本页注\n第2世纪妥协时代开始的;当时基督教的领导人一方面遭到来自诺斯替教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迫害的威胁,因而不得不把他们的争吵搁在一边。在这些后期作品中,有《福音书》:编写它们所根据的纪载现已散失。《马太福音》是最接近于这些原始记载的,因为它最忠实地重现了犹太化基督教气氛。《路加福音》来自另一个阵营,但为了和解的目的已经过修改。《马可福音》则编写得更晚,因为所有的对抗痕迹都已消失。《约翰福音》是一部哲学著作而非历史著作。《使徒行传》是一种巧妙的和解尝试。这种大胆的解释推动了研究工作,但是这座大厦是建造在沙滩上的。他大大夸张了原始教会中的冲突,而忽略了其他力量与运动。首先,他很少注意基督这个人物。人们常说,在鲍尔眼中,保罗是基督教的创立人。他认为基督是他的门徒所讨论的一种思想体系的创始人,而不是他们所追随的一个人物。他按照《新约全书》诸书对彼得派与保罗派之间的斗争的态度来确定它们的编写日期,这种方法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论点一起倒坍了下来。他不得不把《马太福音》列①在《对符类福音书》的首位而把《马可福音》列在它的末位,这就充分证明他的设想是错误的。第三类著作涉及教会的一般历史,是鲍尔晚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在这些著作之前,他写了一部关于教会历史家的专著;他看出在所有这些作家中间,没有人能够深入观察演进过程。教会史的第一卷叙述起初三个世纪,于1853年出版;它的重要性在于概括他久已发表过的意见。第二卷出现于1859年;还有三卷,完成了这项概述,在他死后出版;其中最后两卷只是他的讲稿的翻版。他的长处在于论述最初的几个世纪;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时期的研究,他是没有什么特殊权威的。他的忠实门生兼同事泽勒宣称,《教会史》无论在形式上或方法上,都是鲍尔最完善的著作,尽管不是最重要的著作。他最长于追述思想的发展,而最不善于处理个别人物。尼安德的研究是从情感出发,而鲍尔的研究是从理智出发。两人的意见都是根本上不完备的。可是鲍尔也象尼安德一样,作出了极大功绩,连他的错误也往往是有启发性的。他的学识、他接受抽象思想的能力、他的源源不断地出版的作品、他的长期担任讲座,这一切使这位图宾根教授成为他那时代的最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他没有丝毫反对崇拜偶像者的气味。魏茨泽克证明说,信仰正统派的学生无需因为听过他的演讲而不敢担任牧师的职位。他把基督教的兴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论述,让他的听众自行决定它是人性的还是神性的。鲍尔的影响又因为他周围有一群门生而有所增加;他们跟他合作,共同努力来挽救对早期教会的科学研究。然而,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不能算作他那学派的一个成员。在鲍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使徒时代的时①候,施特劳斯企图将《福音书》中传说部分与历史部分区别开,并否定基督的神性。这个挑战导致对史料的更富于批判性的考证;如果没有施特劳斯和鲍尔的影响,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研究是不会进展得这样快的。①《符类福音书》(Synoptics)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译者①参阅豪斯拉茨:《D.F.施特劳斯》,第2卷,1876—1878年,以及埃克:《D.F.斯特劳斯》,1899年。——原注\n②在堪称图宾根学派的成员中最出色的要算施韦格勒;他关于使徒后时代著作,概述了他老师的研究成果;他也夸大了彼得和保罗之间的矛盾。策勒较为谨慎,他在试作《使徒行传》之批判考证后,放弃神学而转向研究希腊哲学。希尔根菲尔德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指出《符类福音书》的日期比他老师所指出的要早,并扩大了保罗著作的目录。如果说他只能有保留地称做图宾根学派的一个成员,那么那个曾上过鲍尔课的最有①影响的神学家里奇尔显然是站在这个学派之外的。他的《早期教会的起源》写于1850年,修改于1857年,他把彼得派与保罗派之间的矛盾缩小到适当的范围。他对保罗教义的分析揭示出其中有些地方比鲍尔所承认的更密切地联系于犹太化基督教;他对彼得派长期存在这个观念的挑战也是成功的。现在一般批评的意见对保罗派《使徒书》的接受比鲍尔还多,并把《符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编写日期放到第1世纪的下半世纪几十年中。在鲍尔死后,教会史的各个部门已有极大的进步。大家承认对基督教所由产生的土壤有作出仔细研究的必要。许雷尔和博塞特、豪斯拉茨②和普夫莱德雷尔的著作重塑了基督出生的世界。早期教会所受希腊的影③响,已由哈奇作出精辟的估计。霍尔茨曼和于里奇尔在他们的《新约全书导论》里,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察恩一生辛勤地专攻教会法的历史。魏茨泽克是在图宾根大学鲍尔的接班人;他在第一流著作《使徒时代》里描写了早期基督教各团体及其分布和制度、风俗和信仰,并描绘了保罗的生动形象。关于原始教会的组织,曾引起长期的争论。①第一个重要步骤是由罗特采取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而非历史家;他唯一②的历史著作的第一部分,专门讨论教会观念;他认为教会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争论说:基督未曾创立教会;他最早的门徒重视使命多于想到组织。在耶路撒冷陷落前,只有零星分散的宗教集会:只是在众使徒死后和教义分歧开始成为威胁的时候才产生了主教制度。1892年,索姆在他的《教会法》导论里,描绘了关于教会民主起源③的最生动的图景。这个著名的来比锡法学家宣称,教会是属于精神世界的,而法律是世俗的;所以教会法是和教会的本质相对立的。天主教会断言,教皇、主教与教士的组织是神圣的;圣公会[英国国教]建立在主教制度上而长老会建立在长老制度上。然而,最早教会的职员不是传教士而是行政人员。它们是否从犹太教徒的集会或异教团体抄袭而来或与两者都无关系,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这个组织是纯属地方性的,②参阅泽勒的颂赞,见《演讲与论文》,第2卷。——原注①参阅O.里奇尔:《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第2卷,1894—1896年。——原注②博塞特著有《与犹太教对立的耶稣教》、《新约时代的犹太教》。许雷尔著有《耶稣基督时代犹太民族史》,豪斯拉茨著有《使徒保罗传》。O.普夫莱德雷尔系德国自由主义派神学家。——谭注③书名《希腊思想与习俗对基督教会的影响》(InfluenceofGreekIdeasandUsageupontheChristianChurch),1890年。——谭注①参阅尼波尔德:《里夏德·罗特》,共2卷,1873年,以及豪塞拉茨:《罗特及其朋友》,共2卷,1902年。——原注②书名《基督教会的萌芽》(DieAnf■ngederChristlichenKirche),1837年。——谭注③《教会法》,第1卷,1892年。——原注\n因为早期基督徒仅仅是基督的信徒,它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教会。“哪里有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集合在一起,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直到第2世纪中叶,诺斯替教派的威胁才导致基督教建立教会,当时,对组织的要求比信任上帝的指导还要强烈。“教会法的历史,是基督教真理不断遭受损害的历史。”于是,基督教淹没于天主教之中。从主教到教皇,只是一步之差。1870年梵蒂冈的教谕在逻辑上是跟着这项大背教而来的:就是把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与可见的教会等同起来。索姆以非凡的力量与渊博的学识来说明他关于早期基督教这个概念,但它的夸大①的地方已由哈纳克婉转地予以纠正;后者指出,组织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正如灵魂需要肉体;法律也旨在体现基督教的理想。对教条的演进的研究既热烈而又大有裨益。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所激起的许多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著作中间,多纳的《基督品位教义史》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部巨著洋溢着施莱尔马赫和尼安德的精神,并追述基督本人在各个时代支配基督徒的生活与思想的事实,因而它对于研究者还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里奇尔关于“因信称义”说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在勒南的才华横溢的著作里,第一次以通俗形式叙述了早期教会的历史。他青年时代的著作《科学的未来》写于1849年;他在这部著作中宣称,如果按照科学方法来写一部基督教起源史,那将会使思想发生革命,也将是19世纪最重要的著作。1860年他奉命前往腓尼基,使他得有机会参观圣地,并在那里制定了编写耶稣传与研究基督教起源的计划。《耶稣传》,虽然他的著作中最著名的部分,却最无价值;它关于基督的概念既不能使信徒满意也不能使非信徒满意。《使徒传》简述犹太、②罗马和基督教社会,并以巴布教派的兴起和受迫害作为例证,来说明一个新生宗教的热情。关于保罗的一卷,几乎是和《耶稣传》同样不完备的。他宣称,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完全不利的:他是神学的创始人,他把基督教从伦理转化为教条。他是一个伟大的实行家,但他既不是圣徒、学者,也不是诗人。他对宗教很少贡献,他在基督教名人等级中的①地位低于圣法兰西斯和托马斯·肯佩斯。《反基督》描述尼禄的迫害。第五、六两卷包括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统治时代并概述诺斯替教的兴起。第七卷,标题为《马尔克斯·奥里利厄斯》,是描述异教世界的,当时基督教的胜利已经在望。这整个戏剧的突出的重要性、他的广博的知识和对各种思想的同情论述、对历史性地点的生动描写和优美的文笔,这一切使这部著作立即名噪一时。鲍尔纪录的是教义的兴衰,而勒南则在舞台上展览出活生生的人物。近几十年来,我们借助考古学和铭文,已大大增加了关于早期教会的知识。在奥克塞林库斯所发现的第3世纪纸草卷页,由于包括某些被认为是耶稣的言论,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拉姆齐在小亚细亚,尤其是①《教会的宪法与法律》,附录,1910年。——原注②巴布教派(Babism)——约在1844年,由伊本·拉狄克(IbnRadhik,1820—1850年)在波斯创立的泛神论教派。——译者①圣法兰西斯(约1182—1226年),著名的意大利圣芳济修会的创立者。托马斯·肯佩斯(约1380—1471年),德国神学家神秘主义者。——谭注\n在弗里吉亚的考察,发现了若干几乎未被知道的历史事实,因而他能够对圣保罗的旅行作出新的说明,并对《罗马帝国的教会》一书提供一幅生动的图画。居蒙描写太阳神崇拜及其他和基督教相竞争的教派。莱特②富特关于克莱门、伊纳爵和波利卡普的卓越版本,阐明第二世纪的生活①与组织;格沃特金关于阿里乌教派的论著,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基督教传记辞典》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部杰出的不朽的作品。无论是活着的②或已故的,没有人在研究早期教会方面象哈那克那样做了这样多的工作。1882年后他编辑《原文与研究》并为这部著作写过无数专著,该书阐明了最初三个世纪的各个方面。他发起并指导由普鲁士科学院出版的关于尼西会议前的教父的著作。作为《神学文献报》的编辑,他纪录了研究工作的每一项进展。他关于《新约全书》的论著,虽然是他的成就中最小的,却充满锐利的分析。他的《教条史》是穿过推测的迷宫的一③个不可少的向导。他的《攸希比厄斯比以前的基督教文献》概论,是关于正确的学识与锐敏的批判的一部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他的《早期教会组织》的论著总结了两个世代的研究结果。他的《基督教的使命与扩张》试图第一次详细概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前各基督教团体在许多地方的实际成长。他宣称,基督教具有各种使人欢迎的特点——救世主与治病者的品德、慈悲的福音与纯洁的生活,以及同化外来成分的惊人力量。基督教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并为全世界正在探索的一神教提供了形式。④英国读者在半个世纪中,主要是通过米尔曼的《拉丁基督教史》知道一些关于中世纪时代的教会史。他的成名是由于一部具有特殊独立性的著作:《犹太人史》。洛克哈特写道,“它是宏伟的,但有些聪明人对于若干有关神迹的记载却不赞成。你应该写一部基督教史来消除他们的反对态度”。这位圣保罗教堂的教长依从劝告,写了一部关于早期教会的历史,其书平平无奇。然而,他后来以这篇概论作为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却可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突出的史学成就并列。他的《拉丁基督教史》从狄奥多西叙述到宗教改革前夕为止,使英国免于纽曼说它除了吉本的著作外没有什么教会史的指责。他的朋友斯坦利教长称之为“必不可少与无可估价的著作,一部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国度的完整的史诗与哲学”。弗劳德的证词同样漂亮。“你撰写了英语中最优美的历史作品。一个伟大作家必须具备的要素是:沉着与公正,相信在神所支配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信仰或政策的体系对于人类能保有持久的影响,除非其中包含的真理大于谬误;而在这些方面,你是胜过任何处理这类问题的作家的”。米尔曼并不想教诲他的读者:他是把教会作为一种机构而不是②伊纳爵,安提阿主教,为罗马皇帝图拉真投入斗兽场,以身殉教。波利卡普(69—约155年),相传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士每拿(今斯米尔纳)主教,在迫害基督教时被烧死。——谭注①阿里乌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分裂为若干支派,337年以后其中一派被认为是正教,于此时传入哥特人中间,与罗马正教互争雄长。——谭注②参阅他的女儿爱尼斯·冯·察恩-哈纳克所作的全传,1936年。——原注③攸希比厄斯(约260—340)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者。著有《编年史》,用综合年代法为基督教历史提供了统一纪年方法,还著有《教会史》、《巴勒斯坦殉道者列传》、《君士坦丁大帝本纪》等。——谭注④参阅A.米尔曼,《H.H.米尔曼的回忆录》,1900年,以及莱基,《历史论文集》,1908年。——原注\n作为一种影响来描述的。他对于行动比对于思想或感情更感兴趣,因为他的精神基本上是属于世俗的。他和斯坦利一样,对于教义的争论很少关心。教长丘奇虽承认他的力量和公正,却抱怨说,他不能恰当地认识神学所由形成的思想和感情上那些永恒问题是多么真实而深刻。可是,这个超脱态度使他避免了当时流行于新教徒历史家中间的敌视天主教的情绪;他憎恶轻信、不能容纳异己与僧侣制度,不论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毫不例外。他承认若干教皇的伟大以及寺院制度和中世纪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巨大贡献。麦考莱宣称,这部书的主旨是很好的,但它的文笔是拙劣的。的确,它既不优雅,色彩也过于单调,不过,它却是具有格罗脱的论据严肃性。莱基证明说,在认识他的人们看来,他的人品甚至比他的著作还要伟大。他补充说,“很少历史家能在更大程度上把知识丰富、立论严密与坚持真理这三项主要条件结合在一起”。关于中世纪教会的最佳著作,出现于专著方面。罗伊特写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详细传记,吕歇尔写了英诺森三世的传记。萨巴提埃写了世人期待已久的关于圣法兰西斯的引人入胜的传记。豪克一生从事概述直到中世纪结束为止的德意志教会的历史。胡克写坎特伯雷诸大主教的传记。里希特和他最大门生欣席乌斯追述了教会法的演进过程。勒南衡量①了阿维罗伊的影响;勒希勒衡量了威克利夫的挑战。没有人象亨利·查②理·利那样完成过这样多的工作;他的《中世纪异端裁判所史》被阿克顿正确地称为新教新世界对天主教旧世界宗教史之最重要的贡献;他关于僧侣独身制、西班牙宗教法庭、忏悔与赦罪券以及神裁判法的著作没有枉费心血。他的博学愈加使人惊奇,因为那是他在出版生活的余暇中获得的,而且,他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必须经过抄写从大西洋彼岸寄来的。这些巨大的专著虽然文体缺少特色,却能阐明人类经验中许多奇异的领域。1881年梵蒂冈档案的开放,还给中世纪史学者以数量浩瀚的新资料;罗马的法国学校出版了关于教皇的文件的许多宝贵卷帙。保罗·凯尔开始出版关于意大利方面的《罗马教廷的纪录》;继之而起的有布拉克曼关于德意志方面的汇编。芬克一生致力于收集为编写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史所需要的资料。①当然,新教徒对宗教改革的特别注意,决不亚于旧教徒。在研究这个冲突的新教历史家中间,没有人象梅耳·多比涅那样享有盛名;他在描写路德与加尔文时以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这个虔诚的瑞士牧师曾留恋不舍地研究过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但他的作品属于说教的文学,现在已被遗忘。更富于批判性的一代人是从克斯特林、科尔德、卡韦劳获得②关于路德的知识的。克斯特林所作传记的最新版本,提供了关于路德研究的最后定论;它的第二卷经卡韦劳修订过。后者充分注意到宗教改革家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反对者的优点,因而他比任何新教历史家更能以冷①阿维罗伊(1126—1198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大学问家。通晓天文、医学、法学,精研哲学,对亚里斯多德学说所作的解说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派。——谭注②参阅布雷德利:《H.C.利》,1931年,以及鲍姆加腾的攻击:《H.C.利的历史著作》,1909年。——原注①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作家,将于下章叙述。——原注②克斯特林著:《马丁路德传》,卡韦劳修订本,共二卷,1903年。——谭注\n静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冲突。关于伊拉斯谟与梅兰克希通的权威性的传记③尚未出现,但施特劳斯关于胡滕的赞颂和巴奇关于卡尔斯塔特的传记,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路德全集的魏玛版于1883年开始出版;宗教改革史学会也从路德诞生四百周年起,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杜梅尔格关于喀尔④文的豪华版本,为这位日内瓦宗教改革家树碑立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卡农·狄克逊与盖尔德纳从高级英国国教的立场描述了英国的宗教转变过程。卡尔·哈泽的《新教论战手册》分析了各教派间在历史、教义和道德方面的争论。最近三个世纪关于教会史的著名著作中有:多尔内尔的新教神学概论、施韦策的《新教的中心教条》的巨著、普夫莱德雷尔①的《宗教哲学史》、塔洛克关于剑桥柏拉图主义派的杂记和利茨尔关于虔信派的著作。尼波尔德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教的角度来论述从18世纪②中期起的整个领域。艾比和奥弗顿探索了从“不肯宣誓者”到改革法案为止的英国宗教史。教长丘奇写了关于牛津运动的简史,该书把稳妥可靠的判断和他个人的记忆结合了起来。关于新教研究最伟大的不朽之作,是赫佐格的《新教神学百科全书》,该书的第三版是在豪克的指导下出版的。③卡尔斯塔特(约1480—1541年),反对路德的威腾堡新教教士领袖。——谭注④杜梅尔格著《让·喀尔文传》,共七卷,1899—1927年。——谭注①剑桥柏拉图主义派是一批与剑桥大学有联系的哲学家、神学家。他们主张宗教宽容,思想自由,认为教义与真正的宗教有别,前者是外表的,后者才是发自灵魂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思想对17世纪后期宗教界和思想界颇有影响。——谭注②指英国那些在革命后拒绝宣誓效忠于新政府的牧师。(1691年)。——译者\n第二十六章天主教史学Ⅰ在新教学者完成关于教会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的同时,敌对阵营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拿破仑失败后的一个世代里,罗马教会的复兴不仅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被感觉到,同时也在社会生活里被感觉到。这①一复兴最早的中心是在南德意志,它的最早和最有才华的人物是默勒;他在鲍尔之前不久开始在图宾根大学讲授教会史。1825年《教父著作中所揭示的教会的统一》的出版,是天主教德意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凡是真能过目前教会生活的人,也能过最早时期的教会生活并能了解它;凡是不能过目前教会生活的人,就不能过古代教会的生活,也不能了解它,因为它们是完全一致的”。该书第一部分讨论教会的精神统一;第二部分讨论教会的形体统一。此书的魄力与雄辩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五十年后德林格尔对弗里德里希说道,“他使我们青年人着了迷。我们觉得,默勒发现了一个新鲜的而又充满生气的基督教。关于一个清除了弊端的教会这个理想,成了我们的目标,神学科学的复兴会同时带来教会的改革”。两年后,一部更加宏伟的著作《亚塔纳西与他时代的教会》出版,显示出这个历史家在刻划人物和分析哲学概念方面的能力。他最著名的作品《信条神学》,即关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教条分歧的研究,是自博塞特以来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攻击。它的目的,是要根据教父们的著作来证明新教对原始教会的教训是不忠实的。他的同事鲍尔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他在补编里给予答复,争论说,他的对手是根据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观点,而并非根据宗教改革者的观点进行辩论;而且仅仅是以误述新教的教义来为它辩护。默勒和鲍尔的决斗,发生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的同一时期,因而它进一步推动了对教会史和教义的研究。默勒因受到他的图宾根大学同事尖酸刻薄的攻击而深感伤心,所以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聘书。德林格尔是他最忠实的敬佩者之一,他让出教会史讲座给他,而自己担任教会法与教义讲座。但是这位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的新领域里的生涯是短促的,因为他在四十一岁时即死于肺病。天主教德意志对他的早逝所感到的悲伤,正如在古典研究的圈子里对奥特弗里德·缪勒的死亡所感到的哀悼一样。这两人好象一股春风进入尘土飞扬的学术研究领域,以饱满的热情鼓舞着青年和老人。默勒遗著的出版使世人能够甚至更充分地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遭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他关于教父学的巨著,概述起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著作;一个世代后,他关于教会史的讲稿,根据他学生的笔记出版问世。虽然他的主要力量是放在早期教会史,但是他对宗教改革运动也有丰富的知①参阅弗里德里希:《J.A.默勒》1894年;克内普弗勒:《J.A.默勒》,1896年;以及费格纳:《近代天主教的三个形式》,1927年。关于德意志天主教复兴,可从下列著作来研究:威尔纳:《天主教神学史》,1866年;弗里德里希:《梵蒂冈会议史》,第Ⅰ卷,1877年;以及戈约:《德国的宗教》,第Ⅰ—Ⅱ卷,1905年。——原注\n识。他严厉地批评路德,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巨人,把他比诸那些带来破坏的世界征服者。他享有如此巨大的威望,以致当天主教研究队伍被梵蒂冈的命令分裂后,两派都寻求他的支持。他对教廷的态度,当然是不属于教皇极权论派的;因为他曾宣称,宗教大会是教会的最高法庭也是教会的唯一合法权力机构;他对耶稣会会士的敌视也是直言不讳的。当①②耶稣会被召回到卢塞恩城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他的一个门生出版了他在1831年所发表的演讲笔记,在这些演讲中他曾把耶稣会会士与新教③徒相提并论,并宣称解散这个教派是对它的正当处罚。但是施特劳斯宣称默勒闭眼不看他教会的缺点,并且从未在那里感到很愉快,却是说得过火了。默勒的地位,是处在教会极权论派和天主教阵营之间的中道,他的朋友和门生以后也分别属于这两派。当默勒昙花一现的生涯结束以后,他作为德国天主教神学领导人的④地位即为德林格尔取代。他最早的朋友普拉滕,是维茨堡大学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怀疑派诗人。他称德林格尔是“很开明而又宽容,但还是⑤一个天主教徒”。另一个对他产生更重要影响的是巴德尔,后者引导他爱好神秘主义者。十八岁时德林格尔潜心于萨尔皮的著作,并航行于巴罗尼著作的汪洋大海上。他看出教会间的斗争必须以历史家的武器而不①能以玄学家的武器来解决。当德·梅斯特尔关于教廷的论著出现时,他冷淡他说道,它缺少历史的证明。1826年,他的第一部书出版后,他被聘任慕尼黑大学讲座,从此,他使之成为天主教世界中最有影响的讲座。他已担负起这个任务而他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引导他的船舶航行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宣称,天主教会最重要最圣洁的法规,是不接受任何并非建立在一切时代传统基础上的教条。他的演讲包括教会史的全部领②域,因而写一部手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部著作在他的笔下越来越大,以致他在叙述到宗教改革时就决定不再继续写下去。它被译为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因而使它的作者名声广播于整个天主教世界。德林格尔在发表他的《教会史》后不久,开始出版一部关于宗教改③革的更为重要的著作。在他看来,理性主义的增长与教派间的争吵似乎是宣布新教的迅速垮台。罗马和维滕堡之间共同的基督教的纽带正在松①原文Lucerne,曾译琉恩。——译者②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耶稣会徒失势,在欧洲各国先后被驱逐出境。1814年后,随着反动势力的抬头他们回到瑞士天主教占优势的卢塞恩等邦,成为导致1847年该国内战的原因之一。——谭注③参阅《杂文》,第二卷。——原注④参阅弗里德里希的大传记,共三卷,1899—1901年;阿克顿:《德林格尔的历史著作》,见《自由的历史与其他论文》1907年;施蒂韦:《论文》,1900年;科内利乌斯:《历史著作》,1899年;卢伊斯·冯·科贝尔:《多林格尔博士的谈话》,1892年;费格纳:《三种形式》,1927年。关于教皇极权论派的攻击,参阅米夏埃尔:《多林格尔》,1892年,与耶尔格:《历史—政治文选》,1890年分,第237—262页。——原注⑤巴德尔,F.X.(1765—1841年),德意志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是以罗马正教为基础而形成的,带有通神论性质。——谭注①德·梅斯特尔(1754—1821年),法国政治家,哲学家,保皇党人和教皇极权主义者。——谭注②书名《教会史手册》(Lehrbuchderkirdengeschichte),共四卷,1833—1838年。——谭注③书名《宗教改革》(DieReformation),共三卷,1846—1848年。——谭注\n解。他指出,一个研究新教神学的天主教徒,好象一个人站在海岸上瞭望在浪潮激荡中不知去向的一叶扁舟,他打定主意要证明兰克关于民族生活的描写是多么错误,新教神学是多么浅薄,路德反叛的道德和智慧的成果又是多么有害。他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关于灾祸与混乱的证据,并把它归咎于宗教改革,首先是归咎于路德所爱好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和他对“功德”的攻击。然而,这样的偏袒论证是决不能说明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的。该书在天主教德意志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在新教徒中则激起了愤怒的敌意。但是由于篇幅冗长和编排拙劣,它不可能成为受欢迎的作品。当第三卷销路不畅的时候,作者就停止了这项工作。它仍然是一部各派历史家所钻研的资料来源,一所储藏稀有珍奇学识的宝库。当时德林格尔是关于天主教研究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并在法兰克福①议会上表达了教会的要求。1851年,《驳斥异端》的发现导致关于它的作者的激烈争论。德林格尔接受把它归于希彼律图所作的说法,但他仍为教会名誉辩护。随后不久,他即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前厅》,即古代文明的概论,该书在新教徒中引起的称赞不亚于天主教徒的称赞。纽曼由于不懂德文,叫人在祈祷室内翻译它,并欣然阅读它。继后不久,德林格尔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最早时代》的论著,该书也获得保守圈子里的赞赏。这是这个伟大学者所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之后,他就走上了那条引导这个天主教的老卫士被逐出教门的道路。②除默勒与德林格尔之外,在学术界里最有声望的要数黑费累。他在二十年中研究早期教父著作、礼拜仪式和历史,并撰写一部西梅内斯传记因而赢得了盛名;随后,在1855年,他出版了他的《宗教会议史》的第一卷。在后来出版的此卷序言中,他宣称,他的愿望是要提供一部客观的巨著;的确,他的著作是他那时代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史领域内所写的最有权威的作品。他原定的计划是集中于教条方面,但他最后决定把教会法、礼拜仪式和道德都包括在内,因而这部作品对于宗教法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是有用的。“直到现在为止,宗教会议是被个别地论述的。我试图把每次会议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这部著作就变得有些象一部教会史了。它的价值迄今仍得到普遍承认。到了第五卷,叙述范围扩大成为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史;这一卷包括从希尔得布兰德到霍亨斯陶芬王朝末期的世纪,即“中世纪的最伟大的时期”。在完成康斯坦茨会议史后,他被任命为罗滕堡的主教;由于职务上的责任和缺少到大图书馆去的机会,他的研究工作发生了困难,于是他就把著作结束于佛罗伦萨和巴塞尔会议。在回顾他七大卷著作时,他重复说,他不觉得有什么偏见。“我一贯是成功的吗?有任何历史家历来是一贯成功的吗?‘有志者事竟成’”。这部著作的校订工作于1873年开始,由克内弗勒完成。①慕尼黑圈子的第四个成员,是阅历丰富的雄辩家格雷斯。因为他是①《驳斥异端》(philosophumena)系古希腊基督教作家希彼律图(Hippolytus)所作。据传说,他约于公元235年在撒丁尼亚殉道。该书的14世纪手抄本在1842年发现于希腊东北部阿索斯山(MountAthos)。——译者②参阅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与赫措格的《百科全书》。——原注①参阅泽普:《格雷斯》,1877年。——原注\n莱茵地区的产儿,他曾欢迎过法国革命,但是他后来站在反拿破仑的领导地位。他以同等毅力攻击神圣同盟,并宣称,既然各国君主一致反对自由,人民就须仰仗罗马。他以天主教的热情拥护者的身分,接受慕尼黑大学的历史讲座,但他的思想不适于从事系统研究工作。他主要的历史工作,是广泛论述基督教神秘主义。他评述早期圣徒与教父,接受圣②安东尼的奇迹,并追述各时代中的异象和使人心醉神迷的事物。这部著作的后半部专述恶魔——魔鬼作崇、巫术和魔术。格雷斯的名字和声誊促使慕尼黑成为天主教德意志的首都,但是却没有增加它的学术声望。这个圈子由于有一个来自北方的热心改宗者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加①强。乔治·菲利普斯的父母是住在柯尼斯堡的英国人。他跟从萨维尼和艾希霍恩学习,1827年在柏林大学开始讲授法律。次年,他加入罗马教会,不久就接受慕尼黑大学的聘请。1845年,他开始出版关于教会法的巨著,并终生致力于这一工作。他把一切好事都归之于教廷,他相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贯正确绝对无误的,而且处于世界上的至尊无上的地位;所以,他的著作是教皇极权论派的宣言书。1848年,他移居奥地利。他的著作在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那在1870年达到高潮的运动的一个主要源泉。1838年时慕尼黑圈子感到已有足够力量来创办一份杂志。原有的《图宾根季刊》是代表学术研究的,默勒和黑费累是该刊经常的撰稿人;而现在创立的《历史政治杂志》则要在各个领域捍卫天主教会。这个学派的次要成员中,还可举出雅尔克、赫夫勒和拉沙尔克斯。第一个人,是菲利普斯在柏林大学的至交和共同改宗者并伴随他到南德。赫夫勒是一个十分认真的历史学家,是德林格尔的门生。他以一部关于德意志人教皇的历史而成名;1851年他被召唤到布拉格对②帕拉茨基及胡司的拥护者进行论争。拉沙尔克斯对历史研究并不比格雷斯更有才能。当他把他的《希腊化时代的衰亡》读给德林格尔听时,这个大学者为其中日期和资料的混乱而不胜震惊,他的讲演也同样是毫无条理的。可是,所有这些学者都有助于使慕尼黑大学成为天主教学术研究中心,而且教会的未来拥护者,包括克特勒与穆方在内,都来到这个学府以求得到培养。天主教的复兴在南德意志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但在法国也有一个相应的运动。当夏多布里昂使基督教成为时尚时,响应他的呼声迅即兴起。博纳尔要求恢复耶稣会;德·梅斯特尔为承认教皇辩护,认为它是欧洲的依靠;拉梅内攻击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运动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后者与罗马决裂后退出了战线,但是青年人包括他的若干门生在内,又挺身而出。那为天主教学校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教皇对《未来》杂志的谴责,①曾使蒙塔朗贝尔的名字在他三十岁以前就已传遍法国全境。由于失望,②圣安东尼(约251—约350年),埃及隐士,基督教寺院的首创者。曾隐居山中十余年,自称经历了魔鬼多方诱惑与威胁的考验。——谭注①参阅许尔特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②参阅斯特尔兹尔:《沙拉尔克斯》,1904年。——原注①参阅下列作家所写的传记:奥利芬特夫人,1872年,富瓦塞,1877年,以及勒卡尼埃,三卷,1900—1902年。——原注\n②他把目光转向中世纪时代。他在德意志旅行,于圣·以利沙伯节到达马尔堡,但他发现她已被遗忘,连她的圣像路德教徒也不去理睬。他追寻她足迹所曾到达过的地方,并撰写了她的传记。“我对于毁坏了的机构倒没有什么惋惜,但是我深深地痛惜那曾经使它们生气勃勃的神圣精神的丧失。过去人人都懂得他应该信仰什么,他能够知道什么,他应该怎样看待所有那些有关生活与命运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正是苦恼的根源。当时有一种非常健全的道德,是以抵销社会机体的弊病。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要求离开它现在所陷入的凄凉的荒野,它将请求再听听它婴儿时代的歌声,再把它饥渴的嘴唇凑到母亲的胸怀。而那个母亲会比以往更加美丽、更加有力、更加慈悲”。这篇传记,是训世的著作而非科学的著作,但它给天主教复兴以推动力。它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①它有助于促使那无与伦比的斗士路易·弗约的改宗。还有一部更加宏伟的著作,即《西方僧侣的历史》。蒙塔朗贝尔的初衷是要撰写圣贝尔纳的全传,但他写了导论以后,终于改变计划而写一部综合性的寺院制度史。提出“我们是十字军的后裔;我们决不会向伏尔泰的子孙投降”这一著名的战斗口号的作者,当然不是一个客观地进行研究的人;他也坦白地声称,这部著作是“一部天主教书”。他宣称,中世纪时代已遭到荒谬的污蔑。“急切要求学习和工作的愿望当时鼓舞着每个有才智的人”。该书以一幅关于垂死的罗马帝国的暗淡图景作为开始。他宣称,文明是由于蛮族和僧侣的共同努力而得到拯救的。在略谈沙漠隐士后,他即描述本尼狄克,这是他所描绘的形象中第一个有威仪的人物。他的叙述在关于爱尔兰传教士的几卷里达到了最高峰。虽然他为他们的勇敢而欢呼,但并未打算把他们描绘成毫无瑕疵的人。②高隆班与科伦巴两人都是完全合乎人情的,不过科伦巴与其说是一个和③平使者,倒不如说是一个战士更恰当得多。他同样注意到威尔弗里德的缺点;对于他的经历他也恋恋不舍地加以追述。他追述了希尔德布兰德从寺院到教皇宝座的历程,并热烈地支持他同皇帝的生死搏斗。在他即将着手描写贝尔纳的伟大形象时,这项工作由于他的去世而中断。这位著名演说家,在讲坛上比在书室内更为从容自如;他对于资料的使用,①是完全不加批判的。奥萨南是一个较严肃的研究者,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但丁与天主教哲学》的研究。1844年,他在巴黎大学接受替福里尔担任外国文学教授;在他短暂的余生中,他写出了大量精彩的作品。他的《日耳曼研究》和关于第5世纪文明的概论,略述了中世纪的开始时②圣·以利沙伯,犹太祭司撤迦利亚之妻,施洗者约翰之母,参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一章。——谭注①路易·弗约(1813—1883年),法国政论家,原奉新教,1833年在罗马皈依天主教,成为教皇极权派。——谭注②高隆班(Columbanus)爱尔兰教士。6世纪末在欧洲传教,建立了许多据点。科伦巴,爱尔兰僧,是集战士、政治家、传教士于一身的人物。约533年在爱尔兰创建寺院制度,约565年来苏格兰西部传教,感化匹克特王奉教。——谭注③威尔弗里德,英国贵族,大主教。在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站在罗马一边。665年以来任约克大主教,多次被放逐。——谭注①参阅奥米拉(O’Meara),《奥萨南》,1878年。——原注\n期。他的《法兰西斯派诗人》,对于教会史和文学史都有所贡献。1853年,他四十岁时死于肺病,长使后人追念他高雅的人品和罕见的学术造诣。他对中世纪时代的热爱和蒙塔朗贝尔相等,但是他能摆脱那使他这位朋友的著作往往遭受损害的过分热情的影响。他的主要工作,是强调指出基督教对未开化的民族的功绩。吉本曾认为教会是古文化的破坏者之一,但是奥萨南却宣称它是从罗马文明到近代世界的桥梁。②阿尔贝·德布罗利精心创作的《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帝国》极为重要。他后来以他关于路易十五的外交纪录以及他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活动而赢得了全欧的声誉。关于教会从来没有人写过更有说服力的申辩书。他在承认“对天主教会的事业抱有深刻虔诚”的同时,把教会描绘成人类的贤明而又慈爱的母亲。在她遭受异教帝国的无情迫害后,她原可进行报复,但是她宁愿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愿使用武力。她把十字架标志树立在罗马文明上,并通过教义的道德影响来转化整个社会,因而拯救了古代世界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她深信:人类的缺点从来不能危害她教义的纯洁性。所以布罗利能很自由地论断剧中的演员。在舞台①上站着三个伟大的统治者:君士坦丁、朱里安和狄奥多西,但三个非凡②的教士阿塔纳修斯、巴西勒和安布罗斯却占据了舞台。他承认君士坦丁③④⑤的罪行、优西比乌斯的卑鄙和朱里安的德行,但他从来不容许我们忘记教会拯救了世界。书中浸润着下列思想:法国象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改变信仰。法国既然没有堕落也没有信奉异教,但是它已经和教会疏远;因而促使它重新投入教会怀抱,是一个善良爱国者的行为,也是一个善良天主教徒的行为。⑥克雷蒂诺-若利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学派;他选择较近时期的论题来撰写著作。他的令人钦佩的传记作者坦白承认,对他来说,历史不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对象,而是一种武器。他本人是旺代人,他的《军事的旺代》是一部历史,同样也是一篇论战文。他的朋友兼庇护人格列高里十六世喜欢该书,建议他应成为关于耶稣会会士的编年史家。难道他们不是教会的旺代人吗?他响应了这个要求,并很快写出一部多卷集的历史。耶稣会会士帮助这项工作,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不属于这个教派的人所提供的证明,将给公众以深刻的印象。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他接受耶稣会会士的邀请,撰写关于他们遭受取缔的历史。因为该书激烈攻击克莱门特十四世,它在教皇国内被禁止出售;梵蒂冈的档案家泰勒并发表了一篇答辩。克雷蒂诺-若利在晚年潜心论述教会和法国革命之间的斗争。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家,是一个近似于路易·弗约甚②参阅法尼埃:《布罗利公爵》,1902年。——原注①狄奥多西(345—395年),罗马皇帝,支持阿塔纳西教派,引起罗马教会的强烈反抗。——谭注②巴西勒(约329—379年),即圣大巴西勒,该撒利亚主教,以积极反对阿里乌教派闻名。圣·安布罗斯(约340—397年),米兰主教,毕生以维护正教,抨击异端为己任。——谭注③君士坦丁,以所谋叛罪先后将其岳父与长子处死,喜怒无常,嗜杀成性。——谭注④优西比乌斯,世传其在宗教迫害时,因有背教言行而获免,综其一生对正统教义怀有二心,不够坚定。——谭注⑤似指其宗教宽容政策而言。——谭注⑥参阅梅纳尔神父:《克雷蒂诺-若利》与德律费尔,见《历史杂志》,第LⅡ卷。——原注\n于近似蒙塔朗贝尔或奥萨南的人,但是由于他能使用文献,使他的著作获得了一定的重要地位。当这些作家在喜欢争论又有文化的广大读书界中广为流传的同时,公众不大知道的学者们正进行一种不很受欢迎的工作。盖朗热决心恢复法国本尼狄克派在大革命前所占有的地位,他买下了从1802年以来即已荒废的本尼狄克派的索列姆寺院。他写的关于早期教会和宗教仪式史的著作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但是这所寺院最出色的人物,是他的门生①和同事皮特拉;他在许多档案库中所做的研究工作使他获得了一顶红衣②主教帽子的酬报。米涅在写作他的史诗般的著作《希腊与拉丁的教父学》时,曾获得索列姆寺院学者们的宝贵帮助。勒·布朗出版的《基督教高卢铭文集》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他宣称,孤立地研究一个铭文时没有多大意义;集合在一起研究,就揭示出他们祖先的信仰■希望和秘密。他的目的,是要为一般信徒做本尼狄派的《基督教高卢》为神职人员做过的事情。1893年这位年迈的学者还出版了一本论“迫害”的作品,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工作,并为有批判地认识早期殉道者打下了基础。①在意大利,德·罗西对教会史作出了无法估计的贡献;他最早系统地考察了罗马城陵寝内的宝藏。“永恒之城”奇异的地下世界,在16世纪曾被重新发现过并在17世纪由博西奥描写过;后者被他的这个伟大后继者称赞为基督教考古学上的哥伦布。德·罗西引起了庇护九世的注意;后者供给他发掘的经费。1852年他在圣卡利斯塔寺院的陵寝内发现了第3世纪若干教皇的墓;这件事轰动了全世界;在他后来的四十年生涯中,一次胜利接着另一次胜利。1861年,他开始出版《罗马基督教铭文集》;在他逝世时,这部著作几乎已告完成。但是德·罗西最大的成绩是附有精美插图的《地下罗马城》分为四开本三大册,出版于1846到1877年间;它描述陵寝的历史、地形、建筑和壁画。在他的其余贡献中有:创立《基督教考古学通报》季刊,设立拉特蓝博物馆以及关于罗马教堂中镶嵌工艺的详尽研究。他在编辑铭文集的工作中曾与蒙森合作,后者强调指出这个基督教考古学和铭文学的创立人得以成为当时伟大人物之一的各种条件——他关于基督教和古典文学的知识,他对古文书法和铭文的精通,以及他对罗马帝国和古典时期与中世纪城市的深切了解。Ⅱ天主教徒只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为历史研究的复兴而自己庆幸。在50年代已有些关于风暴来临时的隆隆响声,在60年代就出现了一次自相残杀的斗争。1870年,梵蒂冈教谕体现了教皇极权论派的胜利,并把老天主教派驱入荒野。这些大事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德林格尔和梵蒂冈决裂后,教皇极权论圈子里流行着他原来就是一个异端的说法,虽然他仍然被看作自称为天主教的拥护者。然而,在①参阅卡布罗尔:《红衣主教皮特拉》,1893年。——原注②此米涅系法国天主教教士。——译者①参阅鲍姆加登,《G.B.德·罗西》,1892年;吉罗,见《历史评论》,笔LVIII卷;蒙森,见《演说与论文》,1905年。——原注\n他1861年的著名演讲之前,还没有决裂的公开迹象;在这些演讲里,他宣称,教皇世俗权的失误和堕落不是不可能的,但也不会是致命的。同一年,他撰作《天主教会与诸教会》,打算把它作为天主教的自辩书,这部书是他演讲的扩充和说明。庇护九世宣称,虽然他不能同意它的全部论点,但它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可是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表明:他已抱有一种不同的精神;他的演讲所引起的怀疑,又由于他的《中世纪时代的教皇传说》这一引人注目的著作而被证实。他尖锐地攻击1864年①《要目》,1867年他对特兰托宗教会议在世界范围的代表性提出了挑战,理由是它是受罗马控制的并且为意大利主教们所把持。1868年,他写道,“如果我的老友默勒和格雷斯在世而能看到这个时代,他们会怎样说呢?他们会对教皇极权论者说,‘滚出去,我们跟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当梵蒂冈会议召开并宣告它的目的时,德林格尔用雅努斯笔名写了他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一本:《教皇与宗教会议》;该书是为反对教皇极权论所曾提出过的最强烈的历史性控诉。它虽被列入《禁书目录》,但却传诵于全世界,并且在会议召开之前已动员舆论来反对“教皇无谬”论。在会议开会期间,他在《通报》上发表他的《基林努文件》来保持蔓延着的火势;这些文件,是根据阿克顿、弗里德里希和斯特罗斯梅耶从罗马送来的消息编写的。在教皇极权论派胜利之后,这个历史家就被逐出教会而“老天主教派”教会也创立了起来(他从未参加过这个教派)。在他《论重新联合的演讲》和他对慕尼黑科学院的演说中,他的熔炉里飞出了珍贵的火星。但是虽然他以毫不减退的精力工作到九十高龄时逝①世为止,如果没有罗伊施的帮助,他那渊博的知识也很难传给世人;罗伊施曾帮助他准备出版他关于中世纪教派的早期研究著作,刊印贝拉敏的《自传》,以及撰写关于罗马教会在17、18世纪时期在精神上的争论的详细概述。一群年青学者把德林格尔尊为领导人;他们同情他对梵蒂冈教谕的敌视态度。其中罗伊施,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人;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毫不踌躇地追随他年迈的教师。回答是,“你谈信念谈得太多了”。“我一向尊重你;你唯一的过错,是你太多想到科学而太少想到权威”。他积极参加创立老天主教会的活动以后,由于僧侣独身制的取消而退出。②在编写完莱昂的路易斯案件(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著名案件之一)的专著之后,他对伽利略的审判作了深入分析。但是他的声誊之所以能够持久,①是由于他关于《禁书目录》的巨著。它的二千多页的篇幅广泛地阐明了最近三百年的时期,深刻地刻绘了罗马(教廷)蒙昧主义的形象。虽然罗伊斯的特长在于资料收集而不在文学艺术,这部著作也许是老天主教派在学术研究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同德林格尔联系得甚至更亲密的,是他的门生、同事和传记作者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曾伴随红衣主教霍恩洛厄作为他的神学顾问,参①纲领(Syllabus)——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公布当代最大的谬论八十条,称为“要目”。——译者①参阅戈茨,《F.H.罗伊施》,1901年。——原注②莱昂的路易斯(1527—1591年),西班牙著作家、神学家。1544年加入奥古斯①书名《禁书目录》(IndexderVerbotnenBücber),共二卷,1883—1885年。——谭注\n加梵蒂冈会议。他出版了他在罗马所写的关于几个多事月份的日记,编辑了正式文件,然后进而撰写这次会议的历史。它长篇的导论卷综述教皇极权论的来龙去脉;尽管有明显的偏见,却具有持久的价值。在他的老师死后,他写了一部纪念传记,该书既证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是对19世纪教会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在这圈子内的其他成员中间,再没有人比约翰内斯·休伯更有价值了。虽然他从未撰写过大部头的著作,但他关于教会史的知识是渊博的;他帮助他的老师撰写《教皇与宗教会议》的工作。当“教皇无谬”论正式宣布后,他继续写他关于耶稣会的著作。他把这部书题词献给德林格尔。后者同罗伊斯、弗里德里希和阿克顿一起在这项工作中帮助过他。他说明,自从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这个教派以来刚刚历时百年;但它已死灰复燃;现在自由丁派修士团,并执教于萨拉曼加大学讲授神学。1572年因异端分子嫌疑,被宗教法庭判处囚禁。——谭注与文化又有受到它完全掌握的威胁。同样地由于友谊和共同原则而同德林格尔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科内①利乌斯;他在1855年关于闵斯德的再洗礼派的论著而成名。次年,他和西贝尔一起被聘到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在他的门生中间默默无闻地工作到1903年去世,他只不过编写了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在这圈子内年轻的成员中间,还有洛森和德鲁费尔;后者的早逝是对自由天主教派学②术研究事业的一个打击。洛森的专著《科伦之战》,是探索反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插曲;他作为慕尼黑科学院秘书,还帮助德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学术讲稿。德鲁费尔为写反宗教改革和特兰托会议史,进行了资料搜集工作。为了完成我们关于老天主教派学术研究的概述,还有三个名字必须提出。格拉茨大学法学教授马森,出版了关于教会法的资料和著作的第一卷;这一著作虽然没有完成,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不朽作品。朗根的大部头著作《教会史》叙述到英诺森三世为止,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出于一个老天主教派手笔的关于中世纪时代的唯一详细论著。最后还有舒尔特,他出版关于教会法资料的详史,并编辑出关于老天主教派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载。在德林格尔、罗伊斯、舒尔特以及他们的绝大多数朋友拒绝梵蒂冈教谕的时候,其他几乎同样知名的学者却接受了它们。黑费累的屈服虽然很勉强,却使他的朋友感到惊讶。教谕的最积极捍卫者是赫根勒特尔;当“雅努斯”[德林格尔的笔名]正在以突击方式鼓动舆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表答辩;他宣称:教皇极权论的世系比德林格尔所愿意承认的更为长久。他在晚年致力于续编黑费累关于宗教会议史的杰作。他的著作包括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以使用梵蒂冈图书馆内的文献而获得价值;他被任命为该图书馆的总监。为了他的功绩,他被赐给一顶红衣主教帽。①在欢迎新的教皇极权论的历史家中间,最有影响的是扬森。他出生①参阅弗里德里希,《关于科内利乌斯的演说》,1904年。——原注②1688年春,路易十四支持一名亲法的红衣主教竞选科伦教区大主教,以教皇和皇帝的反对而失败。于是法军进驻该市,给帝国、荷兰及新教事业造成严重威胁。荷、德、西、瑞典乃组成奥格斯堡同盟以抗法国。——谭注①参阅帕施托尔,《约翰内斯·扬森》,1894年。——原注\n于莱茵地区,在浓厚强烈的天主教气氛中成长起来;他的母亲还带领他朝谒圣地。他不相信那建造了哥特式大教堂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期。1854年,他二十五岁时被法兰克福高等学校聘为天主教学生的历史教授,他有生之年都在这个帝国首都度过。对他的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是博默,此人虽然名义上不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气息十足。博默停留在查理大帝雕像前时说,“这表明我们所缺少的是什么——一部出于天主教历史家手笔的德意志人民史;因为据我们所知,所谓德意志史是一出滑稽戏”。这些话决定了这个年轻教士的职业,而《德意志人民史》就在他的心里形成起来。在安定下来专心致志于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之前,他写了博默的传记,收集他的信札并编辑法兰克福帝国会议代表的报告。博默曾提示写一部德意志人民的通史,但是杨森决定从中世纪时代末期开始。1874年他把第一章读给帕施特尔听,后者说,“它是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作者回答道,他完全具有同感。1875年,第一卷的前半部问世,受到天主教世界的热烈欢迎。1891年他去世时,已写到三十年战争的前夕。人们爱不释手地阅读这部八大卷的著作。在19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巨著中,再没有获得过这样巨大的成功,或者引起过这样多的争论的著作。德林格尔曾着重指出路德新教运动所引起的混乱状况,但是新教历史家对他的结论置诸不理。扬森更向后追溯;他以详细研究15世纪作为他研究宗教改革的前导。他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个时代(即宗教改革时代)不是一个道德或智慧衰败只有少数“宗教改革前的改革家”发出象在荒野里呼喊的声音的时代,而是一个有着健康活动的繁荣的时代。他描述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欣欣向荣的状况,并宣称,在路德之前至少已有十五种《圣经》全译本。艺术富有活力和创造性。他的著作在纠正新教传统的说法方面的价值得到普遍承认的。在第一卷的后半部里,他讲述农业、工业和贸易,并指出农民的安适生活和城市的繁荣景象。在画面上第一次出现了阴影——财富导致奢侈和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垄断、重利盘剥的可怖情况。祸害又由于罗马法的复兴而加剧,因为它的经济学说是违反基督教原则的。十分奇怪,他未曾描述宗教状况;扬森的辩解理由是:他不是在写教会史;路德的革命是属于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而不是属于教会或智慧方面的。第一卷在新旧教会都找到了赞赏者,第二卷包括宗教改革的早期,当然在新教圈子内就不大受欢迎了。德林格尔追述教义的发展;兰克叙述政治史;扬森则不然: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他对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几乎是粗暴的控诉。他宣称,伊拉斯谟怀疑、轻浮、自私;较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是异教徒而非基督教徒,而且其中有些人品性不良。最坏的是胡滕。扬森对路德本人不多作评论,他也避免咒骂,但是他描绘出一幅在宗教冲突发生时物质和道德方面可怕的混乱图景。虽然他没有把农民暴动完全归因于宗教改革,他却主要从这个原因来追溯这次叛乱的残暴行为。第三卷,叙述到查理五世退位为止,本卷对待剧中的新教徒虽然很严厉,可是对天主教徒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他承认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弊端;并尖锐地指责德意志主教是带着宗教头衔的世俗王公。后面诸卷,论述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前的世代。这是一幅漆黑一团的画面——道德败坏与酗酒、愚昧、残暴和迷信。\n他用几百页篇幅来叙述通俗文学,用几百页来叙述那些使国家蒙受耻辱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还用半卷篇幅来叙述蔓延于全部居民中间的对巫术迷信。这样看来,该书是以15世纪的鲜明色彩开篇,而以深暗的阴影作为终篇的。它的要旨是:德意志不是毁于三十年战争而是毁于宗教改革。扬森的博学确是值得注意,他那独出心裁的方法和结论也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天主教徒终于能有这个历史家而自豪,因为他可以和新教学者平起平坐。他的著作的重要地位,由于他激起了攻击而更加突出。鲍姆加滕(即查理五世传记的作者)、卡威劳和克斯特林、科尔德和伦茨(即路德传记的作者)群起猛攻这个狂妄的反对崇拜偶像者。德尔布吕克宣布,他是一个以伪乱真者,并指斥他的著作是一个大骗局。扬森连续写了两卷著作来答复他的批评者:他虽然接受若干小的纠正,却指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现在,争论的尘雾已经澄清,我们不难估计该书的特点。第一,它确实增加了我们关于德意志人民生活的知识。第二,它修正了新教徒关于15世纪是一个堕落与混乱的时代的传统看法。第三,它证实了德林格尔的论点:路德运动带来了大混乱和文化与繁荣的暂时衰退。泰纳说得对,没有人在将来谈论宗教改革时,能不去钻研并衡量天主教方面的论点和看法。另一方面,扬森不能算作第一流历史家。他虽以“让史料说话”而自豪,但却堆砌一切有损于新教的引文而不提很多不利于旧教的事实,这一作法产生了使人误解的结果。他报道真实,但不是全部的真实。他使用资料常常不加批判。他把可靠的和不可靠的资料堆在一起,往往把孤立的特殊事件用作重要概括的根据。一句话,这部书的甚至经过帕施特尔修订的版本,也还是一部手法巧妙的论战之作,而不是一部公正无私的研究结晶。继梵蒂冈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在教皇极权论派历史家中间,第二个著名的历史家是帕施特尔,他是杨森传记的作者和研究文艺复兴时期①诸教皇的历史家。他的目的是要描写16世纪重大的宗教斗争怎样反映在教廷史上,正象扬森描写这场斗争怎样反映在德意志人民生活上一样。兰克和克赖顿都未能使用梵蒂冈档案。帕施特尔在这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他的大部分资料,还从拉特兰大教堂、异端裁判所和宣传机构的档案库、王公贵族的藏书室,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中进行探索,加以补充。扬森很少使用未刊印的资料,而帕施特尔却宁愿采用手稿中的证词。虽然他宣称,为教皇所作的最好的申辩就是出示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但他也不是全无保留地称赞某些教会王公。他的早期诸卷描写“新学”时期,它的影响在梵蒂冈是深深地感觉到的。他对艺术和文化深感兴趣,因而详细论述庇护二世的人文主义、他的继承人的艺术活动,以及教廷中举世闻名的绘画家、雕刻家和①建筑师。他区别异教和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区别瓦拉和波基奥的一方与②尼古拉五世和维托里诺的另一方。他承认,这些教皇欢迎所有的人文主①参阅巨著:《帕施特尔,日记、通讯、回忆》,1950年。——原注①波基奥,B.G.F.(1380—1459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并以搜集和发现古罗马文献知名。——谭注②维托里诺,daFettre,真名VittorinoRamboldinic(1378—144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谭注\n义者,而不考虑他们的异教信仰,因为教皇本身也是世俗王公而对异教文艺复兴的唯一强烈的攻击则来自萨沃纳罗拉方面。他以利奥一世的名言作为掩护:“彼得的圣职有时会落到不合适的继承者身上”。他哀叹教皇选举中的贿赂和阴谋。在第三卷,即叙述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③二世的一卷里,他在态度上不如克赖顿那样宽大。第一次使用《博尔吉④亚家族记录》时,他宣称,这些文献使之不可能为[亚历山大六世]辩护。可是,他宣布教皇是当时最好的世俗君主,把他的罪行归咎于他姑息自己的家族;并称赞他注意保持对教会教义的纯洁性。他承认尤利乌⑤斯的性格是不配做教皇的,但暗示在一个暴力时代,一个好战的教廷卫⑥士也许是必要的。他责备利奥十世所结交的朋友和克莱门特七世在德意⑦志和英国所推行的政策。他哀叹教会在它命运攸关的时刻缺少主张改革①的教皇,他也不想掩饰保罗三世的过失。帕施特尔的著作是极其勤奋地进行研究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新资料,但是他也不是属于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关于文化复兴的双重性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督教成分和异教成分是这样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必须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按照他的观点和信仰,他是不会同情于一个首先是反对“信仰时代”的运动的。他从未认真正视这一事实:宗教会议运动和德意志人的反叛都是由于根深蒂固而又生死攸关的信念而产生出来的。他用世俗性和社会的道德堕落来解释教皇的缺点,但是他从未想到,教会本身的腐化却正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他对待萨沃纳罗拉很严厉,把他的所作所为比诸救世军,谴责他不服从罗马和参与政治活动。他对教会堕落的指责非但不比对世俗的指责更严厉,反而暗示种种可以原谅的理由,对它的责备只是轻描淡写。他的著作尽管语调温和,但受到基本偏见的损害。象其他天主教历史学家一样,他未能使人真正理解宗教改革运动。②属于奥地利多明我会的德尼弗尔是一个更有影响的人物。他最早的重要著作是叙述德意志的神秘派。和新教传统相反,他认定神秘主义是以经院成长出来的,神秘派决不是反僧侣派,也不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在被他的教派召唤到罗马后,他被利奥十三世请去帮助编辑阿奎纳著作的正式版本,因为1879年的教皇敕谕提出对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应进行特别研究。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他访问了欧洲各地的档案馆,他收集资料③尤利乌斯二世,罗马教皇,1503—1513年在位,被认为是教皇国真正的创建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皇之一。——谭注④亚历山大六世原名为罗德里戈·博尔吉亚(RodrigoBorgia1431—1503年)。——译者⑤指尤利乌斯二世。他任主教时以教区收入营造宫室,任教皇后扶植人文主义文学艺术,怠于教务。——谭注⑥利奥第十,出身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生活方式及趣味深受文艺复兴思想熏陶,厌恶清修生活,任教皇后,广交文艺名流,罗马成了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谭注⑦指克莱门特七世联合法国、威尼斯、米兰反对皇帝查理五世,及拒绝英国亨利八世离婚申请等事。——谭注①保罗三世在位期间(1534—1559年),将英国亨利八世驱逐出教,支持耶稣会的创立,在罗马设立宗教异端裁判所,依靠耶稣会操纵特兰托宗教大会。——谭注②参阅格拉布曼,《海恩里希·德尼弗尔》,1905年。——原注\n不仅是为了这部著作,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计划。在被任命为梵蒂冈档案馆馆长后,他看到有关中世纪大学的资料是如此丰富,于是着手撰写它①们的历史。第一卷于1885年出版;它是关于大学的辩解,并附带地为教会和中世纪时代辩解,但也是一个关于知识的庞大的提纲。他原计划写五卷,但大半由于第一卷的成功,后面几卷他就难以为继了。最显著的赞扬来自巴黎,法国政府邀请他编辑巴黎大学的文献史。他接受了这项工作,在十年期间出版了六卷文献。由于原始稿件的发现,大量伪造和窜改的文件被一扫而空。这项著作也是对法国史的一个贡献,它对法国朝廷和教会同教廷的关系,对各个教派、对亚理斯多德学说的接受以及对中世纪神学,都作了说明。在这样地从事工作的时候,这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偷闲写了一部附有文献的作品:《十四、十五世纪法国教会的瓦解》;该书是关于艺术和宗教仪式、圣徒和圣物、教会财产和组织的资料的源泉。象所有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部著作也是未完成的,因为他对15世纪的研究使他的思想转到了路德方面。德尼弗尔的《路德与路德教》于1904年出版,证明他在梵蒂冈和德意志档案库曾作过深刻的研究。他说由于新教历史家对天主教会的恶毒攻击和他们对路德的盲目的偶像崇拜,他不得不写这部著作。他痛心地宣称,新教神学家被容许怀疑基督的神性,但对于这个宗教改革家却不得有任何触犯之处。路德和他的朋友们为了道德的原因而丧失了他们的信仰。谁能如实地了解路德,就可以了解他的反叛。“本书不是打算为年轻人写的。真正的路德就是这样!”他在结束一篇愤激的序言时说,“愿上帝使新教徒睁眼看看他[路德]的品质,并指引他们回到天主教会来”。这部长达八百页的厚书,竭力损害这个宗教改革家的遗名,这是最令人厌恶的历史著作之一。他宣称,宗教改革家们是肉欲的使徒;他们的哲学总结成一句格言,就是“顺应自然”,而路德本人就是一个肉欲最强烈的人。不是因为他太好而不能留在教会里面,相反,是教会太好而不能容留他,因为他是被一种粗俗、淫荡的本性支配的。该书的①一大部分是用在分析路德关于“僧尼誓约”的论著,路德在其中宣布自然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而教士的结婚,引用德尼弗尔的轻蔑的话来说,被鼓吹为破坏誓约的疗法。德尼弗尔还告诉我们路德嗜酒;在关于他的相貌的一章里,他还强调有书面根据的诛语。这部著作象一颗炸弹投入了路德派的阵营。这场攻击比杨森的攻击更加集中;德尼弗尔还对路德派专家表示轻蔑。他宣称,“他们的原始罪孽是:他们是不科学的。要是他们对待路德象对待基督那样该多好啊!”他指出他们所编路德著作的魏玛版本中的错误,来在编辑技术上给他们一个教训。这项猛烈的攻击引起了无数的答辩和反击,尤其是来自哈纳克、泽贝格和科尔德的答复。他们逐一指出他们的错误,指出他删略有利于路德证据,忽视新旧教标准的比较。豪斯拉茨于1904年出版了路德传记,他宣称,德弗尔故意曲解了辞句,对戏言和悲叹语也太拘泥于文字。路德的讲话远比他的行动激烈,他的粗暴言论原是要鼓动他①书名《中世纪文学的兴起至1400年》(DieEntstehungderunioersitatendesMittelalters)。——谭注①路德在瓦德堡期间写有《论僧尼誓约》一文,指出天主教会因纪律废弛,乃借誓约以挽回颓风。文中鼓励僧尼诸众,走出庵堂,自行婚配。——谭注\n的同胞的唯一方法。他是用英雄的模型铸成的;用迈科尼厄斯的话来说,他是“上帝的奇人”他是一个天才,有一颗赤子之心。德尼弗尔在针对①哈纳克和泽贝格的一本小册子里作了答复;然后在他旅行德、法、英三国搜集关于圣保罗的手稿评注之后,很快写成一卷关于路德时期论述“因信称义”的著作。在他的发现中,有路德本人早期所作的《罗马书》评注。天主教历史家追随杨森和德尼弗尔的领导,特别注意德意志的宗教②改革。帕施特尔发起出版一套有用的专著丛书,称为《杨森历史的例解》。一个改宗者埃尔维斯很详细地探索了路德的一生;格里萨以大规模著作来叙述他的人格和他思想的发展。一个“文化斗争”运动中的斗士马容克认为,路德曾经自杀;这一传奇最后由尼古拉斯·保罗斯揭穿。加斯基特叙述英国寺院的解散;埃塞斯根据梵蒂冈档案对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作了新解释。杜尔大力为耶稣会会士作出辩护。他从“几千种③传说”里精选出几种,来论述克莱门特十四世的中毒案、“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暗杀暴君、蒙昧主义、爱国心的缺乏、贪婪与财富,以及三十年战争的责任等各种问题。他作出结论说,耶稣会会士虽然未能免除人类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却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希尔格斯为《禁书目录》辩护。美因茨的主教布吕克叙述19世纪德意志教会的命运;威尔弗里德·沃德在他为怀斯曼、纽曼和他父亲W.G.沃德所作的传记里,描述教会在英国的复兴运动。格雷斯学会成立于1876年,它创办历史评论杂志,在罗马创办一所研究院及其自己的机关报,并出版关于特兰托宗教会议的资料。在重要性上稍次的是马利亚-拉克的耶稣会士进行的活动。在1864年《要目》发表后,它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马利亚-拉克的呼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后《马利亚-拉克的呼声》发展成为定期刊物。韦策尔和韦尔特的百科全书修订版衡量了从19世纪中叶它出现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比利时的耶稣会会士在德·斯梅和德勒阿耶领导下继续撰写《圣徒传》,现在已写到“十一月份”。本尼狄克派有自己的评论杂志;它的内容由于唐·莫林的渊博论著而更加丰富。法恩巴勒的修道院长唐·卡布罗尔已着手编写《基督教考古学辞典》这一巨著。格里萨和姆格尔·曼已开始撰写广泛论述中世纪教皇的生平。还有少数历史家站在教皇极权论派和老天主教派的中间;他们虽未公开反抗,但不赞同最近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有克劳斯和迪歇纳。克劳斯在波恩大学研究过语言学,在那里他开始和罗伊施结成终身友谊①。刚过三十岁时,他出版了《教会史手册》;这本手册替代了阿尔措格的教会史简编,后者是克劳斯在弗赖堡的导师。1882年出版的第二版是这样地富于批判性,以致梵蒂冈请他停止发行。他曾尖锐地评述教廷的要求,批评耶稣会和经院哲学,并埋怨说,教皇极权论已把教会带到悬崖绝壁的边缘。他迫于形势屈服于梵蒂冈的要求,收回了这一版而出版①《按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来看路德》,1904年。——原注②参阅克勒,《天主教与宗教改革》,1905年。——原注③克莱门十四世于1774年9月病死,传闻死于中毒。——谭注①参阅豪维勒,《F.X.克劳斯》,1904年;布赖格,《对于F.X.克劳斯的回忆》,1902年。——原注\n一种经过删节的版本,声明一个军官必须服从他的将领,但是后来他后悔作了这样的让步,在谈及它时称之为“娼妇版”。主要是想逃避麻烦,他在晚年从事于危险性较少的题材:基督教艺术。他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古迹的概述为概述其他省区的古迹作出了样板。他在罗马碰到德·罗西,并刊印了诺斯科特和布朗洛的《地下罗马城》删节本的德文版,附以自己撰写的重要文章。他还编辑《基督教古文物辞典》,包括考古学和关于最初六个世纪的基督教的组织、仪式和教徒的私人生活。由于他的《莱茵兰基督教铭文集》的出版,他被委派为巴登宗教古迹的保管员。他最大的著作《基督教艺术史》于1896年开始出版。该书是以动人的观察力写成的,并附有精彩插图;它不仅是关于基督教艺术的一部最好的概览而且是对于教会史的有重要价值的贡献。在他关于但丁的专著里,他自称为奎柏林派[皇帝派],因为他对于无论在中世纪时代或在他那时代的教皇的控制,都是很不喜欢的。他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是一个文化史家而不是一个教会史家。他与教皇极权论没有共同之处。他的英雄①是罗斯米尼;他写了一篇最长的论文来论述后者。在他的喀富尔传记里,他尖锐地攻击政治性的教会并欢迎这种教会的倾覆。他认为耶稣会会士是毫无希望的蒙昧主义者,他是红衣主教霍恩罗厄及其他梵蒂冈所厌恶的教士的朋友。他赞赏哈纳克,并使迪歇纳与卢瓦齐于德意志闻名。他的热烈愿望,是要调和基督教与文化、教会与民族、梵蒂冈教廷与意大利皇宫奎里纳尔。但是他不属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走上火刑柱这种类型的宗教改革家。迪歇纳关于资料的批判研究和《教廷圣务录》的出版获得了酬报:他被聘为巴黎天主教学院教会史教授。他的授课激起了学生的热情,其中有卢瓦齐;但是他的方法太独出心裁,因而不为教皇极权论派教会所①容忍,于是他转到空气较温和的高级学术学校去。他的《教廷圣务录》版本得到蒙森的赞赏。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古高卢的主教年表》;它是按照省分排列的,揭穿了关于圣徒的若干神话。他关于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论著更为著名;它评论弥撒的起源、礼拜仪文的发展、圣职任命的仪式、法衣的使用、节日的庆祝仪式以及有组织的基督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关于公元754—1073年间教皇世俗权之起源的一卷演讲稿里,他宣称,即使抛开那些下流的丑事不谈,在那些时候几乎所有教皇的品质也都是远离使徒理想的。关于“分裂的教会”这一卷,加深了他更严格的教友圈子对他所抱的疑虑。1905年他开始出版他的《早期教会史》;这是根据他的已在传阅的手稿讲义写成的。他精通新教的学术研究;哈纳克和舒勒尔、察恩和李普西、卢夫斯和克吕格诸人的名字出现在他作品的脚注内。哈纳克说,任何新教学者都会因写出这部书而自豪。迪歇纳承认:教会起初既无教会法又无信条;主教制度是为防止异端而兴起的。他的文字缺乏热情;他仿佛是在薄冰上轻轻地滑行。在讨论君②士坦丁的异象时,他审慎地说,要衡量这类证明的价值和检查这种内心①罗斯米尼,R.S.A.(1797—1855年),西班牙哲学家、神学家,创慈善兄弟会教派。他的一些宗教观点有背离正教教义之处,其著作被列为禁书。——谭注①参阅乌坦,《十九世纪天主教徒中的圣经问题》,1902年。——原注②传说君士坦丁在进军罗马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乃仿此式样制作军旗,一战而胜。遂定\n深处的事情是困难的。君士坦丁本人在这个历史家看来算不了一个英雄;因为他的故事沾染着太多的血腥。第五世纪是悲惨、毁灭与堕落的时代。这部书是为学者写的;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部天主教徒的巨著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客观叙述标准。①该书最初两卷在“现代主义”被谴责之前不久出版;它们是获得“圣宫长”,即教皇神学顾问批准的。它们作为学识与正教能结合起的证明而受到天主教报刊的欢迎;卢万大学还赠给他博士学位。当它们被译成意大利文时,迪歇纳作了少许修改,再一次获得批准。他送了一本给庇护十世;后者也宣称自己对该书的正统观念感到满意,但当译本出现后,批判的风暴立即在他头上爆发开来。“红衣主教九人法庭”指斥该书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禁止它在意大利神学院使用。译本确是不完善,因而立即被收回■一个耶稣会会士博塔吉西奥在佛罗伦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并把这些文章重印成书,题词献给教皇。迪歇纳写了一封《给天主教会主教的密函》来进行答辩,宣称这个耶稣会会士的书歪曲了他的意见。但是搜查现代主义信徒的运动正处于高潮,他的老支持者如红衣主教梅尔切尔已经失势。虽然对他未曾提出特殊异端罪行的控诉,但他披指责为轻率无礼和缺乏尊敬态度。他的仇敌在1912年如愿以偿,把这个最伟大的近代法国天主教学者的主要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这部主要著作的第四卷,直到他死后才于1922年出版。基督教为国教。——译者①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新教及圣公会的一种教义,主张把教义与现代科学结论相调和:庇护十世(在位期:1903—1914年)曾予以谴责。——译者\n第二十七章文明史Ⅰ历史的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直到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没有人敢再同意西利和弗里曼的主张:前者说,历史是列国的传记;后者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各民族和帝国的成长、活动家的功绩和各党派的兴衰,依然是最能吸引历史家注意的问题。但是,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家的注意。历史家必须不断地观察生活,也必须全面地观察生活。①这类包括文明之中各个非政治方面的著作,最好称之为文化史。它的创立人是伏尔泰;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的全面生活的著作。他的《论风尚》是第一部真正的文明史,这本书第一次企图把无数条线织成一幅单独的图案。伏尔泰开风气之先,其他历史家接②①踵追随。温克尔曼把古代艺术史作为希腊精神的表现来论述。黑伦探②索了商业的发展。尤斯图斯·莫泽尔探索了农民的状况,并揭示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赫德尔和浪漫主义派倾听了民族精神的微③弱呼声。虽然施洛塞尔和基佐的历史著作已在广大的前线上进军,但在19世纪上半期文化史的全部重要性还是很少得到承认的。1848年的革命使政治家和历史家们的注意力转到了第四等级。这件④⑤事大体上决定了里尔的终身工作;他是三大历史家之一,他们被后来的文化史家看作是自己行业的开拓者。洛伦茨选择他作为这个历史类型的主要代表,而施泰因豪森则认为布克哈特和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应占首席地位。的确,里尔从未写出过一部第一流的著作,而且在德国以外他也很少为人所知;但是他在长期的教授、作家和巡回讲演者的工作上竭力宣传了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他的父亲是拿骚公爵城堡的总监,他在作视察旅行时带着这孩子。那个热情对待人民创造力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及在格林兄弟鼓舞下的日耳曼派研究的发展又影响了这个莱茵兰青年的思想。他由于住在奥格斯堡,也加强了对老德意志城市生活的兴趣。①参阅约德尔:《文化史的编纂》,1879年;绍姆克尔:《德意志文化史编纂的历史》,1905年。——原注②温克尔曼的代表作《古代艺术史》(二卷1764年)是希腊文化史最早的著作之一。——谭注①黑伦著有《论古代主要国家的政治、交通和商业》,1796年。——谭注②莫泽尔著有《奥斯纳布律克史》一书,在书中提出了一国的政治组织来源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力量之中的观点。——谭注③施洛塞尔比较重视民族文化对政治史的影响,著有《世界史》、《十八世纪史》等。基佐著有《欧洲文明通史》、《西罗马灭亡后的法国文明史》等。——谭注④参阅西蒙斯费尔德:《W.H.里尔》,1898年;戈泰因,见《普鲁士年鉴》,1898年4月;洛伦茨,《历史科学》,1886年。——原注⑤指他和下文介绍的弗赖塔格和伯克哈特三人,都是文化史专家。——谭注\n1854年,他三十一岁时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召到慕尼黑,并成为后者圆桌上的贵宾。阿克顿曾听过他的讲课,很久以后他记下了对里尔的印象。“一个活着的人对于社会的流动力和固定力都能同样地理解。三十多年前,在布克哈特或弗里兰德、巴克尔或西蒙之前,里尔已开始讲授文明史,向他的幸运的听众显示出对历史的新看法;那是比任何以前的著作中的看法都更深刻的。”他宣称,民俗的研究是在前一世纪创始的,但它的资料则与历史同样古老。荷马诗篇和《旧约全书》原料丰富;希罗多德对于人种志具有清晰的概念,他不仅是历史学的创始人,也是民俗研究的创始人。塔西佗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里最早系统地叙述了居民与国土的联系。直①到社会史的真正创立人尤斯图斯·莫泽尔,才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奥斯纳布律克史》是人民群众取得他们应有地位的一部历史著作。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从各方面源源而来——来自阿肯沃尔所创立的统计科学、亚当·斯密的经济生活的论著、卡尔·里特尔对②地理学的重视、萨维尼的自然法学史方面,尤其是来自格林弟兄的神话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面。现在一般人已承认,人类只能在大自然所规定的限度内获得发展。里尔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德意志人民的自然史》。在该书的第一卷《土地与人民》的序言里,他说:他在国内漫游时了解到,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其明确的历史的和自然的根源。人民以前在图画中仅仅是一个点缀的背景,而现在他们成了主要的形象;历史家和政治家都应以了解他们成长的规律作为主要任务。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因素。他把德意志分成三个地区:气候、土壤、山区或平原的差别导致风俗、土地的使用、食品、衣服、房屋甚至信仰的差别。市镇很快摆脱地域偏见,而乡村生活却还照旧进行,这种状况取决于政府的行动或思想的渗入少,取决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多。他关于自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作用的分析,富于启发性;读他的文字,有登高望远的感觉。里尔在第二卷里进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规律。在社会生活中有两大势力,各自体现于两个阶级中。第一种,即惰性或社会的保守力,主要由农民代表,但它是一种民主的保守力。在法国革命时期,当城市为要求人权而沸腾时,农民则要求森林和草地的特权。第二种代表执著或惰性的,是贵族阶级。施泰因明智地承认:除去贵族的压迫性特权便是加强并永远保持它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第二种基本力量,即运动的力量,主要是在城市里起作用,国家的健全和幸福取决于能否维持执著的力量与运动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平衡。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里尔在第三卷内进而论述了“家庭”,即社会的最后的希望。他宣称,“我们在国家和社会里改变越多,我们就越依附于家庭。”家庭是根据两性间的自然分工的;而文化的发展使他们更进一步分工,因为妇女在原始社会里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他还使人们注意那些使各个家庭各有特性的传统的或非传统的因素。这种家庭的个性反映在路德维希·里希特①参阅克拉森,《尤斯图斯·莫泽尔》,1936年。——原注②里特尔(KarlRitter1799—1859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持地理决定论的观点。——谭注\n①的图片上;他恳求他的同胞保持它。他称这一卷为“德意志家庭的田园诗”。里尔关于法尔茨州的研究,是打算作为对集团心理学的一种贡献;他在那里精确地应用了《自然史》中所推荐的方法。关于这个地区的自然特征、居民的历史、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代的名胜古迹、村庄和城市、服装和食物、政治和社会特点、宗教和方言,他都加以评述。他在研究奥格斯堡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尝试,这本著作有时被称为他的杰作。他宣称:“在民风的研究里象在自然科学里一样,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在任何地方都看到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有机联系。他的方法应用于一部奉国王之命编辑的巨大的集体著作《巴伐利亚的土地和人民》里,也用在慕尼黑国立博物馆的创立方面,他是这个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在文化史工作上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他对艺术的特别重视。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和音乐批评家,他主张音乐也象诗或科学一样,在文化中是一个巨大的因素;音乐形式的演进解决了德意志民族感情史上的许多问题。其次,他认为,过去时代的大教堂和其他古迹构成关于土地和人民的一部附有插图的历史。除了他写历史著作外,他还写了很多故事书,旨在说明德国千余年时期的生活。“每一篇只是一小幅风俗画,但他们合起来就成了一大幅历史全景画。”里尔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联系虽然有锐利的洞察力,但并没有同时认识到其他一些因素。相形之下他对国家的态度漠不关心,这使特赖奇克轻蔑地称他为“沙龙”政治家。与雅各布·格林相同,他宁取典型而舍个别。他先看活着的人民而后才看刊印的文字。他是最缺少职业特性的历史家。他的成绩,在于强调了对人民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并查究它被什么影响所决定,并通过什么途径表达自己。戈泰因证明了他同时代的人怎样愉快地欢迎里尔的描写,他们怎样进行旨在观察和发现的徒步旅行。他从最枯燥乏味的地方和人民中间找到兴趣和意义,并化腐朽为神奇。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们有时称他为1848年后反动势力的理论家,但他属于那种温和的、诗意的保守主义,他留恋“美好的昔日”。他为文化史提出了最高要求,称之为真正的历史哲学。他拒绝承认政治与文化间的矛盾。“这种二元论将消逝,文化史将成为一根树干,以国家、教会、艺术及其他部门作为它的分枝。”①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和里尔同样是热爱祖国的德意志人,他在塑造德意志人民的历史生活的尝试上赢得了比里尔大得多的声誉。他出身于西里西亚,在那里,斯拉夫世界的阴影使种族的自觉心激化起来,因而他在早年时期已对德意志文学和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被拉克曼引入中世纪语言学领域后,他以关于德意志戏剧诗起源的论文获得了博②士学位,继之以研究罗斯威塔的论文。他在早年时期关于半异教、半基督教的古老祝祭剧、神秘剧、喜剧的探索,使他领会了人民的生活和呼①里希特(Richter,AdrianLudwig,1803—1884年)德国画家和插图专家。——译者①参阅弗赖伊塔格:《回忆录》,1887年;阿尔伯特:《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85年;汉施泰因:《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95年;林道:《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907年;多费:《弗赖伊塔格和特赖奇克的通讯选集》,1900年。——原注②罗斯威塔(Roswitha,约932—1002年)德意志修女,拉丁语诗人。——译者\n声。1848年的事件使他走上了论坛。他买下了《边境邮报》,迁到莱比锡,使它成为鼓吹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完成统一这一原则的喉舌。从此,他把政治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就在他自己的报纸栏内,他从1852年开始发表他的《德意志历史图景》。很久之后,他在自传里写道,“在政治事件的暗流中流逝的人民的生活——千百万微贱男女们的境地、悲哀和欢乐对我来说一向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他收集了很多小册子、传单、木刻及其他珍品。“我从这些小书里获得了关于风俗和生活方式的各种知识;关于这方面,大书是不谈的。”他开始时只写16、17世纪的概述,到后来,由于它们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才决定写全部德意志史。弗赖伊塔格的《图景集》共分五册,概述了德意志人民从古至今的生活,普通读者和学者都给予高度的赞扬。这本书既是爱国主义的,又是科学和艺术的著作。舍雷尔宣称,“这本书是我们有过的最好德意志历史;如果这话说得过分,我们可以说,从那里可以比任何别的历史著作找到更多的我们要求于一本好的德意志史的东西。”埃里希·施米特把他列入第一流的日耳曼学家和历史家中间。直至今天,这本书还是无与伦比的。他曾希望这本书成为“家庭之友”,这个希望实现了。由于把人民放在画面的前景,他使二千年时期的历史有了统一性;通过摘录当代人的证词,他使过去活现在眼前。特赖奇克说,“笔锋所及之处,你总是注入一片赤心。”舍雷尔写道,“在雅各布·格林之后,没有任何人象你那样使我满怀对我国人民的热爱”。可是,他坚持不把过去理想化。他宣称,德意志人要寻找美好的昔日,是徒劳无益的。在过去,任何时代的生活都比今天艰苦得多。在过去,很少安全,很少权利,没有舆论,个人也较少自由。他避免了只谈群众而忘却个人这种危险。他有一次谈到文化史时说,他是多半象一爿估衣铺——堆着服装而没有人穿。他充分认识到卓越人物的重要性。他所叙述的第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是查理大帝;他以爱护的心情描写了红胡子,“最后的真正的德意志皇帝”。整个著作的中心是路德,他关于这个宗教改革家的描写成了新教德意志的宝贵财富,正象米什莱关于贞德的描写向法国学校里注入了爱国理想主义那样。在重要性上稍逊的,是关于腓特烈大帝的功绩和性格的详细论著。如果说这些描写是该书最受欢迎的部分,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图景。他描绘了军队、兵营生活、村庄、城市、迷信和恶习、盗贼和警察。在历史家中间,再没有人更现实地显示出一场斗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灾难;这场斗争使德意志倒退了一个世纪。该书是在1866年完成的,当时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在望。弗赖伊塔格写道,“这一年,德意志人重新得到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变得象民族大迁移或十字军运动一样陌生的东西——他们的国家。做德意志人已成为一种幸福;德意志人不久将被看作世界各民族中的一个巨大的光荣。”他还写了一部关于他朋友马蒂的传记,该书可以看作是这个故事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续编;马蒂是巴登的一个大臣,德意志统一拥护者之一。但是弗赖伊塔格的著作就阐明德意志人民生活来说,是不完备的。在他的自传里,他叙述了1870年的战役怎样使他产生了一些幻象,后来这些幻象在《祖先》里又有显著发展;在这次战役中他曾陪同皇太子到过前线。这个种族的整个历史好象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地图。他写道,“我历\n来深感兴趣的是人和他的祖先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他身心的神秘影响。科学所不能测度的事情,诗人可以尝试。”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个单独的家庭应参加德意志历史上一些决定性的事件。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的小说曾讲述勃兰登堡,其它各邦的成员对之没有多大兴趣,可是弗赖伊塔格决心要使统一的德意志的每一个公民都感到兴①趣。第一分册于1872年出版,叙述英戈在罗马危险时期的命运;第二②分册叙述斯拉夫人的侵入东方和卜尼法斯的来临;第三、四分册叙述骑士制的兴起和衰落;第五分册,《马尔库斯·柯尼希》,叙述到宗教改革运动,以托伦的一个商人的事业来反映这一运动;这个商人受波兰的统治,但他的感情则属于德意志方面;第六分册描述三十年战争;第七分册描述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第八分册包括解放战争并包括有关他自己家庭的事情。这个家庭的最近成员维克托·柯尼希于1848年成为新闻记者。弗赖伊塔格称自己的著作是分为八个乐章的交响曲。但个人虽然被描写成时代的继承人,他却从来不受传统的长链所限制或阻碍。祖先是一种鼓舞力量,而不是一种负担。虽然珍珠是串在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线上,但这一连串却具有情绪的统一性。在1870年德意志统一后的时期中,《祖先》被热烈地阅读;它使关于过去时代的无数回忆生动地呈现在统一的德国眼前。这部书的地位可作为《图景集》的诗的释文,正象席勒的华伦斯坦剧本产生于他的《三十年战争》那样。他的这两部著作使全世界的德意志男女都对他们国家的历史感兴趣;在这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别人的工作为多。在里尔和弗赖伊塔格致力于德意志人民和平常人的命运的时候,一③个比他们更有声望的同时代人(瑞士人)布克哈特促使人们注意思想和行为、宗教和艺术、研究和思索——他要重现过去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气氛。里尔喜欢农民,弗赖伊塔格喜欢市民,而布克哈特偏爱优秀分子。这三个人都扩大了历史的范围,但这两个德意志人只叙述了他们本国的历史,而这个瑞士学者的叙述则包括文明的整个领域,他的名声也传播于各国。在柏林,他听过博克、雅各布·格林和兰克的讲课,但弗兰兹·库①格勒对他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后者的《艺术史》那时正开始出版。在二十岁的青年时期,他已写了关于瑞士大教堂的论著;在进入波恩大学后,他又写了关于莱茵兰教会的著作。在1844年,他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历史和艺术讲师;他开始吸引好学的听众;尔后,在半个世纪里他的教室是经常满座的。1847年,应作者的请求,他编订了库格勒的《绘画手册》,①英戈是生活在日耳曼历史萌芽时期的本册的主人公。——谭注②卜尼法斯,盎格鲁撒克逊人,723年来到大陆,在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图林根人中间创建克尔特式的居留地。——谭注③参阅特罗格:《雅各布·布克哈特》,1898年;纽曼,见《全德名人传记集》;格尔策:《小品文选集》,1907年;戈泰因,见《普鲁士年鉴》,第XC卷;迈内克:《兰克与布克哈特》,1948年;克里特迈尔:《雅各布·布克哈特》,1949年;威纳·基吉:《雅各布·布克哈特》,第Ⅰ卷,1947年;第Ⅱ卷,1951年。他著作的十四卷精装本,出现于1929—1934年。他的《通讯集》第Ⅰ卷,由马克思·布克哈特编辑,出版于1949年。——原注①库格勒(Kugler,F.T.1808—1858年)德国艺术史家,《艺术史手册》(Hand-buchderKunstgeschifche,1841—1842年)是其代表作。——谭注\n并加上了他自己的资料。虽然布克哈特的研究工作以前大部分是在艺术界里,但他第一部相当大的著作表明:他是锐敏地注意文明的其他方面的。1842年,他写道,“对我来说,背景是主要的考虑;而背景是由文化史提供的;所以我愿致力于这一方面。”他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于1852年出版,旨在抓住一个迅速过渡的时代的各种特征。当他为演讲而研究第四世纪时,他痛感一般人对这个时代的气氛一无所知。他想描写出这个时代的心理状态,在这个时代里主要的特征是不安全,而支配的倾向是对新奇事物的渴望。旧的和新的世界集中表现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身上。他评述了在旧世界中酝酿着,并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的各种要素,但他认为君士坦丁本人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有些人认为:这个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是一个秘密;而他却回答说,他是没有什么信仰的。而且,当基督教成了官方宗教以后,它本身就很快地堕落了,一些优秀分子则躲进了禁欲主义和修道生活里。该书全面地综述了帝国和它的政府、行省和大都会的生活、异教、新柏拉图主义和秘密的宗教仪式、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他作出结论说,旧世界既不是被蛮族,也不是被基督教,而是被它本身破坏的。这本著作受到了学者们的欢迎,但是,它虽然使作者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历史家,它却从来没有成为一①部普通人爱好的读物。布克哈特的最主要,最强烈的爱好是艺术。他已经走马看花地访问过意大利;在完成《君士坦丁》以后,他又在半岛上住了一年多。结果是他编成了他的《古迹指南》,即意大利艺术古迹的指导书;它是长千余页的一种小型本,分成建筑、雕刻和绘画各篇。这本著作赢得了库格勒和其他艺术史家的热烈称赞;它以后的版本经过别人修订,成了无数旅行者的向导、哲人和伴侣。虽然他的早期建筑学著作是专讲哥特式的,他却热烈地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强调指出它在处理空间上能别出心裁。他对于雕刻不太熟悉,但他关于绘画的论断却是具有鼓舞力的。在全书里,他提出了自己的印象,而不拘泥于传统或专家的意见。在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以后,他转而探索它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决定使意大利也受到象他曾对君士坦丁时代所做的同样深刻的分析,而这个新题目比那个旧题目更合适于他。他对基督教不太同情,所以不能了解第四世纪的某些方面;但是他非常熟悉15世纪的精神上的勇气、它的①艺术和学术。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于1860年,立即跻于第一流历史著作之列,因为它向世人显示了文化史的潜力,并把它提升到史学著作类型中的一个权威的地位上。没有任何历史家曾以更大的魄力和洞察力来抓住并解释一个时代的心理。他宣称,在中世纪时代,一个人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一个社团和一个家族的成员;社会是一种等级制度,传统是至高无上的。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人发现了自己,而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个人。千余年来的锁链从此被打破,自我实现成了目标;对于世界和人的重新估价也风行一时。象皇帝腓特烈二世这一类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在中世纪时代曾出现过一两次,而现在在行动、思①英文译本于1949年出版。——原注①此书的全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KulturderRenaissanceinItalien)。——谭注\n想和艺术世界里,这种“全面的人物”已是司空见惯。“15世纪首先是一个产生多才多艺的人的时代。”这些奇葩异卉所由成长的土壤包含了许多因素——城市国家的紧张生活、古代艺术和哲学的复兴、权威的削弱和信仰的瓦解。暴君和雇佣兵队长,尽管有残暴行为,却是政治艺术家,是从庞大模型内铸出的人物。贵妇人中发出了一种以前或以后的妇女所未曾有过的才华的异彩。布克哈特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所以中世纪时代与宗教改革时期之间所闪出的光彩并未能使他对其他事物视而不见。本书以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详细分析作为终篇;它并不企图掩盖当时的野蛮和兽性,以及同无限怀疑并存的粗野迷信。他由于切萨雷·博尔贾和西吉斯蒙多·马拉泰②斯塔的“肆无忌惮地耽于作恶”而感到震惊,可是他认识到,上层阶级的基本的恶习,即放纵的个人主义,倒是这个时代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条件。“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必然要承受一个新时代的第一次强大冲击。通过他的才干和他的热情,他成了他的时代内容的所有高度和深度的最有特色的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有自己的缺点,但却是近代世界的春天。布克哈特的杰作是历史文献中最有创见的著作之一。许多读者惋惜书中略去了艺术;泰纳回答说,我们并不为此而觉得不足,因为我们感兴趣于人之为人甚于人之为艺术家;尽管如此,略去艺术毕竟使这本著作美中不足。另外有些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那从中世纪晨光熹微到文艺复兴时期骄阳普照的过渡的速度。他极其熟悉文艺复兴的文献资料,但对中世纪时代却从未作过深刻的研究。有些批评家说,他对文艺复兴的看法失于过分颂扬,另外有些人认为,书中关于政治诸章不够充实。他所在的国度对国家的重视比欧洲任何别的地方都少;他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政府问题也就不大感兴趣,而对于帝国,无论新的或旧的,他都觉得没有什么用处。有些读者埋怨说,他过高估价了①关于重新发现古典世界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忽略了意大利文化的物质基础;而且他的论述把各个不同的世代混在一起。这些批评意见虽然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却无伤于这本书的声誊,用阿克顿的话说,它依然是“现有的关于文明史的著作中最警辟,最精微的”。布克哈特虽然后来还活了近四十年,但却没有再出过另一本的王朝。马拉泰斯塔(1417—146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强大的雇佣军头目之一。因反对教皇庇护二世被逐出教会。——谭注书。他为演讲而殚思极虑;关于这些演讲的丰富内容和创造性,尼采及其他听讲者都能证明。当兰克退休以后,柏林大学卑辞厚礼地聘请他接替这个老历史家的讲座;他却拒绝了。他晚年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自己的讲义来编著关于希腊文明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述。1897年他逝世时,有两卷已经编成多年,另外两卷是由他的一个门生编好付印的。1868年,他曾提纲挈领地讲授过一个关于“古代精神”的课程;后来他还常常以希腊为题作讲演。由于听讲者的坚决要求,他编成了讲义,但他始终认为这些讲义太不完备,②博尔贾,C.(约1476—1507年),教皇亚加大六世之子,枢机主教。凶狠奸诈,孤立其父,谋杀其兄弟与部属,攻城掠地,自封为罗马尼阿公爵,试图在中意建立独立①塞勒里:《文艺复兴的性质和起源》1950年,这本书对布克哈特关于这个时期突然变为光明的说法提出了最新的反驳。——原注\n不宜出版;直到弥留之际,他才允许出版。在被敦促的时候,他总是讽刺地回答道,“不——这样一个可怜的门外汉可不敢,我是旁门左道,不学无术;我将被方家硕学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他的著作的不完备处和专家们的尖锐批评,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当这份手稿放在他的书桌上时,对希腊的研究正在大踏步前进。他知道自己是已经落后了,但他相信只要完全掌握文献资料就足以防止严重错误。他从未领会到铭文及其他新证据的重要性。①他的《希腊文明史》是一部详细的综合性概述。他宣称,“最高级的文化只能在那由强权保护的安全的土地上兴起。”但是,他并不把文化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还承认天才至高无上。特别是,在国家衰弱的时候,艺术是可以繁荣的。他以整个一卷篇幅来论述宗教。第三卷叙述了艺术和文学、科学和哲学,第四卷描写了个别的希腊人从荷马到保塞尼亚斯各个接续阶段中的发展。布克哈特反对象库齐乌曾从奥弗里·缪勒、歌德和温克尔曼所沿袭下来的那样,把希腊世界理想化。他不是一个专家,他在研究了其他领域以后较晚才来研究希腊;正是这一事实,使本书格外新鲜。它最突出的特征,是揭示阴暗面的深度。他曾受到指责,说他目眩于文艺复兴;但他肯定没有被希腊所眩惑。他强调指出它的残暴、不容忍态度和奴隶制的污点。虽然他有时被称为“异教徒”,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接受是不让于任何人的。威拉莫威兹竟斩钉截铁地宣称:这本著作不是为科学而写的,但象霍尔姆和卡斯特这样优良的判断者却都称颂它。在布克哈特看来,内部生活比起形式和制度等外部世界具有更多的意义;他之所以重视外部世界,主要是因为它们为表达内部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他这种深入一个时代的灵魂的能力曾鼓舞起泰纳的热情。他是过于独往独来,因而不能组成一个学派,但哪里有从事解释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历史家不为他的泉源所沉醉呢?Ⅱ当里尔、弗赖伊塔格和布克哈特使文化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涌现出一批研究工作者,把他们的方法带入新的领域。弗里德兰德对罗马帝①国的文明作了无与伦比的描述,继他之后,出现了勒启的有吸引力的著作:关于理性主义和道德的历史。象格雷戈罗维的巨著《中世纪时代罗马城的历史》、沃斯勒关于但丁与其时代的论著、拉希达尔的中世纪大①学总论、桑代克关于中世纪科学与幻术的详细纪录,亨利·亚当斯的《圣②密歇尔山与夏尔特尔》(即关于13世纪基督教国家的一个同情的解释)①关于本书的最好评论,是卡尔·纽曼的《布克哈特关于希腊文化史的概念》,《历史杂志》第XXXV卷。——原注①弗里德兰德著有《早期罗马帝国的生活与风习》,共四卷,1862—1871年。——谭注①拉希达尔的著作为《中世纪欧洲的大学》(UniversitiesofEuropeintheMiddleAges)共二卷,1895年。——谭注②圣密歇尔为法国诺曼底之著名寺院,山以此寺为名。夏尔特尔,法国西部城市,有建于13世纪的著名教堂。此书以游记而涉及11至13世纪法国建筑、文学、哲学诸多方面,将中古文化与20世纪文明进行对照,\n以及孔帕雷蒂关于《中世纪的维吉尔》的影响的惊奇故事等,这类著作都丰富并扩大了历史的概念。在为理解近代欧洲思想所作出的著名贡献中,可以举出下列著作:西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鲁菲尼的《宗教自由的历史》、鲍尔森的《德国高等教育史》、莱斯利·斯蒂芬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和《英国功利主义者》、库诺·费希尔的《近代哲学史》(根据他在海德尔堡大学的讲稿编写)、梅尔茨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海姆关于赫德尔和洪堡的传记、尤斯蒂关于温克尔曼与他的时代的出色描写以及迪尔泰的《从宗教改革到施莱尔马赫的德意志思想③家》的解释性论著。罗舍尔把历史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社会史方面。哈兰曾叹息说,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中世纪的英国农村生活;而在半个世纪以后,索罗尔德·罗杰斯以他的七卷《农业和物价史》奠定了英国农业史的基础。坎宁安和阿什利第一次企④图综合地论述我们的经济发展。①勒瓦瑟长期从事追述法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尼茨在柏林大学讲演德②意志人民的社会史。伊纳马—施特内尔格写了第一部有学术性的德意志③经济史。科瓦列夫斯基回溯了欧洲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经济发展④⑤,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追述了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演进。施莫勒⑥学派以施莫勒早期关于施特拉斯堡的织布工业的论著作为典型,编写了一些最高标准的专著来阐明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这位柏林大学的年高望重的教授的学术讨论班曾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生。没有人象他那样有力地强调指出经济现象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有一些人热心地研究文明史,他们是在19世纪中期科学的发现和总结的冲击之下写作的。孔德的有限的历史知识使他的关于文明发展概⑦论的价值打了折扣;他的三阶段规律也是过分简单化了。马克思拘泥于⑧他的经济决定论的体系。巴克尔的未完merce)共二卷,1882年阿什利著有《英国经济的历史与理论导论》(IntroductiontoEnglishEconomicHistoryandTheory〕,共二卷,1888探索两种文化的一致性。1913年初版。——谭注③罗舍尔(Roscher,W.1817—1894年),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界中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这派重视经济史,提倡采用历史方法,强调个别记述和研究,忽视理论与概括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谭注④坎宁安著有《英国工商业的发展》(GrowthofEnglishIndustryandCom-①勒瓦瑟著有:《1789年以前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工业》(Histoiredeclassesouvrièresetdel’industrieenFranceavant1789),1859年。《1789—1870年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工业》(Histoiredeclassesouvriersetdel’indústrieenFrancedepuis1789à1870),1867年等。——谭注②尼茨著有《德国人民史》(GeschichtedesdeutschenVolkes)共三卷,1883—1885年。——谭注③书名《德意志经济史》(DeutscheWirtschaftsgeschichte)共三卷,1879—1901年。——谭注④书名《欧洲经济发展史》共七卷。——谭注⑤桑巴特著有《近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共二卷,1902年。马克斯·韦伯著有《经济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1923年。——谭注⑥施莫勒著有《施特拉斯堡行会史》、《十九世纪德国手工业史》等。——谭注⑦孔德把社会历史发展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即科学的三个阶段。——谭注⑧参阅L.M.罗伯逊的挑战性著作:《巴克尔及其批评者》,1895年。——原注\n①—1893年。——谭注成著作,在刺激人们思考事件的原因和联系以及强调自然条件的持久影响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他关于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国与西班牙的智慧发展的精彩叙述,可以列入最有吸引力的历史著作之林。他的雄心是要对政治和文化的整个广袤领域进行比较和归纳,以此为坚实基础把文明史从编纂转化为一种类似科学的东西。他曾主张进步就是知识增长的成果,这个论点受到了尖锐的责难;但他虽然同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不花力气的教条主义,他的书却在许多读者的生活中标志着一个时代,并为历史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提供了极大的推②动力。赫尔瓦尔是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由于拥护一个类似的自然主义观念,他在1874年写了《文明的自然发展史》。他写道,“我试图考查超自然力量在说明文明现象上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他给以否定的回答,并宣称,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以种族、地理和气候为条件的。文明意味着控制自然和开化人类,而不是指道德的增长。为生存而斗争支配着历史生活的整个过程。该书最好的部分是讲述史前时期的部分,那时自然力在统治着象一个专制君王,而不象一个立宪君主。虽然赫尔瓦尔关于世界史的知识是有限的,他的语调是可商榷的,他的哲学是肤浅的,但这本书却大受欢迎。在他死后刊行了第四版,经过专家修订,并附有精彩的插图。黑尔莫尔特也编辑了大部头的集体著作:《人类的历史》;它同样强调自然界和地理的绝对的影响。原始文明已经被包括进历史研究的范围。布歇·德·佩尔特斯在索姆河流域的发现①和皮特-里弗斯在英国的发现,把人类戏剧的开幕时间提前了几千年,并开创了史前时期的考古科学。在泰勒和麦克伦南、曼哈特和拉策尔·弗②雷泽和威斯特马克等人笔下,人类学成了一门科学;我们祖先的习惯和③信仰变成可以理解的了。梅因以他的广博知识从事解释古代的法律。由于文明史日益受到欢迎,就引起了关于它的性质和重要性的长期争论。戈泰因与舍费尔之间的争论以及由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所④带来的争论引起了最广泛的兴趣。迪特里希·舍费尔是以研究汉萨同盟知名的;他于1888年在图宾根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如果历史要有统①这里指的是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共二卷,1857,1861年)一书。巴氏立志研究世界文明历史,以上两卷仅仅是其计划撰写的专著的一个序论。——谭注②参阅《全德名人传记集》。巴尔特在他的《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97年)里,讨论自然主义学派。卡洛·安托尼,《关于历史主义与社会学》,1940年,这本书是有用的。——原注①德·佩尔特斯,法国考古学家。1830年在索姆河流域的文化遗址发现了燧石工具和武器,被学术界审定为旧石器时代人的遗物。皮特·里弗斯,英国将军、考古学家以搜集史前遗物和人种志标本知名。——谭注②泰勒(Taylor,E.1832—1917年),英国人类学家,首先提出人类社会进化经由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观点。麦克伦南(McLennan,J.F.1827—1881年),英国人类学家,以研究婚姻进化史知名。拉策尔(Ratzel,F.1844—1904),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强调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威斯特马克(Westermarck,E.A.1862—1939年),芬兰人类学家,以研究人类婚姻进化与伦理观念的起源与发展知名。——谭注③梅因(Maine,H.1822—1888年),英国法制史家,著有《古代法律》(AncientLaw,1861年),通过古代法律研究文明的起源。——谭注④《历史研究的适当范围》。——原注\n一性和科学性,它就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国家方面。在我们的民主时代,许多著作家认为,历史的关键在于群众,因而他们所研究的人类的习惯和生活情况,而不是研究人类的最高才能的表现。卷帙浩繁的著作竟用于叙述中世纪时代的房屋这类琐事。现在应该重申:生命的呼吸永远必须来自国家;没有这种呼吸,历史只是一大堆死的知识。甚至文艺复兴也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它的典型人物是马基雅维里。宗教改革使人们有了民族自觉;路德还宣布了国家的神圣的起源。“历史家的任务是使国家了解它的起源、它的任务和它的生活条件。”如果他进入了宗教或法律、文学或艺术的领域,他就必须记住:他是走在岔路上了。这种对传统的政治的坚持,引起了德国的一个最有才干的年轻的文①化史研究者的答复。戈泰因曾以研究南意大利文明的论文而引起注意;②他的声誉又因关于罗耀拉和反宗教改革的巨著而得到提高。他宣称,对于日益增长的科学,我们无需急于限制其范围。国家只是人类社团的一种形式。它可能是最大的,但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宗教、艺术、法律、经济——包括并预先假定一个它们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统一体;那是一个有机体,它们是它的肢体。舍费尔曾谈到文化史,好象它只是讲述物质生活条件。戈泰因驳斥文化史忽略个人这种说法;他宣称:弗赖伊塔格最能接近个人生活与群众生活关系的大奥秘;他所描写的路德与腓特烈高耸于人群之上,就象橡树在矮林中一样。对于文化史会缩小国家作用这个批评意见,他回答道,在人类发展的许多紧要时刻,主要关键都不在政治领域。在君士坦丁时代,基本事件是从异教向基督教的过渡。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思想的力量捣毁了古代的模型,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关于这些时期,只有文化史家才能够从政治的混乱状态里找出条理来。普鲁士的成长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样的例外是罕见的。事件是力量的①产物,而力量乃是思想的产物。舍费尔的答复结束了这项争论。他承认,历史包括生活的一切方面,但他争论说,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掌握全部;并指出,兰克及所有其它伟大的历史家都把他们的视线集中于国家②方面。他对认为有些时代几乎完全是文化期这一论点提出挑战。他宣称,如果没有民族感作为后盾,路德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如果没有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反宗教改革也是永远不会赢得轰动的成功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因而他们各自继续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戈泰因要求扩大历史家的任务的概念是有益的,因为这种要求不仅扩大了政治学派的眼光,而且提醒文化史拥护者注意他们更重大的责任。③那由于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的出版而引起的争论,是更激烈①《文化史的任务》,1889年。——原注②书名《罗耀拉与反宗教改革《(IgnatiusLoyolaunddieGegenreforma-tion),1895年。——谭注①《历史与文化史》,1891年。——原注②按兰普雷希特采用文化分期的概念即所谓“文化期”(Kulturperiode)。——译者③关于论述兰普雷希特的著作很多。关于争论的有用的随笔,见哥德弗里德里希:《德国的历史思想》,第431—465页,1902年;贝尔海姆:《历史方法教程》,第710—718页,1908年;克茨希克与蒂尔:《卡尔·兰普雷希特》,1915年;《近代欧洲的若干历史家》,施密特编辑,第10章。——原注\n更持久的。兰普雷希特曾以论述中世纪时代摩泽尔河与中莱茵河流域经④济生活的厚本专著而赢得声名。他把一个德意志地区所曾有过的最大量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册,这项工作的辛苦,是得到一般承认的,但他在使用他的资料方面却受到尖锐的批评。贝洛夫宣称,他的方法是武断的;他的解释是反复无常的。基尔克惋惜说,他的法律概念是不清晰的。施莫勒声称,这本书出版得太快,思想模糊,阅读困难。1891年,《德意志史》开始出版。它原来没有序言来说明作者的目的,但在三年后出版的第一卷的第二版里,他补充了几句导言。他宣称,纯粹政治历史家应同兰克一起追问,“它实际是怎样的?”他自己要知道“它为何成为那样的?”这个发生学(Genetic)方法,必须替代叙述法,而这个方法包括论述事件所由发生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整个情况。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里历史家必须考查因果关系。关于该书的政治部分,他未曾声称作过研究工作,但关于论述社会组织和文化方面,他却是有充分根据的。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追述德意志意识的发展。他相信,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虽然受到外界势力的影响,但它却是按照它固有的规律发展起来的。①兰普雷希特从皮特亚斯讲起,叙述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自然界的差别。人类学和语言学都被利用了,但他关于原始德意志生活的描②写,却比不上象威廉·阿诺德这样的大师那样透彻。那从恺撒和发禄开始的政治叙述,既缺乏力量又枯燥无味,而对各种形式的艺术,他却留恋地加以评述。查理大帝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第一个血肉之躯,但他却未被描写成具有很强的活力。时势的历史代替了人物的历史;文化也占着政治的上风。他对10世纪的两个统治者——猎禽者亨利和短命的鄂图三世感兴趣,前者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和城市的庇护人;后者是一个希腊母亲的孩子。在亨利四世和希尔德布兰特之间的冲突中,他几乎未曾觉察到这个最伟大的教皇的伟大。第三卷是以关于11世纪的城市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论述开始的。“红胡子”是查理大帝以后的最伟大的人物,但他三言两语地把他说成是属于沃尔夫拉姆或哈特曼小说中的浪漫主角这一类型的人。腓特烈二世是中世纪时代最突出的人物,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世界奇人”;但他象一个影子般地一掠而过。在霍亨斯陶芬朝倾覆后德意志缺少伟大的政治人物,因而我们也不大觉得这个历史家的缺陷,但是就连他自己的文化史领域内,他也不是经常①令人满意的。他很少谈到那些14世纪引以为荣的伟大的神秘学家。关于中世纪末期的叙述,我们觉得,这个向导缺少一把揭开它们深一层秘密的钥匙。到了路德,我们看到第一个其重要地位似乎被他充分认识到的人物。他提供了关于路德著作的一个公正的叙述;在这方面,他还离④书名《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共三卷,1886年。——谭注①皮特亚斯(pytheas)——希腊航海家,约生于公元前第4世纪后半期,考察过西班牙、高卢及不列颠沿海。——译者②发禄,古罗马将军。公元9年为日耳曼人击溃,使奥古斯都深入征服日耳曼的计划受挫,退守莱茵河。——谭注①14世纪起源于德国,流行于欧洲的,神秘主义以抛弃天主教种种仪节,通过“内心启示”和与上帝直接交感,以寻求信仰与安慰为特征,反映了人们对旧教和现实生活不满的心情,是新教教义的一种表现。——谭注\n②开他的惯例,竟摘引“席间闲谈”的段落。在指出这个宗教改革家未能了解1525年的反叛的性质时,他仔细研究了它的社会与经济原因。这一阶段在很快地连续出版了五卷以后,兰普雷希特停下来答复那③些蜂涌而来的批评者。伦茨宣布,虽然非专业历史家称赞他,但学者们必须提出抗议。他对“是”与“成为”之间所作的区别是可笑的,因为兰克原是擅长应用发生学方法来论述历史问题的。兰普雷希特所说明的比兰克说明的要少得多,因为他没有打算把德意志的历史与欧洲事件的主流联系起来,而且他闭眼不看民族伟人的重要性。在检查他关于宗教改革时代即他所研究的特殊时期这一卷以后,伦茨宣称,他的每一页甚至每一行都可引起抗议。腊赫法耳把他关于16世纪几页上的错误列成一张表,并在每一行旁边标出他抄袭其他学者著作的地方。巴塞尔会议法令集的编辑约翰内斯·哈勒宣称: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几乎每一句都有错误。芬克还写了一小卷来改正他关于中世纪时代末期的宗教情况的①描写。②兰普雷希特的第一次综合答复,发表在他的题为《新旧趋势》的论文集上。他宣称,在写《德意志史》时,他已知道他会同主要的学派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没有某种思想观点,是不可能写出严肃的历史的。以前的各学派曾以个人行动即以个人心理来说明历史事件;现在由于研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凡是承认经济影响的作用的人,常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因为经济现象,就其对艺术、文学或哲学而言,是“物质”的,可是每种经济的行为与改变,同任何脑力劳动一样,是以心理为条件的。因果关系的方法,最容易应用于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也应在那里开始。关于人物的历史,必然经常包含一种传奇的或推测的成分,因为我们只能猜测他们的动机;但关于时势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达到接近科学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理解历史的关键,存在于集体心理方面。后来,他写了一篇关于兰克的长篇论文,把战斗推进到敌人阵营里。他宣称,这个大历史家在他的著作中夹杂着一些哲学见解;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人类的发展是依循未知的法则而进行的。所以第一项任务,是分析历史生活的各种因素。他在《德意志史》里企图做的正是这项工作;《德意志史》与其说是一篇叙述,不如说是一篇解释发生学的论文。这项争论在小册子和杂志上进行了若干年;这个莱比锡教授下定决心对抗一群进攻者为自己辩护。他最全面的意见,是1904年在美国发表①的关于近代历史科学的演讲。他宣称,这项论战是个人心理的拥护者和社会心理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是那些认为动力在于英雄的人和那些认为动力在时势的人之间的斗争。赫德尔曾发现群众的心灵,而浪漫主义派继续了他的工作。兰克,尤其是普鲁士学派,曾复兴个人主义的方法。“这几乎是纯政治活动的时期。民族正在渴望那在其灵魂深处长期企求②路德的弟子记其日常生活言谈汇为一篇,名曰《席间闲谈》。——谭注③《历史杂志》第LⅩⅩⅦ卷。——原注①《兰普雷希特关于中世纪末期教会情况的描写》1896年。——原注②《历史学上的新旧趋势》,1896年。——原注①《什么是历史?》1905年。——原注\n的政治统一。跟着它的实现,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正象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世界。于是,描叙不复是口号而是理解了”。兰普雷希特宣称,原始德意志是象征性的,当时,想象力强而个人淹没于家庭和氏族之中。早期中世纪目睹了等级类型的发展。后期中世纪,即一个地域统治和城市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时代。例如,城市和居民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个时期是一个转到个人主义时代的过渡时期,个人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启蒙运动时达到顶点。第五个阶段,或者说主观主义的阶段,开始于浪漫主义运动,这是在感情上反对理性崇拜的反映。我们现在生活于神经紧张的时代,以冒险、投机、忙乱和焦急的精神为特征,而没有受到具有支配力的理想的鼓舞。上述各个心理的阶段在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在评价经济改变对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的作用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虽然它们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物质和因此产生的社会进步,是对一般进步的主要刺激力。在重新开始写《德意志史》时,兰普雷希特表现出人们对他的前五卷的批评意见并未留下什么影响。在论述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各世纪的诸卷里,可以看出它们和前面诸卷有着同样的缺点。他对自己感兴趣的方面,都详细论述,而对其他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则很少给予注意。例如,在第六卷里,我们看到关于早期音乐和乐器发展的很长的一章;在第七卷里看到关于艺术的详细论述。在叙述拿破仑时代时,我们看到他在政治方面已尽量叙述,但他虽以热烈的爱国心来论述解放战争,却很少谈到施泰因及其同僚。那些论述哲学、文学和艺术、论述康德和贝多芬的部分,是有力而又富于思想性的;关于19世纪的诸卷,在很大程度上还证明了他对近代世界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这部著作是以关于1870年以来德意志历史的三卷补编而完成的。“我懂得,我描述我们时代的历史是大胆的,因为许多人对部分事件,有些人对整个事件比我熟悉得多。为了这些原因,我迟迟没有动笔。”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入观察那①些精神的推动力。第一卷,论述艺术、文学和理论,并讨论瓦格纳、尼②③采、斯特凡·乔治及其他先驱者。冯特被誉为自康德以来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哲学上的继续进步是有赖于这门科学的。第二卷是围绕需要和享受这两个原则分门别类地论述经济生活的现象;描述交通的扩充,国际信用的发展,在生产、发明和技术教育上的进步,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应用,第四等级的发展,移民、帮会、波兰劳动者及其他许多问题。第三卷,讨论党派的成长、对外关系、殖民地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著作终止于略述对政治历史家的挑战;对于他们,兰普雷希特一生不停地进行斗争。“人类的发展不是奴隶式地依靠政治命运的。政治的自我保存依靠艺术和科学、宗教、法律和道德的理想价值的发展;因为只有在这些方面的培养,才能使民族倾向与世界倾向结合起来”。①瓦格纳(Wagner,R.1818—1883年),著名德国作曲家。尼采(Nietzsche,F.W.1844—1900年),有名的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鼓吹“自我扩张”,宣扬“超人”哲学。②斯特凡,乔治(GeorgeStephan,1868—1933年),德国抒情诗人,象征主义文艺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谭注③冯特(Wundt,W.1832—1920年),德国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谭注\n《德意志史》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创造力的作品。它对经济因素的坚持、它关于有规律的心理转变的理论,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强调,都有助于扩大历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错误,它不得归入第一流作品之列。关于德国文明的整个过程之详细论述,只有通过集体的方法才能成功地尝试。兰普雷希特精通经济和艺术,但是研究政治史和宗教史的人从他的著作中所能获得的帮助却很少。该书对于学者没有什么价值,而它的大胆概括判断对初学者是一个陷阱。由于他对政治学派抱着反感,他描述德意志而没有说明她的政治骨干。他对人物因素的忽视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最后,他所用的抽象术语和不雅致的混合名词,使这部著作带有使人讨厌的气息。可是,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著作的看法如何,文化史之所以日益受到欢迎,部分是由于他的奋斗。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有才干的工作者中间,有他的门生施泰因豪森,后者于1903年创立了“文化史文库”。他最重要的专著《德意志书信程式史》,是关于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范围的漫谈。这本书的价值立即得到承认,作者在出版中世纪时代德意志书信方面获得了柏林科学院的帮助。如果说政治史和文化史有时看来是有矛盾的,那是因为对于两者所下的定义太狭窄的缘故。为了达到这个无异于纪录和解释人类生活的目标,两者都是同等需要的。时间已消除了两个敌对学派之间的猜忌:一派不一定是要忽略时势,正象另一派不一定要漠视个人。方法是跟着论题而变化的,因为文明是沿着许多路线所做的日常工作的努力与成就的结果。在历史科学这样地向各方面扩大它的优势的时候,历史哲学却落在后面了。我们继续分析、概括和思考,但它还是一项推测的工作。可是,现在虽然不可能制定出足以满意地解释人类演化的模式的规律,每个真正的历史家对于我们关于人类上升过程的知识,却都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