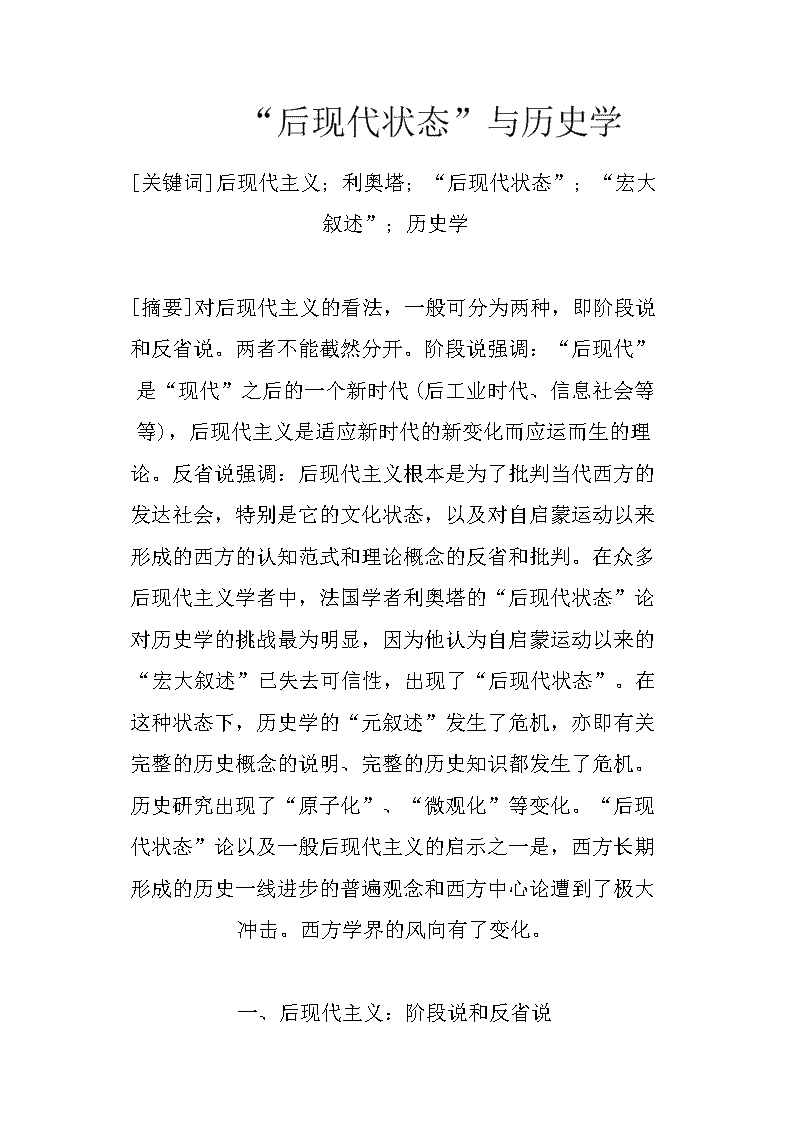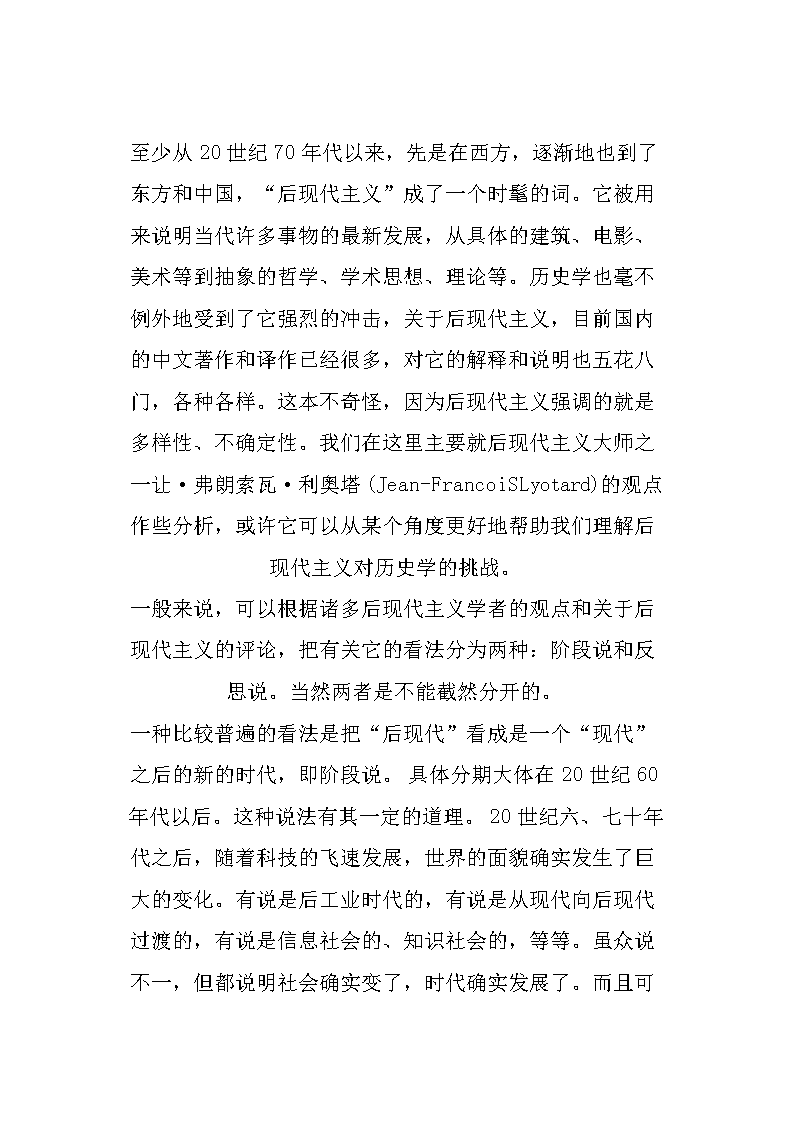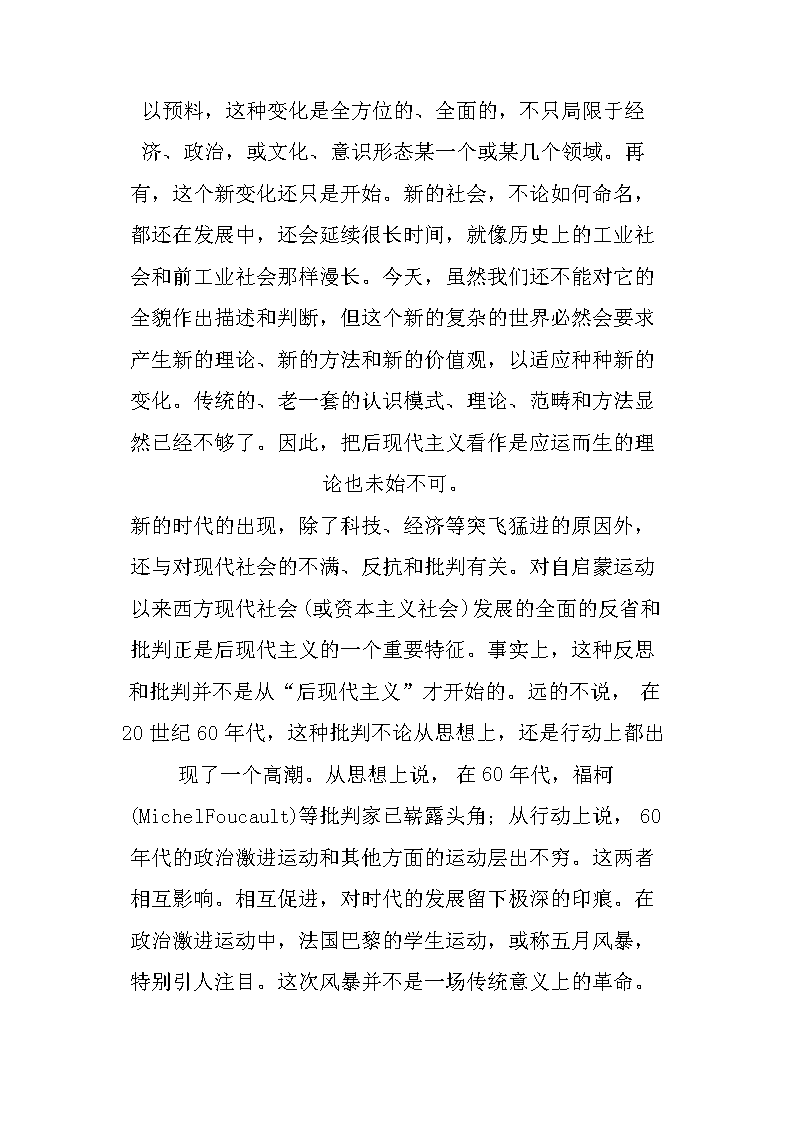- 66.00 KB
- 2022-08-18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宏大叙述”;历史学[摘要]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可分为两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阶段说强调:“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后现代状态”论以及一般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之一是,西方长期形成的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遭到了极大冲击。西方学界的风向有了变化。一、后现代主义:阶段说和反省说\n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西方,逐渐地也到了东方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它被用来说明当代许多事物的最新发展,从具体的建筑、电影、美术等到抽象的哲学、学术思想、理论等。历史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它强烈的冲击,关于后现代主义,目前国内的中文著作和译作已经很多,对它的解释和说明也五花八门,各种各样。这本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就是多样性、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主要就后现代主义大师之一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的观点作些分析,或许它可以从某个角度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一般来说,可以根据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把有关它的看法分为两种:阶段说和反思说。当然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现代”\n之后的新的时代,即阶段说。具体分期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说是后工业时代的,有说是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有说是信息社会的、知识社会的,等等。虽众说不一,但都说明社会确实变了,时代确实发展了。而且可以预料,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全面的,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再有,这个新变化还只是开始。新的社会,不论如何命名,都还在发展中,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就像历史上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那样漫长。今天,虽然我们还不能对它的全貌作出描述和判断,但这个新的复杂的世界必然会要求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以适应种种新的变化。传统的、老一套的认识模式、理论、范畴和方法显然已经不够了。因此,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应运而生的理论也未始不可。新的时代的出现,除了科技、经济等突飞猛进的原因外,还与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反抗和批判有关。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n才开始的。远的不说,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批判不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出现了一个高潮。从思想上说,在60年代,福柯(MichelFoucault)等批判家已崭露头角;从行动上说,60年代的政治激进运动和其他方面的运动层出不穷。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时代的发展留下极深的印痕。在政治激进运动中,法国巴黎的学生运动,或称五月风暴,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风暴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参加风暴的学生和工人都没有推翻和夺取政权的纲领,但它对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生们强烈反对传统价值,摒弃教授及前贤们的经验,尽管从表层上看显得有些粗糙、绝对,但从深层上却极大地促使社会生活的改变,尤其是思想的解放。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法国形成高潮并不是偶然的。福柯、德里达(JacquesDerrida)、利奥塔、鲍德里亚(JearlBaudrillard,又译布希亚)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可谓如鱼得水,大显身手。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发生五月风暴的1968年,在《Manteia》杂志第5期上,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发表了名为《之死》的文章,声称“”是属于现代的;随着现代的结束,“”就死了。未来的文字的全部多样性集中在一个固定点上:这已不是至今一直认定的“”,而是“读者”。除了法国的学生激进运动外,美国的反战运动也是风起云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兴起的嬉皮士运动。它是对历史形成的社会准则的否定。这时出现的“性解放”和“性时尚”也在社会性别问题上掀起风波。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则预示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n所有这些变化,虽然从表面上和性质上看,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都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已经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文明过渡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文明过渡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这种深刻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社会人文科学家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上述种种社会变化和政治激进运动等运动作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就主张这种“后现代”阶段说,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美国的伊哈卜·哈桑(IhabHassan)、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等,尽管各人涉及的领域和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然而,不同意这种“阶段说”,或者认为,主要不应强调“阶段说”的也大有人在。如有的学者指出,把“现代”和“后现代”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本身就受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即把历史的演化视为一种一线发展、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摒弃这种历史观念,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多元的、开放的过程。”因此,“不应该把‘现代’与‘后现代’视为是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视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省”[1]。也有学者认为,不宜把“现代”、“后现代”\n仅仅理解为先后出现的历史分期,而只需看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衔接关系,即“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概念之后,是建立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之上[2]。的确,仅仅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时间上连续的两个历史阶段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传统的认知范式,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如普遍理性、科学主义、进步观念、自由理想、实用主义等等。对这些概念的怀疑和质难并不都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如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不少西方的思想家对“普遍理性”表示怀疑。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加深了这种怀疑。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这种种怀疑的集大成者。它的怀疑是全面的,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要对西方“现代”的人文传统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和改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的那些传统概念已经不能认识、解读当今的世界。对过去的认知范式、已有的文本和话语、原有的知识体系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重新的审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要做的工作。\n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主要意味着一种认知范式上的、文化和意识上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式的、有规律的、线性的、有序的、进步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而特别强调的是多样的、随机的、独特的、另类的、相对的、个人的、能动的观念。虽然具体到人文科学各个学科,在这些观念的变化上还有不少争论和程度的不同,但总的趋势应该是清楚的。从总体上说,这种趋势反映出当代的学术思想对传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的批判和扬弃。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当代在认知范式和文化意识上发生的一种普遍过程。这是旧的文化范式的被打破,并由此引起的人文知识认知论基础的更新。这样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及其带来的变化或许可以看得更深入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那么从众多的对它的概念的解释和定义中,至少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思潮,一种学术思潮、文化思潮,或者文化运动。俄国学者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写道:“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文学批评、艺术和哲学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它的形成与一系列法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和学者(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西利斯·米勒尔)的活动有关。从70年代末起,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开始在民族学、史学理论中显现出来,后来也在历史学中显现出来。”\n[3]这位学者的概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致的轮廓,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以上我们对如何理解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作了一些解释。下面,我们想选择一位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具体分析一下他的观点,作为个案,可以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述的实际感受,看看他们是如何展开阐述的。我们选择的这位学者是法国哲学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并不少,他们的观念又各不相同,因此,选择利奥塔并不是因为只有他才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他的观点不仅很有影响,要探讨后现代主义问题是无法绕开他的;并且,他的观点也便于我们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和冲击这个我们关注的题目。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概念“后现代性”一词并不是利奥塔首先提出的,但他赋予了这个词以独特的含义。在他著名的论文《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4],利奥塔对此作了系统的阐释。这篇论文是利奥塔在1976年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后现代的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n前面已经说过,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指对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认知范式的反省和批判。那么,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如何体现的呢?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说,人类的认识世界的活动的最基本的体现,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的形成途径,都离不开“知识”(knoacy)问题。所谓“知识的合理性”是指知识是否被认可为是“知识”,如果它被认可是“知识”,那它就有了“合理性”,它的存在的理由就得到了确认。而这个知识获得“合理性”的过程就被称为“合理化”(1egitimation)。这个“合理化”过程是长期的、不易发现的。长期以来,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就是“知识”,似乎自然就是如此,不成问题。利奥塔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知识的“合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了解“知识”“合理化”的过程,了解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程序,才能知道这种“知识”获得“合理性”的原因、它目前的状态和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第二:个是“知识”与“叙述”(narrative)的关系问题。利奥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还需要从知识内部来进行考察。这就牵涉到“叙述”问题。因为,“叙述”是“知识”使别人和自己认识到它确是“知识”的必要手段,而且,“知识”在“合理化”过程中对“叙述”的依赖越来越明显。现在的问题是,“知识”需要依赖“\n叙述”来表明自己是一回事,“叙述”能不能使“知识”“合理化”是另一回事;或者说,“叙述”本身有没有“合理性”以致可以成为“知识”“合理化”的根据。利奥塔认为,这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所在。在利奥塔看来,各类“知识”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discourse)活动。在20世纪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依仗某些“宏大叙述”(grandnarrative)而进行的,并构建起一套“元话语”(meta-narrative)。这时,“知识”是凭借某种“宏大叙述”使自己获得“合理性”的。“宏大叙述”是“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利奧塔把这一时代称之为“现代”、“现代性”或“现代状态”。他写道:“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宏大叙述时,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理化的科学”[5]。也就是说,“现代”就是指这个时代的“知识”可以从它所属体系或所依赖的体系本身获得“合理化”的根据。与此相反,当20世纪发生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后现代”就是对这种新状态的表征。因此,“后现代状态”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宏大叙述”\n的怀疑。利奥塔写道:“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述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所谓“元叙述”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本体论性质的叙述。从西方哲学史上可以看出,“元”也就是“形而上”的意思,也就是建立在惟一的起源、基础和出发点之上的叙述。“元话语”也是这个意思。“元叙述”发生了危机,这就是利奥塔所谓的“后现代状态”。而对“元叙述”、“元话语”的怀疑便导致建立在“元叙述”、“元话语”基础上的整个知识大厦发生了时代性的危机。利奥塔强调,所有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统统失去了原有的可信性(credibility)。利奥塔把这种叙述的衰败称之为“合理性的解体”(delegitimation)。在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宏大叙述”,可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或“元叙述”)以及黑格尔的“宏大叙述”(“元叙述”)为例。黑格尔的“宏大叙述”主要以观念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体现在他的《哲学全书》中。至于启蒙运动的“元叙述”主要是启蒙理性。它朝向一个美好的空想世界。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就是以这种理性的“元话语”来作为衡量“合理性”的标准的。至于在“宏大叙述”衰败的“后现代状态”下“知识”的特点,以及利奥塔与其他学者的争辩等等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n三、“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既然“后现代状态”的特征是所有“元叙述”的危机,那么联系到历史学又有哪些影响呢?具体到历史学,除了有启蒙理性或黑格尔的“宏大叙述”的影响外,历史学中的“元叙述”还指对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这套说明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元叙述”实际是指历史学家提出的那套完整的历史知识。要说明的是,“元叙述”比起历史理论来要更为广泛。历史理论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反省。这种反省是完整的,经过思索的,是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元叙述”概念比历史过程理论要广泛。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理论都是“元叙述”,但不是任何“元叙述”都有理论的特性。总起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元叙述”是对历史(主要是历史过程)的一套完整的说明,它常常带有理论性。那么,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危机的表现何在?所谓“元叙述”危机的表现,一是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失去了“元叙述”的功能。在这点上,在学者们中间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种功能是完全失去了,或基本失去了。有的则认为,只是部分地失去了。但总的说来,强调“元叙述”\n功能的丧失或削弱,都是指那种构建完整的或宏大的历史过程解释的努力已经不时兴了。这就涉及“元叙述”危机的另一表现,即历史知识的个别化,历史知识的个人的—心理的功能和社会的—整合的(或分解的)功能的强化。顺便说一句,早在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NietzsChC)就预见到了这种变化。总之,“元叙述”危机导致历史知识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变化,导致历史学的重心从社会—政治任务向个人的—心理的任务的转移。这就使得社会中分解的倾向得到强化。问题是这种历史知识的“原子化”是否意味着方法论的退化,有没有克服危机的方法?由于“后现代状态”下的历史学是一个新的问题,又由于“后现代”原本就反对绝对化、明确化,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历史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讨论若干有关的问题。我们先要看一看在近代形成的群众性历史意识与职业历史学相互关系的机制此时是否还起作用?答案是:它们还在起作用。但是它们在“后现代状态”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个过程的。下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些变化。首先,历史学提供劝谕性榜样的功能。这是历史学最稳定的功能。在“后现代状态”下,它能否还保存下来?按理说,当“元叙述”\n失去其可信性时,历史学即使还保存某些知识,也很难是科学的。自然,历史学会作各种努力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图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近段时间热门的“微观史学”流派和“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冲突。微观史学家在实践微观史学的同时,总是强调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必要性。本来,说明语境的技能是正常的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之一。对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来说,它的最主要的原则虽是区分过去和现在,但同时必须构建历史语境。这些都是正常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至于微观史学,当它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微观事物、“突发事件”时,如何说明宏观的历史语境呢?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成功的范例呢?很遗憾,虽然“微观史学”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也有许多杰出的作品,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说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微观史学”是不可能的[6]。其次,历史学的认同功能。“历史”的概念里包含有一定的寻找“认同”的手段,或者说,“历史学”负有认同的任务。这种寻找“认同”的手段是与“记忆”的一定的“书写形式”的历史类型有关。在“后现代状态”下,这种“认同”功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记忆已不再成为“认同”的基础[7]。这位学者认为。在“后现代状态”\n下,每个人是在同一的文化空间形成自己的认同的。在这个实质上:是同一的文化空间中,不仅有西方古代的圣贤,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而且同样有东方古代的圣贤,如老子、孔子。因此,近代形成的基本上以民族—国家边界为界的历史记忆就不起多大的作用。总之,可以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记忆的类型确实发生了变化。它从原有的历史类型向新的类型转变。前者是为社会在历史空间的集体认同服务的,后者则为在所有文化空间内的个人的认同服务的。总之,在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发展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解决宏观语境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也有学者对利奥塔关于“元叙述”不可信的观点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历史学需要某种整合材料、编织情节的叙事前提。“这就是说,虽然元叙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处,元叙述仍是历史编纂必不可少的认识整合力量。而且,元叙述本身也具有历史性,新的历史经验需要新的解释根据和理由,人们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8]这位学者还引用雷迪(].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3.[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27.[3]Ю.Л.ВессмертныЙ,“некоodemConditi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4.[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n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40,1—2,2.[6]См.н.Е.Колосов,Оневоэможностимнкро-истории//Казус-2.[7]См.м.Ф.Румяндева,Теория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22.[8]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15.[9]FritzStern,ed.TheVarietiesofHistory.ClevelandandNewYork,195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