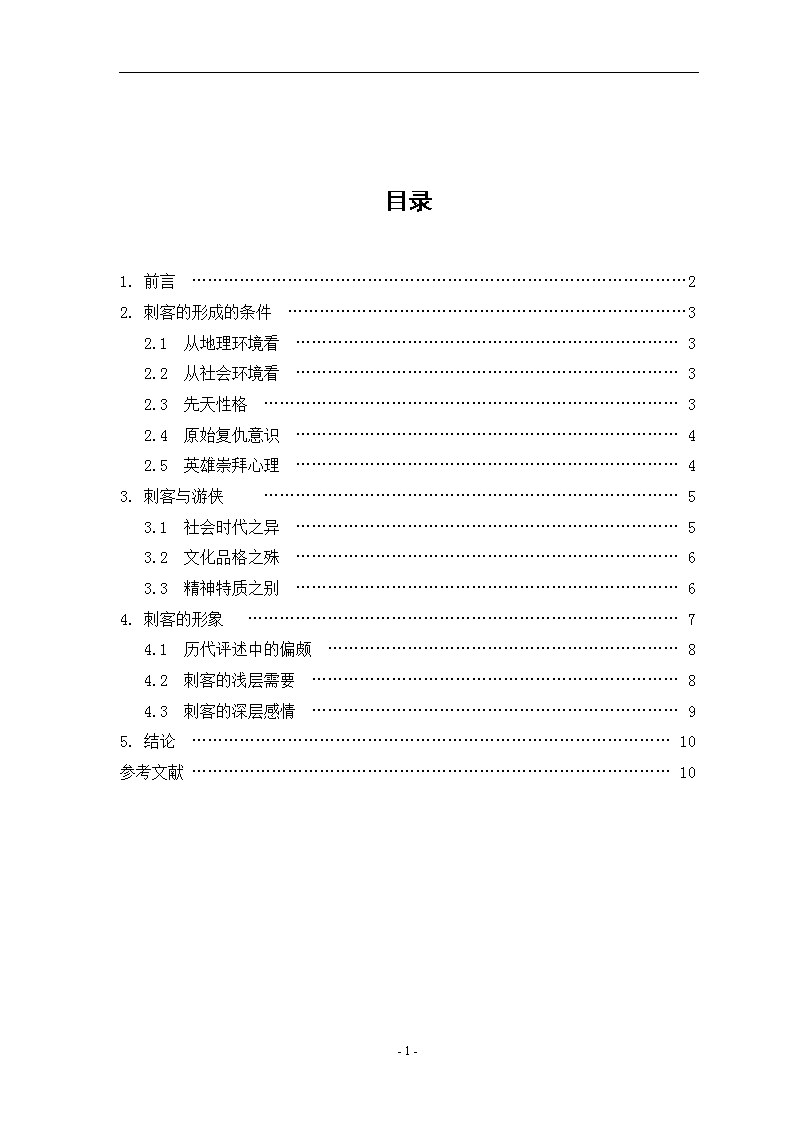- 73.00 KB
- 2022-08-18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为刺客正名——从《史记·刺客列传》谈起摘要本文从社会学及文学的角度,以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为中心,从环境以及气质、原始复仇意识、英雄崇拜心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刺客的形成原因。以文本为基础,从时代背景、文化、以及气质等几方面把游侠与刺客做出区别。再以历史评价的欠缺、基本人性、和深层文化的角度去分析的刺客悲剧英雄形象。关键字《史记•刺客列传》游侠悲剧英雄ABSTRACTBasedonsociologyandliterature,ShihchiAssassinBiographyasthecenter,thepaperstudiescauseofancientChineseassassinsfromtheperspectivesofenvironment,temperament,originalrevengeconsciousness,andheroworshippsychology.TheauthormakesadifferencebetweenPaladinsandassassinsfromtheanglesofbackground,culture,temperament.Also,thethesisanalysistheimagesofassassinsfromthestandpointofdeficiencyofhistoricalevaluation,basicHumanityanddeepculture.KEYWORDSShihchiAssassinBiographyPaladinsPragedyhero-14-\n目录1.前言…………………………………………………………………………………22.刺客的形成的条件…………………………………………………………………32.1从地理环境看………………………………………………………………32.2从社会环境看………………………………………………………………32.3先天性格……………………………………………………………………32.4原始复仇意识………………………………………………………………42.5英雄崇拜心理………………………………………………………………43.刺客与游侠……………………………………………………………………53.1社会时代之异………………………………………………………………53.2文化品格之殊………………………………………………………………63.3精神特质之别………………………………………………………………64.刺客的形象………………………………………………………………………74.1历代评述中的偏颇…………………………………………………………84.2刺客的浅层需要……………………………………………………………84.3刺客的深层感情……………………………………………………………95.结论………………………………………………………………………………10参考文献………………………………………………………………………………10-14-\n为刺客正名——从《史记·刺客列传》谈起1.前言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刀光剑影、群雄逐鹿,恰是我国社会形态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乃至最终确立的时期。在这时期,有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大多没有文化不高而又没有多少的家财。他们空有一腔凌天之志,一身高超武艺而却得不到别人赏识,他们执着而热血,义薄云天,士为知己者死!却只能生活在黑暗当中,被人误解,被人遗弃。他们是独行者,他们就是刺客!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是一篇类传,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正是在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相继浩然登场,定格下一幅幅悲壮淋漓的历史画面,留下先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当今的刺客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流变过程,其社会属性和精神风貌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的中国古代侠义刺客在精神人格和行为方式上已经相去甚远。而基于此种变化,和世人的误解,那么就有必要去通过重新解读刺客而为其正名。学术界对于刺客的形象从古代到现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袁行霈先生“认为刺客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三章))翦伯赞(先秦史)则认为“作了封建专制主义奠基典礼中的‘人祭’”无论是褒贬的评论都不可能否定刺客在历史中留下的深深的痕迹。赞之是感慨其悲壮之情,而贬之不过是叹其过于血性愚忠。刺客更多会和游侠共同出现,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却不同之处。刺客和游侠的关系在学术界中同样是争论不休的。有些人认为刺客是游侠的一部分,如韩云波[9]、江淳[10]有些人认为游侠是养客的,而刺客是游侠所养的部下,如钱穆。[11]陈克标(游侠与刺客之辩)更认为获得报酬而杀人的就是刺客,因“士为知已者死”的是游侠。-14-\n刺客的形象是正面的,他们与游侠相似却不同。他们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是悲剧式的英雄。是政治与复仇者得工具,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本文将总结前人的评价,结合刺客形成的条件和游侠间的本质区别,从人性出发,将刺客形象层层剥离进行解析,或许会对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形象及其精神气质,产生较为客观的认识,获得新的体验。2.刺客的形成的条件要了解刺客,必须要去了解刺客的出现原因。我分为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先天性格原始复仇意识和英雄崇拜心理五个方面去进行刺客成因的解读2.1从地理环境看。一般而言北方的汉子是比较豪爽,侠义的,如东北汉子。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方边地和少数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久而久之,就会沾染上少数民族尚武的风气个性变得的豪迈,侠义。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就是春秋末期晋国的一个刺客中原其他周边少数民族也对中原的尚武精神起了推动作用。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就分析了一定的精神风貌产生于特殊的地域,并且被该地域的人加以实践,同时对其产生影响,像他在文中写道,“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监。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郑、卫、赵一带人多任气好侠;越、楚一带民风剽轻;容易发怒;南阳在秦末以后由于迁入不少不轨之民,故而民风、民俗较为繁杂,人们也多有一种豪爽之气2.2从社会环境看。在人口密集和流动性大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孕育强悍好斗,刚烈竞争的习俗,也会促进任侠尚武、恃力好强风气的蔓延。司马迁在《史记·-14-\n刺客列传》中写到的聂政就是魏国人;而荆轲虽为战国末期齐国人,但是后来却是游于燕、赵一带的。这些也在一个侧面说明刺客生活的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对他们最后走向刺客的道路有一定的影响,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条件。此外,一般人似乎认为只有北方人才具有一种豪爽之气,从通常情况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分析和解释为何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还有不是出自上述那些北方边地的。在司马迁所写到的刺客中还有一个是专诸,他是吴国人。其实如果从人口密集供养不足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就不难理解了。以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可以统摄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下。所有这些方面也在另一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有一种尚气任侠、剽悍勇猛的环境氛围。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这些刺客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样一种环境氛围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群。这种尚气任侠、剽悍勇猛的风气也积淀在了当时不少的人的内心,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极具特色的心理特征。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只是属于外部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人自身的先天性格。2.3先天性格先天的遗传和个性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个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除了后天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努力外,其先天遗传的气质特征和个性特点也是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最后成为刺客的一些人,除了在客观因素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之外,在他们主观的气质特征方面也存在着近似的一些可以分析的特点。可以认为一个性格内向,而且怯懦胆小,行动畏缩的人是很难最后成为一名刺客的。一般来讲,刺客在的心理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刚猛好动,行动果断。行为往往超出常人的水平,具有极大的张力,有一种打破现有格局的倾向。他们往往好竞争,多豪气,较偏执,渴望个性的彰显和社会对他们的价值认同。像《史记·刺客列传》中大多的刺客都具有类似的性格特点,最有代表性的就算荆轲了。荆轲是战国末期齐国的,后来游于燕、赵一带,曾与盖聂论过剑,也常常与一些博徒混在一起,并且与当时善于击筑的高渐离关系要好,经常在燕市纵情狂欢,酣饮尽兴之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引吭高歌。由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他的气质中就有一种率性而为,狂放疏朗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也是那些奉行社会礼法的人做不到的,因而他们也往往与主流社会背离。基于以上,可知,刺客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除了和社会的大环境氛围有密切关系外,还与个人的气质特征有关。-14-\n2.4原始复仇意识刺客的出现与一种原始复仇有关,而原始复仇中,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一种血族复仇。复仇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彼时的复仇是以血族复仇的形态出现的。横死者要求本氏族成员为自身讨还血债;“以血还血”的信念强固了氏族群体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建构了复仇伦理。到了周秦极其以后的宗法社会,复仇演变为为家族、家庭成员雪恨即血亲复仇。古代中国血缘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一族之人按照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彼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为亲人复仇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观念造就了现实中血亲复仇的持久与普遍受推重。这样一种重视复仇的思想,经汉人的复仇世风传递,逐渐形成以能否完成血亲复仇的义务来判断其人的道德品质的评价标准。在这样的复仇中,复仇主体一般都秉承着极大的孝心和忠心,竭尽自己的所能,甚至是生命去实践自己的诺言。在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复仇思想的传承中,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除了这部分血亲复仇以外,侠义复仇的观念也开始逐步出现。复仇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比方说,替亲人复仇、替朋友复仇,替恩主复仇等。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就涉及到这样几个侠义复仇的刺客。曹沫之劫持齐桓公,使之尽数归还所侵得的鲁地;专诸刺吴王僚,使公子光合法继位得以实现;豫让的行刺赵襄子,是为恩主智伯报仇;聂政杀死韩相侠累,乃是为报答严仲子礼贤下士;荆轲的行刺秦王政,也是为了酬报太子丹恩遇。今天看来,这五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一种侠义复仇的意识。在这些复仇之中,刺客本人并没有与其刺杀目标有矛盾冲突,也与要求刺杀之人没任何的血缘关系,只是充当别人的复仇的工具。而由于仇恨的双方可能是自己能力不足或需求保持自身光辉形象等原因不能自己亲自的复仇,那么,代替别人复仇的人就出现了。刺客就是这类人当中的代表。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基于复仇的需要,许多代人复仇的人群出现了,而刺客也在此前提下应运而生。2.5英雄崇拜心理一定社会的文化心理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分析刺客的成因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先民的英雄崇拜心理的探究。-14-\n中国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过程中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先民的原始生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人们的个性和生命意志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整个人类社会也和中国一样经历了这个极具竞争和挑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经常发生。在风云变化的时局环境中脱颖而出了一批杰出的英雄人物,他们大都具有非凡生命力,超出常人的胆识,高度智慧的头脑,坚决果敢的魄力,任气尚武的精神。汪涌豪也曾提到,这个民族的整体充满一种任强尚力的原始激情,因崇拜英雄造致的神秘狂热,竟使这崇拜以极大的张力,延伸到民族文化的每根神经。[2]有时唯有崇尚强力,才能将秩序、法律以及对别人的尊重,真正灌输到那些刚从生活不安定的自然状态中摆脱出来的人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特点和刺客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春秋战国时代,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恰恰这样一种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更召唤少数改变时局的英雄出现!这个时候,细腻的、思致的、温和的、浪漫的一些情怀都不能使当时的许多人在四面楚歌的动荡中突围出来,即就是伟大的孔子也一样没有做到。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孔子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梦想的英雄”!但是他仍然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序和动荡。这个时候,整个时代呼唤着英雄的出现,去变革现有社会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轨礼法、敢于抗争的一些人出现了,比方说当时的不少侠义之士。在他们胸中存在着狂热和激情!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侠义和忠烈!在他们心里涌动着尊严和报答!他们冲决开一切社会的法律和禁令的束缚,走向了彻底的释然!这个时候他们俨然成了自己灵魂和内心律令的主宰!一种英雄的意识被唤起。刺客也正是受这样的英雄意识感召的一群人。因此我们说,潜藏在先民文化心理中的英雄崇拜意识也对刺客的出现以及他们后来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刺客与游侠游侠与刺客的关系学术界没有一致的意见,甚至古代的学者也没有一致意见。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随着历史推移,“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由于刺客与游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将会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精神特质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分析二者的差别。3.1社会时代之异-14-\n《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3.2文化品格之殊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14-\n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扞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3.3精神特质之别-14-\n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客”因勇显而“侠”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14-\n“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4刺客的形象“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陶渊明全集》)自太史公后,世人从未停止过对这一特殊群体形象的褒贬。誉者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广志绎·卷二》)“勇者之圣也”,(《抱朴子·卷十二》)盛赞其为“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5〕抑者则谓之“勇且愚”,(《柳宗元集·卷四十三》)“作了封建专制主义奠基典礼中的‘人祭’”。〔6〕我们不能否认刺客是血腥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理论上说,对人物形象及其精神价值的评论试图做到黑白分明本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结合文本的基础上,将他们从“基本人性”、“深层文化结构”,这样两个层次层层剥离,而不是以“天生的英雄”、“神人”的标准来评判他们,那么,他们有高尚的一面;也有庸俗的一面,有伟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这样,对《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形象及其精神气质,我们或许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获得新的体验。4.1历代评述中的偏颇司马迁把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类传四种。《刺客列传》是属于其中的类传,采用这种方式为人物作传是司马迁的首创,这一类的传文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的,运用到《刺客列传》中,使得刺客的群体形象和文化精神特征明显,非常醒目;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阅读者首先就把这一群体形象定位在“悲剧英雄”的层次上。再加上太史公在文后的论赞中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读到这里,就在客观上促使阅读者产生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英雄与否的评判冲动。清代刘鄂曾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14-\n(《老残游记·序》)章太炎也提到:“《史记》刺客、游侠诸传,极形容之所事,史公意有不平,故为此激宕之文,非后人所当仿佛者也。”(《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所以,太史公论赞的文字中带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倾向是很正常的。对于阅读者而言,产生这种评判的冲动也是很正常的,在这种冲动之下,自然促使阅读者再回过头去对照原文,寻找其英雄与否的证据,而忽视了刺客首先是人,他们身上理应具有人性的基本特点的事实。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评价:比如,“荆轲、聂政,勇敢之圣也。”(《抱朴子·卷十二》)“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5〕当然,也有了这样的评论之辞,“荆轲怀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资治通鉴·卷七》)又有:“阖闾富,故能使专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能使荆轲杀秦王政。”(《新书·卷四·淮难》)在先入为主的评判冲动下,产生诸如此类的评论并不奇怪。先入为主的评判冲动容易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是认定他们就是天生的英雄、义士、勇圣,从而无限拔高,遂有溢美之辞;另一种则是由于对英雄的期望值过高,潜意识里用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神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尤其对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太子丹的金钱往来关系颇多微词。4.2刺客的浅层需要从“基本人性层次”来考察一下《刺客列传》中五名刺客的基本情况,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五刺客中,除了曹沫本为鲁将,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外,其他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闾巷之人。根据马斯诺著名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受到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人只有满足低层次需求之后才会逐步追求更高层次需求。而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也就是为保障生存的物质需求。所以,从“人性基本层次”来看,五刺客对生存的物质需求显然是必要的。就这些引起争议的内容,我们回过头来看《刺客列传》中的记载:关于曹沫的记录比较简单,就他和鲁庄公的关系只提到曹沫有勇力而庄公好力,曹沫三败后庄公仍复以为将,没有直接记录他们之间物质往来关系的文字。关于专诸的记录,引起对专诸非议的大多就是那一句:“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在文中对此没有任何评价。关于豫让的记录,容易引起非议的就是“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史记·刺客列传》)至于怎么个尊宠法,文中没有说明,只是从豫让的话:“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14-\n(《史记·刺客列传》)隐约可见智伯待豫让不薄,而这个“遇”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往。对豫让的这些基本情况,司马迁只是记录,没有评说。对于聂政的记录,引起争议的多是“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也没有直接评述,只是末有一句世人之言为“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对这些内容做了记录,但无评说。至于荆轲,引起的争议更大,且被称为豢养,大致也是从文中“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史记·刺客列传》)得来。但所有的这些文字,都是记录性的文字,司马迁并没有对此有任何褒贬。从人的需要理论来看,刺客与贵族之间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论是纯物质的还是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都是符合人的基本需要的,人既需要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也需要来自外界的重视,而从《刺客列传》中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录来看,也正体现了司马迁作《史记》的“实录”精神。这样的“实录”或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它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完美,它让我们难以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一锤定音的评论。然而,这在作为“人性基本层次”上却是真实的,因为在现实中,很难从头到脚地把人的好与坏做一个彻底的分界,也很难用一个完美的标准来评论真实的人。而它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真”的体验。4.3刺客的深层感情五刺客的故事能流传千古不衰,无庸讳言,最吸引人的是他们身上客观体现出来的,历来被中国人所看重的精神价值———义。司马迁在论赞中也说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望也哉!”而这个“义”归根到底是通过刺客的“士为知己者死”体现出来的,当然,“士为知己者死”也是司马迁的人际关系理想,不管这种理想在今天是否值得赞同,从“深层文化结构”层次来看,它是客观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对于人际关系的普遍理想,因此也打动着中国人的心。那么,为什么“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能打动中国人的心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会发现中国人是用二人关系定义一人的。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8〕这种相知相识的真挚情谊在我国历史上古已有之,例如:《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14-\n,传达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意。伯牙与钟子期的千古知音佳话,更让人思慕上古淳朴至诚的“知己”之交。到春秋战国时期,“知己”便成为士人进身的独特方式,及至纵横家言的《战国策》,已明确提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赵策一》)的口号,所以说“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早已发端,到了司马迁这里,尤其是在其所作的《刺客列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刺客列传》中寄寓“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呢?作为《史记》作者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恰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形成大一统的时期,所以他首先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已经具有了“中国人”的深层文化结构特点,因此对这一传统的人际关系理想有所继承不足为怪,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把“士为知己者死”标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促使他有此动作的,与他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这个准则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他说;“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而根据《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第七年,遭李陵之祸所累,被处以腐刑,《报任安书》正是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的惨痛教训之后写的,鉴于自己遭祸之时,亲朋不救而惨受腐刑的遭遇,司马迁对人情关系重新进行了反思与审视,面对西汉时代日益权势相倾、人情冷漠的现实,加之自身遭遇和痛切的感触,司马迁更加向往尊重、信任、理解等可贵的人际关系,并大力张扬人与人之间相知相识的难能可贵,这在《刺客列传》中得到了彰显。结语《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是血腥的,是政治家与统治者的工具。但刺客并不是麻木不仁的杀手。他们是热血的独行侠,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地位低下,寂寞孤独所以为“义”而无惧。为“义”而执着。刺客是不同于游侠的一类人,无论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精神特质都与游侠有着质的区别。刺客的形象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于这一方面,司马迁是“实录”的;有具有中国人的“深层文化”特征的一面,关于这一方面,司马迁在“实录”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际关系理想,具有相当的感情色彩。不论他们是否符合我们今天的“英雄标准”,但在客观上已冲破“基本人性层次”和具有中国人“深层文化结构”特点的层次,上升为让人产生“悲壮”和“崇高”的美的体验的“悲剧英雄”。-14-\n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2]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J]。山西大学学报,1995,(2)。[4]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M]。上海:上海文艺,1994。[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三章)[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翦伯赞。先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韩云波。试论先秦游侠[J].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2)。[10]江淳。试论战国游侠[J].文史哲。[1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