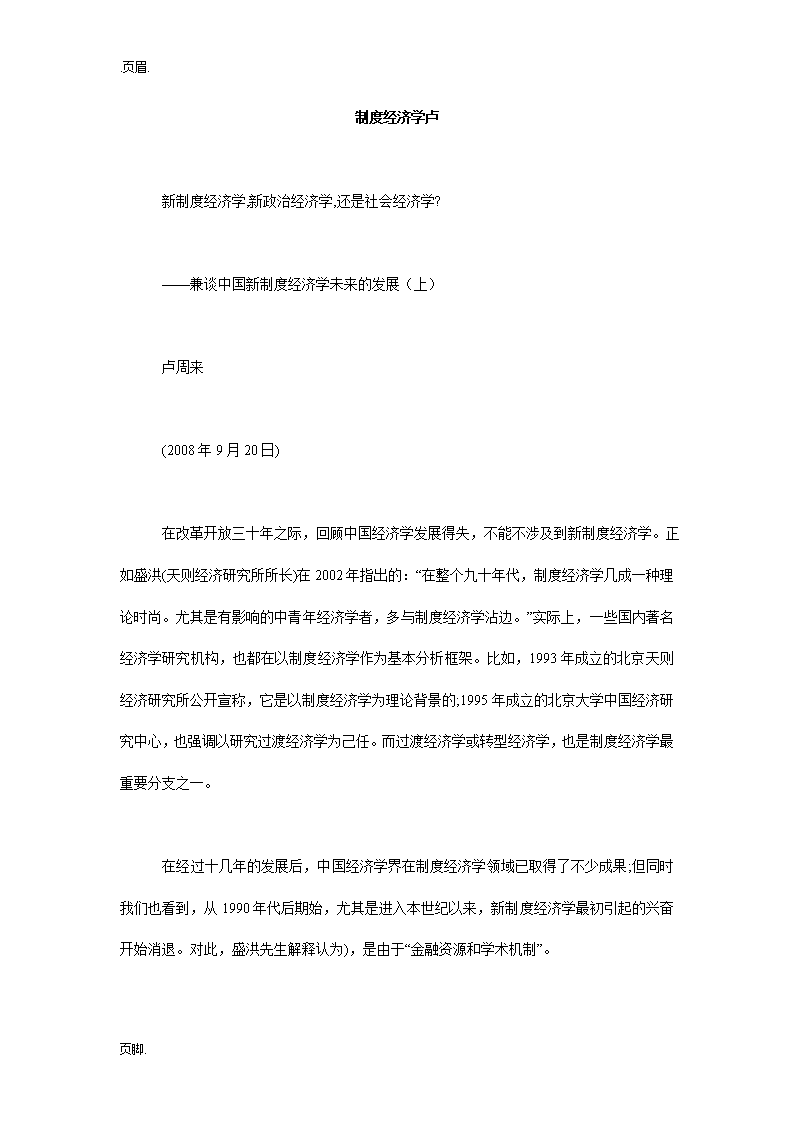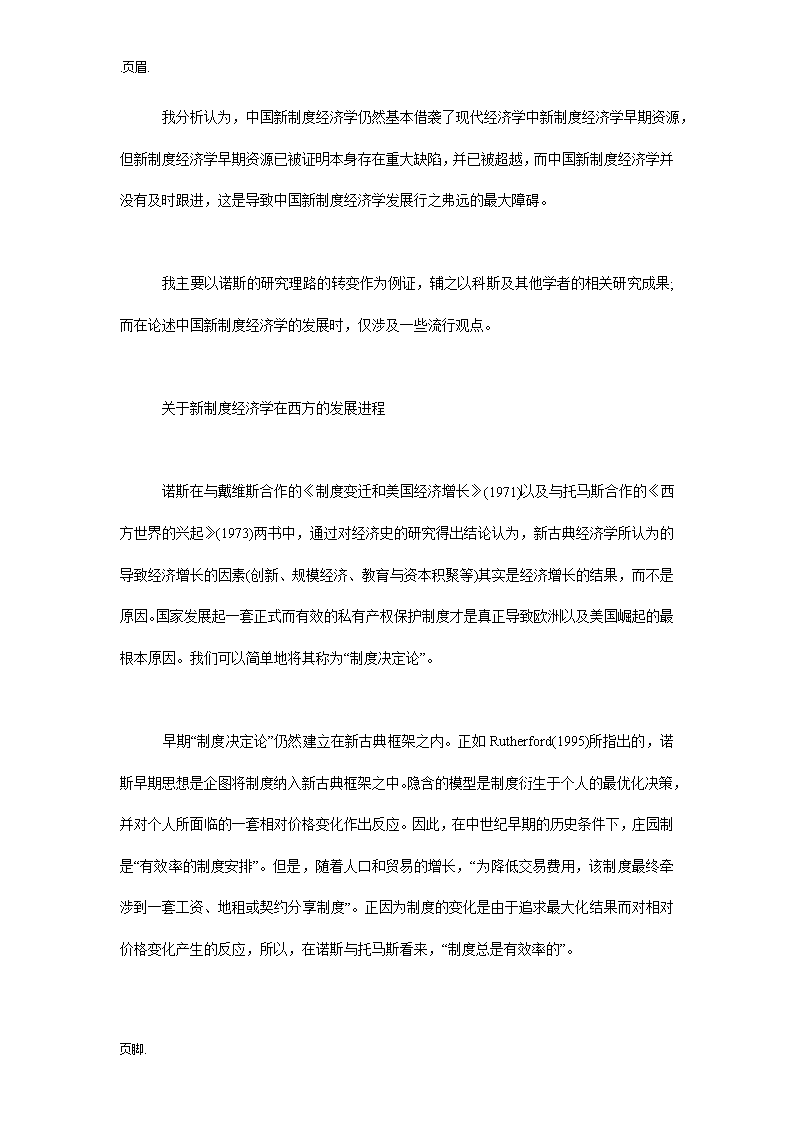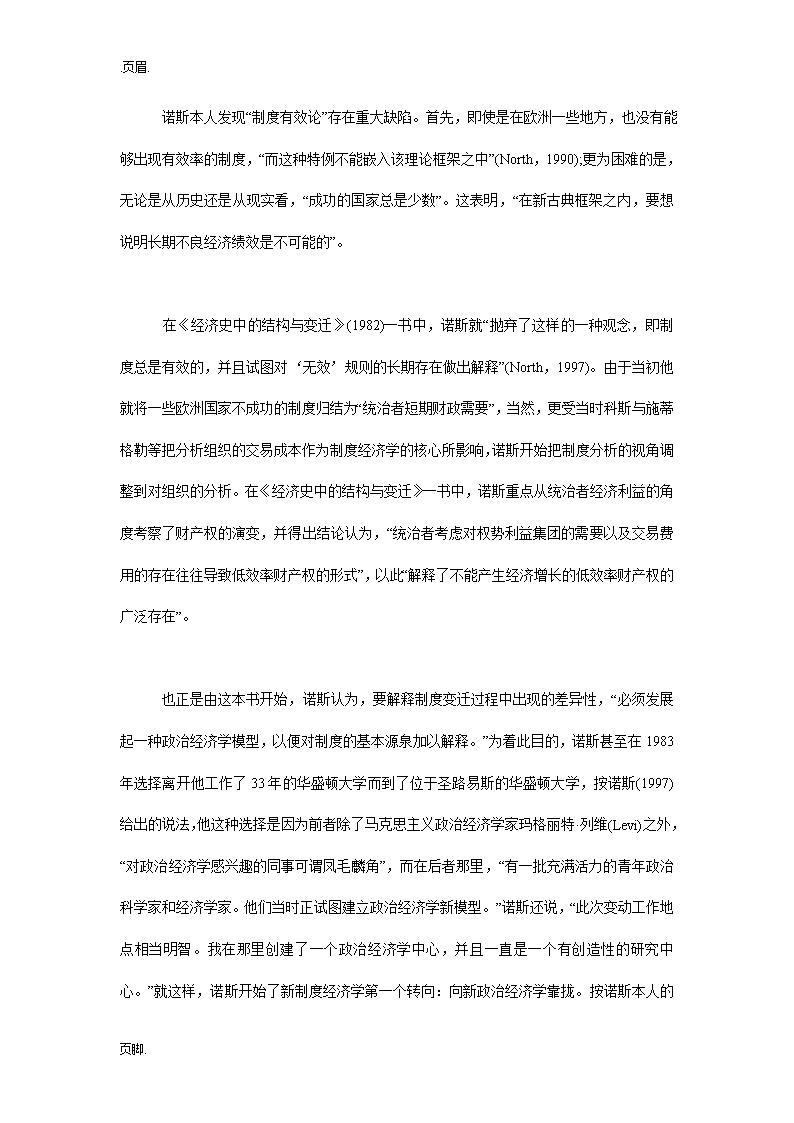- 49.00 KB
- 2022-08-22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页眉.制度经济学卢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上)卢周来(2008年9月20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得失,不能不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在2002年指出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实际上,一些国内著名经济学研究机构,也都在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比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而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也是制度经济学最重要分支之一。页脚.\n.页眉.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学界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从1990年代后期始,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对此,盛洪先生解释认为),是由于“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我分析认为,中国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基本借袭了现代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早期资源,但新制度经济学早期资源已被证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并已被超越,而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及时跟进,这是导致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行之弗远的最大障碍。我主要以诺斯的研究理路的转变作为例证,辅之以科斯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在论述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时,仅涉及一些流行观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进程诺斯在与戴维斯合作的《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1971)以及与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两书中,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与资本积聚等)其实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国家发展起一套正式而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才是真正导致欧洲以及美国崛起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制度决定论”。页脚.\n.页眉.早期“制度决定论”仍然建立在新古典框架之内。正如Rutherford(1995)所指出的,诺斯早期思想是企图将制度纳入新古典框架之中。隐含的模型是制度衍生于个人的最优化决策,并对个人所面临的一套相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条件下,庄园制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增长,“为降低交易费用,该制度最终牵涉到一套工资、地租或契约分享制度”。正因为制度的变化是由于追求最大化结果而对相对价格变化产生的反应,所以,在诺斯与托马斯看来,“制度总是有效率的”。诺斯本人发现“制度有效论”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即使是在欧洲一些地方,也没有能够出现有效率的制度,“而这种特例不能嵌入该理论框架之中”(North,1990);更为困难的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成功的国家总是少数”。这表明,“在新古典框架之内,要想说明长期不良经济绩效是不可能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2)一书中,诺斯就“抛弃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制度总是有效的,并且试图对‘无效’规则的长期存在做出解释”(North,1997)。由于当初他就将一些欧洲国家不成功的制度归结为“统治者短期财政需要”,当然,更受当时科斯与施蒂格勒等把分析组织的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所影响,诺斯开始把制度分析的视角调整到对组织的分析。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重点从统治者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了财产权的演变,并得出结论认为,“统治者考虑对权势利益集团的需要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导致低效率财产权的形式”,以此“解释了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低效率财产权的广泛存在”。页脚.\n.页眉.也正是由这本书开始,诺斯认为,要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性,“必须发展起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型,以便对制度的基本源泉加以解释。”为着此目的,诺斯甚至在1983年选择离开他工作了33年的华盛顿大学而到了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按诺斯(1997)给出的说法,他这种选择是因为前者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列维(Levi)之外,“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同事可谓凤毛麟角”,而在后者那里,“有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当时正试图建立政治经济学新模型。”诺斯还说,“此次变动工作地点相当明智。我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并且一直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研究中心。”就这样,诺斯开始了新制度经济学第一个转向:向新政治经济学靠拢。按诺斯本人的说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完全投入到发展出一套分析长期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工作中。”新制度经济学向新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产生了诸多激动人心的成果。比如,诺斯本人关于“政府悖论”以及关于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观点,为我们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分岔现象提供了一个远未穷尽的深远的视角;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旦引入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框架,其解释力已大大超出当初布坎南以及奥尔森的范围。当然,客观地说,诺斯本人在新政治经济学方向着力并不充分,而是为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进入此领域设置了路标。在诺斯基础之上,新制度经济学在政府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方面涌现出大量的文献。Furubotn和Richter(2005)所指出的,缺乏政府理论的产权理论是不完整的。同样,缺乏权力或者利益集团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完整的。Schmid(2004)则认为,制度经济学并不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其要义恰恰在于研究如何有效分配机会集的一门学科。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当时的出路在于引入新政治经济学视角,而新政治经济学受惠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同样很多。页脚.\n.页眉.诺斯本人将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看成是他整个1980年代工作的总结性成果。这本著作将此前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延伸到讨论不同的政治结构安排如何演化出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著作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型态决定经济规则”。荷兰与英国经济增长得益于进化而来的政体演化出的产权结构,而西班牙政体却导致了长期停滞。因为前者鼓励了“生产性行为”,而后者鼓励的是“分配性努力”。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或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经济停滞的原因。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这本书同时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转向: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认为它与正式规则及它们的实施特征一起界定人类行为的选择集。“单纯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不足以解释制度变迁的源泉,“观念、意识形态、教义、偏好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但是,当时也正如诺斯本人承认的(1990),“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清楚相对价格的变化同形成人们观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两者在诱致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尤其反映在他对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系的看法上。他仍然认为,“非正式规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补足或延拓正规规则。”“一种新的非正式规则均衡将在正式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正式规则用于否定和替换现存那些不再适应新演进的谈判结构的非正式规则”。而“非正式规则”演化的速度则取决于人们对正式规则学习与适应的速度。也就是说,非正式规则在此时诺斯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仍然置于正式规则控制与主导之下。但无论如何,诺斯将意识形态等视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源泉,已经再次远离了仅仅视相对价格的变化为制度变迁的源泉这一新古典框架。有三个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诺斯对于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看法有更彻底的改变。页脚.\n.页眉.第一个原因来自于他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观察。他发现,即使是美国已经给海地这样的国家留下了象美国一样的宪法政治框架与经济规则,但仍然没有导致经济绩效的改善;同时,俄罗斯复制了西方正式规则,其改革后果却是悲剧性的,这与中国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个原因来自于诺斯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在对比研究中他发现(1997),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三个原因,经济史研究中新一代学者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以及路径依赖理论方面的进展正好启发了诺斯。诺斯曾反省他那一代经济史学家时说(1997),“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史学家对这一新方法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甚至认为根本没有所谓新方法,因为经济史一直都在关注(正式)制度。而绝大多数实践者又都是坚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看不到有采用新方法的任何必要。”但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一些年轻的欧洲经济史学家上承马克斯·韦伯的思路,打破了老一代经济史学家的局限。这其中,诺斯反复提到了对他启发很大的Hoffman、Rosenthal与Greif。Hoffman和Rosenthal(1997)通过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路线的研究,论证了“路径依赖”的存在:当下的制度安排与历史是相关的。而Greif(1989,1994,1997)则通过对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不同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力图证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信仰决定了两个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差异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差距:以热那亚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信仰下的西方世界,建立了解决社会大规模交易的匿名市场交易机制;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信仰下的穆斯林世界和东方儒教国家在此方向却很失败。于是,1990年代以来,诺斯抛弃了“正式制度决定论”,转而认为(1994),“由行为者对世界的看法构成的信仰体系(Beliefsystems)及其发展方式将成为制度矩阵的最后决定因素。”而导致行为者信仰体系出现差异的关键又在于“个人通过时间获得的学习方式不同”。页脚.\n.页眉.因此,诺斯得出这样的结论(1994):“我们必须构造这样一种理论框架,它的出发点是使人们能够理解人的学习过程中如何进行的。”而为了构造这一理论,就必须借助于认知科学的进展。通过借鉴认知科学进展,诺斯与他的伙伴一起提出了一个“共享心智模型(SharedMentelModels)”:每个行为选择人都有某种认知能力禀赋,当他面临不确定性环境时,通过预期和意识采取行动,行动的结果反馈回行为人,行为人据此修正其认知;如果行为人与环境之间反复互动,就会形成一套对环境的看法以及环境所决定的行为选择集,这构成了行为人的信仰体系,以此信仰体系进行决策的模式就是其心智模型。而行为人又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中。正是在这种相互交往中,异质心智模型的参与人经过交流与交易,不仅能够间接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因此,相互交往的过程就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经过集体学习,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这一共享心智模型会稳定下来,并构成共同的行为选择集,这就是制度。正因此,制度其实是内生于共享智力模型的一套针对不确定环境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者说,制度是内生于信仰体系的。在此基础上,诺斯把此前的制度分析框架扩展为制度——认知(institution/cognition)分析框架。区别于原来的“正式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简单观点,诺斯将制度——认知框架下的制度观概括为(2003a,2003b,2005):“存在一个感知到的现实,诱发一套信仰,信仰引发形成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制度在社会空白领域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政策改变了现实,现实又返回去修正信仰。”他与合作者还用结构图直观地表达了这套框架(MantzavinosC.,NorthD.andS.Shariq,2004):“‘现实’页脚.\n.页眉.→信仰→制度→特定政策→结果(即改变后的现实)。”在诺斯那里,“现实(Reality)”有时与文化通用,是指人们可以感知到的环境,而这种可感知到的环境又是文化累积因素所决定的,当然包括了历时变化因素。因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中国人常说的“历史和当下”。在构造了理解人的学习过程的框架之后,诺斯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重点进一步往前推:制度内生于信仰体系,那么,“信仰及其演化方式就应该成为讨论的核心”。于是,在2005年他出版的《理解经济变化》一书中,他提出讨论的重点就是“信仰及其演化方式”。而因为信仰是由“现实”决定,于是,理解信仰就再度转化为“‘什么是现实’这一古老哲学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必须借助于社会科学的帮助”。1990年代以来诺斯实质上是把新制度经济学逐渐带入了社会经济学。当诺斯1990年代初期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引入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时,有人就敏锐地认识到了:诺斯有可能回到旧制度经济学。Rutherford较早指出(1995):“如果将诺斯最近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探讨同诸如凡勃伦、米契尔和康芒斯等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作一番研究,很难不对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感到吃惊。”“因为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纲领就是一种‘累积因果论’”,类似于“路径依赖论”;而且,更为相似的是,“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就是从作为文化产品的人出发,从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对行为有重大影响这一点出发”,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行为主义理论”。而我们又知道,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页脚.\n.页眉.新制度经济学转向社会经济学例证一。2005年《新制度经济学手册》的出版。开篇收入的就是诺斯新作《制度和历时经济绩效》,而手册的最后一节,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展望,收入的竟然是诺斯非常看重的Nee和Swedberg合写的论文《EconomicSociologyandNIE》。作者在文中首先论述了经济社会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复杂联系,然后提出,经济社会学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说的尖锐批评,以及将单个人的行为选择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的主张,正好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最新关切完全一致;而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分别根植于不同社会结构下制度安排中的网络、市尝企业以及其他论题,也恰好与新制度经济学未来议题构成交叉;尤其是作者本人对规则与传统如何塑造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分析,正如与诺斯关于共享心智模型的看法完成一致。此外,经济社会学中关于制度互动挑战模型、组织模型以及社会群体模型等都是对威廉姆森相关模型的扩展。正因此,作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由此表明了未来二者可能合流的方向。科斯的例证:谁在误解科斯?页脚.\n.页眉.科斯对于主流经济学竭尽全力将新制度经济学纳入新古典框架一直心怀不满。这点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注释》中就有所表露。他说:“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常被描绘成科斯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现实的了。它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世界,是我一直希望劝告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在1997年9月召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科斯再度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对其观点的误会。在接受奈等人的采访中,科斯甚至说:“我认为科斯定律的成功——因为现在到处都在讨论它——恰恰证明了主流经济学是多么的荒谬。”“如果你仔细看了《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律仅反映了前四页的内容,即仅说明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需要什么样的契约,但后面关于是什么原因妨碍了经济体的效率以及实际的经济体是如何运作的,他们都没有看到;恰前四页内容是最抽象的,而我关心的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当采访者再追问“但科斯定理的确是使你获得成功的关键”时,科斯回答说:“绝对是,但这种成功是因为错误的原因所导致的。对于那些关心成功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但对那些关心发展主题的人来说那不是什么好事。”Nye:That’sagoodsubjecttopursue.Manyeconomistswouldsaythatsincethepublicationofyour1960articlewhichcontainedthegermofwhatpeoplecalltheCoaseTheorem,ithasbeenassimilatedintoeconomics,andyetyouaresuggestingthatthecombinationofeconomicsandthelawhasnotbeenwelldoneyet.Couldyoucommentonthewayeconomistshavetakenyourworkanddevelopedit,versusthewayyouwouldliketoseeitdeveloped?IthinkthesucceoftheCoaseTheorem—becauseit’sdiscussedallovertheplace—isaninterestingillustrationofwhat’swrongwitheconomics;because,ifyouread“TheProblemofSocialCost,”itoccupiesperhapsfourpages.It’suseful.Ithinkit’susefulbecauseyoucanshow,usingit,thetypeofcontractsthatwouldhavetobemadeinordertohaveanefficienteconomicsystem.Butthenyouhavetointroduce,havingdonethat,theobstaclestodoingit.Thenyouseehowthesystemactuallyworks.Butmanypeoplehaveonlyreadthefourpagesoronlythoughtaboutthefourpages—oneofthereasonsthey’vedonethat,ofcourse,isit’sthemostabstractpartofthearticle.科斯的例证:科斯主张什么?页脚.\n.页眉.新制度经济学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他呼吁:不仅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可以应用经济学工具,更应该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成果应用到新制度经济学中来。他还特别对采访者说:“没有一个普世的办法去改善经济制度,因为一切取决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因此,当向一个国家提出建议时,“最好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特别是其社会制度。”而在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时,“最好首先分别研究清楚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而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并没有研究清楚这些问题。”Nye:Accordingtothetypical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rescription,neoclassicaltheorysuggestsstepstofollowtowardamarket-orientedeconomy:privatization,deregulation,macroeconomicstability,andsoon.Isthatenough?Howshouldwethinkabouttheproblemsofdeterminingtheconditionsforaproperlyfunctioningmarketeconomy?Idon’tthinkit’senoughjusttothinkinthoseterms.Oneshouldalsothinkintermsoftheinstitutionsofthatcountry,particularlythesocialinstitutions,andbuildfromwhereyouare.Itseemstomeamistakenottostartfromthepointwhereyouare.Totryandchangeacountrydramatically,pullitupbytherootsandstartagain,thatseemstomewrong.Ferrarini:Youarguein“TheNatureoftheFirm”thatthefirmisthesupercessionofthepricemechanism.Planningandthepricemechanismco-existinaneconomy.Dependingonthecostofanorganizationandtransactions,theagentswilldecidewhichonetouse.Let’stalkabouttheeconomicsystemasawhole.Howshouldasocietydecidewhicheconomicsystemtochoose?Isthereamoreefficienteconomicsystemandwhy?Well,thereisnoonewaybettereconomicsystem,becauseeverythingdependsonthe页脚.\n.页眉.societyyou’rein.在诺斯、科斯等人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向社会经济学方向后,尽管有人批评这将是新制度经济学走向死亡的道路,但诺斯本人坚信(1997):“两个现代领域的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景:其一是认知科学的进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工作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其二是社会科学家对终将迫使他们直接面对理性问题的博弈论的痴迷,因为博弈论最终取决于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被理解为常识的东西。”而我们也的确看到,作为理解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工具,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的成果的确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视野,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向社会经济学转型提供很好的工具。延伸问题:制度起作用吗?既然制度内生于环境,那么,制度有用吗?Przeworski(2004,2005)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最为明晰。他写道:“新制度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1)制度有作用:它们影响规则、信念和行为;因此它们塑造了结果。(2)‘制度是内生的’:它们的形式与功能依赖于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制度既然是内生的,意味着每一种制度安排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而如果不同的制度只能在不同的条件下才可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起作用的究竟是制度还是制度所依赖的特定的条件呢?”页脚.\n.页眉.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制度经济学从产生以来,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最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是正式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但后来,他们发现产权制度是由政治型态界定和实施的,因此,转向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再后来,由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对比研究,发现不同的政治型态是由所嵌入的社会信仰体系所决定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转向了新经济社会学,并越来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第一,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应该尽快脱离新古典的框架。尽管科斯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但早期以诺斯为代表的现代制度经济学承认新古典理性人假设,借用的是新古典价格理论框架;后来的发展表明,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总是试图将制度经济学纳入自身框架之内,但随着诺斯引入意识形态对新古典国家理论的修正,并最终抛弃理性假设,现代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渐行渐远。而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相当多成果仍然没有脱离新古典框架。关于自由市场的观念。国内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任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运作,人们总是能通过寻找适宜的交易结构而向帕累托最优方向改进;制度也就是对既定技术和相对价格环境条件下的有效响应,因此制度的产生和变化也必然是有效的。也正是这些经济学家当初受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启发或直接援引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关于自由市场有效的观点,实际上还是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有效性”观点的翻版。而“制度有效性假设”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尤金·法马(Eugene页脚.\n.页眉.Fama)等人发展起来的有效市场假设(EMH)一样,是从新古典理论“孪生”出来的一对兄妹,都是一种静态完美市场下的产物。而后来诺斯等人明确抛弃了制度有效性假设,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制度总是嵌入在特定政治型态之下;而特定的政治型态又嵌入在特定的社会信仰体系之中。因此,是经济制度应该适应政治型态,尤其应该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与信仰体系。这一点,Shleifer等(在批评Acemoglu等关于制度重要性观点时,特别提到东亚儒教伦理与威权型政治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市场制度作用总是有限的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关于最大化的观念。国内不少经济学家总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从这点出发,有人甚至认为自愿充当童工与自愿卖淫都应该合法化,因为一个人自愿充当童工或卖淫,肯定是出于“最大化的动机”,并且结果肯定能改善其效用。类似的观点还有:“老说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们仍然愿意进城,可见进城还是比在农村好。”这种观点在新古典框架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制度经济学框架下,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此我想重提1960年代科斯与萨缪尔森之间有名的争议(转引卡勒维,1993)。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最大化问题,而科斯反驳认为: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最大化问题,那么,人与老鼠、章鱼、兔子没有什么区别:草原上一只饥饿的狐狸追赶一只兔子,狐狸一定会拼命地跑,否则它会饿死;而兔子也会拼命地跑,否则他会被吃掉。所以,动物也都知道追求最大化。也就是说,最大化不过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趋使。从这个意义上,科斯说:“现代经济学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在1983年新制度经济学第一次年会上,科斯再度提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对这种做法的一个方面持有不合常规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作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入误入歧途。”“诸如‘页脚.\n.页眉.如果价格提高了,那么供给就会增加’这样的命题没有意义。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大化?如果是这样,我的一些同事引用巴特曼的一句说话,疯子实际上也在进行计算,也是追求最大化。”科斯多次指出,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人的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具体地说,一个行将饿毙的儿童或没有钱交学费的儿童,到工厂去打工甚至下煤窑干活,当然是自愿的而且是经过理性计算后的最大化:因为总比饿死好。但这仅仅与草原上拼命奔跑的狐狸或兔子一样是一种趋利避害本能趋使,这不应该成为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更不能成为制度经济学家为不合理现状辩护的理由。既然自称为制度经济学家,更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即约束条件竟然使得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一个未成年人竟然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第二,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是个待进一步展开的领域。目前看来,新政治经济学在整个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中是取得成果最多、最为激动人心的领域。而在中国,一方面受新制度经济学新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改革面临的政治困境,迫使一些经济学家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这一领域。但总的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拓宽。关于利益集团的观点。当前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重点放在中央政府政治架构,或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各级政府在改革及经济绩效中扮演的角色;而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则非常不充分,而且存在诸多对利益集团的误会。页脚.\n.页眉.实际上,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存在中性或扮演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角色的积极的利益集团。恰相反,那些有能力主导制度变迁方向的少数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往往会使制度变迁朝着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大众的方向走;而社会大众因为组织起来交易成本高,无法克服搭便车、无法进行选择性激励等问题,往往至多只能被利用而无法主导制度变迁过程。也正因此,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提出所谓防止民粹主义破坏改革相反,RajanandZingales(2003)的观点更富洞见:“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工会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却都在企业扼杀竞争性市常很不幸的是,在太多的国家,在太多的时候,政府都出面帮助这些商业勾结,限制市场竞争。”关于缔约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最新发展表明,契约安排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基于最优化的安排。只有用博弈的观点去分析,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会导致妥协和一个偏离了完全有效率的竞争体系所要求的模式的权利结构的建立”。也正因此,Libecap在批评最优契约设计思想后明确指出,应该用“缔约(Contracting)”这一概念来描述个人分配或调整产权的努力。因为只有这一概念才能表明组织中的私人产权拥有者之间(即生产要素为私人所有)的讨价还价过程。产权制度是通过政治过程决定的。尽管有时这种讨价还价过程未必会发生,那也是因为“事先的权力分配就已决定了契约权力的竞争格局”。页脚.\n.页眉.但国内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契约都是自愿的,自愿的契约必定是平等的和双赢的。“剥削是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事”。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甚至为血汗工厂辩护。而Rasmusen等人通过博弈论的框架严格证明了这样的观点(1997,P206-207):“在一个非出清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完全可以将员工工资水平压低到外部市场机会所决定的水平。”“通过遏制偷懒,在工厂门口徘徊的饥饿的工人执行着一项对社会来说有价值的功能”。因此,Steiner(2002)这样说:“合同自由学说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它假定了签约各方拥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力,但在实际中,雇主都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的。对于雇主来说,签约合同的自由就是剥削的自由。雇员可以被任意解雇,而不得不最终接受任何工作环境:雇主不受挑战的主导权导致了对雇员待遇的忽视。”第三,着眼社会经济分析,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将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突围的方向。目前,有一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信仰体系对制度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以来,大量的文献出现在关于正式制度的讨论;即使是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也主要是围绕宪政、分权与分税制等等正式政治制度安排进行的。某种程度上,中国制度经济学家有一种对正式制度尤其是经济上的产权保护制度与政治上宪政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正式制度搞对了,其他都没有问题。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社会环境等非正式制度性因素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则很少涉及。关于制度适应性效率的观念。诺斯(1990,1994)较早提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但对适应性效率的定义有微妙的变化。在早期,他主要指政治与经济的正式制度能够经受住动荡和变革;但从1990年代晚期始,他定义适应性效率“是指某些社会面对存量进行弹性调整的能力和演化制度以有效处理改变了的现实的能力。”而且,他认为,这种适应性效率来源于“有效地将非正式规则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将正式规则嵌入社会带来的适应性。”科斯同意这种观点,并提出(1997):“试图戏剧性地改变一个国家,将其从所嵌入的社会中连根拔起,那是错误的”这对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至少有两重含义:页脚.\n.页眉.第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否是由于我们过多关注制度转型带来的短期资源配置效率,而没有关注制度构建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以致于制度转型的成果还相当脆弱?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自负:资源配置效率即经济效率要求政治制度相应变化,而政治制度的变化又要求意识形态以至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为之变化。而从适应性效率的观点看,我们似乎应该考虑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建立提高经济绩效的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如何具有中国的路径依赖性质?我不是说政治形态与信仰体系不需要改变,恰相反,只有首先适应了然后才能从边际上改变它,否则,变革可能是悲剧性的。Przeworski就曾发问,法国为什么频繁发生残酷的革命而社会制度变化却很小?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也适用于中国。第二,看待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不能太短视。诺斯曾不无讽剌地说(2003b),他经常观察到经济学家看到一个国家持续增长了10年20年就会兴奋地说“这个国家正处于通向发展的道路上”,或者“我们最后会克服拉丁美洲式的不稳定”,或者“我们最终会成功实现经济的转轨”。“对经济史学家来说,这的确是谬见。”诺斯本人认为,至少要在50年或100年的时期,“如果发展到这样一个社会:有抵挡冲击的能力,有战胜频繁出现的问题的能力。”这时才能基本判断制度能否有适应性效率。中国经济增长的确非常迅速,但毕竟只有30年。而我发现自05年始,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就非常乐观地宣称改革是成功的,甚至参与到“大国崛起”这样的鼓躁之中,是不是太快了点?否则,我们为什么发现社会问题如此之多?最后,关于“嵌入(embededness)”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作为其前沿的企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使得“嵌入”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主流概念;而将“嵌入”作为一个较基本概念使用最早的是波兰尼(KarlPolanyi)。页脚.\n.页眉.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是就经济论经济,认为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甚至认为,即使是经济与社会发生联系,也是社会从属于经济:比如,有时需要政府帮助克服市场失灵。但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对此,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经济交易对于信任、相互理解以及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等“社会性行为”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潮。而实际上,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并由于“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这种反弹的结果。这一观点与诺斯关于制度嵌入于社会以及适应性效率等观点是一致的。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之际有两种现象被中国经济学界看到了,但没有解释清楚。一是所谓民粹主义现象;二是政府控制的全面加强。在社会经济学框架下,这不难解释。波兰尼早说过两个观点:一是“如果让社会为自由市场让道,社会将会报复市潮;第二,“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所以,“自由市场每增加一分,政府控制也必须增加一分。”上述两种现象的存在,也更证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转向一种社会经济学,用“嵌入”的观点看待制度现象。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