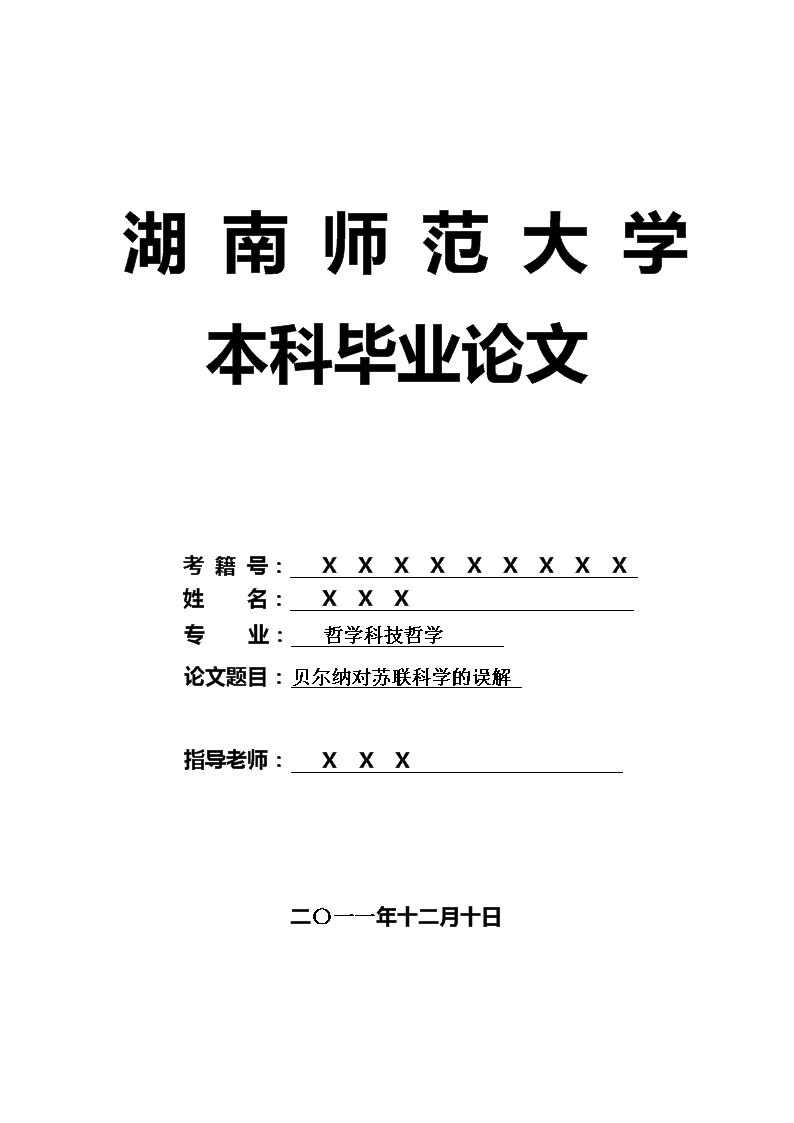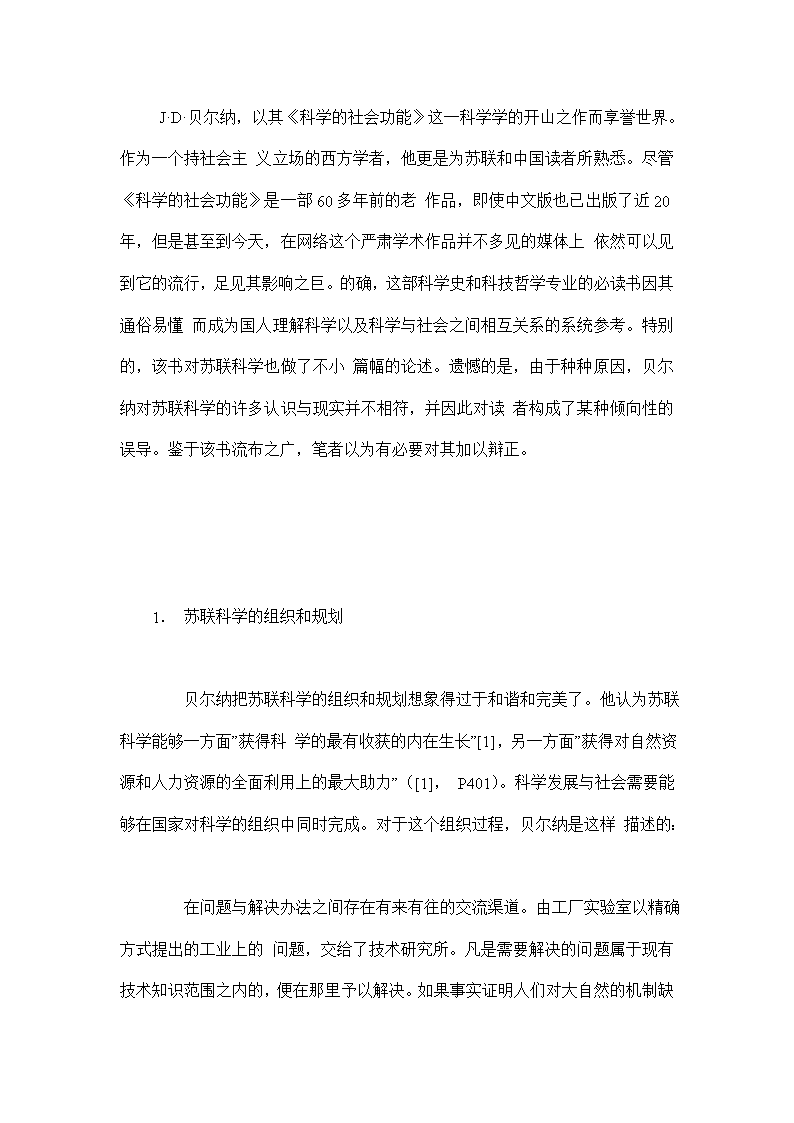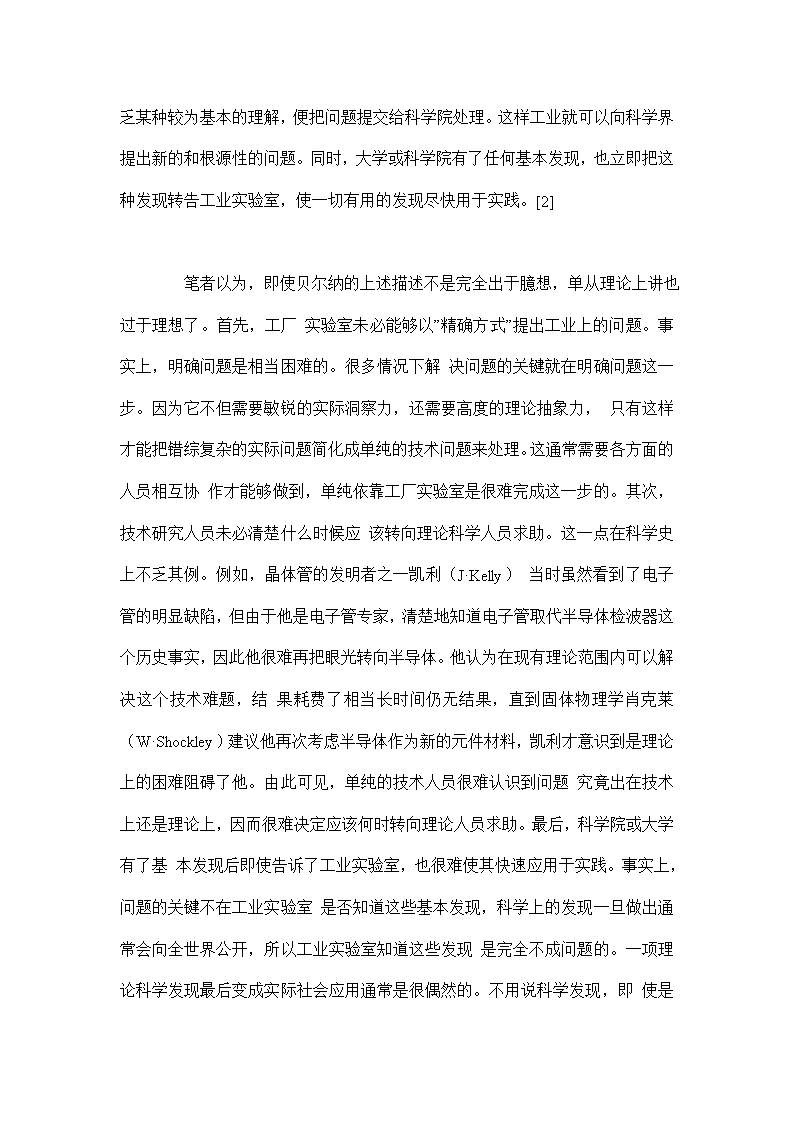- 43.00 KB
- 2022-08-25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哲学科技哲学论文题目:贝尔纳对苏联科学的误解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n J·D·贝尔纳,以其《科学的社会功能》这一科学学的开山之作而享誉世界。作为一个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他更是为苏联和中国读者所熟悉。尽管《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一部60多年前的老作品,即使中文版也已出版了近20年,但是甚至到今天,在网络这个严肃学术作品并不多见的媒体上依然可以见到它的流行,足见其影响之巨。的确,这部科学史和科技哲学专业的必读书因其通俗易懂而成为国人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参考。特别的,该书对苏联科学也做了不小篇幅的论述。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贝尔纳对苏联科学的许多认识与现实并不相符,并因此对读者构成了某种倾向性的误导。鉴于该书流布之广,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其加以辩正。 1.苏联科学的组织和规划 贝尔纳把苏联科学的组织和规划想象得过于和谐和完美了。他认为苏联科学能够一方面”获得科学的最有收获的内在生长”[1],另一方面”获得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面利用上的最大助力”([1],P401)。科学发展与社会需要能够在国家对科学的组织中同时完成。对于这个组织过程,贝尔纳是这样描述的: 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由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的工业上的\n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的,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提交给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现尽快用于实践。[2] 笔者以为,即使贝尔纳的上述描述不是完全出于臆想,单从理论上讲也过于理想了。首先,工厂实验室未必能够以”精确方式”提出工业上的问题。事实上,明确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很多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明确问题这一步。因为它不但需要敏锐的实际洞察力,还需要高度的理论抽象力,只有这样才能把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简化成单纯的技术问题来处理。这通常需要各方面的人员相互协作才能够做到,单纯依靠工厂实验室是很难完成这一步的。其次,技术研究人员未必清楚什么时候应该转向理论科学人员求助。这一点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例如,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凯利(J·Kelly)当时虽然看到了电子管的明显缺陷,但由于他是电子管专家,清楚地知道电子管取代半导体检波器这个历史事实,因此他很难再把眼光转向半导体。他认为在现有理论范围内可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结果耗费了相当长时间仍无结果,直到固体物理学肖克莱(W·Shockley)建议他再次考虑半导体作为新的元件材料,凯利才意识到是理论上的困难阻碍了他。由此可见,单纯的技术人员很难认识到问题究竟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因而很难决定应该何时转向理论人员求助。最后,科学院或大学有了基本发现后即使告诉了工业实验室,也很难使其快速应用于实践。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工业实验室是否知道这些基本发现,科学上的发现一旦做出通常会向全世界公开,所以工业实验室知道这些发现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项理论科学发现最后变成实际社会应用通常是很偶然的。不用说科学发现,即\n使是技术发明有时甚至连发明者本人也不知道它究竟有何用处。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新玩意能干什么。只是到第二年,爱迪生才发表一篇文章,细致说明有10种途径可以证明这项发明对大众有用。在他列举的10项用途中,复制音乐被列在第四位。爱迪生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用途。然而,这个被他轻视的小用途日后竟成为留声机的主要用途,而他开始列举的哪几项全都没有派上用场,这无论如何是爱迪生始料不及的。[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发现和发明用于实践的快慢并不取决于社会知道它的早晚,发明和发现的实际应用也并不一定朝着发明和发现者指明的方向前进。单纯通过增强科学与工业间的交流来加快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只是贝尔纳一厢情愿的设想。 从实际上看,苏联科学组织的运行状况也不像贝尔纳描述的那样和谐。在贝尔纳看来,苏联科学院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地方,但理论研究的动力和方向则由政府和工业部门提供。科学院的选题都是依照实际需要事先计划好的,只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就可以了。并且贝尔纳认为”苏联的科学计划不是做好给科学家们的,而是由科学家们做出来的。”([1],P703)这样,科学家就是主动而不是被迫执行计划,因而与政府之间就不存在摩擦和冲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从一开始,苏联科学家、特别是科学院里的科学家,对计划科学(通常也意味着实用科学)这一观念就是根本反对的。他们公开反对新政府制定的科学政策,尤其毫不妥协地抵制官方对应用科学的强调。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奥麦利安斯基(V·L·Omel’ianskii)引用季米里阿泽夫(K·A·Timiriazev)的话说:科学的发展依靠的”不是外部实际需要引起的压力,而是内部的事实规律”,……一切使科学服从于外部需要的行为都必将限制\n创造性研究的领域和自由。[4]他公开强调: 科学并不产生于实用的实验室,不论其设备是多么精良,……它产生于平静的科学实验室,产生于对绝对真理的不懈的和无私的追求,产生于对那种笛卡儿认为高于一切其他真理的”美的真理”的追求。在这里,永恒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可能性完全变为现实,那些改变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每个领域的思想也由此诞生。([4],P117)1933年,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I·Pavlov)带头反对计划科学,他直截了当地说:要是自己遵从计划的话,很多领先的非计划和不能预见的实验研究就会因此丧失([4],P135)。另一位有代表性的院士引述门捷列夫的忠告说:只有为了科学的内在意义和’绝对纯粹’追求的真理才能成为实用知识的真正来源([4],P95)。直到1936年,著名物理学家朗道仍然没有放弃纯粹科学的立场,他断言:强迫科学家解决技术问题,就是赶鸭子上架。苏联物理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提高他们各自的学科水平。真正紧要的问题是国家缺少精通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物理学家。只有当他们坚持做自己的事--提高他们的科学理论和实验基础,物理学家才能对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起更大的作用([4],P138)。科学家与政府的这种对抗,其旷日持久的程度从代表政府立场的沃尔根院士在1933年的一次的讲话即可见一斑,他说: 除了某些早已在科学院工作的同志以外,许多同志也许都不能想象,为了把科学工作的计划这个简单的思想运用到科学院中来,曾经要求我们进行了怎么样的斗争,作了多少努力,进行了多少谈话,科学院的共产党员和靠近它们的非党人士在这件事情中付出了多少劳动。[5]\n 总之,科学的组织和规划在苏联进行得并不一帆风顺。它不但没有贝尔纳设想的那样和谐完美,反而时时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之中。2.苏联科学研究的特色及成因 关于苏联科学的研究特色,贝尔纳指出了三点:一是各个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二是在质量上的独创性。三是没有足够严格的鉴别力。这三点可以说切中肯綮。遗憾的是,在分析第二点产生的原因上,贝尔纳又误入了歧途。贝尔纳说: 这一点可以直接归因于结合经验来选题的新倾向。苏联科学可以从普通经验中找出科学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来加以说明。而科学过去所以没有能接触到这些方面并不是因为这些方面困难或暧昧不清,而是因为这些方面不在常规科学传统范围以内。([2],P329-330)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杰出科学研究并不离实际经验更近。其所以具有独创性,主要是因为苏联当时并不处在科学中心,因而在许多科学问题上没有先入之见,能够大胆怀疑和创新,从而一举做出令西方瞩目的成就。苏联第一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成就”切连科夫效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n 20世纪30年代初,当切连科夫还是莫斯科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时,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瓦维洛夫(S·Vavilov)曾要切连科夫研究:当镭源放出的辐射穿过不同的晶体或液体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在这之前多年,已经有人对此做过研究,并注意到,当γ射线射进晶体或流体中时,会出现一种微弱的蓝光。他们不仅做了些实验,而且还做过报道,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法国放射学家马利特(L·Mallet)在1926-1929年间的研究。但他们都不过把这种微弱的蓝光误认为是一种当时早已为大家熟悉的荧光现象。切连科夫却不然,他怀疑这种蓝光并非荧光,在导师瓦维洛夫的建议下对它作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最后终于发现了新的物理规律。[6]不难看出,这里的研究既与实际经验无关,也与科学经验(有经验的西方科学家肯定不会再研究这样的陈旧课题)无关。这项研究不但不是贝尔纳所说的”科学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反而恰恰是科学早已接触过的问题。”切连科夫效应”的独创性只能用苏联科学场域的非中心性因而对现有理论更具怀疑和批判精神来解释。[7] 无独有偶,由谢苗诺夫创立的,苏联另一项诺贝尔奖成就”支链反应理论”也是在西方科学权威的不以为然下诞生的: 谢苗诺夫的一位研究生瓦尔塔,在哈里顿指导下做磷蒸气在氧气中氧化的实验时,发现当氧的压力低于某一最低值时,测不出磷与氧反应的痕迹;当氧气压力高于某一界限时,磁蒸汽明显\n地发生从测不出痕迹到闪燃反应的激烈转变,而且当氧气压力由于消耗而降到这个界限或稍低于这个界限时,反应则立即停止。哈里顿和瓦尔塔的这一研究结果在德国《物理杂志》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当时化学动力学领域中的学术权成M·博登斯坦(Bodenstein)的尖锐批评。他怀疑实验的准确性,并断言反应界限是难以置信的,认为这与平衡的科学原理相矛盾。权威的这种看法,使同事们对实验的正确性也产生了怀疑,于是谢苗诺夫决定亲自做实验来解决这个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不仅可以重复反应界限的实验,而且,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重复哈里顿和瓦尔塔所发现的用惰性气体稀释氧气时,氧气压力界限降低的事实。……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谢茄诺夫经过认真分析和思索,用博登斯坦-能斯特(Bodenstein-Nernst)链锁反应的概念作为解释的基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链可以支化的概念……。[8] 众所周知,当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相矛盾时通常有两种态度:要么怀疑实验的可靠性,要么怀疑理论的正确性。但如果该理论已被科学共同体广泛接受,那么受怀疑的对象通常就是实验而不是理论。而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尚处在科学共同体的外围,因此更倾向于怀疑理论,这就是谢苗诺夫能在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的原因。其实,苏联科学的”独创性”和”没有鉴别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分别是苏联远离科学中心所产生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苏联科学。当然,苏联科学的独创性还有其它来源,如环境逼迫。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考拙文”‘科热伏尼科夫佯谬’的内容、解释和意义”。3.苏联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诚如贝尔纳所言:”外国观察家对苏联科学所最不理解的一个方面是它和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2],P330-331)不幸,贝尔纳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贝尔纳认为:\n 苏联科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哲学理论。这一直是一个充满生气的、而且有时几乎还是很激烈的过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老科学家当然是不理解新观念的,而且甚至对新观念抱敌视态度,而青年科学家则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来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论点。([2], P331-332) 诚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苏联这样紧密。然而,造成这种紧密关系的并不是苏联的科学家,而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们通常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由于这一失误,贝尔纳进一步误解了科学与哲学之间冲突的主体、性质和原因。贝尔纳认为冲突是在科学家之间进行的。而实际上,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这是贝尔纳对苏联科学能够观察到的主要年代),恰恰是哲学家之间爆发了激烈争论:他们分成两个阵营--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各自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正在发生的物理学革命,相互指责对方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1926年,这场激烈的争论甚至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辩证论者指责机械论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理论,如抛弃列宁的”矛盾统一”论而信奉”机械因果论”;反对将列宁的”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物质”是科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等等。在争论最厉害的1928年,辩证论者谩骂其对手的哲学自相矛盾、毫无根据、夸夸其谈和玩弄伪科学伎俩。其主要代表德波林(A·M·Deborin)给机械论者贴上”自称的弗洛伊德分子、前马赫主义者、经验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混合物”的标签。另一方面,机械论者则指责辩证论者不忠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建;以教条的态度对待黑格尔\n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无批判无选择地接受现代物理学的革命理论;……如此等等。在是否应该将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作为共产主义学院的首要任务上也发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应该使辩证唯物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派则认为这不是主要工作,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动力才是首要的,如此争论不休。相反,大部分科学家则在这场争论中或者缄默不言,或者保持中立。([4],P88-89) 30年代后期,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哲学家内部逐渐达成统一,于是冲突主体演变为科学家与哲学家(主要是意识形态者),科学家内部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哲学争论仍然相当少见。一个明显的例外也许是瓦维洛夫学派与李森科集团之间关于遗传学的论战。贝尔纳也正是以这个例子作为上述冲突的典型来叙述的(参见[2],P332)。然而,这场论战与其说是一次科学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公开角逐,毋宁说是一场掺和了政治因素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暗中较量。[9] 在分析冲突产生的原因上,贝尔纳认为老科学家不理解新观念(这种新观念主要是哲学上的,即辩证唯物主义,而非科学上的,科学上的新观念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共振论等并不为老科学家们所反对,恰恰是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家们对其抱敌视态度)以及对其抱敌视态度是因素之一。然而事实上,老科学家们并不直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有很多科学家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并利用它作出了重大科学贡献[10],他们所反对的是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独尊的哲学来限制科学,以及因为科学素质低下从而不依靠科学事实而是单凭哲学论断或党性立场来反对某些科学理论的非科学态度和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维尔纳德斯基(V·I·Vernadskii)。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方法论作为\n一种官方哲学来控制科学,他认为高水平的科学创造只有在能够容忍非正统思想存在的领域里才可能产生([4],P99),只有当允许不同的哲学倾向存在时,哲学才能对科学产生大的帮助([4],P162)。著名物理学家约飞(A·F·Iofffe)警告说要注意哲学上对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狄拉克等物理学家乱贴唯心主义标签的倾向。他认为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歪曲和限制物理学家工作的工具。([4],P160)最激烈的反对者可能是弗伦克尔(Ia·I·Frenkel’),在一次公开的物理化学专家会议上,他对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院的一种官方哲学表示了攻击: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辩证唯物主义能够对科学起指导作用。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强加给我们的学者和年青人是在政治上走极端。社会主义需要理论基石,这有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但辩证唯物主义却是发展科学的障碍。无论是列宁还是恩格斯都不是物理学家的权威;……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起反作用的的哲学……。([4],P156) 著名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塔姆(I·E·Tamm)则采取了更为温和的策略:他并不将矛头直接对准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批评那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跟不上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他写道:”即使是一个大学生也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科学上的文盲。他们通过空洞的长篇大论和纠缠于细末尾节来掩饰自己的无知。”([4],P156-157) 科学家们尤其反对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来控制科学。科学院副院长、杰出数学\n家斯捷克洛夫(V·A·Steklov)在其伽利略传中写道:”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头脑服从于先定而僵化的政治口号”,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创造性是互不相干的,”要有创造性,科学就必须被允许在一切政党和政党的命令之外工作”。([4],P96) 总之,苏联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上的冲突其主体不是科学家与科学家:在前期是哲学家内部,后期则是科学家与哲学工作者。冲突的原因也不是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理解,而是政府试图将其变成独尊哲学以及利用它作为意识形态来控制科学从而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反感。4.革命前的科学与革命后的科学 贝尔纳对革命前的苏联科学--俄国科学也作过论述。贝尔纳认为革命前的科学与革命后的科学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述了俄国科学家乔菲对俄国物理学的描述: ……革命前的俄国学者一般都是一个人进行工作,既没有留下科学学派,也没有留下什么具体方针。他们自己的论题往往是通过同法国或者德国学者合作从国外学来的。俄国学者往往参预一个西欧学派,从事同那个学派的论题有关的一些研究工作,然后以硕士学位论文形式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对这个论题加以发挥,作为他们的博士学位的论文主题,因此,他们保持国外思想中心的倾向是很自然的。没有产生出独立的俄国学派。 唯一的例外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捷夫在莫斯科大学所创立的出色科学学派……\n列别捷夫学派和若干列宁格勒物理学家的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科学趣味。不过大部分科学成果都不足以丰富科学世界。这些工作有一部分是”偏狭的”,只限于对观察到现象加以描述,而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解释。它们仅是外国工作的变种,各种常数的测定等等。…… 连俄国物理学家的最出色的工作也只是不连贯的研究,不能形成明确的科学研究路线,没有为自己提出深刻的问题或者任何技术上的目标。可以说革命前的俄国几乎不存在技术物理学,也缺乏形成它的条件。…… 因此,虽然俄国物理学界拥有几个伟大的学者,他在革命前仍然是世界科学中最落后和最薄弱的部分之一。([2],P320-321) 因此,贝尔纳认为革命后的”苏联不得不在实际上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从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和规模更大的科学事业”([2],P320),并且只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才”开始首次对世界科学的某些学科作出卓著贡献”([2],P321)。无可否认,十月革命对苏俄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贬低革命前的科学成就。单以物理学的成就来概括整个俄国科学的发展水平显然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俄国科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在数学、化学、生物学上都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如众所周知的数学家切比雪夫(P·Chebyshev,1821-1894)、马尔科夫(A·Markov,1856-1922);化学家齐宁(N·Zinin,1812-1880)、布特列洛夫(A·Butlerov,1828-1886)、门捷列夫(D·Mendeleev,1834-1907;生物学家巴甫洛夫(I·Pavlov,1849-1936)。他们早在革命前就对世界科学作出了卓著贡献。其中切比雪夫和马尔科夫等人不仅开创了独立的彼得堡数学学派,而且在概率论、函数逼近论等领域已经比西方先行了一步。马尔科夫提出的无后效数学模型(马\n尔科夫链)至今仍广为应用。齐宁则被德国著名化学家霍夫曼(A·Hofmann)评价为:”……对有机化学的发展不仅有显著的,而且是持续的影响。……假如齐宁除了硝基苯转化为苯胺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出来,他的名字照样也是用金字写在化学史上。”([8],P183)齐宁的学生布特列诺夫则为世界贡献了”化学结构理论”,并且开创了俄国的化学学派--喀山学派。门捷列夫和巴甫洛夫的世界性成就更不必说。即使是俄国的物理学,其水平也并不像乔菲描述的那样低下。尽管列别捷夫并无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在实验方法和技巧上仍然功勋卓绝。在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列别捷夫通过创造性的实验设计率先完成了气体光压的测量,英国皇家学会为此于1911年选举他为荣誉会员。著名物理学家H·A·洛伦兹对列别捷夫的评价是:”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头等的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11]当然,革命后苏联的物理学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诞生了一批诺贝尔奖得主,但总的来说,革命前的科学与革命后的科学是有相当的传承关系的,将革命后的苏联科学描述成在一片废墟之上的高歌猛进是极不恰当的。 贝尔纳何以对苏联科学有如此多的误解呢?一部分原因是他掌握资料的不充分,更大的原因则在于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科学抱有先入之见。因此他的很多描述只是理想而非现实。好在贝尔纳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的序言中写道:”我不得不主要依赖个人经验来描述和评论科学工作的管理状况。……我得坦率承认:我是有偏见的。我对于缺乏效率,摧残科学事业和把科学研究用于卑鄙目的感到愤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来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并尝试写作这本书。”([2],P27)。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贝尔纳对苏联科学给予了太多的厚望。\n 贝尔纳写作之时,苏联才建国不过20余年。苏联科学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他都没能看到。今天,苏联已经解体,经过时间的淘洗和远距离审视,我们才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 参考文献与注释:[1]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p401[2]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p325-326[3]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p152[4]AlexanderVucinich:EmpireofKnowledge:theAcademyofSciencesoftheUSSR(1917-197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p95[5]科尼亚捷夫,阔尔佐夫:《苏联科学院简史》,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p94[6]张文卿等编:《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传略》,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p388[7]这种独创性其实在革命前也很常见,最典型的莫过于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需要指出的是,完全远离科学中心也是不行的,必须能够从西方科学中得到一定的熏养而又不为其所局限。[8]胡亚东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化学家二),科学出版社,1992,p155[9]关于这一点已有众多揭露,可参考笑蜀的网上作品《悲情圣殿》。[10]\n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可参考洛伦·R·格雷厄姆的《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p108-134[11]钱临照,许良英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二),科学出版社,1992,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