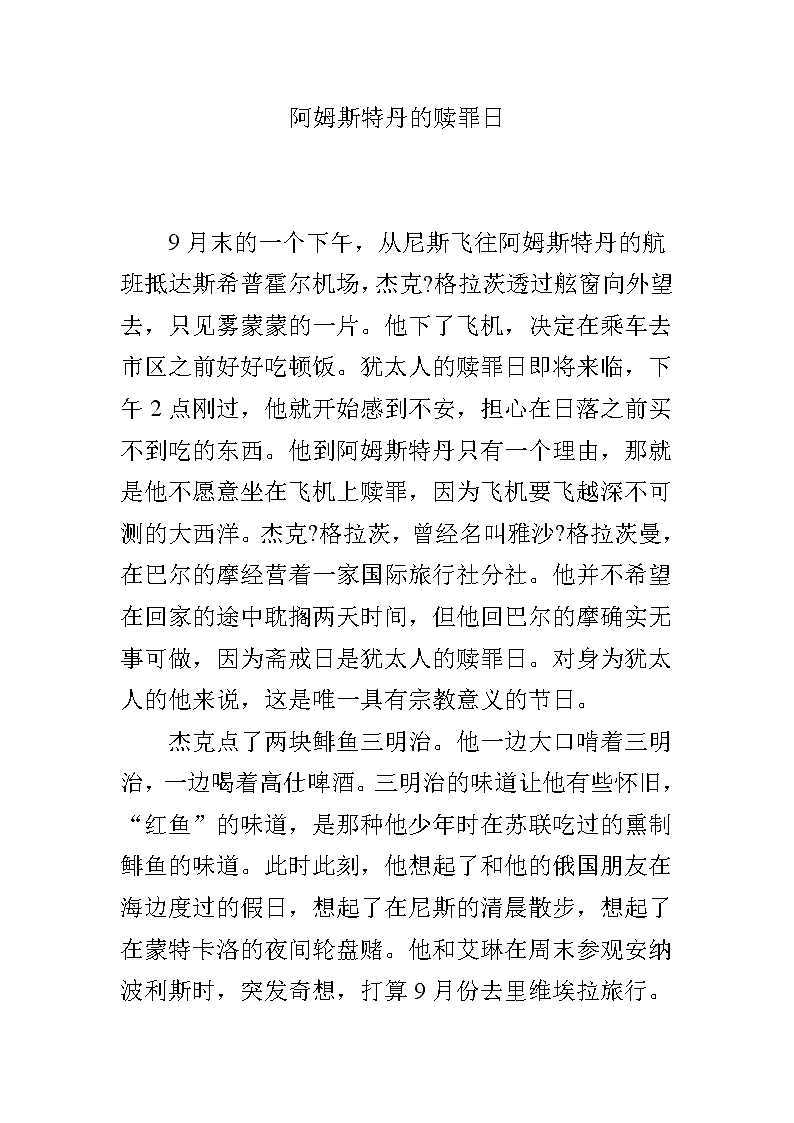- 43.00 KB
- 2022-04-22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阿姆斯特丹的赎罪日 9月末的一个下午,从尼斯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抵达斯希普霍尔机场,杰克?格拉茨透过舷窗向外望去,只见雾蒙蒙的一片。他下了飞机,决定在乘车去市区之前好好吃顿饭。犹太人的赎罪日即将来临,下午2点刚过,他就开始感到不安,担心在日落之前买不到吃的东西。他到阿姆斯特丹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不愿意坐在飞机上赎罪,因为飞机要飞越深不可测的大西洋。杰克?格拉茨,曾经名叫雅沙?格拉茨曼,在巴尔的摩经营着一家国际旅行社分社。他并不希望在回家的途中耽搁两天时间,但他回巴尔的摩确实无事可做,因为斋戒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对身为犹太人的他来说,这是唯一具有宗教意义的节日。 杰克点了两块鲱鱼三明治。他一边大口啃着三明治,一边喝着高仕啤酒。三明治的味道让他有些怀旧,“红鱼”n的味道,是那种他少年时在苏联吃过的熏制鲱鱼的味道。此时此刻,他想起了和他的俄国朋友在海边度过的假日,想起了在尼斯的清晨散步,想起了在蒙特卡洛的夜间轮盘赌。他和艾琳在周末参观安纳波利斯时,突发奇想,打算9月份去里维埃拉旅行。那里,有在大坝上迎风飘扬的旗帜,有鲜美的牡蛎和青蟹,有身穿制服的军校生,还有在远处海面上来回穿梭的游艇。当地中海的炎热渐渐消退,法国游客经过一年一度的8月份休整,纷纷踏上归程的时候,夏日的海滨总是让杰克在安常处顺时盼望着他的里维埃拉之行。 “亲爱的,”艾琳用玩笑但无讽刺的语气问道,“你最近是否看过有关尼斯的故事?有没有读过契诃夫或纳博科夫写的小说?”n 他们在一起差不多有两年了,杰克非常喜欢她那种无可救药的单纯。在他眼里,艾琳是一个传统的美国姑娘,德裔爱尔兰人,脸上的雀斑星星点点,却总是笑意盈盈,无忧无虑,天生一副乐天派;她体态偏瘦,两腿修长,酥胸玲珑;她衣着简单大方,运动鞋、牛仔裤和宽松毛衣是一贯的穿着。他惊奇于她简简单单独自生活的能力,但他永远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她对周围的事物、对她的家乡、对她的时尚杂志和管理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可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却如此冷漠。为了让她更多地了解自己和犹太人,当他们一同驾车,当他们耳鬓厮磨、共享欢愉之后,杰克总是和她一起分享这些特殊时刻;然而,她总是满足于眼前生活中的琐事。其实,艾琳不是不愿意去了解犹太人的血泪史,她总是尽量记住犹太民族历史上的某些特殊时刻。 对艾琳来说,这将是她第一次去里维埃拉旅行,杰克希望这次旅行会使她大开眼界。他在一家四星级酒店预订了房间,这家酒店很安静,原是沙皇俄国驻法领事的宅邸,距离海滨的盎格鲁大道仅仅五分钟的步程。对艾琳来说,天天都会有惊喜:芒通的柠檬树丛,蒙特卡洛的上流社会,位于安提布岬的毕加索画展和卡纳须海的雷诺阿画展,戛纳的电影,格拉斯的香水,圣特罗佩的渔产。杰克虽然是旅行社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假期安排得如此周密。 4月底,他们对前往里维埃拉度假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预订的车票和旅馆票据已经放在了杰克办公室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里。接着,夏天到了,巴尔的摩比平时更加湿热,杰克的心情越来越沮丧。在去了一趟位于宾夕法尼亚中部艾琳的家乡之后,所有的一切就像他办公室电脑屏幕上的简易魔方拼图一样,都归结到一件事上。艾琳的叔叔一直就《辛德勒的名单》问一些虽无恶意但十分白痴的问题。艾琳的姐姐絮絮叨叨,说她曾经在匹兹堡见过哈西德教派的犹太人戴着像“小便帽”的“亚姆尔克”n。紧接着,礼拜日那天,他们全家人一大早都去了天主教教堂,只剩下杰克一个人孤零零地和一条达克斯猎犬待了大半天。艾琳从不向他提及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因为她知道他会生气。杰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说服她皈依犹太教,因为他感觉这种想法有些不地道,不符合犹太人的作风,甚至有些冒犯。但是,那些与非犹太人结婚成家的朋友们的个人经历和他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使他确信,只要他向艾琳开口,请求她改变信仰,皈依犹太教,她准会答应。于是,在从艾琳的家乡回巴尔的摩的路上,他终于在车里向艾琳表达了他的请求,结果却发现,艾琳对天主教十分虔诚,一种他想象不到的绝对虔诚。她眼里滚动着泪珠,马尾辫拖在“海军”牌棒球帽后面,急切地抚摸着杰克的手,不停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杰克,我会给你生一群孩子,我会帮助你把他们培养成犹太人,我会学着做犹太妇女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不能改变信仰。你为什么还不能接受我?”n 杰克气极败坏,全身发抖。他一语不发,默默地开着车,脑子里闪现出一幕幕情景:梵蒂冈主教向礼拜天朝圣的人群表达问候,哥伦比亚特区地铁里黑绿相间的格子,他一次次参加过的天主教徒的婚礼。他曾经相信,在一个基督教世界里,犹太人应该在不失颜面的前提下,尊重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对天主教堂是如此的愤怒,如此的痛恨和敌对,好像是它毁了他的幸福。 几天之后,艾琳又一次打来电话,责问他:“你为什么不接受我?仅仅因为我信仰基督教?” “艾琳,我真的爱你,但是我不能娶你。我们是少数族裔。不管你怎么想,我孩子的母亲必须是犹太人。”杰克哽咽道,接着,他顿了一下,又说,“无论从哪方面考虑。” 四五天后,星期六早上,快递公司一位又瘦又高的女士送来一只箱子,是那种21英寸电视机的包装箱。打开箱子,杰克发现,两年来他给艾琳的全部礼物,都用原来的包装带捆好退了回来。“真是笑话。”他想了一下,打开只剩半瓶的法国香水,这是他送给艾琳的感恩节礼物,接着,他抖开在伦敦给她买的深绿色羊毛披肩。最后,他的手指触到箱底厚厚一叠纸。这是写给她的所有信件,包括他在上班时,或在国外出差时在飞机上写给她的情书,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和传真也都打印出来了,另外,还有20多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都是他在经常出差的地方,如新加坡、那不勒斯、莫斯科和圣保罗寄给她的。所有信件被齐刷刷地剪成两半,用一条蓝色绸带捆扎在一起。最上面的一张纸条上写着:“n杰克,我爱你胜过一切,但是我更爱耶稣。总有一天你会懂我。请不要和我联系。我已经换了电话号码。再见!艾琳。”杰克坐在地上一堆拆开了的礼物中间,盯着天花板发呆,像一个失眠的人在盯着那乱成一团糟的清醒。 杰克有一个非常要好的莫斯科朋友穆利亚?鲍里索夫。尽管穆利亚已经成为两个女孩的父亲,但他仍然保持着大学时代的那种冒险热情。得知杰克的苦恼后,穆利亚和妻子纳嘉(纳嘉也是他们在莫斯科上高中时的一个死党)迅速搞到了打折车票,把孩子留给住在度夏别墅里的爷爷奶奶,然后在尼斯找到一家高档宾馆,和杰克在里维埃拉小聚了一个星期。杰克本来要与艾琳一起在里维埃拉度假,可现在……就这样,他的回程日期提前了五天,在赎罪日前夕来到阿姆斯特丹。n 杰克在斯希普霍尔机场换签过几次航班,但从来没有在阿姆斯特丹市区逗留过。这里,在阿姆斯特丹中心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稀稀落落地站满了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衣着破旧的年轻人,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一切都是灰暗的。街道上,自行车比行人多。海鸥在垃圾桶上空盘旋。这里,有一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杰克,这是一座宜居城市,身处其中精神上倍觉轻松自由。当他缓缓踱回阿姆斯特尔河的船上旅馆时,他看到了这座古城留下的许多文化印记。他自言自语,阿姆斯特丹的市民看似小资,却一点儿也不庸俗。他还欣喜地发现,下午时分,这里成群结队的荷兰年轻女人一点儿也不害怕陌生人,她们对他的好奇报以围观和挑逗。后来,他把这些都写在了日记里。对于一个要赎罪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个多么美妙的地方,杰克想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登记入住船上旅馆后,杰克来到一家舒适的玻璃幕墙餐馆,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份诱人的小牛排和油炸土豆片。现在是下午4点,他决定6点半开始斋戒,这样,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来临之前,他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整理思绪。n 赎罪日说到就到,杰克自言自语,喝干了第二杯啤酒。我作了什么孽?和艾琳分手是一种罪过吗?抑或违背了道德戒律?不和艾琳结婚,我就是犹太人了吗?杰克知道,自从和穆利亚在尼斯相聚又分离度过了那个无眠之夜,经历了早晨的飞行,到达阿姆斯特丹后又喝了许多啤酒,他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知道,他没心思考虑这个问题,却又不能自已。他希望从赎罪日中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真实的答案罢了。他开始责备自己唐突地结束了和艾琳的关系。我本想慢慢来,让她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考虑我的理由。餐馆外面的浓雾由蓝色转为灰白色。杰克点了一杯咖啡。也许我就应该和她结婚,去他妈的犹太性。他想起了第一次和艾琳约会就餐的情景,他们在巴尔的摩内港的一家海鲜餐厅用餐。她整整一个月没有和他亲热了,他也不介意,因为她让他非常享受他们做爱前漫长的前戏。杰克突然感觉到只身一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孤独,渴望身边有女性相伴。他叫来肥胖的侍者,装作喝醉的样子喊道:“你们那个堕落的红灯区在什么地方?埋单!” 没有人感到丝毫惊奇,侍者拿着一幅阿姆斯特丹市区的袖珍地图回来了。这地图像一幅人体解剖图:蓝色的血脉是运河,黑色的神经是主街道,红色的肌肉是桥梁。 “穿过达姆拉克大街,一直向前走,你就会看见。”侍者接过账单和小费,并向他鞠躬表示感谢。n 黄昏时分,一种奇妙的力量驱使杰克在大街上游荡的人群中穿行,来到一条长长的铺着鹅卵石的僻静小巷。几分钟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狭窄破败的小巷。前前后后和他一起在小巷漫步的大都是男人,他们或独行或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偶尔也有成对的男女从身旁经过。杰克还看见带着两个孩子来此旅游的一家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穿着黄色雨衣。运河边,游客们在拍照,相机的闪光一直延伸到运河的尽头。两岸哥特式的建筑,狭窄而又阴暗。每一栋房屋都装着透明玻璃门。起初,杰克为自己盯着这些门往里窥探而感到尴尬。他来来回回走了一会儿,发现这似乎是一个特殊地带的夜间惯例。他听说过,也读过有关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相关信息,但是从来没想到,它竟是一个如此安宁的地方,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大多数城市的红灯区所特有的那种肮脏和犯罪。一些玻璃门挂着帐幔或帘子,灯笼从玻璃门后射出紫红色的光亮,这暗示着女主人正在接客。天气阴冷潮湿,他只能偶尔看见某扇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身着蕾丝内衣的女人。大多数房屋的玻璃门关着,门后站着一些女人,她们面带微笑,频频招手,引诱着游客。运河两岸的街灯发出雾蒙蒙的黄色光亮。透过玻璃门,女人们的身影看起来像褪了色的旧画像。杰克明白了当地的交易规则:轻轻敲门,门半开,如果可以,讨价还价,接着帘幔放下,红灯笼魔法般亮起,透过窗幔缝隙,人影依稀可见。n 杰克在运河水面上的倒影清晰可辨:肉乎乎的大下巴,火红色的短胡子,鹰钩鼻子,浓密卷曲的眉毛,深陷的褐色眼睛。他终于下定决心。黄铜按钮像刚刚抛过光。好征兆,杰克自言自语。他斜靠在门上,舔着干燥的嘴唇,用一块白手帕擦拭着微微出汗的额头。玻璃门后,一名20多岁的金发女子打量着这位顾客。接着,她努起薄嘴唇,打开门。 “上楼吧,下面冷。我已经把暖气打开了。” 这名妓女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只是辅音中夹杂着些许德国口音。她穿一条白色丝质长裤,深红色蕾丝胸罩。她身材娇美,婀娜多姿,杰克看着她像一只体态优雅的暹罗猫爬上楼梯。与身高和体形相比,她的乳房足够丰满,头发染成了金色。 “一次70荷兰盾。你先付钱。” 杰克对这种完全自动的下意识行为感到十分吃惊。正是带着这种下意识,这张苍白的面孔对他下了命令。他打开钱包,付了70荷兰盾。妓女把钱藏在一边,内衣从身上滑落。她解开胸罩,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在一把木椅子上。房间的四个角落里点着四支巨大的红色蜡烛。床很窄,上面铺着富有东方情调的床罩。一个玻璃台面的茶几,两把椅子,光秃秃的白墙,床上方的天花板上装有一面镜子。杰克跨进房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等什么?可以脱衣服了。” 杰克羞赧极了,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喝点水行吗?我口渴。”他小声嘟囔,像个诚实的少年第一次瞒着大人偷买香烟。n “我一般不给客人倒水喝,但对你可以例外。别把杯子打碎了。”妓女用蓝色瓷杯倒了一杯自来水,“算是送你的。” 杰克一饮而尽,“这里的水味道不错。谢谢你。” 他坐在床边,而她坐在正对面的椅子上,抽着烟。 “听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杰克打破了沉默,“我不是来寻欢作乐的,我只是感到孤独。我们聊会儿天,你看怎么样?”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那种只想看看的人。不过,无论是聊天还是鬼混,都一样,付钱就行。如果你打算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就要付100盾。” “那敢情好。”杰克又掏出钱包,数了两次钱。 妓女穿上一件紫色运动衫,用闹钟设定了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杰克问道,感觉轻松了许多。 “安妮特。” “荷兰人?” “不,德国人,来自汉堡。” “为什么来阿姆斯特丹?哦,抱歉,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我收回。”杰克耸了耸肩,这是他表达遗憾的特有方式。 “那你为什么来阿姆斯特丹?”安妮特反驳道。n 杰克本能地想告诉她关于艾琳的事,告诉她他去了一趟尼斯和他来阿姆斯特丹过赎罪日的打算,但不知什么东西阻止了他。 “我是来观光的。我是个作家。”杰克对自己毫不迟疑的撒谎本领感到惊奇。 “看来我一半的客人都是作家。拜托,你撒谎能不能高明点?” “其实……” “这跟我无关,”妓女打断他的话,“你是犹太人,对吧?”她问,直视他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 “你长得和犹太人一样。” “你怎么能看出来?在美国,很少有人能看出来。” “我父亲是犹太人。你的眼睛里有着和他一样的忧郁,即使在你微笑的时候。我父亲过去常说,这忧郁来自于犹太人几百年来的流散生活。” “你母亲是德国人?” “是的。她和我父亲是马戏团的体操演员。我17岁前也经常去演出。” “我还想问一件事,安妮特。你怎么能做这个?” “做哪个?”她又点了一支烟,叉开双腿。 “n哦,这个,我是说,你为了钱和各种陌生男人睡觉,你难道不感到罪过吗?别误会啊,我不是道学家,但仍然……” “有什么不理解的?这是一种职业。钱是好的。阿姆斯特丹物价低,我已经攒了很多钱。” “你打算拿这些钱干什么?” “首先,我打算在法国南部买一套漂亮房子。不过,我想要的多着呢。” 闹钟响了,像消防警报。杰克起身穿上长雨衣。 “哦,非常感谢。”杰克站在屋子中央,打算和她握手。 “我上班时间从不和男人握手。无意冒犯。”她终于露出微笑。 “好,那么,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但请简短点。” “你父母的婚姻生活幸福吗?我是说,一个是犹太人,而另一个不是,这妨碍他们生活吗?” “如果我告诉你,恐怕你还会再来。再说,我不想谈那些事。请记住一点:当你能够理解和包容差异的时候,差异是最好不过了。” 安妮特拉开门,打开了楼梯上的灯,“别忘了带上你的伞,外面正下着大雨。”n 她说中了,倾盆大雨正冲刷着地上的鹅卵石,雨水流进运河,泛起秋天里才有的银光。 第二天上午,杰克睡到10点多钟。他躺在二等舱里狭窄的床铺上,翻来覆去,想让自己再沉入梦中,但饥肠辘辘使他欲睡不能。他必须忍到晚上。在一家露天小吃店里,所有的座椅都是湿漉漉的,杰克要了一杯柠檬茶。赎罪日这一天,他只许自己喝不加糖的柠檬茶。古铜色头发的年轻女招待端来一块刚出炉的苹果蛋糕。 “老实说,我很想吃,但是不行,今天是斋戒日。” “明白了。”女招待报以同情的微笑。 杰克手里拿着一幅地图,径直向南走去。他先是来到罗肯大街,后来沿着维杰泽尔大街一直向前。他走走停停,细细查看那些栏杆和浮雕。他一会儿看看小狮子,一会儿摸摸丘比特,一会儿又盯着一条龙看,不知不觉穿过了六条运河。他向右一拐,来到韦特林大街,发现对面就是国家博物院广场。在一道巨大的拱门下面,街头画家正在出售他们的画作,一支由四个乐手组成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格伦?米勒的作品。杰克从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大胡子画家格列勃那里买了一幅微型石版画,上面画着杰克住的那种船上旅馆、一座小桥及其倒影、一辆歪斜的自行车。n 杰克很喜欢阿姆斯特丹。他喜欢这里暖湿的雾气,喜欢年轻的妈妈们推着婴儿车,喜欢槭树叶子旋转着飘落在河面上。他感觉这个城市不仅需要他,并且已经接纳了他。那位年长的先生,大概是个银行家吧,需要他,因为向他打听前往电影博物馆的道路;鞋店的两位店员需要他,他从他们那里买了一双褐色橡胶鞋。他喜欢这种不拘一格、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赎罪的方式。他感觉越来越饿,身体已经有些飘飘然。大约4点钟的时候,天又开始下雨,起初是毛毛细雨,接着是倾盆大雨,他决定回旅馆换上干净衣服。 往回走的路上,杰克自言自语:“我在这里感觉很幸福。我在这里真的感觉很幸福,我跟着一大群人,可谁也不认识我,就像一片鲜红的槭树叶顺着水流漂向大海。” 雨伞落在了旅馆,杰克很快就被淋了个湿透,感觉就像约拿被鲸鱼吞进了肚子。“一座座小桥、一辆辆自行车、怪兽、男中音、贝迪克大街、市长。”杰克小声嘟囔着,数着他一天里不断变换的印象和《旧约》里的英雄故事,“你能在沼泽地里举起一只怪兽吗?哈,你能吗?你能娶一个非犹太女孩为妻吗?这算是什么问题啊?”n 回到旅馆,杰克冲了个热水澡,然后擦干身体,用毛巾裹住下身,在日记里写着什么。随后,他换上干净衣服,系上领带,穿上外套,在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然后又一头冲进雨中。这一次,他向东奔去,奔向位于塞法迪聚居区的犹太教堂。“塞法迪犹太教堂建造于17世纪。它是全世界最雄伟的犹太教堂之一。你一定要去看看,儿子。”杰克想起了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威严的声音。他的父亲一直为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犹太人感到骄傲,他骄傲那个犹太教堂曾被比作所罗门圣殿。 杰克在雨中穿行时,想象着将要听到羊角号吹响的那幢建筑。可能是因为有关塞法迪犹太人的缘故,他想象中的建筑具有摩尔风格。地图上已经标出了这座犹太教堂的确切位置,就在维萨广场和莫德大街的尽头。但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一座用深色砖块砌成的立方体建筑,上面砌有栏杆,看不见屋顶,比周围的建筑高出许多,雄伟异常。杰克心想,这或许是银行,或许是军械库,或许是铸币厂,但绝对不是犹太教堂。他四处转悠,找到了入口,试图推开那沉重的大门,门上方一只石刻的鹈鹕正在喂三只小鸟。大门紧闭,他开始敲门,无人应答。“怎么回事?犹太会堂怎能在赎罪日不开门?”他边捶门边想,“这建筑不是摩尔式的,一定不是塞法迪犹太会堂。”n他向前走了百十步,希望能找个人问路,可四周空无一人。他来到一个由褐色石头砌成的院落,高大的门廊,白色的柱子和玄关。当他往回走,正要回到大街上去的时候,门开了,两个妇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朝着他走了出来,步态缓慢而又优雅。在杰克看来,这三个人属于地道的荷兰中产阶级,浅黄色头发,皮肤白皙,穿着体面。但是,他走近时,感觉很奇怪:这三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穿着毛料长裙,两个女人的帽子上都戴着黑纱。难道她们是去参加葬礼吗?在星期四晚上?这个时候?杰克跟在后面,边走边想。他跟着她们回到了那幢黑黢黢的、有着高大窗户和栏杆的立方体建筑前。其中的一个女人敲了敲大门,无人应答。她们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个男人用荷兰语说了句什么。杰克冲向门口,向里面窥探。他看到几个体格健壮、头发卷曲、留着黑色胡须、戴着圆顶小帽的男人边抽烟边小声交谈。他立即认出他们是这里的保安,便走进去,向其中的一个打招呼。 “你好,我可以进教堂吗?” “你好,朋友!你一定是美国人吧?”一个保安边回答边递给杰克一顶黑色无檐便帽。 “谢谢,我自己带了。”杰克说着,伸手掏口袋。n 大门又吱呀作响地关上了,杰克听到了沉重的门闩发出的哐当声。他跨上白色台阶,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右边的那扇门一定是为女人们设置的侧廊通道。”杰克心想。他进入一个宏大的圣堂,阳光透过拱形窗户漫射进来。圣堂共有三个侧廊。成排的大理石圆柱支撑着会堂的拱顶,靠墙的地方是稍小一点的圆柱,每根柱子都支撑着二楼上的侧廊。杰克很喜欢一楼圣殿的座位布局:深色木板凳上的托架相互对应,朝向空地的一边,这样,会堂里的信徒在祈祷时就可以面对面。大殿尽头的那面墙上画着诺亚方舟,另一头,正对着诺亚方舟的是高高的诵经台。杰克坐在板凳的一角,开始打量这里的信徒。傍晚5点钟左右,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人。圣堂渐渐沉入昏暗,窗户的颜色由蓝灰变成烟灰,最后变成黑暗夜空的颜色。越来越多的人们来了,离吹响羊角号的时间越来越近。两个小时后,圣堂里已经挤满了人。 杰克对宗教仪式毫不关心,对希伯来人也知之甚少。在家时,即使重要节日,他也一切从简。现在,他急于观察的不是赎罪仪式,而是那些信徒:男人和男孩。他根据脸型把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种人脸型瘦削,皮肤黝黑,是典型的地中海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很粗壮,个子不高,黑眼珠,鹰钩鼻,黑头发,偶尔也有长着红头发的,他们是阿姆斯特丹的奠基者――n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后裔。另一种人是典型的荷兰人和德国北方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这些人个子高挑,皮肤白皙,发色浅,脸形方,鼻子小而尖。“这些男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是居住在德国、波兰和立陶宛等国犹太人的后代。”杰克回味着父亲曾说过的话。 杰克发现,人群中有四个男人与众不同。其中一个长相酷似匹克威克:身材肥胖,脸颊肥厚,三重下巴,笑容温和,眼球突出,眼神幽默,身穿燕尾服,头戴高帽。和他随行的大概有30多个人,其中包括唱诗班的领唱。不一会儿,一个表情严厉的犹太人走了过来,他留着铲形胡子,鼻子特别令人难忘。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少年,他们皮肤黝黑,上嘴唇上已经有了毛茸茸的黑色阴影,正在用祈祷巾上的流苏挠邻排一个男孩的脖子。此外,一个身材修长的绅士,正异常冷静、十分自信地用冷漠的绿眼睛瞅了瞅鼻尖上的眼镜。杰克心想,这家伙要么是律师,要么是银行职员。最后,杰克还看见一个年迈的老人穿着已经破旧的三件套海军服在虔诚地祈祷。老人后背微驼,脸上满是浓密的胡须,微微发红的大耳朵支棱着。n 领唱走上诵经台,他看起来像一个退役的步兵少校,纹丝不乱的银色短发,整齐的小胡子,方下巴。表情虽然严峻,他的声音却柔和嘹亮,充满激情,“哦,它能把黄油融化,它真的能把黄油融化。”杰克回想起了母亲在波西米亚见到理查德?塔克尔并听他演唱时的那种激动。当诵经台上的领唱开始唱起圣歌时,黑夜已经降临,整个教堂陷入一片黑暗,只有诵经台还亮着。两个男人蹑手蹑脚,在台柱周围和墙根来回忙碌着,点燃了一支支蜡烛。他们小心翼翼,尽量不打扰领唱和已经沉浸在赎罪的神秘气氛中的会众。很快,数以百计的烛光开始在教堂里闪烁。n 烛光和低沉的吟唱把杰克从昏昏欲睡中惊醒。尽管他不觉得自己与这紧紧挤在一起的会众们有什么不同,但他仍然感到孤独。此外,在一楼圣堂,女性的缺失使他想到了这些祈祷者的妻子。她们在楼上是否准备与丈夫和儿子再次融为一体。杰克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每个犹太男人都应当娶老婆。可他已经36岁了,结婚却还远着呢,未婚妻连影子都没有。紧接着,他和艾琳一起度过的两年幸福时光和他们突然分手的情景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如何才能爱着某人却不和那人生活在一起呢?他想。这时,圣歌回荡在大殿里的每一个角落,杰克双眼紧闭,十指相扣,回想起了他和艾琳一起游览过的每个地方:两人常去的安那波利斯,3月的基韦斯特,滑雪胜地太阳谷。后来,他又想起了佛蒙特北部山谷中的一个村庄。他和艾琳在相识后的第一个夏天,就去那儿待了一周。 红透的野草莓零零星星散落在草地上。他们已经不想用手采摘,干脆跪在地上,挪动膝盖,直接用嘴巴咬掉枝蔓上那些虽小却极甜的野草莓。当时,草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远处的峰峦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并投下影子。蜜蜂嗡嗡叫。渐渐地,他们挪到了草地深处,远离道路。他们躺在树荫下,树叶沙沙作响。杰克穿着牛仔短裤,艾琳穿一件短背心和一条褪了色的纯棉紧身裤。 “杰克,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艾琳抚摸着他的胸口。 “你告诉我。”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一大片草地,长满了野草莓。” “那太好了。有一大片草地,并且周末不用干活。” “是的,我们,我,你,孩子们,还要一起去教堂。” 杰克感到心中一阵寒冷,冷冷地说:“艾琳,你知道我不去教堂。” 艾琳眼中满是沮丧,脸一下子红了。 “n我是说,我们全家要一起去一个精神上的圣地,不一定是教堂。你怎么啦,亲爱的?” “没什么。一切都好。” 她翻身爬过来,亲吻着杰克的肚子。杰克并不阻拦。她的右手摸到杰克的短裤上,然后低下头。他越来越接近生活的边缘,接近那个无形的世界。他抬起头,望着远处的群山,然后闭上眼睛。后来,他呆呆地盯着头顶上方万里无云的蓝天。躺在温暖的草地上,女友就在身边,他感觉热烈而又真实,而他的另一半――灵魂?精神?抑或呼吸?则已经和身体分离,冲到了九霄云外。他知道艾琳需要他的宽慰和关心,但是,他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那一刻,他十分孤独。那一刻,就在那里,在佛蒙特的草地上,他已经知道有些不对劲。此后,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把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变成了语言。 刺耳的羊角号把杰克带回到现实,带回到阿姆斯特丹。他查看四周,看到两个身穿百褶裙的小姑娘冲过过道。她们兴高采烈,开心地笑着,扑向“匹克威克先生”。从他们的谈话中,杰克只能听懂“爸爸”和“羊角号”n两个词。那位父亲水汪汪的眼睛里溢满了微笑,他胖胖的手指压在嘴唇上向她们示意,然后依次抱起两个孩子,放在膝盖上。两个小女孩吻了父亲,细胳膊环绕在他的胖脖子上。我是否早在佛蒙特时就知道不能娶她了?难道一想到要在礼拜天和艾琳带着孩子们去教堂,我就受不了吗?杰克望着会堂的拱形屋顶,赎罪的狂喜紧紧地掳住了他。像大病初愈一样,杰克感到一阵轻松。会众们相互致意,或拥抱亲吻,或握手问候。杰克也和身旁的人们握手致意,然后匆匆穿过侧廊,向出口走去。 在塞法迪犹太教堂外的拐角处,杰克找到了一家餐馆。里面的陈设和船舱一样,用大桶做餐桌。杰克点了两杯伏特加,一份烤鲱鱼,一份鱼汤和一份西兰花烤鹅肝。“为健康干杯!”他微笑着对侍者说,“祝你永远幸福!”杰克感到无比幸福,狼吞虎咽,吃光了全部食物。末了,他在桶上留下多多的小费,走出门外,将晚上带着咸味的湿气深深吸入胸中。n 在回旅馆的路上,杰克异常清醒,尖顶屋的黑色轮廓,月光下屋顶上光洁湿润的瓦片,运河上轻轻摇曳的船影,都一一抛在他身后,并清晰地留在了记忆中。人生的辉煌和大彻大悟的感觉,都如创作一样,使他醍醐灌顶。杰克不再想赎罪日,不再想艾琳,不再想他的犹太人身份和艾琳的基督徒身份。那些事他早已想开了,即使心中的结还没有完全解开,阿姆斯特丹的见闻也使他感到了些许安慰。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他拿定了主意:他要回到巴尔的摩,因为在他和家人移民美国17年后,他们已经在那里扎根;他们甚至把祖父母的遗骨从莫斯科运至巴尔的摩,并在那里埋葬。再过四年,当杰克年满40岁时,他差不多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半辈子。19岁离开俄罗斯的时候,他已经背着重负上了飞机。这重负如此沉重,以至于他要花上几年的工夫才能卸下;它又如此高耸,以至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曾经数次难以站稳脚跟。第一次飞越大西洋,也是他战胜恶魔、战胜妖怪和战胜犹太人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诱惑的一次飞行。 雨停了,杰克闻到了甜甜的槭树叶味道,闻到了腐烂的树叶、汽油和大麻发出的混合气味。他站在船上旅馆的下甲板上,看着阿姆斯特尔河两岸闪烁的昏黄灯光,呼吸着阿姆斯特丹夜晚的空气,尽情地享受着夜晚的柔情。一想到明天将要飞回巴尔的摩的家,他顿觉心旷神怡,心中描绘着他那造化弄人、天意难违的美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