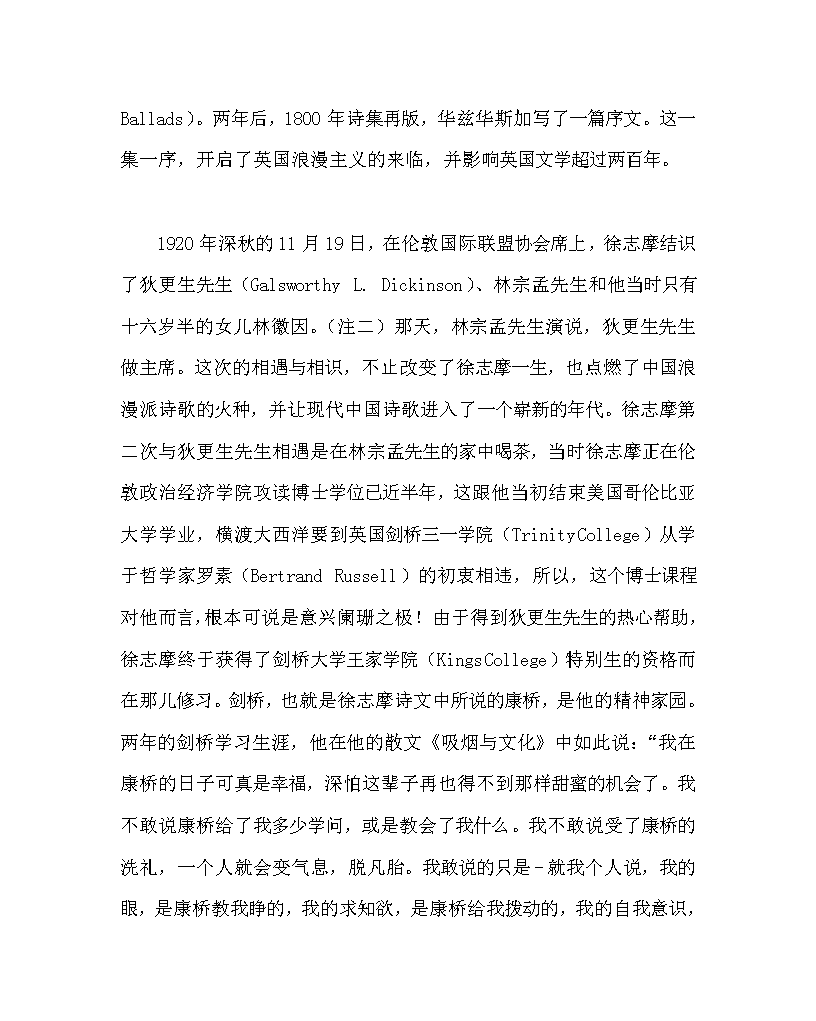- 65.50 KB
- 2021-02-26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语文论文之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 廖钟庆
廖钟庆
On Xu Zhimo's “Farewell again to Cambridge!”
Liu Chung Hing
一、
1795年,是英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9月26日,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与他唯一的妹妹多罗茜(Dorothy Wordsworth)搬进了由友人裴尼先生(John F. Pinney)无偿提供的在多塞特郡的雷斯唐农庄的住所(Racedown in Dorsetshire),一方面,诗人华兹华斯结束了多年飘泊无依、到处寄居的流浪生涯,另一方面,他挥别了烦嚣的伦敦,并且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真正的家,让他的诗歌创作生命重新找到了据点。两年后,华兹华斯和他的妹妹多罗茜从多塞特迁到Somerset的Alfoxden,最后在1799年12月定居在卡斯米尔的“鸽舍”(Dove cottage at
Grasmere),华兹华斯才真正重新回到这个曾长期滋润了他的幼小心灵与养育了他的绚烂诗情的湖区。在这个地灵人杰的栖息之所,诗人得以再出发,重新开始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是,同年的秋天,诗人华兹华斯和妹妹往访恩人裴尼先生,在他的家中,结识了当时比华兹华斯远较有名的诗人兼评论家柯尔律治(Samuel T. Coleridge)。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兄妹的频繁亲密的交往要在1797年他亲自到Alfoxden去拜访华兹华斯兄妹之后(根据Everyman´s Library 的S. T. Coleridge Poems一书里p.78的记载,柯尔律治全家在1796年年底搬到在Nether Stowey居所,同书的《年谱》记载,1797年3月华兹华斯来访,他在6月到雷斯唐回访,7月华兹华斯兄妹与另一诗人Charles Lamb一起去拜访柯尔律治。7月之后,华兹华斯为了住得更靠近柯尔律治在Nether Stowey居所,已由雷斯唐农庄搬到Somerset的Alfoxden,两家相隔仅仅是三英里多!),他们谈诗论艺、一起进餐、喝茶、散步、写诗,并互相鼓励和彼此之间为对方的作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从1797年至1798年,这一整年,根据柯尔律治自己对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的描述是如此:“三个个体,而一个灵魂。”(Three persons and one soul)(注一)由于这一整年的持续谈论和经常作长长的散步(根据多罗茜的1797年与1798年的《日记》Journal所载,他们常常是在朗月的光辉下散步),这样过了一年,也就是1798年,这两位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而又对剑桥彻底失望的诗人华兹华斯和诗人柯尔律治,便合作出版了他们的诗歌合集 - 《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两年后,1800年诗集再版,华兹华斯加写了一篇序文。这一集一序,开启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来临,并影响英国文学超过两百年。
1920年深秋的11月19日,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徐志摩结识了狄更生先生(Galsworthy L. Dickinson)、林宗孟先生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半的女儿林徽因。(注二)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狄更生先生做主席。这次的相遇与相识,不止改变了徐志摩一生,也点燃了中国浪漫派诗歌的火种,并让现代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徐志摩第二次与狄更生先生相遇是在林宗孟先生的家中喝茶,当时徐志摩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已近半年,这跟他当初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业,横渡大西洋要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从学于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初衷相违,所以,这个博士课程对他而言,根本可说是意兴阑珊之极!由于得到狄更生先生的热心帮助,徐志摩终于获得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特别生的资格而在那儿修习。剑桥,也就是徐志摩诗文中所说的康桥,是他的精神家园。两年的剑桥学习生涯,他在他的散文《吸烟与文化》中如此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 -
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除此之外,这里有他的盟誓,这里有他的梦……。离开剑桥,返回中国的六年后,1928年的初秋时分,徐志摩重访了剑桥,在回国的归途船上的11月6日,他写下了他的传世名篇《再别康桥》。《再别康桥》是现代诗歌中公认的佳作,是一首多层次的诗,寄意深远隐晦,不易解读,在诠释这一首诗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名诗。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二、
《再别康桥》是一首英国民谣体(ballad)体裁的抒情诗歌,它具体地充分体现了一种情理交融、主客合一的诗歌理论,也就是说,徐志摩在这首诗里,将康桥客观的自然风光与诗人的主观沉思想像,通过一个不断锤炼消融的历程,而最终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达至一种高度的冥合。显然地,这首诗的独特风格,深深受到华兹华斯的诗歌以及他的诗歌理论的影响。徐志摩相同风格的诗还有1925年所写的《秋雪庵芦色》与《在哀克刹脱教堂前》二诗。不过,《再别康桥》这首诗的韵脚已彻底摆脱了英国民谣体abab押韵方式,与单数诗句抑扬四步格(iambic tetrameter)以及双数诗句抑扬三步格(iambic trimeter)交替转换的机械性(注三),而向传统中国诗歌歌行体的韵律回归,并以深具中文特性的音顿、意顿的方式取代了英诗机械化的抑扬四部格与抑扬三步格的迭相交替。
全诗分别以六小节去展开。第一节一开始便点出了三个最重要的意象,一个是“静”,一个是自我意识的“我”,和一个是诗人要作别的对象–西天的“云彩”。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过,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并且,这些好诗都“导源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情感”。(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注四)“静”,客观地言之,是离别时康桥的主旋律,但主观地言之,则同时也是诗人徐志摩创作这首诗歌时的内心宁谧境界,这是客观的自然景致与主观的心灵活动的密切同一,(这在下面的诗行中仍会进一步充分地展开,他透过写今晚的康桥的宁静来全面彰显诗人的内心世界),所以,诗人的归来与别去都是“轻轻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南北朝梁代江文通《别赋》里的话。离别的情绪,当然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强烈的感情就是浪漫主义诗歌所要凸显的所谓属于自我的真实的感情。自我真实的感情背后的“自我”,在浪漫主义的诗歌中,完全充尽地提升到君临于一切之上的地位。是不是正因为这自我真实的强烈感情的真实呈现,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才能真正引发出我们的真实共鸣和强烈地感染了我们?西天的“云彩”有特指,诗歌的标题是“再别康桥”,事实上,诗人这次要告别的却是黄昏暮色中永恒停驻在康桥的西天上的“云彩”!
“云彩”
指的是林徽因,河水是徐志摩。这在徐林的诗作中都充尽地展示出来,如徐志摩《偶然》与《云游》,林徽因的《藤花前》与《死是安慰》等诗,并且,徐志摩在他的散文《自剖》中就说的非常明确,他说:“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在这首诗里,天空中的“云彩”,轻盈明艳,她凭藉着夕照余晖的那一点子光亮,便投影到静静的康河的河水上,于是便形成了倒影 - “波光里的艳影”。“云彩”,她点染了地面上卑微的河水的空灵,让他觉醒过来,这对地面上的河水来说,是否就是一种意外?还是意味着一种命定?不管怎么样,对河水而言,确然无疑地便是:“在我的心头荡漾”。不单如此,夕照的余晖,同时也照耀着康河河畔的“柳”树,让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泽,金光闪闪,像黄昏暮色中的新娘一样娇艳。金“柳”,她象征着什么?她也投影在康河的河水上吗?那岂不是形成了多重倒影?云影,再加上柳影,这是何等的灿烂缤纷!云与河水的投影关系也许只是偶然的,但是,这却是一个“永恒的图画”,一如徐志摩在《偶然》、《云游》诗中所展示的。但是,在《再别康桥》这首名诗里,这个“永恒的图画”似乎将被打破。难道加上了柳影,就让这个投影关系变得如此地异常复杂?是否金“柳”仅仅只是“云彩”的化身而蒙骗了河水?不然,她又可能是什么?难道诗人要在这里制造一种扑朔迷离,故意增添了我们的困惑?
让我们重新回到康河的河畔。从河畔下滑到河边的软泥上,那绿油油的参差荇菜,色泽光润而轻灵摇晃地在康河河水的温柔的轻波中曼舞。那迷人的舞姿,那逍遥的韵致,竟会让诗人徐志摩不期然地许下重愿:“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是他对康桥无限的眷恋吗?是他期盼着能融入康桥的美景中而与康桥成为一体吗?是他对美艳迷人的夕阳中的新娘太过痴情迷恋而甘心成为一条水草自愿留下相伴?假如夕照下的金柳欺骗了你,那你该怎么办?又假如那只是一个垂死的新娘,那你也甘心留下来陪伴着她?
但是,诗人没有让我们停下来 - 停在河水中软泥上的青青水草上。他的想像的翅膀竟凭藉着夕照余晖那一点子的亮光,沿着康河的河水溯洄而上,引导我们来到榆树树荫下的拜伦潭(Byron´s Pool)。拜伦潭原为一个堰潭(the weir pool,就是筑坝堤将河水拦起来而形成一个大水潭),因为浪漫派诗人拜伦在剑桥学习时经常在这儿游泳而得名。夕照的余晖洒落在这个遍长着水草的潭水上,彩色的鱗漾伴随着水面上的浮藻,在这河水的回流的水潭中共舞。这个拜伦潭,它“不是清泉”,而是神圣之地,是立下永约的地方,所以说“是天上虹”!《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第12节至17节上记载说:“上帝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旧约《创世纪》里的云彩、虹与水这个盟誓的组合,是徐志摩这首诗之所本,也是全诗最难解读出来的地方。(注五)我确信,1921年的四五月间,林徽因和徐志摩在这拜伦潭前确曾指水为誓的。假如我依据这首诗所引导出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他们的誓言的内容具体地说了些什么?能完整地还原出来吗?是谁没有信守誓言而最终导致了两个“今之伤心人”?是不是正因为盟誓的毁弃,所以那作为盟誓记号而缤纷五彩的虹才被揉捏成无数的碎片飘散在浮藻之间?破碎了的彩虹,这永约誓言的记号,还显现在天上的云彩中吗?不!它们早已沉淀在拜伦潭潭底下而变成一个残破不堪、再也无法组合但仍美丽迷人的梦 - “彩虹似的梦”!
1922年年底徐志摩离开剑桥回国,他写下了《再会吧康桥》一诗,这首诗后来收进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里,到1924年林徽因彻底斩断了与徐志摩的感情纠缠,而与梁思成远赴美国宾州大学求学,徐志摩的感情世界完全崩解,苦闷伤心已极!(可参阅他1923年的《西湖记》)到《志摩的诗》再版时,他就把这首《再会吧康桥》从诗集中抽出。这首诗里就详细地记录了这个甜美的“梦”!诗上说: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
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透过以上的诗句,我们可以综合分析得出他们盟誓的具体内容不外两点:一、创作诗歌,二、落实爱情。徐志摩与林徽因于1921年四五月间在剑桥发生了短暂但激烈的爱情故事,除了陶醉在他们的初恋的甜美之中外,他们还共同地热爱着英国浪漫派的文学,尤其对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与诗歌理论更有一种痴情的迷恋,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开创出中国的浪漫派诗歌风潮,进一步,他们更想仿效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一样,出版一本他们的诗歌合集–中文版的“抒情歌谣集”!这就是当初他们的盟誓,这就是当初他们的梦!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待林徽因在1923年春天能和徐志摩一起回剑桥进修才有其可能性,然而,事实上,徐志摩回国奋斗了一年多,直到林徽因在1924年选择与梁思成赴美而宣告彻底终结!
誓言已毁,梦已破灭。徐志摩在他的《再会吧康桥》一诗的结尾处这样写: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显然地,1923年春天,徐志摩并没有重返剑桥,要等到六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初秋,他才重返故地!华兹华斯的名诗《丁登寺》(Tintern Abbey)一开头如此写道:
Five years have past; five summers, with the length
Of five winters! And again I hear
These waters, rolling from their mountain - springs
With a soft inland murmur.
五年过去了,五个夏天,还有
五个漫长的冬天!并且我重又听见
这些水声,从山泉中奔流而下,
在内陆的溪流中柔声低语。
我确信,1928年初秋,当徐志摩重返剑桥,再次见到这被他认为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的康河和重新再听到康河潺潺的流水声时,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应该就是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所不同的是,华兹华斯经过了五年,而徐志摩经过了六年!华兹华斯初访丁登寺时是只身而来,五年后,与妹妹多罗茜同来再访,而徐志摩当初与林徽因两人在康河这儿指水为誓,等到徐志摩离开剑桥后六年再次回来,却是带着无尽的悲伤与疲惫孤身前来!面对着拜伦潭,连同着一颗破碎的心,想到了那个沉淀在潭底下的破碎的梦,我相信徐志摩的内心是有怨言的,他能做些什么呢?“寻梦?”是不是那只是文学上修辞学的反讽?
诗人徐志摩真是痴傻!究竟是他不服气、不接受梦已破碎这个客观的事实吗?还是他仍期盼着奇迹的出现?他要让他的小船逆流而上,那怕是追寻到康河河水的源头,他也要继续寻回那个完整的美梦!“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是不是还有更青处?能停下来吗?是不是他这样子想,让小船逆流而上,就能让时间倒回去,回到1921年,然后再让它永恒停留在那个时间点永远不动?还是他想回到那个时间点再出发,让梦能够实现?但是,小船又如何能办得到?事实上是,黑暗早已经成形了,桃源望断,寻梦无处,斑斓的星辉洒落,压满一船。本来,在星光下听流水声,是他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他认为,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人的性灵,但是,现在呢?现在诗人只想放怀高歌。狂歌当哭?是他要唱出他内心的悲伤?-“她的负心,我的伤悲”。假如仍有可能寻得到梦,是不是寻到的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黯淡而无光辉的梦?是否诗人只能躲在这样的一个“梦的悲哀里心碎”?(注六)那就放怀高歌吧!然而,今晚剑桥离别的主旋律是“悄悄”、是“静”!那一片静,在星辉寂静的夜里,无休止地、无穷尽地向四面八方蔓延,连夏虫似乎也受到了感染而噤声,今晚剑桥的静似乎就是绝对的!难道诗人已别无选择?是不是生命早已描定了她的式样?难道“无梦也无歌”竟是命定的?我常想,一个人,假如活到了生命里无梦也无歌的地步,那岂不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吗?是不是徐志摩在这一长段共八行的诗行中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无梦也无歌的悲哀?
誓言已破,寻梦无从。诗人原想放怀高歌,唱出内心的心声,是苦闷吗?还是孤寂?是无奈吗?还是悲伤?然而,剑桥今晚的宁静却是绝对的,诗人的离去,只可能是“悄悄的”,一如他的回来。停驻在剑桥西天的那片永恒的云彩似已渐渐隐入夜空中,诗人面向着她,摆一摆手,珍重吧!云彩,再见吧!诗人踏上他长长寂寞孤单的归途,便与剑桥西天上永恒的云彩无穷地拉开……。
三、
柯尔律治曾经将华兹华斯的诗歌特点归纳为六大优点:一、语言极度纯粹。二、思想感情明智而强烈。三、每个诗行、诗节,既有独到之处,又有力量。四、完全忠实于自然界中的形象。五、沉思中,包含同情,深刻而精致的思想中带有感伤。六、想象力丰富。假如我们将华兹华斯诗歌的六大优点去透视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一首诗,那么,我们就清楚地发现,《再别康桥》与这“六大优点”完全对应,若合符节!也可以说,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以及他们两位的诗歌理论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对诗歌语言有很深入的讨论,一方面反对那些令人生厌的“诗歌辞藻”(poetic diction),也就是反对使用那些陈言套语,(唐朝的韩文公的《答李翊书》中谈到创作古文特别提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另一方面是强调人的实际使用的语言(the real language of men),让日常语言入诗。他们摒弃了英国新古典派诗歌所强调的“艺术的语言”,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艺术的语言”出现在那些二三流诗人的诗歌中,事实上,只是一些陈腔滥调的重重复复罢了!(我一看到那些现代写诗的人也鹦鹉学言地写“春暖花开”什么的那些滥调陈腔就头特别疼!此外,我看到不少人谈论徐志摩《再别康桥》这首诗时喜谈这首诗具备所谓的“三美”–
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显然是不懂英国民谣体是怎样的一种诗体而有的滥调陈腔!)是不是正因为活生生纯粹的语言的注入,才使诗歌表达出的感情更亲切、更真挚动人?此外,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在诗歌的创作中是最重要的,它是点化日常生活与自然景致的神奇力量,日常语言应用到诗歌里,本来很容易流于庸俗,但是,英国浪漫派却没有让他们的诗歌走向写实主义,靠的就是诗人瑰丽驰骋的雄奇想象力!(注七)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说把诗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在本文的第二节中我已对这首名诗做出了长长的分疏,但是,我想在下面更进一步深入去探讨这首诗中更深微之处,看看诗人徐志摩那瑰丽驰骋的雄奇想象力!
一首好诗,往往是多层次的。《再别康桥》亦然。
首先,《再别康桥》是一首描写剑桥自然风光的抒情诗,而主题则是离别与离别的感伤。
进一步,隐藏在《再别康桥》一诗背后的深层结构里,是盟誓被背弃后的原先的美梦之破碎,与深入地写寻梦之不可能性。这个意旨,由诗中的“云彩”、“金柳”、“虹”、“彩虹似的梦”与“寻梦”等意象组成。最为关键之处,是对夕阳中的新娘的“金柳”之文学隐喻的理解。假如在这里把“金柳”了解为“欺骗”的话,那么,诗人徐志摩在这首诗里就不单只是“有怨言”
而已,根本就是控诉云彩化身为金柳,对他的感情的欺骗以及背弃了他,也就是说,诗中使用了隐晦的方式指责林徽因欺骗了他的感情与背弃了婚约。(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年谱》里说徐志摩和林徽因有婚约,可信!他的资料来源应该得自徐志摩的好朋友凌叔华女士,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是徐志摩亲自交给她保管的,凌女士自己看过日记,还在她家中让叶公超先生看。婚约之说,可能出自《康桥日记》,也不排除是徐志摩本人亲自告诉凌女士,后由她转告陈从周先生。然而,这首诗却同样拥有确实的证据!)“柳”,在英国文学中有“遗弃”、“背弃”的意思,开始这样使用始见于华兹华斯的朋友诗人兼小说家Sir Walter Scott的小说The Fair Maid of Perth,里面有一句话如此说:“柳叶花环展示了我被遗弃的婚约。”(A wreath of willow to show my forsaken plight.)自此之后,一个恋爱中的人为他所爱的人所遗弃就叫“带着柳环”(to wear a willow)。假如照这样去理解的话,那么,夕阳中的新娘的“金柳”就是一个感情与婚姻的欺骗者!由代表林徽因的“云彩”,演化为骗人的新娘的“金柳”,到永约的记号的“虹”的崩解,一直发展到“梦”的破灭以及“寻梦”的不可能,这首诗背后的伤悲的确不易解读出来!
然而,《再别康桥》这首诗里还有一层意思是更深微的,我认为它是深受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的“死亡”概念所影响。(Lucy
Poems,共五首,全都是英国民谣体,写于1799年,在1802年《抒情歌谣集》第三版出版时,五首“露西组诗”全被收入诗集里。这是华兹华斯仅有的五首情诗,意境凄美,淡淡的韵味,自然、朴素而柔和!)要掌握这层意思的关键也在“金柳”。在这儿,“柳”是死亡的象征!柳象征死亡,在英国文学里,远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Othello)中的黛丝泰蒙娜(Desdamona)临死时曾唱过一首“柳树歌”,就表达了她的悲哀和暗示了她的死。丹麦的安徒生童话中的《柳树下》(Under the willow tree)也是写在柳树下死亡。此外,英国的传统民歌里就有《柳树歌》(The Willow Song),其中的歌词有:
She hears me not, she heeds me not
Nor will she listen to me
While here I lie alone
To die beneath the willow tree.
Sir W. Scott也曾写过一首Where shall the lover rest的诗,里面也提到“在柳树下死亡”。徐志摩喜爱的诗人克里斯蒂娜 • 罗塞蒂(Christina G. Rossetti)的哥哥丹蒂•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就曾写过《柳树林》(Willow Wood)的组诗,这是一组悼念爱人的诗,柳,就代表着哀伤、死亡与悼念。在这首诗里,除了“柳”代表着哀伤、死亡与悼念之外,还有“榆荫下的一潭”
这一诗句中所彰显的“榆”与诗人“拜伦”的关系,似乎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哀伤、死亡与悼念!因为拜伦早年曾有一首叫做《在哈劳墓园的榆树下》诗(Lines Written beneath an Elm in the Churchyard of Harrow),这个墓园正是拜伦早年常来的地方,并且常常坐在榆树下一坐就几小时!在他的诗里或后来给朋友的信里都经常提到他“自己曾愿望躺在这儿”。1822年4月仅仅只有五岁的拜伦的女儿Allegra去世,拜伦就是将她安葬在这儿!剑桥的拜伦潭,现在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一直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树,为什么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特别钟情于潭边的榆树?是不是他重点地提到了榆树正是要加强我们对金柳是死亡象征的认识?假如徐志摩在这首《再别康桥》中的“金柳”是代表死亡的话,那么,夕阳中的新娘就是一个垂死的新娘,而“云彩”也就代表死亡,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一样ceased to be!1928年3月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与梁思成结婚,对徐志摩言,他心中的林徽因已经彻底死亡,并且在他的内心中,她已演变成了永恒的林徽因,她的美丽也是永恒的,因为那种美是来自自然的,正如华兹华斯“露西组诗”中的露西一样。并且,已经没有人能把她抢走,因为她永恒地停驻在剑桥西天的天空上!她来自自然,最后又回到如诗一般美丽的剑桥的自然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再别康桥》就是一首悼亡的抒情诗,也就是说,它是哀悼爱情的死亡与埋葬的挽歌,也许叫做Elegy更恰当。它的基调仍是凄美的、悲伤的,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
以上列述《再别康桥》一诗中所包含的三层意义,每一层意义都可以是独立的,但是,也可以是三层意义合而为一的,诗人徐志摩写这首诗时也许就是多义性的。这种多层次的诗,正显出诗人徐志摩的想象力雄奇丰富!是不是正因为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一首诗,展现了他的非凡的想象力与抒发了他的深挚的感情,所以这首诗才一直为我们所喜爱,并且成为一首传世之作?
四、
假如华兹华斯的朋友卡尔瓦特(Raisley Calvert)不是因为极度欣赏他的诗才,在他逝世的1795年1月份留下给华兹华斯900英磅的巨款,我想,就算是裴尼先生无偿地让出雷斯唐农庄给华兹华斯兄妹居住,以他们当时的经济能力言,根本是无法住下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穷了。假如柯尔律治在剑桥进修时,不是早已读到华兹华斯最早的《黄昏漫步》(An Evening Walk,1793)与《景物素描》(Descriptive
Sketches,1793)这两本诗集,对华兹华斯的诗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就算他们于1795年在裴尼先生家中相遇相识,恐怕也很难击出什么火花。因为当时的柯尔律治在文坛的名声远高于华兹华斯,他们极可能只会寒暄几句,而不会有进一步的来往甚至深交。正因为柯尔律治自己是一位天才横溢的杰出诗人,并且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慧眼能识别谁是真正的英雄。他一眼就能辨认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密尔顿(John Milton)之后最伟大的诗人!假如不是因为这位杰出的诗人兼评论家柯尔律治对华兹华斯的才华的肯定、激赏、鼓励与衷心的赞美,本来早已对诗歌创作失去信心的华兹华斯,就不会恢复自信,并且进一步把他潜在的诗才像火山一般迸发出来,在他们早期密切相交的十一年间,也就是说,从1797年到1808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所有他的好诗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包括他那首伟大的《序曲》(The Prelude)也早在1805年写出。(是他的自传式的长诗,一直不断修改,到死后才出版!)相对地,柯尔律治在1797年分别写出《忽必烈汗》(Kubla Khan)与《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等名诗,也得到华兹华斯的鼓励与催促而完成。1798年10月4日,《抒情歌谣集》出版,收集华兹华斯的诗19首,柯尔律治的诗4首,这个第一版的诗集共收集了他们两位诗人的诗共23首,于是便宣告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来临,并让英国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年代!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里对他与华兹华斯的相交有如下的说明,他说:
在华兹华斯先生与我成为邻居的第一年间,我们的谈论,常常交集在诗歌的两个基本课题上,那就是:藉着一种对自然之真理的坚决忠诚,以激起读者的同情的力量;与藉着对想象力之缤纷的修饰,以促成对新奇产生兴致的感觉的力量。突然变化的光与影,或来自月光,或来自夕阳,散发在已知与熟稔的景致上,这种偶现的迷人魅力,似乎正表示着两者之间之结合的实用性。这些都是自然的诗歌。……《抒情歌谣集》的计划,便源于这种观点。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彼此同意,我致力于集中在人物与角色的超自然上,或者说,这至少也是浪漫的;不过,尚须从我们的内在的本性中,移植出人性的情趣,与真理的投影,从而为想象力所形构的这些影像,充分获致当前的怀疑态度之自愿搁置,这便形成了诗意的信仰(poetic faith)。另一方面,华兹华斯先生的创作目标是:从习焉不察的昏慵中,以唤醒心灵的注意力,并将这心灵的注意力导向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之美好与惊羡,从而给与日常的事物一种新奇的迷人魅力,并激起一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情思。(注八)
以上我花了许多笔墨去叙述诗人华兹华斯与诗人柯尔律治两人灵性上交往的水乳交融,正因为这种无间的相契,与彼此之间定下了高远的目标,再加上他们不懈地对这个高远的目标的忠诚的坚持与不断的奋斗,(他们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文艺界接受的,正相反,开始的那几年却招来无数严厉的批评!)英国诗歌才能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相对去看,我们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去对照徐志摩与林徽因,他们二人,从1920年11月19日相遇相识,到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9日空难意外逝世这十一年,真是令人嘘唏不已,感慨万千!我确信,徐志摩会走上文学创作之途,一开始是因为认识林徽因的缘故,也正因为他们深陷情网,得尝自由恋爱初恋的甜美,才导致徐志摩“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注九),也就是说,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推断,当时未满十七岁的林徽因,是由徐志摩的引导而进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的,剑桥的如诗一般的自然风光,百年多前的剑桥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当然还有拜伦、但尼生Alfred Tennyson等)歌咏自然的浪漫派美妙抒情诗歌,很自然地便成为徐志摩林徽因这两位中国年青人的模楷。只要大家细心去读徐林的诗作,不难看出他们都深受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影响。我相信他们相交的第一年,对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肯定花了很大的功夫去作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两人在这个研探的过程中,肯定地产生了不少热切的讨论与精神上的灵质的契合。(注十)(我习惯于把那些出现在他们两位的诗歌与散文中的共同用语,叫做“康桥原话”
。这几个月来,我持续地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了解上,渐渐地,我已比几年前写《谁是人间的四月天》一文时,对这些用语,似乎更能妥善地掌握其根本意旨!)我也确信,当年他们雄心勃勃,确曾许下深愿,信誓旦旦地要去创造中国未来的浪漫派,并且约定日后要出版诗歌的合集,正如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一样。然而,这一切,竟都因为林徽因在1921年年底回国后整个变了样!假如1923年春天,林徽因接受了徐志摩,一起回到剑桥进修,我确信,不需三四年,中国的浪漫派诗歌必将会开创出完全的另一番风貌!我也不明白徐志摩怎么知道林徽因拥有惊人的诗才?他不会看错人?就像他后来看错了陆小曼一样?显然地,林徽因的才华是天生的,而很多所谓的“才女”,却只不过就是父母花很多金钱时间大力“栽培”出来的,也许陆小曼就是这一类的吧!很可惜,中国的浪漫派实际上就只是徐志摩一个人在孤军奋斗而已,影响了方令孺、方玮德和陈梦家几位诗人,1931年林徽因加入,但不到一年,徐志摩就离开了人世。尽管林徽因在徐志摩死后仍然继续努力,但是浪漫派诗歌在中国的命运,却无法跟英国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所开创的浪漫派相比,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空前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密切相交的十一年,是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然而,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中国诗人从相遇相识一直到徐志摩逝世的十一年间,却只有1921年和1931年,这一头一尾的两年,他们确曾齐心合力地为中国浪漫派诗歌创作而奋斗。我常想,假如他们在这整整十一年里,能为中国浪漫派诗歌倾注他们全部心力的话,那么,浪漫派诗歌在中国的后徐志摩时代肯定会有一完全不同的发展!然而,命也乎?也许是。人为乎?也可能。捧读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诗人的诗歌,我读出了他们对诗歌创作的真诚(对他们二人来说,诗歌创作是神圣的!),我也读出了他们的悲伤(两位“今之伤心人”
!)。但最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诗人的非凡的诗才,竟因为个人的际遇而没能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陆小曼的存在可以说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噩梦,林徽因选择了建筑专业,再加上肺结核病的长期折磨,都对她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有一定负面的影响,就是这样,中国的浪漫派诗歌在神州大陆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徐志摩的去世后,竟难有后继者!但是,1931年之后,林徽因还是坚持着,继续写,继续为当年的承诺而戮力以赴,人们可能不明白一个建筑学教授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家里的客厅持续地举办文学座谈,不断地奖掖提携新人,假如不是当年她和徐志摩曾立下盟誓,我想,她大概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她一直坚持到1937年倭寇入侵中国被迫离开当时的北平才停止!从这一点去看,林徽因只能算是在感情上背弃了徐志摩,从写诗这一面来说,她却一直坚持写到1948年。所以,我不认为林徽因是一个背弃诺言的人。至于感情方面,试想想,一个十七岁多一点的女孩子,在那样一个久远守旧的年代里,我们竟要求她承受那巨大无比的社会压力,让她去做一个导致别人家庭婚姻破裂而离婚的“第三者”,这难道是人道的吗?更何况,尽管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是无可置疑地真诚的,纯洁的,但是,徐志摩本人在言语上、行为上,总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风流文人,并且,他似乎总喜欢在异性面前展示出他那种游戏人间和到处留情的不羁言行,这也许就是林徽因后来不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此,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隐藏着的严厉指控,我们就当作是诗人的“不平则鸣”也就可以了。
最后,我愿意提出三点来结束这篇文章。第一点是,梁从诫先生在他的《悠忽人间四月天》一文中说:“她(指林徽因)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事实上,“新月”并不是一个诗歌的流派,只是一群诗歌爱好者的团体,他们对诗歌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尤其对现代诗歌在格律与押韵等问题上,然而,这个团体中的各人,在诗歌创作的风格上却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还不算少,只有徐志摩与林徽因,和几位直接受到徐志摩影响的年青诗人,他们有一共同的风格,大体上是以歌颂自然和抒发个人的感怀为主。但是,徐志摩与林徽因则是紧密地遵从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理论去创作他们的诗歌的,他们的许多好诗,都是依从“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与“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情感”这两条主线去创作的,尤其是林徽因,常常在当前的一片静中,通过回忆、沉思、想象力,便能回到时空睽隔的剑桥去,这是英国浪漫派尤其是华兹华斯的诗歌的特色之一。所以,应该称徐志摩与林徽因的诗为浪漫派诗歌。有些人误解浪漫派一定擅长写“情诗”,到现在,徐志摩还是这样被误解!华兹华斯的诗歌里便极少“情诗”,徐志摩深受他的影响,他的诗歌,大多以歌咏自然,写自己的感怀,写普通的人物,写儿童等主题为主,林徽因也一样。因此,我也不赞成把徐志摩和林徽因归到“新月派”,他们应该是浪漫派!第二点是,梁从诫先生在他的《悠忽人间四月天》同一文里,引述林徽因本人的话如此说:“
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的人。”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浪漫”、“情绪”与“想象”
等专门术语,依据英国浪漫派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与实践,客观世界中景色与人物透过诗歌的描写,是与诗人的想象力紧密相关联的,这些景色与人物,是经过诗人在宁静中的沉思回忆过程中而产生出来的意象和情绪,但是这些意象与情绪,却必须忠实于客观景色与人物。所以,徐志摩爱的仍是真正的林徽因。林徽因的这一番话,很可能只是引导我们回归到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去落实她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着的林徽因与诗人所想象的林徽因是无二无别的!第三点是,很多人对徐志摩的诗歌真正的价值还不能提升到文学与文学史的高度去衡量,他那四本诗集的创作实践与尝试,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言,绝对是开创性的。如果大家能够好好地去了解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与诗歌理论,加上英国浪漫派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但尼生、布朗宁等大诗人的诗歌风格,就能了解到徐志摩从他们那里吸收了许多诗歌创作的要领,并且技巧地应用到中文现代诗歌的创作上,进而开创了我国现代诗的全新风格。虽然,有一些是不成功的,但是很多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只可惜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客观地去认识罢了!事实上,要真正客观如实地了解一首诗也不容易,更不要说对一位一流的大诗人的全面了解了。我便以这三点结束本文的论述。最后,我愿意引用诗人林徽因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诗名是《记忆》,写于1936年2月,距离徐志摩的逝世已五年多,距离她到剑桥访问已经整整十五年。诗上说:
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
夜,带着一天的星。
记忆的梗上,谁不有
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
无名的展开
野荷的香馥,
每一瓣静处的月明。
湖上风吹过,头发乱了,或是
水面皱起象鱼鳞的锦。
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
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
不着痕迹,谁都
认识那图画,
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廖钟庆写于诗人徐志摩先生75周年逝世纪念日,时惟2006年11月19日。
注释:
注一:参阅A. S. Byatt 的Unruly Times –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in Their Time一书p.20。
注二: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于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此见于徐志摩本人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与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时间是1920年11月17日后一两天,此见于林徽因为“康桥日记”之争夺而写给胡适的长信中,该信写于1932年元旦。林徽因的原信如下:
(九) 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指凌叔华)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天。
(十)十二月十四日(星一)
half a book with 128 pages received (dated from Nov. 17, 1920 ended with sentence "it was badly planned.")叔华送到我家来,我不在家,她留了一个note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徐志摩逝世于1931年11月19日。故此,两人的相识整整十一年,而非十年。林徽因在1931年12月所写的《悼志摩》一文作“十年”,显误。也许她太伤心了。也可能有别的用意。
注三:抑扬格,亦称轻重格(iambus),是最常见的一种格式,此即每个音步由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构成。我们以华兹华斯之前一点的前浪漫派苏格兰诗人Robert Burns (1759 - 1796) 的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一诗的第二节为例来说明,如下:
As fair / art thou, / my bon/ny lass,
So deep / in luve / am I ;
And I / will luve / thee still, /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 gang dry.
注;art是are, luve是love, bonny是beautiful, a´是all, gang是go的意思。
上面的例子是抑扬四步格与抑扬三步格交叉,可标示为:
︶-/︶-/︶-/︶-
︶-/︶-/︶-
︶-/︶-/︶-/︶-
︶-/︶-/︶-
读作:
da DUM/da DUM/da DUM/da DUM
da DUM/da DUM/da DUM
da DUM/da DUM/da DUM/da DUM
da DUM/da DUM/da DUM
全诗与中译如下:
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My luve like the melody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y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ugh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一朵红红的玫瑰》
罗伯特.彭斯
啊!我爱人象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苞放;
啊,我爱人象一支乐曲,
乐声美妙、悠扬。
你那么美,漂亮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直到四海涸竭,亲爱的,
直到太阳把岩石消熔!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只要生命无穷。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再见吧,小别片刻!
我会回来的,我的爱人,
即使万里相隔!
注四:Lyrical Ballads, Edited by Michael Mason, Longman,
1992, p. 82.
“feelings”与“emotion”,在徐志摩与林徽因谈论及写诗的文章中都说成是“情绪”,现在较普遍的译法是“情感”。我认为应该译作“情思”,因为这两个概念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论的文章中主要是审美的美学的概念,而非心理学的概念,并且,它引发自心灵的回忆能力与观照能力(或叫做沉思能力),这跟想像能力有关。F. E. Halliday 在他的Wordsworth and his world一书P.65里对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谈论到“feelings”与“emotion”时有下面的简明综述,他说:
The true poet, he maintained, is not only a man of exceptional sensitivity, but also one who thinks long and deeply, so that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of a secondary emotion induced by recoll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in tranquility of the original stimulus. (We get a glimpse of this creative process in Dorothy´s note: ‘William kindled, and began to write the poem.’ His aim was to communicate a comparable emotion to his readers; by the imaginative use of ‘a selection of language really used by men’, to make them feel the wonder
and beauty, the strangeness, in the objects and incidents of ordinary life.)
徐志摩与林徽因诗歌创作的历程完全紧守着华兹华斯这个创作历程。他们不属于一般所言的“新月派”,而是浪漫派。
注五:徐志摩也许是怕日后没有人能读得懂他这首《再别康桥》讲到云彩与虹的关联(因为这两个意象在这首诗中隔得还挺远的),所以,他就在第二年的年头,也就是1929年3月写了另外一首诗,在那首诗中,云彩与虹就靠得很近了。那首诗的诗名是:《拜献》。此外,也可以参阅华兹华斯的《我的心跳荡》(My heart leaps up),这首诗也影响了徐志摩一首诗的诗题《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般对这首诗讨论最多的是“儿童乃成人的父亲”,因为华兹华斯在他的许多诗歌里都贯穿着“终生保持儿童时期对自然的感通与体悟”这一理念,但我更重视这首诗里的“彩虹”,它是作为一个盟誓的“标记”而存在,盟誓,一方面是对自然而发,另一方面也对自己而发!
My heart leaps up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我的心跳荡》
我的心跳荡每当我看见
天上的彩虹。
年幼时候我是这样;
现在成人后我还是这样;
但愿年老时我依然这样;
要不就让我死亡!
儿童乃成人的父亲;
我希望这种天赋的虔诚崇敬
贯穿我的一生。
注六:参考徐志摩在1928年年初发表的那首悲伤的《我不知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注七:William K. Wimsatt Jr. 与Cleanth Brooks 合著的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Univ. of Chicago,1983(原著写成于1957年)一书在第十六章与第十八章这两章中分别详细地讨论了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歌理论中的“诗歌辞藻”与“想象力”,值得参考。
注八:Biographia Literaria,1817,Chapter 14, From English Literature Anthology for Chinese Students by John J. Deeney, Yen Yuan-shu, Chi Ch´iu-lang and Tien Wei-hsin, Taipei, 1975, Vol. II, pp.152 - 153.
注九:见《猛虎集序》。
注十:林徽因在1936年2月26日写给沈从文先生的信上说:“我方才所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 -
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感情全觉得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闻,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林徽因这一封信的内容,对了解她与徐志摩认识的第一年那种水乳交融的契合,以及对了解林徽因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
后记:我在写这篇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一诗的诠释文章的时候,常常情不自已地怀念我的一位学问上的好朋友。林士琛兄是台湾宜兰县五结乡孝威村人,善玄谈,有高致,精古典与现代中国文学。他是我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同窗兼室友,我们经常热切地谈论哲学与文学,现代诗也为我们当年所热爱。我们曾广泛地阅读与热烈地讨论以及深入地探究现代诗,其实这些主要都是由他建议与引发的,不然,恐怕我还停留在中学时期对现代诗的感性认识的初始阶段。士琛兄不幸于今年8月车祸逝世,让我顿感生命之无常!假如我在大学时期不是因为认识他,我想也许我永不会写任何现代诗歌的评论文章!又假如这篇文章真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我想士琛兄的建议与引发之功是最值得提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也特别用来悼念我这位亡友,愿他在天之灵永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