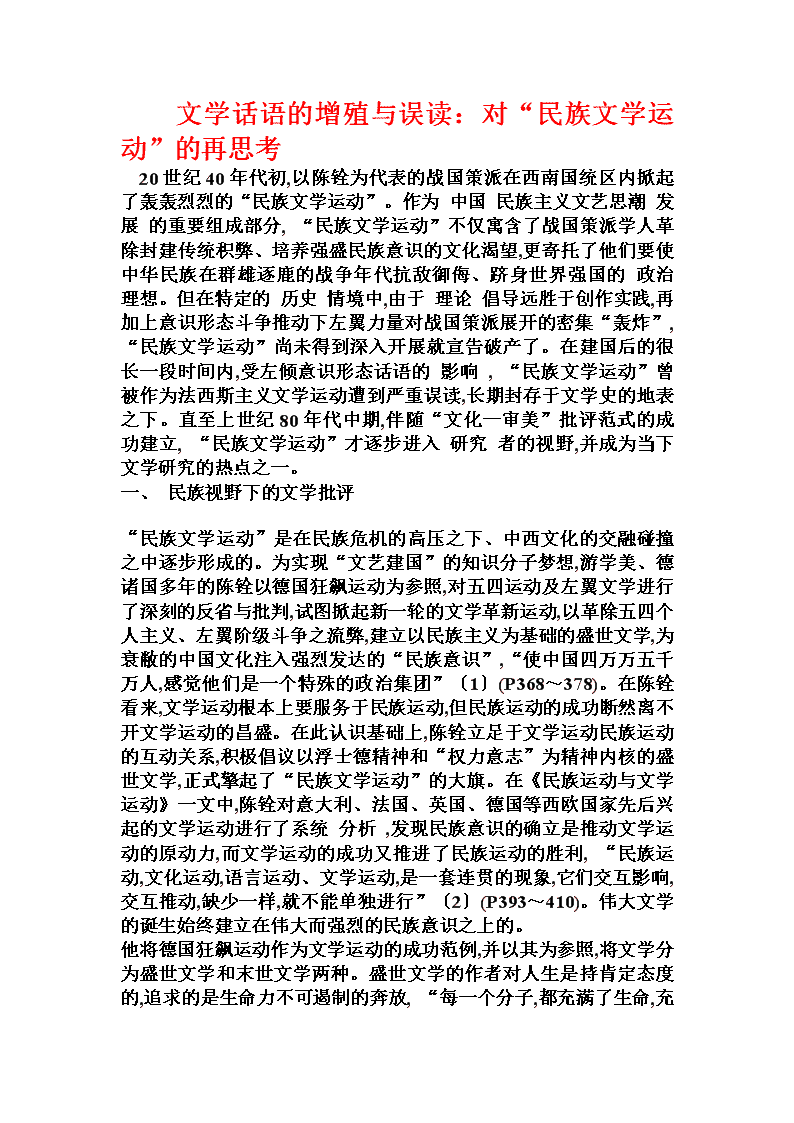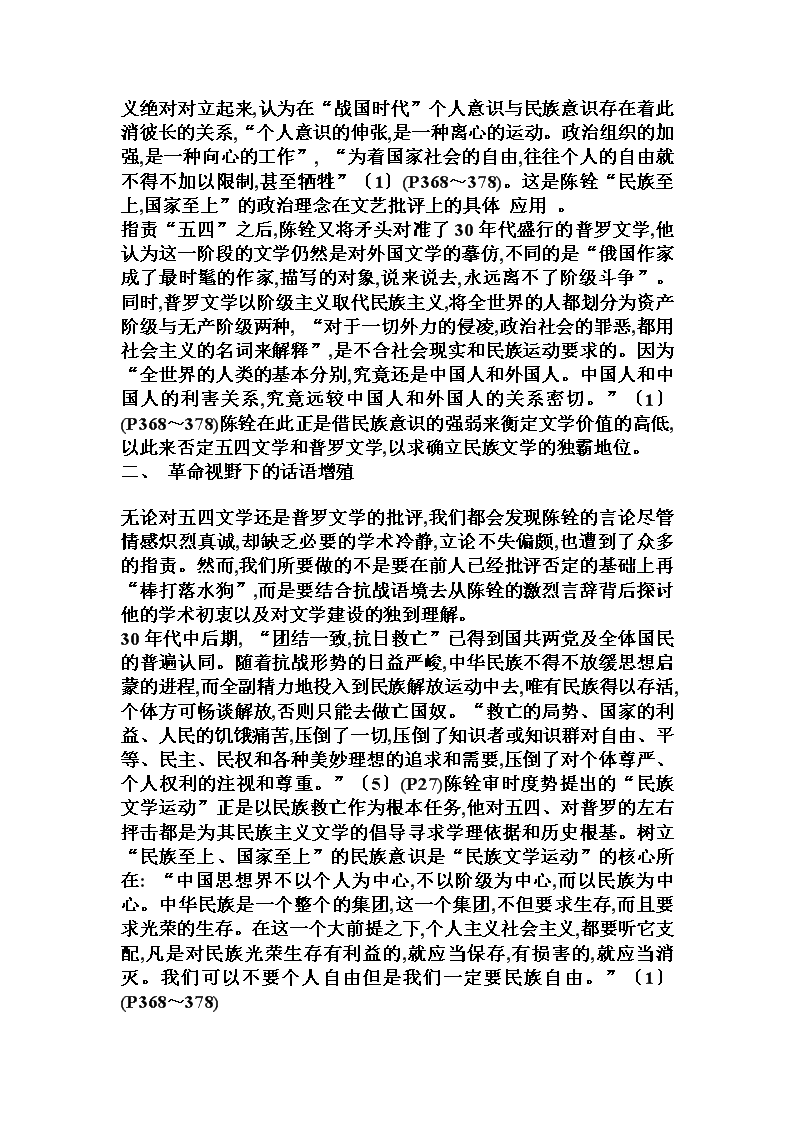- 55.50 KB
- 2022-09-2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20世纪40年代初,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在西南国统区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文学运动”。作为中国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运动”不仅寓含了战国策派学人革除封建传统积弊、培养强盛民族意识的文化渴望,更寄托了他们要使中华民族在群雄逐鹿的战争年代抗敌御侮、跻身世界强国的政治理想。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由于理论倡导远胜于创作实践,再加上意识形态斗争推动下左翼力量对战国策派展开的密集“轰炸”,“民族文学运动”尚未得到深入开展就宣告破产了。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左倾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民族文学运动”曾被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运动遭到严重误读,长期封存于文学史的地表之下。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文化—审美”批评范式的成功建立,“民族文学运动”才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民族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民族文学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的高压之下、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中逐步形成的。为实现“文艺建国”的知识分子梦想,游学美、德诸国多年的陈铨以德国狂飙运动为参照,对五四运动及左翼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试图掀起新一轮的文学革新运动,以革除五四个人主义、左翼阶级斗争之流弊,建立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盛世文学,为衰敝的中国文化注入强烈发达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1〕(P368~378)。在陈铨看来,文学运动根本上要服务于民族运动,但民族运动的成功断然离不开文学运动的昌盛。在此认识基础上,陈铨立足于文学运动民族运动的互动关系,积极倡议以浮士德精神和“权力意志”为精神内核的盛世文学,正式擎起了“民族文学运动”的大旗。在《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一文中,陈铨对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先后兴起的文学运动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民族意识的确立是推动文学运动的原动力,而文学运动的成功又推进了民族运动的胜利,“民族运动,文化运动,语言运动、文学运动,是一套连贯的现象,它们交互影响,交互推动,缺少一样,就不能单独进行”〔2〕(P393~410)。伟大文学的诞生始终建立在伟大而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上的。他将德国狂飙运动作为文学运动的成功范例,并以其为参照,将文学分为盛世文学和末世文学两种。盛世文学的作者对人生是持肯定态度的,追求的是生命力不可遏制的奔放,“\n每一个分子,都充满了生命,充满了野心,他整个身心都投放在不断的活动”〔3〕(P412~416)。而末世文学的作者则对人生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生活在他们是沉闷的,无聊的,怎样看透一切,享受一切,玩弄一切,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他们著作的流行,只能摧毁民族生命的力量,使一个时代有用的天才悲哀颓废,政治军事社会道德,腐化崩溃,终陷于不可收拾之境。”〔3〕(P412~416)盛世文学的代表就是德国狂飙运动,它以浮士德精神作为理论旗帜和时代象征,拥有炽热激烈的情感冲动、对世界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执着追求以及为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不惜一切代价的无畏勇气和坚强意志。而末世文学的杰作则是堪称中国传统文学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坚定不移的意志、激荡汹涌的情感、充盈张扬的生命、僭越陈规的极端叛逆等等这些盛世文学的精神标志,在《红楼梦》中都荡然无存。因此,作为民族意识异常低迷的时代符号,《红楼梦》成了一个时代走向没落、一种文化走向衰亡的标志。在以浮士德精神为标尺抨击传统文学之余,陈铨又对五四文学、普罗文学的罪状逐一进行清算。他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运动划为三个阶段:20年代前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五四文学;30年代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普罗文学;四十年代,也就是陈铨倡导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文学。在陈铨看来,无论五四文学还是普罗文学,“其文学都是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不是谈个人伤感就是讲阶级斗争,缺少真正的民族意识,唯独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才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强烈的民族意识”〔1〕(P368~378)。尽管他承认五四运动同狂飙运动一样为整个民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的提倡上卓有贡献,但又认为五四运动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注入生机勃勃的生命气息,更没有推动中国民族运动的勃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狂飙运动是感情的,是民族的,是战争的,所以能使德意志民族生气蓬勃斗志昂扬;而五四运动却背道而驰,是理智的,是个人的、是和平的。而在“战国时代”的政治潮流中,民族自由、集体主义是第一位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必须服从民族利益,科学与理智必须让位于饱满甚或狂热的民族情感与战斗意志,“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然就同归于尽”〔4〕(P341~348)。然而五四先驱对“战国时代”的来临却浑然不觉,在创作上一味摹仿西洋文,“诗歌学习美国的自由诗,戏剧尊崇易卜生的问题剧”,在思想上个人主义“变态发达”,“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都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社会问题,也站在个人立场上来衡量一切”,最终将中国推入了“意志沉沉”“精神涣散”\n的彷徨歧路〔1〕(P368~378)。陈铨对五四运动及五四文学的尖锐批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他主观的将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在“战国时代”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个人意识的伸张,是一种离心的运动。政治组织的加强,是一种向心的工作”,“为着国家社会的自由,往往个人的自由就不得不加以限制,甚至牺牲”〔1〕(P368~378)。这是陈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在文艺批评上的具体应用。指责“五四”之后,陈铨又将矛头对准了30年代盛行的普罗文学,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仍然是对外国文学的摹仿,不同的是“俄国作家成了最时髦的作家,描写的对象,说来说去,永远离不了阶级斗争”。同时,普罗文学以阶级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将全世界的人都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对于一切外力的侵凌,政治社会的罪恶,都用社会主义的名词来解释”,是不合社会现实和民族运动要求的。因为“全世界的人类的基本分别,究竟还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利害关系,究竟远较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密切。”〔1〕(P368~378)陈铨在此正是借民族意识的强弱来衡定文学价值的高低,以此来否定五四文学和普罗文学,以求确立民族文学的独霸地位。二、革命视野下的话语增殖无论对五四文学还是普罗文学的批评,我们都会发现陈铨的言论尽管情感炽烈真诚,却缺乏必要的学术冷静,立论不失偏颇,也遭到了众多的指责。然而,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在前人已经批评否定的基础上再“棒打落水狗”,而是要结合抗战语境去从陈铨的激烈言辞背后探讨他的学术初衷以及对文学建设的独到理解。30年代中后期,“团结一致,抗日救亡”已得到国共两党及全体国民的普遍认同。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华民族不得不放缓思想启蒙的进程,而全副精力地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唯有民族得以存活,个体方可畅谈解放,否则只能去做亡国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5〕(P27)陈铨审时度势提出的“民族文学运动”正是以民族救亡作为根本任务,他对五四、对普罗的左右抨击都是为其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寻求学理依据和历史根基。树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运动”的核心所在:“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1〕(P368~378)\n值得深思的是,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民族文学运动”刚刚出笼就遭左翼的彻底否定。戈矛于1942年6月在《新华日报》上著文《什么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认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味追求民族主义,不仅否定了五四新文艺运动,也否定了当下的抗战文艺,是对希特勒“奋斗哲学”的演绎,“它的基本精神,当是‘力’和希特勒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于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6〕(P220~225)。《解放日报》也发表《“民族文学”与法西斯谬论》的文章,称陈铨的民族文学“挽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毒药”,是“卑劣恶毒的暗箭”,它对五四运动的反对就是对人民民主运动的极尽侮蔑。左翼对“民族文学运动”的高度警觉、极端憎恶,从侧面反映出“民族主义”在特定语境下的复杂与暧昧。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民族主义仍是一个能够有效整合意识形态分歧的概念。30年代末,因中日战争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促成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高涨。无论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团体,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自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文人都在民族主义这面大旗下达成了一致,“他们都强调要取消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地融入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更大的单位中去,使个人的利益服从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7〕(P270)乍一看来,“民族文学运动”的出场可谓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张汝沦所说:“文字有其独立性,一旦产生后就不属于个人,而有在不同语境下增殖的无限可能性。”〔8〕(P4)陈铨对“民族主义文学”在政治语境之下的增殖效应是始料不及的。他原本希望以民族意识为粘合剂,使得举国一致、共赴国难,减少因党派争斗、阶级对抗所引起的国力消耗。但是,这一主张在形式上却为国民党排除异已、一党专制提供了理论援助,并与其文艺政策实现了某种契合。1942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在其党刊《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将“国族至上”规定为“文艺所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共济,不需要仇恨,需要生产,初期的普罗文学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挑拨阶级的仇恨,鼓励阶级的斗争”,“提倡阶级意识的结果,便是阶级斗争,然阶级斗争用之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许有效,但用之我们这种无大资本农而只有大贫小贫的中国绝对不必。”〔9〕(P281~288)国民党的民族文艺政策有着明确的“一箭双雕”的政治策略: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来夺取民族文艺的领导权,为其政党统治的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铺平道路;以民族主义来攻击普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基础、党治思想上否定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由此看来,“民族文学运动”被左翼视作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反动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面对“民族文学运动”\n在政治效应上的错位与偏移,停留于学术理念层面的战国策派早已无力控制。本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战国策派最终被卷入意识形态的争斗决非历史偶然。限于知识分子的视界,战国策派没有充分预料到“民族文学运动”会引发如此巨大的政治漩涡,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主义在抗战语境中凸现出的含混性、繁复性。专注于学理探讨而对社会功效极端漠视恰好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幼稚和单纯。尽管从学理角度来看,在民族危难之际,建立一个强大的军政统一体,以民族意识为内核凝聚全体国民的战斗意志,确保战争的最后胜利,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民族文学运动”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却满足了国民党借民族主义限制、消融、打击共产党,实现独裁专制的政治需求,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以民族文学建设、民族意识培植为已任的“民族文学运动”最终在政治语境中被左翼视作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而围剿棒杀,成为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民族主义话语无非是某种权力的语言载体而已,而民族主义则是争夺社会资源的方式。”〔10〕(P19)国共双方都希望通过这场民族主义文艺论战巩固并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防线,以文学话语的强势扩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使文艺直接而迅速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有效地转化为革命运动的内动力。在此动机下,“民族文学运动”由普通的文艺主张迅速演化为以党派政治为背景的话语征伐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以政治规范来权衡艺术得失的文学批评模式早已被当今学界所批判。但文学文本在特定时代语境下所生发的社会功效、特别是在政治层面所引发的增殖效应以及相应的误读,往往是文学创作者甚至文学批评者难以预设和控制的,也是当下文学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幸运的是,“民族文学运动”在现代文学史的浮现恰好为我们研究探讨文学话语的增殖及误读效应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标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