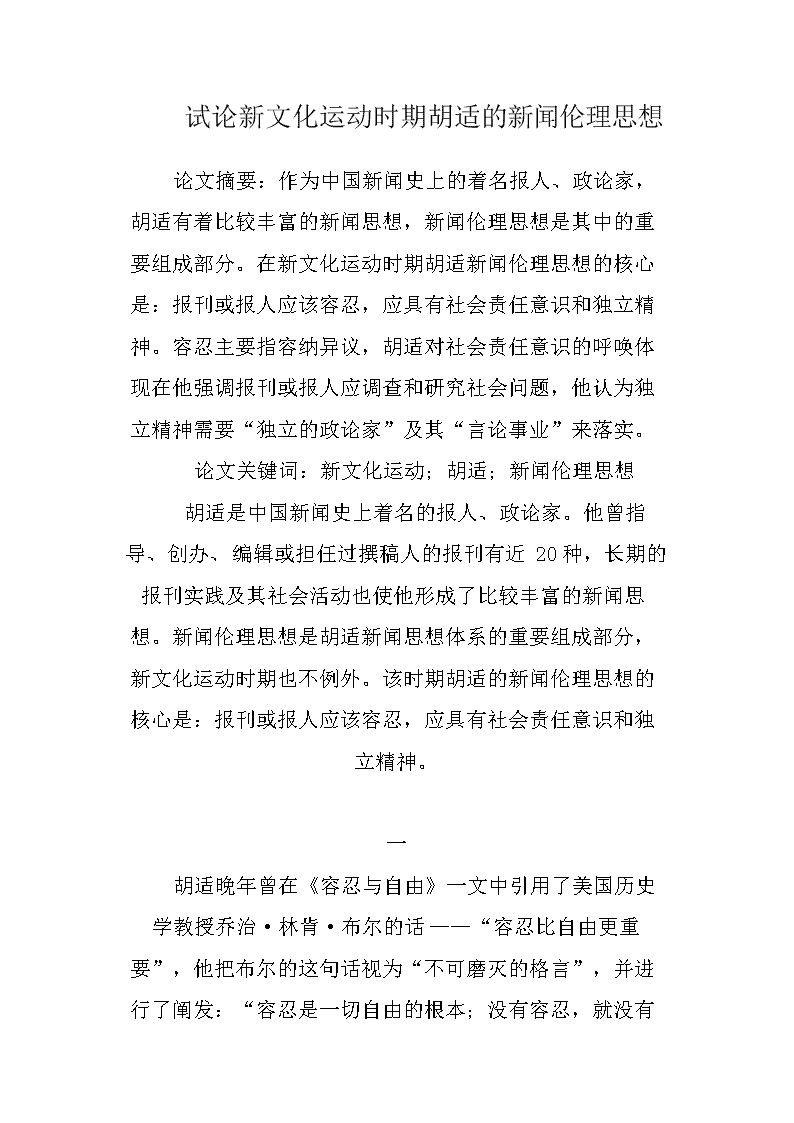- 62.50 KB
- 2022-09-27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试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着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论文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中国新闻史上着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指导、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近20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一 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n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1917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n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心理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n‘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年》”\n。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触及到了新闻伦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传播的“公正”或“公平”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平的传播。 二\n 社会责任意识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道德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400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中国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的军国民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n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n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新闻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社会责任,研究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n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调查,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传播“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也发出了赞叹:“《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n 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希望人民“\n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1922年6月4日《努力周报》第5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政治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政党所羁绊,在表达意见时才不会为一党私利所障目,也才有可能不会被误认为某个政党的喉舌。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政治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n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n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新闻传播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四 胡适所倡导的容忍、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n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市场”,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伦理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n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指导的报刊有近20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