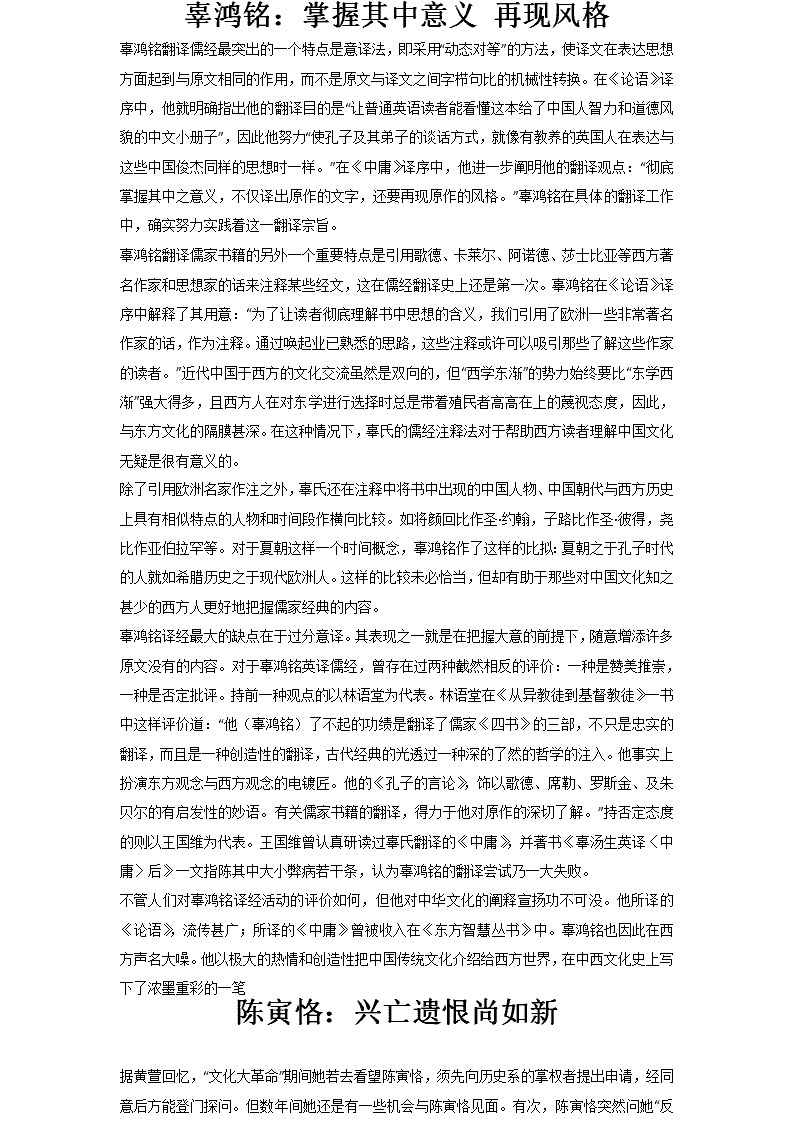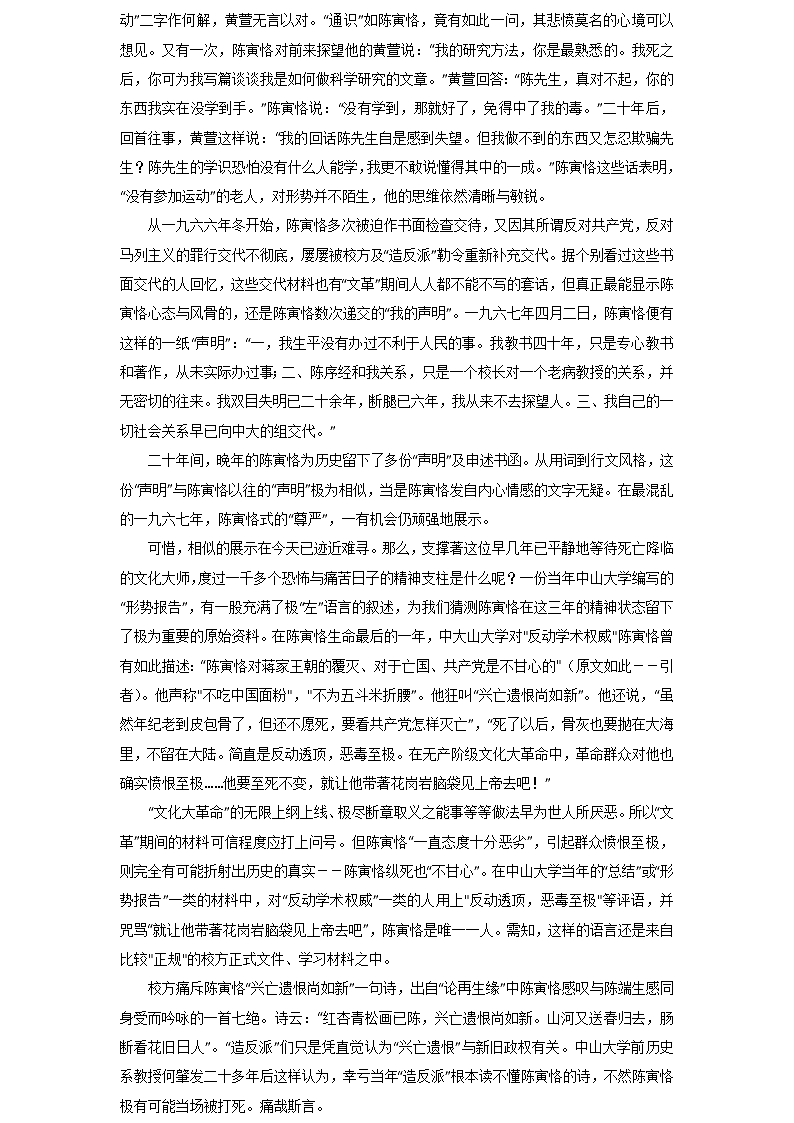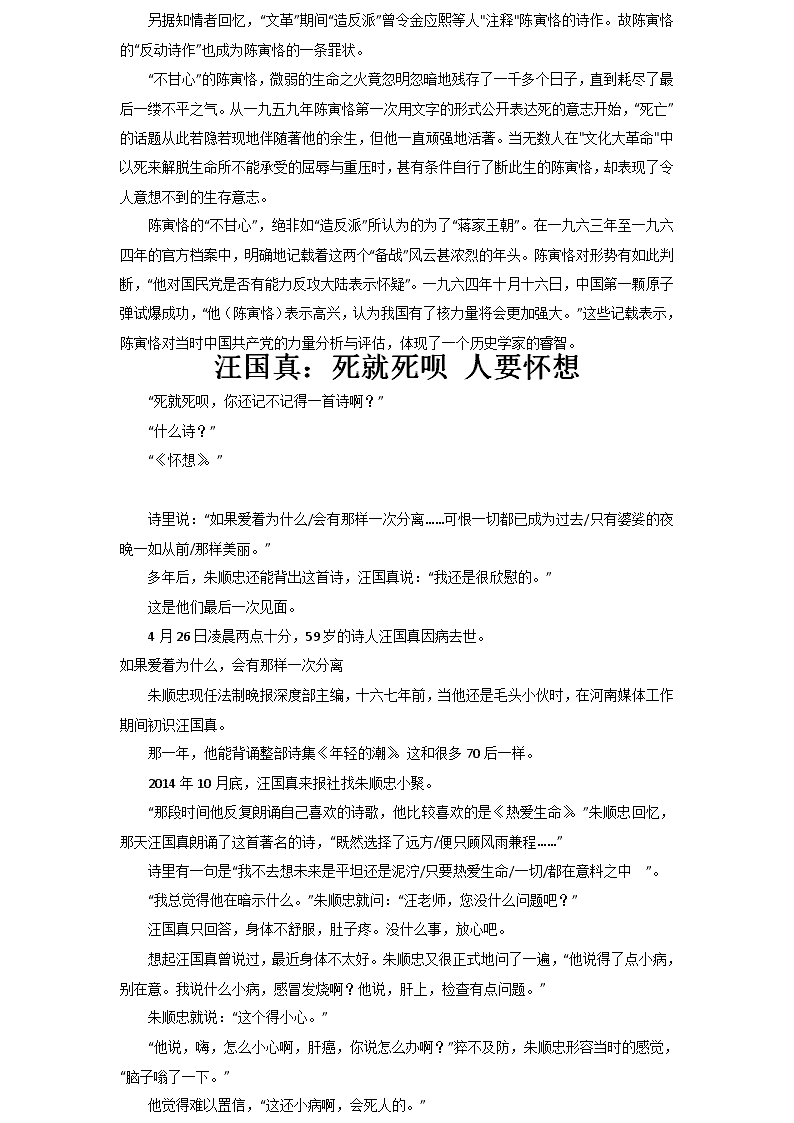- 49.00 KB
- 2021-05-13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辜鸿铭:掌握其中意义 再现风格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著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股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大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据知情者回忆,“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令金应熙等人"注释"陈寅恪的诗作。故陈寅恪的“反动诗作”也成为陈寅恪的一条罪状。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一九五九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著。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
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示,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汪国真:死就死呗 人要怀想
“死就死呗,你还记不记得一首诗啊?”
“什么诗?”
“《怀想》。”
诗里说:“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可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只有婆娑的夜晚一如从前/那样美丽。”
多年后,朱顺忠还能背出这首诗,汪国真说:“我还是很欣慰的。”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4月26日凌晨两点十分,59岁的诗人汪国真因病去世。
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朱顺忠现任法制晚报深度部主编,十六七年前,当他还是毛头小伙时,在河南媒体工作期间初识汪国真。
那一年,他能背诵整部诗集《年轻的潮》。这和很多70后一样。
2014年10月底,汪国真来报社找朱顺忠小聚。
“那段时间他反复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他比较喜欢的是《热爱生命》。”朱顺忠回忆,那天汪国真朗诵了这首著名的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诗里有一句是“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
“我总觉得他在暗示什么。”朱顺忠就问:“汪老师,您没什么问题吧?”
汪国真只回答,身体不舒服,肚子疼。没什么事,放心吧。
想起汪国真曾说过,最近身体不太好。朱顺忠又很正式地问了一遍,“他说得了点小病,别在意。我说什么小病,感冒发烧啊?他说,肝上,检查有点问题。”
朱顺忠就说:“这个得小心。”
“他说,嗨,怎么小心啊,肝癌,你说怎么办啊?”猝不及防,朱顺忠形容当时的感觉,“脑子嗡了一下。”
他觉得难以置信,“这还小病啊,会死人的。”
汪国真说:“那死就死呗,你还记不记得一首诗啊?”
汪国真提到的这首诗,就是《怀想》。这并不是一首像《热爱生命》一样出名的诗歌,朱顺忠当即完完整整朗诵了一遍。
这原本是一首写分手的诗,有着追忆似水年华的失落。那时却像是与生命分手。
就是这次见面,汪国真第一次告诉这个忘年好友自己的病情。
尽管朱顺忠感到难以接受,但汪国真的态度很从容,那么轻松地 说着“肝癌”两个字。
当天晚上,朱顺忠给汪国真发了一条短信,是汪国真自己的诗歌——《只要彼此爱过一次》。
诗里说:“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
汪国真回复了一个省略号。
这首诗是为了鼓励他,给他信心。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前他们曾频繁往来。“据我所知,去世前,除了亲属和工作室的人,他没有再见任何朋友,可能是想给大家留个‘背影’吧。不是有那句诗吗——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温文尔雅的一句脏话:我操妈的
武云溥曾是新京报的文化记者,2007年第一次采访汪国真之后,多年来一直有往来。
“淡淡的忧伤,励志的、奋进的,积极向上,有点像现在的心灵鸡汤。”经过80年代带着毁灭气息的北岛、海子等带来的理想主义,汪国真成为了90年代的心灵导师。
“他从不批判现实,只告诉人们要向着远方。”有人质疑他的文学性,“但是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来说,能说出来的诗人除了他还有几个?” 武云溥是个80后,他说自己的中学时代就是读着汪国真走过的,女同学们都迷恋着诗集上那张温和的面孔。
武云溥说,采访汪国真的契机,是报社当时做一个专题,叫做“远去的偶像”。
那一年,他见到汪国真精神焕发,很和气,笑呵呵的。“这和我中学时的想象,和诗集上的照片给人的印象完全一致。”
武云溥觉得,此后多年,汪国真都是这样。
早在1993年后,汪国真就淡出诗坛,少有新作发表。此后多是书法、画画和作曲。
2007年的时候,汪国真的一副四尺整张书法作品,标价是一万八千块钱。
和武云溥相识后,汪国真有新的作品发布,都会叫武云溥去捧捧场。“这么多年过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没变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写着关于青春的诗。”
这和朱顺忠印象中的形象一致。
唯有这对忘年交的最后一通电话不同。
朱顺忠说,最后一次见面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话。2014年末至2015年年初,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成了汪国真特别关注的一件事。
“他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报道,每次打电话都问呼格案有什么进展。”朱顺忠说,汪国真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朱,呼格案件的那几个制造冤案的坏家伙抓了吗?他回答,还没有。很少说脏话的汪国真骂了一句:我操,妈的。
我们怀念的不是诗,怀念的是青春
就像武云溥说的,汪国真是一代人的偶像。
朱顺忠回忆起一些轶事。汪国真有一段时间抽烟很厉害,后来几乎戒掉了。
一次他们在一间咖啡馆聊天,邻桌一位女士正要点烟。汪国真非常礼貌地走过去问她:“您能别抽烟吗?”那位女士说:“这里是吸烟区。”
汪国真说自己对烟过敏。
过了一会,这位女士又走过来,问他是不是汪国真,看着很眼熟。
见到了青春时的偶像,女士请他签名。汪国真不仅签了名字,还即兴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位女士。大意就是劝她不要抽烟,有害健康。
“现在想想,不知道当时戒烟是不是因为生病。”朱顺忠说。
他回忆,汪国真私下里给朋友写了很多诗,都是当场即兴的新诗,他的书法作品虽然很贵,却从来没根朋友提过钱。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出席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还引用了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向世界重申中国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决心。
对此,汪国真对媒体说:“老实说,习主席能背下我的诗词,我觉得得挺欣慰的。”
不管是50后的习主席,还是70后的朱顺忠,亦或80后的武云溥,汪国真的诗都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影子。
作为曾经资深的文化记者,武云溥同意一种说法——不是有人说么,我们怀念的不是汪国真的诗,也不是汪国真这个人,我们怀念每个人自己的青春。
村上春树:美式与和风相结合
村上春树本身是个很好的、中短篇好过长篇的小说家,而且态度颇为严肃——可惜贴给他的标签,大多很是偏颇。明明写过《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那样的结构佳作、《奇鸟行状录》那样的反战抨击政治小说、青春四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舞舞舞》)那样的青春小说转型到反右翼和反思社会小说,以及一大堆精妙短篇,像1995年《奇鸟行状录》里,居然都涉及到诺门坎战役战后苏联战俘营日本右翼选举这些话题了,结果每每都挂上《挪威森林》和《1Q84》加上跑步书,好像这点东西就是他的代表作了似的。
村上春树的写作技巧,不算很日本。论到“和风”,则老一代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长他一辈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们,都比他风味浓郁,更有“这玩意一望而知是日本作品”的辨识度。相比于前辈日本作者,村上春树是个更美式的小说家。生活方式上,他读大学期间就筹谋爵士乐酒吧,29岁才出道写小说,又搞翻译,数十年如一日的跑步。他大学毕业晚到26岁,在短篇小说《出租车上的吸血鬼》里,他曾自嘲过“大学上了七年之久”。他和太太结了婚,贷款攒足了500万日元开酒吧,直到30岁关张。这段生活,在《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里都有描写。《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男主角干脆就是开爵士酒吧的。
这样一段很美式的生活,令到村上春树,至少是早期,对美式品味和美国作家甚为推重。实际上,如果要讨论他早年风格,很难脱开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和雷蒙德·卡佛这三个人。
村上春树在他作品里,不只一次提到菲茨杰拉德。《且听风吟》里,谈及他虚构的作家“哈特费尔德”时,就列了菲茨杰拉德与之比照。《挪威的森林》里,永泽和渡边这对男一号和男二号,就是通过菲茨杰拉德开始对话,言谈之间,直接把菲茨杰拉德封到了经典地位。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许多部分都可以看作对菲茨杰拉德的致敬,尤其末尾离开爵士酒吧,上长途车看海岸灯灭,“一切一去杳然,无人可捕获”,时光抛掷,茫然若失,其风味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处,尼克的海滩独白绝似。在《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前半段,村上春树总在呢喃着一个很菲茨杰拉德主题。菲茨杰拉德在告别他的少年时光,村上春树在告别他的海边故乡(《寻羊冒险记》里被填埋了的海、《1973年的弹子球》里的“宇宙飞船”号弹子球机)和“二十岁的年代”。
村上春树1979年写完《且听风吟》,1980年《1973年的弹子球》。如上所述,那时他风格清丽洗练,但已经隐约出现这些主题:“被过去时光吸噬进黑暗之中的往昔”。同时期的短篇,1981年《意大利面之年》、《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他更喜欢摆弄“个人情怀+回忆”的路数。
到1982年,他完成《下午最后的草坪》时,已经露出了一些“彼侧的阴暗”。那个小说里,他为某中年妇女除草,受邀去观看她女儿的房间:在端详这个“主人不存在”的房间时,笔触间渗透着阴森味道。1983年的《烧仓房》,他点到了这个主题:“那些被黑暗暴力吞噬掉的、不被注意的人”。也就是这年,《寻羊冒险记》出版。
村上春树后来说他喜欢雷蒙德·钱德勒。他说他读了十几遍钱德勒的名作《漫长的告别》。2006年亲自把这书译成日文了。实际上,对照村上春树的《舞舞舞》和《漫长的告别》,有个显而易见的细节。《舞舞舞》里主角被“渔夫”和“文学”俩警察带去讯问的经典黑色幽默段落,可以类比《漫长的告别》里,特里·伦诺克斯刚失踪时,俩警察闯到马洛家来敲门的情节——根本就是致敬段落。
《舞舞舞》和《漫长的告别》里的两位男二号,同样身处富贵,但同样对之厌倦不堪,喜欢没事来找主角喝酒发牢骚的五反田和特里·伦诺克斯,嗅来也不无相似
村上春树自己也说过,《1973年的弹子球》写完后,他有过选择。然后就是《寻羊冒险记》里。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可以推演为:他从菲茨杰拉德转向钱德勒。《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风格类似,清新、悒郁,略微有他后来招牌的“彼侧之空虚”的意境了,但大多还是在和流逝的时间对抗。而在《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主角开始行动起来,开始有类侦探小说的味道,各类村上春树式的想像力、黑色幽默和比喻也出来了。《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里的第一人称男主角,都不是个省油的灯:日常的冷硬幽默,到处溜达,与其他势力对抗,有碰撞,有斗智,类似细节,都像复制了一个钱德勒笔下的马洛侦探。
村上春树喜欢卡佛的事尽人皆知。“极简主义”也早被说成烂话题了。换个角度想:卡佛的小说里,一个有趣的特色:《大教堂》和《真跑了那么多英里吗》这两篇,都试图从现实开始,逐渐过渡入一个近于虚空的情境。《大教堂》结尾尤其如此,主角就坐观他人慢慢把现实感抽离掉,反客为主,进入一种虚空领域。卡佛在其唯一一篇描写父亲的小说里,也用过此手法:结尾处,大家都开始念“雷蒙德”这个父子通用的名字,死者彷佛荡漾在生者之重。这种玄空的、与死亡连接的彼侧世界,恰好是村上春树所喜爱的。
村上春树的小说里,真正参与到剧情中的人,基本都比他聪明。接话茬神神叨叨的姑娘个个都比他伶俐,不必再提。而他擅长描写“现实得令人恐惧的反派”,而且描写出他们的黑暗魅力。比如《寻羊冒险记》里的秘书,比如《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里的小个子,比如《舞舞舞》里的牧村拓,比如《奇鸟行状录》里的牛河。他们的作派,普遍有这种潜台词:
“喂喂,大家都是混口饭吃的,都是成年人了,何必拐弯抹角呢。我也不想刻意伪善,但就这样直接把事情说清楚比较好吧!”
如是,村上春树早期和中期的大多数小说,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个类似的故事:
一个“不合时宜”的,守旧的,怀念着早年故乡海滩风景和故友的,不喜欢大城市现实主义冷酷面貌的,性格独立的,爱耍冷幽默的主角。
一个黑暗的、现实的、狡猾的、庞大的、吞噬时光的、带有死亡阴影的、填海造陆把一切美好旧时代事物吃掉的、资本式的、暴力的,大家伙。
(《且听风吟》里的流逝时光和战争阴影,《1973年的弹子球》里的虚空时光和新别墅区,《寻羊冒险记》里的羊,《舞舞舞》里贯彻始终的死亡阴影,《奇鸟行状录》里的绵谷升及他身后剥皮鲍里斯的阴影,《海边的卡夫卡》里把中田强行变笨而且始终侵袭他身体的黑暗,都是这样的)
他擅长一两人之间的对话,很擅长气氛的描摹,所以他描写“正常世界过渡到彼侧世界的幽暗”时非常随心所欲。所以无论他的篇幅多么长,三人以上的对话其实很少。这也是后期他主角必须到处活动的原因:主角是书胆,得串起一切来。而且,他非常擅用比喻。他的比喻需要的不是精准,而是极强的画面感。所以他的小说有非常细碎亮丽的镜头感,“如空中所见西奈半岛般横无际涯的饥饿”,“静得像沉在湖底”,之类。
这个独善其身的、偶尔有小伤感但大体冷幽默的、怀旧美好抵制按部就班社会的、对政治和战争及庞大机器抱着反感的、偶尔卖萌玩象征的、想象力泛滥的家伙,在跟一个庞大呆滞黑暗的对手捉迷藏。在偏长的小说里,他经常被对手搞得很压抑;但短篇小说里,他就有机会得胜了。所以,他的短篇总是比长篇轻扬跳脱得多。
东野圭吾:打破单调
1958年2月,日本大阪生野区,东野圭吾出生。“我家里经营着一个生意萧条,卖钟表、眼镜、贵金属等饰物的小店。我是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我的户籍所在地写的是‘东区玉造’,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我自己没有在那里住过。父亲以‘这个地方说起来比较好听’为理由,就把我的户籍地安到了这里……”这段出生经历在他出版的唯一一本自传体随笔《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中有记述。
小时候的东野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会考虑去尝试和体验。比如看了本有趣的漫画,就会想着自己也来画一本。
东野圭吾有两个从小门门得五分的姐姐,他的父亲曾经是个军曹(日本独有的对中士级别士官的称呼)。
东野圭吾的两个姐姐后来一位做了空姐,另外一位成了老师,这两个身份在《杀人现场在云端》和《浪花少年侦探团》中有体现。
与读者脑海中幻想的畅销书作家生活不同,东野圭吾曾经租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用他的话来说:“上厕所要跑去屋外,屋里会有蜈蚣光顾。”
1974年,东野从大阪市立小路小学和市立东生野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同一座城市的府立阪南高等学校读高中。此前从未看过书的他才开始接触小说这一门类,于是他读到了一本以高中生为主角的推理小说,“觉得这样的小说实在有趣,……自己好象也可以写写看。”这成为他以后从事推理创作的最初契机。
之后,东野考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系电气工程专业,一度停止的小说阅读又恢复了,而且开始构思一些东西,不过那主要是想确认自己究竟能不能写小说而已,尚未有当个小说家的念想。
1981年,大学毕业后东野圭吾成了日本电装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在公司呆了两年左右,由于感觉上班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单调,所以很想给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来些不一样的……该说是刺激吧,……因为其他目标的实现可能需要花钱,或是需要购买些道具之类的,而小说则不同,只要有铅笔和纸,到哪里都能写。所以我就每天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写小说,并且将把写好的作品寄去参加江户川乱步奖当作目标,希望在工作之外,能有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支柱……虽然收入稳定,但我觉得自己的薪水太少了。所以想如果能够靠奖金,或是稿费收入来赚点外块,应该也不错。”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1983年东野终于以《人偶们的家》(人形たちの家)应征第29届乱步奖,可惜只进入了第二轮预选。
在酝酿第二部征文作期间,与来自某女子高中的非专职教师结婚。1984年,东野以《魔球》应征第30届乱步奖,这一次最终入围决选,离拿下大奖仅一步之遥。翌年(1985),终于凭借校园青春推理小说《放学后》摘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而正式出道。
东野以27岁的年轻年龄获得大奖,令其创作信心大增,加上获奖一事被所属公司知晓,边工作边写作的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遂毅然于1986年3月辞职奔赴东京,开始了自己职业作家的道路。
但此后的十年,东野圭吾的作品一直备受冷落,直到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出版畅销,东野圭吾才重新受到关注。
2011年11月21日,2011年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东野圭吾以48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5位,引发广泛关注。
创作历程
东野圭吾是一位尝试型作家,出道至今一直不断探索独特的小说风格,在吸收国内优秀作品养分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写实本格派”风格。在东野看来,没有什么元素不能被运用到推理小说中,因而他的小说表现出多领域的融合性,他解释道:“因为每一种领域都有长处,我想攫取这些不同的优点。”融合是循序渐进而非一蹦而就,从他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风格一点一滴的变化,按照小说主题和艺术手法的不同,东野圭吾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1990年创作的《宿命》和1997年创作的《名侦探的守则》和《名侦探的诅咒》为界。
前期
1985年至1990年,东野圭吾以校园本格推理为主,偏重设迷解谜和逻辑推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以描写犯罪手法为主,涉及传统本格小说中的密室、童谣、密码等元素,在小说艺术手法上有较多模仿的痕迹,主要以弗里曼经典模式“提出问题一一展示数据一一了解真相一一验证结局”的单线结构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放学后》、《毕业前杀人游戏》、《以眨眼干杯》、《十一字杀人游戏》等。《放学后》和《毕业前杀人游戏》将背景放置在校园中,刻画师生和同窗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以眨眼干杯》运用传统推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密室,并以拜金虚荣的陪酒女小田香子作为女主人公。《十一字杀人游戏》中共有十一人相继死去,他们的头颅均被重器所伤,且死前都会收到写着“来自无人岛的满满杀意”的纸条……这些情节常被用于传统推理小说中。同江户川乱步一样,东野这一时期的作品将“犯罪动机”归结为个人原因,或为了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或掩饰不为人知的过去。这一时期的作品偏重逻辑推理,内容单薄,将“意外性”固定在“凶手是谁”上,例如《放学后》全篇以师生矛盾为主,结局却以妻子为凶手,这样的布局给人刻意、突兀之感。作者在1986年出版的《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中说道:“我非常喜欢的设定就是密室和密码,这些所谓古典式的小道具让我着迷,纵使我会被一般读者认作落伍者,我将继续沉溺其中。”从重视本格元素到偏重逻辑推理再到个人宣言,东野圭吾的前期创作无疑是以本格推理为主。
中期
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宿命》,这篇小说被推理界认为是东野创作风格的分水岭。在《宿命》中作者讲到:“犯人制造了怎样华丽精彩的诡计,这样的谜团设定固然不错,但我更希望创作出其他类型的意外性。”东野不再拘泥于凶手和手法,所谓“其他类型的意外性”是指为什么,即“犯罪动机”,作者“寓谜团于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作者开始涉及社会问题,例如滥用权力和科学、虐童等。故事通常以凶杀案为起点意外牵引出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代表作有《宿命》、《回廊亭杀人事件》、《过去我死去的家》、《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等。在叙述模式上,作者一改前期简单的经典模式,尝试运用较为复杂的结构方式,例如《宿命》拥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和仓勇作的成长之路,一条是须贝正清的谋杀案。通过谋杀案件引出战后日本政府为培育间谍在人脑中安置金属以进行脑科学研究的故事,这项研究的被害者日野早苗是勇作和晃彦的亲生母亲,须贝正清正是想重新开启这项研究而遭到谋杀,这样的情节安排着实给人意外感。政府高层为一己之私轻视生命,给三代人带了了无法平复的悲惨记忆。小说将悲剧根源归结为滥用权力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目的。作者没有将重点放在案件上,而是深入剖析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有时甚至不涉及凶杀,例如《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它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营造悬念,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事,以“记忆”模糊或丧失为基点,将重点放置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以“关系”体现“人性”。
这一时期东野的小说具有“新社会派”的特点,一方面他关注社会和人性,另一方面在叙事技巧上不断创新,运用了独具风格的双线平行交叉式的结构方式,为“写实本格派”风格的产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性创作。